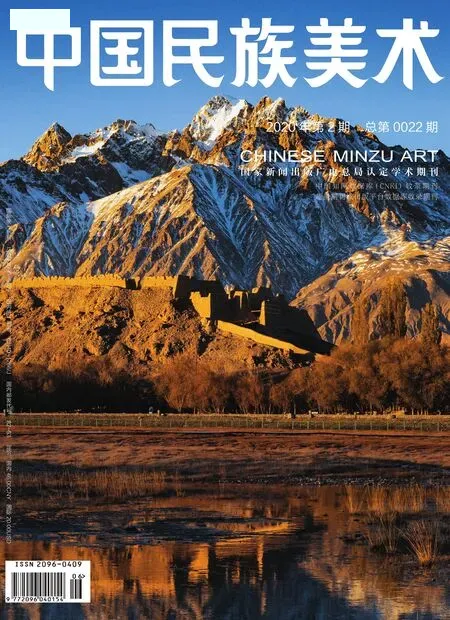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下的蘇雪林繪畫及其藝術評論觀點評述
文/圖:韓笑 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
20世紀上半葉的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女性的社會身份前所未有地多樣起來,女革命家、女學者、女作家、女畫家等身份的出現,使女性廣泛地參與到當時的社會實踐之中,為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變革添上了一抹殊異的色彩。在高舉文學改良旗幟的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語境中,文學與繪畫在新文化運動后文化構建與教育解放等方面的重要地位,為女性提供了一個自我表達的窗口,這其中,就有蘇雪林、凌叔華等由繪畫出身,在文壇大放異彩的女性,在文學與繪畫兩個領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本文從民國女作家蘇雪林在美術領域的經歷為視點,通過探尋蘇雪林的繪畫學習、創作與評論經歷,以窺民國時期女性表達的心理特征,解讀這一特定歷史語境下,女性主義的模糊、無意識,但同時也具有先鋒性的一面。
一、從蘇雪林的繪畫看民國時期的女性繪畫的意識
蘇雪林生于浙江省瑞安縣,成長于安徽省太平縣嶺下村(今黃山市黃山區永豐鄉),黃山是她真正的家鄉,蘇雪林的山水畫也常常描繪黃山。她幼時對繪畫產生興趣,后接觸《吳友如畫集》和四王等人的山水畫,開啟了她繪畫學習的歷程。1921年,蘇雪林考入法國里昂的海外中法學院,學習西方文學和繪畫藝術,她與著名的女畫家潘玉良即在此時結識,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蘇雪林在赴法后學習素描,但時間不長,1925年因母親病重而輟學,回國結婚,并未完成西畫學習的學業。她后期的繪畫創作則轉回國畫創作,但仍然可見西方繪畫中素描與透視對蘇雪林繪畫的影響。蘇雪林的繪畫不常示人,其繪畫經歷多見于她的紀實性散文中的自述,直到1994年,她才出版了一部《蘇雪林畫集》,共收錄37幅作品。
事實上,蘇雪林的繪畫并不能達到使她成為一名女畫家的成就,將蘇雪林的文學作品與繪畫作品相較,顯然她身為女作家的藝術成就要高出許多。她的學畫、繪畫經歷,更類似于一名民國時期的女文人對繪畫自娛式的藝術實踐。拿起畫筆是容易的,正如蘇雪林的繪畫創作開始于孩童時期極為偶然的娛樂,但她的繪畫創作在何種程度上構成一種藝術價值,卻值得商榷。在這一維度上,對蘇雪林繪畫的關注正體現出在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下,女性的繪畫實踐如何形成了女性獨特的美術史。
與蘇雪林繪畫所呈現出來的藝術特征相似,女性的繪畫與男性的繪畫,在藝術語言上,并無懸殊不同,它們呈現出與同時代藝術在風格上的一脈相承,與藝術史中同時期的繪畫總體保持著一致。學習文人畫的女性,繪畫就與文人畫的風格一致,學習西方繪畫的女性,繪畫也延續著西方繪畫的普遍規律。觀者無法透過一幅繪畫來判斷畫家的性別,相反地,我們總是先知道一幅繪畫的作者是女性,從而推定這幅繪畫里具有著怎樣的女性主義色彩。而這會使我們愈發忽略像蘇雪林這樣,創作繪畫卻不曾在美術史上留下姓名的女性。值得思考的是,斷定一幅繪畫具有女性主義色彩,是否必須從區別于傳統的男性繪畫的繪畫特征的角度去思考。如英國人類學家埃德溫·阿登納和雪莉·阿登納提出的噤聲理論所提示的那樣:“是否社會中的所有個體都能平等參與公共話語的編碼?那些具有不同價值及生活方式的群體是否得到社會主流的承認?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是否被貶低,而被排除在激勵系統之外?”[1]
從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來看,我們對女性繪畫的定義,就不能局限于具有女性主義色彩的繪畫上。誠然,具備女性主義色彩的繪畫,帶有深刻的女性表達的繪畫,進行女性身體、女性心理敘事的繪畫,更具有女性繪畫的知識生產價值,但是如蘇雪林這樣的繪畫,同樣為我們揭示了女性繪畫的另一面孔——拿起畫筆的女性,接受美術教育的女性,在繪畫創作中保持活躍的女性。她們的繪畫也許并未呈現出與父權制社會對抗的女性主義話語特征,卻真實地保留了女性群體在繪畫創作中的生存狀態,這種狀態,參照同處于民國時期的女作家,如孟悅與戴錦華所分析的那樣:“她尚然不是獨立于男性主體之外的另一種觀察主體,或許,只能算是半主體,她的視閾大部分重疊在男性主流意識形態的陰影后,而不曾重疊的那一部分是那么微不足道,不足語人亦不足人語,至今未得到充分注意。”[2]因此,如果我們要探尋女性繪畫的歷史,就要將這層陰影照亮,從而揭示那些曾經微不足道,未得到充分注意的部分。
然而,如果我們認為,女性繪畫處于被男性主宰的主流繪畫圖式的限制中,全無自己的特色,這顯然也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在精神控制高壓的封建社會中,文人畫所形成的固定的圖式和在儒學為統治思想,要求藝術創作的“成教化,助人倫”的思想指導下,主流繪畫也處在固步自封的僵化境地中,而生存在這一場域以外的女性繪畫,承載了較少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然展示出一種寄托著女性敘事、女性情懷與女性感知經驗的意識,使女性繪畫的表達帶有野生的、帶有內在經驗性質的特征,從而呈現出一種女性心理的模糊與無意識。

蘇雪林肖像畫
陶詠白在《失落的歷史——中國女性繪畫史》一書中這樣定義女性繪畫:“出自女畫家之手,以女性的視角,展現女性精神情感,并采用女性獨特的表現形式——凡此種種的繪畫,稱女性繪畫。”[3]這個定義強調了女性繪畫的主體,也強調了女性表達的獨特價值。從被遮蔽的歷史中走出,當女性的聲音逐漸出現在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界,女畫家的主體意識和表達意識也在逐漸增強。這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而是隨著民國時期婦女的獨立地位逐漸得到提升而逐漸明確的。
蘇雪林的繪畫經歷在這一歷史特征中,展示出一種矛盾和分裂的面貌,這種矛盾與分裂,恰好為我們展示了女畫家的主體意識與表達意識的構建過程。蘇雪林于1925年輟學回國結婚,因此中斷了她在法國的繪畫學習,而她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幸。蘇雪林在對自己一生的文學、繪畫和學術成就的歸因中說,這是緣于“婚姻的失敗與一生的落寞”。她身為民國時期所定義的“新女性”,卻走入了包辦婚姻,后半生都與丈夫分居。可以說,她是在妥協著封建的婚姻與追求自我的對立中度過了一生。從封建時代走出的女性,一方面處在擺脫封建制度對女性的重壓,尋找一種出口,另一方面,脫離封建制度的新時期依然由男性主導,如戴錦華在對民國時期的女作家分析時所說的那樣:“苛刻地說,或許由于新文化初期‘女性’概念的結構性缺失和所指的匱乏,她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再次充當了話語世界的空洞能指。她在過去封建文化中的特定語義固然被拋棄,但她以往在話語結構中的位置卻仍在延續,她仍然是那個因為沒有所指或所指物,因此可以根據社會觀念、時代思潮、文化密碼及流行口味時尚來抽出或填入意義的純粹載體……這樣一種既要女人覺醒又要女人沉睡的話語,為男性造就了完滿的意識形態神話,而給女性帶來的卻只能是自我分裂——如果她還堅持這份自我的話。”[4]可以說,蘇雪林的創作背后,這種來自時代的大敘事始終貫穿于她的意識背后,這在她的作品里,呈現出的就是一種與主流話語保持一致,卻無意識流露出女性主義特質,并帶有一定先鋒性的心理特征。因此,對蘇雪林繪畫的關注,為我們揭示了女性畫家在初登歷史舞臺時的渴望獨立又保守束縛、與主流話語格格不入的狀態。

寫黃山天都蓮花二峰 蘇雪林
二、從蘇雪林的藝術評論看民國時期女性繪畫的價值
如果說,蘇雪林的繪畫為我們揭示了民國時期女性繪畫的創作狀態,那么身為民國初期的重要散文家,蘇雪林留下的許多與繪畫相關的散文以及與民國時期女畫家們交往的回憶錄則為我們保留了更珍貴的女性繪畫研究資料。從這些文章中,我們一方面能看到蘇雪林身上樸素的女性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觀點,另一方面也能窺見民國初期女畫家在創作、交往、展覽上的景象。
蘇雪林對于繪畫問題的觀點與評論散見于其散文中。如自敘性質的《我與國畫》《黃海游蹤》,藝術評論性質的《看了潘玉良女士繪畫展以后》《孫多慈女士的史跡畫與歷史人物畫》《儲輝月女士的畫》,以及回憶錄性質的《記畫家孫多慈女士》《悼念一位純真的藝術家方君璧》等文。蘇雪林的藝術評論觀點雖不具備嚴謹的學術體系性,但其觀點鮮明,對藝術的思考非常深入,在反思中國傳統繪畫與認識西洋繪畫兩方面之間保持著辯證的眼光,同時,她極其在意女性畫家的主體地位,為女畫家仗義執言。借由她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女畫家之間交往的盛況,同時看到不同女畫家在創作中逐漸覺醒的自我意識,對于我們感受民國時期的女性繪畫表達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陶詠白在《失落的歷史——
中國女性繪畫史》中論及女性走入藝術的原因和狀態時這樣說:“藝術不再是閨秀賢淑自娛消遣的一種形式,而是生存的手段。她們從閨閣出走,步入社會,有的是作為事業去追求,也有的是為了擺脫封建包辦婚姻或不幸婚姻的束縛,求獨立自主的生活,有的是為了負擔家庭生計。總之,為了擺脫對男性或家庭的依賴和依附關系,她們紛紛走自食其力的路,或教畫,或賣畫,把自己融進了社會生存競爭的機制中,從而以獨立的人格,確立自己的獨立地位,塑造著‘獨立女性’的形象。”[5]可見,繪畫不再僅僅是女性自我表達、抒發閨閣情感的藝術形式,它也幫助女性樹立了職業的社會身份,帶來社會存在價值和經濟收益。可見,盡管女性是以一種話語渺茫、失落,且無意識的狀態踏出被遮蔽的陰暗境域的,這種出現本身卻帶來極大的震撼和進步。無論其視閾在何種程度上分裂和模糊著,這種狀態已經成為獨立的象征,而蘇雪林的記錄無疑是這種獨立最好的見證。在對民國時期女畫家的研究中,我們無法繞過蘇雪林的這種評述。一方面,作為同時代的新女性,蘇雪林的評述顯然更接近第一手資料,她的散文中甚至詳細記錄著潘玉良在留法時期練習素描人體的細節,另一方面,蘇雪林以女性的視角看待女性畫家,為我們揭示著那個時代女性的共同命運、共同經歷、共同情感作用在藝術上的表現。事實上,那個時代的女權主義思考是非常微茫的。如前文所述,女性以無意識的心理進入社會,而西方的女權主義觀點建立在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中,和中國民國時期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同步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語境。站在當下的視角去感受民國女性的生存狀態與心里經驗,現代的女權主義只能給我們提供話語的參照,并不能作為理論上的定性。而蘇雪林散文中流露出來的樸素的女性主義色彩,所呈現出的先鋒價值,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獨立女性”群體,或者說新女性群體的一種表達。

山水 蘇雪林
蘇雪林非常關注同時代的女性畫家,她與潘玉良、孫多慈、方君璧,以及同為作家卻擅長作畫的凌叔華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她對潘玉良的評價極高,論及潘玉良的畫展時,稱“除了林風眠先生的外,玉良的是使我滿意的了”[6],她評價潘玉良的繪畫時用了八個字:“氣魄雄渾”“用筆精確”,可以說,前四個字將潘玉良的繪畫從舊時期的閨閣女性的繪畫中區隔出來,后四個字將潘玉良的繪畫從中國傳統美術的寫意,或曰文人畫的風格中區隔出來,將潘玉良繪畫為中國美術現代化帶來的新風尚評價得頗為到位。
蘇雪林認為潘玉良的繪畫“絲毫不露女性”。她從對女性繪畫的刻板印象談開,將閨閣繪畫的特點歸納為“細膩、溫柔、幽麗、秀韻”,并說潘玉良的作品有“魄力”,因此與女性的作品不相似,反而與男性的作品相似。一方面,這是傳統話語在蘇雪林性別觀念中形成的刻板成見,另一方面,得益于蘇雪林這樣誠懇、大膽的表述,正為我們對潘玉良作品中突破刻板成見,反抗傳統性別結構,背叛主流性別話語的價值提供了重要的判斷。這成為一個有趣的邏輯,即女性的獨立表達,首先反抗的是原有的自己。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經典論述,女性是被構建的,是第二性的。女性原有的自我色彩,就處在這樣的構建之下,而走向獨立的第一步,是解構這樣的構建,祛除原有的父權制話語,毋寧是打破、消解、反抗、改造,總之,是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下,形成了對舊有性別秩序的逆反。

九老圖 蘇雪林(仿傅抱石之作)
同樣的,她在對儲輝月的山水畫的評論里這樣說道:“女性作家不管她是詩人、文人,也不管她是畫家、雕刻家,作品多偏于纖柔,小巧,線條弱,棱角圓,新清秀麗有余,莽蒼雄渾不足,而儲女士的山水則筆法遒勁,大氣磅礴,完全不似出自女子之手。”[7]儲輝月是民國時期國畫家黃君璧的夫人,其作品在美術史上幾乎沒有留下印跡,關于她作品的評述,也大致只可見蘇雪林這一篇。由此我們就大致可以感受,女性之間的藝術交往所留下的互相矚目,為揭開女性藝術被遮蔽的面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女性對女性的關注,不僅出于性別同一的同理心驅使,更出于女性本身對女性主體性的天然的敏感。這一動機,如清代女史家楊漱玉編纂《玉臺畫史》的動機相似,成為一種女性出自個人心理,對女性群體敘事與女性話語的本能的呼應。
蘇雪林在惋惜自己繪畫學業中斷,無法完成畫歷史畫的愿望時這樣說:“不過多少年來,看了許多現代中國畫家的作品,很少有合于我之理想者。當然有幾個資格較老的畫家如過去的徐悲鴻、林風眠,現在的梁鼎銘諸先生屬于例外,可是女畫家則實無一人,以女界人才論,實是一種恥辱。現見孫多慈女士居然有這么大的魄力來作盧溝橋抗戰畫,我們女界當然要分外高興,所以我要勸她再生產幾幅了。”[8]蘇雪林作為繪畫的觀者與藝術評論家,其女性的視角和對女性主體地位的強調在這段話中表露無疑。一方面,來自時代和社會現實的客觀束縛,使她認為女性的繪畫本應展現閨閣情致,表現嬌柔、溫順的風格;另一方面,新女性爭取獨立的進步思想,使蘇雪林如此關注“女界”——這一表述無疑強調了女性文化群體,與男畫家在創作表達上是否勢均力敵的狀況,并表達自己期待女性畫家多創作氣勢恢宏的歷史畫的祈愿,這實在不能說不具有一種樸素的女權主義的獨立精神與斗志。
蘇雪林的藝術評論觀點,一方面流露出時代籠罩在女性身上的巨大陰影,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民國時期女性追求獨立的進步姿態。民國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實際上屬于宏大敘事中革命解放運動的一支。在20世紀初期,在反抗封建壓迫與帝國主義侵略的主流思想下,民主思想將重視個人表達,追求人文精神擺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這使得女性的獨立成為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蘇雪林的藝術評論里,也隨處可見這樣的感召。蘇雪林對文人畫的批評非常深刻,她認為國畫“積弊太多”,主張師法自然,學習西方的寫實和透視,講究色彩和空氣,形成國畫的新風尚。她時常引用郭思的山水畫論和沈括對于透視的觀點,以強調追求自然對繪畫的重要作用,并推崇宋元之前,董源、巨然的山水。她自己的山水中便可見透視學習的影響,“以目光所能及者為限”。此外,她對于中西繪畫的交流也有一些零散的論述,她說:“他們贊同我們保持文化特色,其實想我們永遠滯留在時代落伍階段上,讓他們像動物園奇禽異獸一般來欣賞。”可以說,在反抗侵略的民族革命中,察覺到西方文化中心論對于東方文化異化的目光,既是蘇雪林身為中國藝術家的一種敏銳,同樣也是蘇雪林出于性別的弱勢——女性群體,對于中國作為種族的弱勢的一種敏銳。這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邏輯的共通性。
蘇雪林的藝術評論,為我們補充了民國時期美術的諸多細節。女性繪畫的價值也由于蘇雪林的這些藝術批評得以展示在歷史中。1928年11月,潘玉良的留學歸國繪畫展在上海舉辦后,蘇雪林即寫作了《看了潘玉良女士繪畫展覽以后》一文,“被滬上報刊爭相轉載”[9],可見她的評論在當時的輿論界與藝術界所引起的震動,而正是這樣的寫作與討論,使女性畫家的主體地位,不再隱藏于美術史的陰霾中,女性逐漸獲得了更多的主體性,女性繪畫的價值也在藝術史上獲得更多的認可。
蘇雪林是一個身份復雜的民國女性。她一方面恪守了傳統思想,另一方面堅持著獨立女性的精神;她既是作家,又是一個畫家,同時也是學者、評論家,并從事教育工作,蘇雪林因此成為了民國時期女性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藉由關注蘇雪林的繪畫與藝術評論,民國女性繪畫在我們面前驟然打開了一幅廣袤的圖景,生動而深闊。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看到新女性在繪畫中的話語建構與心理表達,更可以看到女性繪畫價值逐漸獲得認可的過程,這個過程既艱難,又充滿了女性進步與獨立的力量,也使中國現代美術史愈發多元、開放。
注釋
[1]楊欣泉.文化,權力與傳播:噤聲理論初探[J].科教文化,2008(05):157.
[2]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4.
[3]陶詠白,李湜.失落的歷史——中國女性繪畫史[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14.
[4]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3.
[5]陶詠白,李湜.失落的歷史——中國女性繪畫史[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120.
[6]蘇雪林.青鳥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203.
[7][8]蘇雪林.蘇雪林自述自畫[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211,202.
[9]左志英.冰雪梅林:蘇雪林[M].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