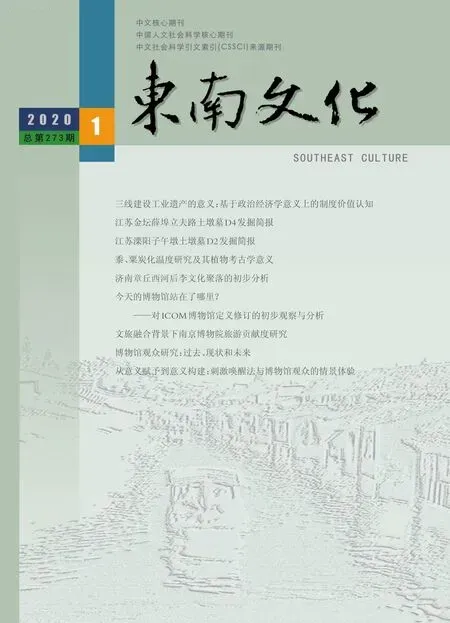從意義賦予到意義構建:刺激喚醒法與博物館觀眾的情景體驗
〔法〕丹尼爾·施密特米歇爾·拉布(著)〔中〕陳莉(譯)
(1.法蘭西綜合理工大學 法國;2.復旦大學 上海 200433;3.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
內容提要:博物館作為推動意義制造的特殊場所,其空間、主題、展品、闡釋文本等為觀眾提供了獲取意義的憑借。博物館通過這些中介發揮主導作用,影響著觀眾的意義構建過程,即“意義賦予”。然而,每個人都有著獨特的、不斷變化的意義構建模式,對觀眾進行外部觀察并不足以讓研究者洞悉觀眾體驗及意義構建的動態過程。刺激喚醒法聚焦觀眾“在原地”的情緒反應,關注觀眾從不同信息中構建意義的不同策略,凸顯了“干擾因素”的存在及意義構建過程與幸福感的相關性。基于此,博物館和展覽的設計應當重視建立必要的結構,鼓勵參與式意義構建過程;增加創造幸福感的因素,減少妨礙積極的意義構建的負面因素。
一、緒論
一個多世紀以來,歐洲和北美的博物館觀眾研究側重于觀眾的參觀路線、姿勢、注意力和疲勞度[1]。這些研究往往通過測試觀眾的反應、中介裝置的效果及觀眾發現博物館傳播信息的途徑等,來評估博物館的教育項目,以試圖了解觀眾[2]。此類研究傾向于采用調查問卷/參觀后訪談等以外部觀察為基礎的調查方法,其結果是我們可以較好地洞悉觀眾在博物館學習的動機[3]、博物館對觀眾顯而易見的影響,以及博物館的布局、特效、沉浸式技術的影響[4]。
但是,就參觀體驗的核心—情緒—角度而言,這些研究并不能清楚地說明觀眾對博物館的某件展品或裝置究竟有何期待及其學到了哪些知識。從這一點看,這些研究忽視了幾個關鍵問題:觀眾如何明確地表示其從參觀中“獲得了意義”?在參觀的不同階段,是什么給觀眾提供了“意義”?觀眾如何學習和構建/重構知識?——對于這些問題,我們現在才剛開始尋找答案。
觀眾“在原地”(參觀時)的體驗為何沒有得到更多關注?這有很多原因。約翰·福爾克(John Falk)認為,很多觀眾在參觀時或參觀后短時間內無法對原地學到或未學到的知識概括出有意義的細節,“學習”很可能發生在參觀結束很久之后[5]。除了可能的非正式/體驗式學習以外,哈里斯·謝特爾(Harris Shettel)提出觀眾體驗很難被確認,也難以被測量;因為研究方法是最新的,可能會對觀眾體驗造成干擾,同時研究需要大量時間和財力[6]。博物館管理者還提到,若過于重視觀眾,則會剝奪其決定博物館參觀“意義”的權力。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將觀眾體驗全面整合到博物館設計過程中[7]的范式轉變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全面整合”意味著將觀眾身體、認知、情緒等動態因素整合到參觀當中。這仍是一個幾乎未知的研究領域[8]。
在本研究中,我們力圖了解影響觀眾體驗的確切因素,從而為博物館展覽的設計打開有益的新視角。
二、研究背景:了解觀眾體驗
研究博物館觀眾的理念并不新穎。早在1884年,時任英格蘭利物浦博物館(Liverpool Museum,England)榮譽館長、后榮升英國博物館協會(British Museums Association)首屆主席的亨利·休·希金斯(Henry Hugh Higgins)深信向觀眾詢問其對展覽的意見可以讓博物館人積累很重要的經驗[9]。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展覽評估研究和觀眾研究才在美國變得多起來。當時肯尼迪(Kennedy)和約翰遜(Johnson)政府向社會項目提供了很多財政撥款,大力倡導博物館合理使用公共資金[10],特別是發揮博物館的教育作用[11]。美國博物館受益于此,并偏好使用調查問卷和心理學工具[12]。在法國,觀眾研究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受到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阿蘭·達爾布(Alain Darbel)的社會學影響。哈娜·戈特斯迪納(Hana Gottesdiener)[13]及20年后由杰奎琳·艾德曼(Jacqueline Eidelman)、梅蘭妮·魯斯坦(Mélanie Roustan)和伯納黛特·戈爾茨坦(Bernadette Goldstein)[14]開展的研究表明,法國觀眾研究的重點仍然是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及觀眾與展覽的關系,并且很大程度上以訪談調查為基礎。
發表《博物館:象征性體驗》(The Museum as a Symbolic Experience)一文的謝爾登·安妮斯(Sheldon Annis)似乎是第一位正式討論觀眾體驗的學者。根據馬琳·錢伯斯(Marlene Chambers)的說法[15],該文章在美國博物館界廣為流傳。20世紀90年代末,約翰·福爾克和林恩·迪爾金(Lynn Dierking)具有開創意義的著作《觀眾體驗》(The Visitor Experience)確立并擴大了“觀眾體驗”的概念[16]。這可能會使人以為當時的研究重點已轉向捕捉觀眾體驗中更個性化的方面,但仔細審視后會發現這樣的研究少之又少。事實上,大多數研究仍然關注的是公共知識、廣泛觀眾及博物館的發展和前景。2012年,沃爾克·基希伯格(Volker Kirchberg)和馬丁·特倫德爾(Martin Tr?ndle)通過整理北美和歐洲1990—2010年間有關觀眾體驗的研究,發表了《體驗展覽:博物館觀眾體驗研究綜述》(Experiencing exhibitions:a review of studies on visitors’experiences in museums)[17]。他們的研究證實了之前的結論——“博物館觀眾體驗很少被當作一個興趣點”。此外,以觀眾體驗為焦點的調查也往往基于觀眾參觀前和參觀后的訪談,目的是抓住總的觀眾體驗,而不是在原地觀察觀眾當時的情緒和認知上的反應。
然而,博物館的一些特性使得觀眾體驗值得作為獨特的研究領域加以重視。博物館被認為是具有社會“意義”的社會機構,觀眾可以從展覽中獲得意義。不同的調查[18]都表明公眾對博物館的信任程度極高。在過去幾年,這個數據并未發生大幅度變化。調查顯示,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在25%左右,對司法系統在55%左右,對政府在66%左右,而對警察在70%左右。盡管曾出現切爾諾貝利(Chernobyl)和福島(Fukushima)悲劇事件,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度仍達到90%左右。而參觀博物館的人群對博物館的信任則達到了98%這一超高水平。博物館觀眾相信博物館能夠闡述事實,呈現出有關真實生命的物件和擁有對社群意義重大的物件,提供了安全感;博物館出于“充分理由”展示物件,而觀眾的任務則是發現這一“充分理由”具有意義[19]。
因此,博物館被當作可以推動意義制造的特殊場所,可以讓我們更多地了解人類如何在自然環境(如在沒有老師、向導和正規活動的情況下)中構建意義及廣義上的人類知識生產機制[20]。
如今,博物館常用較多的新手段來促進非正式學習和無意學習,尤為適合從實踐和理論層面研究觀眾如何利用這些手段。博物館也因此常被看作“傳播空間”[21],并且不同的空間有著不同的主題、展品和闡釋性“文本”。文本可以包括語音導覽、視頻和互動裝置等,構成了博物館設計師影響觀眾意義構建過程的關鍵因素。丹尼斯·A.喬亞(Dennis A.Gioia)和庫馬爾·奇蒂佩迪(Kumar Chittipeddi)將這一共同籌劃的、由上游部門主導的意在影響觀眾意義構建的過程稱為“意義賦予”[22]。意義賦予的顯著特征是推崇一種場景(或闡釋方案),鼓勵觀眾通過建立共識來學習新知識[23]。建立共識的過程可以與伊齊基爾·迪·保羅(Ezequiel Di Paolo)、埃琳娜·克雷爾·庫法里(Elena Clare Cuffari)和漢妮·德·耶格(Hanne De Jaegher)等人的“參與式意義構建”(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24]聯系起來。另外,莉薩·鄧(Lise Degn)認為意義賦予可以讓我們從觀眾及博物館設計師的雙重視角審視“已付諸實踐的決策(這些決策也是未來決策的基礎)”[25]。
“參與式意義構建”的路徑表明博物館不應降格為單向傳播與接收的空間。這種空間傳遞的是合理構建好的信息,讓人想起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業已過時的“傳播”(communication)模式[26]。事實上,博物館也向觀眾提供復雜多樣的意義體驗和情緒。然而,香農關于傳播的數學理論將情緒排除在重要“信息”(information)之外。我們的研究通過“生成”(enaction)的概念[27]將情緒與信息理論融合到一起,發展出一套更為豐富的信息理論來整合各種觀眾體驗。我們可以從反復出現的體驗中識別出某種模式,然后將下游的鮮活體驗與博物館設計師在上游的意義賦予行為進行比較。
“信息”的概念被理解為社會行為者與其環境的整體耦合。無論是環境,還是社會行為者——從信息的角度來說——都不存在于自身,而在于相互依存之中。鑒于此,我們的研究試圖抓住這種耦合的本質——它作為一種結構動力,在“信息”構建中形成硬數據和軟數據。這一路徑遵循湯姆·弗羅斯(Tom Froese)、卡珊德拉·古爾德(Cassandra Gould)和亞當·巴雷特(Adam Barrett)等人的做法,他們試圖對與情境相關的直接體驗進行準確描述,而非籠統地描述“對一段體驗的想法、觀念、判斷或其他間接評價”[28]。正是基于這一挑戰,我們建立了刺激喚醒法,關注觀眾參觀博物館的行為。
三、研究目的:是什么讓一次參觀具有意義?
這項研究旨在確定通過何種方式來了解觀眾參觀博物館時發生了什么,及博物館設計能否考慮到“發生了什么”。從觀眾的角度而言,這項研究試圖了解是什么使參觀博物館具有意義或失去意義。對于研究者來說,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三個相關的核心問題。第一,如何更清楚地說明什么對觀眾具有意義;若具有意義,以何為參照點(價值體系)。第二,觀眾參觀博物館時,博物館如何獲知哪些要素關系重大。第三,如何確定觀眾通過何種方式決定其在博物館參觀的對象。如果觀眾觀看某些展品而忽略其他展品的行為不是一種隨意的、自發的“直覺”行為,那么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抑或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觀眾在參觀過程中是否優先考慮不同的選擇,例如明確安排參觀路線?若是,又如何做到?這三個問題必然使我們獲得關于觀眾的期望、情緒和價值體系及如何將新想法納入個人知識體系等方面的清晰認識。
最終,我們還試圖將研究成果延伸至其他類型的博物館、科學中心,并將研究對象擴展至與父母一起觸摸展品、觀看展覽、使用裝置的年少觀眾。為此,我們首先要更清晰地認識觀眾參觀博物館時構建意義的個人和集體動因,并考察可能構成或無法構成“有意義”參觀的因素。我們的研究陳述可概括為:如何在不顯著改變觀眾在原地的意義構建過程的情況下,通過觀眾體驗中的動態張力和存在的局限,更好地理解這種體驗。
四、研究方法論:生成法
在使用科學方法時,我們認為有必要在人類復雜性的背景下分析意義構建和賦予過程,需要了解“自然”環境(非實驗室)中的社會行為者在參觀博物館時如何從在原地感知到的物件中獲得意義。在社會科學中找到適當研究方法的途徑之一是澄清研究所使用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方法[29]。研究方法論的橋接作用確保了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相結合。通常,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拓撲學”(topology),可反映在所研究的概念世界里存在什么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本質。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我們將本體方法論限制在兩個相互關聯的基本維度上。
第一個本體論維度涉及人類“語言”的性質。一種觀點認為,語言的主要基礎是由“客觀的外部觀察者進行的描述,可通過與獨立實體進行對照,從而被明確識別出來”[30]。語言的主要功能是對信息進行編碼,并通過分析和組合進行信息傳遞[31]。另一種觀點認為,語言的主要基礎是通過建構性的生成和表達探索“意義世界”(不僅僅是一個“內在”世界)[32]。若如此,語言必然涉及“理解人類為實現意義而進行的努力及/或更廣義上的對生命的思考”[33]。第二個本體論維度涉及“意義構建”的性質。理解一個現象的意義,在本質上取決于一個人處理從外部世界中所提取數據的能力,而這個外部世界從根本上說是被動的;換言之,意義構建本質上是否由個體與一個動態的多主體的社會物質世界共同構成[34]?
那么,我們的研究使用何種本體論?關于個體與多主體(“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Meaning’)一文中運用了“孿生地球思維實驗”(Twin Earth thought experiment)來說明一個人的語言和思想的語義內容在本質上取決于其對外部環境的認識[35]。用普特南的話來說,“意義不在頭腦之中”(meanings just ain’t in the head)[36];一個人不僅僅是一個“缸中之腦”(brain in a vat)[37]。迪·保羅、庫法里和德·耶格的“非還原自然主義”法(nonreductive naturalism)[38]就使用了普特南的“涉及世界的解釋”(world-involving explanations)。后者突出強調了行為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并且在兩者的關系中“行為/意義不僅產生于適當的身體和環境條件,而且產生于身體和環境之間的親密接觸和相互改變[39]。換句話說,意義構建就是“涉及世界的解釋”[40]。
鑒于此,本研究的本體論是基于一種“生成”法。根據大衛·J.斯諾登(David J.Snowden)對意義構建本體論的兩大分類,“生成”法在某種程度上可被歸類為不可分割的、自然發生的、辯證的本體論[41]。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的生成法是一種現代的“新萬物有靈論”,可以從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四類“認知人類學”本體論[42]來理解。
使用生成法首先涉及這樣的問題,即在具體的歷史互動情境中,為何某些事物對一個人具有意義[43]。這樣一種生成本體論的主要認識論影響是什么?針對參與研究的博物館觀眾,我們如何獲知影響他們的是什么,如何確定在他們的意義構建過程中什么對他們有意義?我們從兩個方面回答以上問題。第一,雖然我們對硬數據和軟數據進行了形式上的區分,但它們在數據分析層面存在事實上的交織關系,這與我們在生成本體論的一元論觀點是一致的。有關數據交織的更多細節將在研究方法部分解釋。第二,我們認識論的核心部分是觀眾在陳述他們的參觀體驗時賦予話語的“具體”價值。這種一元論的方法論包含了分布式認知的思想。語言學家阿蘭·拉巴特爾(Alain Rabatel)指出,一元論的方法論否定任何思想與語言的分離[44]。從這個角度出發,普特南駁斥將語言視為中立的描述性“代碼”(獨立于不斷變化的語境和人類思想的可能偏見)的觀點。“這是一個錯誤,不僅因為最簡單的思想在語言表達中也會發生改變(如語氣變得更加肯定),而且因為語言改變了我們可以擁有的體驗邊界。”[45]換言之,語言不僅延伸了與世界的認知關系,而且也改變了這種關系[46]。同樣,迪·保羅等指出:“人類語言無法擺脫吸收與轉化的矛盾。對于人類而言,‘具體化’這個詞最主要的兩方面就是吸收和轉化,前者是指某物融入身體的過程,后者描述了身體作為一個整體意味著什么。”[47]
方法論為我們的研究方法鋪平了道路。我們的研究方法將觀眾的口頭話語(軟數據)與追蹤眼動的視覺記錄(硬數據)結合起來。這一方法可以讓我們研究影響博物館觀眾的因素及在觀眾的意義構建過程中什么對他們富有意義。
五、研究方法:刺激喚醒法
基于上文所述,本研究的核心假設是了解博物館觀眾的意義構建過程對設計吸引人的、以觀眾為中心的博物館具有直接指導意義。研究方法分為三個主要部分。
第一,觀眾在參觀過程中接受訪談,此時他們仍處于參觀的情緒當中。這種方法的一種變體是讓游客在參觀時“自言自語地”(think aloud)[48]表達他們的思想和情緒,并記錄所說和所做。“自言自語”法的主要問題是其不符合觀眾的常規做法。事實上,在許多博物館里都有盡量避免喋喋不休的傳統,因為沉默是一條黃金法則。通常,“自言自語”的方法會改變參觀體驗,因為邊參觀邊這樣做很可能造成“認知超載”(cognitive overload)[49]。
第二,在觀眾參觀結束后對其進行訪談,以便根據觀眾的記憶捕獲不同時刻的亮點。這種方法的一個主要缺點是過于依賴于觀眾記住的內容。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遺忘曲線》(Forgetting Curve)中的開創性研究表明,大約20分鐘后,大多數人失去68%的記憶,一小時后失去44%[50]。此外,心理學家阿蘭·利厄里(Alain Lieury)也提出著名的系列位置效應理論(serial position effect hypothesis)[51]。根據這一理論,在一系列材料中,系列開頭的材料比系列中間的材料更容易被記住(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而系列末尾的材料最有可能被記住(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
第三,基于眼動追蹤法了解觀眾體驗的主要前提是“眼運數據能到位地標示認知過程”[52]。然而,我們認為這種方法并不令人滿意。當技術識別出一個人的“注視點”時,我們仍然不可能準確地知道他在認知上關注了什么。我們并不知道這位觀眾是在看書、看音符,抑或在看書頁的顏色或書的厚度等(圖一)。一系列注視點的記錄并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并不意味著眼動追蹤技術沒有用,實際恰恰相反。
鑒于目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和我們理解觀眾體驗的研究目的,我們設計了一種名為“刺激喚醒法”(reviviscence,experience,emotions,sense-making micro-dynamics,即REMIND)的新研究方法,其背后是刺激回憶的傳統。本杰明·S.布魯姆(Benjamin S.Bloom)提出了刺激回憶法的基本概念,那就是“如果我們向一個人呈現大量在原始情境中出現的東西作為一種暗示加以刺激,我們就可以幫助他生動準確地再次體驗原始情境”[53]。這些暗示被用來刺激喚醒思想,即“行動中的思想”。

圖一// 基于眼動追蹤法的觀眾體驗(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在此背景下,丹尼爾·施密特(Daniel Schmitt)和奧里維爾·奧伯特(Olivier Aubert)在眾多研究中發展了刺激喚醒法[54]。它被設計成一種通過人類的情緒、期望、知識和決策等分析人類活動的方法。其方法論基礎是將觀眾的口頭話語(軟數據)與追蹤眼動的視覺記錄(硬數據)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的生成法[55]。這里的雙重前提是注視點對觀眾來說具有某種“意義”,并且觀眾能夠口頭陳述其“意義”。
在事先與博物館觀眾達成協議后,研究小組為博物館觀眾配備了眼動追蹤儀或微型攝像機,以便在他們參觀時對其注視點進行第一人稱視角的視聽跟蹤,然后通過讓觀眾自己點評視頻記錄進行訪談。為了確保博物館觀眾在“自然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56]中參觀的真實性,觀眾可以在任何時候做想做的事,也不會得到任何關于在博物館做什么、去哪里的指示。為了不以任何方式影響觀眾,研究小組會避開他們的視線。這樣的舉措確保體驗能夠留下“痕跡”(traces)。
“事實上,這些痕跡并不是被收集起來以隨性的方式加以闡釋,而是被看作是一種資源,可以創造與公眾溝通、協商的環境。換言之,觀眾在交流行為中不會失去參與主體地位,不是‘工具行為’[57]的對象。”[58]。
視頻不僅能夠記錄行為痕跡,還能夠在觀眾參觀結束后立即投屏,以刺激觀眾的情景記憶(圖二)。觀眾觀看的視頻記錄不會經過任何編輯或更改,這樣,視頻就變成了重溫參觀體驗的刺激物。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大量注視點的視頻記錄本身是不夠的。視頻確實表明了吸引觀眾眼球的具體方面(真實的或想象的)。但為了更加準確,研究者會對觀眾進行訪談。從研究目的上確定了觀眾已“充分”參觀博物館后,研究者就會作出訪談的決定。
在刺激喚醒式訪談中,觀眾陳述眼動追蹤儀記錄視頻中的行為,從而一步一步地、一秒一秒地回憶參觀時的思想和情緒。正常情況下,訪談室必須設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以便受訪者集中注意力;訪談地點還應靠近觀眾使用追蹤儀的區域,以確保受訪者快速、及時地進入訪談室,使得觀眾的參觀體驗盡可能鮮活地留在記憶中。
在訪談前,研究者取下追蹤器,受訪者舒適地坐在顯示屏前,觀看眼動追蹤儀的記錄,回憶當時的感受和想法。至關重要的是,研究者不在受訪者在場的情況下分析視頻內容,而只在必要時讓受訪者澄清一些事實。研究者會提問,要求受訪者對活動進行描述和評論,同時說明對應的情緒。當受訪者被要求評論其行為時,他們往往會從個人的角度自發地將行為的變化分成幾個獨立單元。

圖二// 視頻記錄觀眾行為痕跡,并在觀眾參觀結束后立即投屏(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典型的刺激喚醒訪談時間表如下:(1)選擇受訪者,為受訪者佩戴裝備(5~10分鐘);(2)記錄受訪者的行為(30~60分鐘);(3)拆除受訪者的裝備并安排訪談(5~10分鐘);(4)以重溫的模式進行訪談(30~45分鐘);(5)訪談后的一些活動(5~15分鐘)。訪談總時間為90~120分鐘。
訪談本身也會被錄制。訪談時第二人稱視角的記錄重點關注哪些痕跡促使受訪者開口講述,而非參觀行為本身;而眼動追蹤儀的記錄則重點關注受訪者的目光、期望值等。簡而言之,我們把以第一人稱視角錄制的視頻投放在屏幕上播放給受訪者,然后以第二人稱視角錄制受訪者與研究者的訪談。
訪談結束時,研究小組會掌握以下信息:(1)觀眾的注視點視頻(硬數據);(2)觀眾重溫體驗的錄像(軟數據);(3)觀眾的情緒指標(軟數據)。這樣,研究小組可以對數據進行三角測量,了解觀眾的體驗,推動他們的意義構建過程。我們從以下六方面分析觀眾的表述(表一)。

表一// 分析參觀者有關活動的表述
通過確認表一的各部分,我們可以對觀眾有意義的行為動態及構建(重構)的知識、產生的情緒加深了解。該過程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個體的微觀世界,從而發現對觀眾有意義的內容[59]。
在博物館,我們對觀眾體驗數據進行的分析可以按照人工制品、藝術品、裝置、空間使用等進行分類,并從中找到關聯。在收集和分析了長達10年的數據之后,我們發現博物館觀眾的意義構建與“幸福感”之間似乎存在著穩固的正對應關系。當觀眾理解了展品或藝術品的意義時,他們就會表達一種幸福感。
刺激喚醒法的一個主要優點是讓人們口頭陳述個人體驗。在這一過程中,它為研究者提供了有關個人體驗和行為的精確線索。例如,受訪者關注某件展品的情緒出現明顯變化時,他會直接進行評論。這就為研究者提供了線索,豐富對參觀者意義構建過程的認識。
六、情緒地圖法:刺激喚醒法的升級版
刺激喚醒法可以升級為情緒地圖法(E-MOTION)。其主要特征是研究以下問題:不同的博物館參觀者會選擇哪些不同的路線,幸福感的強度有多大,與幸福感相關的詞匯有哪些。
情緒地圖法的目標是將博物館參觀者的路線繪制成一幅情緒地圖。該方法假定我們可以在設計博物館空間時參考情緒地圖,反思博物館向觀眾提供的指導建議。可通過三個基本步驟來實現。

圖三// 觀眾在法國里爾美術宮(The Palais de Beaux-Arts in Lille)配備情緒地圖設備(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圖四// 情緒地圖系統識別觀眾的參觀路線及其情緒表達(圖片來源:作者繪制)
第一步,提取、收集觀眾的情緒信息,并制作成“我喜歡它”“我覺得它很美”等“標簽”(labels)。該語料庫源自十幾年來通過刺激喚醒訪談法收集的10家博物館的觀眾體驗描述。然后,我們將標簽導入在智能手機的“心理效價喚醒網格”(Valence-Arousal Grid)中。標簽的初始位置并不至關重要,因為標簽的位置是動態的,并隨著觀眾的使用習慣固定下來。在目前階段,我們的情緒語料庫并不包括在博物館體驗到的所有情緒,只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第二步,在面對繪畫作品時,約110名博物館觀眾被要求配備情緒地圖設備(圖三),并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心理效價喚醒網格”上標識他們的感受。觀眾每標識一種感受時,彈出式功能就會列出可供選擇的詞匯(其他觀眾使用過的詞匯)。
第三步,為了識別參觀路線(圖四),觀眾需使用攝像頭前裝有45°小鏡子的智能手機。通過這種方式,每當觀眾標識其感受時,智能手機就會自動拍攝其在博物館的確切位置。
總之,情緒地圖法可以在觀眾標識情緒強度的同時記錄其確切位置。這可以讓不同觀眾針對同一件人工制品、藝術品、裝置表達他們的情緒,由此讓研究者確定哪件展品最吸引觀眾。這種吸引可以源于展品本身,也可源于許多人聚集在一件展品周圍。后者是參與式意義構建的一種形式[60]。在任何情況下,最終結果是觀眾通過與展品建立聯系(事實上的生成關系)而獲得幸福感。
我們認為意義構建和幸福感是聯系在一起的。可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解釋:當人們就一件展品的意義交換意見時,它創造一種社會關系并由此帶來幸福感。對意義的共同構建是讓觀眾經由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誤解和溝通失敗,最終協商獲得一種穩定的意義,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參與式意義構建”[61]。“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參與式意義構建:在互動中協調有意識的活動,從而影響個人的意義構建過程,制造社會性意義構建的新領域,這些領域不是個體能夠獨自涉足的。”[62]
七、結果與討論
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人類具備在不同元素之間建立聯系的能力。當觀眾進入博物館或科學中心時,他們知道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等待著他們——識破秘密關系、發現未知的元素等。當這些被實現之后,觀眾會因為理解某件事物而獲得一種接近幸福的滿足感。
例如,一家以中世紀為主題的博物館有一黑色的小房間,旁邊有一白色的大房間,其內展示著大型雕塑。在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我們試圖了解為什么約有三分之一的觀眾喜歡小而暗的黑色房間,而不喜歡展示著美麗雕塑的白色房間。在館長看來,黑色房間看起來并不十分有趣。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觀眾認為中世紀是一段黑暗且充滿暴力的歷史,因此他們中意黑色小房間,因其傳達了那個時代的壓抑氣氛。而白色的大房間與觀眾對中世紀“黑暗氣質”的先入之見相沖突。后來小房間被漆成了白色,改變了觀眾的理解方式。現在由于兩個房間都是白色的,觀眾也喜歡大房間,兩個房間再也不存在不和諧之處。
我們的研究還從更廣義的角度發現了八種類型的聯系,它們似乎與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63]相呼應。每一種智能的核心是一種獨特的“信息處理裝置”(information-processing device)[64]。我們將其稱為“風格”,即觀眾在與世界互動時首選的一種非排他性聯系(“智能”)。主導風格指一個人與世界建立聯系時的慣用選擇。鑒于此,觀眾試圖通過以下方式與其在博物館的體驗建立聯系。(1)文本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人們喜歡閱讀抒情性的單詞和句子。這似乎對應了“語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65]。(2)與世界形成有形的認知聯系。這類似于對節奏、音調等更為敏感的“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3)身體—動覺感知(bodily-kinesthetic awareness)。這在盡管被禁止但仍想觸摸展品的“兒童”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加德納將其描述為一種對事件作出恰當的身體反應及控制身體的能力[66]。(4)對事物進行整理、分類的偏好。這是一種源自視覺觀察的“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67]。(5)注重展品和文本之間的邏輯關系。加德納將其歸類為“邏輯—數理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68]。(6)情緒和同理心。例如,當觀眾看到一尊神情痛苦的雕塑時,他們會體驗到痛苦的情緒。這可以與加德納的“交往—交流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聯系起來[69]。
更重要的是,加德納將以上六種智能按照本體論分為三大類[70],即“我們必須開始從更廣泛的范疇來思考——個人的經歷、參照系、意義構建方式及整體世界觀”[71]。這種分類也是參與式意義構建過程的核心,有助于博物館設計師和觀眾增進相互了解[72]。
加德納的第一類別是展品相關模式,關注觀眾接觸的特定展品的結構和功能[73]。這一模式從根本上涉及加德納的空間智能、邏輯—數理智能和身體—動覺智能[74],可對應于福爾克觀眾形象分類中的探險者(explorers)、專業人士/愛好者(professional/hobbyists)[75]。第二類別受不同語言和音樂系統的交流結構和功能的影響[76]。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聽覺和語言系統的特征[77]。加德納的語言智能和音樂智能可被視為“脫離展品”(object-free)。這兩種智能似乎與福爾克觀眾形象中的指導者(facilitator)有關[78]。第三類別源自個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評價。從本質上講,它指加德納提出的自知—自省智能及交往—交流智能[79],可對應福爾克形象分類中的經驗尋求者(experience seekers)和充電者(rechargers)[80]。
多年來,我們的研究強調所謂“干擾因素”(irritants)的影響。如果干擾因素普遍存在,它們會對觀眾的意義構建產生負面影響:消耗觀眾有限的精力,使其無法全神貫注地沉浸于博物館體驗中。我們可以將干擾因素視為“感知噪音”(perceptual noises)。干擾因素包括物理或人體工程學方面的干擾,如展品的標簽或展品本身位置太低、太高或不易找到,老年人閱讀展品標簽后無法輕松起身,透過窗戶的室外光線、反射在陳列柜玻璃表面或油畫上的燈光影響了展品的觀賞效果;又如空間照明反差過大,照射到文字上或某些空間內的光線不足,沒有為觀眾提供足夠多的椅凳,缺少指示牌等。干擾因素也包括認知干擾,如用對母語者來說都不易理解的文字書寫的標簽,內容不夠清晰(場景不匹配),解釋不當(技術細節過多),中介裝置不符合人體工程學、難以操控等。最令人不快的干擾似乎是“亂七八糟”的“誤導”觀眾的指示牌。
八、建議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僅從文本中介及信息和傳播技術的角度審視博物館,而必須注意到觀眾基于閱讀展品標簽或說明牌的參觀是不夠的。研究觀眾行為的刺激喚醒法確定了設計意義構建的兩個關鍵維度。
第一個維度指博物館設計師和觀眾兩者間及觀眾自身需要有效的意義構建過程。通過各種反饋模式進行的互動可幫助觀眾擁有更豐富、難忘的體驗。這些模式可以與加德納的多元智能[81]及三大意義構建的廣泛范疇[82]聯系到一起。
加德納的每一種模式和范疇都添加了一個特定元素,而非以不同的方式重復相同的元素。必須指出,加德納的多元智能和廣泛范疇在功能上是相互依存而非相互排斥。正如加德納所指出的:“正常情況下,多元智能實際上從生命的開始就相互作用,并在彼此的基礎上不斷發展。”[83]設計師應當避免從過分強調單一模式(如文本閱讀)的一個極端到濫用多種模式的另一個極端。提供太多模式可能會讓觀眾不知所措,無法從體驗中獲得意義。在意義構建的過程中建立一種平衡取決于模式的互補性。這對設計師來說不是一件易事。
在現實中,每個人都有獨特的、不斷變化的意義構建模式。設計師首先要從加德納多元智能的角度出發,審視提供給觀眾的各種模式。一般來說,設計師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三大模式的配置,無需系統地使用六種智能來吸引觀眾。如果系統使用六種智能,即使不至于使觀眾完全失去興趣,也很可能導致令人疲倦的“認知超載”[84]。簡而言之,這三種模式對意義構建過程有著不同的要求,取決于意義賦予者希望觀眾在參觀的特定時刻把重點放在何種“智能”上。這意味著在參觀的關鍵時刻,意義賦予者的配置會與觀眾的構建意義過程存在出入。
第二個維度是審視是否存在妨礙積極的意義構建的要素,包括與展品、標簽、展品說明有關的干擾因素,以及互動性的缺失——許多觀眾都對“現代”博物館的互動性抱有期待。這些都會將觀眾的注意力從預期的重點轉移到其他要素上,不利于形成積極的博物館體驗。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有必要建立一種觀察機制(如博物館工作人員的觀察)和反饋機制(如快速問卷調查),以便發現干擾因素并提供解決方案[85]。
如果有限的資源不允許糾正干擾因素(如改寫展品說明和標簽),那么可以鼓勵觀眾減少在可能造成困擾的展品上的逗留時間,延長在其他展品上的逗留時間。這種尋求反饋并根據數據采取行動的做法是觀眾和設計師雙方共同進行意義構建的核心[86]。
九、結論
我們在本文開頭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觀眾的現場體驗。我們看到,過去一個世紀的研究并沒有明確指出觀眾體驗的各個組成部分。簡而言之,從外部對觀眾進行觀察不足以了解觀眾“在原地”的行為。通過使用生成范式,研究者可以設計并科學調整刺激喚醒法,以準確識別觀眾體驗及意義構建的動態過程。刺激喚醒法對博物館專業人員的重要貢獻之一是為審視觀眾活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通過使用刺激喚醒法,作為意義賦予者的博物館管理者和設計師,需要敏銳地意識到觀眾根據周圍提供的線索并從展品中構建意義的意識和創造力。
刺激喚醒法強調觀眾從包含普及(非專業)內容的中介裝置中成功構建意義的獨特創造力,強調刺激喚醒法背后認知模式的重要性,因為認知模式決定了可以提出的問題。然而,有關知識的人為或工具中介的傳播,卻長久處于香農機械傳播模式的陰影中。這一模式使得人們很難將傳播的信息與在特定情況下個人接收到的信息聯系起來。
刺激喚醒法通過識別觀眾從不同信息中構建意義的不同策略,彌合了“硬”科學和“軟”科學之間的差異。除此之外,通過刺激喚醒法得到的研究結果還凸顯了“干擾因素”的存在。這些干擾會嚴重影響觀眾的幸福感。為了排除干擾,我們不僅可以減少干擾,還可以從“參與式意義構建”的視角進行設計[87],從而形成一種讓觀眾從有意義的體驗中構建意義的積極渠道。
觀眾對博物館的巨大信任可以成為一種催化劑,讓他們參與創造有意義的體驗。我們認為,這種意義構建過程與幸福感密切相關。在設計以現場體驗為重點的展覽時,在幸福感與意義構建之間建立聯系可以產生良性循環。博物館專業人員應考慮到這些因素,以便觸及更多不同類型的觀眾。總的來說,我們提出兩項基本建議:(1)重視建立必要的結構,鼓勵參與式意義構建過程;(2)增加創造幸福感的因素,或至少減少妨礙積極意義構建的負面因素。
(一)研究的局限性
一方面,通過刺激喚醒法獲得的研究結果,其質量取決于參與者整合實際信息的能力及其描述活動、情緒和想法的口頭表達能力。另一方面,它們還取決于研究者的口頭表達能力、移情能力及所受過的培訓。通過多少調查才能使研究結果有效?觀眾的構成決定了研究是否客觀。
(二)未來展望
通過構建觀眾體驗的概念和詞匯系統,從不同的語料庫分析觀眾的言語行為,可以構思出觀眾體驗的“語法”(規則)。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確定基本的意義構建的序列,以及這些基本序列在觀眾體驗網中的位置。這種方法與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觀點相呼應。泰勒指出,當一個人試圖弄清楚發生什么時,“組合似乎是按照規則進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語法和句法”[88]。更好地理解體驗的語法可以引導我們使用適當的工具和技術思考博物館設計。這樣的語法還需要將情緒定為“軟數據”。我們的生成研究法為把情緒設定為可用“硬數據”進行解釋的“軟數據”開辟了新視角。
在關注意義構建時,我們還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有意義的體驗如何在不同的觀眾之間共享、協商和傳播,從而達成一種相對穩定的意義構建模式?鑒于此,在以觀眾為中心的博物館中使用能夠提供意義的AR等中介設備,似乎有助于推動觀眾的意義構建過程,并且可以運用于不同的場景中。
(致謝:感謝參與研究的博物館觀眾、經理和設計師。此外,本研究的實現離不開無數同仁的建議和貢獻,特別是Virginie Blondeau、Marine ThinBault、Olivier Aubert、Johann Saint-Mars、Muriel Meyer-Chemenska、Sylveleeleu-Merviel。)
[1]a.A.Melton,N.Goldberg Feldman&C.Mason.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a museum of science.Studies in Museum Education,1936,15.b.A.Melton.Som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museum visitors.The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33,30:720-721.c.E.Robinson.The behavior of the museum visitor.Washington: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28,5.d.E.Robinson.Exit the typical visitor,Museums take thought of real men and women.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1931:419-423.e.B.Gilman.Museum fatigue.The Scientific Monthly,1916,12(1):62-74.
[2]a.C.Screven,K.Gessner.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for Visitor Studies;Biblography ans abstracts(éd.Seconde).Milwaukee,Wisconsin: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for Visitor Studies,1988.b.P.Elliott,R.Loomis.Studies of visitor behavior in museums and exhibition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ources primaril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Office of museums programs,1975.
[3]J.Falk,L.Dierking.The museum experience.Whalesback Books,1992.
[4]B.Schiele.Les études de visiteurs.Les musées et leurs public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2014:7-69.
[5]J.Falk.Expérience de visite,identités et self-aspects.La lettre de l'OCIM.2012,141:5-14.
[6]H.Shettel.No visitor left behind.Curator,2008:4,51,365-375.
[7]a.V.Kirchberg,M.Tr?ndle.Experiencing exhibitions:a review of studies on visitor experiences in museums.Curator,2012,55(4):435-452.b.E.Russner.Publikums for schung für Museen;Internationale Erfolgsbeispiele.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2010.
[8]a.D.Schmitt,O.Aubert.REMIND,une méthode pour comprendre la micro-dynamique de l’expérience des visiteurs de musées.(Europia,ed.)RIHM,Revue des Interactions Humaines Médiatisées,2016,17(2):43-70.b.同[7]a。
[9]P.McManus.Museum and visitor studies today.Visitor Studies: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1996:1-12.
[10]H.Shettel.Evaluation in museums:a short history of a short history.Dans D.Uzzel.The visitor experience.Belhaven Press,1989:129-137.
[11]a.D.E.Marsh.From“Extinct Monsters”to Deep Time.PhD dissertation,Ethnography of Fossil Exhibits Production at the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Vancouver: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4:437.b.R.Lakota.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exhibit effectiveness.Office of Museum Programs-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6.
[12]a.J.Koran,M.Koran&J.Ellis.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eld experiences:1939-1989.Visitor Behavior,1989,2:7-10.b.S.Bitgood.An overview of the methodology of visitor studies.Visitor Behavior,1988,3(3):4-6.c.同[3]。
[13]H.Gottesdiener.Evaluer l'exposition.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caise,1987.
[14]J.Eidelman,M.Roustan&B.Goldstein.La place des publics.De l'usage des études et recherches par les musées.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caise,2007.
[15]M.Chambers.The new paradigm is already here.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eum Exhibition,ed.Exhibitionist,1999.
[16]同[3]。《策展人》雜志的文章標題中,90%帶有“體驗”一詞的文章出現在1999年后。
[17]同[7]a。
[18]D.Boy.Sciences en société au XXIe siècle:autres relations,autres pratiques.Colloque,Strasbourg,28 et 29 novembre 2007.
[19]D.Schmitt.Ce que“comprendre”signifie pour les jeunes visiteurs dans un centre de culture scientifique.Dans P.Chavot,A.Masseran.Les cultures des sciences en Europe,2015,2.
[20]P.McManus.Le contexte social,un des déterminants du comportement d'apprentissage dans les musées.Publics et Musées,1994,5:59-78.
[21]J.Davallon.Le musée est-il vraiment un média?Publics et Musé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1992,2:99-123.
[22]D.A.Gioia,K.Chittipeddi.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in Strategic Change Initiation.Sensemaking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433-448.
[23]同[22]。
[24]E.Di Paolo,E.C.Cuffari&De Jaegher.Linguistic Bodies.The Continuity between Life and Language.Cambidge,Mass:The MIT Press,2018.
[25]L.Degn.Sensemaking,sense-giving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Danish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2015,69:6,901-913.
[26]C.E.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1948,27,(3):379-423.
[27]D.Schmitt.L'énaction,un cadre épistémologique fécond pour la recherche en SIC.Les Cahiers du numérique,2018,15:93-112.
[28]T.Froese,C.Gould&A.Barrett.Re-viewing from within:A commentary on First-and Second-Person Methods in 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Constructivist Foundations,2011,6(2):254-269.[DB/OL][2019-07-12]http://constructivist.info/6/2/254.
[29]a.M.Labour.Sens décisionnels et facteurs humains:méthodologie et application.Saarbrücken,Allemagne: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2016.b.P.Clough,C.Nutbrown.A Student’s Guide to Methodology.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2.c.A.Bhattacherjee.Social Science Research:Principles,Methods,and Practices.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Scholar Commons.USF Tampa Library Open Access Collections,2012.[DB/OL][2019-04-22]https://scholarcommons.usf.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2&context=oa_textbooks(accessed 22/04/2019).d.M.Saunders,P.Lewis&A.Thornhill.Research Methods for Business Students.Edinburgh Gate,Harlow: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2007.
[30]C.Taylor.The Language Animal:The Full Shape of the Human Linguistic Capacity.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252.
[31]同[30],第87頁。
[32]同[30],第252頁。
[33]同[30],第253頁。
[34]同[24],第333頁。
[35]H.Putnam.“The meaning of‘meaning’”.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2: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36]同[35],第227頁。
[37]H.Putnam.Reason,Truth,an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38]同[24],第6頁。
[39]同[24],第58頁。
[40]同[24],第333頁。
[41]D.J.Snowden.Multi-ontology sense making:A new simplicity in decision making.Informatics in Primary Care,2005,13:45-53.
[42]P.Descola.Anthropologie de la nature,cours de l’année 2001-2002,[DB/OL][2019-04-21]https://www.college-de-france.fr/media/philippe-descola/UPL28453_UPL31695_descola.pdf
[43]同[24],第81頁。
[44]A.Rabatel.Idiolecte et représentation du discours de l’autre dans le discours d’ego.Cahiers de praxématique,2005,44:93-116,[DB/OL][2019-07-13]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praxematique/1664.
[45]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and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48.
[46]同[45],第69頁。
[47]同[24],第211頁。
[48]a.C.Dufresne-Tassé,M.Sauvé&A.Weltzl-Fairchild eds.Pour des expositions muséales plus éducatives,accéder à l'expérience du visiteur adulte.Développement d'une approche.Revue canadienne de l'éducation,1998,23(3),302-315.b.C.Dufresne-Tassé,M.C.O'Neill,M.Sauvé,eds.Un outil pour conna?tre de minute en minute l'expérience d'un visiteur adulte.Revista Museologia&Interdisciplinaridade,2014,3(6).
[49]J.Sweller,P.Ayres&S.Kalyuga.Cognitive Load Theory.New York:Springer,2011.
[50]H.Ebbinghaus.Memory.A Contribution to Experimental Psychology.New York: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13.
[51]A.Lieury.Psychologie cognitive.Paris:Editions Dunod,2013:159.
[52]S.P.Liversedge,J.M.Findlay.Saccadic eye movements and cogni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0,4(1):6-14.
[53]B.S.Bloom.Thought-processes in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1953,7:160-169.
[54]同[8]a。
[55]同[27]。
[56]F.Jambon,N.Mandran,B.Meillon.Evaluation des systèmes mobiles et ubiquitaires: proposition de méthodologie et retours d’expérience.Journal d’Interaction Personne-Système(JIPS),2010,1(l.1):1-34.
[57]J.Habermas.Rapports au monde et aspects de la rationalité de l’agir dans quatre concepts sociologiques d’action.Dans Théorie de l’agir communicationnel.I Rationalité de l’agir et rationalisation de la société.Fayard,Paris,1987:90-118.
[58]Y.Jeanneret.La fabrique de la trace.London:ISTE Editions,2019.
[59]D.Schmitt.Describ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xperience of visitors.Visiting the Visitors,2016.
[60]同[24]。
[61]同[24]。
[62]H.De Jaegher,E.Di Paolo.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An enactive approach to social cognition.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7,6(4):485-507.
[63]H.Gardner.Frames of Mind.New York:Basic Books,1993.
[64]同[63],第278頁。
[65]同[63],第73—77頁。
[66]同[63],第206頁。
[67]同[63],第174頁。
[68]同[63],第129頁。
[69]同[63],第274—276頁。
[70]同[63],第104—276頁。
[71]同[63],第298頁。
[72]同[24],第333頁。
[73]同[63],第276頁。
[74]同[63],第129、174頁。
[75]J.Falk.Identity and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Walnut Creek,CA:Left Coast Press,2009.
[76]同[63],第276頁。
[77]同[63],第73—77,104頁。
[78]同[75]。
[79]同[63],第274—276頁。
[80]同[75]。
[81]同[63],第104—276頁。
[82]同[63],第276頁。
[83]同[63],第278頁。
[84]D.Kahneman.Système 1/Système 2.Paris:Editions Flammarion,2012.
[85]同[24]。
[86]同[22]。
[87]同[24]。
[88]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