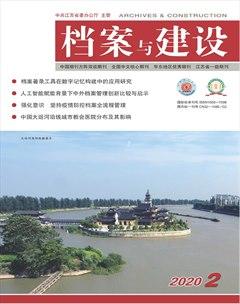檔案資源在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中的建構(gòu)作用及實現(xiàn)路徑探析
陳琴
摘要:文章以南京大屠殺事件為主要分析對象,主要探討的是集體語境下的創(chuàng)傷記憶。首先,對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意義以及國際認(rèn)同面臨的困境加以探討;其次,指出檔案資源在創(chuàng)傷記憶中的建構(gòu)作用及其作用機理,詳盡闡釋創(chuàng)傷記憶的延續(xù)傳承直至國際認(rèn)同離不開檔案資源的建構(gòu);最后,從檔案的視角探討促進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實現(xiàn)路徑,將創(chuàng)傷記憶的研究引申至檔案學(xué)領(lǐng)域,以期在豐富檔案學(xué)理論的同時讓集體創(chuàng)傷記憶得到更大范圍的認(rèn)同。
關(guān)鍵詞:檔案資源;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南京大屠殺
分類號:G279
The Construction Rol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Archives Resour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Trauma Memory
Chen Qin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njing Massacre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traumatic memory in the collective context.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raumatic memory and the dilemma faced by its international identity. Secondly, it points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resources in traumatic memory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elaborates the continuation of traumatic memory until international identity is inseparable from archival resources. In the 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v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raumatic memory, and extends the research of traumatic memory to the field of archival science. It enriches the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and hopes to make the collective traumatic memory more widely recognized.
Keywords:Archive Resources; Traumatic Memory; International Identity; Nanjing Massacre
創(chuàng)傷記憶研究最初集中于心理學(xué)領(lǐng)域,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擴展至社會學(xué)、文化學(xué)、歷史學(xué)等諸多學(xué)科領(lǐng)域[1]。諸如戰(zhàn)爭、大屠殺、自然災(zāi)害等都會造成個體或者集體的創(chuàng)傷,從而形成創(chuàng)傷記憶。李昕將創(chuàng)傷記憶定義為人類在經(jīng)歷突發(fā)性、災(zāi)難性事件時,由于事件本身的殘酷性超出個人的承受能力,而導(dǎo)致創(chuàng)傷主體在生理尤其是心理上的創(chuàng)傷[2]。趙靜蓉認(rèn)為只有在集體的或世界性的語境中考量個體創(chuàng)傷,后者才能從個體苦難上升為集體危機,從文學(xué)主題演變?yōu)檎軐W(xué)、倫理或道德主題,從身體、精神及社會創(chuàng)傷深化為“文化創(chuàng)傷”[3]。所謂國際認(rèn)同,是國際社會所持的相對穩(wěn)定的肯定和認(rèn)可的情感、態(tài)度和思想意識,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4]。本文強調(diào)的創(chuàng)傷記憶,指的是集體語境下的歷史性創(chuàng)傷記憶,特別是由戰(zhàn)爭導(dǎo)致的文化創(chuàng)傷,其國際認(rèn)同不單單是指得到國際權(quán)威機構(gòu)、組織的認(rèn)同,同時要得到更多國際友人的關(guān)注、了解,最終上升為全人類的記憶,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目前學(xué)界關(guān)于創(chuàng)傷記憶認(rèn)同方面的研究多從個人創(chuàng)傷記憶的自我身份認(rèn)同、集體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族認(rèn)同角度出發(fā),缺乏國際認(rèn)同方面的研究,以檔案為視角的探討更是寥寥無幾,因此,本文從檔案的視角,闡述檔案資源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建構(gòu)作用及作用機理,詳盡闡釋創(chuàng)傷記憶的延續(xù)傳承直至國際認(rèn)同離不開檔案資源的建構(gòu),最后,探討利用檔案資源促進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實現(xiàn)路徑,以期豐富檔案記憶理論,結(jié)合多學(xué)科滲透,提供新的研究視角,讓創(chuàng)傷記憶得到更大范圍的認(rèn)同。
1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意義及困境
1.1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意義
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是把創(chuàng)傷記憶的認(rèn)同上升到國際層面,而不單單從個人身份認(rèn)同角度以及國族認(rèn)同角度加以探討。以南京大屠殺為例,其發(fā)生于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期間,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后日軍進行大規(guī)模屠城的慘案。其國際認(rèn)同的意義在于:其一,從共情的角度上表達著世人對災(zāi)難事件的同理心。世人在了解這個史實真相的基礎(chǔ)上,往往會產(chǎn)生對受害者所遭受苦難的同情,對施暴者反人類行為的譴責(zé),對造成不同程度創(chuàng)傷的幸存者一些行為的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對幸存者的二次傷害,同時也是對受害者的告慰。其二,從和平的角度上表達著全球祈愿和平、維護正義的共同價值理念[5]。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國際認(rèn)同,意味著將其從中國記憶上升到世界記憶的意義,不僅可以加深世人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認(rèn)知,也在緬懷逝者、銘記歷史的基礎(chǔ)上,向世人表達祈愿和平、維護正義的共同價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世界各國和平發(fā)展和共同進步,這與黨的十九大報告多次呼吁的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高度契合。其三,從教育角度上對各國的沖突矛盾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當(dāng)今世界的和平問題仍然面臨不小的挑戰(zhàn),如敘利亞內(nèi)戰(zhàn)和烏克蘭東部沖突仍在持續(xù),恐怖主義蔓延肆虐,持續(xù)動蕩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難民危機等[6],這些威脅世界和平的挑戰(zhàn)都給一定國家和地區(qū)的人民留下創(chuàng)傷記憶,因而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對各國的沖突、內(nèi)戰(zhàn)等有一定的教育警示作用,讓更多的人認(rèn)識到由于不必要的戰(zhàn)爭而留下的創(chuàng)傷記憶,是一種人類文明的倒退。正如武秀波在《認(rèn)知科學(xué)概論》中提到:“記憶的多重結(jié)構(gòu)意味著記憶的不同類別或組合,它是指功能相互獨立的過程所引發(fā)的性質(zhì)不同的記憶效果。”[7]因此,記憶與記憶之間的保存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促進的,對于創(chuàng)傷記憶的保存與傳遞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世人對創(chuàng)傷危害的認(rèn)知,以達到警示教育的效果。
1.2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上的挑戰(zhàn)
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挑戰(zhàn)指的是一些集體創(chuàng)傷記憶特別是一些主體涉及多國家參與的民族創(chuàng)傷記憶,在國際范圍內(nèi)還沒得到廣泛的認(rèn)同,與此同時,國際上還有許多創(chuàng)傷記憶被逐漸遺忘。創(chuàng)傷記憶被逐漸遺忘甚至長期遺忘,一方面,會造成后一代的人對幸存者的指責(zé)與不理解,產(chǎn)生代際溝通問題,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幸存者的相繼離開,人們對歷史真相的認(rèn)知愈發(fā)模糊,那么就很有可能發(fā)生篡改歷史、扭曲歷史、創(chuàng)傷記憶資源相互爭奪等情況,因而,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還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例如,二戰(zhàn)期間的三大慘案即納粹屠猶事件、南京大屠殺事件、屠殺波蘭戰(zhàn)俘的卡廷森林慘案,其中國際認(rèn)同度最高的應(yīng)屬納粹屠猶事件,戰(zhàn)后德國對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認(rèn)不諱,并設(shè)立許多猶太人紀(jì)念館。但是反觀與之相似的中國南京大屠殺問題,南京大屠殺雖然已經(jīng)申遺成功,可也僅僅是得到了相關(guān)國際權(quán)威組織的認(rèn)可,卻還沒有成為一個受到足夠重視和廣泛認(rèn)同的世界性問題。這是因為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多是停留在抒發(fā)情緒、還原歷史真相層面,儀式紀(jì)念的活動也多局限于南京這一區(qū)域,而且與加害國的敘事話語并不一致,以至于南京大屠殺話題的公共討論程度還未在國際范圍得到普遍認(rèn)同。
2檔案資源在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中的建構(gòu)作用及其作用機理
美國密歇根大學(xué)本特利歷史圖書館前館長弗朗西斯·布勞因曾說,檔案正在成為理解、恢復(fù)和表達社會記憶這一挑戰(zhàn)的中心問題。[8]關(guān)于檔案與社會記憶的關(guān)系研究,學(xué)界已經(jīng)做了相當(dāng)多的探討,目前主要有屬性論、要素論(或說工具論、途徑論)、載體論等觀點[9]。屬性論認(rèn)為,檔案具有記憶屬性;載體論認(rèn)為檔案是承載社會記憶的載體。[10]本文采用馮惠玲、徐擁軍要素論的觀點。馮惠玲指出,“檔案是構(gòu)建集體記憶重要且不可代替的要素”[11];徐擁軍認(rèn)為:“檔案是構(gòu)建社會記憶不可替代的要素。檔案作為物質(zhì)的文獻和固化的信息,是一種承載社會記憶的工具和傳承社會記憶的媒介。”[12]而創(chuàng)傷記憶屬于社會記憶的范疇,因此,檔案也是建構(gòu)創(chuàng)傷記憶重要且不可代替的要素。正如美國社會人類學(xué)家保羅·康納頓認(rèn)為“記憶的恢復(fù)借助了外來原始資料”[13],創(chuàng)傷記憶的建構(gòu)與傳承離不開檔案的作用。檔案資源可以被理解為建構(gòu)創(chuàng)傷記憶的要素集合,它不是簡單的要素疊加,還包括矯正補充的過程,因為檔案資源會被開發(fā)利用并通過各種媒介進行傳播,因而所建構(gòu)的創(chuàng)傷記憶是再生產(chǎn)的創(chuàng)傷記憶。
2.1檔案資源刻寫固化創(chuàng)傷記憶
檔案是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中不可或缺的建構(gòu)要素,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承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保羅·康納頓在談到社會記憶如何傳承和積累時說到:“用刻寫傳遞的任何記述,被不可改變地固定下來。”[14]從中可以看出刻寫實踐,即文本對社會記憶的影響[15]。以南京大屠殺檔案為例,第一手的檔案資料對南京大屠殺的記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再現(xiàn)歷史,還原歷史。眾所周知,南京大屠殺事件其實經(jīng)歷了一段被長期遺忘的過程。從被長期遺忘到被再次關(guān)注再到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離不開相關(guān)人士關(guān)于受害者、加害者、目擊者完整檔案證據(jù)鏈的系統(tǒng)收集與整理。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網(wǎng)站顯示,中國在申遺中提交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共有三部分,分別包括日本侵略軍占領(lǐng)南京期間大肆殺戮中國軍民和平民的檔案、對日本戰(zhàn)犯調(diào)查和審判的檔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構(gòu)提供的文件。[16]這些檔案中不僅包括文件、日記、卷宗和信件等文字記錄,還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和丹麥等國的傳教士、記者和教師拍攝的影像檔案[17]等,這些檔案是對日軍暴行的固化,在申遺成功的過程中功不可沒。同時《南京大屠殺檔案》的申遺成功,還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從中國記憶上升為世界記憶,有利于促進南京大屠殺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要知道,過去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特別是在西方國家,批判討論二戰(zhàn)法西斯暴行時一般以講納粹屠猶為主,而對南京大屠殺的探討寥寥無幾,而回憶探討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主要以中國人民為主,對日軍暴行的揭露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因而,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具有十分深遠(yuǎn)的意義。[18]
2.2檔案資源重塑傳播創(chuàng)傷記憶
檔案自身不會傳播創(chuàng)傷記憶,它需要結(jié)合大眾傳媒工具,進行大范圍的傳播,而在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播過程中,讓更多的受眾了解這段歷史、記住這段歷史,可以達到創(chuàng)傷記憶傳承的目的。大眾傳媒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中具有大量受眾的一類傳播媒體,一般包括報紙、書刊、廣播、電視、電影、網(wǎng)絡(luò)等形式,現(xiàn)已成為各種傳播工具的總稱。[19]而自檔案與大眾傳媒工具結(jié)合起,它就在一定程度上對創(chuàng)傷記憶進行建構(gòu),包括其對創(chuàng)傷記憶挖掘并傳播的方式與內(nèi)容。檔案資源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建構(gòu)與傳承看似矛盾,實則并不然。如丁華東教授在《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一書中說到檔案從其產(chǎn)生起,就在社會記憶的傳承與建構(gòu)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時進一步提出了社會記憶的傳承與社會記憶的建構(gòu)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傳承影響建構(gòu),建構(gòu)來源傳承,傳承也是建構(gòu)的再現(xiàn),并把檔案與大眾媒體相結(jié)合的形式稱為檔案記憶展演,認(rèn)為展演一詞包含對社會記憶的挖掘、建構(gòu)、演示、傳播、傳承等[20]。以南京大屠殺為例,檔案參與創(chuàng)傷記憶重塑和傳播的形式有:南京大屠殺系列紀(jì)錄片、相關(guān)報紙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事件以及國家公祭日的報道、建立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jì)念館、相關(guān)書籍等。網(wǎng)絡(luò)媒體的發(fā)展為檔案建構(gòu)和傳播創(chuàng)傷記憶提供了重要的途徑和廣闊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生動地展示與再現(xiàn)歷史場景,擴大了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播范圍,延展了創(chuàng)傷記憶的生命力,而當(dāng)這種傳播范圍足夠廣時,創(chuàng)傷記憶將會在世界范圍上被認(rèn)同。
2.3檔案資源雙向控制創(chuàng)傷記憶
檔案資源控制創(chuàng)傷記憶涉及政治權(quán)力因素,主要是與不同權(quán)力主體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有關(guān)。近年來,檔案中的權(quán)力因素逐漸受到檔案學(xué)界的關(guān)注,其對社會記憶的雙向控制作用日益顯現(xiàn)。在正向控制方面,檔案中的權(quán)力因素起到一種導(dǎo)引性的控制作用,引導(dǎo)、強化社會主流記憶,比如歷朝歷代的“玉牒”“圣訓(xùn)”等都在宣揚封建統(tǒng)治者的意志。而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記憶能夠傳承至今甚至申遺成功,少不了國家權(quán)力因素的積極推動。從申遺的過程來看,對南京大屠殺申遺材料選取、整理、申報等無不滲透著國家權(quán)力因素[21],同時在國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jì)念館所展出的檔案也大部分是國家權(quán)力正向控制的結(jié)果。在反向控制方面,檔案中的國家權(quán)力因素是通過阻斷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承或者改變其傳承的內(nèi)容來讓大眾無法觸及歷史真相,主要方式可以歸納為銷毀歷史記錄、封禁歷史記錄、篡改歷史記錄、回避歷史記錄[22]等。例如,日本掩蓋南京大屠殺史實的一系列行為:其在進行大屠殺開始前就制定了嚴(yán)密的宣傳計劃,收買各國主流媒體,發(fā)布有利于日本的相關(guān)宣傳報道;在屠殺消息仍然不脛而走時,又緊急采取措施,通過封鎖南京城、破壞城內(nèi)的新聞媒體機構(gòu)、阻撓外國記者進入、禁止本國記者報道戰(zhàn)況等手段,極力抑制南京大屠殺的消息傳播,同時銷毀記錄暴行的證據(jù),制造假象,散布南京城內(nèi)一派和諧等不實消息;在戰(zhàn)后基本對侵略歷史避而不談,使學(xué)者以及日本老兵大多對相關(guān)研究以及采訪采取回避態(tài)度;在教科書中篡改歷史,將日軍強奸、屠殺等罪惡暴行有選擇地抹去,[23]后來在《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過程中頻頻阻撓。而這一系列的行為使南京大屠殺記憶在日本人民記憶里面消失,同時嚴(yán)重阻礙世人對歷史真相的了解。
2.4檔案資源在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中的作用機理
我們不僅要明晰檔案資源在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中的作用,同時要深入其內(nèi)部,弄清檔案資源在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中的作用機理,以便更好地理解檔案資源不僅有利于創(chuàng)傷記憶歷史事件建構(gòu),而且檔案本身還具有建構(gòu)行為的雙重性質(zhì)。正如科瑟在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導(dǎo)言中所說,“集體記憶在本質(zhì)上是立足現(xiàn)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gòu)”[24]。社會記憶的傳承與建構(gòu)是在交互演變的,檔案在這其中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檔案資源對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作用機理可以從檔案對社會記憶的作用機理中受到啟發(fā)。由此,檔案對創(chuàng)傷記憶建構(gòu)的作用機理可以歸納為內(nèi)在建構(gòu)與外在建構(gòu)的統(tǒng)一。所謂內(nèi)在建構(gòu)表現(xiàn)在檔案記錄的形成,檔案雖然具有原始記錄性,但是檔案所記載的創(chuàng)傷記憶內(nèi)容并不是對歷史事件毫無偏差的復(fù)制,它受記錄人主觀意志的影響,檔案不可能把創(chuàng)傷記憶完整地記錄下來;而外在的建構(gòu)表現(xiàn)在檔案工作者對創(chuàng)傷記憶相關(guān)檔案的選擇、存取、銷毀以及對相關(guān)檔案的編纂開發(fā)利用。無論是檔案的內(nèi)在建構(gòu)還是外在建構(gòu),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認(rèn)同。如外在建構(gòu)中檔案資源的整合與開發(fā),通過選擇、組合、敘事、傳播等機制的有機統(tǒng)一,對創(chuàng)傷記憶進行喚醒、重構(gòu)、固化、刻寫的良性循環(huán),即首先選擇創(chuàng)傷記憶相關(guān)檔案材料和展演方式,然后對選取的檔案文獻材料進行組織和梳理,接著對整理的檔案材料進行闡述,最后通過一定的途徑實現(xiàn)社會傳播,在傳播中強化創(chuàng)傷記憶,以期將創(chuàng)傷記憶上升到國際認(rèn)同的高度。
3檔案資源促進創(chuàng)傷記憶國際認(rèn)同的實現(xiàn)路徑
3.1借助現(xiàn)代傳媒優(yōu)勢擴大認(rèn)同場域
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離不開對檔案資源的深度挖掘與開發(fā),而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網(wǎng)絡(luò)媒體的發(fā)展為檔案建構(gòu)創(chuàng)傷記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與現(xiàn)代傳媒結(jié)合的檔案記憶展演,展示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深刻,傳播的形式更加方便快捷,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與再現(xiàn)歷史場景,不僅打破了時空的限制,延展了創(chuàng)傷記憶的生命力,而且更有利于擴大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播范圍,提升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影響力,進而促進創(chuàng)傷記憶的國際認(rèn)同。檔案部門只有注重與現(xiàn)代傳媒(特別是國際媒體)的合作,才能進一步擴大創(chuàng)傷記憶的聲音和影響力,擴大傳播范圍,所以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后仍需要檔案部門以及相關(guān)文化機構(gòu)的繼續(xù)努力。為了充分發(fā)揮南京大屠殺檔案的教育意義,不僅可以在國家公祭日、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的紀(jì)念日之際,借助現(xiàn)代傳播媒介的優(yōu)勢,通過網(wǎng)絡(luò)、網(wǎng)站、報道等形式構(gòu)建“認(rèn)同場域”、強化“符號記憶”,喚醒民族記憶的同時強化海內(nèi)外情感共鳴,還可以舉辦相關(guān)主題的國際學(xué)術(shù)交流來促進世人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情感認(rèn)同、身份認(rèn)同乃至價值認(rèn)同。
3.2檔案部門與大眾傳媒應(yīng)承擔(dān)的社會責(zé)任
創(chuàng)傷記憶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創(chuàng)傷,而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承離不開檔案資源的建構(gòu),所以檔案部門在與大眾傳媒進行合作時,應(yīng)承擔(dān)好各自的社會責(zé)任,注意處理好歷史真實和藝術(shù)真實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不能純粹為了迎合觀眾,就將創(chuàng)傷記憶相關(guān)內(nèi)容進行“娛樂化”。例如,近年來活躍于電視熒幕上的“抗日神劇”,違背了歷史的真實性,顛覆了人們對于抗日戰(zhàn)爭那段記憶的客觀認(rèn)知,夸大了中國人民在戰(zhàn)爭中的反抗能力,淡化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艱苦經(jīng)歷。[25]因而,檔案部門在與現(xiàn)代傳媒合作時,特別是在影視拍攝選材時,要進行嚴(yán)格的把關(guān),所選取的檔案內(nèi)容均要以尊重歷史為原則,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最大限度真實準(zhǔn)確反映創(chuàng)傷史實,在這個基礎(chǔ)上再適度地進行內(nèi)容取舍以及藝術(shù)創(chuàng)作。
3.3將事件放置于更廣更高的全人類視角看待
對于集體創(chuàng)傷記憶的探討,不應(yīng)當(dāng)僅僅停留在歷史真相的證明,也不能把它當(dāng)作一種恥辱,而應(yīng)該將創(chuàng)傷記憶轉(zhuǎn)化為對歷史的反思,將創(chuàng)傷事件放置于更高更廣的全人類視角看待。審視南京大屠殺與納粹屠猶事件,同樣形成了大屠殺性質(zhì)的創(chuàng)傷記憶,為什么納粹屠猶的國際認(rèn)同程度更高?答案肯定不僅僅是出于納粹屠猶事件中死傷的猶太人數(shù)量更多以及牽扯的國家范圍更廣等原因,相比之下,對于納粹屠猶事件,無論是德國人還是猶太人都傾向從更加多向的角度進行思考,而不單單是爭論誰是誰非,逃避責(zé)任。德國人方面首先正視歷史,承認(rèn)錯誤,并大范圍建立相關(guān)的猶太人紀(jì)念館;猶太人方面也不是一味地譴責(zé)德國納粹、批判法西斯主義,而更多的是反思自己種族劫難的根源,對自己種族的信仰進行重新定位,甚至在電影領(lǐng)域、文學(xué)領(lǐng)域逐漸將一個民族問題變成了一個世界問題。因而納粹屠猶的記憶之所以能擴散至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與其在傳播過程中秉承的世界情懷不無關(guān)系。由此可以得出,檔案在傳承創(chuàng)傷記憶的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對苦難保持同情和尊重,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書寫保持清醒和警惕;盡量避免對幸存者的二次傷害,同時融入世界情懷,以公平、正義、自由、人權(quán)、文化為根本向世界發(fā)聲。
4結(jié)語
大屠殺不應(yīng)該被遺忘,忘記大屠殺等同二次屠殺,不僅屠殺了受害者以及幸存者的冤屈,也屠殺了歷史的真相與連續(xù)性。如近日發(fā)生的澳大利亞的原住民不滿國慶日事件,也正是說明了大屠殺的記憶不應(yīng)該被遺忘。同時記憶與記憶之間的保存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促進且多向的,因而對一個國家民族創(chuàng)傷記憶的紀(jì)念有利于其他國家民族提高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認(rèn)知,向全球表達不忘歷史、緬懷逝者、祈愿和平的共同價值理念,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gòu)建。檔案資源在其中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檔案部門應(yīng)該加強與現(xiàn)代傳媒的合作,爭取將集體創(chuàng)傷記憶上升至受各國重視且廣泛認(rèn)同的世界記憶高度,而不是任其遺忘、扭曲、篡改或陷入無休止的爭論。
注釋與參考文獻
[1][2][25]李昕.創(chuàng)傷記憶與社會認(rèn)同:南京大屠殺歷史認(rèn)知的公共建構(gòu)[J].江海學(xué)刊,2017(5):157-163.
[3]趙靜蓉.創(chuàng)傷記憶:心理事實與文化表征[J].文藝?yán)碚撗芯浚?015(2):110-119.
[4]張治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認(rèn)同建構(gòu)路徑[J].理論學(xué)刊,2018(4):79-85.
[5][23]王書川.從“被遺忘”到“被關(guān)注”再到“成為人類記憶”——南京大屠殺的媒介傳播過程分析[J].阜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6(3):148-151.
[6]狄英娜.銳評|當(dāng)今世界面臨著嚴(yán)峻的和平赤字挑戰(zhàn)[EB/ OL].[2019-11-21].http://www.sohu.com/a/208356393_122905.
[7]武秀波.認(rèn)知科學(xué)概論[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7:107.
[8]弗朗西斯·布勞因.檔案工作者、中介和社會記憶的創(chuàng)建[J].曉牧,李音,譯.國際檔案界,2001(9):48-51.
[9]古同日.“檔案記憶”概念辨析[J].檔案管理,2018(5):33-35.
[10]萬啟存,牛慶瑋,張愛新.歷史的遺忘與記取——探析檔案與社會記憶的關(guān)系[J].檔案學(xué)研究,2015(2):44-48.
[11]馮惠玲.檔案記憶觀、資源觀與“中國記憶”數(shù)字資源建設(shè)[J].檔案學(xué)通訊,2012(3):4-8.
[12]徐擁軍.檔案記憶觀:21世紀(jì)檔案學(xué)理論的新范式[J].山西檔案,2017(4):5-12.
[13][14][美]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4.
[15][19][20][22]丁華東.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4,313,176,336-338.
[16]中國新聞網(wǎng).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慰安婦”檔案落選[EB/OL].[2019- 11- 21].https://new.qq.com/cmsn/ 20151010/20151010008388,2015-10-10/2018-11-18.
[17]李瓊.集體記憶視角下紀(jì)錄片的檔案價值探析——以“南京大屠殺”系列檔案紀(jì)錄片為例[J].陜西檔案,2017(6):41-43.
[18]馬振犢.《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的重大意義[N].中國檔案報,2015-12-14(001).
[21]劉迪.檔案建構(gòu)社會記憶中的權(quán)力因素及其積極作用——從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說起[J].檔案學(xué)通訊,2016(2):90-94.
[2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