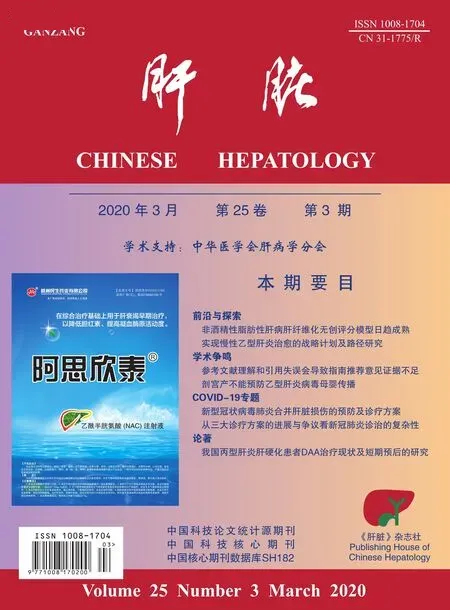TLR4和腸道菌群在原發性肝癌進展中動態變化及與預后的關系
王雨 許達峰 周開倫 武金才 丁驛超 古海強 謝明微 林明花
原發性肝癌是全球最常見惡性腫瘤之一,致病因素多種多樣,在我國,以HBV感染為主,可進展為肝硬化和或甚至肝癌,威脅生命安全[1-2]。Toll-樣受體4(toll like receptors 4,TLR4)隸屬于TLR家族,是機體天然免疫系統識別病原微生物的主要受體,在固有免疫反應及獲得性免疫反應中均占有重要地位[3-4]。研究表明,TLR4可通過激活Toll受體結構域、髓樣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MyD88)及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因子6(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associated factor 6,TRAF6)等,誘導下游核轉錄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 活化,啟動IFC軸[5]。腸道菌群是指寄居在人體腸道內所有微生物,研究發現其可通過調節宿主代謝和免疫功能等參與疾病的發生發展,疾病進展過程中菌群差異明顯[6]。本研究探討TLR4和腸道菌群在原發性肝癌進展中動態變化,并分析其與臨床病理及預后之間的關系。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于本院診治的100例慢性乙型肝炎、80例肝硬化合并乙型肝炎和60例肝癌合并乙型肝炎作為研究對象,診斷均符合《內科學·第8版》對應疾病的診斷標準。納入標準:①肝癌患者臨床分期Ⅰ-Ⅲ期;②所有肝癌患者均給予根治性手術治療;③所有患者資料均完整;排除:①合并其他類型肝炎患者;②合并其它惡性腫瘤者;③合并其他胃腸道疾病者;④近1月內未給予任何治療者。乙型肝炎組:男65例,女35例;平均年齡(45.8±7.2)歲;肝硬化組:男53例,女27例;平均年齡(45.2±6.8)歲;肝癌組:男41例,女19例;平均年齡(46.1±7.7)歲;3組在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上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另選取同期年齡及性別與前3組匹配的100名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所有研究對象均知情并簽署同意書,并已通過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二、各組外周血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檢測
入組后第1天,抽取各組研究對照空腹靜脈血3 mL于EDTA抗凝管,充分混勻;流式細胞術檢測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每份血液標本有2支試管(各含100 μL抗凝血血液標本),1支分別加入FITC-CD14單抗(5 μL)和PE-TLR4單抗(5 μL),另一支試管加入PBS液(5 μL),充分搖勻,4℃靜置30 min,后向2支試管中加入2 mL紅細胞裂解液,震蕩混勻,室溫避光靜置20 min,PBS洗滌2次,離心棄上清,加PBS調整濃度,上流式細胞儀檢測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
三、腸道菌群分布檢測
收集各組新鮮大便,取0.5 g標本按10倍系列稀釋法將其稀釋,后分別用MRS瓊脂培養基、雙歧桿菌BS培養基、腸球菌培養基和麥康凱瓊脂培養基培養乳酸桿菌、雙歧桿菌、腸球菌及大腸埃希菌,培養2~3 d后用法國梅里埃公司生產的半自動微生物鑒定儀及軟件進行鑒定,并計算每克糞便濕重中菌落形成單位對數值(lg CFU/g)。
四、隨訪
對60例肝癌患者進行隨訪,記錄1年內其復發和生存情況。
五、統計學方法

結 果
一、各組外周血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水平比較
對照組、乙型肝炎組、肝硬化組和肝癌組外周血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分別為(34.92±4.79)%、(41.92±7.46)%、(49.21±8.83)%和(57.62±10.58)%,4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78.624,P<0.01)其中乙型肝炎組高于對照組(t=7.896,P<0.01),肝硬化組高于乙型肝炎組(t=6.002,P<0.01),肝癌組高于肝硬化組(5.120,P<0.01)。
二、各組腸道菌群分布比較
4組乳酸桿菌和雙歧桿菌含量依次減少,4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4組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含量依次增多,4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組腸道菌群分布比較(lg CFU/g,±s)
注:與對照組比較,①t=7.260;②t=5.814;③t=10.149;④t=9.044;與乙型肝炎組比較,At=6.197;Bt=4.197;Ct=6.600;Dt=8.588;與肝硬化組比較,at=5.706,;bt=8.193;ct=5.125;dt=4.309;均P<0.01
三、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與腸道菌群分布的關系
經Pearson相關分析得知,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與乳酸桿菌和雙歧桿菌呈負相關(r=-0.643,P=0.012;r= -0.672,P=0.021);與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呈正相關(r=0.771,P=0.008;r= 0.734,P=0.010)。
四、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與肝癌患者預后的關系
隨訪1年,60例肝癌患者中,18例復發,15例死亡。復發者外周血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為(59.32±9.17)%,明顯高于未復發者的(55.21±5.2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200,P=0.032);死亡者外周血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為61.04±10.23)%,明顯高于生存者的(53.29±8.11)%,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998,P=0.004)。
五、腸道菌群分布與肝癌患者預后的關系
與未復發者比較,復發者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含量明顯減少,但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含量則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生存者比較,死亡者復發者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含量明顯減少,但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含量則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腸道菌群分布與肝癌患者預后的關系(lg CFU/g,±s)
注:與復發者比較,①t=3.305;②t=3.691;③t=3.441;④t=3.596;與死亡者比較,At=4.596;Bt=4.288;Ct=4.382;Dt=4.437;均P<0.01
討 論
在TLR家族中,共有10個基因(TLR1-TLR10)可介導機體免疫功能[7]。TLR4是一種跨膜蛋白,主要包含3個結構域:胞內結構、跨膜結構和胞外結構[8]。其中,胞內結構主要包含Toll 受體結構域;而胞外結構則包含多個亮氨酸重復序列,可特異性識別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和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9]。近年研究發現,在乙型肝炎中TLR4識別PAMP后可激活MyD88-NF-κB信號通路,上調肝臟相關炎癥因子、趨化因子及相關介質,最終使肝臟發生病理改變[10]。在本研究中,對照組、乙型肝炎組、肝硬化組和肝癌組外周血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呈逐步升高,提示TLR4可促進HBV-肝硬化-肝癌進程,這與周東曉等[11]學者部分結論基本一致,但其與肝癌預后的關系尚不清楚。隨訪1年發現,復發者外周血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明顯高于未復發者,死亡者外周血CD14+TLR4+單核細胞陽性率明顯高于生存者,提示TLR4與肝癌預后密切相關,有望成為肝癌預后監測及評估的重要指標。
肝臟是人體最大的代謝器官,此外,其還具有一定的免疫調節功能[12]。在長期進化過程中人體腸道形成了穩定的腸道菌群,約有10萬億個,其中可被培養的有400多種,主要分為以雙歧桿菌為代表的優勢菌群和以大腸埃希菌為代表的次要菌群,其代謝產物主要由肝臟門脈系統完成分解及排放,與肝臟關系密切,共同承擔著調節代謝和免疫的作用[13]。當人體患肝病時,代謝解毒能力明顯降低,而腸道菌群多樣性降低,有害菌群數量及代謝產物明顯升高,構成惡性循環,加重肝臟損傷[14]。近年,腸道菌群與肝臟代謝的關系逐漸成為治療和預防肝病的熱點之一。而糞便是腸道菌群和宿主代謝產物的共同排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腸道菌群狀態[15]。本研究腸道菌群優勢菌群代表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硬化患者和肝癌患者中依次減少,而其有害菌群代表大腸埃希菌和腸球菌則依次升高,提示腸道菌群變化與HBV-肝硬化-肝癌進展密切相關。此外,與未復發者和生存者比較,復發者和死亡者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含量明顯減少,但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含量則明顯升高,提示腸道菌群變化在肝癌預后預測中也具有一定價值。綜合以上結果,不難發現TLR4和腸道菌群變化在HBV-肝硬化-肝癌進展及肝癌預后預測中都有一定價值,為此,本研究進行了Pearson相關檢驗,發現單核細胞表面TLR4表達與乳酸桿菌和雙歧桿菌呈負相關,與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呈正相關,說明TLR4表達水平越高,乳酸桿菌和雙歧桿菌水平越少,而腸球菌和大腸埃希菌則越多,提示TLR可能與腸道菌群相輔相成共同影響著肝臟結構。
綜上認為,TLR4可促進乙型肝炎進展為肝癌,與腸道菌群變化明顯相關,兩者在肝癌預后監測中有一定價值。但關于TLR4與腸道菌群中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對肝癌進展的影響尚不清楚,有待后續繼續探討,且未涉及其在肝癌預后監測的具體價值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