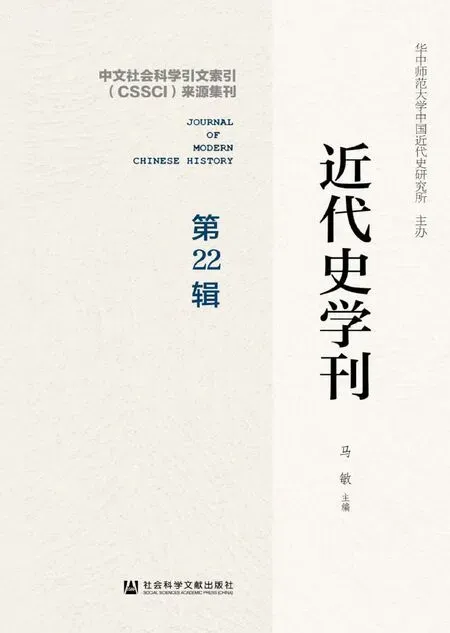胡適疑古思想再探討
——兼論20世紀30年代的胡、顧關系
王學進
內容提要 疑古辨偽是胡適學術思想的重要特征。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中稱,胡適曾于1929年對他說其不疑古而要信古。受顧頡剛的歷史敘述影響,大多數研究者認為胡適在1929年之后疑古思想發生轉變,將此視為胡適與顧頡剛及古史辨派分道揚鑣的肇端。二者疏離固為事實,然別有隱情,學術觀點的差異并不表明胡適疑古思想發生了變化。從胡適在30年代前后的學術研究情況尤其是禪宗史研究來看,其疑古思想一以貫之,甚至較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20世紀早期,疑古思潮催生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作為胡適的學生,顧頡剛的疑古思想受胡適的影響頗大,也可以說是胡適引導他走上疑古辨偽之路。顧頡剛所言“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與胡適提倡的“歷史的觀念”如出一轍。顧頡剛的疑古思想又反過來影響了胡適,胡適的“滾雪球說”與顧頡剛的“層累說”所表達的意思幾乎完全一致。兩人在整理國故中對古書古史的懷疑和考辨可謂心有靈犀,相對于他人對胡適整理國故的誤解和批評,顧頡剛對胡適的意圖心領神會,與胡適步調高度一致。后因局勢的發展,兩人“南轅北轍”。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稱:“到了一九二九年,我從廣州中山大學脫離出來,那時胡適是上海中國公學的校長,我去看他,他對我說:‘現在我的思想變了,我不疑古,要信古了!’我聽了這話,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為什么會突然改變的原因。”①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顧頡剛全集》(1),中華書局,2010,第160 頁。受顧頡剛的歷史敘述影響,大多數研究者認為胡適在1929年之后疑古思想發生了轉變。劉起釪在《顧頡剛先生學述》中根據顧頡剛所說,認為胡適后來不再疑古,從此兩人分道揚鑣。①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第262—263 頁;路新生認為隨著疑古運動的發展,胡適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從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胡適發表的對于考信辨偽的方法論檢討的系列論文,我們實際上也就可以將其視為‘疑古派’分化的標志”。②路新生:《諸子學研究與胡適的疑古辨偽學》,《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 期。此外,如趙潤海、王學典、李政君等均認為胡適的疑古思想后來發生了轉變。③參見趙潤海《胡適與〈老子〉 的時代問題——一段學術史的考察》,劉青峰編《胡適與中國現代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第397 頁;王學典:《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中華書局,2011,第149 頁;陳勇:《試論錢穆與胡適的交誼及其學術論爭》,《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3 期;李政君:《1930年前后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變與不變》,《史學月刊》2014年第6 期。然而通過對顧頡剛和胡適的日記和書信,特別是1930年前后兩人之間的關系,以及胡適學術研究情況的考察,可以發現事實并非如此,胡適的疑古思想是否發生轉變仍有探討之必要。
一日記折射下的胡顧關系
1929年2月,顧頡剛以請假之名辭別中山大學,轉道香港,于3月1日抵達上海。在離開廣州之前,顧頡剛給胡適寫信告知:“大約是三星期內到滬,屆時當和內子等赴謁。”④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3 頁。顧頡剛抵滬次日,即“到適之處,并晤梁實秋等”。⑤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45),第255—258 頁。此為顧頡剛第一次拜訪胡適。之后,顧頡剛為購書和探親之事往來蘇滬杭等地。3月20日,顧頡剛再次拜訪胡適:“到伯詳處,同到名達家,予與名達訪適之先生。”⑥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45),第264 頁。顧頡剛日記對自己的行程和探親訪友均有詳細記載,從日記可以看出,他在3月拜訪胡適只此兩次,所記極簡,沒有涉及具體談話內容。
顧頡剛來訪期間,胡適剛從北平回到上海,察其日記,對顧頡剛拜訪之事并無記錄,只在3月3日提到:“顧頡剛得著一冊抄本《二馀集》,是崔東壁的夫人成靜蘭的詩集,我與顧頡剛求之多年未見,今年由大名王守真先生抄來送他,他又轉送給我。”①胡適:《胡適全集》(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27 頁。此書很可能是顧頡剛3月2日拜訪時所送。
3月23日,顧頡剛回到蘇州老家,連日奔波,舟車勞頓,使他感到身心俱疲。“幾乎日在輪轂之中,精神身體兩皆勞頓矣。此數日中始得在家稍息。”②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中華書局,2011,第193 頁。25日,顧頡剛致信胡適,邀游蘇州。28日,顧頡剛再次致信胡適,詢問能否來蘇,由于大戰在即,“時局緊張,因封船故到甪直不方便矣”。③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4 頁。4月24日,顧頡剛在信中稱:“先生上月來信,說十天內一定到蘇州,但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十天了,還不見來,而我也要到北平了,我們只得在暑中再見了。”④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4 頁。可知胡適對顧頡剛的邀請應有回信,可惜在胡適往來書信中未見此信,日記亦無記載。
6月底,顧頡剛回蘇州為父親籌備六十大壽,適逢胡適在蘇州參加振華女校的畢業典禮,兩人再次晤面,并同游獅子林等處。據顧頡剛7月3日記:“適之先生來電話。適之先生應振華女校畢業式之招,偕師母兩兒到蘇州,今日偕丁庶為夫婦游天平山,晚乃來一電話。”⑤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45),第299 頁。4日,顧頡剛冒雨“到蘇州飯店,訪適之先生及其眷屬”。即日,“適之師母偕祖望來。適之先生偕丁庶為夫婦來。同到獅子林及耕蔭義莊游玩”。⑥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45),第299—300 頁。7月12日為顧父六十大壽,胡適此時登門應有順便賀壽之意。因工作關系,加之長子在蘇州讀書,胡適經常往來滬蘇兩地,兩人晤面機會較多。8月16日,胡適應蘇州青年會之邀,再次來到蘇州,顧頡剛“到蘇州飯店訪適之先生”。⑦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45),第313 頁。8月31日,顧頡剛離蘇北上,途經上海,在上海逗留一周,于9月8日赴京。其中,9月7日,顧頡剛“到適之先生處,并晤林語堂”。⑧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45),第321 頁。胡適此日日記只記錄了帶祖望到滬江大學訪問詹森教授,請其檢測祖望的英文學習情況,并無顧頡剛到訪記錄。⑨胡適:《胡適全集》(31),第453—454 頁。
從顧頡剛的行程來看,從3月到9月,他先后共五次拜訪胡適,分別為3月2日、3月20日、7月4日、8月16日和9月7日,其中三次在上海,兩次在蘇州。此段時間,顧頡剛的日記從未間斷,對自己的行程和日常事務,從會客訪友到家務瑣碎,悉有記載。顧頡剛生性敏感,謹小慎微,不善處理人際關系,無論家庭或親朋,稍有矛盾和糾紛都會令他緊張不安,這也是其日記重點著墨之處。顧頡剛日記與胡適日記不同,完全是私人性的,故其情感思緒,甚至家庭矛盾和個人隱私,均可以從中察出。如果胡適真對他說過其不疑古而要信古,把他嚇出一身冷汗的話,此等“大事”,理應在其日記中出現。另外,此時胡適因“詆毀”國民黨成為打壓對象,日記極簡,且多為剪報。胡適對7月3日在蘇州游覽天平山的印象頗深,在日記中記錄了天平山的歷史風光,而對顧頡剛拜訪之事沒做任何記錄。①胡適:《胡適全集》(31),第411—414 頁。胡適此日日記時間為“十八,七,三”,疑為7月4日之誤,因前一篇是7月3日,后一篇為7月5日。從日記來看,此時兩人關系仍十分融洽,并非像顧頡剛晚年回憶所說開始產生裂痕。由于歷史原因,顧頡剛晚年所述很可能是為了撇清與胡適的關系。
對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兩人1929年之后的關系。1929年9月,顧頡剛的學生何定生編了《關于胡適之與顧頡剛》一書,頗有抑胡揚顧之意,“一時引得北平學界議論紛紛”。②王學典:《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第109 頁。這使顧頡剛甚感不安,生怕影響了他與胡適之間的關系。他一面斥責何定生,將其逐出師門,一面通知樸社停止發行該書,并寫信向胡適說明情況。同時邀請胡適到北平去他家小住,試圖消除胡適的疑慮。③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6—467 頁。可見,顧頡剛在處理與胡適的關系時非常謹慎。
1930年1月,顧頡剛致信胡適稱,“三個月前接來書,敬悉。那時盼望先生來北平,故未復。哪知到現在還未來”,并向胡適報告在燕大的情況。④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7 頁。4月,顧頡剛再次致信胡適,解釋前幾次沒有回信的原因:“所以然之故,一因討論《易傳》事,胸中頗有些意見,要寫出至少須費半天功夫,而半天功夫著實不易找到。二因《清華學報》囑我做一篇文字,那時擬定的題目是《五德始終說的歷史和政治》,當時想想,有一兩萬字也盡夠了,一個寒假也寫得完了。但一落筆之后,三萬四萬還寫不完,現在寫到了六萬字還不完,怕要十萬字了。這兩個月來的時間差不多全耗費在這研究上,很有可喜的發見。”⑤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8 頁。6月初,胡適到北平,“先后在北大、北師大等處講演”。⑥耿云志:《胡適年譜》,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第151 頁。由于燕京大學地處郊外,離城區較遠,顧頡剛得知后,寫信給胡適:“昨日錢玄同先生來,始知先生已到平四五日了。我很想立刻進城奉訪,可是今日有課,明日必送講義稿若干頁,這兩天無法進城。想擬星期六上午坐八點汽車到先生處,不知道那天先生有沒有空?請告我。”①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69 頁。相信胡適看到此信應能理解,對顧頡剛的忙碌感到欣慰,曾經辛勤誘掖的學生今已逐漸成熟,獨當一面。至于有人認為顧頡剛的成名掩蓋了胡適的光芒,而引起胡適不快,致使兩人產生罅隙,恐屬臆斷。
由于胡適聲望正隆,儼然青年之導師,顧頡剛多次應學生之請,致信胡適請求接見指導。1930年7月3日,顧頡剛在信中稱:“北大同學余譲之兄,今年在史學系畢業,茲就返湘之便,晉謁先生,特為介紹,請賜接見為幸。”并報告“《東壁遺書》序已著手,在暑假內必可寄滬,乞告汪孟鄒先生是感”。感謝胡適所贈朝鮮本《五倫行實》,“承囑勿過懷疑,自當書之座右”。同時,請求胡適為《燕京學報》賜稿,“只希望從《哲學史》稿中抽出一章就好了”。②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70—471 頁。
1930年11月底,胡適重返北京大學,任文學院院長。12月7日,北京大學研究所請顧頡剛為胡適四十歲生日作一篇壽文,顧頡剛因病無法應命。為此,顧頡剛特意寫信向胡適致歉:“前日研究所同人囑我作先生壽序,這是義不容辭的事,只為疾病所困,無法應命,歉仄之懷,如何可言。”并稱今后將加強“鍛煉身體”,“只要此后起居稍有節制,則先生五十壽辰時之論文及壽序,自當由我包辦也。先生布置新房,當需燈盞,茲謹送奉紗燈一堂,以應需要,乞哂收為感”。③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39),第471 頁。從上可知,兩人關系在1930年前后仍十分融洽。
二 學術觀點的差異與罅隙的產生
顧頡剛稱其與胡適之間產生裂痕,是因為在“觀象制器”和“《老子》成書年代”問題上觀點相左,使胡適“大為生氣”。然細察之下,此說很有疑問。1929年秋,顧頡剛作《周易卦卜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第6期),認為《易經》與《易傳》中的歷史觀念處于完全相反的地位,“《易經》中是片斷的故事,是近時代的幾件故事;而《易傳》中的故事都是有系統的,從邃古說起的,和這個秦漢以來所承認的這幾個人在歷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完全一致”。所以,“我們要把時代意識不同,古史觀念不同的兩部書——《周易》和《易傳》分開”。①顧頡剛:《周易卦卜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1929年第6 期,第1006 頁。此后,他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再次討論此問題,認為《易傳》“原來只是一部占卜的書,沒有圣人的大道理在內”,其作者絕不是孔子,也絕非出于一人之手。《系辭傳》中所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圣人“觀象制器”,即一切的物質文明都發源于《易卦》是錯誤的,“制器”時看的“象”乃是自然界的“象”,而不是“卦爻的象”,是后人把“制器”歸到了圣人伏羲、神農等頭上。因此,他得出:“那發揮自然主義的《易傳》的著作時代,最早不能過戰國之末,最遲也不能過西漢之末”;“《系辭傳》中這一章是京房或是京房的后學們所作的,它的時代不能早于漢元帝”。②顧頡剛:《中國上古史講義》,《顧頡剛全集》(3),第233—251 頁。
1930年2月1日,胡適讀了顧文之后,作了一封長信,與顧頡剛討論“觀象制器”問題。胡適在信中稱:“頃讀你的《周易卦卜爻辭中的故事》,高興極了。這一篇是極有價值之作。不但是那幾個故事極有趣,你考訂《系辭傳》的著作年代也很有意思,引起我的興趣。”他認為《系辭》出現甚早,“至少在楚漢之間人已知有此書”,“觀象制器”是一種文化起源的學說,“所謂觀象只是象而已,并不專指卦象,卦象只是象之一種符號而已”。胡適認為顧頡剛的看法不免苛責,“卦象只是物象的符號,見物而起意象,觸類而長之,‘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此學說側重人的心思智慧,雖有偏處,然大體未可抹殺。你的駁論太不依據歷史上器物發明的程序,乃責數千年前人見了‘火上水下’的卦象何以不發明汽船,似非史學家應取的態度”。他批評顧頡剛是“受了崔述的暗示,遷怒及于《系辭》,也不是公平的判斷。至于你的講義中說制器尚象之說作于京房一流人,其說更無根據。京房死于西歷前三十七年,劉歆死于紀元后二十二年,時代相去太近,況且西漢易學無論是那一家,都是術數小道,已無復有‘制器尚象’一類的重要學說”。最后,胡適強調:“以上所說,于尊作本文毫不相犯,我所指摘皆是后半的余論。至于本文的價值,此函開始已說過。我不愿此文本論因余論的小疵而掩大瑜,故草此長函討論。久不作長書,新年中稍有余暇,遂寫了幾千字,千萬請指教。”①胡適:《致顧頡剛》,《胡適全集》(24),第31—35 頁。
從信中可以看出胡適對顧文的肯定和贊賞,但并非完全贊同他的觀點。胡適此日日記載:“晚間讀顧頡剛的新作《周易卦爻中的故事》(《燕京學報》6),其中有論《系辭傳》中‘制器取象’的一段,引起我的注意,作長函和他討論,約二千多字。”②胡適:《胡適全集》(32),第598 頁。不難看出,胡適乃本著研究的興趣和學術批評的態度,與顧頡剛商榷,表達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顧頡剛亦坦然接受批評。此后,顧頡剛將講義連同與胡適、錢玄同的討論書信刊于《燕大月刊》(1930年第6 卷第3 期),并收入《古史辨》(第3 冊)中。據顧頡剛記述:“去年秋間作《周易卦卜爻辭中的故事》一文,刊入《燕京學報》第六期。作完了之后又發生了些新見解,因就編講義的方便,編入《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里去。適之玄同兩先生見之,皆有函討論。今以《月刊》索稿,即以講義原文及兩先生函件發表。”③顧頡剛:《論易系卜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燕大月刊》1930年第6 卷第3 期,第1 頁。此即顧后來所稱:“這篇文章在《燕大月刊》上發表后,我收到了錢玄同和胡適的來信,兩個人的態度完全不一樣,錢玄同認為‘精確不刊’,胡適則反對,說觀象制器是易學里的重要學說,不該推翻。前面說過,他從一九二九年起就不疑古了,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具體例證,也是我和他在學術史上發生分歧的開始。”④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顧頡剛全集》(1),第169 頁。事實上,胡適與之討論的是發表在《燕京學報》上的《周易卦卜爻辭中的故事》,而非《燕大月刊》之文。
另一問題是關于老子及《老子》成書年代,顧頡剛的觀點亦與胡適相左。此前,在老子和《老子》成書年代問題上,胡適與梁啟超、馮友蘭等有過討論。胡適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歷前五七〇年左右”;而孔子約“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歷紀元前551)”。⑤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胡適全集》(5),第233、252 頁。梁啟超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后,《老子》很可能是戰國末期作品。⑥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中華書局,1996,第57—58 頁。1930年12月,錢穆作《關于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認為孔子在老子之前。1931年3月22日,顧頡剛偕錢穆拜訪胡適,與胡適討論這一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早出;錢穆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后,《老子》晚出。①胡適:《胡適全集》(32),第92—93 頁。顧頡剛與錢穆觀點一致,認為孔子在老子之前。1932年4月,顧頡剛作《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刊于燕京大學《史學年報》。1933年1月,胡適作《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批評梁啟超、錢穆和顧頡剛等人的觀點,認為他們提出的證據難以證明《老子》晚出。尤其是顧頡剛的文章,他認為考證還不夠嚴謹,存在“斷章取義”、“強為牽合”等問題,以構造“時代意識”來證明《老子》晚出的方法是很危險的。胡適稱自己“并不反對這種懷疑的態度;我只盼望懷疑的人能舉出充分的證據來,使我們心悅誠服的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書移后”。他強調自己的辯駁是充當“魔的辯護士”,“我攻擊他們的方法,是希望他們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評他們的證據,是希望他們提出更有力的證據來”。②胡適:《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適全集》(4),第114—139 頁。
學術批評者,指其正,辨其謬,商榷異同。民國時期學術批評風氣甚濃,這正是當時思想文化勃興的原因之一。如胡適與蔡元培私交甚篤,但并不認同他的《紅樓夢》研究。“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并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③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第3509 頁。兩人在探討和爭論中將《紅樓夢》研究推向縱深。陳垣稱:“文成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惜胡、陳、倫諸先生均離平,吾文遂無可請教之人矣。”④陳垣:《致陳樂素》,陳智超編《陳垣往來書信集》,三聯書店,2010,第1109 頁。此“諍友”顯然是指胡適,兩人作文常請對方批評“指摘”。胡適有“好爭”之名,在學術上有股較真勁,凡事要爭個水落石出。多年后,他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修訂后記中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直到今天,還沒有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把老子這個人和《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后期去”。⑤胡適:《 〈中國古代哲學史〉 臺北版自記》,《胡適全集》(5),第540 頁。后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和《黃帝書》則進一步證實了胡適的觀點。
胡適主張思想和言論自由,其所論乃正常的學術批評,并非如顧頡剛所稱“不加考慮,一口拒絕”,把他“痛駁一番”,“從此以后,他就很明顯地對我不滿起來”。⑥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顧頡剛全集》(1),第170 頁。此系顧頡剛后來的說辭,不足為憑。另據錢穆晚年回憶,胡適之文并非針對顧頡剛,“適之后為文一篇,專論老子年代先后,舉芝生頡剛與余三人。于芝生頡剛則詳,于余則略。因芝生頡剛皆主老子在莊子前,余獨主老子書出莊子后。芝生頡剛說既不成立,則余說自可無辯。然余所舉證據則與芝生頡剛復相異,似亦不當存而不論耳。但余與芝生頡剛相晤,則從未在此上爭辯過。梁任公曾首駁適之老子在孔子前之主張。在當時似老子出孔子后已成定論。適之堅持己說,豈猶于任公意有未釋耶”。①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2010,第152 頁。
但兩人的關系在1931年之后確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31年5—8月,顧頡剛多次致信胡適,均未得到回復。9月7日,顧頡剛再次致信胡適詢問是否有“開罪之處”,因“連上數函,迄未得復,甚為惶恐。未知是我有開罪先生呢,還是有人為我飛短流長,致使先生起疑呢?如有所開罪先生,請直加斥責,勿放在肚里”。②顧頡剛:《致胡適》,《顧頡剛全集》(45),第560 頁。從兩人書信中未見胡適對此信做出回應,顧頡剛所說的“裂痕”很可能是指此事。但從胡適致錢玄同信來看,兩人之間似乎又不存芥蒂。1932年5月10日,胡適在致錢玄同的信中稱:“頡剛的信使我很高興,姚立方的遺著的發現,是近代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不單是因為姚氏的主張有自身的價值,并且這事可以表示近年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明顯的傾向。這傾向是‘正統’的崩壞,‘異軍’的復活。在思想方面,李覯、王安石、顏元、崔述、姚際恒等人的抬頭,與文學方面的曹雪芹、吳敬梓的時髦是有同一意義的。”并詢問“頡剛何時回來?杭州住址何處?”請求錢玄同告知。③胡適:《致錢玄同》,《胡適全集》(24),第118 頁。1933年4月26日,胡適到燕京大學演講,顧頡剛陪同,并為之主持。④顧頡剛:《顧頡剛全集》(46),第38 頁。但此后兩人關系確有“遇冷”現象。12月17日是胡適的生日,只要條件允許,他都會接受拜訪并宴客,賓客中自然少不了顧頡剛。1933年12月17日,胡適日記寫道:“朋友來賀生日者,上下午都有人;我每年都備酒飯,但不發帖請客;朋友上午來的,則住留吃面;下午來的,則留住吃晚飯。今天來的約有五十人。”⑤胡適:《胡適全集》(32),第247 頁。而此日顧頡剛在家中“校《古史辨》”,⑥顧頡剛:《顧頡剛全集》(46),第123 頁。沒有參加胡適生日宴會,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但是,12月30日,燕京大學國文系同學會舉行年終聚餐,托顧頡剛邀請胡適參加,胡適應約。⑦胡適:《胡適全集》(32),第247 頁。
從兩人日記和書信來看,很可能是胡適對顧頡剛疏遠,但原因不一定是學術觀點的差異。胡適提倡思想言論自由,主張容忍異見,從當年與梅光迪、任鴻雋等爭論到“劍拔弩張”時關系尚未破裂,如因學術觀點不同而對顧頡剛和錢穆“懷恨在心”,則厚誣了胡適的度量。顧頡剛晚年回憶顯然夸大了他與胡適之間的分歧,刻意制造了兩人的“矛盾”,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好像因為學術觀點的不同,兩人早在1929年之后便已分道揚鑣。究其個中原委,故是時代使然,但我們不應將此視為兩人產生裂痕的原因,更不能以此認為胡適的疑古思想發生了轉變。有人以胡適在老子問題上的態度作為他信古的證據,事實上胡適的疑古并非推翻全部歷史,而是疑其不實之處。同樣的例子還體現在《四十二章經》和《牟子理惑論》真偽之爭上,胡適與梁啟超等人觀點相反,認為兩經系真。對此,有學者認為:“往往被人們認為傾向于‘疑古’的胡適,在早期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卻是相當‘信古’。”①葛兆光:《“聊為友誼的比賽”——從陳垣與胡適的爭論說到早期中國佛教史研究的現代典范》,《歷史研究》2013年第1 期。其實,胡適在早期佛教史研究中并不“信古”,只是不全疑古而已。
胡適對顧頡剛的疏遠另有隱情,雖然具體原因無從得知,但有一點或許有助于了解兩人的疏離。顧頡剛在成名前追隨胡適,無論是學術還是生活上,胡適均給予極大幫助。后來,隨著名氣的擴大和經濟的獨立,尤其是因《古史辨》聲名鵲起后,顧頡剛逐漸擺脫對胡適的依賴,開始出現驕傲情緒。胡適曾勸他不要有驕傲之心,但他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顧頡剛自我意識較強,其“到一處鬧一處”的性格更是聲名在外,當洪業與他談起此事時,顧頡剛認為那是別人詆毀自己。②顧頡剛:《顧頡剛全集》(45),第505—506 頁。顧頡剛無論在北京大學,還是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以及后來到燕京大學,不僅對傅斯年,甚至對性情溫和的陳垣也頗有微詞。成名后的顧頡剛確實表現出驕傲之情,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明顯察出。雖然顧頡剛知道別人對自己“飛短流長”,但并沒有認真反思,每當感到胡適對他表現冷淡或疏遠時,便認為有人在背后搗鬼,蓄意破壞。
1937年,胡適赴美出任駐美大使,兩人聯系一度中斷。1946年7月,胡適使美歸來,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及史學會舉行的歡迎會上,顧頡剛逢場必到,并欲編纂《胡適文存》續集,籌備胡適六十大壽紀念文集。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4月6日,顧頡剛“到上海銀行,送適之先生西行”。他在日記中不無傷感地稱:“適之先生來滬兩月,對我曾無一親切之語,知見外矣。北大同學在彼后面破壞我者必多,宜有此結果也。此次赴美,莫卜歸期,不知此后尚能相見,使彼改變其印象否。”①顧頡剛:《顧頡剛全集》(48),第440 頁。顧頡剛的憂慮不幸言中,從此兩人再也沒有相見。多年后,當胡適在美國看到顧頡剛的批判文章時,非但沒有指責,反表現出理解和同情。②1952年1月3日,胡適在香港《大公報》上看到顧頡剛的《從我自己看胡適》,將其作為剪報收藏在日記中,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對什么。……我本是跟著他走的,想不到結果他竟變成反對我”下面加上著重號。胡適:《胡適全集》(34),第158 頁。
顧頡剛晚年因環境所迫,不得不與胡適劃清界限。從《 〈古史辨〉 第一冊自序》(1926)到《我的治學計劃》(1950),再到《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979),可看出其對胡適由尊崇到省略的過程。顧頡剛稱引導他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姚際恒、崔述和鄭樵,而矢口不提胡適,并言當代學者中他最佩服的、真正引為學術上的導師是王國維,而非胡適。③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顧頡剛全集》(1),第157—162 頁。雖然顧頡剛多次向王國維表達仰慕之情,請求“許附于弟子之列”,④顧頡剛:《致王國維》,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第55—56 頁。但并未得到回應。王國維并不認同當時的疑古思潮,顧頡剛“心儀于王國維”,其實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研究方法,顧頡剛早期的治學方法和路徑都與王國維相去甚遠,而近于胡適。特別是在胡適大批判中,顧頡剛精神高度緊張,常“賴藥而眠”,⑤顧頡剛:《顧頡剛全集》(50),第662—666 頁。足見其內心的痛苦和恐慌。《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此影響。
三 從禪宗史研究看胡適疑古思想的一貫性
1930年前后,胡適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禪宗史方面,如《菩提達摩考》(1927)、《論禪宗史的綱領》(1928)、《 〈壇經〉 考之一》(1930)、《菏澤大師神會傳》(1930)、《神會和尚遺集》(1931)、《禪宗在中國之發展》(1932)、《 〈四十二章經〉 考》(1933)、《 〈壇經〉 考之二》(1934)、《楞伽宗考》(1935)等。胡適的疑古思想突出表現在對佛教疑偽經以及由偽經建構起來的偽史的質疑和考辨,也即顧頡剛所說的“辨偽書”和“辨偽事”。他從源頭上考證“西天二十八祖”的真偽、菩提達摩神話傳說故事的來源和發展演變過程、神秀與慧能的法統地位,以及神會的歷史作用等,認為從《楞伽師資記》到《付法藏因緣傳》,以及《壇經》、《寶林傳》、《曹溪大師別傳》、《五燈會元》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偽造和作假,凈覺開了惡例,神會大造,后人續之,從而“層累地”造成了佛教禪宗史。
1924年,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之初,即因對傳統燈史的懷疑而停止撰寫禪宗史,認為現存的禪宗史料大多數經過了后來和尚的竄改和偽造,故不可信。若要作一部可靠的禪宗信史,必須先搜求佛教早期史料,如唐朝的原料,而非五代以后被改造過的材料。1926年,胡適利用庚款會議之機,赴巴黎和倫敦查閱敦煌文獻,搜集到了大量佛教早期史料,基本證實了此前對禪宗史作偽的懷疑,從而提出了“捉妖”、“打鬼”說。①胡適在《整理國故與打鬼——致浩徐先生信》中把整理國故解釋成“捉妖”、“打鬼”。胡適關于整理國故前后不同的說法,曾引起研究者的頗多關注和討論。從此信的內容、時間以及胡適的前后活動上看,此時他對整理國故的態度突然轉變,把整理國故說成“打鬼”,很可能是因為敦煌佛教早期史料的發現,基本上印證了此前他對佛教禪宗史作偽的懷疑。1927年,胡適根據在巴黎和倫敦所搜集到的敦煌佛教早期史料,對比國內所存的佛教史料,特別是唐代以后的佛教史料,梳理和考證菩提達摩如何從簡單的歷史記載演變成復雜的傳說故事,逐漸被神化。他以菩提達摩會見梁武帝為例說明傳說故事由簡單到復雜、由模糊到清晰的演變過程,指出“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銷溶凈盡了”。②胡適:《菩提達摩考——中國中古哲學史的一章》,《胡適全集》(3),第326—329 頁。通過胡適對菩提達摩的考證,我們可以看到菩提達摩被神化的過程:由起自荒裔的波斯國胡人到南天竺婆羅門種,再到南天竺國王第三子,菩提達摩的身份越來越尊貴;從“初達宋境南越”到會見梁武帝,再到與梁武帝見面的具體時間和玄妙的對話內容,菩提達摩的教義越來越深奧;從折葦渡江到六次遇毒,再到只履西歸,菩提達摩的形象越來越神化。他認為菩提達摩的神話傳說故事“起于八世紀晚期以后,越到后來,越說越詳細了,枝葉情節越多了,這可見這個神話是逐漸添造完成的”。③胡適:《楞伽宗考》,《胡適全集》(4),第215 頁。胡適對史料和證據的選擇“以古為尚”,取敦煌佛教早期史料論證后期禪宗史的作偽,認為菩提達摩傳說故事是后人偽造的。
同樣的事情還體現在慧可傳說故事上。道宣《續高僧傳》中對慧可的記載較為簡略,僅說慧可在鄴傳教時,“深遭鄴下禪師道恒的嫉妒”,而《傳燈錄》、《慧可傳》中卻增添了許多故事情節。胡適認為:“《傳燈錄》全抄襲《寶林傳》(卷八)偽書,《寶林傳》改竄《續僧傳》的道恒為辯和,改鄴下為莞城縣,又加上‘匡救寺三門下’,‘邑宰翟仲侃’,‘百七歲’,‘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等等詳細節目,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其實全是閉眼捏造。七世紀中葉的道宣明說慧可不曾被害死,明說‘可乃從容順俗,時惠清猷,乍托吟謠’,然而幾百年后的《寶林傳》卻硬說他被害死了! 七世紀中葉的道宣不能詳舉慧可的年歲,而幾百年后的《寶林傳》卻能詳說他死的年月日和死時的歲數,這真是崔述說的‘世愈后而事愈詳’了!”①胡適:《楞伽宗考》,《胡適全集》(4),第220—223 頁。此即顧頡剛提出的“層累說”,所謂世愈后而事愈詳,傳說中的人物愈放愈大。
以此類推,胡適對禪宗的傳法世系、慧能的法統,以及《壇經》的作者等均提出了質疑和考證。他認為神會是一個善于編造謊言的專家,為了爭法統編造了許多故事,事實上,弘忍并沒有將“法衣”傳給慧能。“他是一位善于辭令的傳道家,又會編造生動的故事。許多關于達摩傳道的故事,如與梁武帝見面和二祖斷臂求道等,起初皆系由他編造,而后加以潤色,才混入中國禪宗史的整個傳統歷史之中。”②胡適:《禪宗在中國:它的歷史和方法》,《胡適全集》(9),第311 頁。胡適在與湯用彤討論“禪宗史綱領”的信中指出:“九世紀禪宗所認之二十八祖,與宋僧契嵩以后所認之二十八祖又多有不相同,尤其是師子以下的四人。其作偽之跡顯然,其中有許多笑柄。”③胡適:《論禪宗史的綱領》,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中華書局,1997,第35—38 頁。從他所擬的十三條禪宗史綱領中,可以看出其欲撰寫的“禪宗史”,實際就是一部疑經辨偽史。他認為不只是佛教經典存在偽造和作假,道教亦是如此,《道藏》幾乎完全是“賊贓”。陶弘景本人就是一個“大騙子”,《真誥》便存在有意作偽,“四十二章之中,有二十章整個兒被偷到《真誥》里來了”。④胡適:《陶弘景的〈真誥〉 考》,《胡適全集》(4),第176—177 頁。
禪宗史研究是胡適整理國故的一部分,受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的影響,他把佛教禪宗列為整理國故的對象,認為佛教的迷信思想和出世觀念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思想障礙,旨在“打破枷鎖,吐棄國渣”,實現“再造文明”的根本目的。而整理國故又與民國疑古思潮相關聯,整理國故本身就含有很深的疑古辨偽成分。根據胡適的解釋,整理國故是“以漢還漢”、“以宋還宋”,①胡適:《 〈國學季刊〉 發刊宣言》,《胡適全集》(2),第8 頁。“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②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全集》(1),第699 頁。那么,他對禪宗史的整理也是要還其“真面目”和“真價值”。在剔除了神化和傳說,還其本來面目之后,他得出禪宗的傳法世系是后人偽造的、菩提達摩傳說故事是后人編造的、慧能的法統是篡奪的、《壇經》是神會的偽作、佛教經典是故弄玄虛的騙人的“文字障”。撕掉了神秘的面紗,一切神奇和玄妙歸于平常。誠如梁啟超所論:“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許作為學問上研究之問題。一作為問題,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搖動矣。今不唯成為問題而已,而研究之結果,乃知疇昔所共奉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則人心之受刺激起驚愕而生變化,宜何如者?”③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第19 頁。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他把整理國故說成“捉妖”、“打鬼”的原因,聲稱整理國故可以“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④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胡適全集》(3),第146—147 頁。
1937年,胡適受命出任駐美大使,在禪宗史研究的黃金時期,戰爭打斷了原本的研究進程。⑤胡適:《致顧維鈞》,《胡適全集》(24),第380 頁。胡適原想“犧牲一兩年的學術生涯”,“至戰事一了,仍回到學校去”。⑥胡適:《致傅斯年》,《胡適全集》(24),第381 頁。但事實并非如他所料,胡適此去禪宗史研究中斷了十五年之久。1952年,胡適重新回到禪宗史研究上,其對禪宗史的懷疑和批判依然沒有改變。他在《口述自傳》中稱:“我個人雖然對了解禪宗,也曾做過若干貢獻,但對我一直所堅持的立場卻不稍動搖:那就是禪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團胡說、偽造、詐騙、矯飾和裝腔作勢。我這些話是說得很重了,但是這卻是我的老實話。”他把自己的禪宗史研究稱作“耙糞工作”,聲稱要“把這種中國文化里的垃圾耙出來”,“大體上說來,我對我所持的禪宗佛教嚴厲批評的態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橫蠻理論,認為禪宗文獻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偽作——這一點,我是義無反顧的。在很多(公開討論)的場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來充當個反面角色,做個破壞的批判家不可!”①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18),第386、422—423 頁。足見其態度之堅決。
學術實踐是學術思想的反映,兩者具有一致性。以往研究多根據顧頡剛的歷史敘述,從胡適方面出發尋找其疑古思想轉變的蛛絲馬跡,而忽視了顧頡剛敘述的歷史語境。考察胡適疑古思想轉變與否不僅要根據他人記述,更應根據胡適學術研究的具體實踐。根據20世紀30年代前后胡適學術研究情況,特別是禪宗史研究來看,其疑古思想并沒有發生改變。疑古不是對歷史的全部否定,胡適在一些問題上“信古”,不等于整體不疑古。懷疑和批判是胡適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征,伴隨他學術研究的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