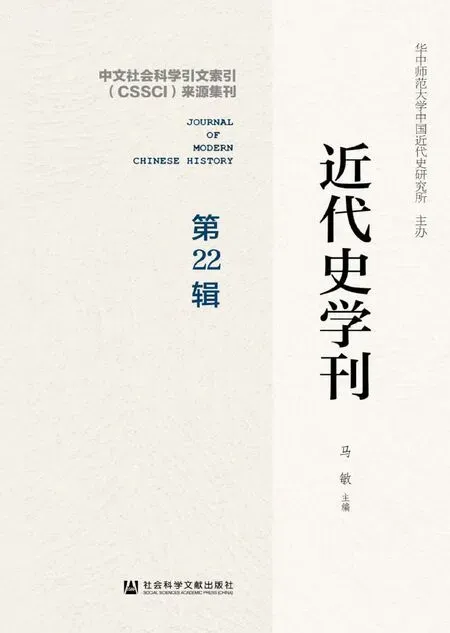從配角的視角重訪五四新文化運動
周月峰
一部電影除了主角之外,還需要有配角。塑造成功的配角,不僅本身具有鮮活的個性,并且常是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同時在關聯比較中,也能促使觀眾對主角有進一步理解。
歷史亦是如此,在具體的事件與運動中,有主角也有配角。即使是歷史中的絕對主角,也是處于周流變動的關聯性結構之中,有其一定的位置。如果只關注主角,而不留意配角,有可能會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困局,所看到的也就成了“獨角戲”。所以梁啟超主張用“合傳”,“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關系的人物,聚在一處,加以說明,比較單獨敘述一人,更能表示歷史真相”。然而,以往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便有時會有類似“獨角戲”的傾向。在研究中,我們比較多的注意到《新青年》與北大同人,這是無可非議的主角;只偶爾注意到他們的“敵人”,如林紓、學衡派或者安福系等,但常以反派的身份出現于研究中,有時甚至成了扁平的符號。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派是主角,安福系等是反派,那數量更多的大小、顯隱不等的配角,最被忽視。
有人統計,1919年的期刊有數百種,進入全國視野的期刊也有數十種,每一種或每數種背后便是一個新文化群體。正如余英時所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所構成”,“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沖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除去主角之外,其他五四方案都可以說是配角。其中,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等人(以梁啟超為核心的一個讀書人群體,以下簡稱“梁啟超諸人”)可以說是配角中最為重要的。如果降一格,以“梁啟超諸人”這一配角的視角重訪五四新文化運動,會不會有一些新的發現?我覺得可能有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讓我們有機會重訪一種被遺忘的聲音。
以往一些研究即使注意到這些配角,不少仍受整體論影響,心中有“新文化運動”的特定圖像,以此為標準,規范、選擇甚至裁剪其他方案與行動,削足適履,反而忽視了配角們自身新文化方案、實踐的獨特性,也沒有能進一步呈現他們展開“新文化運動”的故事。事實上,梁啟超這一派人想要做什么?他們做了什么?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梁啟超一派在當時所舉辦的文化事業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其一,辦報,包括《時事新報》、《晨報》、《國民公報》,尤其是它們的三種副刊,一般認為新文化運動四大副刊中,《學燈》與《晨報副刊》便占半壁江山。其二,創辦了五四時影響極大的《解放與改造》雜志。1919年前后在中國講學的杜威觀察到,當時有三份“發揮著重大影響”的刊物成為“新文化運動喉舌”,除了《新青年》、《新潮》之外,便是梁啟超一派的《解放與改造》。其三,成立共學社,出版“共學社叢書”。其四,成立講學社,邀請羅素、杜里舒、泰戈爾等人講學,曾形成一種講學之風,轉變學風,激起新潮。其五,接辦中國公學,創辦自治學院,梁啟超等人陸續講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等,在教育界成為一股重要力量。
他們不僅在思想界到處成為一種力量,背后又有一個大致清晰的新文化方案。他們的“新文化運動”分前后兩個階段:1918年底梁啟超、張君勱、蔣百里游歐,國內文化事業由張東蓀、藍公武主持,又以張東蓀為主導,這一狀況持續到1920年初;之后梁啟超、蔣百里歸國,親自主導他們的“新文化運動”,對此前的事業與方針均有重大調整。所以他們的新文化方案也可分為前后兩種:前期側重社會改造,“主張先改造一個新社會,由新社會的力量來刷新政治”;后期側重文化與政治,一面努力文化運動,一面“以政治運動與之輔行”。前期具有徹底的革命性,“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狀態”,“以為改造地步”,要來“一個真正的大革命”;后期則只強調“思想解放”。前期將改造事業分成“總解決”和之前“不是短期的”培養階段,在“大改造”之前的預備中,“以文化運動為最要”;后期不再提“總解決”。前期以社會主義為改造藍圖;后期強調“決非先有預定的型范”,基本放棄原先的社會主義改造趨向。在文化層面,前期主張從中西文化中解放,認為“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工夫”;后期雖也認同從中西文化解放,但又倡導傾向東方文化的“以復古為解放”。總體來說,他們前后都試圖創造一種既不同于中國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實現“再造文明”。
這是一個既有理念又有行動的群體,一度甚至讓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產生了被包圍的緊迫感,可見他們在當時的聲勢。并且這是一群典型的天下士,他們對當時的觀察以及對未來的思考,都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
第二,對配角的考察,為我們對五四新文化群體的了解增加了關聯比較的維度,既幫助我們理解配角,也能幫助我們理解主角。
以往關于梁啟超諸人的研究中,他們與《新青年》同人的關系,常常是被關注的重點,不過大多是一種“贊同”與“反對”的定性研究。其實,梁啟超一派有自己的新文化方案,他們的目的是實行他們的新文化方案,而不是為了“贊同”與“反對”《新青年》同人。
正因為他們前后期均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追求,方式、目標異于時流,故與其他方案時相沖突。比如他們前期側重社會,雖與國民黨人相近,但與胡適所主導的“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不同;即使是均側重社會,卻又因主張在預備期“少管小事”、“養精蓄銳”、“不要做零碎的犧牲”,而被運動中的學生及主張“去作大破壞與大建設的工夫”的國民黨人責難。他們后期的文化方案雖調整為多談思想、學術,卻因東方文化的傾向與《新青年》對立,又因放棄了社會主義及具有革命性的社會改造方案,而常與國民黨人及后來的共產黨人為敵。
整體來說,五四思想界是由《新青年》主導的,梁啟超一派想要進入思想界,就無法回避《新青年》的話題,在某種意義上,有追隨的一面。不過,他們雖然整體傾向于新派,但即使在追隨時,也常常有調節以《新青年》一派為主導的時代橫流的努力,白話文如此,在民主與科學之外強調哲學如此,其他如社會主義、整理國故諸方面也是如此。兩派之間的關系是追隨、角逐,又有調節。在面對舊的勢力時,他們都屬于新派陣營,但其實又潛伏著矛盾。正因雙方同在新文化運動之中,本有競賽,而新文化方案又有重要不同,且梁啟超他們常常想要調節后者,胡適一方才如臨大敵。這樣的關系,與其說是贊成或反對,不如說是兩種(多種)新文化方案的競爭。
第三,在配角與主角的競合關系中理解新文化運動的過程。
從配角出發,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配角(甚至主角),但這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故事的發生情況。梁啟超諸人因懷抱以自己的理想調節時代潮流,故在當時的思想界與其他勢力常處于時而追隨、時而競爭,時而合作、時而對立的交錯、動態的關系之中,深刻影響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走向。他們在競合中形成自己的主張,塑造自己的形象,又在互動中影響其他群體,最后又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整個新文化運動。
從這層意義來說,他們有沒有統一的藍圖,是否完成,都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對于作為整體的新文化運動的構成作用。作為配角的梁啟超等人不是整體新文化運動的外在對立物,也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獨立的一部分,而是參與整體的新文化運動創造的建設性力量,對于整體的新文化運動有構成性作用。他們參與了時代的思考,形塑了時代的思潮,在新文化運動風氣轉變過程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所以,被歷史記憶抹去的,也不只是他們的文化觀點與作為,更重要的是抹去了他們的這一構成性作用。
總之,將主角、配角或反派一起納入思考,其意義在于為歷史提供一個更原生態的舞臺,這樣才能使得新文化運動真正回歸于歷史,我們的研究才能盡可能體現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并且讓讀者看到文化運動者如何“運動”,在當時各方的互動中展現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發展進程。這樣也就改變了我們看待新文化運動的眼光,從考察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把它當作一個靜態的東西,轉向將新文化運動當作一個過程。如果以“成竹在胸”之畫竹為喻,我們要畫之竹,不只是希望畫出已成之竹,更希望將竹子破土成筍、在風雨與陽光中的成長過程和生命歷程一并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