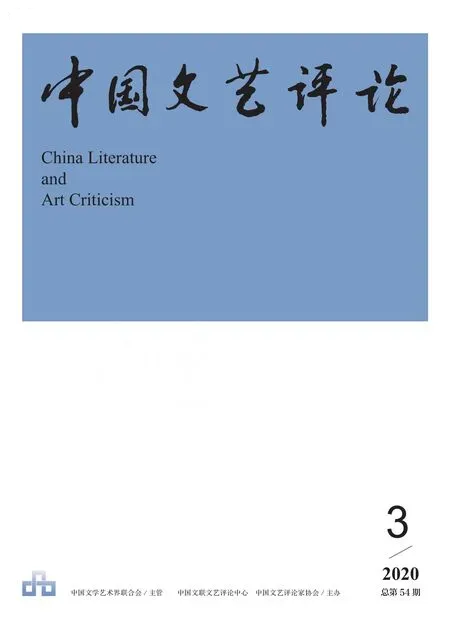柯軍:昆曲不分傳統(tǒng)和當(dāng)代
采訪(fǎng)人:張之薇
作為江蘇省昆劇院第三代傳承人,昆曲表演藝術(shù)家柯軍早年師從張金龍、白冬民、侯少奎,后為昆曲“傳字輩”鄭傳鑒入室弟子,又受到周傳瑛、包傳鐸等前輩傳教。工武生、兼文武老生。第二十二屆中國(guó)戲劇“梅花獎(jiǎng)”榜首,現(xiàn)任江蘇省演藝集團(tuán)藝術(shù)總監(jiān)。其昆曲折子戲代表劇目有《夜奔》《云陽(yáng)法場(chǎng)》《對(duì)刀步戰(zhàn)》《沉江》《闖界》等,新編昆劇代表劇目有《宦門(mén)子弟錯(cuò)立身》《顧炎武》等。2004年以來(lái),他在傳統(tǒng)昆曲的表演和創(chuàng)作之余,進(jìn)行了一些實(shí)驗(yàn)性的探索,開(kāi)始了先鋒昆曲的創(chuàng)作,主演并導(dǎo)演了《余韻》《浮士德》《新錄鬼簿》、實(shí)驗(yàn)版《夜奔》、中英版《邯鄲夢(mèng)》《319·回首紫禁城》等一系列作品,逐漸樹(shù)立起“最傳統(tǒng)、最先鋒”的昆曲藝術(shù)觀(guān)念。他還長(zhǎng)期致力于昆曲的現(xiàn)代傳播,在任江蘇省昆劇院院長(zhǎng)期間創(chuàng)建了昆曲網(wǎng)站“環(huán)球昆曲在線(xiàn)”,使江蘇省昆劇院所有演出和重要藝術(shù)活動(dòng)均能通過(guò)網(wǎng)站進(jìn)行直播,擴(kuò)大了昆曲的傳播面和吸引力。

圖1 昆曲表演藝術(shù)家柯軍
2017年,我偶然在北京大學(xué)百年講堂看了江蘇省昆劇院(以下簡(jiǎn)稱(chēng)“江蘇省昆”)版的《桃花扇》,看罷這部已經(jīng)演了30年的江蘇省昆保留劇目,讓我有種難抑的興奮感。演出中的《沉江》一折,實(shí)為孔尚任“借別離之情,寫(xiě)興亡之感”的點(diǎn)題之筆,卻讓我在以生旦為主,強(qiáng)調(diào)婉約靜雅的昆曲中發(fā)現(xiàn)了陽(yáng)剛之美、英雄之氣,以及昆曲別樣的氣質(zhì),從那時(shí)起昆曲在我心中有了更廣闊的維度。之后有幸與柯軍老師合作,便有了更多的交流。他告訴我,昆曲本身是文人的藝術(shù),是優(yōu)雅的文學(xué)和精致藝術(shù)的高度融合,昆曲素有“十部傳奇九相思”之說(shuō),的確是以男女愛(ài)情為主。但真正能夠留得下的經(jīng)典作品,如《長(zhǎng)生殿》《桃花扇》等,本質(zhì)上還是關(guān)注人的命運(yùn),關(guān)注人的。即使是寫(xiě)愛(ài)情,也是透過(guò)愛(ài)情來(lái)表現(xiàn)文人更深層的家國(guó)情懷,即通過(guò)江山更迭、國(guó)破家亡來(lái)表達(dá)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傷感和悲愴,表現(xiàn)人面對(duì)社會(huì)變遷時(shí)無(wú)法掌控自己命運(yùn)的無(wú)力。昆曲很多作品的內(nèi)容其實(shí)是豐厚和深刻的,單純用小生和旦的花前月下來(lái)涵蓋昆曲的唯美其實(shí)是偏頗且淺薄的。更何況,昆曲的樣式分南曲和北曲,無(wú)論是唱腔還是音樂(lè),既有南曲的婉約細(xì)膩,善于抒情;也有北曲的高亢、激昂、悲愴,富有張力,善于敘事。昆曲本來(lái)就不是單面樣貌的。他說(shuō)他希望自己在昆曲創(chuàng)作的格局上更大些,不僅能夠洞悉其中的文人氣質(zhì),也能洞察人內(nèi)心更為豐富的情感表達(dá)。他也希望要常懷悲憫之情,讓昆曲從表演和人物內(nèi)心上體現(xiàn)出屬于昆曲的精致性和典范性。
用作品表達(dá)我心中的昆曲精神
張之薇(以下簡(jiǎn)稱(chēng)“張”):2004年您開(kāi)始了對(duì)先鋒昆曲的探索,對(duì)傳統(tǒng)昆曲舞臺(tái)觀(guān)念有極大顛覆性,這樣的探索是機(jī)緣使然,還是主動(dòng)追求?
柯軍(以下簡(jiǎn)稱(chēng)“柯”):是不是有顛覆性我不敢說(shuō),只是當(dāng)時(shí)參加了由香港導(dǎo)演榮念曾老師策劃的香港國(guó)際獨(dú)角戲展演,因?yàn)槭仟?dú)角戲,自然想到了我常演的《夜奔》。當(dāng)時(shí)榮老師說(shuō)最好有一點(diǎn)新意,但我說(shuō)我是不會(huì)創(chuàng)新的。所以在整個(gè)排練過(guò)程中,我請(qǐng)音樂(lè)老師幫我重新做了配器,錄音后我就去香港演出了。那次國(guó)際獨(dú)角戲展演的觀(guān)眾都是奔著實(shí)驗(yàn)戲劇來(lái)的,但我演的傳統(tǒng)昆曲《夜奔》也征服了他們。當(dāng)時(shí)我就想,傳統(tǒng)既然這么好,為什么還要?jiǎng)?chuàng)新?也讓我體會(huì)到,傳統(tǒng)戲曲應(yīng)該多深入到實(shí)驗(yàn)戲劇觀(guān)眾群體中,這樣就可以爭(zhēng)取到更多這類(lèi)的觀(guān)眾。之后臺(tái)灣“當(dāng)代傳奇劇場(chǎng)”與香港“進(jìn)念二十面體”聯(lián)合舉辦了“‘獨(dú)當(dāng)一面’——兩岸三地戲曲藝術(shù)節(jié)”。藝術(shù)節(jié)邀請(qǐng)了越劇演員趙志剛、川劇演員田蔓莎等中國(guó)大陸的戲曲演員參加,我是作為昆曲演員被邀請(qǐng)的。其參演要求就是每位演員要做一個(gè)傳統(tǒng)戲、一個(gè)創(chuàng)新戲。當(dāng)時(shí)的我雖然對(duì)創(chuàng)新很懵懂,但還是創(chuàng)作出了《余韻》。所以說(shuō),一開(kāi)始并不是我主動(dòng)要去探索或顛覆。
作為我先鋒昆曲的第一部作品《余韻》,其原型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折。《余韻》中的【哀江南】當(dāng)時(shí)是請(qǐng)的曲家王正來(lái)老師給我拍曲的,唱是比較蒼涼的。這個(gè)戲很少演,我想把《余韻》挖出來(lái)唱給大家聽(tīng)。在這個(gè)戲中我是素顏,穿水衣上場(chǎng)。水衣是傳統(tǒng)戲曲中演員與角色相連的衣服,是進(jìn)入角色的“密碼”,我成為了介于演員和角色之間的一個(gè)人物。可以說(shuō),水衣是貼在演員肉身,又附在角色靈魂上的“通道”。所以,我可以演角色,也可以演自己,由此就打通了演員與角色之間的隔閡和壁壘。角色說(shuō)的話(huà)都可以變?yōu)槲业男穆暎磉_(dá)我所要表達(dá)的一切。另外,沒(méi)有妝扮也是這部作品與傳統(tǒng)戲曲最大的區(qū)別,這在傳統(tǒng)戲曲舞臺(tái)上是沒(méi)有過(guò)的。雖然《余韻》中有不少藝術(shù)形式的混搭、組接,但我認(rèn)為主體還是昆曲。因?yàn)椤队囗崱返奈谋臼抢デ模~皆是按照孔尚任的《桃花扇》原著而來(lái),并沒(méi)有新加的詞,唱、念也是昆曲原來(lái)的腔格和韻味。昆曲的手眼身法步,以及昆曲的表現(xiàn)手段和氣韻還是主要的。
張:《浮士德》是您第二部探索性質(zhì)的作品,創(chuàng)作時(shí)您心態(tài)上有了什么變化?對(duì)昆曲的探索和實(shí)驗(yàn)有什么新的理解嗎?
柯:《浮士德》是我繼《余韻》之后的第二部實(shí)驗(yàn)作品。之前創(chuàng)作《余韻》時(shí),還是從清傳奇作品中取材,有中國(guó)傳統(tǒng)元素以及昆曲元素在里面,雖有突破,但還在整個(gè)傳統(tǒng)文化的框架里,沒(méi)有走太遠(yuǎn)。而《浮士德》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就是一個(gè)全新的創(chuàng)作了,因?yàn)闆](méi)有現(xiàn)成文本,也不可能去唱歌德《浮士德》的原文,更不可能去照搬《浮士德》在話(huà)劇、歌劇中的呈現(xiàn)。所以,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好在創(chuàng)作《余韻》時(shí)已有了一點(diǎn)點(diǎn)經(jīng)驗(yàn)的積累,特別是在打通我和我的角色這一方面。這部戲中的角色不是單一的,我可以不斷穿梭在不同的角色中,既可以演繹《浮士德》的故事內(nèi)容,也可以將自己的現(xiàn)實(shí)所想附著在角色之上。
當(dāng)時(shí)創(chuàng)作《浮士德》是和香港“進(jìn)念二十面體”合作的,對(duì)于藝術(shù)的多種表現(xiàn)形式我是樂(lè)于嘗試和探索的,覺(jué)得舞臺(tái)不僅僅是用來(lái)表演,還可以用來(lái)思考。實(shí)驗(yàn)創(chuàng)作讓我從原來(lái)所學(xué)的規(guī)范的戲曲動(dòng)作中解脫出來(lái),并為我所用,將演員的被動(dòng)創(chuàng)作轉(zhuǎn)為主動(dòng)創(chuàng)作,這對(duì)于當(dāng)代的戲曲演員來(lái)說(shuō)是很有益處的。創(chuàng)作讓我體會(huì)到了快感,可以直接表達(dá)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讓我更有信心。
其實(shí),我對(duì)浮士德的理解并不是很深,但我知道他是不斷地毀滅,不斷地再生,不斷地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從有我到無(wú)我,再?gòu)男∥业酱笪遥瑥挠鹑〉胶甏罄硐耄罱K他跳出“小我”框架,成就永恒的生命精神,這就是我理解的“浮士德精神”。盡管他人生有多面性,有被欲望和享樂(lè)操縱的時(shí)刻,但最終還是戰(zhàn)勝了自我,讓崇高的靈魂成為自己的追求。
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我并沒(méi)有局限于表現(xiàn)歌德筆下浮士德這個(gè)人物,也沒(méi)有力圖去體現(xiàn)里面的故事情節(jié),而是想通過(guò)浮士德表達(dá)我心中的昆曲精神。那就是:昆曲昨天的精華就是今天的傳統(tǒng),昆曲人要堅(jiān)守自己獨(dú)立的品格,從而讓昆曲具備不斷完善、不斷超越的力量。創(chuàng)作中,我用昆曲把“浮士德精神”、昆曲精神揉在了一起,希望運(yùn)用昆曲的元素來(lái)表現(xiàn)我心中的“浮士德精神”,并把我對(duì)昆曲處境與道路的思考熔鑄在浮士德這個(gè)人物之中。
在舞臺(tái)形式方面,我不想用多媒體占據(jù)舞臺(tái),因此就盡可能多運(yùn)用昆曲的、戲曲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手法。一開(kāi)始,浮士德為了換取青春出賣(mài)了自己的靈魂,簽下了賣(mài)身契。首先,在表演時(shí),簽了契約之后演員摘下髯口,從末行變?yōu)樯小w卓诘拇骱驼鋵?shí)在傳統(tǒng)戲里都有。例如,京劇《文昭關(guān)》中,伍子胥一夜白頭,進(jìn)睡帳換了三次髯口,從黑髯換到黲髯,再到白髯,表現(xiàn)須發(fā)一夜蒼白,烘托出人的精神變化。在《浮士德》中,髯口的變換達(dá)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觀(guān)眾每每都會(huì)有驚奇感。

圖2 昆曲表演藝術(shù)家柯軍
其次,說(shuō)到褶子的穿和脫,這在傳統(tǒng)戲里也有很多。比如,人中了狀元后,現(xiàn)場(chǎng)會(huì)有人拿著紅色官衣上場(chǎng),給主角穿戴上。《白羅衫》中徐繼祖詰問(wèn)養(yǎng)父后,養(yǎng)父自殺,此刻又有人報(bào)說(shuō)自己的親生父母到堂,其當(dāng)場(chǎng)加穿紅色褶子,而為了表達(dá)悲喜交集的情境,紅色的褶子被斜穿了一半,很好地表達(dá)出人物的情感。脫衣的運(yùn)用在傳統(tǒng)戲中也有。如《刺虎》中費(fèi)貞娥趁李過(guò)醉睡,當(dāng)場(chǎng)脫下蟒袍,拔刀刺殺。不過(guò)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和魔鬼梅菲斯特兩個(gè)人當(dāng)場(chǎng)同時(shí)互換褶子還是首創(chuàng),對(duì)方拿著彼此的袖子,一扯兩扯,把左手套在另一個(gè)人的右手中,就完成了換衣,表現(xiàn)出浮士德與魔鬼的兩個(gè)方面。扇子的運(yùn)用也是借助了傳統(tǒng)武戲《對(duì)刀步戰(zhàn)》中周遇吉和李洪基的步戰(zhàn)對(duì)打,我把其中的套路運(yùn)用到《浮士德》里。兩人的撕扯、對(duì)壘和相互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現(xiàn)了浮士德和自己心中的魔鬼爭(zhēng)斗、角力。最后在唱到“白駒過(guò)隙這一剎”時(shí),身體一邊慢慢旋轉(zhuǎn),一邊脫下穿了一半的紅褶子,然后再把黑色的褶子脫下來(lái)也抓在手上,最后紅褶子突然從黑褶子的袖子里滑脫到了地上,然后浮士德露出白色的水衣,慢慢離場(chǎng),讓紅色的褶子留在舞臺(tái)上。這一半紅一半黑寓示著浮士德在人鬼之間游走的復(fù)雜心境,也寓示著對(duì)光陰如梭無(wú)盡的嘆息。這些手段都是傳統(tǒng)戲曲里的手法,實(shí)在豐富,只要拿一點(diǎn)出來(lái)就夠用了。
從《余韻》到《浮士德》,是有比較大的進(jìn)步的。前者是獨(dú)角戲,比較簡(jiǎn)單,只有15分鐘,劇情也不復(fù)雜。到了《浮士德》,主題更加明確了,概念也清晰了,表演也更豐富了,特別是在唱腔上的實(shí)驗(yàn)性比較大,沒(méi)有按照傳統(tǒng)的曲牌體去譜曲,突破了曲牌體,只選擇了有昆曲韻味的唱,并加入了新的音樂(lè)配器和電聲。在傳統(tǒng)中既保留了原有的東西,也做了一些全新的嘗試,我個(gè)人感覺(jué)這次創(chuàng)作是有了一定的進(jìn)步。而且我認(rèn)為,用傳統(tǒng)戲曲表現(xiàn)心理沖突,是未來(lái)戲曲創(chuàng)作所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傳統(tǒng)戲曲不僅僅是演故事的,還要表達(dá)精神內(nèi)涵,注重表達(dá)人的靈魂。所以,以注重思想的、思辨的西方戲劇來(lái)適度影響我們的戲曲,讓我們的戲曲在精神內(nèi)涵上有所提升,是我的一點(diǎn)點(diǎn)追求。
做有主體創(chuàng)作意識(shí)的當(dāng)代演員
張:在很多先鋒昆曲作品中,您總以素顏出現(xiàn),素顏的意義是什么呢?
柯:妝扮了之后演員就可能成為了角色,素顏就是要把“我”放進(jìn)去。我可以不是劇中人,可以站在觀(guān)眾角度去旁觀(guān)、解讀;也可以是角色,為角色代言;同時(shí)我還可以是柯軍自己。除此之外,我還可以表現(xiàn)某種情感,比如糾結(jié)、悲壯;還可以去表現(xiàn)色彩,紅色、黑色、白色,情感的色彩;還可以表現(xiàn)人物,觀(guān)眾和我,時(shí)而打通或間離。我認(rèn)為,素顏就是一種抵達(dá)“最先鋒”的通道。
我雖然是一名昆曲的武生演員,但演戲之余,也在其他領(lǐng)域?qū)W習(xí)鉆研。比如我練習(xí)書(shū)法已有三十余年,書(shū)法已經(jīng)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作品《藏·奔》(2006年)中,就把書(shū)法與自己的昆曲創(chuàng)作進(jìn)行了融合。我感覺(jué)武生和書(shū)法之間有很多關(guān)聯(lián),其實(shí)這兩者都是傾向安靜的藝術(shù),只是表現(xiàn)形式不同。
武生的安靜是突出一個(gè)“定”字。第一,要有堅(jiān)定的方向。因?yàn)槲鋺蛑饕恐w語(yǔ)言來(lái)塑造人物,不僅僅只有情感、戲和表演,還有一套功法。這就要求武生必須通過(guò)不懈的堅(jiān)持,以堅(jiān)定的方向來(lái)完善自己、錘煉自己。第二,要有篤定的心境和神情。在表演武戲的過(guò)程中,即使身體運(yùn)動(dòng)是迅猛的,但心里必須是沉穩(wěn)的狀態(tài),呈現(xiàn)出的是穩(wěn)、準(zhǔn)、狠,所以必須篤定。第三,武生的功法要有確定性和規(guī)范性。武生的一套功法是前輩日積月累傳承下來(lái)的,比如走邊、起霸,其中都蘊(yùn)含著故事和內(nèi)涵。所以必須要按照規(guī)范來(lái)做,否則形式就僅僅成為了形式而失去了意義。第四,要有穩(wěn)定的氣息和亮光。要不斷地呼吸,才能夠調(diào)整自己的心跳和脈搏。哪一個(gè)轉(zhuǎn)身要呼,哪一個(gè)轉(zhuǎn)身要吸,哪里需要停頓,都是有穩(wěn)定安排的。至于穩(wěn)定的亮光,亮光就是閃光點(diǎn)、亮相。亮相之前的收和放也都要有穩(wěn)定的安排。這四個(gè)“定”,讓武生必須要保持挺拔安靜的狀態(tài),不能有心血來(lái)潮的隨意性,也不能有模棱兩可的恍惚,更不能有似是而非的游離,內(nèi)心只有靜和清醒才能有章法、有韻律。這和我寫(xiě)書(shū)法的狀態(tài)實(shí)際上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寫(xiě)書(shū)法的時(shí)候我是很安靜的,但內(nèi)心是極其震蕩的,字里行間都會(huì)和古人的心跡對(duì)話(huà),每一筆每一劃都用心體會(huì)。因此,寫(xiě)字時(shí)身體安靜,內(nèi)心卻澎湃,仿佛要呼喚古人的魂到筆下。武生則相反,身體動(dòng)、內(nèi)心靜。
昆曲是一種無(wú)形的書(shū)法,書(shū)法又是一種無(wú)聲的昆曲。昆曲之中的唱念做表與書(shū)法的正、草、行、隸、楷可以說(shuō)是相映成趣,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書(shū)法里的變化、節(jié)奏、濃淡、枯澀、起承轉(zhuǎn)合,與昆曲里的表演——唱念做表、強(qiáng)弱呼吸、收放、張力都是相得益彰的。所以在《藏·奔》這部作品中,昆曲與書(shū)法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意味著最好的融合,是我的生命儲(chǔ)存在劇場(chǎng)中的最好呈現(xiàn),也有著最多的自我感悟,對(duì)我的意義是很大的。
張:您對(duì)昆曲的傳統(tǒng)性與當(dāng)代性有什么樣的觀(guān)念和看法呢?
柯: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是今天我們自己給昆曲設(shè)置的界限。昆曲本是不分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的,在我看來(lái),昆曲藝術(shù)一直是講究當(dāng)代性的。比如《邯鄲夢(mèng)》里湯顯祖寫(xiě)盧生,就把張居正也寫(xiě)入戲中,用盧生和宇文融兩個(gè)角色來(lái)表現(xiàn)當(dāng)時(shí)的權(quán)臣張居正。孔尚任的《桃花扇》也以明末的“當(dāng)下”為書(shū)寫(xiě)對(duì)象。那么,究竟明代湯顯祖的《邯鄲記》是傳統(tǒng),還是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傳統(tǒng)呢?他們相隔了半個(gè)多世紀(jì)。昆曲,包括戲劇藝術(shù),只要作品能夠?qū)ι鐣?huì)、對(duì)人的內(nèi)心進(jìn)行挖掘,就是具有當(dāng)代性的。真正好的作品是不存在古今之界的。
正如在我的先鋒昆曲里,我不再演別人寫(xiě)好的“角色”,而是讓“我”成為了劇中人,我演我自己,自由出入于不同時(shí)空,化身各類(lèi)人物,變成了自由的、主動(dòng)的創(chuàng)作者。在作品《新錄鬼簿》中,我飾演商小玲這一角色是為了服務(wù)于演“我”,而不是“我”為角色存在。這強(qiáng)調(diào)了演員的主體意識(shí),突破了替劇作家代言的局限,直接讓演員在舞臺(tái)上表達(dá)自己的困惑、思索與感悟。從傳統(tǒng)昆曲的演員轉(zhuǎn)變?yōu)橛兄黧w創(chuàng)作意識(shí)的當(dāng)代演員,消弭了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之分。
在《新錄鬼簿》中,作為一名武生演員的我第一次挑戰(zhàn)了旦行。這之前我從來(lái)沒(méi)有扮過(guò)閨門(mén)旦。為了變身商小玲,我斷食三天讓體形清瘦一點(diǎn),貼片子,梳大頭,戴花,穿上湖綠色的絲綢褶子,借助這一身皮相,借助舞臺(tái)營(yíng)造的情境,我仿佛進(jìn)入了商小玲的情感世界里,觸摸到了她的內(nèi)心,甚至體會(huì)到了她那種將死的情緒。我一直很喜歡《牡丹亭》,喜歡戲中的杜麗娘生生死死,甚至為愛(ài)而死。所以我在扮演時(shí),好像感受到自己也死過(guò)了一回,感受到了自我怎樣在戲中又變成無(wú)我。只有達(dá)到這樣的極致程度才能讓演員為之癡迷,也能讓觀(guān)眾為之灑淚。作為武生,隔行如隔山,但作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我以這樣的方式,托體商小玲做了回杜麗娘,雖屬滄海一粟,卻獲得了關(guān)于人生和藝術(shù)的無(wú)盡感悟。
張:從傳統(tǒng)昆曲《夜奔》,到2010年完全顛覆傳統(tǒng)的實(shí)驗(yàn)版《夜奔》,您在表演中是如何跨越心理上的門(mén)檻呢?
柯:我從小學(xué)習(xí)武戲,但要演好《夜奔》,難度非常大,正所謂“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但我喜歡林沖這個(gè)人物,在他的身上有一種精神吸引著我。我知道《水滸傳》里的林沖和《寶劍記》里的林沖并不相同。昆曲《寶劍記》中的林沖性格并非逆來(lái)順受,而是有一種心懷天下的士子精神。昆曲《夜奔》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是一出不同尋常的折子戲,因?yàn)橛泻脦孜焕蠋煻冀踢^(guò)我。戲校開(kāi)蒙的時(shí)候,白冬民老師曾教過(guò),畢業(yè)之后又跟張金龍老師學(xué),之后又和“傳字輩”老師鄭傳鑒先生學(xué)了南派老生的《夜奔》,然后又在北方昆曲劇院向侯少奎老師學(xué)了北派的《夜奔》。除了林沖身上的士子精神,更多傳承到我身上的是這些老師對(duì)林沖這個(gè)人物的理解,除此之外,還有我自己對(duì)《夜奔》演繹的體悟。他們每一位演繹的林沖都不相同,集中到我一人身上之后,經(jīng)過(guò)發(fā)酵,產(chǎn)生了變化。林沖這個(gè)人物豐富的情感和先輩們的靈魂注入到我身上,最終產(chǎn)生的情感不同尋常。
演繹傳統(tǒng)版《夜奔》是很難的。作為演員,你的情感是通過(guò)林沖在抒發(fā),你的心力、體力都要為塑造林沖這個(gè)人物而全身心投入,演員是要死在角色身上的。但實(shí)驗(yàn)版《夜奔》是開(kāi)放的,層次比較豐富,演出的時(shí)候比較放松。因?yàn)闆](méi)有更多的伴奏和規(guī)則限制,發(fā)揮空間比較大,同時(shí)可以借助演員自身的情感體驗(yàn)來(lái)表現(xiàn)。人面對(duì)社會(huì)感受到的多種生命體驗(yàn),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和情感積蓄,都可以作為表達(dá)人物的借力。所以每一次表演都會(huì)有不同的體驗(yàn)和感受,實(shí)驗(yàn)版讓我活在了舞臺(tái)上。如果說(shuō)傳統(tǒng)版《夜奔》是我為林沖而死,那么實(shí)驗(yàn)版《夜奔》則是林沖讓我而活。
榮念曾老師導(dǎo)演的這版實(shí)驗(yàn)版《夜奔》,打碎了傳統(tǒng)《夜奔》的條條框框,對(duì)他的這種創(chuàng)作觀(guān)念,我是能夠理解的。2004年中挪建交50周年,榮老師和我合作了第一個(gè)版本的《夜奔》,那時(shí)我是執(zhí)行導(dǎo)演,在那版《夜奔》中榮老師就開(kāi)始運(yùn)用椅子和影子的關(guān)系了。舞臺(tái)上,椅子還是那把椅子,但椅子的影子就不再代表那把真實(shí)的椅子了。回到角色,林沖還是那個(gè)林沖嗎?柯軍還是那個(gè)柯軍嗎?榮老師的創(chuàng)作給我很多觀(guān)念上的思考。那時(shí)榮老師讓我素顏表演下半場(chǎng)的林沖,我是拒絕的。當(dāng)時(shí)的我堅(jiān)持前半段現(xiàn)代服裝,后半段還是要勒頭、上妝,認(rèn)為那樣才是《夜奔》,才是林沖,才能展現(xiàn)出昆曲演員的唱念做表,才具備昆曲精神。其實(shí),我和榮老師也一直在“夜奔”的狀態(tài)之中,他讓我反叛傳統(tǒng),我不答應(yīng),一直在抗拒反叛。就是這樣不知不覺(jué)地被他引著往前走,我不知道往前的方向?qū)Σ粚?duì),可就是往前走了……

圖3 實(shí)驗(yàn)版《夜奔》劇照
藝術(shù)融合帶來(lái)傳統(tǒng)與先鋒的辨證
張:榮念曾老師總以全新的視角去創(chuàng)作,實(shí)驗(yàn)版《夜奔》在演出中,字幕上打出“獻(xiàn)給所有的檢場(chǎng)們”一行字,讓作品成為了600年昆曲檢場(chǎng)人視角下的《夜奔》,是否正因?yàn)槿绱耍抛兊酶酉蠕h和現(xiàn)代?

圖4 實(shí)驗(yàn)版《夜奔》劇照
柯:可以這樣說(shuō)。這個(gè)作品中的貫穿角色是由我扮演的——一個(gè)中國(guó)傳統(tǒng)劇場(chǎng)中的檢場(chǎng)人,他們負(fù)責(zé)搬道具、接道具、打小鑼、催場(chǎng),等等。實(shí)驗(yàn)版《夜奔》中的這個(gè)檢場(chǎng)人不僅僅是古代的或當(dāng)下的人,而是假設(shè)他活了600年,一直在觀(guān)察著舞臺(tái)上的演出——每一出戲的開(kāi)始和結(jié)尾,每一天演出的開(kāi)鑼和結(jié)束,每一代昆曲人的上場(chǎng)和下場(chǎng)。他在舞臺(tái)的側(cè)幕觀(guān)察了幾百年舞臺(tái)上下的變化,看的是從明朝到清朝到中華民國(guó),再到新中國(guó),這一歷史變遷中的《夜奔》。作為見(jiàn)證者、親歷者的檢場(chǎng)人,看到了臺(tái)上和臺(tái)下的人們?nèi)绾稳ッ鎸?duì)磨難,迎接挑戰(zhàn)。因此,以檢場(chǎng)人作為創(chuàng)作視角是一個(gè)大膽的探索和實(shí)驗(yàn),當(dāng)時(shí)在昆曲中還沒(méi)有出現(xiàn)過(guò)以檢場(chǎng)人為主角的作品。
舞臺(tái)如果只用來(lái)表演別人的故事就有點(diǎn)太可惜了。實(shí)驗(yàn)版《夜奔》中,書(shū)房/舞臺(tái)其實(shí)是榮老師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的知識(shí)分子的情懷歸屬地。他把舞臺(tái)當(dāng)作書(shū)房,因?yàn)闀?shū)房是產(chǎn)生知識(shí)分子的地方,是文人思考和評(píng)議的地方。真正有力量的恰恰是文人拿起手中的筆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思考。所以,書(shū)房是榮老師對(duì)舞臺(tái)的再思考,他用了“一桌二椅”,讓舞臺(tái)回歸到文人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李開(kāi)先/林沖也是如此,劇中的角色李開(kāi)先就是林沖,因?yàn)槔铋_(kāi)先就是通過(guò)林沖來(lái)抒發(fā)他對(duì)朝廷和社會(huì)的思考。李開(kāi)先被貶官,所以他通過(guò)作品來(lái)表達(dá)對(duì)人生的思考,舞臺(tái)在這里成為了靈魂洗滌、思想升華的地方。
傳統(tǒng)昆曲《夜奔》里的林沖妝扮用了紅色大帶,在這部實(shí)驗(yàn)版作品中,紅色大帶的運(yùn)用通過(guò)實(shí)驗(yàn)變得更加豐富。楊陽(yáng)[1]實(shí)驗(yàn)版《夜奔》中的另一位主演,柯軍的徒弟。一開(kāi)始解開(kāi)紅色大帶,是在解開(kāi)一種束縛,掙脫一種桎梏,逃脫現(xiàn)實(shí),要斗爭(zhēng)。我再拿大帶時(shí),它可以代表一條路,是紅色的路、正確的路、革命的路,也可以是一條傷痕累累的血路,也可以是捆綁著每一個(gè)人心靈和軀體的絞索。那么,如何去掙脫這條鎖鏈,直面悲傷、痛苦、血淚?如何去轉(zhuǎn)換自己的思維方式?有的是茍延殘喘,有的是茍且偷生,也有的走上了叛逆之路、逃離之路,也可以像林沖這樣奔向他理想的反面。紅色大帶的寓意在這里變得深刻起來(lái)。
演出中的桌子來(lái)自于戲曲的“一桌二椅”。有了桌子就有了檢場(chǎng),就有了書(shū)房,就有了和椅子的關(guān)系;有了椅子就有了位子,有了位子就有了身份,桌子和椅子的關(guān)系就可以是一種審判的、談判的關(guān)系,也可以是交流的方式,也可以是權(quán)威。所以,桌子實(shí)際上指代書(shū)房的概念,代表了舞臺(tái)上“一桌二椅”的樣式。
演出中,圓月是變化的,一開(kāi)始清澈透明,然后漸漸烏云密布。圓是中國(guó)人情感的思維方式,可以體現(xiàn)中國(guó)文人空靈高蹈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影子。在劇中有大量的影子出現(xiàn),有椅子和影子的關(guān)系,有桌影框住了人物的關(guān)系,有寓意著人影遮蔽了人,人影指向人,人影抽打人,人影背叛人,等等。影子與物象的關(guān)系、虛與實(shí)的關(guān)系是這個(gè)戲中最出彩的地方,也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還有音效的運(yùn)用,如火車(chē)的聲音在那場(chǎng)戲中是表達(dá)送別自己的學(xué)生,但也可以是送別這個(gè)即將離去的時(shí)代。在整個(gè)戲中,導(dǎo)演把我們的唱和念幾乎都去掉了,只保留了一點(diǎn)兒。這是想通過(guò)肢體來(lái)擴(kuò)大語(yǔ)言的張力,包括動(dòng)作的能量。其實(shí),這也表達(dá)了知識(shí)分子面對(duì)時(shí)代產(chǎn)生的一種困境,這種感受不受具體時(shí)代所限,最具現(xiàn)代感。
應(yīng)該說(shuō)這部戲超越了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東方和西方的范疇。它對(duì)我最大的影響,是怎么樣把排練場(chǎng)的狀態(tài)呈現(xiàn)在舞臺(tái)上面。在排練場(chǎng)排戲的時(shí)候,人是可以真正進(jìn)入到角色里的。因?yàn)槟菚r(shí)候沒(méi)有觀(guān)眾,不需要演給觀(guān)眾看,可以全情投入。演員沒(méi)有化妝,只要把握人物的情感,將此注入到自己的身體中,就可以將自己的心和角色打通。在排這版《夜奔》時(shí),椅子怎么放、桌子怎么放、大帶怎么運(yùn)用,怎么面對(duì)楊陽(yáng)……這些都是在我演藝生涯中遇到的最深的碰撞,這樣的碰撞使我產(chǎn)生了一些共鳴,可以把不同人物的情感裝到里面去,也可以把不同時(shí)代人物的情感點(diǎn)注入進(jìn)來(lái),包括我自己身上的情感點(diǎn)也可以通過(guò)這個(gè)戲來(lái)傳達(dá)。
張:2016年是英國(guó)劇作家莎士比亞和我國(guó)戲曲家湯顯祖逝世400年的特殊歷史節(jié)點(diǎn),由您主創(chuàng)的中英版《邯鄲夢(mèng)》在2016年首演于英國(guó)倫敦圣保羅大教堂。您為什么會(huì)選擇湯顯祖的《邯鄲記》,而不是其他劇目?
柯:首先,《邯鄲記》是湯顯祖“臨川四夢(mèng)”中的最后一“夢(mèng)”,也是最深刻、最有哲學(xué)意蘊(yùn)、最關(guān)注當(dāng)時(shí)時(shí)代的一部作品,它的文學(xué)性、思想性,包括我們演出的藝術(shù)性都是很完美的。湯顯祖通過(guò)“黃粱一夢(mèng)”這一主題,道出了一種人生的哲學(xué),所謂超脫、一切即空等思想,我很認(rèn)同《邯鄲記》的精神內(nèi)涵。

圖5 中英版《邯鄲夢(mèng)》劇照
其次,促使我最終決定排《邯鄲記》是因?yàn)槲覀€(gè)人的表演藝術(shù)能力可以掌控這部作品。湯顯祖的“四夢(mèng)”中只有這一部劇是用正生、末的行當(dāng)來(lái)扮演,而且盧生這個(gè)人物比較復(fù)雜。早年我和鄭傳鑒、包傳鐸兩位昆曲“傳字輩”老師學(xué)過(guò)《云陽(yáng)法場(chǎng)》這場(chǎng)戲,2009年在排演《湯顯祖·臨川四夢(mèng)》時(shí)把《邯鄲記》其中一折《生寤》也排演了出來(lái)。有這兩場(chǎng)戲作為主干,我又把《邯鄲記》前面兩場(chǎng)《入夢(mèng)》《勒功》一起串成了一個(gè)小全本。第一折《入夢(mèng)》主要講盧生想做官、想飛黃騰達(dá),認(rèn)為仕途能體現(xiàn)人生最高的價(jià)值,之后通過(guò)不正當(dāng)手段得了狀元,做了大官。而后的《勒功》可以體現(xiàn)我的武戲功底,《云陽(yáng)法場(chǎng)》又有甩發(fā)、跪步等大量戲曲身段、動(dòng)作,載歌載舞。最后的《生寤》則是人生的感悟,是思想上的升華。所以我最終選擇了這個(gè)作品,這是一個(gè)慢慢剝離、梳理出來(lái)的結(jié)果。
中英版《邯鄲夢(mèng)》由我和英方導(dǎo)演合作完成。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英國(guó)導(dǎo)演對(duì)我的創(chuàng)作理念、創(chuàng)作方向和創(chuàng)作手法很認(rèn)同,同時(shí)他也很尊重我們傳統(tǒng)昆曲的演劇樣式。在中西兩種傳統(tǒng)演劇樣式的碰撞中,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的生命、愛(ài)情、死亡、情感等問(wèn)題通過(guò)碰撞啟發(fā)人的探討和思考。排練時(shí),我會(huì)把昆曲部分先排好,然后把英國(guó)導(dǎo)演請(qǐng)到南京來(lái)看我們的戲。看完后他就深深被我們的表演所折服,他沒(méi)想到昆曲藝術(shù)如此精彩。之后的排演過(guò)程中他都積極配合我。這個(gè)戲是在我構(gòu)思的基礎(chǔ)上達(dá)成了雙方的共識(shí),然后共同推進(jìn)完成的。
表演中,《云陽(yáng)法場(chǎng)》一折,由我扮演的盧生即將被殺時(shí),被皇帝叫刀下留人,然后引到莎劇《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讓麥克白去刺殺君王。此刻的盧生,實(shí)際上轉(zhuǎn)換成了莎劇里的麥克白。我手中的匕首因?yàn)榭謶值粼诹说厣希藭r(shí)我的右手高抬,眼睛看著掉落在地上的匕首,手始終在顫抖,并慢慢拿起匕首。記得英國(guó)演員當(dāng)時(shí)問(wèn)我,為什么不一下子把匕首拿起來(lái)?為什么手要顫抖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我告訴他們,我們的戲曲是講究虛擬和夸張的,不停顫抖的手是內(nèi)心慌張矛盾的外化。于是他們意識(shí)到原來(lái)中國(guó)戲曲可以通過(guò)這樣的表演來(lái)表現(xiàn)內(nèi)心,感到我們的表演方式很高級(jí),是需要觀(guān)眾通過(guò)想象完成觀(guān)看的。
創(chuàng)作時(shí)我們并不知道最終會(huì)是什么樣子,但在排練的過(guò)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越來(lái)越多的驚喜。英國(guó)導(dǎo)演時(shí)常會(huì)把莎劇片段放在與昆曲所表現(xiàn)內(nèi)容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比如在《云陽(yáng)法場(chǎng)》一折,當(dāng)他看到我在喝斷頭酒時(shí),就提出要增加一段莎劇《雅典的泰門(mén)》中的片段。因?yàn)檫@片段講述的是泰門(mén)平時(shí)樂(lè)善好施,家中常常設(shè)宴款待,但當(dāng)他落魄之后,所有人都離他而去,他感到了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當(dāng)他后來(lái)又發(fā)達(dá)了再次款待賓客時(shí),盤(pán)子端上來(lái)的不是酒,而是水。
張:中英版《邯鄲夢(mèng)》讓我們看到了傳統(tǒng)和先鋒的辯證性,中國(guó)昆曲傳統(tǒng)表演與英國(guó)戲劇傳統(tǒng)方式相結(jié)合,卻從傳統(tǒng)中“混搭”出一個(gè)全新的、極具當(dāng)代劇場(chǎng)性的作品,這是您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時(shí)的初衷嗎?
柯:是的。我認(rèn)為,國(guó)際文化交流不能僅僅停留在展示、炫耀的層面,創(chuàng)作是人與人之間的碰撞,交流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藝術(shù)家和藝術(shù)家之間只有通過(guò)作品的交流才能實(shí)現(xiàn)真正的對(duì)話(huà),兩國(guó)藝術(shù)家只有充分發(fā)揮他們各自的創(chuàng)造力,才有可能打動(dòng)彼此、吸引彼此,從而創(chuàng)作出一種全新的演劇樣式。
在我的藝術(shù)觀(guān)念中,沒(méi)有傳統(tǒng)、當(dāng)代,東方、西方之別,人與人之間的默契、洞察力,來(lái)自于相互的尊敬、學(xué)習(xí)和欣賞,不是彼此征服的關(guān)系。當(dāng)前我們對(duì)外文化交流中還存在一些問(wèn)題:不能換位思考,總是按照自己的思維定勢(shì)去揣摩別人,不具備真正的文化自信,缺少一份真誠(chéng)的水乳交融的心態(tài)。所以,雙方之間總隔著一層,用國(guó)籍的、地域的框定限制彼此。我想,《邯鄲夢(mèng)》這部作品的“新”,是“新”在了兩國(guó)藝術(shù)家真正的交融上,呈現(xiàn)出了一種既傳統(tǒng)又先鋒的藝術(shù)作品,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當(dāng)然,更多的是驚喜,尊重,是知道怎么去做文化交流才會(huì)更有價(jià)值。
回到昆曲創(chuàng)作的初始狀態(tài)
張:同樣是表現(xiàn)崇禎皇帝最后的一段時(shí)刻,您創(chuàng)作的《319·回首紫禁城》(2018年)與傳統(tǒng)昆曲《鐵冠圖》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柯:首先,戲劇結(jié)構(gòu)上有很大不同。《319·回首紫禁城》講述了崇禎在臨死之前的所思所想。該劇完全是根據(jù)崇禎內(nèi)心來(lái)結(jié)構(gòu)的,以意識(shí)流的形式推進(jìn),不是傳統(tǒng)戲曲一線(xiàn)到底的講述方式。這部戲劇情跳躍,其明確的指向就是一個(gè)字“殺”——朝堂上殺奸臣魏忠賢,殺忠臣袁崇煥,內(nèi)宮殺妻女、殺侍從,最后在煤山自殺。《鐵冠圖》則是一個(gè)純粹的昆曲,曲牌都是套曲,唱念做表法度嚴(yán)密。
其次,《319·回首紫禁城》采用一種回到排練場(chǎng)的形式,演員與角色之間可以隨意轉(zhuǎn)換,演員既可以是劇中的角色,也可以是生活中的自己。比如楊陽(yáng)既可以是崇禎帝朱由檢,也可以是演員楊陽(yáng)自己。袁崇煥、李自成等角色的扮演者皆是如此,不停轉(zhuǎn)換身份。劇中傳遞給觀(guān)眾的不僅僅是劇情,還有演員、人物、角色的互換所傳達(dá)出的寓意。演員也不只是塑造角色,而是通過(guò)角色來(lái)表達(dá)自己的情感。《鐵冠圖》中的舞臺(tái)樣式是傳統(tǒng)的“一桌二椅”,桌子、椅子可以指代不同的事物,可以是椅子、也可以是山。但是《319·回首紫禁城》中椅子的含義就更深了。從來(lái)沒(méi)有哪一個(gè)傳統(tǒng)戲中的椅子可以升到空中的,是我們賦予了它更多的寓意,并用舞臺(tái)的呈現(xiàn)讓這種含義更清晰。
《319·回首紫禁城》的外在形式給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極素與極簡(jiǎn)。最初的昆曲也是極簡(jiǎn)的,傳統(tǒng)戲里的服裝都比較素雅,舞臺(tái)上也只有一桌二椅,通過(guò)演員表演和劇本來(lái)體現(xiàn)人物情感,化妝也非常淡雅。所以極素與極簡(jiǎn)是我的先鋒昆曲的舞臺(tái)觀(guān)念,這不是我的創(chuàng)造,是讓昆曲回歸到昆曲最初的樣式中。

圖6 實(shí)驗(yàn)版《夜奔》劇照
除此之外,我還追求回歸到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的最初狀態(tài)。我之所以讓演員以黑衣、素顏登場(chǎng),一方面是可以讓演員隨時(shí)從角色中抽離出來(lái),隨時(shí)可以破除自己的行當(dāng)。讓行當(dāng)色彩消減,人物的貴賤、敵我身份消減,更多地變成人與人、演員與演員、演員與角色、古人與今人內(nèi)心直接的較量。另一方面是讓表演者的最初狀態(tài)能夠呈現(xiàn)出來(lái),讓昆曲演員的身段、表情能夠清晰地呈現(xiàn)在觀(guān)眾面前,就好像在排練場(chǎng)上排練一樣。排練場(chǎng)上最質(zhì)樸、最自然、最接近表演本真狀態(tài)的樣貌就是我認(rèn)為最鮮活、最生動(dòng)、最有力量的藝術(shù)。所以說(shuō),舞臺(tái)越是精簡(jiǎn),越能傳達(dá)出更為豐富的含義,這是我對(duì)舞臺(tái)的理解。
在《319·回首紫禁城》中,椅子不僅是布景,還承擔(dān)著劇中道具的角色。它既是崇禎的寶座、袁崇煥的枷鎖,也是崇禎最后自縊的象征。椅子與光影結(jié)合也是有意味的。李自成的影子踩著崇禎的椅子,象征了皇權(quán)的旁落。而最后迸裂的紅椅與幕布上完整椅子影子的對(duì)照,更有不可言說(shuō)之妙。椅子、影子都是有多重象征意義的。
視覺(jué)上我設(shè)計(jì)了三種顏色效果。整個(gè)舞臺(tái)只有三種顏色——“黑” “白” “紅”。黑的側(cè)幕、地幕,黑色的地毯,演員身穿日常生活中的黑色圓領(lǐng)衫,下身穿普通黑色彩褲,男角色腳下厚底靴的梆子也是黑色。五張椅子,四張是黑色的。空間的“黑”,體現(xiàn)在最后15分鐘全場(chǎng)的“停電”,臺(tái)上臺(tái)下一片漆黑,渾然一體,沒(méi)有古今,這是整部戲的魂,魂是看不見(jiàn)的。至于“白”,后半場(chǎng)的底幕是白色的,皇后自縊的白綾是白色的,崇禎自縊時(shí)綁在椅子上的綾子也是白色的,等等。還有“紅“,唯一一張?jiān)宜榈囊巫邮羌t色的,唯一一個(gè)女角色的彩鞋是紅色的,寶劍穗子是紅色的,最后蠟燭移動(dòng)時(shí)微弱的光也是紅色的。聽(tīng)覺(jué)上,有昆曲最純粹的唱念,演員通過(guò)行當(dāng)聲腔轉(zhuǎn)換來(lái)塑造人物,特別是在臺(tái)下觀(guān)眾席間清唱的歌謠,唱出了主題,細(xì)膩而悠遠(yuǎn)。
整個(gè)演出,沒(méi)有濃墨重彩、華麗妝扮,演員皆素顏登場(chǎng),只有腳上的厚底和彩鞋告訴觀(guān)眾,這可能是一出古代戲。為什么我非要堅(jiān)持素顏演出?因?yàn)槲蚁肟吹窖輪T的真面目;想聽(tīng)到演員發(fā)自靈魂深處的聲音;想感受演員剝離戲服后如何塑造人物的內(nèi)心;想了解觀(guān)眾能不能接受沒(méi)有傳統(tǒng)妝扮的演出。
其實(shí),傳統(tǒng)與先鋒是辯證關(guān)系。《319·回首紫禁城》的舞臺(tái)雖然很先鋒,但也在找回傳統(tǒng)昆曲的框架和美學(xué),回到昆曲創(chuàng)作的本來(lái)。不再是演員扮演人物,而是把自己放進(jìn)去直接表演,演員可以在臺(tái)下稱(chēng)為觀(guān)眾,觀(guān)眾也可以上臺(tái)參與表演。當(dāng)舞臺(tái)漆黑時(shí),煙霧彌漫全場(chǎng),觀(guān)眾席里六個(gè)來(lái)自不同方向的手電筒光線(xiàn)穿透煙霧,直射垂吊的白綾、冷冰冰的椅子和無(wú)路可行的崇禎。白綾纏繞捆綁著椅子,此時(shí)的崇禎已被抽離,他看著自縊的自己升上天空,使勁地拽住,寓意著自己無(wú)法擋住自己的黃泉之路。他手推椅子,椅子晃動(dòng)的光影在手電燈光的交錯(cuò)中虛虛實(shí)實(shí),產(chǎn)生多重疊影,紛亂而悲涼,造就一種臺(tái)上臺(tái)下融為一體的心理氛圍。這樣的處理是在探索一種先鋒昆曲的舞臺(tái)極簡(jiǎn)美學(xué),也是借當(dāng)代劇場(chǎng)尋找古典昆曲的美學(xué),但其實(shí)又是以傳統(tǒng)昆曲舞臺(tái)觀(guān)為出發(fā)點(diǎn)的。
關(guān)注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是昆曲非常擅長(zhǎng)的。我的先鋒昆曲就是把昆曲中最有價(jià)值的、最擅長(zhǎng)塑造人物內(nèi)心的段落運(yùn)用到創(chuàng)作中。在傳統(tǒng)昆曲中,如要演出林沖在背叛中內(nèi)心絕望與希望之間的煎熬、糾葛與痛苦,就要把這份內(nèi)心的悲涼、悲憤,帶著英雄之氣外化于演員的唱念做表中。所以不管是傳統(tǒng)昆曲還是先鋒昆曲,都是擅長(zhǎng)刻畫(huà)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都是人物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對(duì)話(huà)。而我的先鋒昆曲是傳承并延續(xù)傳統(tǒng)昆曲之后我個(gè)體藝術(shù)追求的產(chǎn)物,希望能夠與昆曲的未來(lái)有一點(diǎn)兒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