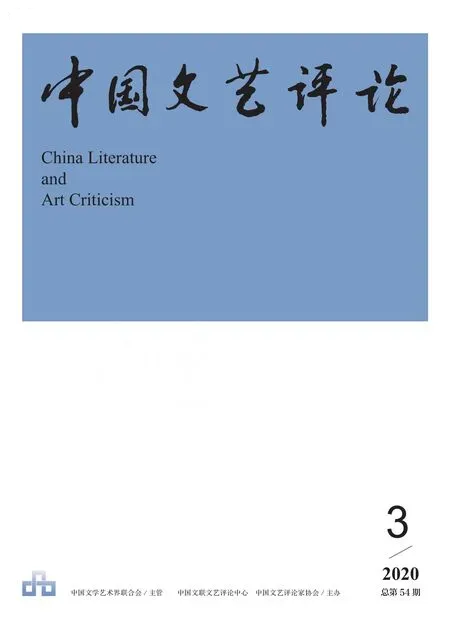藝術與科技融合視域下的未來“全才”反思
陳 靜
1832年,41歲的塞繆爾·摩斯遭遇了人生的一個拐點。這一年的10月,他結束了在歐洲兩年多的游歷,坐上了返回美國的海輪。他此時還不知道即將遇到的人將會改變他一生的命運。兩年多在意大利、瑞士和法國等各地臨摹大師畫作的經歷使他收獲頗豐,多少彌補了之前因為《眾議院》(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在商業上與口碑上的失敗所帶來的不甘與苦澀。尤其是在離開之前才剛剛完成大體初稿的《盧浮畫廊》(Gallery of the Louvre)更是凝結了他在巴黎宵衣旰食的創作心血,讓他離實現年輕時候的蓬勃野心:“成為重振15世紀繪畫輝煌、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和提香比肩之人”,似乎更近了一步。然而,在游輪上,摩斯不期而遇了查爾斯·托馬斯·杰克森(Charles Thomas Jackson),一位哈佛醫學院的優秀學生畢業。他向摩斯聊起了他在此前參加會議時獲取的有關電磁感應的信息[1]Kendall, Amos.Morse's patent, full exposure of C.T.Jackson's pretensions to the invention.Washington:Jno.T.Towers, 1852.,為摩斯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域。上岸之后,摩斯的生活開始了雙重的軌跡,一方面,他繼續繪制《盧浮畫廊》中的人物形象部分,并在1833年終于完成了作品;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尋求新的可能,創造一種可以進行遠距離傳輸的通訊方式。這種雙重任務最終的結果是畫作反響平平和摩斯密碼大獲成功。摩斯從此也建立了他的第二個“發明家”或者說“科學家”的身份。盡管有學者稱其為“十九世紀的達芬奇”,但與達芬奇作為不世之全才被全世界和各個領域所追捧相比,摩斯,尤其是作為藝術家的摩斯,遠遠沒有達芬奇那樣的身后榮光。不過,故事至此并沒有結束。當我們在對藝術家摩斯表示遺憾的時候,我們卻忽略了作為科學家的摩斯實際上也在他的科學研發中使用了藝術的眼光和方法。在1837年,他在測試第一個原型的時候,把藝術家的畫架改造成為了無線電信息的接收器,而信息接收本身是通過鉛筆在畫布上畫出波浪線來表示的[1]Lisa Gitelman, “Modes and Codes: Samuel F.B.Morse and the Question of Electronic Writing”, This Is Enlightenment, eds.Clifford Siskin, William War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120.。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思維轉化過程,摩斯實際上是以藝術家的思維方式,用視覺可見的書寫方式來表達/再現不可見的科學設想。此外,摩斯還巧用了他原本用于繪畫的瀝青顏料去作無線電設備電線的保護材料。盡管這種瀝青顏料在繪畫中實際上是會帶來一些不好的結果的,比如會讓畫作表面干裂或者起泡,但在電線保護上的表現卻還不錯。我們往往會將這種藝術與科技的結合視為一種“偶然”的巧合或者不期而遇的靈感印證。但事實上,經歷世事的我們也明白,沒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百分之百靠純粹的偶然所造就的,偶然的背后是一定的必然。然而有意思的是,盡管摩斯此后在無線電的事業上越走越遠,但他的《盧浮畫廊》卻并沒能如他預期的那樣帶來聲譽與財富。這幅承載了藝術家摩斯勃勃野心和巨大心血的畫作,不僅生動地模仿了40幅不同時期的、精心挑選的歐洲畫作,而且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在空間中精準呈現出來。這幅畫所承載的不僅僅是藝術家摩斯個人的藝術抱負和對歐洲藝術傳統的解讀,也體現了美國藝術發展的一個歷史節點,即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藝術家及相關社群開始有意識打造的以國家認同為基礎的美國藝術。可惜的是,這幅畫的命運卻頗為多舛。摩斯原本寄期望于的買家臨時打了退堂鼓,使他不得已另尋了以前相熟的買家友情購買。在此后的150年里,這幅畫并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甚至很少被展出,直到被一位意大利籍的美國化學家、企業家丹尼爾·J·特拉(Daniel J.Terra)以當年美國藝術家作品最高拍賣價購得,從而得以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范圍內巡回展出。

圖1 塞繆爾·摩斯 《盧浮畫廊》

圖2 塞繆爾·摩斯發明的電報接收機原型
摩斯的故事到此為止,但他作為個案卻很值得在有關“藝術與科技”議題的討論中被反復檢視。這是因為我們常常在宏觀的層面討論藝術與科技,會習慣性地延續查爾斯·斯諾(Charles Percy Snow)提及的《兩種文化》或者杰羅姆·凱根(Jerome Kagan)意義上的《三種文化》來看待科學、人文以及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強調三者之間在認識論、學科規范和知識體系建立和傳授上的分歧與共通,卻往往忽略了盡管藝術屬于“大人文”的范疇,但藝術并不純粹的等同于人文學或者社會科學:藝術更強調個體意義上的創造性實踐與審美性經驗,而其作為認識論和知識體系上的價值是通過對個人的系統培養,比如審美及素養訓練所完成的,而并不著力強調其在學科意義上的規范,也并不依賴于一定的學術共同體所達成的群體共識。相反地,藝術實踐活動、藝術評論及藝術研究、藝術史及理論研究以及相關領域(比如審美經驗研究)在不同但彼此交叉的領域中相互影響,因此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套用“兩種文化”或者“三種文化”來審視藝術與科技的關系,則會掉入已有的對立思維判斷,從而失去了一種對話的可能性。而“摩斯案例”之于本文的意義恰恰就在于打開了一種看待藝術與科技的另一種視角:從個體層面來看待藝術與科技融合的可能,并由此反思我們如何在創造、教育與研究中如何促進兩者的融合,從而實現新型“全才”的可能。本文通過數字藝術個案,尤其是人工智能及生成藝術來對這種可能性進行深入探討,以期能為我們思考藝術與科技的未來提供一種思路。
兩種還是三種文化?
1959年5月7日,英國物理化學家、小說家斯諾,在劍橋大學做了一場名為《兩種文化》的里德演講,引發了持續熱度的討論。此后該演講也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為題單本發行,在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廣泛關注。“兩種文化”也成為了討論科學與人文的一個通用術語,而被科學和人文學者所共同認可和接受,時至今日都廣為討論。
斯諾在這場講座中的核心觀點非常明確和清晰。他指出,作為知識界的兩大陣營,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往往老死不相往來,且互相“鄙視”,造成了現代社會的兩種文化,從而造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以及教育質量的下降。他特別提到:
兩種主題、兩種學科、兩種文化——或者更廣泛地說兩種星系的沖突應該能產生創造性的機會。在人類思維活動的歷史上,一些突破正是源于這種沖突。現在這種機會又來了,但是它們卻好像處于真空中,因為兩種文化中的人不能互相交流。20世紀的科學很少有被吸收進20世紀的藝術中的,這是令人不解的。……
我此前說過這種文化分裂不僅僅是英國的現象,也存在于整個西方世界。但是似乎有兩個原因使這種現象在英國更明顯。一個是我們對教育專業化的狂熱信仰,比起世界上東西方的任何國家都根深蒂固。另一個是我們傾向于社會形態的具體化。我們越想消除經濟不平等,這種傾向就表現得越強,而不是越弱,在教育上尤其如此。這意味著像文化分裂這種現象一旦建立起來,所有的社會力量不是促使其減弱,而是使它變得更僵化。[1][英]C·P·斯諾著:《兩種文化》,陳克艱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14-15頁。
斯諾確實觸及了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的核心問題,即現代制度下的學術共同體是有其社群壁壘的,換句流行語說,是有其鄙視鏈的。這種鄙視關系的形成并不是因為學術本身的高下,而是因為群體之間的不交流、不溝通以及不理解。斯諾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改革教育。他以美國為例來說明進行通識性教育的可能性。盡管斯諾認為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比英國做的更好,但實際上,美國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同樣嚴峻。美國哈佛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杰羅姆·凱根(Jerome Kagan)在50年后受到了斯諾“兩種文化”的啟發,撰寫了《三種文化》一書,對該命題進行新的闡釋。凱根認為斯諾的觀點已經顯得過時,首先是因為當代學術界的“游戲規則”已經發生了變化,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鄙視性關系并不僅僅建立在社群基礎上的認知困難之上,而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實體資源(比如理工科對機器以及經費的依賴)以及學科術語的專業化和內向化之上的。簡單來說就是學術資源的分配依賴于專業化及與之相配的排他性,相應地,學術地位的高下及專業壁壘的高低也取決于學術資源,尤其是外部資源的流入。因此凱根提到:
機器帶來了另外兩個問題。 其運營的高成本使得研究者需要聯邦政府和/或私人慈善機構的大量資助,只有少數幸運的研究者才能使用這些機器,從而做出重要發現。 因此,一個年輕的、有野心的科學家必須在正確的位置,才能享受這些神奇而有力的前沿優勢。 這種情況造成了少數特權研究者與對同一問題感興趣但無法觸及這些資源的大多數研究者之間的分歧。時至今日,在一個孤立的修道院里,一個僧侶在遺傳學上有重大發現的幾率比孟德爾試驗豌豆植物時的幾率低得多。
……
而那些選擇了哲學、文學或歷史的學者則遭遇了更嚴峻的打擊,因為他們不能為學校帶來數百萬美元的慷慨資助。而且,由于媒體影響,公眾已經接受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只能由自然科學家提供解決答案的說法。 所以當德里達和福柯等后現代主義者抨擊知識分子自己的家庭成員提出的主張時,人文主義者無法相互信任就變成了災難。[2]Jerome Kagan.The Three Cultures: Natural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p viii-x.
與此同時,凱根還提到了斯諾在《兩種文化》中徹底忽略了第三種文化,即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專業領域。同時他還明確指出,學術專業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其所用詞匯表的專業性,哪怕是同一個詞語,在不同領域中其意義也是不同的,而每一個學術共同體所使用的概念,其意義對于其研究方法而言都是獨特的。凱根還從九個方面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進行了差異性特征的總結。這九個方面包括“首要興趣”“證據來源與控制條件”“重要詞匯”“歷史條件影響”“倫理影響” “對外部資助的獨立性”“工作條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美的標準”。在凱根看來,這些方面決定了三種文化之間根本性差異[1]參見Jerome Kagan.The Three Cultures: Natural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無論是斯諾還是凱根,其對于兩種或者三種文化的討論,對于當下,尤其在中國當下的學術及教育語境中,有一定意義。比如我們在推崇專業化、精英化和學科化的同時,畫地為牢,為學術劃定了邊界與封閉空間,造成了交流上的障礙,乃至情感上的不信任;另一方面,當今社會也同樣面臨著高度專業化、分工化的問題,反向也為教育和學術研究本身提出了相應的人才培養要求,因此,雙向激勵機制下的教育在跨學科培養機制上就變得舉步維艱。而社會普遍接受的科學與人文價值觀有著長久的歷史根源,而對科學價值的單方面推崇和對人文價值的嚴苛審視都使得科學與人文在當代社會中受到了不一樣的對待。
藝術與科技的交融
然而,如果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斯諾與凱根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偏頗,最重要的就是對個體創造性,尤其是藝術創造性的忽略。非常有意思的是,斯諾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個案,因為他自己就是小說家,而他關于兩種文化的反思恰恰就是從他自身的經驗出發的:作為小說家的他與作為物理學家的他,同時與兩個不同的社群互動,白天不懂夜的黑。他自己恰恰是在個體的意義上實現了科學與藝術的融合之后,反過來對兩種文化、兩個社群產生了反思,這難道不是一種基于藝術實踐的創造性思維?
藝術實踐對于科學發展所具有的創造性幫助,其實也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曾獲1981年天才獎(麥克阿瑟獎)的麥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生理學教授及科學歷史學者羅伯特·魯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長期以來致力于關于創造性的研究。他在一項研究中追蹤了1958年至1988年的38位科學家,其中包括一些只發表過少量論文的科學家,以及四位最終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魯特-伯恩斯坦指出:“成功小組中排名倒數第三的所有人——最糟糕的一群——基本上都說有兩種文化,科學家、藝術家或文學界的人們無法互相交談。” 而“所有人中,無一例外,高層都說這很荒謬。”他還發現,不太成功的科學家傾向于將自己的嗜好視為逃避工作,而非常成功的科學家則將他們的所有創造性努力整合在一起,相互借鑒。 這似乎影響了他們如何思考自己的時間[1]Root-Bernstein, R.Etl, “Correlations Between Avocations, Scientific Style, Work Habits, and Professional Impact of Scientist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8 (2).pp.115-137.。他還在藝術與科技頂刊《萊奧納多》雜志上連續發文,以個案方式介紹這些將藝術與科學成功融合的全才們,比如獲得190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羅納德·羅斯(Ronald Ross)不僅在瘧疾的侵入機制與治療方法方面頗有建樹,同時還是一個非常卓越的詩人、聰穎的畫家和技藝精湛的音樂家[2]Robert Root-Bernstein, “Ronald Ross: Renaissance Man”, Leonardo, 43(2), 2010, pp.165-166.;而另一位1965年諾貝爾獲獎者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則受母親影響從而深愛繪畫與雕塑,而他自己則對藝術之于他個人科學研究的影響有著非常坦率而熱情的論述[3]Root-Bernstein, R., “Andre Lwoff: A Man of Two Cultures”, Leonardo, 43(3), 2010,pp.289-290.。
當然關于這樣的個案我們還可以找出很多,甚至還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的達芬奇以及之后的歷史長河中的很多不世之材。但這并不是我們此處所討論的目的和重點。魯特-伯恩斯坦所致力的,以及此處想討論的恰恰是這種成功個案在普遍性意義上的可能性。魯特-伯恩斯坦多年來一直在致力于創造力的研究及方法教育,他在《萊奧納多》2019年最新一期上分三部分刊登了他及團隊關于如何將適用于視覺、造型、音樂及表演藝術,手工藝及設計領域(藝術手工-設計[artscraftsdesign],簡稱ACD)的方法應用于并促進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及醫學(簡稱STEMM)的學習,以期解決以下三個問題:(1)ACD和STEMM可以有效地進行交互的方式是什么?(2)這些互動中哪些得到了深入研究?以及其有效性如何?(3)新方法可以輕松解決哪些差距(以及機遇)?(4)哪種方法可以用來生成關于有效ACD-STEMM交融的可靠數據?[4]Robert Root-Bernstein, Ania Pathak, and Michele Root-Bernstein, “A Review of ACD-STEMM Integration:Part 1&2”, Leonardo, 52(5), 2019, pp.492-495.相比較斯諾和凱根而言,魯特-伯恩斯坦的研究則更為具體和具有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立一種新的橋梁,致力于在兩/三種文化之間達成對話,以及進行實質性的交流。這個也是近年來國際學術及教育界在探討與推動的,如何將藝術融入傳統STEM(科學、科技、生物、醫學)的框架之中,從而形成新的STEAM框架的一個具體體現。魯特-伯恩斯坦還提出融合性人才的培養其實是可以通過一系列方法實現的,其核心是跨學科地發展能力以及培養審美素質和創造性能力,因此個體人才培養才是真正推動藝術與科技交融的可能突破點所在。
楊振寧關于“物理之美”的討論則從個人研究以及中國文化的角度指出了科學與藝術在物理學中的融合之美。他在形容狄拉克的物理學研究的時候,不僅引用了高適的一句詩,“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還特地進一步闡釋將之與性靈觀聯系起來:
……若直覺地把“性情” 、“ 本性”、“心靈”、“靈魂”、“靈感”、“靈犀”、“圣靈”(Ghost)等加起來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
剛好此時我和香港中文大學童元方博士談到《二十一世紀》1996年6月號錢鎖橋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1568—1610)(和后來的周作人[1885—1967] ,林語堂[1895—1976]等)的性靈論。
袁宏道說他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3)的詩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也正是狄拉克作風的特征。“非從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獨創性![1]楊振寧:《美與物理學》,《二十一世紀》總第40期。
楊振寧將“創造性”這個在西方18世紀才開始逐漸流行的觀念與中國性靈觀關聯,以此來探討狄拉克研究中所體現的簡潔、直接與直指人心的邏輯性,不僅是一種語言的妙用,也體現了科學與藝術之間在精神層面的互通,實際上也具有超越中西方文化語境的能力。同時,楊振寧還以自身的研究高度指出更高層面的科學研究必須要達到一種美感,這種美不僅僅是一種認識的美,更重要的是能夠體現一種未曾預料到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具有超越表象和事實,指向真理以及真理之上的美。如果我們再聯系到楊振寧與李政道兩位分享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宇稱不守恒理論也以優美著稱,或可以看到這種對科學之美的追求事實上不僅僅是一種語言層面上的感悟了。而李政道也同樣對科學與藝術有著獨到的見解,與許多著名藝術家交往廣泛而深入,以至于藝術家們如吳作人、李可染、吳冠中等大家都創作了具有“科學意味”的藝術作品。這從中國文化的層面為羅伯特·魯特-伯恩斯坦理論提供了有效論據和有力支撐。
近年來,數字藝術的出現和興起為藝術與科學的融合提供了一個更新、更為具體的語境。數字藝術是最具代表性的科技與藝術融合的創造性呈現方式。數字藝術體現了基于數字信號電路技術的數字技術作為新的媒介生成方式、生存條件與環境給藝術創作主體所帶來的新的可能。因為數字藝術生成的最基礎層面就在于數據及數據結構的構成形式上。換句話說,一定程度上,是數據特征及數據結構而非是藝術家單純的個人意愿決定了以什么樣的方式來描述需要被表達、被呈現的內容以及相應的審美趣味。同樣的,數字藝術的內容和形式構成所希望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建立一種內部關系就需要通過對數據及數據結構的設計來實現。與此同時,除了像集成電路、中央處理器、電線、網絡、屏幕、手柄、鼠標或鍵盤等物理硬件之外,數字藝術創作還包括了正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數據編程或者分析技術。盡管并不是所有的數字藝術作品都會涉及數據庫或者數據編程,有的只是直接使用了封包軟件生成內容,但無論哪種,只要是在數字處理系統中,都會涉及到機器語言、模擬語言和編程語言。尤其是編程語言,作為再現性語言,通過句法和表達邏輯來傳達思想。以C++語言為例,作為一種面向對象程序設計語言,在體現面向對象的各種特性的同時,盡可能的去貼近人對于語言的使用方式。它允許一種同等術語表達問題和結論,其語言結構執行了機器行為和人類認知之間的翻譯工作。海爾斯就指出,“這一革新的核心就是允許編程者表達自己對問題的理解,通過定義分層或者抽象的數據類型,這既是特征(數據因素)和行為(功能性)”[1]N.Katherine Hayles,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70.。這就使得使用該語言的編程者從開始就參與到了其所要設計的對象的意義解釋與建構過程中。簡單來說,數字藝術對于藝術家和欣賞者都從數字技術的層面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這個要求不僅僅是藝術方面的,更是技術實現層面的。

圖3 凱西·瑞斯 《微像(軟件1)》(2002/2014)
回顧一下數字藝術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數字藝術家往往都有著雙重身份,他們創造藝術的同時還擅長某一種編程語言或者算法。比如在數字藝術領域里最常用的開源編程語言Processing的開發者之一凱西·瑞斯(Casey Reas)同時也創作藝術作品,他的作品小到紙上作品,大到城市公共裝置。與此同時,他與諸多建筑師和音樂家也均有合作。他的軟件作品、印刷作品和藝術裝置作品曾在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多家美術館與畫廊中展出,并被納入一系列私人和公共收藏,收藏機構包括蓬皮杜藝術中心和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等。他對于代碼生成和主體參與的看法是:“軟件《微像》的核心算法是一天之內寫成的。該軟件目前這一版是逐步迭代開發而來的。雖然控制運動的基本算法是理性構建的,隨后的發展卻是多個月以來和軟件互動后美學判斷的結果。通過直接操控代碼可以創建成百上千個快速迭代,并在分析響應結構的基礎上進行調整。整個過程更像是跟隨直覺繪制的草圖而非理性的計算。”[2]參見Artnome網站中凱西對作品的描述,https://www.artnome.com/news/2019/10/21/augmentingcreativity-decoding-ai-and-generative-art, 2019-10-21.
由此可以看出,數字藝術的創作中融入了人與機器之間的互動及人的技術能力的體現,但在創作的過程中又考慮到了審美體驗的重要性和個人情感的參與。這其實對藝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際上,我們從宏觀上審視一下一般人對數字技術的參與情況,我們就可以看到,大部分人是在用戶層面介入技術,而由淺入深則是設計師、程序員、科學家及工程師;在藝術介入的層面也是,從藝術家到觀眾逐漸由深入淺。但從最核心或者說最深層次的層面來看,在藝術的領域介入技術的層面,藝術界尚沒有可以和科學家相對等的角色。往往藝術家是無法深入到技術核心的“黑箱”之中去的,也就無法形成藝術對技術的反向影響。因此,就目前來看,以個體為對象和基礎的全才培養還是更為實際的可能路徑。
但我們相信,這個時間將很快到來。新一代數字生成(born-digital)的青年在數字素養的學習方面將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先天優勢”,因為將相對容易地介入技術的層面,并創造更多可能性。像羅比·巴拉特(Robbie Barrat)這樣的年輕藝術家,年僅19歲就已經成為了生成對抗網絡藝術中的佼佼者,他創作的超現實裸體和風景作品獲得廣泛關注,并且有著非常明確的藝術創作意識和理念。如果我們可以樂觀一點,或者未來的幾十年間,兩種或者三種文化的問題將不再是問題,而不同專業的人才將都成為一種人——未來的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