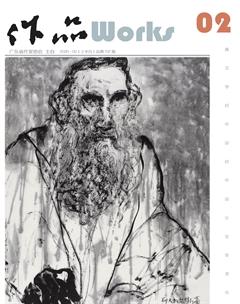刷新,刷新(短篇小說)
本杰明·佩西(美國)著 李寂蕩譯
當學校放學,我倆來到我家后院練習格斗。我們想讓彼此變得更加強壯。在草地上,在松樹和杜松樹的樹蔭下,我和戈登扔掉背包,將淺綠色的花園澆水用的水管,一根接一根,做成一個圈。然后我們脫下襯衫,戴上金色的拳擊套,開始格斗。
每輪兩分鐘。假如你踏出這個圈,你就輸了。假如你哭了,你就輸了。假如你被擊倒或者你大喊叫停,你就輸了。之后,我們喝可口可樂,抽萬寶路,我們的胸部起伏著,我們的臉蛋都是深淺不一的色塊,青一塊,紅一塊和黃一塊。
我們是在賽斯·約翰遜之后開始格斗的。賽斯·約翰遜是一個沒脖子的后衛,牙齒像玉米粒,手掌像T形骨的牛排,他將戈登的臉打腫,打裂,邊緣變成青紫。最終他痊愈了,堅硬的痂殼正在脫落,露出一張不同于我記憶中的面孔——更老,更方,更兇,左邊的眉毛被一條黏糊糊的白色傷疤分開了。戈登的想法是,我們應該相互搏擊。他做好了準備。他想傷害那些傷害過他的人。假如他倒下,他將像他所信賴的父親那樣搖搖晃晃地倒下。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取悅于我們的父輩,讓他們驕傲,即便他們已離開我們。
俄勒岡的克羅,是一個坐落在喀斯喀特山脈山麓的高地沙漠小鎮。在克羅,我們有一千五百人口,一個奶品皇后店,一個英國石油公司的加油站,一個Food4 Less[1]商場,一個肉品加工廠,一個由管道水灌溉的鮮綠的足球場,還有以你們標準配置的酒館和教堂。我們小鎮與本德·雷德蒙·拉派恩或97號公路沿線的其他無名小鎮沒什么明顯的區別,除了一點:我們是第34海軍陸戰隊第二營的駐地。
海軍陸戰隊駐扎在小鎮外的山上五十畝的基地里,那是一群一層樓的煤渣磚建筑,建筑間生長著黑雀麥和山艾。我整個童年,只要我將一只手握成杯狀放到耳邊,公牛的低哞、山羊的咩叫,以及山頂上來復槍呼嘯的射擊聲,就會傳入我耳朵。據說,俄勒岡牧場地區的條件與阿富汗和伊拉克北部山地很相似。
我們的父親——戈登和我的——像克羅其他父親一樣。他們差不多都是作為兼職軍人和預備役軍人入伍的,作為操練的報酬,一個列兵每年幾千英鎊,一個中士比幾千英鎊還要多。這個報酬他們稱呼為啤酒工資,他們的訓練是,每年兩周,加上每月一個周末。他們穿上軍裝,往帆布背包里裝東西和我們吻別,然后第二營的大門在他們身后關閉。
我們的父親會消失在嵌滿松樹的山丘上,星期天晚上,帶著因天氣造成的紅撲撲的臉龐,回到我們的身邊,他們的二頭肌因疲勞而顫抖,他們的手能聞到來復槍的油脂味。他們談論著緊急避孕藥、PRPS牛仔褲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會在臥室中央做俯臥撐,他們將六點鐘叫作“一千八百小時”,他們會擊掌并叫喊:“永遠忠誠[2]。”然后過不了幾天,他們又回到以前的樣子,成為我們所熟悉的男人:喝康勝啤酒,打棒球,撓胯,能聞到Aqua Velva[3]味道的父親們。
不久,一月份,這個營有行動了,三月份他們乘船開往伊拉克。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教練,我們的老師,我們的理發師,我們的廚師,我們的加油站服務生,UPS快遞公司送貨員,以及代理人、消防員和機械師——我們的父親們,他們是如此之多,他們爬上了橄欖綠的學校巴士,將他們的手掌壓在車窗上,留給我們最勇敢,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具希望的微笑,然后消失了。就那樣。
夜晚,我有時騎著我的本田越野摩托,穿過德舒特縣的山丘和峽谷。我身下的引擎轟鳴著,顫抖著,而我周圍的風,像某種活物,欺負我,竭力想將我從車上拽下來。當我調低速擋,傾斜著到達一個拐彎,到了直道上,我便提速,一個黑暗的世界從我身旁滑過——七十,八十——我注意到前面二十碼的提示路牌閃亮著。
我騎著摩托,奔跑著,奔跑著,奔跑著,從這兒,翻越喀斯喀特山脈,穿過威拉米特峽谷,到達大海,鯨魚寬大的黑色的背脊有規律地沖破水面,遠處——更遠處——我看見了地平線,我父親在那邊等著。必然地,我最終來到地洞。
很久以前,一顆流星呼嘯著從太空墜落,留下了一個五千英尺寬三百英尺深的隕石坑。冬天,地洞經常被我們中的愛冒險的雪橇手光顧,在夏天,則經常被蓄著大胡子的地質學家光顧,他們對地洞底部四處散落的金屬塊感興趣。我將腳懸晃在地洞口邊緣,仰靠著雙肘,凝視著黢黑的蒼穹——沒有月亮,只有星星——僅比烏鴉亮一點點。每隔幾分鐘,一顆星星似乎失控,疾速劃過夜空,發出閃亮的光芒,焚燒于無。
不遠的距離外,牛郎星在黑暗中閃爍著暗綠色的光——提醒著,我們的存在多么接近于遺忘。一塊太空冰或一陣太陽風可能撞著流星的側面,使其不是著陸于此,而是著陸于彼,隕石坑與法維交界處。那樣就不會有女王峽谷、克羅山脈、第二營了。毋庸多想,天空中掉下什么東西都會改變地面上的一切。
十月份時,放學后,我和戈登在后院里練習格斗。我們戴上爛了的金色的拳擊手套,當我們出拳時,手套因為時間久了而破敗,變成絮狀。褐色的草在我們的運動鞋下蜷伏,灰塵一縷縷騰起,就像求救信號一樣。戈登骨瘦如柴。他的鎖骨撐著他的皮膚就像皮膚下包著一副衣架。他的腦袋相對于他的身子顯得很大,就像他的眼睛相對于他的頭顯得很大一樣。足球運動員——其中的賽斯·約翰遜——經常將他扔進垃圾箱,叫他外星人。
他度過了倒霉的一天。我從他臉上的神情——水汪汪的眼睛,顫抖的嘴唇因快速翕動而顯露出的齙牙——可看出他的想法,他的需要,就是擊敗我。于是我讓他去實現。我舉起戴著拳擊套的雙手擋著臉部,將雙肘頂著肋骨,戈登向前跨步,他的雙臂像橡皮帶噼啪作響。我靜靜地站立,由他上下向我擊打,由他將憤怒之重砸向我,直到最終他因疲憊得不能再打時,我移動站姿,用一記右掃拳打在他的太陽穴上,將他擊倒在地。他躺著,在草叢中蜷曲著身子,“外星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縷微笑。“該死的。”他夢囈般地說。一滴鮮血沿著他的眼角凝聚,滑過他的太陽穴,鉆入他的頭發。
我的父親穿著鋼頭靴、卡哈特牌牛仔褲,身著一件T恤,T恤上打著他旅行到過的地方的廣告,也許是黃石或者西雅圖。他看起來就像你在派瑪特超市遇到的買機油的人。為了遮蓋后退的發際線,他戴著一頂約翰·迪爾帽,帽子在他瞼上投下了一道陰影。他褐色的眼睛在一只大鼻子上端眨著,鼻子下端是一撇灰色的胡子。和我一樣,我的父親又矮又胖,像一只牛頭犬。他的肚子像一只鼓鼓的口袋,他的肩膀很寬,在我年幼的時候,很適合馱著我漫步和逛集市。他經常笑,他喜歡游戲節目,他喝很多的酒抽很多的煙,花很多的時間和他的伙伴在一塊,釣魚,打獵,哄騙,這有可能與我母親和他離婚搬去博伊恩和一個叫查克的理發師同時也是鐵人三項運動員同居有關系。
起初,他離開后,像其他父親一樣,只要可能,他會隨時發郵件給我,他會告訴我天氣有多熱,他每天喝多少加侖的水,沙子無孔不入,他用嬰兒濕巾洗澡。他會告訴我他有多么安全,非常的安全。那時他駐扎在土耳其。當預備役軍人乘船前往基爾庫克,那兒的叛亂分子和沙塵暴幾乎每天都在發動襲擊。電子郵件來得不那么頻繁了。在他們之間是幾星期的沉默。
有時,在電腦上,我點擊刷新,刷新,多希望能刷新啊。十月份我收到了一封郵件,上面寫著:“嗨,喬希。我好著呢,別擔心。做你的作業。愛你的,爸爸。”我將這封郵件打印出來,用透明膠粘著掛在門上。
我父親在羅斯爾公司工作了二十年——那是一家設立在本德的子彈制造商——海軍陸戰隊將他作為一個彈藥技師來訓練。戈登喜歡說他的父親是一位射擊軍士,他確實是,但是我們都知道他也是一名軍營伙食部經理,一名廚師,這成了他在克羅的謀生之道,在漢堡肉餅店做燒烤。我們知道他們的頭銜,但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頭銜意味著什么,我們的父親在那兒做什么。我們想象著他們的英雄壯舉:從燃燒的房屋中救出伊拉克嬰兒,在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人流擁擠的街道引爆炸彈之前對他們進行狙擊。我們借鑒好萊塢電影和電視新聞,精心設計了這樣的可能的場景:黃昏時分,在伊拉克北部的山脈跋涉時,蓄著大胡子的恐怖分子用火箭發射器伏擊了我們的父親。我們想象著他們在猛烈的爆炸中顯出的剪影。我們想象著他們像蜥蜴鉆進沙子里,用M-16步槍射擊,子彈在黑暗中穿越就像我在無眠之夜觀察到的隕石。
當我和戈登格斗時,我們將臉涂成黑色、綠色和褐色——用我們父親留下的油彩。這使得我們的眼睛和牙齒顯得驚人的白。油彩將我的拳擊套弄臟了,就像腳下的草被我們的運動鞋弄臟了一樣——拳擊場變成了一圈塵土,塵土是紅色的,看起來很像結痂的肉。有一回戈登重重地捶在我的肩膀上,以致我一周都不能抬起手臂。而另一回我肘擊了他的一個腎,使他尿血。我們以如此的力量和頻率相互擊打,以致金色的拳擊套破爛,從浸著汗水,浸著鮮血的泡沫中露出指關節,就像從破裂的嘴唇露出牙齒一樣。于是我們買了另一副拳擊套,隨著天氣持續變冷,我們格斗時,嘴巴大口喘出熱氣。
盡管我們的父親離開我們,但克羅還有男人。年邁的男人,像我的祖父,我和他們在一起生活的男人——償清了債務,他們曾經干活和打仗,現在在加油站打發日子,用泡沫塑料杯子喝著劣質咖啡,抱怨天氣,爭論著收割苜蓿的月份。還有難以忍受的男人。他們很少刮胡子,穿著曾經一度是白色的內褲,看日間電視節目。男人們住在活動房里,往購物車里放主燈、夏季香腸、奧利奧餅干。
還有像戴維·萊特納這樣貪婪的男人——他們把我們父親留下的一切東西都撿拾殆盡。戴維·萊特納的職業是一名招募官。我猜他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的開著摩托車的招募官,車后面掛著“支持我們部隊”的絲帶磁鐵。我們有時看到這車停在丈夫上戰場的年輕婦女的家門之外。戴維長著一對大耳朵和一雙小眼睛,他戴的頭發是又高又密的那種標準發型。他經常大聲地談論他在費盧杰巡邏隊時擊斃的所有叛亂分子。他和他的母親住在克羅,但卻成天在本德和雷德蒙逛百思買、肖普克、凱馬特、沃爾瑪和山景城的商場。他在尋找像我們這樣的人,憤怒、失望和貧窮的人。
但是戴維·萊特納知道不該打擾我們。他的工作完全避開克羅。在那兒的招募非常像在森林焚燒過的地段偷獵,在那兒僅有肋骨如板條、腿腳搖晃的鹿,在灰燼中伸出鼻子,尋求綠色的東西。
我們并不完全理解我們父親打仗的原因。我們只知道他們不得不打。戰爭的必要性使得原因無關緊要。“它就是游戲的一部分,”我的祖父說,“戰爭就是這樣。”我們只能交叉手指對著星星許愿,然后點擊刷新,刷新,希望他們能回復我們,祈禱我們將永遠不會發現戴維·萊特納站在我們家門廊里說:“我抱歉地通知你……”
一次,我祖父把我和戈登扔在山景城商場,在靠近玻璃門入口處,站著戴維·萊特納。他穿著皺巴巴的卡其制服,同一群十幾歲的墨西哥少年說話。當我們走近時,這群少年正大笑著,搖著頭離開他。我們將帽子拉得很低,他沒有認出我們來。
“先生們,向你們提個問題,”他用一種電話推銷員和挨家挨戶上門的耶和華見證人的口氣說,“你們打算怎么度過你們的一生?”
戈登瀟灑地摘下他的帽子,仿佛他就是某種機關槍,動作神奇,表情詭異。“我打算殺死那些瘋狂的穆斯林,”他說著,擠出一絲微笑,“你呢,喬希?”
“好,”我說,“殺掉那些人,然后自己被殺。”我是一邊附和一邊扮鬼臉,“聽起來是一個不錯的打算。”
戴維·萊特納的嘴唇緊緊地抿成一條細線,他站得筆直,問我們,聽到剛才我們說的話,我們認為我們的父親將作何感想,“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正保衛著我們的自由,而你們卻在開惡心的玩笑,”他說,“我認為惡心。”
我們討厭他柔軟的手和干凈的制服。我們恨他,因為他將像我們這樣的人招去送死,因為他在二十三歲時就獲得了比我們父親更高的軍銜,因為他睡軍人孤獨的妻子。而現在我們更恨他是因為他讓我們感到恥辱。我想說一些諷刺的話,但是戈登說得更快。他將手伸到戴維面前,他的手指抓住一個想象中的瓶子。“這是你的糖漿。”他說。
戴維說:“那是干什么的?”
“舔我的屁股。”戈登說。
恰在這時,一個綠頭發、戴著鼻環的滑板運動員模樣的人從商場里走出來,他握拳拎著一滿袋DVD,晃悠悠的,戴維·萊特納拋下我們。“嗨,朋友,”他說,“讓我問你一件事,你喜歡戰爭片嗎?”
十一月,我們駕著越野摩托車到森林深處去打獵。陽光透過高大的松樹和白樺樹叢灑到伐木道旁的水坑里,伐木道穿過長滿黑果木的山坡,陽光灑在土狼亂竄的冰磧上,土狼試圖逃離我們,滑倒時引起了松動的巖石輕微的崩塌。差不多有一個月沒下雨了,所以馬堂草、旱雀麥和松針失去了顏色,像玉米殼一樣干枯、發黃。當我們的車駛入荒地時,我們下車步行,枯葉在我們的靴子下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響。在這沒有水的寂靜里,你似乎能聽到一英畝內每只花栗鼠啄食松子的沙沙聲,而當微風吹拂,變成冷風時,森林變成了一個巨大的低語者。
我們將帳篷和睡袋扔在一個玄武巖洞旁,從洞里流出的泉水汩汩地淌著,戈登說:“出發,士兵們。”像士兵一樣,他握著步槍斜橫在胸前。他也穿戴得像士兵一樣,穿著他父親的超大號背心,而不是強制性的火焰橙色的裝備。我們彼此相距五十英尺,向山下走去,穿過森林,穿過一叢叢黑果木,穿過一片滿是樹樁的被砍伐的地帶,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太大的聲響,不滑倒在覆蓋著松針的地上。一只正為一顆松果發愁的金花鼠,當一只游隼俯沖下來抓住它時,它驚叫起來。游隼在樹木間將它逮住,把它帶到某個秘密的所在。游隼的翅膀沒有發出聲音,當那個渾身冒火怒氣沖沖的獵人出現在我們下面幾百碼的一塊空地時,他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戈登做出某種突擊隊的手勢——我認為,它的意思是,小心前進——我小心翼翼地走向他。從一塊大石頭后,我們通過我們的望遠鏡窺望,追蹤那個獵人,他穿著背心,戴著有耳飾的帽子,像一個巨大的南瓜。“那個混蛋。”戈登嚴厲地低語說。那個獵人是賽斯·約翰遜。他的來復槍綁在背上,嘴巴在動——他正跟某人說話。在草地一角,他加入了四位大學橄欖球隊隊員的行列,隊員們圍坐在陰燃著的篝火旁的圓木上,當他們將啤酒往嘴里送時,他們的手臂像油泵千斤頂一樣上下移動。
我將眼睛從我的望遠鏡移開,我注意到戈登正用手指扣動著他的30.06步槍。我告訴他不要干蠢事,他立馬將他的手從槍把上移開,內疚地一笑,說他只想知道對他人擁有權力是啥感覺。然后他扣動扳機的手指抬了起來,觸了觸將他的眉毛分裂開的那道黏糊糊的白色傷疤。“我說我們對他們使一點壞吧。”
我搖頭表示不解。
戈登說:“只一點點——嚇嚇他們。”
“他們帶著槍。”我說。
他說:“所以我們今晚得返回。”
后來,我們的晚餐吃得早,晚餐有牛肉干、干果和佳得樂飲料。當時我剛好碰見一只四點雄鹿正在啃吃熊草,我將我的來復槍安放在一個土堆上,向它射擊,它向后栽倒,它的肩部后面炸開,像玫瑰綻放一樣,那地方就是心臟隱藏的地方。戈登跑了過來,我倆圍著鹿站著,抽了幾支煙,看著釅稠的動脈血從它的嘴巴涌出。然后我們取出小刀開始工作。我將它肛門周圍切開,割掉它的陰莖和睪丸,然后用刀在它的肚子上劃動,切開它的皮,露出了它鮮嫩粉紅的肌肉和綠色的血管,我們的手消失于其中。
血液在寒冷的山區空氣中冒著熱氣,當我們結束時——當我們剝下鹿的皮,在它的關節處砍劈,砍出它的背肋條,剔出它肩部、臀部、脖子和肋部的骨頭,弄成排骨、烤肉串、肉排,將肉分成四份,使之可以包裝成隔熱的馱包——戈登拎著鹿角將鹿頭舉到自己的腦袋前。血從鹿的脖子處滴到地上,發出滴答的聲音,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線中,戈登跳起舞來,雙膝彎曲,跺著雙腳。
“我想我有了一個主意。”他說,他假裝用鹿角來戳我。我將他推開,他說:“別對我撒嬌,喬希。”我精疲力竭,渾身血腥,但我贊賞必要的復仇。“只是嚇唬一下他們,對嗎,戈登?”我說。
“對。”
我們拖著鹿肉回帳篷,戈登帶來鹿皮。他在鹿皮的中央切開一個洞,將腦袋從洞口戳出來,以至這鹿皮在他身上掛著,松垮垮的,像一個毛茸茸的袋子,我幫他在臉上抹上泥漿和鹿血。然后,戴著他的皮人,他鋸掉鹿角,每只手里各拎一只,在空中舞動著,仿佛兩只獸爪。
夜幕降臨,月亮懸掛在喀斯喀特山脈上空,灰暗地照著我們穿越森林的道路,我們想象著自己置身于敵人的領地,每個角落布有絆網、瞭望塔和吠叫的狗。從大石塊后面可以俯瞰他們的營地,我們觀察到,我們的敵人交換打獵的故事,拿西卡·羅伯遜的大屁股似的乳房開玩笑,傳遞著一瓶威士忌猛喝,最后撒尿在火堆上讓火熄滅。我們等了一個小時,他們撤回了帳篷里,我們下山抵達他們那兒,因為小心翼翼,又花了一個小時。某處貓頭鷹咕咕地叫著,幾乎不引人注意,因為被帳篷里升起的混雜的呼嚕聲所掩蓋。賽斯的野馬車就停在附近——牌照上寫著“男主”——他們的來復槍都放在駕駛室里。我將槍收集起來,斜掛在肩膀上,然后將我的刀輕松地插進賽斯的每只汽車輪胎。
當我們站在賽斯帳篷外時,我仍然拿著刀,當一片云遮住月亮,四周一片黢黑時,我迅速將帳篷的尼龍布扎出一道口子。戈登沖了進去,鹿角做的獸爪舞動著。除了黑影我什么也看不見,但我能聽見賽斯發出小女孩發出的那種尖叫,戈登用鹿角向他耙去,發出嘶叫聲和咆哮聲,像某種穴居動物饑渴于人肉一樣。當我們周圍的帳篷帶著喧囂熱鬧起來,戈登的臉上浮現出恐怖的微笑,我跟著他,穿過灌木叢,沖到小山上,將噩夢一般的感覺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降臨到賽斯身上。
冬天來了。雪降落,我們穿上工裝服,擰上裝滿飾釘的輪胎,駕著我們的越野摩托到地洞去,身后用拖繩拖著我們的雪橇。我們的引擎聲打破了午后白色的寂靜。我們的后輪刨起層層粉塵,急轉彎時在我們身下打滑,我們躺在了路中央,流著血,大笑著,無所畏懼。
早些時候,做午餐時,我們用一根黃油棒烹飪了一磅培根。我們把硬成白色蠟狀物的油脂用作上光劑,把它抹到雪橇的底部。在地洞我們是需要速度的。我們從洞穴最陡峭的地方往下降落,降到離我們三百英尺深的底部。我們在同一條道上相互跟隨著,貼著雪地,開創出一道滑道,藍色的,光滑無比,使得我們能以自由落體的速度滑行。當我們火箭般下滑時,我們的眼球凍成了釉,我們的耳朵里是風在呼嘯,我們的胃提到了嗓子眼。我們仿佛回到了五歲——然后當我們沿來路返回緩慢爬行時,感覺到了五十歲。
我們戴著冰爪,沿著彎彎曲曲的一系列坡道攀登。花費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當我們再次站在火山口時,空氣隨著夜幕降臨變成紫色。我們穿著工裝大汗淋漓,透過我們呼出的霧氣看四周。戈登摶了一個雪球。我說:“你可不要用那個砸我。”他笑著威脅地揚起手臂,然后蹲下雙膝,將雪球滾成一個更大的東西。他滾動著直到它形成像嬰兒蜷曲的姿勢的大人形狀。從他的摩托車后面,他取出園藝用的軟管,對著它的尾端吮吸直到氣體流動。這軟管他曾用來從昂貴的外國汽車缸吸汽油,然后將其灌進他的油缸。
他向這個大雪球潑灑東西,仿佛他希望其長出芽來。它并沒有融化——他將它摶得很堅實——但它只是稍有皺褶,顯得沉甸甸的,當戈登拿出他的芝寶打火機,打燃,將火機伸向雪球,火焰引著了氣體,整個雪球滋滋地爆燃起來,那聲浪使我踉蹌地向后退了幾步。
戈登沖上前,踢向火球,使得火球滾動著,跌落到隕石坑,像隕石一樣沿著我們的滑道跌落,所到之處雪瞬息融化,但一會兒又凝起了,形成了一條光滑的藍色緞帶。當我們駕著雪橇車在上面滑行時,速度如此之快,使得我們的大腦一片空白,我們立馬有一種飛翔和墜落的感覺。
新聞報道伊拉克叛亂分子發動襲擊。新聞上說,在巴格達一處交通檢查站,一輛汽車炸彈炸死了七名美國士兵。總統在新聞中說,他認為提出一個撤軍時間表是不明智的。早餐前我檢查我的郵箱,除了垃圾郵件什么也沒有。
我和戈登穿著雪地靴在雪地里格斗。我們格斗得如此頻繁,以致我們的傷口永遠沒有機會愈合,我們的臉蛋永遠是腐爛的樣子。我們的手腕感到腫脹,膝蓋疼痛,我們感到關節充斥著細小的干黃蜂。我們打斗到傷實在太多,以致我們不得不以飲酒來代替。周末,我們駕著越野摩托車到二十里地遠的本德,買了啤酒將其帶到地洞去喝,直喝到地平線上出現耀眼的陽光,陽光照亮了白雪覆蓋的荒漠。沒有一個人詢問我們的身份證,當我們舉起空酒瓶時,凝視著玻璃瓶上我們的影像,面目扭曲,鬼一樣,我們知道為什么。就像克羅人[4]一樣,克羅人的兒子、女兒和妻子都這樣,眼睛下長著兩只黑眼袋,肩膀彎曲,圍著他們嘴巴的皺紋就像一對括弧。
我們的父親縈繞著我們。他們無處不在:當我們瞧見三十一扎的銀子彈啤酒打折賣十塊時,他們就在這家雜貨店里;在高速路上,當我們經過一輛車廂里高高疊放著一打干草堆的道奇車時;當一架噴氣式飛機轟隆隆地從天空飛過時,我們想起了遙遠的地方。現在,我們身體的肌肉在變得厚實,當我們不修面時就會胡子拉碴的,我們看見我們的父親就在鏡子里。我們開始長得像他們。我們的父親,從我們身邊被帶走,無處不在,在每一個角落,與我們不離不棄。
賽斯·約翰遜的父親是一名陸軍上士。像他兒子一樣,他是一個大塊頭,但還不夠大。就在圣誕節前,他踩到了一顆集束炸彈。那是一架美國戰機扔下的,沙子將其掩蓋,他踩著了,炸彈將他撕碎成許多肉塊。當戴維·萊特納戴著黑色的臂章,一臉沉痛的表情爬上前廊時,當時正在烹制蜜汁火腿的約翰遜夫人立馬癱倒在廚房的地板上。賽斯沖出門來,一拳猛擊在戴維的臉上,他還未來得及表達:“我抱歉地通知您……”,鼻子便被打破。
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難過了足足十秒鐘。然后我們又感到不難過了,因為他的父親不是我們的父親。然而我又再次感到不快,在圣誕節前夕,我們駕車到賽斯家,將我們偷來的來復槍和六扎銀彈子啤酒放在廊道里,后來,就在我們將要離開時,戈登從他的后面口袋里掏出錢夾,并從錢夾里摸出六沓錢放下,這是他所有的錢——幾張伍圓的,一些壹圓的。“操你媽圣誕節。”他說。
我們變得更加勇敢了,我們去酒吧——金磚酒吧,疲憊旅行者酒吧,松樹酒館——我們在這兒和老女人們跳廣場舞,老女人們涂著紫色的眼影,戴著亮晶晶的捕夢者耳環,束著托舉式胸罩,腳蹬咔嗒作響的高跟鞋。我們告訴她們,我們是從六個月服役期返回的海軍陸戰隊員,她們說,“真的嗎?”我們說:“是的,太太。”當她們詢問我們的名字時,我們給她們的是我們父親的名字。然后我們的給她們買酒水,她們大口大口地喝,熱烈地朝我們臉噴氣,我們將嘴湊到她們嘴上,她們的味道像薄荷煙,像燒焦的洗滌劑,然后我們將她們帶回家,或者去她們的活動屋,在她們的水床上,在她們的填充動物玩具中操她們。
下午三時左右,天完全黑了。在我們去疲憊旅行者酒吧的路上,經過我家時我們停下來準備向我爺爺討要一些錢,卻發現戴維·萊特納正等著我們。他一定是剛到——他正踏上門廊臺階的半途——當我們的前燈蒼白的光照著他,他轉過臉,一臉皺巴巴的表情,好像在竭力分辨我們是誰。他手臂上戴著一圈黑色的帶子,鼻子上是一塊白繃帶的夾板。我們沒有關掉引擎。相反,我們坐在行駛道上,無所事事的樣子,摩托車排出的廢氣和我們呼出的氣體在空氣中形成了霧氣。我們的頭頂,月光照亮的天空嘶嘶地劃過一顆星星,星星的光微弱得像白晝亮堂的房間打開的一盞燈光。戴維走下臺階,我們跳下了車迎向他。他還沒來得及開口,我已經將拳頭送到了他的橫膈膜,敲得他大口喘氣。他看起來像極了西部片里的槍戰演員,雙手捂著肚子,更甚的是,他的臉成了戈登膝蓋的好靶子。一陣噼噼啪啪之后,戴維仰面躺倒在地上,鮮血從已經斷了的鼻子里流出來。
他舉起雙手,我們則打穿過去。我猛擊他的肋骨一次,兩次,而戈登則踢他的脊椎和腹部,然后我們站著大口地喘息,讓他掙扎著站起來。當他站直了,他用手揩臉上的血,血從他的指間滴落。我走近,左右開弓,拳擊他的腦袋,他的腦袋耷拉下來。他再次倒下,成了一個男子血袋。他的眼睛被遮擋了,翻動著,竭力想看清他面前模糊出現的動物軀體。他張口想說話,我伸出一根指頭指著他,用充滿仇恨的聲音停頓了一下說:“不要說一個字。你敢。一個字也不成。”
他閉緊嘴巴,竭力想爬起來,我一靴子踩在他的頭蓋骨上,踩了一會兒,將他的臉碾壓進雪地,以致當他抬起頭時,雪地上留下了他的臉的血印。戈登走進屋里,一會兒后出來,帶來了一卷管道膠帶。我們將戴維摁倒,捆了他的雙腕和雙踝,將他扔到雪橇上,將他綁了很多道,然后將雪橇綁在戈登的摩托車上,以一種危險的速度向地洞駛去。
月光照在雪地上,雪地閃耀著蒼白的藍光,我們吸著煙,俯瞰隕石坑,將戴維踩在腳下。我們從嘴巴里吐出小小的煙霧,顯得有點孩子氣,仿佛我們在模仿玩火車玩具。一會兒,也就一會兒,我們又變成了孩子,一對愚蠢的孩子。戈登一定也感到如此,因為他說:“我很小的時候,我媽媽甚至不讓我玩玩具槍。”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仿佛他不能理解他,我們,怎么來到這兒的。
然后,突然一動,戴維掙扎著,用模糊不清的聲音向我們喊叫,我的臉因為憤怒而僵硬,我將雙手放在他身上,緩慢地推他到隕石坑口,他變得沉默了。有片刻我忘了我自己,向下凝望著那黑色的忘川。它是美麗的和恐怖的。“我現在就可以推你下去,”我說,“假如我那樣做,你必死無疑。”
“請不要。”他說,他聲音沙啞。他開始哭。“哦,操。請不要。”聽著他抽搐著的慟哭,并沒有帶給我預期的滿足。要說真有什么的話,那天我所作所為的感覺,就像很久以前,當我們在山景城商場停車場戲弄他一樣——恥辱,虛假。
“真的嗎?”我說。“一!”我一點點地將他拖近隕石坑邊緣。“二!”我繼續將他拉近一點,我感到自己笨拙,既瘋狂又疲憊,我的身體似乎增加了二十,三十,四十歲。當我最后說“三”,我的聲音幾乎是低語。
我們將戴維留在那兒,在隕石坑邊緣哭泣。我們騎上摩托車,駛往本德,開得如此之快以至讓我想到著火的流星,瞬間燃燒起來,呼嘯著,我的熱量在消耗,我們走向美國海軍陸戰隊招募辦公室,在那里,我們終于對戰爭警報做出了回應,將筆落在了紙上,要讓我們的父親感到驕傲。
注釋:
[1]?Food4 Less,美國全國性倉儲式商店和雜貨連鎖店。
[2]?永遠忠誠,源于拉丁語,美國海空陸戰隊的座右銘。
[3]?Aqua Velva,須后水(刮胡后的化妝水)。
[4] 克羅人,美洲土著,多居住于美國蒙大拿州。
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