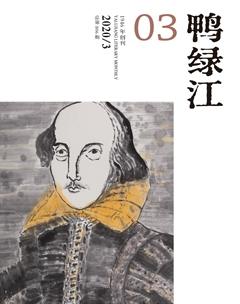小說的魔幻和寓言(對(duì)談)
陳培浩 王威廉 路魆
1
陳培浩:很高興一起來作關(guān)于路魆新作《竊聲》的對(duì)話。這篇小說有一種神秘迷離的氣質(zhì),通過寫“我”在神秘樂園小區(qū)的奇遇,構(gòu)造了一個(gè)當(dāng)代寓言,挺有想法的。小說開篇就暗示了它的讀法,即我們不能將它作為一個(gè)寫實(shí)小說來讀,而應(yīng)該注意到它的夢(mèng)游氣質(zhì)及其生發(fā)的隱喻、象征。小說開篇寫道:“三更半夜,有一頭長頸鹿模樣的動(dòng)物,從窗外伸進(jìn)長長的腦袋,趁我睡得迷迷糊糊時(shí)在我那亂成野草的頭發(fā)上啃了一口。我驚醒,跳起,扯亮燈。那截長脖子卻不見了。”從嚴(yán)格寫實(shí)的角度看,這段敘述是不成立的。“我”既熟睡,如何能看到一頭長頸鹿模樣的動(dòng)物從窗外伸進(jìn)長長的腦袋呢?等“我”驚醒,扯亮燈,它已經(jīng)消失了。但這種對(duì)寫實(shí)邏輯的公然違背,要么是生手的疏忽,要么就是對(duì)小說調(diào)性的某種暗示。《竊聲》當(dāng)屬后者。因?yàn)槲覀凂R上讀到主人公被一個(gè)莫名其妙的電話通知到神秘樂園小區(qū)認(rèn)領(lǐng)舅舅的尸體,他一路尋找神秘樂園小區(qū)的那種曲折,讓人幾乎懷疑這個(gè)神秘樂園小區(qū)就是卡夫卡筆下的城堡。這種現(xiàn)代主義的寓言寫法,有經(jīng)驗(yàn)的讀者應(yīng)該是別有會(huì)心的。路魆請(qǐng)你先談?wù)勥@篇小說的構(gòu)思,小說的靈感和構(gòu)思何時(shí)產(chǎn)生?你想傳遞給讀者的是哪些信息?哪些地方是你特別滿意,特別希望讀者注意到的?
路魆:若追根溯源,嚴(yán)格意義上,《竊聲》是我六年前寫下的第一個(gè)小說,一篇關(guān)于追尋主體和真相的小說。但它不是一個(gè)舊作品,因?yàn)樵谶@六年里,它被我不斷修改,面目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樹木增加年輪似的,在不斷擴(kuò)充內(nèi)部的肌理。
我當(dāng)初寫這篇小說,是源于一種受迫害的焦慮,對(duì)于自身被人群同化、被世界禁錮的恐慌。外部的一切都在虎視眈眈。在我剛寫作時(shí),盡管知曉何為精神的苦痛,但落實(shí)到寫作上,并沒有觸及具體問題,于是產(chǎn)生了一個(gè)象征性的空間——神秘樂園小區(qū)。在我看來,世界是一個(gè)符號(hào)性的世界,這就是為什么小說中布滿隱喻,就連最后主人公尋求出路也是符號(hào)性的行為。隱喻不是一個(gè)偷懶的手法,我相信那是作者開始嘗試給事物進(jìn)行歸類,形而上地去理解,我也相信隨著寫作的深入,當(dāng)初靠天生的思維所感知的東西,會(huì)在現(xiàn)實(shí)里得到一一的對(duì)應(yīng)。這也是這篇小說在六年里不斷被修改的意義,它隨著我的生長而生長,得到充實(shí),我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寫作發(fā)展的軌跡。可以說,《竊聲》是我寫作的一棵生長樹,對(duì)它的構(gòu)思沒有停止過。
今天,對(duì)于這場發(fā)生在神秘樂園里的超現(xiàn)實(shí)的迫害,我有了新的想法,這里面有一個(gè)三位一體的結(jié)構(gòu):“神秘樂園——人類——聲音”。神秘樂園代表的,或許是籠罩整個(gè)世界的陰影,是謊言和蒙蔽。而它的代言人,卻是小女孩蘆花。蘆花,多么通俗簡單的一個(gè)名字,而且,你可以說她是狡猾的,也可以換一個(gè)詞,說她是機(jī)靈的。類似的這種具備多重解讀性的人物,作為整個(gè)神秘樂園的代言人,作為一個(gè)象征,非常有可塑性,因?yàn)樗皇且粋€(gè)傀儡,看起來整個(gè)神秘樂園都在圍繞著蘆花轉(zhuǎn),其實(shí)那只是障眼法。真正的操縱者,是背后那群生活在小區(qū)里的成年人,本來神秘樂園早就應(yīng)該拆除重建,他們卻各司其職,維護(hù)著虛假世界的繁榮,茍延殘喘,守著可憐的利益,對(duì)外面的世界置若罔聞。主人公正是看破了這種假象,察覺到了危機(jī),才不愿意受制于人,但他的生活卻又建立在這樣的基礎(chǔ)之上,他要在這里守著舅舅的房子,要在這里獲取寫作的靈感,矛盾重重,看似無法逃離,出路遙不可及。這種近似于宗教世界的空間非常有趣,人類創(chuàng)造神明,建立無形的權(quán)威,對(duì)其他人類進(jìn)行規(guī)訓(xùn)。即使沒有籬笆,沒有圍墻,可是一旦被浸潤,即使你出去了,身上依然被烙下的刻印的疼痛提醒著你的歸屬,就如小說里那個(gè)離開了神秘樂園的女人,在外面毫無依憑,最終返回,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歸屬意味著精神的故鄉(xiāng),然而,假如精神的故鄉(xiāng)不再完整,精神便開始流浪,開始尋求出路。這條出路,就是墻壁后面那個(gè)引誘主人公的聲音。
要說我最滿意的地方,是墻后那個(gè)神秘聲音的設(shè)置。它是人的一種覺醒,一份良心,愚昧之中的光明。當(dāng)神秘樂園所有人都在勸阻主人公不要追尋聲音的來源時(shí),他依然一意孤行。人類應(yīng)該擁有這份叩問和追尋真相的勇氣。福柯在《說真話的勇氣》里寫:“當(dāng)言說真相的時(shí)候,主體就呈現(xiàn)了他自己。”主體需要在承認(rèn)真相的同時(shí)得到呈現(xiàn),謊言是抹去主體的迷霧,這也是我當(dāng)初寫這篇小說時(shí)所說的那種被同化的焦慮之一:主體被集體抹去了。
人一旦見識(shí)過黑暗,精神的黑暗就不可能根除。主人公受到聲音的召喚,決定鑿開墻壁,發(fā)現(xiàn)后面有一條不知通向何處的黑暗通道。那條通道通向的,也許是真正的現(xiàn)實(shí),不是肉眼所見的外部現(xiàn)實(shí),而是要用思維感知的世界真相。象征是普遍性的,思維是多維度的,世界是無窮的,這條探索真相的通道永遠(yuǎn)不會(huì)有盡頭。
陳培浩:《竊聲》是一篇現(xiàn)代主義氣息很濃的作品,威廉,你對(duì)這篇小說有哪些觀察?
王威廉:這部小說優(yōu)點(diǎn)是很鮮明的,象征的氛圍有著較大的密度。一種強(qiáng)烈的怪異氣息貫穿始終,而且越往后看越毛骨悚然。看到后面,“沒有身體的腦袋從黑暗中飄了出來。那是個(gè)骯臟殘損的頭顱,臉色蒼白,頭發(fā)像亂草一樣”。敘事人認(rèn)出了那居然是自己尋找的死去的舅舅,“它用暗黃的眼珠觀察我的房子,還在墻壁上撞擊,這個(gè)撞擊聲我再熟悉不過。它轉(zhuǎn)過頭來看我,嘴巴流著哈喇子。我去廚房給它端來一杯水。由于杯口太小,它根本無法正常飲用,用舌頭撥弄幾下后,杯子摔在地上碎了。我只好又去廚房拿點(diǎn)蛋糕來。它吃的時(shí)候,蛋糕不斷從它的脖子根掉出來。”這段描寫很有意思,它在驚恐中抽空了驚恐,而是讓惡鬼式的出場顯得稀松平常,“我”還去廚房給它倒了一杯水,仿佛來了一個(gè)客人。在這里我是非常期待的。此外,“神秘樂園”的種種細(xì)節(jié)設(shè)置,都能看到路魆的匠心所在,他在用力營造一個(gè)獨(dú)屬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這是極為重要的才華。不過,“我”的進(jìn)一步反應(yīng),卻只是震驚于發(fā)現(xiàn)自己老了會(huì)是這種丑陋的模樣,舅舅頭顱的情節(jié)就此滑過了,這就令人覺得有些遺憾。無論是“我”的反應(yīng),還是怪異的頭顱,都失去了現(xiàn)實(shí)的支撐。反觀《變形記》中格里高爾雖然變成了甲蟲,但他依然是一個(gè)人,能夠和讀者產(chǎn)生共情。這就涉及荒誕的背后機(jī)制展示得不夠。作家可以創(chuàng)造荒誕,但必須也展示這種荒誕背后的機(jī)制。正是這種機(jī)制讓故事凝結(jié)成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
陳培浩:《竊聲》會(huì)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卡夫卡的小說。比如寫主人公到神秘家園小區(qū)去的路上,“還得往前走,走多遠(yuǎn)不知道,但總會(huì)到的。路越走越荒蕪,工廠越來越多,飛過的鳥群像一縷蒼涼的煙。一個(gè)個(gè)冷卻塔如巨大的墳頭,不規(guī)則地排列在荒野里”,這里的描寫是隱喻性的,這個(gè)時(shí)候就讓人感覺主人公是被卡夫卡小說中的K附體了。當(dāng)然,卡夫卡《城堡》中,K一直在尋找,不得其門而入,但《竊聲》更多筆墨放在神秘家園而不是去神秘家園的路上。小說中,主人公初到神秘家園就碰到守門保安蝦叔,后來卻被安排頂替了蝦叔的崗位,蝦叔被宣布為一個(gè)從未存在的人。這里又有著某個(gè)卡夫卡的影子。我想請(qǐng)問路魆,卡夫卡是否是你自覺學(xué)習(xí)的文學(xué)家?我們知道有一個(gè)著名的說法叫作“影響的焦慮”,作家總是力圖不活在前輩的陰影下,因?yàn)槭苡绊懚箲]。你覺得作家該如何站在前人肩上,又免于影響的焦慮呢?
路魆:我讀《城堡》讀了許多年都沒讀到結(jié)尾,卡夫卡到死也沒把《城堡》完結(jié),這種關(guān)系可以說是“未完成的未完成”。但《城堡》散發(fā)出來的力量,以及它對(duì)我的影響,即使我沒讀完,也絲毫沒有減弱。相對(duì)于卡夫卡啰唆的長篇,我更喜歡他的短篇,《鄉(xiāng)村醫(yī)生》里醫(yī)生與病人呈現(xiàn)的關(guān)系,那種對(duì)人世重負(fù)、精神救贖和道義的承擔(dān),一直貫穿我的寫作日子。
普遍認(rèn)為,卡夫卡的城堡形象代表的是權(quán)力制度,但我更傾向于殘雪認(rèn)為城堡是理想的化身,是至高無上的理性,K在不斷接近卻又無法抵達(dá)它的過程中認(rèn)識(shí)了自我。這里就必須提到卡夫卡作品形象的普遍性。也可以說,與其講我在自覺學(xué)習(xí)卡夫卡,不如說卡夫卡為我提供了一種可以被無限解讀的作品的形象,提供了一種文學(xué)表達(dá)方式。也正如布羅德寫道:“卡夫卡的《城堡》超越了書中所寫人物的個(gè)性,成為一部對(duì)每個(gè)人都適合的認(rèn)識(shí)自我的作品。”《竊聲》中蝦叔這角色,他是神秘樂園中隨時(shí)可被代替的一只螻蟻,姓名不重要,身份是脆弱的,在更高的力量面前,只能像一只蝦那樣弓著身軀。我想,或深或淺,這角色也有某種普遍性。當(dāng)然我寫的神秘樂園,其中的普遍性遠(yuǎn)遠(yuǎn)比不上卡夫卡的城堡,甚至也不能說我站上過巨人的肩膀,說是“依靠”或許更恰當(dāng)。
現(xiàn)在回到“影響的焦慮”這個(gè)問題。在我寫作初期,卡夫卡和殘雪所代表的那種文學(xué)表達(dá)形式,一直是我努力去學(xué)習(xí)的東西。那我是否會(huì)因?yàn)榭ǚ蚩ê蜌堁槲姨峁┝艘环N方法、一種視角,而我一直在探索這種方法以及不斷用這種視角去看世界并進(jìn)而感到焦慮呢?是的,肯定會(huì)存在這種焦慮的時(shí)刻,會(huì)反問自己在這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東西我未曾探索過?但只要在這過程中,寫作者得到了極大的精神享受,能在一個(gè)更獨(dú)特的視角層面去看待這個(gè)世界,并愿意踏出新的步伐,我覺得這種焦慮就是正面的。因?yàn)槊恳淮翁剿鞯纳钊牒蛣?chuàng)作的進(jìn)步,都伴隨著自我懷疑,同時(shí)也自覺地懷疑一切,接受未知法庭的審判。但這份焦慮不會(huì)消失,只會(huì)慢慢減弱,它是一種文學(xué)烙印。
陳培浩:上面談的其實(shí)是寫作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問題,威廉,這個(gè)問題你怎么看?
王威廉:路魆談得很真誠,卡夫卡和殘雪為他提供的實(shí)則是一種小說的方法論。借助這種方法論,年輕的作家可以嘗試著建構(gòu)自己的文學(xué)世界。但這個(gè)過程是很不容易的,作家必須把自己的獨(dú)特發(fā)現(xiàn)表達(dá)出來。這里邊有兩層意思,一個(gè)是獨(dú)特,一個(gè)是表達(dá)。獨(dú)特,表面上的意思是與眾不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就是這樣的,首先必須有“我”的風(fēng)格,不能寫的東西像是任何人寫出的東西,那就失敗了。這種與眾不同可以是題材的,也可以是風(fēng)格的,也可以是別的。但肯定不僅僅如此,獨(dú)特的深層要求是要有深刻的洞見,那些獨(dú)特的形式是為什么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是一個(gè)成熟的作家需要對(duì)自己進(jìn)行的追問。關(guān)于表達(dá),便是如何說,如何寫,如何落地,如何呈現(xiàn),如何將蕪雜的意象統(tǒng)一在一起,形成藝術(shù)上的有機(jī)整體。我們?cè)趯懽魃系睦^承,便是看經(jīng)典作家如何“獨(dú)特”和“表達(dá)”,我們的創(chuàng)新便是如何發(fā)現(xiàn)自己的“獨(dú)特”和“表達(dá)”,還要在深層次上借助與經(jīng)典的對(duì)話關(guān)系而形成文脈上的真正延續(xù)性。
2
陳培浩:路魆,你的作品在《花城》《天涯》《山花》《香港文學(xué)》等刊物發(fā)表過,簡單談?wù)勀愕膶懽髦泛脝幔?/p>
路魆:從寫下《竊聲》這篇小說的最初版本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六年時(shí)間。六年時(shí)間,模糊地回憶自己的寫作歷程,心想:好像寫下了很多文字啊。但查看文件夾,大概只有四十個(gè)正式的作品留下,包括一個(gè)長篇小說《暗子》。若從更長遠(yuǎn)的時(shí)間刻度看,這四十個(gè)作品只能算是同一個(gè)時(shí)期的產(chǎn)物,但我在里面看到了許多精神的流變,這大概源于自己天性的多變,性情的反復(fù)。大學(xué)期間,我總是幻想著能在畢業(yè)前發(fā)表一篇小說,當(dāng)然最后也沒實(shí)現(xiàn)這個(gè)愿望。當(dāng)年對(duì)發(fā)表沒有什么執(zhí)念,我只是單純想知道,到底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擠進(jìn)某個(gè)文學(xué)世界。或許因?yàn)檫\(yùn)氣,在2016年,我得以在《天涯》發(fā)表第一篇散文《死與蜜》,關(guān)于祖輩的生與死。或許也是因?yàn)檫\(yùn)氣,我同年在《青年作家》發(fā)表了第一篇小說《拯救我的叔叔衛(wèi)無》,是那種填滿隱喻符號(hào)、純粹屬于幻想的小說,放到今天,我想它很難有機(jī)會(huì)被發(fā)表出來。
2016年是我工作的第二個(gè)年頭,我在建筑設(shè)計(jì)院里做設(shè)計(jì)師。當(dāng)其他同期進(jìn)來的人都已經(jīng)能在項(xiàng)目上有所擔(dān)當(dāng)?shù)臅r(shí)候,我依然無法在工作上取得太多進(jìn)展,上班時(shí)偷閑寫作,滿腦子都是文學(xué)的事。后來我選擇辭職。在長篇小說《暗子》里,我虛構(gòu)了一個(gè)建在懸崖邊的建筑設(shè)計(jì)院,主人公源于對(duì)自己天性的認(rèn)識(shí),認(rèn)為在這種涉及生命安全的行業(yè)領(lǐng)域,自己分裂的靈魂遲早會(huì)被傷害,膽戰(zhàn)心驚。我辭職的心理,部分在這里有所投射。從設(shè)計(jì)院辭職后,我去了做文案,那一年我的寫作基本停頓,文案工作對(duì)文字感有很嚴(yán)重的傷害。在做文案工作半年后,我的甲狀腺出了問題。疾病成了我寫作生活的轉(zhuǎn)折,在家養(yǎng)病期間,我決定再次辭職。一直至今,接近兩年,我沒有工作,寫作和閱讀成了我的日常。
陳培浩:有一個(gè)問題,上面也約略提到了。在你的寫作過程中,哪些作家構(gòu)成了你的師承或資源?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王小波很坦蕩地寫了《我的師承》一文來交代,但也有很多作家并不愿意讓讀者知道他的真正師承,有點(diǎn)遮遮掩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