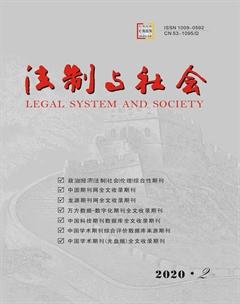當代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缺失及其轉型分析
關鍵詞 中國法理學 主體性缺失 轉型
作者簡介:劉鵬昊,北方工業大學,研究方向:法理學。
中圖分類號:D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236
現如今,中國法理學在獲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也逐漸暴露了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其中關鍵性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缺失與否”,而判斷標準即是否能夠作為理論依據指導中國法治的發展。當前,有關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的質疑已經遍及法學的各領域,對該問題的研究引發越來越多人的關注。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轉型,對此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大。因此針對當代中國法理學主體性缺失問題的探討,是新時代法理學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
一、當代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缺失的具體表現
(一)針對中國法制實踐的研究存在不足
不言而喻,法學講的就是針對法律的學問,進而明確法學和法理學都更應關注的法制實踐。在系統的法理學理論中,法理學是其中最為基礎和普遍的理論,更是作為理論對部門法學發揮著指導作用,直接關系到我國法學體系的整體發展水平。但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我國的法理學與部門法學并未形成相互溝通合作的形式,彼此之間相互獨立封閉。造成此種現狀的原因,即法理學更加關注結論是否與某種體制和理論相符合對應,并不會關注是否能夠應用于指導本國的法制實踐。所以說,我國法理學缺少對法制實踐的關注和研究,這是其主體性缺失的主要表現之一[1]。
(二)針對西方法學尚未形成反思意識
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法理學是十分需要具備反思意識的。其自身發展也是獨立且兼具創造性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在吸收和借鑒西方法理學思想的基礎上,實現對我國傳統優秀法律思想的傳承。然而實際情況皆表現為:我國法理學領域長期處于被動地位,對西方法學進行吸收,缺少對其的質疑與反思過程。例如,現階段一些法學碩博士論文,更是將是否有外文文獻參考作為判定文章質量的指標之一。此種表現實際上是西方法學的教條化,并未對其實際內容進行探討反思,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法理學理論,可想而知僅僅是生搬硬套,是中國法理學主體性缺失的突出現狀。
(三)無法應對法律秩序中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法理學相關專業的教材過于教義化、主觀化,其內在缺少嚴謹的思辨性與連貫性。進而導致我國法理學者處于政治化與公知化的困境。為了法學新生未來的發展,我國法理學主體性的轉型成為當務之急。依據中國法理學界的普遍觀點,法理學如果具備了理論指導能力,克服自身發展局限,就能充分發揮其指導作用。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中國法理學已然喪失了問題意識,相關學術研究更是不具備提出問題的能力。這就導致針對實際的法律秩序問題,借助法理學并不能從容應對。法理學的整個學科呈現出“腦死”的狀態,喪失了問題探究能力,這是其主體性尚不明顯的另一重要表現[2]。
二、當代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缺失原因分析
(一)傳統學術派系過于混雜
我國法理學發展過程歷經了一系列的派系發展,最初中國的法理學是轉經日本流傳至我國。由日本的法學家穗積陳重對德國法哲學領域中“Rechtsphilosophie”一詞進行的翻譯[3]。該法學家有這樣一個觀點即:法理學是針對法律現象的一種較為特殊的哲學,其介于法學和哲學之間。但是由于歷史與文化背景等原因的影響,當采用一種語言在翻譯另一語言的過程中,極易造成語義出現失真的情況。在“法理學”從日本流傳到中國期間,由于受到我國傳統“法理”一詞的影響,造成中國民眾對法理學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偏差。在當時將法理學看作是法學的基礎理論和分支學科。當新中國正式成立后,將法律哲學釋義為“資產階級法學中論述法的抽象概念的學科,是唯心主義的一部分”。這一時期有關法理學與法哲學等日本流傳過來的理論均受到了抵制。此時中國法學領域開始借鑒蘇聯等國家的法學教育方式,將原有的法理課程取替,開始借鑒由蘇聯引進過來的“國家與法權學說”等思想,這時,“國家”概念被納入了我國法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80年代,我國首部教科書出版——《法學基礎理論》,代表我國法理學和政治學開始獨立。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法學基礎理論逐漸被更名為“法理學”。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逐漸深入。學術界思想更加開放,西方思想開展涌入中國。而這些西方學術成果與我國原有的理論相互混雜在一起,進而引發了諸多不必要的學術爭論。總的來說,“法理學”始于清末時期流傳到我國,因為被錯誤判讀將其劃分為法學分支學科。后來又因時代不同,以及師從對象的不同,諸如蘇聯、英美法德哲學等,致使法理學界將關注重點用于不必要的爭論上,無暇將關注點放在對部門法學的理論指導上。
(二)法理學教材統編存在局限性
鑒于我國法理學的成分十分繁雜,針對如何有效融合各分支觀點,形成相對獨立的法理學科成為該學科的一大困境。就該問題的解決,我國法學界采用了統編教材的方式。縱觀我國的法理學歷史,主要有兩次較大規模的統編教材行動。一是依托于北大法律系出版社出版的《法學基礎原理》為藍本,出版的《法學基礎》。二是20世紀末期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法理學》。但是通過統編教材的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成分繁雜的問題。例如第二次統編的《法理學》教材,全書主要分為六大部分,依次為總論、本體論、起源與發展、法的運行、法的作用與價值、法與社會。而上述六部分的劃分標準并不相同,因此根本無法從其中了解到法律價值、法律效果以及哲學史上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等綜合性法學架構。其法學內在結構存在強行拼湊堆砌等嫌疑。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依賴于通過統編教材的方式促進法理學的發展,致使中國法理學的知識理論及話語體系的缺陷和弊端逐漸暴露出來。一是法理學教材內容易受到文本獨特性局限,而這種限制表現形式多樣,如意識形態限制、學科體系限制以及作者和讀者素養限制等,進而導致后期的教材雷同現象嚴重,其創新性極度缺乏;二是由于邏輯沖突和法學剛性標準的限制,教材編寫者大多缺乏思辨能力與論證能力,僅僅是自說自話的向讀者傳遞法學基礎理論;三是在開展教學活動過程中,法理學經常被簡單理解為法學基礎理論,致使其備受輕慢[4]。
(三)法理學研究范圍過于狹隘
雖然法理學在我國已經有了百余年的歷史,但對其研究并不廣泛,甚至存在狹隘的表現。具體表現為:
其一,中國法理學的相關研究并未滲透延伸到對部門法學的研究。現階段,中國法理學的眾多研究學者中,其中一些并沒有部門法學的學習背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理學研究對于我國法律實踐的引導效果。法理學研究內容,主要屬于普遍意義層面的法律,也就是說在法律范疇里,法理學是共性,而部門法學是個性,共性與個性相輔相成。在本質來講,法理學是服務于部門法學的。從我國現階段的法學教研機制來看,大多數法理學研究人員并未真正參與到部門法學的深入研究中。二者之間形成閉塞的趨勢,致使我國法理學領域的研究范圍過于狹窄。
其二,我國法理學研究工作開展期間并未聯系到相關法學知識。法學并不是獨立的,而是與社會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這表明法學研究無法實現自我延伸,必須依托于其他學科,諸如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等,以此來豐富法理學的研究內涵。但是中國多數法理學研究人員并不看重對此的研究,致使學術研究資源十分困乏,尚不能構成完善的主體性法理學。
三、當代中國法理學的轉型切入點研究
(一)始終堅持科學的批判態度
由于我國法理學是借鑒西方法理學的研究模式,所以相關研究始終沒能擺脫以往的桎梏,導致長時間以來,我國法理學呈現了較為明顯的西方化格局。這也是導致中國法理學主體性缺失的重要緣由。現階段,中國法學界面對西方法理學,已經初步具備了批判和質疑的態度。此外,本國法理學研究人員已經逐步開始探究中國發展過程中具備本土特殊色的思想精髓,并始終堅持科學的批判態度,珍視本土資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逐漸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法理學。
(二)將構建法治中國作為前提
法理學是一個廣泛的研究領域,因此為了促進其進步發展,既要秉持著開放的接受態度,使其置于法學領域的研究前沿,吸收和借鑒其他學科的最新成就,還要站在法學的層面對快速轉變的社會現實作出實時的反應與回饋,積極參與法治實踐。其中法治中國建設就屬于意義重大的社會實踐,具有其獨特的不可復制性。
基于此,我國法理學不能簡單的將西方法理學作為模板和教材,進行生搬硬套。而是扎根于法治中國的具體實踐工作中,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使法理學研究能夠凝聚著時代特點、中國特性,從而形成具有共識性認識的法理學系統,通過總結與提煉,使中國法理學相關理論更具說服性、實踐指導性[5]。
(三)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助力
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全面建設法治中國成為歷史性的重要任務,這就要求中國法理學能夠展開深入而廣泛的系統思考,從法理學的高度層面來探究依法治國的科學性、合理性,確保能夠為依法治國提供有力的理法支撐。鑒于此,要求針對法理學的研究必須面向民眾,進行大眾化的普及推廣,使其更“接地氣”。從而形成全民懂法、知法、守法的良好局面,以期推動民眾通過法律手段切實維護自身權益,樹立法律權威,讓法治意識潛移默化的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四、總結
當前,法理學在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相關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伴隨著法理學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其自身主體性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因此解決當代中國法理學主體性缺失及其轉型問題成為法理學研究的重點內容。本文從法理學主體性缺失的表現、原因作為切入點,探討轉型的方向以期為推動法治中國建設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泮偉江.在科學性與實踐性之間——論法理學的學科定位與性質[J].法學家,2019(6):30-44+192.
[2]舒國瀅.新中國法理學七十年:變化與成長[J].現代法學,2019,41(5):3-22.
[3]李擁軍,侯明明.法外之理:法理學的中國向度[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59(4):50-61+220.
[4]劉振竚.當代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缺失及其轉型研究[J].現代農業研究,2019(1):107-108.
[5]張擁軍.當代中國法理學的主體性缺失及其轉型研究[J].學習與實踐,2018(8):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