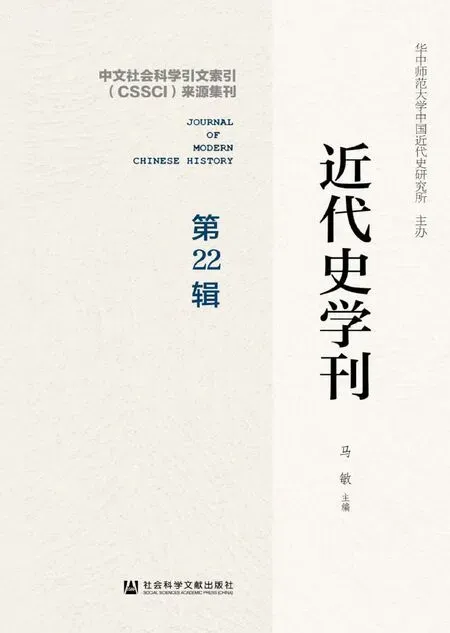西風吹散白云飛:北京白云觀鐘鼓樓與近代佛道之爭*
秦國帥
內容提要 與一般“晨(東)鐘暮(西)鼓”宗教認知不同,北京白云觀的鐘樓、鼓樓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東鼓西鐘”建筑布局。通過圍繞此一建筑布局而產生的一則與佛道之爭相關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東鼓西鐘”其實是先秦以降中國城市建筑通行的布局樣式,而“東鐘西鼓”相對而立的寺廟建筑布局則直到元末明初才正式確立下來;至于以火燒白云觀為故事高潮的佛道之爭,則本質上是近代民間宗教與全真教以文學創作為工具進行的自我理論宣揚與身份調適,與中國歷史傳統上的佛道之爭并不相同。
作為全真宗師丘處機的瘞骨之所,北京白云觀是全真道教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宮觀之一。事實上,圍繞北京白云觀,學術界已經做出了非常細致的探討,尤其是關于清中期以后直至民國時期的著名道士、傳戒歷史及其自我改革運動。①Vincent Goossaert,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中央民族大學尹志華教授圍繞北京白云觀從王常月傳戒開始直到清中期以來的傳戒歷史、北京白云觀藏《龍門傳戒譜系》、歷代律師方丈監院畫像等資料,先后發表了不下10 篇文章,如《民國時期的全真道傳戒活動考述》,《中國道教》2016年第5 期;《清代全真道傳戒若干史實再考察》,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5 輯,齊魯書社,2016。關于北京白云觀民國時期的自我改革運動,華中師范大學的付海晏有極為精彩的研究,參見付海晏《安世霖與1940年代北京白云觀的宮觀改革——以〈白云觀全真道范〉 為中心的探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 期;《1930年代北平白云觀的住持危機》,《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 期;《安世霖的悲劇:1946年北平白云觀火燒住持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 輯,2008年。在此基礎上,付海晏以白云觀為中心,形成了一部專著,參見付海晏《北京白云觀與近代中國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應該說,這些研究的出現,極大地加深了我們對于北京白云觀的了解。在這些研究中,對于白云觀的宮觀建置及沿革歷史,諸位學者雖不專門討論,但也偶有涉及;至于專門的宮觀歷史研究,學術界也絕非鮮見,自民國時期的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吉崗義豐,直至當代學者李養正、張廣保、程越等,都對白云觀的宮觀歷史及建筑布局進行過考察。①小柳司氣太:《白云觀志(附東岳廟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吉崗義豐:《白云觀の道教》,新民印書館,1945;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張廣保:《祖庭與堂下:全真教各宗系的整合》,《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第21—112 頁;程越:《全真祖庭白云觀在金元時期的沿革》,陳鼓應編《道家文化研究》第23 輯,三聯書店,2008。
現今白云觀的玉皇殿前,其東南側為鼓樓,西南側為鐘樓。與當下一般所認為寺廟的“晨(東)鐘暮(西)鼓”布局不同,白云觀這樣一種東側鼓樓、西側鐘樓的建筑布局就顯得比較特殊。無獨有偶,對于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對稱布局,日本學者吉崗義豐提過一則與之相關的佛(西風寺)、道(白云觀)二教相爭的傳說故事,而中國學者李養正、鄧夏等人則從建筑學的角度進行過分析。②鄧夏:《北京白云觀源流考與建筑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建筑工程學院,2008。不過,就筆者而言,與建筑學意義相比,吉崗義豐所提及的傳說似乎從清末民國時期的全真教研究角度來說更為有趣。準此,筆者以吉崗義豐的佛道之爭傳說為切入點,首先從建筑學角度考察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布局的現實原因,其次分析這則傳說故事的編纂起源及影響,最后借由故事編纂者立場的不同來展示佛道之爭背后全真教的自我認知與調適。
一 東鼓西鐘與東鐘西鼓
關于鐘、鼓的歷史起源及其作用,學術界已經進行了相對詳盡的考證,認為它們作為樂器,被廣泛地應用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宗廟祭祀、宮室宴享以及古代戰爭等重要的場合。不僅如此,作為能夠播放“八音”中金和革兩種聲音的樂器,鐘、鼓還能與八卦以及八方配合在一起(參見表1)。

表1 鐘、鼓與八卦、八方的關系
依照表1 中鐘、鼓與八卦的對應關系,鐘為兌,屬陰卦,鼓為震,屬陽卦。或許正是由于對鐘、鼓各自的陰陽卦象和原理有所了解,至少從《詩經》開始,擊鼓進攻成為軍事戰爭中一種的傳統:“鉦人伐鼓,陳師鞠旅。”①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87 頁。至于鳴金,則相應地成為收兵止戰的信號,如《荀子·議兵》所說:“聞鼓聲而進,聞鐘聲而退。”②荀況:《荀子》,方勇、李波譯注,中華書局,2011,第237 頁。到東漢時期,規模較大的城市如洛陽已經使用鐘聲作為宵禁的信號,如崔寔《政論》所說:“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③崔寔撰,孫啟治校注《政論校注》,中華書局,2012,第187 頁。至于如此規定的原因,還在于鐘、鼓在軍事戰爭中的作用:“鼓以動眾,鐘以止眾。夜漏盡,鼓鳴即起;晝漏盡,鐘鳴則息也。”④蔡邕:《獨斷》,中華書局,1985,第24 頁。總而言之,經過細致的考證后,玄勝旭認為:“在中國古代傳統觀念中,鐘和鼓具有明確而豐富的象征意義及文化內涵,即鐘是西、秋、金、兌、陰、退、息、止等的象征;鼓是東、春、革、震、陽、進、起、動等的象征。”⑤玄勝旭:《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清華大學,2013,第10 頁。
若上述分析無誤的話,按照中國古代的傳統觀念,如一座城市中分別設有鐘樓和鼓樓,鐘樓應該位于西方,其功能是司夜,鼓樓應該位于東方,其功能是司晨,即建筑布局是東鼓西鐘,功能區分則是晨鼓暮鐘。然而,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直到隋唐時期,中國的宮殿建筑中才真正出現東西對稱分布的鐘樓與鼓樓,至于其布局,則正是之前所說的“東鼓西鐘”。⑥玄勝旭:《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第16 頁;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2006,第110 頁。直到元朝時,宮殿建筑當中“東鼓西鐘”的布局才發生根本改變,如元大都大明殿前鐘樓和鼓樓的位置變成了“東鐘西鼓”。不過,到明清時期,宮殿中的鐘鼓樓設置逐漸廢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中的鐘鼓樓對設制度。然而,或許是受到元朝“東鐘西鼓”布局的影響,“就城市鐘鼓樓的東西方位而言,除了元大都、明清北京的‘南鼓北鐘’布局以外,其他城市中‘東鐘西鼓’和‘東鼓西鐘’布局都可以見到”。①玄勝旭:《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第27 頁。換言之,至少對明清時期的一般居民來說,無論是在城市中,還是在宮殿中,“東鐘西鼓”或“東鼓西鐘”并非一定如此的建筑布局。
然而,與皇家宮殿以及城市的建筑布局不同,到唐武宗時期,中國佛教已經形成了鐘樓在東的建筑制度,只不過與鐘樓相對而設的并非鼓樓,而多為經藏,即“東鐘西經”的布局,如泉州的開元寺、長安的保壽寺以及西明寺等。②玄勝旭:《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第33 頁。直到元末明初,中國的佛寺中才開始出現“東鐘西鼓”的對稱格局,而到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之后,伴隨著大規模寺觀修建活動,“東鐘西鼓”成為佛寺中固定的建筑布局和制度。③玄勝旭:《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第65—68 頁。
作為現今北京白云觀的前身,天長觀在金大定十四年(1174)被詔重修,并得賜名“十方大天長觀”。至于其重修后的建筑布局,鄭子聃所撰《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稱:
前三門榜曰十方大天長觀。中三門曰玉虛之門,設虛皇醮壇三級,中大殿曰玉虛,以奉三清,次有閣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慶,以奉元辰眾像。翼于東者,有殿曰澄神,翼于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東有鐘閣曰靈音,兼奉玉皇上帝、虛無玉帝,次有閣曰大明,以奉太陽帝君,次有殿曰五岳,以奉諸岳帝暨長白山興國靈應王。西閣曰飛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寶君,次有閣曰清輝,以奉太陰皇君,次有殿曰四瀆,以奉江河淮濟之神。④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第741—742 頁。波浪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從上文中可以發現兩個事實:第一,作為皇家敕修的道教宮觀,天長觀的建筑布局遵循了與傳統佛教寺廟相同的原則,即“東鐘西經”,而非我們現在所通常以為的“東鐘西鼓”;第二,天長觀的鐘閣與經閣,并非純為報時或藏經之用,還肩負著祭祀的功能,因為它們里面供奉著神像。
關于此時天長觀的布局,日本學者吉崗義豐在20世紀初訪問北京白云觀時,依據上述資料對其進行過推定復原(見圖1)。從復原圖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天長觀的鐘閣與經閣分立于東方與西方。①〔日〕吉崗義豐:《白云觀訪信錄》,汪帥東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第163 頁。不過,當1227年丘處機去世之后,尹志平在天長觀(其時受成吉思汗之命改稱長春宮)東側建立了白云觀,我們從復原圖中亦可以找到它的位置。然而,關于此時白云觀的建筑布局,限于史料缺乏,我們不得而知。元明易代之后,天長觀廢壞為墟,而白云觀則由于明朝前期諸多帝王而保留下來。明正德十三年(1518),白云觀在朝廷的支持下得以重修,而恰恰是在此次重修過程中,白云觀出現了鐘樓與鼓樓的配置:

圖1 金十方天長觀復原
幾飾舊者,如殿廡若干楹;而移建者,則長生堂、施齋堂;新增者,則鐘鼓樓,配于方丈也。①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第703 頁。
盡管此次的重修碑文并沒有明確提及鐘樓、鼓樓的位置,然而,借助于現今北京白云觀鐘樓、鼓樓俱為明清寺廟中常見的重檐歇山頂二層樓閣式形制,②關于明清時期中國寺廟中鐘鼓樓的建筑形制及布局特征,參見玄勝旭《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第93—113 頁。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北京白云觀的鐘樓和鼓樓應為明正德重修后的遺產。③鄧夏:《北京白云觀源流考與建筑研究》,第84—85 頁。換言之,明正德十三年重修時,白云觀鐘樓與鼓樓的建筑布局就已經是“東鼓西鐘”了。

圖2 現白云觀鐘鼓樓
對于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布局,李養正在其《新編北京白云觀志》介紹配祀建筑時予以了關注,稱鼓樓始建于明英宗正統八年(1443),“從建置時起便位于玉皇殿前東側”。①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第98 頁。至于鐘樓,則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燕王朱棣再建毀于戰火時的長春宮時重新建置了鐘樓與鼓樓:
燕王朱棣命再建長春宮(位今白云觀西側),建置鐘樓(位長春宮東側)、鼓樓(位長春宮西側)。②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第99 頁。
李養正還進一步解釋了為何現今白云觀是“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
關于鐘鼓樓的位置,按古規制,一般畢是在坐北朝南宮觀的東側建置鐘樓,在其西側建置鼓樓,可是現在白云觀卻未沿慣例,而是鼓樓位東,鐘樓位西,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現存鐘樓乃原長春宮建置,長春宮毀于火,但其東側的鐘樓幸免,明代正統年間在此鐘樓之東營造白云觀,鐘樓也就在了白云觀中路殿堂的西側,爾后在中路殿堂東側建置與鐘樓相對立之鼓樓,于是也就變成東鼓而西鐘了。這既表明了由長春宮到白云觀位置的變遷(東移);也表明因大鐘既懸樓內,搬遷不易,故只得權便而破例建置,并無宗教方面的用意。③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第99 頁。
對于這番介紹,首先,我們從現有碑刻史料中找不到明確記載稱鼓樓建于正統八年以及燕王朱棣重新建置了鐘樓、鼓樓等事,盡管朱棣為藩王時確實重建長春宮,英宗皇帝朱祁鎮也確實重修過白云觀;其次,長春宮毀于火以及鐘樓幸免等事,我們也未找到任何明確的史料記載;最后,因鐘樓搬遷不易而新建鼓樓于東的說法,從重修的規格即皇家工程以及現實的建筑布局來說,也實難以成立。④可參見李養正的自述碑文以及當前從建筑學角度所開展的研究,如李養正《新編北京白云觀志》,第735—737 頁;鄧夏:《北京白云觀源流考與建筑研究》,第84—85 頁。
與李養正的看法相反,如前所述,筆者認為,現今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實際上是明正德十三年新建時方確立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當時重修碑刻所遺留下來的明確記載,另一方面是出于明永樂遷都北京之后“東鐘西鼓”或“東鼓西鐘”的城市建筑布局并無一定之規的現實狀況。盡管李養正在說明“東鐘西樓”的建筑布局時稱“按古規制”,但正如我們之前所述,寺廟建筑中“東鐘西鼓”建筑布局的形成并沒有那么久遠,其確立于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后,而恰恰也正是在此時期,“東鼓西鐘”的城市布局時常出現在普通民眾的視線當中。因而,北京白云觀之于當前或許頗為讓人驚奇的“東鼓西鐘”布局,在明正德時期或許并不讓人感到奇怪。

圖3 白云觀(左)與東岳廟(右)鐘鼓樓位置
除此之外,可以作為側面證據的是,與白云觀相似,同樣是道教宮觀的北京東岳廟,其鐘樓、鼓樓的建筑布局也是“東鼓西鐘”。①在現存有關東岳廟建筑布局的記載中,筆者只找到一份康熙四十三年的《東岳廟碑文》,稱東岳廟曾于康熙三十七年遭焚毀,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重修完畢。在這次重修過程中,鐘樓和鼓樓得以建立,不過對于兩者的具體位置并沒有提及。參見北京市朝陽區文化委員會編《北京東岳廟與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輯錄》,中國書店,2004,第117 頁;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王云五主編《十通》第九種,商務印書館,1936,第57751—57752 頁。到民國時期,有兩份關于東岳廟結構的平面圖,一份來自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其中鐘樓與鼓樓的位置為東鼓西鐘,另一份來自美國學者富善(Anne Goodrich),其中鐘樓與鼓樓的位置為東鐘西鼓。參見小柳司氣太《白云觀志(附朱岳廟志)》,第629 頁;〔美〕安·絲婉·富善:《東岳廟》,李錦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第257 頁。在富善的書中,她稱這幅東岳廟的平面圖由坦恩·布洛克(Janet Rinaker Ten Broeck)提供,而據布洛克自述,這幅平面圖的真正創作者是“不知姓名的藝術家和詹姆斯·卡什(James Cash)”。不僅如此,布洛克在《1927年的北京東岳廟》一文中還明確稱“從山門進到第一進院,兩側邊墻內筑有重檐鐘鼓樓,左邊是鼓樓,刻有鼉聲;右邊是鐘樓,刻有鯨音”,即前述“東鐘西鼓”布局。參見〔美〕安·絲婉·富善《東岳廟》,第231、202 頁。盡管富善對在她之前出版的小柳司氣太的《白云觀志(附東岳廟志)》一書有所了解和引用,但她書中所載東岳廟的平面圖以及布洛克所記載的鐘樓與鼓樓位置應該是錯誤的。作為泰山東岳廟即現今岱廟的復制建筑,布洛克引用了法國學者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泰山》一書,稱北京東岳廟的建筑布局與泰山東岳廟相似,但在沙畹所提供的泰山東岳廟布局圖中,鐘樓與鼓樓的位置是“東鼓西鐘”,而且,筆者認為,至少從明末查志隆的《岱史》開始,泰山東岳廟的建筑布局便已如此。參見édouard Chavannes: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Paris:Ernest Leroux,1910,p.130;查志隆:《岱史》,明萬歷戴相堯刻本,筆者私藏,1.15b-16a。準此,與富善以及布洛克的記載相反,小柳司氣太所說北京東岳廟“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應該是正確的實地調查資料,并且,重檐式的建筑結構是明清的通例,極有可能是康熙敕修的重建過程進而更早(盡管并無明確的歷史記載)就已經如此布局了。
二 火燒白云觀的故事與傳說
借助上述對建筑歷史的考察,可以確定,與中國佛教寺廟自唐時便已確立鐘樓在東布局的制度不同,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最晚從明正德十三年便如此了,至于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北京白云觀作為屢受朝廷眷顧的皇家道觀,其建筑布局與當時的宮殿和城市建設需表現出一種同步性。至于更深刻的宗教原因,我們并未找到與此相關的任何記載。
然而,1940年代,日本學者吉崗義豐繼小柳司氣太調查北京白云觀時,在鐘樓與鼓樓的位置問題上提供了一則與佛道之爭相關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白云觀的西側有座佛寺,叫作西風寺。這座寺廟的和尚與白云觀的道士冰炭不投,他們之間的斗牙拌齒也從未平息。不知不覺間,白云觀的勢力越來越大,并逐漸壓過西風寺,和尚們因不堪忍受屈辱而四散,于是寺廟就被白云觀所合并。據說自那里起,這座寺廟的鐘樓就作為道觀的鐘樓所用,故形成了今日所見之格局。①〔日〕吉崗義豐:《白云觀訪信錄》,第16—17 頁。
對于這則故事,吉崗義豐也有自己的看法,即認為“這只是一個傳說,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足以使人信服。況且,還有其他像白云觀這樣來排列鐘鼓樓位置的道觀”。不過,對于這則傳說產生的原因,吉崗義豐還是有所推測:
從長居于白云觀附近的年長者的口中聽到這個傳說時,我覺得它應該來自于元朝的《佛道論衡》。元代期間,佛道的論爭異常激烈,主要是白云觀的道士與佛僧之間的論爭,最后道士徹底敗論,論爭的結果導致了憫忠寺(今北京外城的法源寺)的《道藏》焚毀事件。那個虛構出來凸顯白云觀強盛的傳說,或者是由對佛僧的橫暴感到悲憤的道士,或者是由同情道士遭遇的民眾所編造的吧。因為佛教畢竟是外來宗教,而道教則是中國人的傳統信仰,所以道教雖在實際的佛道論證中失敗了,但卻被三人成虎地演繹成取得了完勝,如果將其作為民族排外心理的案例表現,這絕對是頗具價值的資料。①吉崗義豐:《白云觀訪信錄》,第17 頁。
吉崗義豐認為這則故事來自元代的佛道之爭,此為合理的推斷,不過他將故事的起源歸于“對佛僧的橫暴感到悲憤的道士,或者是由同情道士遭遇的民眾所編造的”,則因文獻涉獵不足而有失偏頗。據元代《佛祖歷代通載》和《至元辯偽錄》載,全真教在憲宗朝佛道論辯失敗之后,除要焚毀偽經45 部外,還應將之前非法侵占的佛寺237 所歸還,但全真道士甘志泉仍據吉祥院而不還,“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為征理,長春宮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梃,毆擊僧眾,自焚廩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②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4 冊,第716 頁;釋祥邁:《至元辯偽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289 冊,第460 頁。事實上,正是長春宮道士自焚廩舍而反誣僧人的舉動,導致了隨后的第二次佛道論辯以及全真教的進一步失敗。③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p.425.或許,佛教當中關于雙方直接沖突的這則記載,才是吉崗義豐所聽聞傳說故事的原型和靈感來源。不過,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與之相似的傳說直到清朝中期方產生,即明正德十三年重建鐘鼓樓的三百年之后。
據車錫倫的《中國寶卷總目》,清道光元年(1821),北京地區出現了一部以王重陽和全真七子故事為主題的仙傳,名為《七真天仙寶傳》。④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203 頁。在這部典型的民間宗教寶卷中,丘處機憑借高超的道法擊退了進犯的番王,宋朝皇帝因此龍心大悅,封他為國師,并命他在清靜寺養靜參禪。不過,丘處機的獲封遭到了同為國師且受皇后寵幸的白云禪師的嫉妒。是時恰逢皇后有孕在身,皇帝便命二人預測皇后所懷是男是女,白云禪師算定是女,丘處機亦算定是女,不過為顯道法高超,便針鋒相對地猜測是男。兩人立下賭約,丘處機若輸的話將頭割于白云禪師,白云禪師若輸的話將雙眼剜于丘處機,并將他所居住的白云寺騰讓出來。結果,皇后生產之時,丘處機令六丁六甲將外邦的男嬰與皇后所生的女嬰調換,白云禪師因此輸掉了白云寺:
宋帝登了九五殿,宣詔二人來朝參。叫聲國師你失算,你算是女偏生男。
二人賭帖孤為見,失算要把眼睛捥。國師聞言嚇破膽,三呼萬歲把恩寬。
貶職以免捥雙眼,遂出京外不入簾。邱祖講情職休貶,看在小臣臉面前。
宋帝準情看卿面,僧職不貶位要遷。從今休住白云觀,另尋廟宇把身安。
陀僧遵旨下金殿,清靜小寺去參禪。陀僧憂氣且不嘆,再說圣上封邱仙。
真人八卦是妙算,不由孤王心喜歡。加封妙化真君宦,受享天爵在帝前。
從今請住白云觀,半付鸞駕助威嚴。邱祖謝恩回廟轉,白云寺中去煉丹。
丘處機占據白云觀之后,白云禪師又幾次三番企圖羞辱丘處機,卻被丘處機一一化解。眼見扳不倒丘處機,便聽從一位精通堪輿之術的弟子的建議,在白云觀西邊修建了一座名為西風亭的寺院,取“鐘鼓響,吹西風,白云吹盡;云從龍,虎從風,廟倒人傾”之意,要把白云觀夷為平地。對于白云禪師的舉動,丘處機早已知曉,并做出了應對:
卻說陀僧在西風寺右邊修一西風亭,懸起鐘鼓。邱祖門人知覺,報與邱祖,言道:“把左邊鐘倒掛鼓樓,右邊鼓倒掛鐘樓。”門人細問來歷,邱祖道:“過了三日,自然明白。”
邱祖念,早已知,計法兩定;鐘移東,鼓移西,風來倒行。
西風亭,擊鐘鼓,果然風應;白云寺,敲鐘鼓,反吹吼聲。
不倒那,九日內,風狂太勝;西風亭,遭天火,竟化灰塵。
這正是,想害人,人反吉慶;把自己,必害得,莫處安身。
陀禪師,怪徒弟,地理不應;怨桐油,那風鑒,未曾學精。
借由上述對故事的簡述,可以得出兩點明確的認識:第一,白云觀原為白云禪師居住的佛寺,是丘處機憑借自身高人一籌的道法強行奪取而來;第二,面對白云禪師等佛教僧人的回奪之舉,丘處機最終憑借鐘鼓倒置的高超道法徹底將他們打垮,西風寺被焚為平地,而白云禪師也被發配云南。準此,“東鼓西鐘”成為丘處機取得最終勝利的紀念和象征,盡管他的奪觀和毀寺等行為似乎并不是那么光彩。
與《七真天仙寶傳》相似,清同治十二年(1873),湖北漢陽府皇殿刊印了由全真教龍門派弟子王誠章作序的《七真祖師列仙傳》。在這部作品當中,丘處機因為巨大的戰功而獲得了元順帝的賞識,得封護國軍師長春真人。心生妒意的白云禪師便與丘處機賭算皇后所生為男為女,丘處機最終因道法高超而取得了勝利,并在獲得白云禪師原住的大廟之后,將之改名為白云觀。至于隨后發生的事情,《七真祖師列仙傳》似乎是用白話文的形式重新講述了一遍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來歷:
那白云禪師的門人,又遇了皇后緣法,皇后許修一座寺院。眾僧人領了千萬兩銀子,就在白云觀西邊造寺。當家的和尚名叫李善,能通陰陽地理、五行生克之法,取名西風寺。眾僧問曰:“為何叫做西風寺?請問緣故!”李善道:“我原有心事在內,咱的大廟與邱祖住了,我心不服。咱明陰陽,按五行之法,他住的叫白云觀,我取名西風寺,西風吹去,白云必散,邱祖門人必然散去,這廟仍是我們的。”眾和尚聽言稱妙,都說:“師兄高見。”邱祖的門人聞說此言,告于邱祖,說西風寺的緣故。邱祖吩咐道:“把左邊的鐘掛到鼓樓上,右邊的鼓架到鐘樓上,互相掉換。”門人問故,邱祖道:“過了三日,自然明白。”后到第三日,西風吹起,大鐘不打自鳴,打西風頂回,反在廚房內吹起火來。眾僧忙提水潑火,潑他不滅,一時滿寺通紅。眾僧都跑出來躲過,就把西風寺燒了個干凈。這正是“主意不正害別人,誰知反被損自身;勸君須要行公道,報應來時難脫身。”
不過,與《七真天仙寶傳》不同的是,《七真祖師列仙傳》在講述完這個故事之后添加了評論,即引文最后畫浪線的部分。而恰恰是這四句類似七言律詩的評論,表明故事的編纂者完全站在全真教一方,因為白云禪師及其門人建造西風寺是“主意不正害別人”的表現,而丘處機“東鼓西鐘”的應對策略則是“報應來時難脫身”的象征。
或許是意識到之前兩部仙傳雖然并未對丘處機持批判態度,但白云觀的來歷實屬并不光明正大,所以,清光緒十九年(1893),另一位龍門派道士黃永亮重新編纂了一部《七真因果傳》,并修改了丘處機與白云禪師之間的恩怨。對于丘處機憑借高超的道法贏得了原屬白云禪師的白云寺,《七真因果傳》借“地利”之說進行了一番合法化的解釋,并特意注明丘處機并非強占白云寺:
你道邱真人為何定要這白云寺?因北京地方王氣正盛,知是久都之地,欲借此盛地開一開壇,演一演教,二者白云禪師應在南邊發跡(南僧北道——引者注),開闡三江一帶地方,若久在京都守著這白云寺,終難開闡,故此竟將這寺院占了,使他好向南去普渡眾生,故而天地生人,各有其所(說明邱祖不是強占其寺院——引者注),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或利于彼而不利于此,上士修真,必取其相生相應者而居,其于相克相妨者則避之,此謂得其地利也。
隨后,白云禪師屢施計謀,如飲毒酒、戴金冠等事,但被丘處機一一識破,并次次退讓,自歸其咎。在丘處機的感化之下,白云禪師亦自悔用意差失,兩家重歸于好。元順帝眼見如此,正式將白云寺改名白云觀,令丘處機居住,而白云禪師則移居他寺:
朕已發皇餉,與國師新建寺院,待工程圓滿,可將白云寺佛像移于新修寺院內,另取寺名,將白云寺改為白云觀,重塑道祖神像,以別僧道,各有所宗,為千秋香火,作萬世觀瞻,素不負二師保朕之功也。
準此,順天時而得地利,行忍讓而息紛爭,假王命而正名分,丘處機占領白云觀成為順天意、承王命而得人心的正義舉動。不僅如此,對于之前兩部仙傳都記載的火燒白云觀一事,《七真因果傳》也進行了技術化處理,稱白云禪師的門人不滿丘處機的奪寺之舉,于是謀求反攻:
內有一位好事的僧人,自言懂風鑒:“若依我主意,在白云寺前面修一座西風寺,管教白云寺大敗。”眾僧問致敗之由,那多事的和尚曰:“豈不聞風水怕人破?以我西風吹彼白云,何愁不敗?何愁不散?”
當眾僧人將募修西風寺的緣簿拿到白云禪師面前時,白云禪師卻否定了他們的計劃:“邱真人與我原無怨恨,這白云寺是我輸與他的,又非他來強奪。昨日天子曾御賜皇餉,另修寺院,汝今捏造這些言語,滋生事端,倘天子知道,降下罪來,老僧擔帶不起,你要修你去修罷。”眾僧聞言便放棄了這個計劃,只有起意修建西風寺的僧人心中不服,逢人便宣揚他的計劃,以恐嚇白云觀的道士:“我化得有幾千銀子,要在白云寺前面修座西風寺,我這西風一起,將他白云定然吹散,管教他們那些道人,一個也住不成。”白云觀的道士在聽聞此事之后,也散播出去一些流言:
他以為說些大話,將白云觀道友們嚇一嚇,殊不知道友們十個就有九個會說大話,聽得這些言語,也散些流言出去,說是:“叫他只管修,等他修起,我們在前面筑起一垛高墻,如扇子一樣,等他風來,我一扇扇去,名為返風,自吹自散。”忽一人大喊曰:“你們能返風,我便去放火。”
事實上,依《七真因果傳》所說,佛教復奪白云寺的舉動也就到此為止了,佛道雙方只是產生了一些言語上的沖突,并未進入實質階段:佛教僧人的建寺之舉僅為逢張對李的流言,而白云觀道士的返風放火也以“大家笑了一陣”而告終。然而,對于之前兩部仙傳言之鑿鑿的火燒白云觀之事,《七真因果傳》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解釋:
誰知就有那好事的道人,把那些言語傳將出去,也是逢張對李胡說一番,年代久了,話柄還在,相傳不實,以為真有此事,說和尚修一座西風寺,要吹散白云觀,被道人用個破法,回風返火,把西風寺燒了。其實并無此事,不過那邊出了一個多事的和尚,這邊出了一個講大話的道人,你說過來,我說過去,惹動了那喜歡生事的人,編成話柄,有許多老修行在京地土生土長,都把這莊事情摸不清白,今依古書校正無訛,庶使后世門人不爭強論弱,則于因果有光輝也。
若按此說,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實際上與佛道之爭沒有任何關聯,但《七真因果傳》維護白云觀及全真教形象的意圖也十分明顯。
上文按刊印時間之先后依次介紹了三部仙傳的最初版本及其中與白云觀“東鼓西鐘”相關的故事,但每種仙傳在清中期直到民國時期不僅有多個版本,而且流傳的地域非常廣泛。光緒三十三年(1907),同善社信徒云山煙波氏在《七真天仙寶傳》的基礎上,縮編了一部《七真寶卷》,幾乎原文重述了火燒白云觀傳說。丘處機因軍功獲封國師之后,同為國師的陀僧心懷不滿,加之因賭輸皇后所生為男為女而將白云寺讓于丘處機,便在他弟子的建議之下修建西風寺,最終卻引火燒身:
說陀僧,這場事,憂氣不平;細思想,怎教我,有臉見人?
有命我,去白云,讓與道人;清靜寺,一小廟,怎么安身?
千思想,這件事,如何計定;金想到,廣智徒,地理高明。
要破他,白云觀,風水可定;廣智言,甚容易,一敗而凈。
白云觀,白虎頭,造一廟庭;鐘鼓響,起西風,白云吹盡。
命魏相,上金殿,奏了一本;清靜寺,和尚多,無處安身。
白云觀,地基寬,右邊修整;王準奏,造一個,西風寺名。
邱祖爹,早已知,安排制鎮;鐘移東,鼓移西,風來到行。
西風寺,擊鐘鼓,果有西風;白云觀,敲鐘鼓,西風反吟。
不到那,一百日,風火齊臨;西風寺,一霎時,化為灰塵。
這正是,想害人,反害自身;陀國師,怪廣智,地理不明。
雖然是,做國師,無人奉敬;悔不該,與妖道,斗智逞能。
到今日,想破了,修己安分;時不際,運不泰,聽天由命。
鑒于《七真天仙寶傳》與《七真寶卷》之間的文本連續性,云山煙波氏的縮編雖然并沒有太多的新意,但還是進一步強化了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建筑布局背后的宗教含義,即佛教與道教之間的廟產之爭。
與《七真寶卷》相似,1919年,萬國道德會刊印了由全真居士養真子改編的《重陽七真演義傳》,而這部仙傳的文本來源,則是《七真祖師列仙傳》。據養真子的改編,丘處機因為軍功獲封國師之后,與皇后供奉的國師白云禪師進行了一場生男生女的比賽,丘處機雖然憑借道法高超而贏得了比賽,卻并未占取白云禪師的大佛寺,而是返回了太極宮。后來,丘處機為完成玉皇大帝開壇衍教七十二處的命令,請求元朝皇帝的幫助,于是,元帝敕令建造白云觀,并為之親書匾額。白云禪師賭算失敗被發配云南之后,他的弟子們心懷不滿,于是起意在白云觀西修建西風寺,冀求火燒白云觀:
白云禪師的門人又結了皇后大緣,許修大寺。眾僧領銀十萬兩,就在白云觀西邊修寺,當家和尚名叫理善,能通陰陽五行、生克制化之法,題名西風寺。眾僧問其緣故,理善說:“我有妙法在內。俺們的寺被邱神仙住了,我心不服,按法修理,蓋西風吹起,白云必散。”眾僧聽言,個個稱妙,都說:“方丈高明。”邱神仙早已默知,偶見梧桐落下一葉,即命曉事門人,把左邊的金鐘取掛鼓樓上,右邊的大鼓移架鐘樓頭上,門人問何故,邱神仙道:“過了三日,自然明白。”立秋后四日,西風吹起,鐘不打自鳴,把西風頂回,反在和尚廚房吹起火來。眾僧慌忙提水救火,潑他不滅,一時滿寺通紅,眾僧都跑出躲禍,把西風寺燒個干凈。這正是“主意不善害別人,誰知反害自己身;勸君個個行公道,報應來時難脫身。”
由此可見,《重陽七真演義傳》的基本立場與《七真祖師列仙傳》相同,即丘處機是“行公道”而獲勝,而與《七真祖師列仙傳》稍有不同的是,北京白云觀在《重陽七真演義傳》中是受皇帝敕命而建,并非奪佛教廟產而來。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養真子如此重述這則故事,合理地解釋了北京白云觀為何是“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
綜合以上五部仙傳,我們可以看出它們的基本態度和傾向:首先,《七真天仙寶傳》和《七真寶卷》作為兩部具有明顯文本繼承性和民間宗教背景的仙傳,都認為白云觀是丘處機強占白云禪師的寺廟而來,且“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來源于全真教與佛教的廟產之爭;其次,《七真祖師列仙傳》和《重陽七真演義傳》因為都有全真道士的參與擁有著相似的觀點,即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是丘處機“行公道”的象征,只是《七真祖師列仙傳》認為白云觀原為佛寺,是由丘處機憑道法贏來的,《重陽七真演義傳》則認為丘處機雖然憑高超的道法贏得了賭局,白云觀卻是由皇帝敕命另建;最后,《七真因果傳》認為丘處機雖然憑高超的道法贏得了賭局以及作為賭資的白云觀,卻順天意、承王命而得人心,甚至賭輸的白云禪師也認為兩方之間不存在糾紛,至于火燒白云觀之事,則僅止于流言,并未成為事實,進而,北京白云觀的“東鼓西鐘”布局與佛道之爭并無關聯。
如果說從建筑史角度來考察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可以確定這種規制是明清時期城市和宮殿建筑的常見樣式的話,那么,清中期以來的七真文學作品則揭示了“東鼓西鐘”背后全真教與佛教之間的紛爭。由于現有資料的限制,我們并不能通過文本獲知此一宗教敘事的源頭,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文學作品的存在及流通,事實上已經影響到人們的宗教認知。1935年,馬芷庠撰寫《北平旅行指南》,提及北京白云觀中作為景點之一的窩風橋:“相傳早年有西風僧與邱真人斗寶,西風僧在觀之西建一廟名西風寺,取‘西風吹散白云飛’之義相克制,邱真人因在觀中建一窩橋以御之。”①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經濟新聞社,1935,第195 頁。

圖4 現白云觀窩風橋
此一說法盡管與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布局無關,它們共同的來源卻是清中期以來七真文學作品中的佛道之爭。至于前述吉崗義豐的傳說,則是在共同的佛道之爭母題之下,用“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來進行填白和解說。
三 佛道之爭與仙傳編纂
關于佛教與道教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在王重陽和全真七子駐世之年并沒有發生過,相反,我們從他們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他們與佛教僧人的和諧相處以及對于“三教合一”反復強調。①盡管全真教與當時以萬松行秀為代表的佛教在三教合一的方向上有所不同,但這尚不足以引發爭論。參見〔日〕窪德忠《金代的新道教與佛教》,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7 卷,中華書局,1993,第478—496 頁。然而,自丘處機去世之后,以耶律楚材為代表的佛教居士首先發難,對丘處機進行了公開指責。此時全真道教一方并沒有明確回應,秦志安《金蓮正宗記》記載譚處端被打落牙齒一事時稱是禪師所為,或許這可以看作佛教指責在全真道士內部引起的波瀾。至于元憲宗以及元世祖時期所發生的兩次佛道辯論,全真教雖然是道教方面當中的教派之一,卻承擔了最嚴重的損失,部分全真道士申志應等甚至遭受了脫冠落發、改道為僧的羞辱。②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第382—382 頁。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清中期以來的七真文學作品與全真教在元初的這段悲慘經歷有文本關聯,但考慮到佛道之爭的巨大影響力,吉崗義豐將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傳說與此事聯系在一起,也屬情理之中。與此同時,吉崗義豐之所以能在1940年代的北京聽聞此傳說,極有可能與上述五部七真作品多版本、大范圍流傳有關。據筆者調查,自清中期直至民國末年,《七真天仙寶傳》等五部仙傳共計至少產生了43 個版本,傳播到18個省份。在所有這些版本中,以丘處機為代表的全真宗教力量都實現了對佛教勢力的逆襲:北京白云觀不僅原本就是佛教的產業,其“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更是代表對佛教力量的最后一擊和完全勝利。
不過,與元初的佛道之爭主要由佛教方面記載不同,正如前文約略提到的那樣,這些七真文學作品中的佛道之爭,或者是出于民間宗教家之手,或是出于全真道士之手。正是因為編纂者自身不同的宗教認同,清中期以來七真文學作品中的佛道之爭表現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特點,即在佛教完全失聲的情況下,民間宗教雖然借用了佛道之爭的戲劇性故事,但其目的在于一視同仁地借取佛道兩家的優勢與長處;而全真道士則完全站在了道教的立場上,在強調全真教優越性的同時,盡量緩和與佛教之間的緊張和沖突關系。

表2 清中期以來五種七真仙傳的版本及刊刻地點統計

續表
首先,就《七真天仙寶傳》及其縮編本《七真寶卷》而言,據清宣統三年的養真仙苑刊本,《七真天仙寶傳》問世是由于王重陽和全真七子的仙跡“流芳年遠,而丹書之更易未免無訛;遺后歲深,而道情之添改更多虛杳”。全真教祖師鐘離權和呂洞賓有鑒于此,降鸞開化演繹了三十二回的《七真天仙寶傳》,“闡明七真修行奧妙,引證三教悟道格言”,最終的目的則是希望“鐘呂二祖造法船,諸仙七真指云路,愿人人而上天堂,望個個以離地獄”。對于自署康熙壬辰年(1712)造作于北京北皋雙龍寺禮義堂的乩文《七真天仙傳序》,由于背景資料的缺乏,我們沒有任何關于其真正創作者的信息。然而,到宣統元年(1909)青陽山人易南子作《序刊文》時,我們可以明確地知道,易南子為一貫道十七祖路中一的弟子,甚至出資助刊的李正旺等人也都是一貫道的信徒。①秦國帥:《 〈七真天仙寶傳〉 的版本、內容及使用初探》,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7輯,第139—141 頁。至于《七真寶卷》,據現有的研究,它的改編者云山煙波氏是清末民國時期另一個重要的民間宗教教派同善社的信徒。②秦國帥:《明清民國時期七真度化故事的流傳及版本研究》,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6 輯,第66—67 頁。事實上,無論是一貫道還是同善社,從現有的研究資料來看,它們對于儒、釋、道都持開放的態度,不論是它們著名的歷史人物,還是各自獨特的修行方法,一貫道和同善社都予以認同和接納,并以之為自身的先天大道或一貫之道服務。或許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考慮,在描述丘處機斗法白云禪師時,《七真天仙寶傳》和《七真寶卷》一方面直言道教的法術比較高超,另一方面對于丘處機詐贏白云觀的行為也并未避諱,此中情由,主要在于無論是道法還是佛法,都遠不及一貫道和同善社推崇的先天道。
其次,就《七真祖師列仙傳》和《重陽七真演義傳》而言,我們看到,《七真祖師列仙傳》對于全真七子的態度并不友善,不僅大量使用“賤人”、“孽障”、“牛鼻子道教”等鄙俚粗語,而且借用托名張三豐的《無根樹》細致描寫劉處玄于妓院行采戰雙修之術,一度使劉處玄成為近代娼妓行業的祖師爺和保護神。①依筆者拙見,劉處玄“插花劉真人”的稱呼應是從此一仙傳開始使用的。或許是由于《七真祖師列仙傳》的廣泛流傳,加之其中劉處玄與妓女采戰雙修的描寫,“插花老祖”逐漸變成近代以來娼妓行業的祖師爺和保護神。參見劉平《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靈》,李長莉、左玉河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第469—482 頁。此一仙傳現今可查的最早編纂者全真道士王誠章卻依舊認為《七真祖師列仙傳》“字挾風霜,非蕓編瓠史之可比;聲成金石,豈宋艷班香之能同。萬緣俱凈,八垢皆空。讀百回之不厭兮,舌本生蓮;覽一字之莫減兮,頭點頑石”。與之相似,《重陽七真演義傳》的編纂者全真道士養真子也高度推崇王重陽與全真七子的仙跡,認為“重陽七真本記,必有功世道,有益人心”。但因為擔心《七真祖師列仙傳》此類仙傳存在誤導民眾的可能性,所以養真子又依照《道藏》等書,“凡傷風敗俗之言,邪術異端之說,左道旁門之謬,概不容以雜入”,刪正了舊有的七真傳記。之所以如此,正如筆者在他處所言,王誠章和養真子的全真道士身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正是基于自身的宗教認同,他們才在宗教感情上明顯地偏向了全真教,進而在描寫丘處機與白云禪師斗法以及白云觀的來源問題上,一改之前民間宗教家的做法,有意識地美化了丘處機的形象,并合情、合理、合法地解釋了白云觀的由來。
至于《七真因果傳》,其編纂者黃永亮也是一位全真道士。他之所以起意重新編纂王重陽與全真七子的故事,主要是因為舊有的七真仙傳“文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不僅如此,在最終目的上,他與王誠章和養真子也并無二致,“以通俗語言,鼓吹前傳,以人情世態,接引愚頑,以罪福醒悟人心,以道妙開化后世,其于勸善懲過,不為無助”。不過,在具體的仙傳編纂策略上,黃永亮卻不以“借法力而為衛道”、“托仙佛以作引誘”的做法為可取,既不認可丘處機與白云禪師因廟產之爭而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更是從根本上否認了“火燒白云觀”一事可能性,只不過將之淡然處理為以訛傳訛的流言而已,一如我們在前述引文中所看到的那樣。
總之,作為中國宗教歷史上產生時間最早的兩個教派,佛教與道教關系盡管絕非全然和諧相處,全真教與佛教的關系也并非一直相安無事,但在近代以來的全真仙傳當中,丘處機與白云禪師的斗法以及火燒白云觀等事,卻成為不同仙傳編纂者闡述自身宗教教義的文學武器或工具:民間宗教如一貫道和同善社著力描寫了兩者之間的沖突,同時無意于照顧道教或佛教的形象,而是以之反襯先天大道的優越性;全真道士則在高調宣揚丘處機道法高超的同時,著力淡化丘處機作弊取勝的不義之舉,至于火燒白云觀之事,則因不同編纂者采用不同的編纂策略而有無兩可,但無論如何,全真教相比于佛教的宗教優越性是無可置疑的。①事實上,以全真教著名的祖師以及他們的故事作為宗教爭論的工具,如呂洞賓飛劍斬黃龍等,并非清代才有的創新之舉,而是元代就已經產生了。參見吳光正《八仙故事系統考論——內丹道宗教神話的建構及其流變》,中華書局,2006,第73—109 頁;Joshua Capitanio,“Buddhist Tales of Lü Dongbin,” T'oung Pao,Vol.102(2016),pp.448-502。換言之,在近代民間宗教大量興起的社會背景下,全真仙傳中的佛道之爭,已經不再是歷史上佛教與道教之間的爭斗了。
四 結論
上文以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為切入點,首先討論了鐘、鼓本來所具有的方位含義及其在城市和寺廟的不同應用,其次從清中期以來的全真仙傳考察了白云觀如此布局的文獻記載及各仙傳不同的態度,最后分析各種不同態度形成的原因及其背后各自的宗教考量。準此,可以得出以下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晨鐘暮鼓”及其背后所隱含的“東鐘西鼓”建筑布局其實并不符合先秦以來的文化傳統。相反,從《詩經》開始,直到帝制晚期,中國城市建筑的布局一直遵循的是“東鼓西鐘”樣式。至于寺廟中“東鐘西鼓”相對而立的建筑布局,直到元末明初才出現,并在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后成為中國寺廟固定的布局樣式。
第二,現今北京白云觀“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對于明清時期的城市居民來說,并非罕見之事。這主要還是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宗教地位,即白云觀在明清時期屢受皇室照拂,因此,與同樣地位特殊的北京東岳廟相似,它們“東鼓西鐘”的布局應該是遵循當時的城市建筑布局,含有濃重的政治含義,卻與宗教爭斗無關。
第三,清中期以來相繼成書并廣泛流傳的全真仙傳,以佛道之間的宗教爭斗解釋白云觀“東鼓西鐘”建筑布局的成因,雖然似乎與全真教在元朝佛道之爭中失利有關,實際上卻只不過是民間宗教家的文學創造而已,表明自身借取但又顯然優越于佛道二教的宗教教義和地位。相反,全真道士則同樣訴諸文字的力量,或解釋了白云觀宮觀來源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東鼓西鐘”的建筑布局正是其與佛教相比宗教優越性的明證,或拋棄了這樣一種敘事傳統,表明佛道兩教之間并不存在沖突,火燒白云觀之事更是子虛烏有,力圖消解這一廣泛流傳的故事背后所隱含的挑起宗教沖突的可能性。
總之,宗教歷史無疑是宗教文學創作的源泉,但同時,宗教文學創作反過來重塑了人們對宗教歷史的認識,一如火燒白云觀這則原本極有可能是清代中期才虛構出來的故事,卻直到現在都流傳于教門內外,并影響著人們對于北京白云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