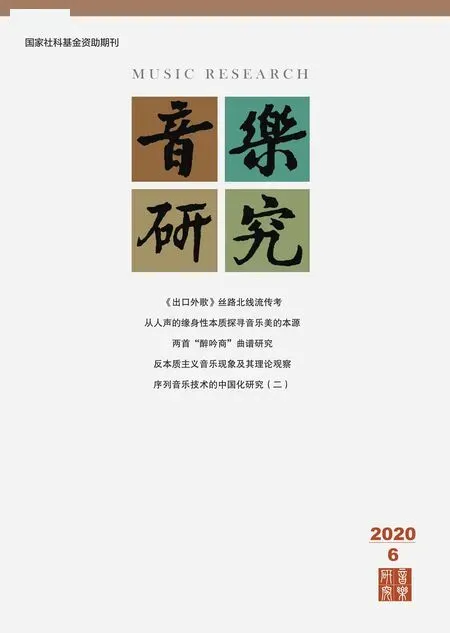兩首“醉吟商”曲譜研究
——曲牌“原型—類型化”視角下的詞樂流變考證之一
文◎李宏鋒
宋代是近古音樂形態風格融匯新變與定型發展的重要階段之一。詩詞音樂作為兩宋音樂乃至藝術創作的突出代表,對當時音樂作品、旋律形態乃至時代風格的形成與轉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是見證宋代音樂融通各民族、各地域色彩并內斂、精致發展,最終開啟一代“新音樂”之風的重要體裁之一。
本文擬以《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以下簡稱《九宮大成》)所錄姜夔【醉吟商】①說明:后文論及的【醉吟商】,均特指《九宮大成》所錄的這首【醉吟商】曲牌。曲譜為對象,分析其音樂形態和曲牌原型,并與《白石道人歌曲》同名樂曲相比較,在綜合辨析前人成果基礎上,以曲牌“原型—類型化”理念,探究不同時代同名曲牌的形態差異和原型關聯;辨析《九宮大成》所載詞樂譜的音樂屬性,關注詞樂在南宋至清初的形態流變與內在規律,完善基于“宮調變遷”與“原型分析”的曲牌音樂考證的方法論基礎。
一、【醉吟商】分析
《九宮大成》成書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共收錄正體、別體、變體曲牌及套曲等計6639 曲,②參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中國音樂詞典》(增訂版),人民音樂出版社2016 年版,第858 頁。涵蓋詞樂、諸宮調、散曲、南戲、雜劇和傳奇等各時期主要音樂體裁,是考證特定時代音樂面貌的重要參考文獻。從中國傳統音樂歷程及其“移步不換形”的創作模式③關于中國傳統音樂“活態”傳承下獨特的集體創作模式及其與西方專業音樂創作異同的分析,參見秦序《音樂創作門外談:試從“大創作”角度看中西音樂創作的若干異同》,《中國音樂學》2020 年第1 期。看,《九宮大成》所存非一時一地之信息,其樂曲的“層累”“疊壓”性質及學術內涵,如不同時代宮調信息的存留,唐宋詞樂演變與“昆化”譜的關系,同名曲牌的“原型—類型化”關聯,曲牌創曲和潤腔的傳統繼承等,都是我們基于“實踐第一”和“傳統是一條河流”等理念,開展歷史形態分析與曲調考證的重要資源。從這種意義上講,《九宮大成》這部匯聚了清初豐富南北曲資料的曲集,依然是我們考證歷代古樂不可忽視的存在。④關于《九宮大成》所錄唐宋詞樂譜的時代屬性與音樂特質等問題,楊蔭瀏、傅雪漪、黃翔鵬、鄭祖襄等諸位先生均有討論。參見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 (上冊),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 年版,第296—298 頁;傅雪漪《試談詞調音樂》,《音樂研究》1981 年第2 期;黃翔鵬《〈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簡譜示意本〉題記》,《中國音樂學》1998 年第3 期;鄭祖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詞調來源辨析》,《中國音樂學》1995 年第1 期。
(一)【醉吟商】解譯
【醉吟商】曲牌,收于《九宮大成》卷十一“南詞宮譜”,列于“中呂宮正曲”,譜式如下(見圖1)。

圖1 《九宮大成》【醉吟商】⑤[清]周祥鈺等《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乾隆十一年(1746)內府朱墨套印本。圖片由浙江音樂學院孟凡玉教授提供,謹致謝意。
與姜夔原作相比,這首【醉吟商】第一句首缺一“又”字,宮調歸屬與《白石道人歌曲》“雙調”的調高標注整體一致(詳后)。因樂曲被歸為南曲曲牌,工尺譜板眼記寫稍復雜,除常規板眼符號外,又出現了豎長條形的徹眼符號“□”。這是一種在唱腔出音之后的眼,與實眼相對,又有腰眼、掣眼、側眼、宕眼之稱。⑥同注②,第900 頁。徹眼的使用意味著弱拍(或弱位)上切分音的出現,譜中“細”“千”“鴉”三字便是。
傅雪漪所著《中國古典詩詞曲譜選釋》,有【醉吟商】的譯譜,樂曲依近代笛色定為小工調(1=D)。今參照傅先生譯寫成果,依張炎《詞源》八十四調表所示“中呂宮”和宋大晟律黃鐘音高(d1),以夾鐘宮均調高(1=F)為準,按首調工尺譜原則解譯該譜,并附板眼符號如下(見譜例1)⑦本譯譜參考了傅雪漪的譯譜方案,其中調高 “宮=F”的選擇及“一點”二字的節奏處理與傅先生有異。參見傅雪漪編著《中國古典詩詞曲譜選釋》,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 年版,第85—86 頁。。
筆者曾對宋以后歷代宮調理論變遷做過集中探討,認為從宋代俗字譜隸屬的俗樂二十八調體系,到明清時期工尺譜隸屬的工尺七調系統,期間的俗樂調名含義曾發生部分脫離、部分保留原有樂學內涵的情況。工尺譜字也經歷了從明初以正宮調為基礎的固定調讀譜,到清代以小工調為基礎的首調讀譜等轉化。⑧參見李宏鋒《明代音樂圖譜所見工尺唱名體系初探》(《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 年第3 期)、《清代工尺七調系統的豐富發展與多類型并存》(《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6 年第2 期)等文。這種因宮調理論變遷而導致歷代宮調信息疊壓的情況,在明清曲譜中有較為普遍的存在。
譜例1 《九宮大成》【醉吟商】譯解
以《九宮大成》這首【醉吟商】為例,其曲譜前標記的“中呂宮”調名,保存了南宋姜夔創制此作品時的宮調信息——樂曲“雙調”隸屬中呂宮均。在后世演變中,雙調之名被指示樂曲宮音的中呂宮取代,俗樂調名被簡化為失去“煞聲”內涵,只用來標記調高的符號,起著類似“工尺七調”的指示作用。樂曲的工尺譜字記寫,也由原來的固定調記譜,變為更適于南北曲演唱之需的首調唱名。首調唱名譯譜,使【醉吟商】樂曲用音嚴格遵循著南曲的五聲性規范;F 宮定調標準,既反映出《九宮大成》部分俗樂調名對唐宋樂學內涵的延續,也使全曲整體處于適合人聲歌唱的音域。

傅雪漪曾以夏承燾、楊蔭瀏譯譜為基礎,對比《白石道人歌曲》與《九宮大成》所收的兩首“醉吟商”,認為二者曲調截然不同,后者完全是昆曲化的結果,“在旋律上基本是‘劇曲’的行腔,字少腔多(特別是加贈板的南曲曲調),散板的曲譜,則完全同于昆曲劇中人上場時所唱的引曲;其次無論引曲、正曲,無論是按南曲處理或按北曲處理的詞調,在風格行腔方面,和清代乾隆時期流行的昆曲(如《納書楹曲譜》《吟香堂曲譜》以及手抄本曲譜)基本一致。”⑨傅雪漪《試談詞調音樂》,《音樂研究》1981 年第2 期,第50 頁。
傅先生對《九宮大成》音樂的昆曲性質和文獻屬性的定位值得重視。另一方面,若以歷時性視角觀照《九宮大成》與歷史音樂間的可能聯系,則這首同名【醉吟商】曲牌與姜夔擬定的《醉吟商小品》⑩為與后進入曲牌系統的【醉吟商】相區別,后文姜夔原作“醉吟商小品”及宋代“醉吟商”曲名特以書名號標識。另,文章涉及兩首樂曲的聯系論述時,曲名統一以引號標識。是否截然不同?昆化的南北曲曲牌與宋代同名詞調音樂間,是否存在關聯的話可能?一系列問題,或可從曲牌“原型—類型化”視角獲得進一步研討。
(二)【醉吟商】之曲牌原型
曲牌作為中國傳統音樂的結構要素乃至思維模式,在音樂傳承、創造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所蘊含的‘思維框架’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特性”[11]喬建中《曲牌論》,原載《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又收入喬建中文集《土地與歌》,山東文藝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8 頁。。如果一首樂曲的唱詞格律和音調形態基本確定,且成為詞曲創作以資借鑒的標準,它的詞曲結構形態便具備了曲牌意義,成為一種既定模式影響著后世的音樂創造。基于曲牌音樂的這一特征,從理論上講,一種樂調一旦進入曲牌系統,其音樂構成的基本屬性,包括旋律的宮調、基序(motif)、原型等,便以一種相對穩定的形態貫穿音樂實踐,成為同名曲牌(當然也存在同名異曲或同曲異名的情況)音樂傳承的核心要素之一。[12]此處有關曲牌音樂構成要素的論述,參見李宏鋒《三首【脫布衫】曲牌音樂對比分析——兼及傳統曲牌“原型—類型化”分析的方法論思考》,《中國音樂》2019 年第6 期,第117—118 頁。正因如此,一般說來,同名曲牌在旋律構成方面,人們往往會基于一定的曲調原型,因不同時期風格、體裁及表演需要,做出新的加工創造,使傳統音樂形態呈現出絢麗多彩的風貌。在這種音樂的創新發展中,曲牌宮調、基序與原型相對穩定性,是傳統音樂“萬變不離其宗”的基礎。可以說,近古時代中國音樂歷史上的創新,幾乎都是在繼承先前藝術資源上的新發展,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基于以上思考,筆者曾提出傳統曲牌音樂分析中的“原型—類型化”構想,力圖循此理念深入認識傳統音樂的多樣化構成,并以此為基礎逆流而上,“探尋特定歷史時期音樂體裁的結構特征與相互關聯,抽繹隱藏于音樂表象背后能夠反映民族音樂傳統的普遍規律,包括旋律形態原型(素材原型)和結構邏輯原型(語法原型)”[13]同注[12],第138 頁。,深入發掘包括《九宮大成》在內的傳統音樂文本與音響的歷史內涵,不斷豐富和充實古代音樂風格史研究。
以此反觀南宋姜夔的《醉吟商小品》,可知其問世后,文辭格律和旋律原型即成為后人創作因循的基礎,逐漸完成了【醉吟商】的曲牌化歷程。至清初該曲牌收入南曲時,其旋律已根據南曲風格和潤腔需要極大發展,“昆化”的結果使其從表面看與《白石道人歌曲》中的《醉吟商小品》原作差別很大。然而,如果我們從“基序”和“原型”視角審視【醉吟商】的旋律構成,或可得到若干新的認知。
下面據譜例1 譯譜,將【醉吟商】的曲牌旋律原型分析如下(見譜例2)。
【醉吟商】共6 句,分作上下兩闋,每闋3 句,句式字數為(4+6+4)+(5+6+4)。譜例2 中的小節線用以區分各句;全音符是從各句旋律中提取出的骨干音,其局部連接構成曲牌的“基序”,即核心音高序列;環繞在全音符周圍的黑符頭各音,是樂曲行腔時形成的主要裝飾音。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曲牌骨干音的提取,參考了德國作曲家保羅·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旋律構成理論。欣氏認為,根音、最高音、最低音、節奏重音等在旋律構成中具有特殊意義,這些特殊意義的音形成二度連接時可獲得良好旋律。將這些地位重要的點用一條線連接起來,不考慮點與點之間較次要的旋律部分,便得到級進線條,這是旋律構成的重要因素。級進線條也會視旋律結構的復雜程度,表現出不同層次的重疊。[14]〔德〕保羅·欣德米特著,羅忠镕譯《作曲技法》(第一卷),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年版,第195 頁。欣德米特所言旋律構成的“級進線條”,與本文使用的“核心序列”(基序)基本相當;考慮到五聲性旋律中小三度的級進性質,特將小三度音程作級進處理。各樂句依照旋律級進和骨干音突出原則提煉出基序并作系統組合后,便得到整首曲牌的旋律原型。
譜例2 【醉吟商】之曲牌原型
觀察譜例2 中全音符所示曲牌原型可知:第一、三句落音相同,為徵;第二、四、五、六句,落音也相同,為商;上闋落于徵,下闋煞于商,前后段構成五度支撐關系。從旋律形態看,第一、二句旋律骨干音基本呈平穩進行,核心音分別為徵和商,兩句間形成五度呼應;第四、五句都落于商音,均強調自上而下的級進線條;第二、六句的原型圍繞宮、商兩音展開,旋律基本是以二度基序為基礎的環繞進行。原型分析表明,以商音為樂句結音的基序,是塑造【醉吟商】曲牌性格的主要因素;同時,兩個以徵為結音的基序,在旋律展開中起著五度鏈支撐作用。各樂句基序共同構成的原型框架,是旋律據以展開的基礎,也是【醉吟商】曲牌傳承中“應萬變”之“不變”因素的體現。

二、《醉吟商小品》的宮調結構與曲牌原型
《白石道人歌曲》保存的17 首樂曲,依據音樂部分的不同來源,可分為如下類型:(1)姜白石記錄整理前代樂曲后,依曲填詞的作品《霓裳中序第一》和《醉吟商小品》;(2)友人范成大(或其樂工)作曲,姜白石填詞的作品《玉梅令》;(3)姜白石本人作曲、作詞的自度曲,14 首。盡管這些樂曲的音組織邏輯同屬唐宋流行的俗樂二十八調體系,但依楊蔭瀏譯解方案參照[15]譯譜參見楊蔭瀏、陰法魯《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人民音樂出版社1957 年版。,三類作品風格確有明顯差異——相對姜夔自度曲而言,范成大制曲的《玉梅令》強調同宮五聲性特質,呈現出鮮明的清新、秀美之風;而包括《醉吟商小品》在內的第一類樂曲,風格更偏古樸、凝重,是宋代詞樂保存前朝舊曲的例證。
(一)《醉吟商小品》的宮調結構
詞作《醉吟商小品》寫于1191 年,是姜白石依據舊傳“醉吟商《胡渭州》”琵琶品弦法寫譜并填詞的作品。下段引文摘自詞前“小序”。
石湖老人謂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濩索(一曰濩弦)《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16][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附別集)》卷2,《叢書集成初編》據“榆園叢刻本”排印,商務印書館1939 年 版,第29 頁。按,原書作“湖渭州”,今從《欽定詞譜》作“胡渭州”,見[清]王奕清、陳廷敬等《欽定詞譜》卷2,中國書店2015 年版,第22 頁。
《胡渭州》本為唐代教坊曲名,是流傳至宋的琵琶曲調之一。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載,黔南節度使王保義女善彈琵琶,夢美人授曲,其中便有《醉吟商》,可知此曲唐代即有。[17]參見陰法魯《詞與唐宋大曲之關系》,載《陰法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 年版,第132 頁。另據吳坰《五總志》記載,《醉吟商》曲在北宋末年尚存,其友人田為(字不伐)通音律、善琵琶,“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應圣羽》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不伐死矣,恨此曲不傳”[18][宋]吳坰《五總志》,《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三”,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可能由于《醉吟商》曲高和寡,到南宋時便很少為詞人所用了。
姜白石的“小序”表明,“醉吟商”確實為琵琶曲,是《胡渭州》的宮調之名。[19]《欽定詞譜》卷2,第22 頁。辛亥年(1191)夏天,姜白石從金陵楊廷秀官邸的琵琶樂工那里,學得醉吟商《胡渭州》彈法,便記寫下這首曲譜。楊蔭瀏認為,小序中所言“實雙聲耳”,又樂曲名《醉吟商》,可知其曲調為商調無疑。又因樂曲以“么”字結尾,對照張炎八十四調表可知,樂曲只能是中呂宮均“雙調”的商調。小序所言“雙聲”實際是“雙調”的別名。
關于樂曲的旋律結構,楊先生進一步論述道:
本曲仍分前后二疊;二疊之句法雖相同,樂調卻相異。真正完全相同的,就只有二疊最后兩字的音譜而已。然不同的樂調中,卻并不是沒有法則可尋。前疊“春歸”“千縷”的音譜之順級下行,與末尾“啼處”二字的音譜之上行作對比;后疊“鞍去”“休訴”的音譜之順級下行,與末尾“解語”二字的音譜之上行作對比。這樣,乃在變化之中,有了整齊之美。[20]以上詞樂分析、譜字考訂及《醉吟商小品》譯譜,參見注[15],第28、41 頁。
據張炎八十四調表和楊蔭瀏譯譜,可知《醉吟商小品》實為夾鐘(F)均夾鐘(F)宮之商(G)調,基礎音列為“G—(#G)—A—B—C—D—E—F—G”。為表“醉吟”商之意,原曲特以小二度清商(#G)裝飾商音,別具韻味。因該曲是姜白石從樂工處學得的瀕臨失傳之曲,可知倚照舊曲填詞是南宋詞樂創作的基本類型之一。“胡渭州”的曲名,也印證了此曲雜有的“胡夷里巷”之曲特質。姜白石以《胡渭州》宮調名創制新作,確立了“醉吟商”的地位,為宋代詞樂又添一例不同風格的詩詞曲調。
(二)《醉吟商小品》之旋律原型
姜夔這首保留著北宋、五代甚至更早音樂信息的《醉吟商小品》,作為【醉吟商】曲牌的“正體”[21]成書于清康熙年間的《欽定詞譜》在收錄詞譜時,特別強調以該詞牌首創之人所作本詞為正體,以彰顯其調譜正源。(參見《欽定詞譜》“出版說明”,第2 頁。)依此,則姜夔所作《醉吟商小品》即為【醉吟商】曲牌的正體,后世同名曲牌詞作或曲譜編創,均為該曲牌的“變體”或“又一體”。,其基序及原型有何特征?與后世同名曲牌(變體)樂調間有無相通之處?我們可據前述曲牌原型分析原則,抽取《醉吟商小品》的旋律原型,將其與【醉吟商】原型對比如下(見譜例3)。
譜例3 兩首“醉吟商”原型對比

譜例3 中,第二行譜為《醉吟商小品》旋律原型,系據楊蔭瀏譯譜提煉所得。[22]楊蔭瀏譯譜的《醉吟商小品》,采取沒有調號的譜式記寫。事實上,如考慮到雙調的F 均正聲音階歸屬,該曲調號應采用一個降號記寫,旋律中的B 音(變徵)前要加還原記號。今暫從楊先生譯譜方案,調號未做調整。由于姜白石歌曲譜多“一字一音”的特征,除個別裝飾小腔外,曲譜中的每個譜字幾乎都可納入原型,以全音符形式呈現出來。第一行是【醉吟商】曲牌原型的下方純四度移位,即將譜例2 原型從“宮=F”移到 “宮=C”,以便和《醉吟商小品》正體原型對比。[23]《九宮大成》中的各曲牌調高,編者并無明確規定。《九宮大成·凡例》云:“今度曲者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于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衰,則用凡字調或六字調。”可知其編者有意讓演唱者根據自身嗓音條件和旋律的“抗”(偏高)或“衰”(偏低),酌情選擇調高。前文譜例2 將【醉吟商】按“宮=F”譯譜,是為體現“中呂宮”樂調的歷史內涵。這里為原型比對方便,將譜例2 旋律作移調處理,與《九宮大成》對曲牌調高的約定并不矛盾。
觀察兩曲調原型不難看出,《醉吟商小品》的上、下闋均落于商(G);將其與【醉吟商】的第二、四、五句對比,二者對應樂句的旋律原型基本相同;如將《醉吟商小品》原型中的宮(F)、清商(#G)、變徵(B)音以相鄰音級替代,則這三句原型幾乎完全相同。此外,兩曲原型的第三句為反向進行;《醉吟商小品》最后一句下方純四度移位后,與【醉吟商】的終止原型完全相同。兩首樂曲原型框架的初步對比表明,該曲牌在從宋至清的傳承中,旋律間依然存在或多或少的聯系。換句話說,即便【醉吟商】是清人按南北曲風格所創,其中也蘊含了歷史上該曲牌原型的若干“基序”,不能否認其與正體原型間的可能性關聯。
宋代詞樂從音樂構成來看,既包括詞人“倚聲填詞”的各類既有曲調,如唐大曲民間化后形成的短小體裁,民間樂曲典型化后形成的曲牌樣式等;也包含體現詞人個體風格的音樂創作。它們都是兩宋多樣化詞樂風格的有機組成。陰法魯認為,白石道人的這些詞樂作品,不僅保存了一些傳統的音樂因素,也可能間接吸收了一些民間音樂因素,反映著當時作曲技巧的一個側面。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材料,探索宋代音樂發展過程中某個流派的特點和成就。[24]參見注[15]之“姜白石和他的作品”一節,第4 頁。筆者認為,這種對姜白石自度曲音樂性質與價值的評價,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從目前學界研究來看,一些學者或以楊蔭瀏譯譜音調怪異、姜夔為雅樂復古派代表、自度曲僅代表個人創作風格等為據,認為白石道人歌曲“旁譜”不足以作為擬構宋詞音樂的證據,其價值甚至遠在《九宮大成》等詞樂資料之下。然而,如將白石道人歌曲置于唐宋宮調理論的整體邏輯之中,充分考慮不同時代宮調體系變遷對詞樂形態的影響,以“曲調考證”及曲牌“原型—類型化”視角重新審視音樂歷史傳承,則姜白石自度曲的獨特樂風及與后世曲牌間的承繼關系亦非無跡可尋。
三、兩首“醉吟商”旋律對比及衍化探析
除以曲牌骨干音為準開展原型一致性對比外,我們還可以曲牌唱詞為準對比兩首“醉吟商”,觀察二者的原型關聯和旋律衍展手法,剖析不同時代曲牌的旋律構成與衍化關系。
(一)兩首“醉吟商”旋律對比
現將【醉吟商】旋律降低純四度(自 “宮=F”移調至“宮=C”),作為對照譜第一行,工尺譜字標于五線譜上方;將楊蔭瀏翻譯的《醉吟商小品》作為對比譜第二行,俗字譜標于五線譜下方,考察二者在曲牌原型和旋法結構上的關聯。
譜例4 中,畫圈音符表示旋律核心音,各句核心音連接構成核心音列(基序);連接上、下兩聲部核心音的實線,指示兩首樂曲共有的基序和原型;連接上、下聲部的虛線,指示經變化(轉寫)后二者一致的核心音;方框內音符為樂曲煞聲;最后一行輔助譜,是《醉吟商小品》第六句的C 均轉寫,以便與九宮譜旋律形態比較。現將兩首“醉吟商”旋律形態方面的關聯歸納如下。
第一句,兩曲均強調G、A 音;“春歸”二字,【醉吟商】將《醉吟商小品》作下方二度移位,突出G 音,并使白石譜B 音變為九宮譜羽音A。
第二句,兩曲均圍繞核心音D 平穩進行;【醉吟商】第四、五小節,增加了向上波動的裝飾性潤腔;《醉吟商小品》核心音B 轉為九宮譜C、D 兩音(虛線所示)。
譜例4 兩首“醉吟商”旋律對比

第三句,為該詞作上闋,兩曲均煞于G 音;【醉吟商】旋律級進下行,《醉吟商小品》級進上行,呈同結音逆行,構成不嚴格的鏡像對稱。
第四句,兩曲核心音框架相同;【醉吟商】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向上波動的裝飾性潤腔。
第五句,【醉吟商】的前半句為級進上行的旋律擴充,后半句下行核心序列,與《醉吟商小品》基序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醉吟商小品》中“一點”的B、#G 兩音,在【醉吟商】中已變為C、A;“心”字F 音也被【醉吟商】中的E、G 取代,突出了旋律的五正聲風格。
第六句,【醉吟商】前半句同樣為上行級進衍展,后半句的核心音序列與《醉吟商小品》基本相同;將《醉吟商小品》第六句下移純四度“C 均轉寫”,與【醉吟商】框架的一致性清晰可辨。
通觀譜例4 旋律對比譜可以看出,其一,兩首“醉吟商”之間存在較密切的關聯;由《醉吟商小品》定型的基本旋律框架,是【醉吟商】據以展開的重要基礎。【醉吟商】通過對《醉吟商小品》原型的五聲化、潤飾化處理,以及唱詞句讀(板眼、長短)關系的重新組合,使【醉吟商】形成與明清南曲風格相一致的音樂表達。其二,二者不僅呈現出宋詞曲牌在后世“昆化”的具體樣態,也揭示出曲牌“昆化”的原型所本。南北曲所存前代曲牌,其音樂唱腔應與詩詞格律一樣,都是在對曲牌正體及原型的代代承續中不斷新變發展的。
(二)兩首“醉吟商”旋律衍化關系
《醉吟商小品》以宋代流行的俗字譜記寫,【醉吟商】以明清流行的工尺譜記寫。前者隸屬唐宋俗樂二十八調系統,為中呂宮均“雙調”;后者隸屬明清工尺七調系統,調高可據演唱者嗓音條件酌情選擇。筆者先前研究表明,明清工尺七調在傳承發展中,經歷了以“尺”字為調首,以“五”字為轉調關鍵音的“正宮調工尺七調系統”;以“合”字為調首,以“工”字為轉調關鍵音的“小工調工尺七調系統”;以“上”字為調首,以“乙”字為轉調關鍵音的“乙字調工尺七調系統”等類型。各工尺調名系統在不同樂種實踐中又有因地制宜的豐富和衍化。[25]參見注[11]。
《醉吟商小品》所用譜字為“厶、マ、一、么、ㄥ、人、フ、リ、六”,其中“合(厶)”字應黃鐘律。陳旸《樂書》“篳篥”條末注文曰:“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后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譜其聲。”[26][宋]陳旸《樂書》卷130“樂圖論·胡部·篳篥”條,清光緒丙子春刊本。可知“厶”為當時“眾器之首”篳篥的筒音。及至明代,俗字記譜轉為工尺記譜,調首音出現向“尺”字轉化的傾向,即“尺”字成為某些管色樂器的筒音標識。在宋、明宮調系統變遷大背景下,宋代俗字譜文獻或出現適應新時代記譜規范的轉寫——以宋俗字譜調首音“合”對應明代工尺譜調首音“尺”,各譜字形成如下對應關系(見圖2)。

圖2 宋代俗字譜與明代工尺譜音列轉寫對照
如果按明代以“尺”為調首的正宮調工尺七調系統轉寫宋譜,即以“厶”與“尺”相對應,以宋俗字譜“リ”(C)為宮的下徵音階重讀《醉吟商小品》,則《醉吟商小品》中的“一”(F,對應“凡”字)和“フ”(B,對應“一”字)即成為工尺譜中的“清角”和“變宮”兩個變音。為突出南曲工尺譜的五正聲核心地位,這兩個譜字分別被臨近的“マ”或“么”(E 或G,對應“工”或“六”字)和“リ”或“人”(C 或A,對應“上”或“五”字)替代;《醉吟商小品》中的“勾”字“ㄥ”(#G,對應“下五”),則被“人”(A,對應“五”字)就近取代。
經過上述轉寫,《醉吟商小品》的俗字固定調記譜,便衍化出一個以“上”字為宮的五聲性曲牌框架(見譜例3 第一行譜)。以這個新的五聲性曲牌原型為基礎,按照明代以來逐漸定型的南曲韻唱規范潤腔,即通常所謂的“昆化”(包括旋律裝飾和與之相應的句讀重組),便得到【醉吟商】新的“曲唱”[27]洛地先生在《詞樂曲唱》中指出,“曲唱”是“以文化樂”的唱,根本特征是“依字聲行腔”。該著系統論述了“依字聲行腔”的規律與特點,以及“詞樂”與“曲唱”的演化與構成,可資參考。參見洛地《詞樂曲唱》,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 年版。風格。由此推測,姜白石創作或記錄的17 首詞樂譜,經過明代樂(文)人的創造性轉寫和曲唱,被作為一種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言的“被發明的傳統”繼承下來,成為唐宋以來曲牌“原型—類型化”制約下“移步不換形”式傳承的例證。姜白石詞樂創作是宋詞音樂諸多流派之一,在后世又演變為《九宮大成》同名曲牌唱韻,表現出不同的時代風尚和音體系傳承。[28]南宋姜白石的自度曲與明清南北曲傳承的宋詞音樂,二者形態及表現各不相同。孫玄齡指出:“這種同為宋詞,但音樂表現不同的現象,大概是兩種音樂體系的傳承。所以,楊(蔭瀏)先生把兩種都翻譯了出來,并無側重于一種。”參見孫玄齡《實踐與音樂研究——談楊蔭瀏先生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對昆曲的使用》,《中國音樂學》2019 年第4 期;收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編《天韻社曲譜》(下冊),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 年版,第188 頁。結合近古宮調系統變遷和聲腔體系發展,可推測這種大規模的音樂風格轉型,大抵發生于明代南曲(南戲,尤其昆腔)興盛之際。
四、溯流探源:近古詞樂流變蠡測及考證構想
本文對兩首“醉吟商”的初步分析表明,唐宋以來詞調音樂在流傳中,會基于對曲牌正體和原型的傳承,產生適應時代風尚的新變,繼而創造出具有特色鮮明的“新藝術”風格。明確這一點,可為完善古譜解譯和曲調考證提供新的方法論視角。
(一)近古詞樂流變與宋明音樂轉型
關于唐、五代及兩宋音樂的胡化之風,文獻多有反映。《舊唐書·音樂志》曰:“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29][后晉]劉昫等《舊唐書·音樂志三》卷30,中華書局1975 年版,第1089 頁。北宋陳旸論及當時宮廷音樂時說:“至于曲調,抑又沿襲胡俗之舊,未純乎中正之雅。其欲聲調而四時和,奏發而萬類應,亦已難矣。”[30][宋]陳旸《樂書》卷157“樂圖論·雅部·歌·曲調上”,清光緒丙子春刊本。蘇軾《書鮮于子駿楚詞后》亦云:“譬之于樂,變亂之極,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于雅音乎?”[31][宋]蘇軾《蘇軾文集》卷66,中華書局1986 年版,第2057 頁。這些出自士人立場的論述,表明當時無論宮廷還是世俗音樂,均沿襲了“胡俗之舊”。一些代表性胡俗舊曲被反復使用,融入填詞所依曲調中來,逐漸具有曲牌屬性。包括姜白石之類能自度曲的詞人,即便其“先撰腔子,后填詞”[32][宋]趙令畤《侯鯖錄》卷7,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184 頁。,也難完全擺脫胡樂風尚的影響。脫胎于中外音樂大交融背景的詞樂,以“未純乎中正之雅”的“胡夷里巷之曲”,構筑起近古時代音樂歷史形態流變的邏輯起點。這一音樂風格的直接體現,就是規范旋律用音和宮調結構的俗樂二十八調系統。張炎《詞源》記錄的這一宮調系統,是唐宋樂調規范的客觀反映,其均、宮、調三層次的宮調模型,在《敦煌樂譜》和《白石道人歌曲》等作品中均有實踐[33]相關論證,參見李宏鋒《含英咀華 聚沙成塔——從兩例古譜譯解看“同均三宮”理論的實踐意義》,《音樂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26—41 頁。,是涵蓋“五正聲”和多民族、地域音樂元素在內的、更為宏闊的理論架構。
然而,從文獻記載看,這種有著多調性色彩空間的音樂語言,隨著詞樂時代的消退和劇曲時代的來臨,在金元之際已然為之一變。清劉熙載《藝概》曰:“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又引王元美之語云:“詞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后有南曲。”[34][清]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載俞為民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清代編,第四集),黃山書社2008 年版,第457—458 頁。稱以曲補詞之不足、以南曲補北曲之闕如,可見兩宋詞樂在金元開始轉變,宋代詞樂與元代北曲、元明南曲的音樂形態已明顯不同。
時至明清,詞曲風尚又為之新變。據清毛奇齡《竟山樂錄》記述,金章宗時已有“以番樂為北調,古樂為南調,北調則七聲并行二變交作,而南調則僅周旋于五聲之間”的觀念;元末明初這種觀念進一步強化,“始有南曲行于世,則是古樂用五聲,今樂用七聲。凡和平宛轉,春容樂易,如今吳人所傳之南曲,即古樂也。”[35][清]毛奇齡《竟山樂錄》卷4,“叢書集成初 編”本,商務印書館1937 年版,第53—54 頁。黃翔鵬認為,后世所謂南曲五聲、北曲七聲的總結,不過是人為制造的結果,大抵出現于明中葉之后。[36]參見黃翔鵬《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分期研究及有關新材料、新問題》,載《樂問》,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0 年版,第217 頁。這種人為約定的法則一經提出,便迅速在明代劇壇得到實踐。在歷代音樂逐漸失傳的背景下,明代樂人以較之二十八調簡化得多的方式轉寫(唱奏)舊譜,包括弱化俗樂調內涵、首調讀譜、以上代勾、乙凡不分上下、消弭變律等,加之適應時代語音和審美的依字行腔與旋律潤飾,終于翻出以南北曲為主流的“新聲”。這些依前朝舊曲“昆化”得到的曲牌,至清初在《九宮大成》中獲得系統整理。[37]如果從這一傳承過程看,對于宋詞音樂而言,《九宮大成》確是在以南北曲唱法為宋詞訂譜,但其創腔的核心基礎之一,則是兩宋傳至明清的曲牌原型。
從充盈著胡夷之音的兩宋詞樂的邏輯起點,到明清昆化后宋詞音樂“被發明的傳統”,二者音樂形態可謂天淵之別。黃翔鵬在概括這種變遷時指出:“我以為,古時五聲與七聲、九聲原是并行的,后來之所以在某種廣泛流傳的音樂(如戲曲中之‘南曲’)中形成了五聲獨霸的局面,實在很難說是遠古的傳統,恐怕這也正和胡須的下垂一樣,恰也另有來源。”[38]黃翔鵬《兩宋胡夷里巷遺音初探》,載《中國人的音樂和音樂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年版,第41 頁。并且認為明清這種“抹平了三種音階,把豐富多彩的不同音律變成了同一種味道”的流變,實在是“傳統音樂的一種失真的危機”[39]黃翔鵬《〈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簡譜示意本〉題記》,《中國音樂學》1998 年第3 期,第9 頁。。
以上述兩宋至明清的音樂風格變遷,比照學界熱衷探討的唐宋音樂轉型(斷層),可以看出:文史學界所謂唐宋轉型或斷層,或更多就大文化層面而言;具體到音樂本體形態,如敦煌曲譜與白石樂譜,二者風格差別并非巨大(同屬俗樂二十八調系統),反而宋元與明清間的音樂形態有天淵之別。以近古詞樂曲牌流變情形觀之,則唐代以來的音樂史變遷中,宋明斷層甚于唐宋。至于宋明音樂歷史斷層(或曰轉型)的原因,學界自可結合時代背景從內因、外因兩層面探尋。[40]黃翔鵬《怎樣確認〈九宮大成〉元散曲中仍存真元之聲》一文,除從音樂形態變遷和曲調考證角度探討近古音樂流變外,還特別提道:“明代人制造‘南五聲、北七聲’理論,大約與過去的民族矛盾有一定聯系。歷史上有兩個時期絕對地提倡五聲,一是隋文帝楊堅時期,一是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楊堅是從北周手里奪得江山,故排斥北方的東西,把江南當作中國文化的中心。朱元璋則起自吳地,曾號‘吳王’,這與他在音樂文化上的態度也有關系。”該文由路應昆錄整理,原載《戲曲藝術》1994 年第4 期;又收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黃翔鵬文存》 (下冊),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7頁。筆者認為,連接唐宋與明清的元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主流音樂形態,諸如夷夏之辨與民族矛盾、游牧民族音樂性格、音樂體制變遷等,或許是考證近古中國音樂歷史演變的重要節點。[41]關于此點,筆者擬另撰文研討。
(二)基于“宮調變遷”與“原型分析”的曲牌音樂考證
以詞樂考辨為例,厘清唐宋至明清曲牌音樂的若干衍化,我們便能夠基于后世可以憑借的音樂史料,包括古譜、文獻和傳統音樂遺存等,在一定限度內合理推測前代某些體裁音樂的形態特征。從以【醉吟商】為例的宋詞曲牌音樂流變來看,開展溯流探源式曲牌音樂考證的途徑,可從如下五個方面考慮:宮調體系變遷、曲牌原型分析、核心音列調整、旋律潤腔裝飾、詩詞句讀重組。
“宮調體系變遷”,即同名曲牌在不同時代所隸屬的各不同宮調系統之間的關聯。唐宋以來音樂調名系統變遷繁雜,總體包括俗樂二十八調、工尺七調、琴調、雅樂宮調等不同類別。明清時期的工尺七調又衍變出正宮調、小工調、乙字調等不同基礎調的命名系統。宮調系統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歷代黃鐘音高變遷。在固定調譜字系統中,黃鐘音高的改變直接影響不同調名的對應關系。通過對歷代黃鐘音高變遷和調名體系內在關系的考證,厘清曲牌不同時期所屬宮調的名實關系,便意味著基本掌握了樂曲音列、調高、調式的用音規范,進而在把握時代整體宮調體系的基礎上,對樂曲形態做出符合歷史邏輯的推斷。黃翔鵬晚年傾力于以宮調考辨為主體的“曲調考證”研究,從《九宮大成》等近世曲譜和傳統音樂遺存中考證出一批前朝作品,極大地豐富了古代音樂形態研究。
“曲牌原型分析”與“核心音列調整”,是筆者基于曲牌“原型—類型化”理念而提出的考證設想。通過前文對兩首“醉吟商”的分析,可初步推知唐宋以來詞調音樂傳承中,除宮調系統變遷有可循之跡外,不同時代同名曲牌旋律間,也可能存在基于共同原型的衍變關系。我們可據后世留存的曲牌音樂,抽繹其中具有基因意義的原型框架,以此作為上溯前代音樂風貌的基礎。將此原型框架重置于特定時代的宮調系統,以其原調名內涵調整個別原型骨干音,得到歷史上該曲牌正體的原型框架,以此作為擬構宋詞曲牌音調的基礎。
“旋律潤腔裝飾”和“詩詞句讀重組”是在曲牌原型基礎上對曲牌正體旋律的擬構,包括依宋詞格律還原句讀、重組節拍、寫定旋律,進而以宋代詞樂吟唱特點對旋律作進一步潤飾豐富,最終得到貼合時代風格的完整曲牌音樂。這一工作實質是曲牌歷史衍變發展的“逆過程”。在近古音樂歷程中,不僅宋詞曲牌被后世諸宮調、南戲、雜劇、散曲和南北曲等新體裁吸收,宋代詞樂的諸多編創手法,如減字、偷聲、添字、添聲、攤聲、攤破和犯調等[42]相關術語說明,參見劉明瀾《論詞調的變化》,《音樂藝術》1994 年第2 期,第12、13 頁。同樣影響深遠,目的是使原曲牌音調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詞曲組合要求。《欽定曲譜》載:“然亦隨宜消息,欲曼衍則板可贈,欲徑凈則板可減,欲變換新巧則板可移,南北曲皆然。”[43][清]王奕清等《康熙曲譜》“凡例”,岳麓書社2000 年版,第2 頁。可知南北曲應用中的曲牌句讀和板眼安排存在很大靈活性。曲牌音樂考證中的“詩詞句讀重組”和“旋律潤腔裝飾”,就是在整體把握宋詞曲牌正體框架的基礎上,合理還原歷史上已發生的“減字、偷聲及添字、攤破”等處理,綜合考慮宋詞音樂特征,擬構出符合特定時代風格的曲牌音樂。
現以《九宮大成》宋詞曲牌考證為例,試將“基于宮調變遷與原型分析的曲牌音樂考證”的具體步驟和方法歸納如下:首先,分析九宮譜相關宋詞曲牌旋律,對其作“原型—類型化”分析,剝離其中因“昆化”形成的潤腔裝飾等信息,提取九宮譜曲牌的旋律原型;其次,以唐宋俗樂二十八調理論為基礎,對提取的九宮譜變體原型作溯源式處理,考訂其中因歷代轉寫而丟失的宮調信息,補充或調整曲牌原型骨干音,得到與俗樂調名樂學內涵一致的擬宋詞樂新原型;再次,依照宋代詞樂吟唱風格,對第二步所得新的曲牌正體原型作進一步整理,擬構出宋詞同名曲牌的“筐格”[44][明]王驥德《方諸館曲律·論腔調第十》曰:“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文中所用“筐格”即取法于此。參見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版,第114 頁。,即工尺(或俗字)骨干音譜;最后,將宋詞原作填入擬構的筐格,并作一定的唱腔潤色,最終得到可供演唱的宋代詞樂考訂之曲。
從學科方法論方面看,黃翔鵬提出的立足古譜和傳統音樂遺存“溯流探源”,是考察音樂歷史形態及其流變的重要方法。綜合運用宮調變遷考證和曲牌原型分析,深入曲牌形態內部回溯歷史,有可能通過對同名曲牌不同時代核心原型、旋律潤腔、語言規范、句讀組合等規律的考辨,不斷接近兩宋詞樂藝術風貌。本文以兩首“醉吟商”對比研究為例,通過對近古詞樂流變與宋明音樂轉型的思考,提出基于宮調變遷與原型分析的曲牌考證理念,正是上述思考的初步嘗試。曲牌“原型—類型化”研究,在歸納曲牌素材類型和衍展手法,拓展傳統音樂技術理論,為音樂風格史建構提供時代標準的同時,或可對音樂史學方法論建設有所補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