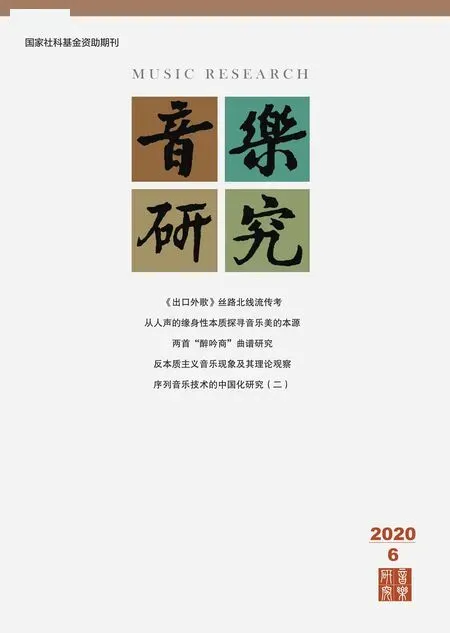序列音樂(lè)技術(shù)的中國(guó)化研究(二)
——十二音創(chuàng)作技術(shù)與理論的發(fā)展(1990—2000)
文◎張 巍
本文之所以將論述聚焦于1990—2000年這一時(shí)段,一方面是因?yàn)樵跁r(shí)間上承接了筆者之前的相關(guān)研究;①?gòu)埼 缎蛄幸魳?lè)技術(shù)的中國(guó)化研究——十二音創(chuàng)作技術(shù)與理論的發(fā)展(1980—1990)》,《音樂(lè)研究》2017年第4 期。另一方面是因?yàn)樵趦?nèi)容上所提到的相關(guān)作品和理論研究與前一個(gè)階段緊密相連。“序列音樂(lè)”這一概念,在本文的研究中具有分類上的總括性與概念內(nèi)涵上的包容性,而并非僅僅用來(lái)指稱整體序列主義所代表的一種特定音樂(lè)風(fēng)格。它代表了自十二音作曲技術(shù)產(chǎn)生以來(lái)的一系列相關(guān)的創(chuàng)作思維和方法,并與之后所形成的以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為分析對(duì)象的集合理論有著深層的邏輯聯(lián)系。
所謂“序列音樂(lè)中國(guó)化”,在本文中也具有特殊的含義。曾有學(xué)者就此提出了另一個(gè)說(shuō)法,即“中國(guó)音樂(lè)序列化”。然而筆者認(rèn)為,這種反向理解并非是一個(gè)順序顛倒的文字游戲,二者有著本質(zhì)的差別。前者中的“序列音樂(lè)”,盡管包含了一種由預(yù)制技術(shù)——各種音樂(lè)材料被嚴(yán)格地組織起來(lái)——所產(chǎn)生的在整體音響風(fēng)格上的不確定性與音高組織聽(tīng)覺(jué)上的無(wú)調(diào)性風(fēng)格特征,但這種特征在中國(guó)的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并沒(méi)有得到完全一致的體現(xiàn);盡管中國(guó)作曲家采用了這種創(chuàng)作技術(shù),但這種技術(shù)的應(yīng)用和發(fā)展,自始至終都沒(méi)有產(chǎn)生與西方無(wú)調(diào)性風(fēng)格相一致的結(jié)果。準(zhǔn)確地講,序列音樂(lè)自進(jìn)入中國(guó)后,就未形成基于西方概念上的嚴(yán)格的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風(fēng)格。許多作品的音響盡管聽(tīng)上去有無(wú)調(diào)性的感覺(jué),但從分析理論的角度來(lái)看卻是有調(diào)性的。對(duì)于許多中國(guó)作曲家而言,“序列音樂(lè)”這一詞匯所表達(dá)的并不完全是一種風(fēng)格的含義,而更多是一種技術(shù)的含義。用這種技術(shù)所展開(kāi)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是一種技術(shù)意義上的中國(guó)化實(shí)踐,是西方技術(shù)理論的“中國(guó)風(fēng)格”的運(yùn)用與操作。因此,對(duì)一種技術(shù)進(jìn)行民族化風(fēng)格的“改造”,使其更加適合中國(guó)聽(tīng)眾(在一定時(shí)期這個(gè)聽(tīng)眾只是專業(yè)聽(tīng)眾)的聽(tīng)覺(jué)習(xí)慣,便形成了最初的“民族化—中國(guó)化”的思維范式。在這種思維范式主導(dǎo)下的民族風(fēng)格具有一種“泛化”特征,“五聲性”的音高組織特征被看成其最典型的 代表。
本文不將序列音樂(lè)進(jìn)入中國(guó)的過(guò)程僅僅看成是外來(lái)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過(guò)程,或視之為將中國(guó)的民族風(fēng)格去貼合西方創(chuàng)作技術(shù)的過(guò)程,也不將其看成是中國(guó)的專業(yè)創(chuàng)作對(duì)西方無(wú)調(diào)性理論單純的借鑒與接受過(guò)程;而是認(rèn)為無(wú)論從技術(shù)上或理論上,序列音樂(lè)在中國(guó)的運(yùn)用與發(fā)展,是在新的風(fēng)格與文化語(yǔ)境下自覺(jué)再造與新建的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它不僅僅是“歷史化”、“技術(shù)化”與“融合化”,而是要對(duì)已經(jīng)“中國(guó)化運(yùn)用”的這些技術(shù)和理論提出(中國(guó))自己的問(wèn)題。本文將基于這樣的觀點(diǎn),對(duì)這一時(shí)期作曲家的音樂(lè)作品進(jìn)行分析與觀察,對(duì)這一階段中的理論研究成果進(jìn)行探究和歸納;并嘗試去理解作為一種技術(shù)背后所包含的西方當(dāng)代思想與文化,是如何在我們的使用中,對(duì)我們的音樂(lè)風(fēng)格產(chǎn)生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并成為一種經(jīng)過(guò)改造了的序列音樂(lè)風(fēng)格(流派),以及如何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改變了其西方觀念和風(fēng)貌并具有了中國(guó)特征。
一
20 世紀(jì)80 年代,序列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技術(shù)在中國(guó)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實(shí)踐與理論研究中已經(jīng)產(chǎn)生重要影響。首先,它極大地激發(fā)了作曲家們的創(chuàng)作沖動(dòng),產(chǎn)生了一批真正具有十二音技術(shù)含量的音樂(lè)作品。雖然此前也有過(guò)相關(guān)技術(shù)的創(chuàng)作嘗試,②比如1947 年,桑桐在弗蘭克爾的指導(dǎo)下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作品《夜景》(為小提琴和鋼琴而作),以及同年年底創(chuàng)作的鋼琴作品《在那遙遠(yuǎn)的地方》;1947年,在譚小麟的支持下,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舉辦了譚小麟及其學(xué)生們(如瞿希賢、秦西炫、楊與石等人)的實(shí)驗(yàn)作品音樂(lè)會(huì),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音樂(lè)的發(fā)展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xiàn);1962 年,羅忠镕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歌曲《囚歌》的片段中初次使用了十二音技術(shù),直至20 世紀(jì)80 年代的一批十二音作品《涉江采芙蓉》(藝術(shù)歌曲)、《第二弦樂(lè)四重奏》開(kāi)始系統(tǒng)地采用十二音技術(shù);等等。但是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嘗試局限在一個(gè)很小范圍,加上對(duì)十二音技術(shù)理論的理解與運(yùn)用并不準(zhǔn)確和嫻熟,故并未形成一種創(chuàng)作的風(fēng)尚。而隨著1979 年底羅忠镕的藝術(shù)歌曲《涉江采芙蓉》的完成,更多優(yōu)秀的作品接踵而至。不僅羅忠镕本人繼續(xù)以這種方法創(chuàng)作了許多作品,其他作曲家如黃育義、陳銘志、汪立三、楊立青、高為杰、許舒亞、朱踐耳和彭志敏等,也在創(chuàng)作中或整體、或局部地對(duì)這種方法進(jìn)行大膽實(shí)驗(yàn),使得十二音創(chuàng)作成為20 世紀(jì)80 年代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主流風(fēng)格。其中的許多作品,無(wú)論是創(chuàng)作觀念,還是體裁與內(nèi)容的多樣性等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成為當(dāng)時(shí)所謂“新潮音樂(l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歷史發(fā)展的眼光來(lái)看,此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盡管不乏優(yōu)秀的作品,但大多都是一些獨(dú)奏、獨(dú)唱或室內(nèi)樂(lè)的表現(xiàn)形式,在內(nèi)容的表達(dá)方面相對(duì)單一。尤其在民族風(fēng)格探索方面,大多以是否在序列中體現(xiàn)五聲性因素為標(biāo)志。③這種做法本身就與十二音技術(shù)回避調(diào)性(或回避中心)的經(jīng)典理論相悖。但是,這些作品是五聲性音高材料的組織方式相對(duì)單一,更多側(cè)重于五聲性旋律的表達(dá),而對(duì)于整體音響風(fēng)格特質(zhì)起決定作用的五聲性和聲,在十二音技術(shù)中的研究和運(yùn)用是不足的。鄭英烈在1986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道:“和聲問(wèn)題仍然是一個(gè)薄弱環(huán)節(jié),在某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和聲處理上還沒(méi)有取得主動(dòng)權(quán)”④鄭英烈《十二音技法在中國(guó)音樂(lè)作品中的運(yùn)用》,《音樂(lè)研究》1986 年第1 期,第34 頁(yè)。,這也導(dǎo)致了許多缺乏內(nèi)在民族風(fēng)格特質(zhì)的音響因聽(tīng)覺(jué)上比較生硬、不自然,使人難以接受。此時(shí)的作曲家在這種序列構(gòu)成中普遍有意識(shí)地采用五聲性音列的做法,不僅表現(xiàn)出他們面對(duì)西方新的技術(shù)理論的民族化——中國(guó)化的自覺(jué),而且也在這個(gè)時(shí)期中國(guó)的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形成了被稱之為“五聲性序列”的技術(shù)范式。⑤參見(jiàn)注④。“五聲性”和“序列”這兩個(gè)本身具有矛盾的概念的結(jié)合,被王震亞(在他1990 年的研究中)認(rèn)為是具有某種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性和必然性的。在《民族音階在現(xiàn)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延伸(九聲音階·含五聲音階因素的十二音序列)》一文中,他認(rèn)為五聲音階之所以可以被融合到十二音序列中,一是因?yàn)槲迓曇綦A可以由任何一個(gè)音作為調(diào)式的“起音”,二是五聲性三音列、四音列的靈活組合與十二音序列的組合性特征相得益彰。因此,“以各種方式將五聲音階滲入十二音序列”是中國(guó)作曲家采用五聲化十二音技術(shù)的著眼點(diǎn)。這種觀點(diǎn)本身也說(shuō)明,序列這一技術(shù)自身的生成邏輯和無(wú)調(diào)性風(fēng)格特征,在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創(chuàng)作或理論研究中,并未按照西方的理論邏輯被堅(jiān)守或保留,而是進(jìn)行了與之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方向的發(fā)展。
這一時(shí)期理論家或作曲家的研究所產(chǎn)生的作用是顯而易見(jiàn)的,它體現(xiàn)出兩個(gè)方面的價(jià)值:一方面是許多與序列音樂(lè)直接相關(guān)的重要經(jīng)典理論和方法,被引進(jìn)、理解與闡釋,并系統(tǒng)性地進(jìn)入作曲教學(xué)的知識(shí)體系構(gòu)建中;⑥目前國(guó)內(nèi)通用的《序列音樂(lè)寫(xiě)作教程》(上海音樂(lè)出版社2007 年修訂版),初版的第一稿完成于1981年,由原來(lái)的講稿修訂的第二稿《序列音樂(lè)基礎(chǔ)》完成于1985 年,1989 年由上海音樂(lè)出版社出版了《序列音樂(lè)寫(xiě)作基礎(chǔ)》,直到2007 年最終版本的章節(jié)內(nèi)容擴(kuò)展到了二十章,并且增加了中國(guó)十二音作品的創(chuàng)作分析,以此突出了該書(shū)的“中國(guó)化”特色。另一方面是許多理論家的研究緊緊圍繞著創(chuàng)作實(shí)踐進(jìn)行總結(jié)和發(fā)現(xiàn)。⑦參見(jiàn)注①。這不僅消除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音樂(lè)界一些人對(duì)于這一新鮮事物的不理解甚至偏見(jiàn),也為這一時(shí)期作曲家們充分認(rèn)識(shí)這種風(fēng)格與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放開(kāi)手腳大膽去進(jìn)行新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和技術(shù)實(shí)驗(yàn),提供了有力的技術(shù)理論支撐。鄭英烈在1982 年發(fā)表的《十二音體系的歷史繼承性》中就指出,十二音體系的產(chǎn)生經(jīng)歷了四個(gè)階段的發(fā)展。起始階段是旋律的裝飾性半音體系,然后是和聲中的和弦半音體系,接下去是綜合調(diào)式半音體系,最終從無(wú)調(diào)性過(guò)渡到十二音體系。從這個(gè)觀點(diǎn)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的邏輯就是從一種調(diào)性體系向另一種“調(diào)性體系”的轉(zhuǎn)換。從勛伯格《我的演進(jìn)》⑧阿諾爾德·勛伯格著,鄭英烈譯《我的演進(jìn)》,《黃鐘》1988 年第2 期。一文中也可以看到,這一創(chuàng)作技術(shù)的形成,是繼承西方技術(shù)理論的發(fā)展邏輯所產(chǎn)生的必然結(jié)果。這種新的技術(shù)理論對(duì)于傳統(tǒng)的繼承性研究,在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理論研究中還不止于此。朱世瑞在他的《勛伯格的傳統(tǒng)繼承性》一文中⑨朱世瑞《勛伯格的傳統(tǒng)繼承性》,《音樂(lè)探索》1983 年第1 期。也特別提到,十二音作曲技術(shù)與傳統(tǒng)音樂(lè)思維的緊密關(guān)系,還體現(xiàn)在對(duì)傳統(tǒng)的曲式、復(fù)調(diào)思維和音樂(lè)體 裁方面。
對(duì)于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研究則是從兩種途徑開(kāi)展,二者相輔相成,既有西方的經(jīng)典作品,也有中國(guó)借鑒這一技術(shù)創(chuàng)作完成的優(yōu)秀作品。前者的研究更多地側(cè)重于發(fā)現(xiàn)可供我們借鑒的一些有益經(jīng)驗(yàn)。鄭英烈在對(duì)韋伯恩的《鋼琴變奏曲》(Op.27)第一樂(lè)章進(jìn)行研究⑩鄭英烈《韋伯恩的〈鋼琴變奏曲〉第一樂(lè)章——序列音樂(lè)研究之六》,《廣州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3 年第3 期。時(shí)就認(rèn)為,韋伯恩偏愛(ài)將十二音序列設(shè)計(jì)為四個(gè)三音組,這些三音組一方面具有“動(dòng)機(jī)”的性質(zhì),但又不包含任何調(diào)性因素,并且具有組合性的特征。不同的是,這種三音組被替換成為具有中國(guó)五聲性特點(diǎn)的三音組。作者對(duì)于這首作品的另一個(gè)重要發(fā)現(xiàn)是,作為一種組織力量,韋伯恩在作品中所采用的“鏡像結(jié)構(gòu)”,使主題與各個(gè)變奏之間保持著一種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種做法,同樣可以在陳銘志創(chuàng)作的《鋼琴小品八首》之七的“吟唱”中找到。雖然這首民族風(fēng)格的序列小品總長(zhǎng)只有17小節(jié),但其中的鏡像結(jié)構(gòu)卻得到了非常完整的表達(dá)。實(shí)際上,除了個(gè)人的創(chuàng)作之外,陳銘志對(duì)于韋伯恩的研究也同樣值得 關(guān)注。
有關(guān)貝爾格的研究,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來(lái)說(shuō),具有借鑒意義。作為新維也納樂(lè)派“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風(fēng)格作曲家中的一員,與韋伯恩對(duì)于十二音材料“定序”的熱衷并最終趨向于整體序列主義的趣味不同,貝爾格在用十二音技術(shù)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從來(lái)不回避對(duì)“調(diào)性”的偏愛(ài),在他創(chuàng)作的大部分作品中,“調(diào)性”或“調(diào)性因素”都似乎顯而易見(jiàn)——這是對(duì)新維也納樂(lè)派的即時(shí)背叛。但如果從理論邏輯的角度來(lái)看,貝爾格的“調(diào)性—中心”思維,實(shí)際上是一種更加廣義的、經(jīng)過(guò)發(fā)展的調(diào)性概念,其中對(duì)于德奧傳統(tǒng)繼承的線索是非常清晰的。錢(qián)仁康在對(duì)貝爾格《小提琴協(xié)奏曲》的分析[11]錢(qián)仁康《一曲回腸十二音——貝爾格〈小提琴協(xié)奏曲〉賞析》(上、下),分別載于《音樂(lè)藝術(shù)》1985 年第4 期,1986 年第1 期。中就指出,這首作品的十二音序列是由小三和弦、大三和弦交替疊置,最后加上四個(gè)音的全音音列構(gòu)成;而朱建在對(duì)貝爾格《抒情組曲》的研究[12]朱建《貝爾格〈抒情組曲〉的十二音技法初探》,《音樂(lè)藝術(shù)》1988 年第3 期。中發(fā)現(xiàn),這部作品中相當(dāng)多的部分并非采用了嚴(yán)格的十二音技術(shù)理論原則,其序列構(gòu)成不僅采用了與《小提琴協(xié)奏曲》相似的“調(diào)性”方法,而且是一個(gè)全音程序列。上述研究也說(shuō)明了一個(gè)事實(shí),即這種與傳統(tǒng)保持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以及在規(guī)則與聽(tīng)覺(jué)需求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的十二音技術(shù)的折衷觀念,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作曲家們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更加受用并更具啟發(fā)性的,盡管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中所包含的就是德奧的古典傳統(tǒng)和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民族風(fēng)格。
以上對(duì)于序列音樂(lè)經(jīng)典作品的研究,幾乎同步反映在中國(guó)的序列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鄭英烈對(duì)于羅忠镕序列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跟蹤研究,總體上可以反映出,理論家對(duì)西方序列傳統(tǒng)的研究成果在本國(guó)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代表性反饋。
二
如果將20 世紀(jì)90 年代與80 年代在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方面的整體狀況作一個(gè)簡(jiǎn)單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80 年代那種旺盛的學(xué)術(shù)與創(chuàng)作活力在90 年代似乎消退了許多。至今為專業(yè)界所稱道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和作曲理論領(lǐng)域在80 年代舉辦的一些標(biāo)志性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13]比如1985 年,武漢音樂(lè)學(xué)院舉辦了“第一次全國(guó)中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huì)”;1986 年,由文化部主辦,在武漢舉行的“全國(guó)高等音樂(lè)院校和聲學(xué)學(xué)術(shù)報(bào)告會(huì)”,會(huì)議共收到學(xué)術(shù)論文近80 篇;等等。,并未在90 年代承接延續(xù)下來(lái);過(guò)去一些在“現(xiàn)代與民族”“傳統(tǒng)與新潮”“和諧與不和諧”等問(wèn)題上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鳴與觀點(diǎn)碰撞也逐漸沉寂下來(lái)。就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而言,不難發(fā)現(xiàn),80 年代的諸多未有深入思考的問(wèn)題,在90 年代卻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關(guān)注和認(rèn)識(shí)上的深化。一些技術(shù)的借鑒與模仿,逐漸轉(zhuǎn)向創(chuàng)作與思維觀念上的變化;對(duì)于風(fēng)格的局部化與表象化的認(rèn)識(shí),逐漸向多元化與關(guān)注風(fēng)格的內(nèi)在氣質(zhì)轉(zhuǎn)變;新理論的引入與學(xué)習(xí),不斷向創(chuàng)作技術(shù)的實(shí)踐進(jìn)行轉(zhuǎn)換。這其中,集合理論作為一種對(duì)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最為有效的分析理論,在中國(guó)的引入是具有標(biāo)志性的,其對(duì)中國(guó)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和教學(xué)觀念的發(fā)展具有推動(dòng)作用。由于集合理論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在于,一個(gè)集合內(nèi)部盡管其音高呈現(xiàn)時(shí)無(wú)序,但其形成音響時(shí)各個(gè)音高彼此之間的音程關(guān)系在總量上的不變性特性,使得這一理論在中國(guó)的作曲家手中從最初的分析理論演變成為一種作曲技術(shù)理論,而且最終成為一種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思維。對(duì)于這種技術(shù)思維作用而言,由于音高材料所具有的風(fēng)格特性存在于更深層次的音高組織層面,作曲家無(wú)須在音高材料的設(shè)計(jì)上過(guò)多地在意其材料組織時(shí)表面的風(fēng)格特征。因此,這種思維對(duì)于序列音樂(lè)的民族風(fēng)格化發(fā)展,乃至非序列音樂(lè)的其他風(fēng)格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都具有重要的啟發(fā)作用。我們無(wú)須爭(zhēng)論到底是密爾頓·巴比特,還是阿倫·福特發(fā)現(xiàn)了集合理論。這一理論復(fù)雜的形成過(guò)程,不僅包含巴比特創(chuàng)作本身的技術(shù)積累和他自身在音樂(lè)理論研究中的哲學(xué)方法——他確信通過(guò)把傳統(tǒng)調(diào)性理論與十二音理論的概念加以系統(tǒng)化并轉(zhuǎn)換成邏輯語(yǔ)言的形式,從而使音樂(lè)理論成為一門(mén)在科學(xué)意義上十分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科;也包含了阿倫·福特本人對(duì)于巴比特在申克研究和非調(diào)性音樂(lè)理論方面成果的消化與繼承。但觀察一些作曲家作品的技術(shù)思路轉(zhuǎn)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過(guò)程的變化與發(fā)展。
從高為杰1987 年創(chuàng)作的鋼琴曲《秋野》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在80 年代,中國(guó)音樂(lè)界對(duì)于集合理論的研究并未深入到歷史背景之中,但其理論之于實(shí)踐的指導(dǎo)價(jià)值已經(jīng)逐步被作曲家認(rèn)識(shí)到了。
譜例1

整首作品的技術(shù)使用被作曲家稱為“十二音場(chǎng)技術(shù)”(后又被他本人稱為“集合配套技術(shù)”),從譜例1 這個(gè)序列中可以看出,作曲家將十二個(gè)半音分成了3 個(gè)四音集合。[14]這里需要說(shuō)明的是,為了能確定集合具體音高,在集合名稱之前使用了P 和數(shù)字表示,如P5:4-23,是指集合最低音為音級(jí)5,向上構(gòu)成【0,2,5,7】的集合。從譜例2 第1—2 小節(jié)可以看出,作品開(kāi)始的八音和弦,并非像過(guò)去傳統(tǒng)序列那樣的音高陳述,而是由兩個(gè)同構(gòu)集合4-23疊加而成,上方的四個(gè)音為集合P5: 4-23, 下方的四個(gè)音為集合P6: 4-23,二者雖然音高不同,但集合內(nèi)涵相同,同時(shí),這兩個(gè)集合的縱向結(jié)合又可以形成新的集合配套。隨后出現(xiàn)的具有動(dòng)機(jī)特征的三連音音型,是前面集合的對(duì)比集合P9: 4-6,它是由前面兩個(gè)集合各截出兩個(gè)音進(jìn)行重復(fù)而產(chǎn)生的。到此并未出現(xiàn)完整序列中的十二個(gè)音,直到第2 小節(jié)出現(xiàn)了集合P2: 4-6 (E—D—bE—A),才與前面兩個(gè)同構(gòu)集合P5: 4-23 組成了一個(gè)完整的十二音序列——這就是作者所謂的“十二音場(chǎng)”。即便在之后對(duì)各種集合內(nèi)部進(jìn)行了音高順序的置換或是移位轉(zhuǎn)位等處理(如譜例2 后面音型所示),其集合本身的性質(zhì)不發(fā)生改變。這便使得一種音響的基本風(fēng)格特征得到了更加深層次的保留。
譜例2

這種風(fēng)格特征的保留,即便是在復(fù)雜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通過(guò)分析也可以看出。在譜例3 中,織體盡管看似單一,但依然是 由P5: 4-23、P6: 4-23、P2: 4-6 三個(gè)集合構(gòu)成的十二音場(chǎng),其內(nèi)部的組合方式也更加復(fù)雜。第10—11 小節(jié),右手聲部是兩個(gè)同構(gòu)的五聲性集合4-23,左手聲部則是非五聲性集合4-6 的不斷重復(fù),雙手聲部之間交錯(cuò)呈示的音高材料又形成了一種隱伏的形態(tài);第12—15 小節(jié),雙手陳述的集合不變,卻形成了橫向交叉—甚至需要將其調(diào)換位置才能分辨 清楚。
正是由于按照集合配套的方式來(lái)組織十二音,就使得在作品的發(fā)展中,即便是非常靈活地對(duì)十二個(gè)音進(jìn)行使用,集合本身的固有特質(zhì)也不會(huì)改變。也就是說(shuō),這種集合的方法,不僅強(qiáng)化了音高材料在形成整個(gè)作品中的一致性作用,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了其整體風(fēng)格的一致性。而在高為杰1994年的作品《遠(yuǎn)夢(mèng)》中,用集合的方法去處理五聲性特征被改換一種方式去使用。由于作品中的序列被作為縱向的和弦化的方式去陳述——沒(méi)有橫向的陳述方式,故這個(gè)“縱向化”的序列,就被視為一種具有結(jié)構(gòu)性標(biāo)志作用的“定位和弦”來(lái)使用。每當(dāng)出現(xiàn)重要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折時(shí),都會(huì)陳述這個(gè)特定和弦(序列)的音響。在整個(gè)和弦結(jié)構(gòu)中,典型的五聲性結(jié)構(gòu)被嵌入兩段的兩個(gè)“三和弦”中,這也使得在分析時(shí)所呈現(xiàn)的風(fēng)格特征在整體發(fā)音時(shí)卻并不明顯。與一個(gè)序列內(nèi)部的截段按組合配套的方式進(jìn)行處理的方法不同的是,序列作為定位和弦,不僅具有其原始的形態(tài),而且在不同的結(jié)構(gòu)部位中還可以被整體“轉(zhuǎn)位”使用,使得過(guò)去局部集合內(nèi)音高位置的變化,變成了整個(gè)序列(視整個(gè)序列為一個(gè)全集)內(nèi)部音高位置的變化。譜例4 顯示了將這部作品中和弦抽象后所得到的處于“原位”的十二音定位和弦。如果把這個(gè)和弦與其他三個(gè)“轉(zhuǎn)位”的音響效果進(jìn)行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cè)谧髌分械亩ㄎ唬粌H僅是一種結(jié)構(gòu)音響的定位,也是一種特定音響特征與風(fēng)格的定位。
譜例3

譜例4

譜例4-1 最下方的音為“原位”定位和弦序列的第一號(hào)音;譜例4-2 的十二音和弦是原始十二音和弦移位三全音到bB 之后的第一轉(zhuǎn)位形式——把1 號(hào)音bB 移到最高音;譜例4-3 的十二音和弦是原始十二音和弦向上移位大二度后到#F 的第二轉(zhuǎn)位形式——把1 號(hào)音#F、2 號(hào)音B 移到最高音,同時(shí)在樂(lè)曲中省略了部分音,這在十二音定位和弦技法中是被允許的;譜例4-4 的十二音和弦是原始十二音和弦向下移位小三度之后的第三轉(zhuǎn)位形式——把1 號(hào)音#C、2 號(hào)音#F、3 號(hào)音#A 移動(dòng)到最高聲部。
五聲性序列的集合配套技術(shù)在中國(guó)的運(yùn)用,不僅僅表現(xiàn)為以上所分析的有規(guī)律的、秩序化的音組配套,也表現(xiàn)為無(wú)序化的、自由的配套使用。在賈國(guó)平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歌曲《立秋》中,其組合性序列用法就表現(xiàn)出這種特點(diǎn)。
譜例5

從譜例5 中的這個(gè)序列可以看到,如果依序來(lái)分析這個(gè)序列,其中的五聲性集合是局部的,但如果要使整個(gè)集合都形成所謂【0,2,4,7,9】的五聲性集合,其配套方式就不能按照以往有序化的三音組和四音組的方式進(jìn)行組合,而只能采用目前這樣一種極為自由的方式。
從五聲性序列技術(shù)向五聲性集合技術(shù)的轉(zhuǎn)變,不僅標(biāo)志著序列作曲技術(shù)的發(fā)展,同時(shí)也反映了這種技術(shù)在其“風(fēng)格化—中國(guó)化”的進(jìn)程中,風(fēng)格模式從一種直接和樸素的形態(tài),向更為精致的藝術(shù)化的方向轉(zhuǎn)變。羅忠镕在其《第三弦樂(lè)四重奏》中對(duì)這一技術(shù)的運(yùn)用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首作品中,他采用了“五聲—非五聲性集合”的序列處理技術(shù)。在序列形成的過(guò)程中,他發(fā)現(xiàn)在十二個(gè)半音之間無(wú)法完全組成不同的四個(gè)五聲性三音集合或三個(gè)五聲性四音集合,也就是說(shuō),其中必定會(huì)出現(xiàn)一個(gè)非五聲性集合。因此,無(wú)論是按三音集合還是四音集合作為單位來(lái)構(gòu)成不同的十二音序列,只能產(chǎn)生20 種“五聲—非五聲”序列模式。[15]羅忠镕的《第三弦樂(lè)四重奏》于1997 年發(fā)表在 《音樂(lè)創(chuàng)作》第4 期。在作品的后面,作者附上了這20種“五聲—非五聲”性集合的十二音序列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兩個(gè)序列中的集合計(jì)算有誤。由于一個(gè)序列中的非五聲性集合以非常清晰和完整的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出來(lái),且在實(shí)際音響效果上與五聲性集合相比具有更強(qiáng)的張力特征和色彩變化,因此在實(shí)際創(chuàng)作中,兩類集合之間的相互協(xié)調(diào)和融合,便形成了更加豐富的音響和情感表現(xiàn)力。通過(guò)譜例6 中一個(gè)局部的片段,可以看到作曲家對(duì)序列的安排,以及在實(shí)際創(chuàng)作中對(duì)序列材料的精心處理。
譜例6

這個(gè)組合性序列是第二樂(lè)章中的原型序列——是其20 種“五聲—非五聲”序列表中的第一種。其中的符號(hào)A 與C 代表五聲性四音組集合,X 代表非五聲性四音組集合。兩個(gè)五聲性四音組集合彼此是非同構(gòu)的。前者具有明顯的C 宮調(diào)式特征,后者則是bD 宮調(diào)式。盡管二者都具有五聲性特征,但實(shí)際上二者之間的宮音關(guān)系是很遠(yuǎn)的,而且第二個(gè)集合在縱向音響上呈現(xiàn)為小七和弦特點(diǎn)。如果進(jìn)一步觀察第三個(gè)非五聲性四音集合會(huì)發(fā)現(xiàn), 它實(shí)際的縱向音響是一個(gè)大小七和弦(屬七和弦)結(jié)構(gòu)。也就是說(shuō),三個(gè)集合的排列呈現(xiàn)出緊張度逐漸增長(zhǎng)的特點(diǎn)。這一特點(diǎn)使得作曲家在運(yùn)用時(shí),無(wú)論是將音組作線性處理,還是將音組縱向?qū)χ锰幚恚伎梢院芎玫剡M(jìn)行音響的張力安排。
三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曲家仍然在通過(guò)對(duì)五聲性序列的創(chuàng)新處理,來(lái)實(shí)現(xiàn)序列技術(shù)的“風(fēng)格化—中國(guó)化”轉(zhuǎn)型這一目標(biāo);而另一些作曲家的做法,則是通過(guò)對(duì)五聲性序列技術(shù)風(fēng)格的“逃逸”,來(lái)對(duì)這種風(fēng)格的表達(dá)進(jìn)行思考。對(duì)于這個(gè)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來(lái)說(shuō),許多作曲家顯然一方面受到了這種民族風(fēng)格的內(nèi)在約束,同時(shí)也希望回避這種過(guò)于明顯的風(fēng)格符號(hào),而以其他的 方式來(lái)表達(dá)這種民族性的內(nèi)在特質(zhì),并最終實(shí)現(xiàn)“風(fēng)格化—中國(guó)化”的表達(dá)。
從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上講,這種風(fēng)格“逃逸”的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其一,是對(duì)于早期的、嚴(yán)格的十二音寫(xiě)作技術(shù)的回避,并轉(zhuǎn)向序列集合化的技術(shù)。這種回避,主要是因?yàn)樵缙诘男蛄惺魧?xiě)作首先以回避調(diào)性為技術(shù)目的。其二,是在選擇表達(dá)風(fēng)格的材料上表現(xiàn)出對(duì)于那種過(guò)于明顯的五聲性因素的淡化——所謂“要有點(diǎn)五聲性但又不能太五聲性”——甚至是回避的傾向,而代之以其他的風(fēng)格要素來(lái)強(qiáng)化這種民族性。這種情況并非始于20 世紀(jì)90 年代,在80 年代的許多作品中就已出現(xiàn)端倪。如賈達(dá)群1988 年創(chuàng)作的《弦樂(lè)四重奏》便是如此。作曲家將一些具有風(fēng)格性特征(如黃河流域的嗩吶音樂(lè)、長(zhǎng)江流域的船工號(hào)子、五臺(tái)山地區(qū)的寺廟音樂(lè)等)的材料單獨(dú)作為一種象征性音調(diào),以拼貼的方式進(jìn)入整體的音高組織中,但序列音高材料的組織卻是用三個(gè)四音集合:集合a【0,1,6,7】、集合b【0,1,2,7】、集合c【0,1,3,6】來(lái)構(gòu)成。有意思的是,這三個(gè)四音集合各自作四個(gè)半音的移位,便可構(gòu)成一個(gè)獨(dú)立的十二音序列。顯而易見(jiàn),這三個(gè)四音集合絕非五聲性風(fēng)格,其中的三音子集更是強(qiáng)調(diào)了小二度與三全音這兩個(gè)與五聲性特征明顯沖突的音程。
秦文琛1990 年創(chuàng)作的《幽歌Ⅱ號(hào)》,對(duì)于風(fēng)格的塑造更多是從其整體的“音色—音響”的組織與設(shè)計(jì)上完成的,而在音高的設(shè)計(jì)上,四個(gè)三音組(集合3-1【0,1,2】)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音響特征完全是半音化的。在排練號(hào)7 的鋼琴片段中,集合通過(guò)作曲家對(duì)織體的處理被分置在不同的層次中。整個(gè)序列共陳述了11 個(gè)音(只有#D 沒(méi)有出現(xiàn))。在鋼琴左手部分,前三個(gè)音“A—G—#G” 是核心音組逆行形態(tài),第4—7 號(hào)音是核心音組倒影形態(tài);而觀察左手部分的次中音聲部,可以發(fā)現(xiàn)由“G—#F—#G”構(gòu)成的核心音組原型形態(tài),以及由“#F—#G—G”構(gòu)成的核心音組倒影逆行形態(tài);鋼琴右手部分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在兩個(gè)聲部中各自形成了三個(gè)核心音組的不同形態(tài),最高音聲部出現(xiàn)了由“F—E—#F”構(gòu)成的核心音組原型形態(tài),中音聲部則是由“bB—C—B”構(gòu)成的核心音組倒影逆行形態(tài),以及由“B—C—bB”構(gòu)成的核心音組原型形態(tài)。但從這個(gè)局部的音響風(fēng)格來(lái)看,我們很難想象它與民族風(fēng)格有什么關(guān)系,但整體音響上,中國(guó)的風(fēng)格與文化氣息是可以感受到的。
從20 世紀(jì)90 年代的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來(lái)看,許多作品關(guān)注了知識(shí)分子生命個(gè)體的感受,以及人文精神的張揚(yáng)。對(duì)這一主題的深刻表達(dá),也要求作曲家選擇一種更加恰當(dāng)?shù)募夹g(shù)語(yǔ)言去實(shí)現(xiàn)這一目的。因此,在序列技術(shù)的風(fēng)格化改造中,淡化五聲性標(biāo)簽語(yǔ)言、強(qiáng)化序列風(fēng)格中音響的“表現(xiàn)主義”張力,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這種內(nèi)在人文精神的抒發(fā),也成為序列技術(shù)在中國(guó)的風(fēng)格化演進(jìn)中的另一條路徑。王西麟在他的《第三交響曲》中,就大量采用了這種風(fēng)格化的處理。作為一部被作曲家視為對(duì)民族歷史和人類命運(yùn)進(jìn)行哲理性思考的作品,他在音高的序列技術(shù)處理時(shí),就明確地回避了五聲性材料,也沒(méi)有采用五聲性序列若干處理手段,而是大量運(yùn)用了具有典型無(wú)調(diào)性風(fēng)格的“三全音”音程結(jié)構(gòu)。通過(guò)在這種結(jié)構(gòu)框架中編織其他的音程,同時(shí)在旋律的發(fā)展處理及和聲的處理上,以一種自由十二音的方式來(lái)調(diào)和經(jīng)典十二音技術(shù)中的定序規(guī)則,從而滿足特定的以三全音的構(gòu)造為旋律特征與和弦主體結(jié)構(gòu)的需要,最終獲得音樂(lè)內(nèi)在的持續(xù)性張力。
在第一樂(lè)章第29—34 小節(jié)中,弦樂(lè)聲部在較低音區(qū)陳述的“跋涉主題”是非序列化的半音運(yùn)動(dòng),并在最后兩個(gè)小節(jié)導(dǎo)入了序列結(jié)構(gòu)中連續(xù)的三全音疊置的和弦形態(tài)。而在其上方英國(guó)管聲部陳述的所謂“苦澀主題”(原型序列P7)完全由三全音構(gòu)成。在第11 號(hào)音和第12 號(hào)音之間,為了強(qiáng)調(diào)這種持續(xù)性的音響特征,還采用了自由12音的寫(xiě)法,專門(mén)嵌入了一個(gè)三全音音程來(lái)延長(zhǎng)這種冷峻壓抑的效果。這種技術(shù)手段被作曲家執(zhí)拗地使用在作品的各個(gè)部分。
這種通過(guò)在音高的組織技術(shù)上回避五聲性特征,來(lái)表達(dá)一種更為廣義的民族風(fēng)格與民族精神的做法,在朱踐耳的交響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比比皆是。縱觀朱踐耳的全部交響曲創(chuàng)作,從作曲技術(shù)上講,序列技術(shù)幾乎是他每一部交響曲中的核心技術(shù)。因此,其音響風(fēng)格雖然在不同的作品中由于不同的表現(xiàn)需要而千差萬(wàn)別,但其中內(nèi)在的技術(shù)邏輯大致是相同的。不過(gu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90 年代之后的創(chuàng)作中,使用的非五聲性集合與他早期的序列風(fēng)格的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觀察他的《第八交響曲》中的序列處理方法,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其獨(dú)特的音樂(lè)語(yǔ)匯對(duì)于其人文精神和情感的表達(dá)所產(chǎn)生的作用。
通過(guò)上述對(duì)相關(guān)作品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典的十二音技術(shù)與理論的根脈上,呈現(xiàn)出兩條技術(shù)風(fēng)格的生長(zhǎng)與演化路徑:一種是盡可能保留具有普遍性的中國(guó)音樂(lè)風(fēng)格的五聲性特征來(lái)組織序列材料;另一種是在序列的組織與技術(shù)構(gòu)成中盡可能淡化甚至是回避這種五聲性材料。看似相悖的二者之間同時(shí)存在著兩種關(guān)聯(lián)性,即核心技術(shù)表達(dá)的一致性與對(duì)“民族化—中國(guó)化”風(fēng)格理解的兩面性。前者表現(xiàn)為,無(wú)論這種十二音技術(shù)是嚴(yán)格、無(wú)調(diào)性的,還是自由的、有“調(diào)性”的,它最終都通過(guò)集合理論獲得了技術(shù)的發(fā)展——集合作為分析理論證明了這些作品的音高組織關(guān)系的合理性,而這反過(guò)來(lái)又使得作曲家不斷形成“按照集合的思維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一定具有其合理性”的思維方式;后者則表現(xiàn)為,當(dāng)我們尋求對(duì)西方的現(xiàn)代技術(shù)進(jìn)行消化與改造來(lái)創(chuàng)作具有“中國(guó)風(fēng)格”的音樂(lè)時(shí),無(wú)論其方式是“可見(jiàn)的”還是“不可見(jiàn)的”,它都是同一種風(fēng)格的外化和內(nèi)化的體現(xiàn)。這其中的邏輯,撇開(kāi)文化的差異不論,僅從技術(shù)上講,或是從風(fēng)格上看,都與新維也納樂(lè)派對(duì)于德奧古典傳統(tǒng)的發(fā)展,或是韋伯恩和貝爾格對(duì)于勛伯格的技術(shù)與理論的發(fā)展沒(méi)有什么不同。
四
與創(chuàng)作實(shí)踐相比,有關(guān)序列音樂(lè)理論的研究也尤為突出。20 世紀(jì)80 年代的諸多相關(guān)理論問(wèn)題,以今天的眼光來(lái)看,盡管在那個(gè)時(shí)期顯得特別重要且在創(chuàng)作中已經(jīng)有了技術(shù)化的運(yùn)用與反應(yīng),但研究是滯后的。這也使得一些序列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關(guān)鍵問(wèn)題難以得到廣泛的關(guān)注與重視。羅忠镕在1987 年創(chuàng)作的《嫦娥》中完整地采用了喬治·珀?duì)柕睦碚摚⒔Y(jié)合了整體序列主義的方法,按照音高序列的方式設(shè)計(jì)了48種節(jié)奏序列矩陣作為全曲節(jié)奏生成的依據(jù),但是這一理論的核心問(wèn)題及其理論中關(guān)于十二音和聲結(jié)構(gòu)組織的一些問(wèn)題與方法,在當(dāng)時(shí)并未為人所知。
從文獻(xiàn)來(lái)看,勛伯格及其早期的追隨者們?cè)诋?dāng)初的理論構(gòu)建中,并未專門(mén)就十二音寫(xiě)作的和聲問(wèn)題進(jìn)行過(guò)理論化的描述。這也使得早期的十二音創(chuàng)作更多地關(guān)注橫向的線性問(wèn)題——這也是復(fù)調(diào)音樂(lè)在20 世紀(jì)復(fù)蘇的技術(shù)原因之一。至于對(duì)縱向和聲效果的評(píng)價(jià),作曲家還是以傳統(tǒng)的和聲語(yǔ)言組織作為坐標(biāo)。以至于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都有一種值得推敲的說(shuō)法,即一個(gè)作曲家如果在一部作品中采用十二音寫(xiě)作的和聲音響不夠協(xié)調(diào),那么并非是十二音這一理論出了問(wèn)題,而是他的傳統(tǒng)(或是作曲的技術(shù))基礎(chǔ)不夠好。持這種觀點(diǎn)的人并非少數(shù)(即便是勛伯格本人)。盡管邏輯似乎正確,但情況卻并非如此,一個(gè)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十二音技術(shù)理論的產(chǎn)生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tǒng)和聲理論的“基本構(gòu)詞法”。如果不考慮二者之間的形式邏輯關(guān)系的話,就十二音的音響組織及其內(nèi)在發(fā)展邏輯而言,傳統(tǒng)的調(diào)性和聲理論根本就無(wú)法作為十二音和聲音響是否動(dòng)聽(tīng)與合理的依傍。即便是魯?shù)婪颉だ椎僭谟懻撜{(diào)性、無(wú)調(diào)性與泛調(diào)性三者的關(guān)系問(wèn)題時(shí),提出了所謂“旋律調(diào)性”和“和聲調(diào)性”的概念,[16]參見(jiàn)魯?shù)婪颉だ椎僦嵱⒘易g《調(diào)性·無(wú)調(diào)性·泛調(diào)性》,人民音樂(lè)出版社1992 年版。但對(duì)于十二音理論的技術(shù)化實(shí)踐來(lái)說(shuō),這一概念也更多存在于旋律調(diào)性的層面。過(guò)去貝爾格的調(diào)性十二音寫(xiě)作如此,后來(lái)的中國(guó)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仍然如此。從多聲部音樂(lè)形態(tài)的音樂(lè)本體而言,旋律的問(wèn)題本質(zhì)上也是和聲的問(wèn)題,因?yàn)槁曇舻目臻g的結(jié)合,無(wú)論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它一定會(huì)產(chǎn)生聽(tīng)覺(jué)意義上的“和聲”。
對(duì)于中國(guó)的序列音樂(lè)創(chuàng)作來(lái)說(shuō),調(diào)性的問(wèn)題似乎得到了解決,因?yàn)閺膹V義的調(diào)性而言,五聲性序列的本身就是一個(gè)調(diào)性序列。這里的五聲性音高材料,既是一種風(fēng)格化的材料,也是一種調(diào)性材料。但這并不意味著與傳統(tǒng)的調(diào)性和聲理論一樣,調(diào)性一詞代表著和聲運(yùn)動(dòng)邏輯的自然目標(biāo)。而五聲性序列所具有的“調(diào)性感”,更多的是一種聽(tīng)覺(jué)意義上的“風(fēng)格感”,它對(duì)序列中的其他音實(shí)際上并沒(méi)有產(chǎn)生所謂“功能上的約束力和目標(biāo)上的向心力”。從這個(gè)意義講,中國(guó)的作曲家從一開(kāi)始就有意忽視了十二音理論的基本規(guī)則,并在違背規(guī)則的情況下,植入了這種具有典型風(fēng)格特征的“五聲性調(diào)性”因素——這與勛伯格音樂(lè)中的廣義調(diào)性特征和貝爾格極為隱晦地將調(diào)性因素滲透在音樂(lè)中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前者(五聲性調(diào)性)可以直接被音響感知,后者則需要“極為專業(yè)的耳朵”和分析家的眼光。正因如此,十二音的和聲問(wèn)題再得到關(guān)注,在中國(guó)就有了兩個(gè)方面的意義,即獲得一種能使音響協(xié)調(diào)的和聲組織方法,且這種方法具有序列理論的邏輯與支持。
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理解陳銘志等理論家的研究趣味及其觀點(diǎn),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理論的價(jià)值所在。我們知道,十二音寫(xiě)作中的“和聲”的產(chǎn)生,雖然是一種表層的形態(tài),但它的形成是由一些規(guī)律性的構(gòu)造方式完成的,諸如縱向合成、橫向合成和縱橫交錯(cuò)的合成等。與傳統(tǒng)不同的是,這些和聲音響雖得以構(gòu)造,但使它們按照類似傳統(tǒng)的調(diào)性組織起來(lái)的一種結(jié)構(gòu)力是不清晰的,以至于我們難以在判斷和聲運(yùn)動(dòng)是否適切時(shí)給出基本的標(biāo)準(zhǔn)。陳銘志的研究[17]陳銘志《十二音和聲的表層結(jié)構(gòu)》,《音樂(lè)藝術(shù)》1990 年第1 期。認(rèn)為,在十二音音樂(lè)中,和聲一詞是“既保留了傳統(tǒng)的含義,又引入了非傳統(tǒng)的內(nèi)容”。通過(guò)對(duì)勛伯格作品的研究,他強(qiáng)調(diào)“有音列所產(chǎn)生的和聲的表層形態(tài),能產(chǎn)生音響相似的效果時(shí),卻是一個(gè)重要的統(tǒng)一因素”。這種統(tǒng)一因素,顯然就是一種“調(diào)性”的概念。顯然,文章觀點(diǎn)認(rèn)為的“廣義的調(diào)性”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就在于序列形態(tài)的本身就形成了一種音響組織的結(jié)構(gòu)力。這些觀點(diǎn),一定程度上與Wallace Berry 關(guān)于音高結(jié)構(gòu)功能討論[18]Wallace Berry, Structural Functions in Music, Prentice-Hall Inc,1976, School of Music,University of Michigan. Wallace Berry 是美國(guó)音樂(lè)理論家,該著作主要從調(diào)性、織體、節(jié)奏節(jié)拍三個(gè)方面論述了音樂(lè)的結(jié)構(gòu)功能。在調(diào)性方面,他認(rèn)為可以將調(diào)性寬泛地理解為一個(gè)結(jié)構(gòu)化的系統(tǒng),在這個(gè)系統(tǒng)中,音高內(nèi)容可視為與功能性相關(guān)的一個(gè)特定的音高級(jí)(pitch-class)或音高級(jí)的復(fù)合體(pitch-class-complex)。這種釋義不僅可以闡釋西方18—19 世紀(jì)的調(diào)性音樂(lè)實(shí)踐,同樣也適用于近現(xiàn)代的非調(diào)性音樂(lè)。中所持的觀點(diǎn)一致,即在非調(diào)性音樂(lè)中討論調(diào)性問(wèn)題,首先涉及調(diào)性觀念的拓展,否則就無(wú)從討論調(diào)性。由于陳銘志的研究涉及十二音的復(fù)調(diào)寫(xiě)作問(wèn)題,所以引入了Ernst Krenek[19]Ernst Krenek(1900—1991),美籍奧地利作曲家。對(duì)于其名的翻譯有克熱內(nèi)克、克謝內(nèi)克等,其代表作有歌劇《容尼奏樂(lè)》,以及《第四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等十二音序列風(fēng)格的作品。他在《根據(jù)十二音技巧的對(duì)位研究》一書(shū)中,根據(jù)音程緊張度的逐步上升將和弦分為六類,被陳銘志引入到其研究之中。的音程協(xié)和度理論,來(lái)論述根據(jù)音程的協(xié)和度對(duì)于和弦的張力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陳銘志認(rèn)為,一個(gè)音列截段的和聲化變奏,可以通過(guò)合理地重新排列音列中的各音來(lái)獲得,這樣也可以獲得特定結(jié)構(gòu)的和弦;和聲的線性化處理可以根據(jù)對(duì)稱性原則去對(duì)特定結(jié)構(gòu)的和弦進(jìn)行可變性處理。由此可見(jiàn),這些對(duì)于音列或和聲中的音高排序位置的改變,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集合思維的表現(xiàn)。
盡管我們認(rèn)可廣義的調(diào)性存在,也承認(rèn)一個(gè)十二音列從形式本身對(duì)于音列中的各個(gè)音結(jié)合所產(chǎn)生的和弦具有邏輯上的結(jié)構(gòu)力,但是,在實(shí)際的使用過(guò)程中,作曲家并不能就此而獲得一種更加具體的和聲張力,以及和弦價(jià)值的判斷。因?yàn)椤笆艉吐暿鞘€(gè)半音任意組合的產(chǎn)物,它沒(méi)有固定的和弦結(jié)構(gòu),不存在和弦的功能屬性,并且和弦之間的連接不以任何功能邏輯為依據(jù)”[20]楊路《十二音和聲寫(xiě)作基本要點(diǎn)(現(xiàn)代實(shí)用作曲技法之三)》,《音樂(lè)探索》1992 年第4 期,第54 頁(yè)。。所以,楊路就從欣德米特的音序理論與和弦的協(xié)和度與緊張度的排序中去尋找依據(jù)。根據(jù)這一理論,他認(rèn)為十二音和弦的產(chǎn)生,可以通過(guò)嚴(yán)格的排列、各截段自由的排列,以及移位與變形之間的自由排列來(lái)產(chǎn)生,并按照緊張度理論進(jìn)行組織。這里的自由排列,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是一種自由十二音的組織方式了。由此所產(chǎn)生的矛盾不可避免,即旋律的序列與和聲的序列在風(fēng)格上可能存在明顯的差異——按照嚴(yán)格的十二音規(guī)范產(chǎn)生的旋律是無(wú)調(diào)性的,但和聲的序列卻有可能產(chǎn)生調(diào)性甚至產(chǎn)生調(diào)性體系中的和弦結(jié)構(gòu),和聲運(yùn)動(dòng)時(shí)張力的內(nèi)在邏輯或和聲整體風(fēng)格的一致性(如無(wú)調(diào)性音響的平衡與協(xié)調(diào)等)就成為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問(wèn)題。
十二音和聲在理論和實(shí)踐中所面臨的諸多問(wèn)題,隨著喬治·珀?duì)柪碚撛?0 世紀(jì)90 年代中后期的引進(jìn),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楊衡展1997 年發(fā)表于《黃鐘》第4期的《循環(huán)音集論:G·珀?duì)栮P(guān)于十二音和聲結(jié)構(gòu)組織的新概念》一文,較詳細(xì)地介紹了珀?duì)柕难h(huán)音集理論。作為對(duì)該文的回應(yīng),羅忠镕在1998 年發(fā)表的文章中[21]羅忠镕《〈嫦娥〉自述——喬治·珀?duì)枴笆粽{(diào)式體系”簡(jiǎn)介與〈嫦娥〉分析》,連載于《黃鐘》1998年第2、4 期。,結(jié)合自己的作品《嫦娥》,進(jìn)一步解釋了在實(shí)際創(chuàng)作中如何理解與應(yīng)用循環(huán)音集理論。作為一個(gè)重要的補(bǔ)充,他在文章中還進(jìn)一步介紹了珀?duì)柕挠闪N循環(huán)音集對(duì)子聯(lián)合而構(gòu)成的“十二音調(diào)式體系”,以及如何在實(shí)際的創(chuàng)作中使用這一體系。羅忠镕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說(shuō)明了一個(gè)事實(shí),即珀?duì)柕睦碚撌强梢詾榻鉀Q上述問(wèn)題提供很好參照的。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說(shuō),“這是一個(gè)思想十分周密、邏輯性很強(qiáng)的體系,所以我認(rèn)為還是很值得對(duì)它加以關(guān)注的。”[22]羅忠镕《〈嫦娥〉自述(上)——喬治·珀?duì)枴笆粽{(diào)式體系”簡(jiǎn)介與〈嫦娥〉分析》,《黃鐘》1998 年第2 期,第3 頁(yè)。有些遺憾的是,我們雖然在20 世紀(jì)90 年代就已經(jīng)意識(shí)到這個(gè)體系對(duì)于解決中國(guó)序列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中所面臨的問(wèn)題有所幫助,但是并沒(méi)有在這個(gè)方面做進(jìn)一步的深耕。
五
集合理論作為20 世紀(jì)最重要的分析理論之起源問(wèn)題在西方理論界所面臨的一些爭(zhēng)議,[23]很多人都認(rèn)為,集合理論的產(chǎn)生最早可以溯源至美國(guó)音樂(lè)理論家巴比特的研究,例如,鄭艷在其博士論文《結(jié)構(gòu)主義視域下的序列主義音樂(lè)研究——以密爾頓·巴比特與路易吉·達(dá)拉皮科拉序列作品為例》(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2012 年)中將巴比特稱為“唯理性”數(shù)學(xué)家,并提出巴比特的“數(shù)意識(shí)”引領(lǐng)著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探討了十二音音級(jí)集合的作曲潛力,如《十二音體系中集合結(jié)構(gòu)的功能》(1946)等論文。和其針對(duì)的對(duì)象之一——十二音序列音樂(lè)的早期理論到底出自誰(shuí)手所產(chǎn)生的爭(zhēng)議,在世紀(jì)末的中國(guó)音樂(lè)理論研究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這也使得作為作曲技術(shù)理論的序列音樂(lè)理論的研究,和作為音樂(lè)分析理論的集合理論的研究,在中國(guó)相互交織在一起,呈現(xiàn)出一種相互補(bǔ)充和相互促進(jìn)的局面。近年來(lái)的研究表明,由于這一早期理論的許多內(nèi)容已經(jīng)在中國(guó)80 年代以來(lái)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得到了驗(yàn)證,因此,過(guò)去將序列音樂(lè)理論作為一種封閉性理論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盡管這一技術(shù)理論在西方的發(fā)展繼整體序列主義之后就已經(jīng)窮途末路,但如果我們以一種更加開(kāi)放的觀念去理解,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一理論實(shí)際上從一開(kāi)始就有著二元化的相互排斥的概念解釋。與此相似的是,巴比特也常常被視為集合理論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盡管他沒(méi)有把這一概念及其引申出來(lái)的許多內(nèi)容徹底符號(hào)化和系統(tǒng)化,但作為一個(gè)作曲家和理論家,他對(duì)于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的音高結(jié)構(gòu)中所存在的音高不同但音程內(nèi)涵相同的集合組織現(xiàn)象,以及從一種音高組織中派生出另一個(gè)與之具有相似性關(guān)系的音高組織的這種包含與被包含的集合關(guān)系,是有著深刻理解的。也正是因?yàn)槿绱耍囊魳?lè)完全可以被視為是高度組織化與理性化的,是阿倫·福特?zé)o調(diào)性音樂(lè)結(jié)構(gòu)分析理論的最好對(duì)應(yīng)物。而在阿倫·福特的視野中,他盡管將這樣一種無(wú)調(diào)性音高組織及其運(yùn)動(dòng)的現(xiàn)象進(jìn)行了數(shù)理化、邏輯化的表達(dá),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分析理論體系,但并未將集合理論視為僅僅服務(wù)于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的一套封閉的分析體系。從1990 年陳丹布的譯文[24]阿倫·福特著,陳丹布譯《音樂(lè)的新線性分析方法》,連載于《音樂(lè)探索》1990 年第3、4 期。中可以發(fā)現(xiàn),阿倫·福特將集合理論與申克的分層理論進(jìn)行了有效的結(jié)合,用來(lái)觀察在19—20 世紀(jì)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音樂(lè)。這二者的結(jié)合,使得集合理論不僅在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的分析中顯示出其工具的有效性,而且對(duì)于調(diào)性音樂(lè),或調(diào)性處于高度半音化或不確定性狀態(tài)的音樂(lè)分析來(lái)說(shuō),這種獨(dú)特的視野和兩種理論的有效結(jié)合所產(chǎn)生的分析結(jié)果也是令人驚喜的。
90 年代的許多研究,也是伴隨著這些理論所產(chǎn)生的相關(guān)問(wèn)題展開(kāi)的。例如,對(duì)于巴比特的研究,不僅使我們?cè)谡w序列主義的研究領(lǐng)域更進(jìn)一步,而且在整體序列主義對(duì)所有音樂(lè)要素進(jìn)行全面控制過(guò)程中所產(chǎn)生的音響的無(wú)序性效果,使我們對(duì)于這種音樂(lè)風(fēng)格所具有的嚴(yán)格控制與自有隨機(jī)的兩極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認(rèn)知;[25]參見(jiàn)楊衡展《現(xiàn)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兩個(gè)極端——趨于全面控制與走向自由隨機(jī)》,《天津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0 年第1 期。與此同時(shí),一些除音高要素之外的,在全面要素的控制中產(chǎn)生特別作用的要素(如節(jié)奏等),在序列音樂(lè)中的呈現(xiàn)方式、數(shù)列性特征,以及在音樂(lè)中所具有的獨(dú)特的結(jié)構(gòu)力作用,也受到了理論家的關(guān)注。[26]參見(jiàn)張巍《序列音樂(lè)中的數(shù)列化節(jié)奏》,《交響》1990 年第2 期。而另外關(guān)于巴比特所謂十二音“集結(jié)態(tài)”理論[27]參見(jiàn)陳小兵《十二音序列的集結(jié)態(tài)》,《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3 年第2 期。與集合的不變量問(wèn)題[28]參見(jiàn)陳小兵《十二音的不變量——巴比特序列思維研究札記》,《黃鐘》1997 年第3 期。的引進(jìn),盡管是對(duì)序列的組合性原則與組合方法、類別的一個(gè)比較詳細(xì)的介紹(我們完全可以將巴比特關(guān)于集結(jié)態(tài)的定義與豪爾的“特洛普”理論的概念進(jìn)行比較而發(fā)現(xiàn)其中的淵源,也可以將之與集合理論相比較而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致性特征),但對(duì)于這一理論的獨(dú)立思考還引發(fā)了一些理論家對(duì)此問(wèn)題的批評(píng)。根據(jù)陳小兵論文的介紹,我們可以將集結(jié)態(tài)理解為序列的不同集合形式的同時(shí)組合所產(chǎn)生的一種可控狀態(tài)。與經(jīng)典的十二音序列理論的定序原則不同的是,雖然這種由集結(jié)態(tài)構(gòu)成的新的集合保留了原來(lái)序列形式的音級(jí)內(nèi)容,但這些集合實(shí)際上是無(wú)序的。其集結(jié)的類型通常被分成半集結(jié)態(tài)與全集結(jié)態(tài)。半集結(jié)態(tài)包含倒影集結(jié)態(tài)(無(wú)共同音級(jí)的P 與I6音集合的集結(jié)形式)、逆行集結(jié)態(tài)(無(wú)共同音級(jí)的P 與R6音集合的集結(jié)形式)、逆行倒影集結(jié)態(tài)(無(wú)共同音級(jí)的P 與RI6音集合的集結(jié)形式),以及原型集結(jié)態(tài)(無(wú)共同音級(jí)的P 與P6音集合的集結(jié)形式);而全集結(jié)態(tài)則是指兼有以上四種集結(jié)態(tài)類型,并在一個(gè)或者更多的移位位置上構(gòu)成的集合。這種集合的音高發(fā)生變化而涵量不變的組合方式,實(shí)際上也就是巴比特所謂的集合的不變量概念的核心。實(shí)際上,這一概念的內(nèi)涵,也從另一個(gè)方面證明了其理論與阿倫·福特的集合理論中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有意思的是,上述部分內(nèi)容受到了華萃康的質(zhì)疑與補(bǔ)充。[29]華萃康《對(duì)〈十二音序列的集結(jié)態(tài)〉一文的看法——兼談兩六音組之間的“互補(bǔ)”關(guān)系》,《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4 年第3 期。他認(rèn)為,在所謂這些集結(jié)態(tài)類型中,將六音組集合的集結(jié)視為六音組“互補(bǔ)”關(guān)系,更加有利于理解集結(jié)態(tài)的內(nèi)涵及意義。而且,后者還對(duì)于前文中出現(xiàn)的一些關(guān)于六音集合集結(jié)態(tài)的缺失,以及移位音組的音名錯(cuò)誤進(jìn)行了校正。與其說(shuō)這是對(duì)陳文的一個(gè)質(zhì)疑,還不如說(shuō)是對(duì)巴比特本人的質(zhì)疑。就上述問(wèn)題來(lái)看,陳文實(shí)際上是對(duì)巴比特理論的介紹而已。直到1997 年,二者之間的討論隨著陳小兵的再次回應(yīng)[30]陳小兵《十二音序列集結(jié)態(tài)的幾個(gè)問(wèn)題——對(duì)〈看法一文〉的看法》,《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7 年第2 期。才告一段落。在這次回應(yīng)中,陳文認(rèn)為華萃康對(duì)于一些集合的基本概念進(jìn)行了主觀的判斷,并在此就“集結(jié)態(tài)的有序性”“關(guān)于P/R 集結(jié)態(tài)”“關(guān)于六音集合的數(shù)量與Z 關(guān)系對(duì)”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的討論。這些討論似乎最終也沒(méi)有獲得結(jié)論或達(dá)成共識(shí)。前者是巴比特理論的陳述與理解,而后者則是以集合理論的思維來(lái)對(duì)巴比特的理論進(jìn)行重新審視。從邏輯的角度來(lái)看,二者之間雖然有思維上的繼承,但絕非要獲得相同的結(jié)果。由此可見(jiàn),對(duì)于這些看來(lái)非常復(fù)雜的音樂(lè)理論,我們并沒(méi)有照單全收,而是通過(guò)這些不同視野、不同理論之間的相互碰撞,進(jìn)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早期的十二音理論和集合理論,在其體系的創(chuàng)立過(guò)程中,實(shí)際上也衍生了大量新的問(wèn)題。這一方面說(shuō)明一種理論的啟發(fā)性價(jià)值所在,另一方面也為相關(guān)的理論研究留下了大量的空間。盡管陳銘志在20 世紀(jì)90 年代初就提到集合理論還僅僅是一種分析方法而不是作曲技法的觀點(diǎn),但也就是從那時(shí)起,一些試圖將集合理論轉(zhuǎn)化為集合思維來(lái)指導(dǎo)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研究,就值得我們的關(guān)注。陳士森在他的研究中不僅討論了集合理論的原理,將集合程控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構(gòu)架運(yùn)用在音樂(lè)作品的分析操作之中,他還將這種理論看成是一種作曲技法,將相當(dāng)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在創(chuàng)作中運(yùn)用集合理論的思維,[31]參見(jiàn)陳士森《集合程控理論及技法》,連載于《交響》1990 第1—4 期。去組織和安排音高材料等方面。鄭英烈這一時(shí)期所提出的基本集合的概念,是基于十二音序列的寫(xiě)作,是希望將一個(gè)基本集合中的音程內(nèi)涵作為十二音寫(xiě)作過(guò)程中其他和聲構(gòu)成的參照,并借以形成十二音和聲在音響風(fēng)格上的一致性。
六
上文對(duì)于十二音調(diào)性與和聲問(wèn)題的討論,以及對(duì)于集合理論在20 世紀(jì)90 年代中國(guó)的發(fā)展性研究的一個(gè)分析與回顧,實(shí)際上是希望從序列音樂(lè)理論諸多問(wèn)題的研究中管窺其核心要點(diǎn)。無(wú)論從哪個(gè)方面看,這兩大問(wèn)題中都包含了序列音樂(lè)或無(wú)調(diào)性音樂(lè)風(fēng)格在與中國(guó)音樂(lè)風(fēng)格相結(jié)合的專業(yè)創(chuàng)作中所面臨的問(wèn)題與訴求。實(shí)際上,在80 年代就盛行的五聲性序列音樂(lè)的研究,在90 年代并未銷聲匿跡。這一研究不僅在整個(gè)90 年代中持續(xù)下去,而且,研究的視角從過(guò)去較為寬泛的一些內(nèi)容轉(zhuǎn)向更為深層次的概念本體之中。許多的研究甚至視角獨(dú)特,將十二音創(chuàng)作中的一些具體實(shí)踐與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中調(diào)式問(wèn)題的研究形成了交叉與滲透。
值得注意的一個(gè)方面是對(duì)于五聲性序列概念的討論。當(dāng)鄭英烈在1982 年的文章《序列的類型及結(jié)構(gòu)》[32]鄭英烈《序列的類型及結(jié)構(gòu)(序列音樂(lè)研究之二)》,《廣州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2 年第3 期。中首次提出“五聲性序列”這一概念時(shí),雖然提到序列類別的劃分是根據(jù)其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而來(lái)的,但是他并未就五聲性序列的結(jié)構(gòu)特征進(jìn)行完整的描述。羅忠镕在其《第三弦樂(lè)四重奏》的創(chuàng)作說(shuō)明[33]羅忠镕《第三弦樂(lè)四重奏》,《音樂(lè)創(chuàng)作》1997 年第4 期。中談到五聲性音級(jí)集合時(shí)指出:“我所謂的‘五聲性音級(jí)集合’即不包含音程級(jí)1(半音)和6(三全音)的集合……在這里我并不想下一個(gè)學(xué)術(shù)上的定義,而只是作為一個(gè)主觀上的規(guī)定。”[34]同注[33],第62 頁(yè)。顯然羅忠镕認(rèn)為,的確需要一個(gè)“學(xué)術(shù)上”的定義,才能真正將五聲性音級(jí)集合的概念弄清楚。但在他“主觀上”看來(lái),五聲性集合應(yīng)該是一種突出其五聲性調(diào)式中音程特征的集合,但只要是其中包含了半音與三全音就不可能構(gòu)成五聲性集合。這一觀點(diǎn)的局限性在于,如果我們將五聲性集合作為一種具有特定風(fēng)格特征的集合的話,或者說(shuō)這個(gè)集合會(huì)因?yàn)槟承┪迓曅缘奶卣髯鳛橐粋€(gè)辨識(shí)的標(biāo)志,那么,即便這個(gè)集合中包含了上述音程,我們也是可以將之視為五聲性集合的。實(shí)際上,在此之前的一些研究者(包括鄭英烈)也同樣意識(shí)到了相同的問(wèn)題。在他給學(xué)者周雨的回信中談到了他對(duì)五聲性序列的看法:“一個(gè)十二音序列可以劃分成若干個(gè)五聲性音組的階段(無(wú)剩余音),這個(gè)序列便是五聲性的,即使截段與截段之間構(gòu)成半音或三全音;一個(gè)十二音序列可劃分成若干個(gè)五聲性音組,但有剩余的不能歸入音組的音,只要這些音能與前后鄰音構(gòu)成五聲性音程,也屬五聲性序列。”[35]周雨《五聲性序列初探》,《黃鐘》1992 年第2 期。雖然這種對(duì)于五聲性序列的概念描述更加深入——三全音和半音可以出現(xiàn)在音組的相鄰處,但對(duì)于在五聲性音組的內(nèi)部是否能容忍這種音程關(guān)系卻只字未提。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周雨的研究?jī)r(jià)值或許更加客觀。在周雨看來(lái),有的十二音序列可以被盡數(shù)劃分為五聲性集合而無(wú)剩余音,而有的被分割為五音之內(nèi)的集合之后,仍有剩余尚不能納入五聲性集合之中的這些音,可以將它們稱之為“變聲”。根據(jù)這一理解可以發(fā)現(xiàn),假如將三個(gè)音作為具有五聲性特征的最小集合單位,不包含小二度和三全音的在五個(gè)音之內(nèi)的五聲性集合共有八個(gè),我們可以將這八個(gè)視為第一類五聲性集合,而如果周雨的“變聲”概念可以成立的話,那么就存在第二類包含有變聲的五聲性集合。這樣,整個(gè)五聲性集合的種類就會(huì)大大增加。
與通過(guò)“變聲”的方式來(lái)拓展五聲性序列的研究同出一轍,在陸金墉的論文[36]陸金墉《五聲性序列與序列的異化——現(xiàn)代作曲技法探討之一》,《交響》1996 年第3 期;《五聲性序列與序列的異化──現(xiàn)代作曲技法探討之二》,《交響》1997年第1 期。中可以發(fā)現(xiàn)相似的論點(diǎn),但作者卻是采用了“有限與可變”的概念來(lái)對(duì)其理論進(jìn)行描述。還有一些研究是從中國(guó)傳統(tǒng)樂(lè)學(xué)的角度來(lái)討論五聲性序列的音高特征。例如,趙金虎就以黃翔鵬的“同均三宮”理論作為依據(jù),并受到童忠良80 年代末期《論十二音級(jí)雙均多宮》中觀點(diǎn)的影響,試圖用“均控場(chǎng)”的方法,來(lái)解釋五聲性序列作品中的音高構(gòu)造現(xiàn)象。這一說(shuō)法及其理論研究中的一些觀點(diǎn),也受到了學(xué)者王青的質(zhì)疑,[37]參見(jiàn)王青《“均控場(chǎng)”理論與中國(guó)音樂(lè)的十二音實(shí)踐——與趙金虎商榷》,《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3 年第2 期。根據(jù)筆者的理解,其大意是:其一,如果將符合均控場(chǎng)理論的十二音序列之內(nèi)部的音序進(jìn)行顛倒調(diào)換,那么,再將所產(chǎn)生的不同排列形式的序列置于“均”的音組結(jié)構(gòu)中,這一做法既牽強(qiáng)也無(wú)邏輯的必要;其二,一個(gè)五聲性序列用“均”來(lái)進(jìn)行劃分是否必要或合理,這種傳統(tǒng)樂(lè)學(xué)理論的分析結(jié)論對(duì)于音樂(lè)的實(shí)際聽(tīng)覺(jué)感受的意義何在;其三,作者以均控場(chǎng)的理論將貝爾格《抒情組曲》的序列分析為F 均與bF 均的組合,這是否意味著均控場(chǎng)理論不僅可以解釋五聲性風(fēng)格的序列,也是一個(gè)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理論。通過(guò)上述質(zhì)疑,或許我們可以對(duì)所謂均控場(chǎng)理論所持的觀點(diǎn)有些許了解。
至此,本文以上的討論,不僅說(shuō)明了序列音樂(lè)給中國(guó)當(dāng)代音樂(lè)風(fēng)格帶來(lái)了觀念沖擊和影響,也推動(dòng)了我們專業(yè)音樂(lè)創(chuàng)作技術(shù)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作思維的轉(zhuǎn)變。筆者通過(guò)對(duì)20 世紀(jì)90 年代序列音樂(lè)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等相關(guān)問(wèn)題的研究,得出以下觀點(diǎn)。首先,序列音樂(lè)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所謂中國(guó)化的過(guò)程,并非是靜止和固化的,而是不斷摸索和持續(xù)糾偏的過(guò)程。在這一過(guò)程中,它不僅反映在中國(guó)民族風(fēng)格對(duì)這一外來(lái)風(fēng)格的滲透和聽(tīng)覺(jué)習(xí)慣的不斷糾偏上,也更加深刻地反映在突破西方技術(shù)理論的概念、范疇和思維方式,并最終要建立自己的邏輯起點(diǎn)和概念系統(tǒng)方面。這并不是說(shuō)我們一定要繞開(kāi)西方原始的基礎(chǔ)概念而去生造一個(gè)全新的概念,而是要對(duì)那些看似基礎(chǔ)的概念作出新的哲學(xué)化的、美學(xué)化的、藝術(shù)性的理解。其次,由于序列音樂(lè)伴隨著中國(guó)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轉(zhuǎn)型的特殊狀態(tài)進(jìn)入中國(guó),以這種風(fēng)格為載體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和理論研究,彼此相伴相生。從技術(shù)的運(yùn)用到發(fā)展,從理論的吸收到理論的發(fā)散與創(chuàng)新,看似都在不斷回答“如何比較充分地體現(xiàn)內(nèi)在的民族氣質(zhì)或民族韻味”[38]同注④。這一問(wèn)題,而實(shí)際上其內(nèi)在動(dòng)因都是中國(guó)文化基因使然。因此,中國(guó)化這一概念的形成決不能通過(guò)將一種現(xiàn)存的觀念與另一種現(xiàn)存的觀念進(jìn)行簡(jiǎn)單拼湊來(lái)完成。如果理論與實(shí)踐僅僅是滿足于“有用的”“即 用即拋”的即時(shí)與工具性心態(tài),滿足于西方理論的“中國(guó)式引用與操作”,卻不問(wèn)這種做法是否對(duì)建立中國(guó)音樂(lè)風(fēng)格與理論的主體性具有穩(wěn)定的意義,是否能在中國(guó)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是否對(duì)中國(guó)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產(chǎn)生實(shí)質(zhì)性意義,那么,我們將永遠(yuǎn)無(wú)法就序列音樂(lè)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到底是序列音樂(lè)的中國(guó)化還是中國(guó)音樂(lè)的序列化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得到滿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