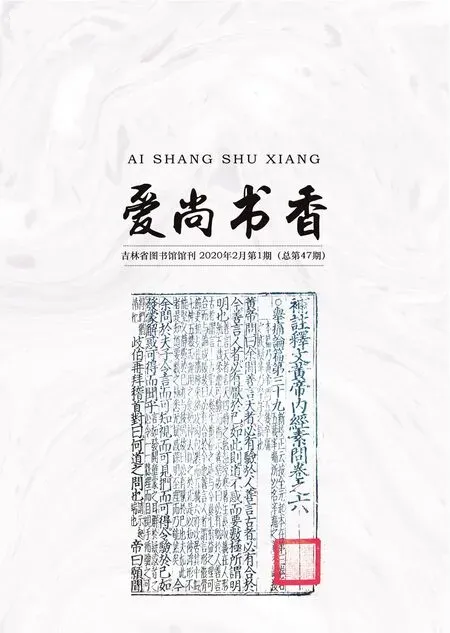詩樣年華
曹 泓

看林白的《玻璃蟲》,有一句話特別能產生共鳴,大意是這樣,女主人公說她對20世紀80年代曾經寫過詩和熱愛過詩歌的人充滿敬意。我想,這根本就是林白的心里話。
那個年代,的確是一段詩歌如飽滿的乳汁般香甜酣美地流淌的日子,我們這些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人,正值青春年少,心靈是一片單純得未被開墾的處女地,胸口卻有一團團火焰熱辣辣地燃燒,就是這樣無知一樣的單純和火樣的熱情,讓我們不斷地將一行行詩歌當作乳汁暢飲下去,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滿足與充實。
然而,說真的,我現在卻很難相信甚至羞于表達當時的自己對詩歌是充滿了怎樣的熱愛、敬畏與仰慕之情。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感呢?很執著,深深地裝在心里。在無人處細致地閱讀、咀嚼與琢磨所能找到的每一首詩,于是,舒婷、北島、江河、楊煉、顧城、王小妮、徐敬亞們便如一座座豐碑在我心中樹立起來,他們的每一首詩、每一句話甚至一個簡單的破折號在我眼里都是那么意味深長、耐人尋味,人生的所有況味似乎都藏在那些長長短短的句子中,等待我去品味探尋。
夜不能寐的皎潔夜晚,深邃的藍天下,風兒溫和地撫平招搖了一整天的花樹枝葉,闃靜中,那些我所敬愛的詩人的詩句在我的心中麥浪一樣翻滾,有青澀、有翠綠、有橙黃,卻都是一樣的馨香襲人——
“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的肩頭痛哭一晚”(舒婷《神女峰》);
“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立在一起/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舒婷《致橡樹》);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銘”(北島《回答》);
“上路的那天,他已經老了,否則他不去追趕太陽,青春本身就是太陽”(江河《追日》);
“在秋天,有一個國度是藍色的/路上落滿藍瑩瑩的鳥和葉片(顧城《凈土》)”;
……
這些說也說不完,數也數不清的詩句啊,這些充滿了摯情、充滿了反思、充滿了哲理、充滿了反世俗意味的詩句啊,它們把愛情、把人生、把為人的準則是那樣通透地涵養在簡潔的詩行中,這詩行在我可望而不可即的遠方高懸,讓我心燈忽明忽暗,在不停走近它們的過程中,心里產生了深深的敬畏和仰慕。
那些金子一樣閃閃發光的詩句早已隨著生存的種種磨礪消失在似水流年里,我只會在某個呼朋引伴、喧囂過后的靜夜里,讓某一首詩、某一行刻骨銘心的詩句,在備感失落的心中緩緩漂浮起來,萬分感慨地咀嚼一番,卻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景仰與信服。只有一句話風一樣從耳邊掠過:我曾瘋狂喜歡過詩歌。然而,這話風一樣掠過便算了,人前,我是絕不會承認自己年少時對詩歌的鐘情以及偷偷摸摸在日記中練筆的事情。
可無論何時何地,我都必須承認,在那些真情流露的日子里,詩的情感有時便是自己的情感,詩的啟迪有時真是打開心結的一雙妙手。至今我還保存著一首小詩,詩來源于一位高中好友,她當時已舉家遷往異鄉,但我們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在我高考失利心情郁悶時,她的信中沒有只言片語的安慰,只摘抄了這樣一首小詩:“別把夢做得過于美麗/你我以及他之間的距離/已經構成/許多蒲公英流浪的故事/哪天與你相遇/你也會流下一串很長很長的淚滴……/向著一樣的日光一樣的晴朗/我們總是細心地將每個無味的日子捏響/卻不理睬/黑夜的偷襲。”當時我反復地讀這首詩,眼淚一次次地流,后來我真的平靜下來。
20多年過去了,那些熱愛詩歌,到處尋找詩歌并不惜筆墨摘抄詩歌,想方設法參加詩歌講座,被詩歌啟發感化,為詩歌激動流淚,在詩歌里尋覓生活的意義與方向的單純日子早已蒸發在日常的生活中,只是蒸發的水總會在某一個春夜里化作雨絲詩意充盈地回到凡塵,讓我在淅淅瀝瀝的吟喁聲中回到自己的詩樣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