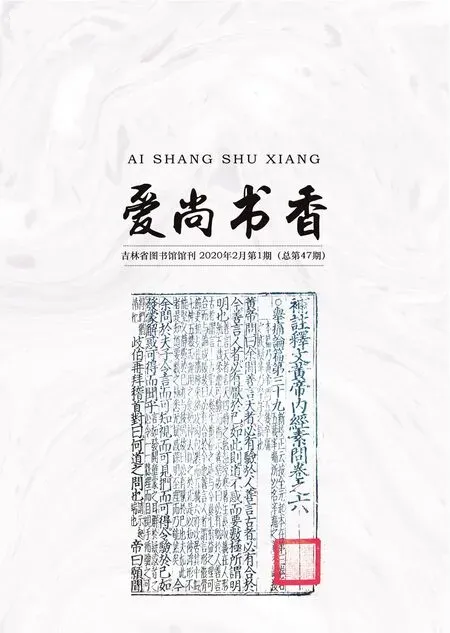翻譯家查良錚的詩路歷程
石 華
查良錚(1918-1977),又名穆旦,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寧市袁花鎮。曾用筆名梁真,是清代著名詩人査慎行的后裔,也是九葉派詩人的主要代表。穆旦少年時便展露詩才,曾寫下《哀國難》這樣的詩篇,憤怒控訴日寇鐵蹄蹂躪中華的累累罪行。1935年,他入讀清華大學外文系,繼續探索和寫作詩歌。據同學王佐良回憶,穆旦愛詩,他的詩歌散發著雪萊式的浪漫抒情氣質。后到昆明,發表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詩》《從空虛到充實》《贊美》等作品,他的詩風轉入現實主義,語言漸趨硬朗,成為著名的青年詩人。
大學時代的穆旦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深受左翼文化和政治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具有熾熱的愛國情懷。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國內國際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作為詩人的穆旦命運也經歷了悲愴的轉折。為了與英美盟軍合作開辟印緬戰場,他投筆從戎,作為第一陸軍副司令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的翻譯,參加了中國遠征軍。可是由于盟軍協助不好且指揮不力,在激烈的對戰之后,盟軍潰敗,各支軍隊倉皇撤退,穆旦一部陷入崇山峻嶺之間,與淫雨癘疫、遍野尸骨為伴,慘絕人寰,九死一生。王佐良在《中國的一個新詩人》中有這樣一段講述曾被廣泛引用:“那是1942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后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豪雨里,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之外,阿薩密的森林的陰暗和沉靜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蝗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饑餓……”。這段慘烈經歷給穆旦的心靈造成強烈的震撼,在他的經典名篇《森里之魅》,副標題為《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中,他寫道:“……在橫倒的大樹旁,在腐爛的葉上/綠色的毒,你癱瘓了我的血肉和身心……”。
穆旦常常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詩歌第一人,同時,也是迄今為止中國詩歌翻譯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個人。作為一個天賦異稟的詩人,他卻又如何走上翻譯的道路,以翻譯家查良錚的身份廣為人知的呢?
1937中日戰爭爆發。清華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撤出北平,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一起抵達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南岳的衡山圣詩學院重新開課。后來,隨著南京失陷,日軍緊逼武漢、長沙,臨時大學只好從衡山湘水再遷云南昆明。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長途跋涉68天,3000多里,才到達昆明。“長征”路上,他竟然學習不輟,背完了一本英漢詞典。在昆明,長沙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建,是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中國學術文化的中心。這里有眾多中國詩歌史上的精英人物,如朱自清、聞一多、卞之琳等,也有袁可嘉、鄭敏、王佐良等青年愛詩者,他們一起探討中外詩藝、切磋交流。當時,他還選讀吳宓教的《歐洲文學史》和威廉·燕卜蓀教的《莎士比亞》和《英國詩》等課程。威廉·燕卜蓀,這位來自英國的講師,給穆旦以很大的影響和啟示,穆旦英詩文論的領路人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這位英國詩人。在西南聯大兩年期間,燕卜蓀獨特的教學方式和人格魅力,無疑持久而深刻地影響到穆旦及其同學,塑造了一大批現代詩人,使西南聯大成了打造中國現代派詩歌的基地。燕卜蓀畢業于劍橋大學,從數學專業轉至文學專業,曾師從大名鼎鼎的文學理論家瑞恰慈,寫出《復義七型》這部經典著作,開創了“細讀”批評典范。當時,燕卜蓀給二年級外語專業講授《英國詩》,從史文朋、霍普金斯開始,一直講到三十年代的奧登,引介了當時英國文學史上主要的現代主義詩人。此外,他還在1937-1938年主講《英國散文及作文》,以及四年級專業必修課《莎士比亞》。王佐良回憶說:“燕卜蓀是位奇才……他的那門《當代英詩》課內容充實,選材新穎,……所選的詩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輩詩友,因此他的講解也非一般學院派的一套,而是書上找不到的內情、實況,加上他對語言的精細分析。”在當時的西南聯大,生活艱苦,教學條件極端匱乏,沒有現成的教材,燕卜蓀用他的便攜式打字機憑記憶打出戲劇與詩歌作品,他對英語文學的稔熟程度令學生敬佩不已。總的說來,詩人燕卜蓀對穆旦的詩學影響可追溯至題材、思維范式、表現手法上,如題材中的現實主義內容,玄學的思辨方式,朦朧手法的運用,在兩人的詩歌中都能找到連接點與契合處。
穆旦在聯大接觸的西方詩歌與文論,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他的語言和風格都折射出西方詩歌的影子,而他的語言才能又是得天獨厚的,是一個成功的詩歌翻譯家的必備條件。1948年,穆旦漂洋過海,赴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攻讀英國文學,同時選讀俄語和俄語文學。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匯集了一批來自中國的優秀留學生,其中有理科的李政道、楊振寧、周與良(后為穆旦妻子),文科的鄒謹、盧懿莊、周玨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穆旦在郵局打夜工,搬運郵件,靠勤工儉學維持學業。1952年,穆旦夫婦放棄在國外工作的機會,力排周圍朋友的勸阻,踏上歸國的旅程。 之后,在南開大學外國文學系工作,陸續翻譯出俄語文論,如季摩菲耶夫《文學概論》和《怎樣分析文學作品》,以及一些文學作品。他先后譯出普希金的抒情詩500余首、敘事詩10首,從《波爾塔瓦》《青銅騎士》,到《葉普蓋尼奧涅金》。此后,他轉入英國浪漫主義,拜倫、雪萊、濟慈各有詩選譯集。他的譯名漸以查良錚而廣為傳播。回國后的查良錚放棄大規模詩歌創作,卻從事了翻譯活動,背后當然有其政治原因。“……現代派詩歌在建國后的文學格局中沒有棲身之地,政治意識形態對其深惡痛絕,將其隔絕在譯介推廣的藩籬之外,因此,主流話語對現代派詩歌譯介和創作的代表人物穆旦采取了有意忘卻的策略,雖然穆旦主動歸國,但起先幾年,在中國新詩創作史上仍盡量去除他的一切身影。”盡管他有意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譯介了許多積極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但是1957年,他的詩《葬歌》和《九十九家爭鳴記》仍被批為“毒草”,“幾乎是一個沒有改造的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改造的誣蔑”,穆旦失去了創作的自由。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他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收審,開除公職,處以三年勞改徒刑。從此以后直到1977年去世為止,大約二十年時間,其作品、翻譯、研究論文等被禁止公開發表。勞改期滿獲釋,降級降薪,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圖書館工作,接受監督勞動改造。但他每天回家以后,仍伏案埋頭于翻譯工作,盡管他知道根本沒有發表的機會。拜倫的詩《唐璜》的翻譯是從這時開始的。穆旦醉心于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也曾專心研讀艾略特、奧登等人的現代詩歌,但他的翻譯作品中最令人矚目的成就,莫過于拜倫的《唐璜》。拜倫的詩歌在世界范圍內影響都很廣泛,許多文豪,如法國的雨果、德國的海涅、俄國的普希金等,都曾表達過對拜倫的敬仰。在中國,拜倫也以“拜倫式英雄”而聞名,他多首詩歌曾被不同翻譯家反復翻譯,仿佛成了一決高下的標桿。長篇敘事詩《唐璜》結構宏大、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是拜倫最著名的代表作。全詩充滿悲壯、幽默、諷刺、挽歌的音調,夾雜著政治的議論、田園詩式的愛情;全詩結構松散,敘述人時而寫景狀物、時而嬉笑怒罵、時而抒情懷舊,用口語體對當時的保守派、正統派加以嘲諷。可想而知,這樣一首長詩,要準確傳遞內容信息、要表現拜倫時而莊嚴文雅、時而詼諧俏皮的語體,這對翻譯者將是多么嚴峻的挑戰。更何況,譯者身處一個人性扭曲的年代。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的手稿或被抄走或焚燒,六口人被趕到一間十七平方米的小屋居住,家貧如洗。穆旦被押往天津郊區大蘇莊農場強制勞動,每周只準回家一次。1971年,強制勞動解除,穆旦得以重返南開大學圖書館,每晚與兒子住在學生宿舍樓一間十平方米的宿舍里。他每天除了在圖書館工作八小時外,還被罰以其它勞動,很晚才能回家。在家里吃過飯后,又騎車返回學生宿舍,伏在黑木飯桌上,在昏暗燭光下,一直翻譯到深夜。《唐璜》翻譯始于1962年,1965年完成初稿,1972年經過三次修改,到1973年完成《唐璜》的翻譯及注釋時,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了。而這部浸透譯者十年心酸的譯稿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所以,不妨說,作為“九葉派詩人”的穆旦在1958年就已經死亡,剩下的則是作為翻譯家的查良錚,在無法進行詩歌創作的情況下,他把滿腔熱情傾注于詩歌的譯介,在翻譯《唐璜》的過程中,查良錚變得更加成熟老練,促使他的詩歌語言也更加流暢,達到了無論是詩人還是翻譯家都難以企及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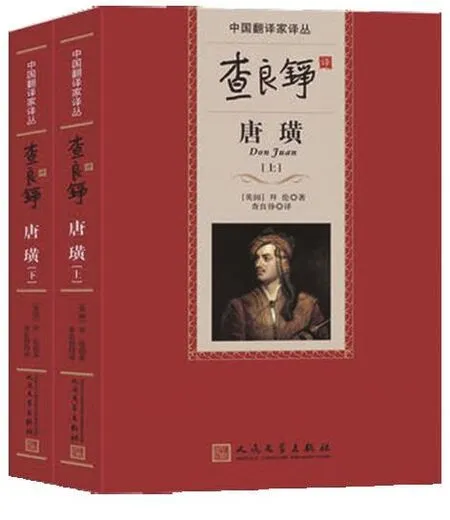
如果說對英美文學和現代主義詩歌的熱愛是成就著名翻譯家查良錚的內部因素,那么極端的政治環境就是穆旦隱身,借翻譯以容身的外部因素。詩人的隱身,翻譯家的出現特別令人想到穆旦的長詩《隱現》:“白日是我們看見的,黑夜是我們看見的,/我們看不見時間/未曾存在的出現了,出現的又已隱沒……”這一隱一現之間投射出人間許多無奈,隱現似乎最能暗合他悲涼卻豐富的人生。
王佐良在《穆旦:由來與歸宿》中寫道:“詩歌翻譯需要譯者的詩才,但通過翻譯詩才不是受到侵蝕,而是受到滋潤。能譯《唐璜》的詩人才能寫出《冬》那樣的詩。詩人穆旦終于成為翻譯家查良錚,這當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許不是一個壞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