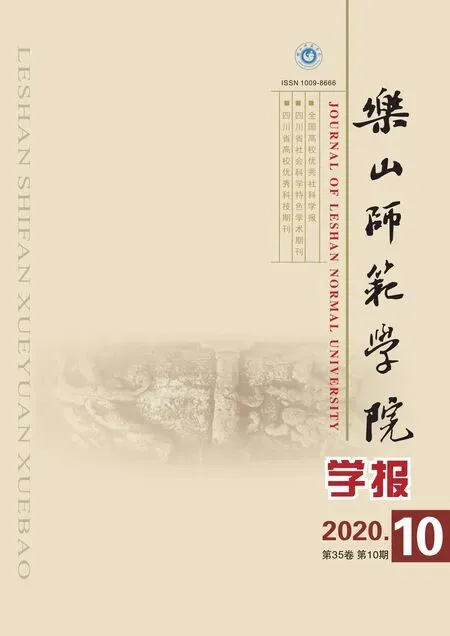論《太平經》中“賢儒”的含義與文論的批評對象
——兼與連登崗、劉湘蘭先生商榷
鄒 旻
(安徽理工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劉湘蘭先生發表于《文學評論》2015年第1期的論文《〈太平經〉與中國早期道教文學觀念》,對中國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中的文學思想作了歸納。其中,“反對‘邪偽文’與‘浮華文’的文章批評論”一條,提出“對于當時社會文尚浮華的現象,《太平經》時有抨擊。……對當時居主流地位的儒家文風極度不滿。《太平經》認為儒者以浮華文教授天下學子,為害甚大。……正因為儒家以浮華巧文傳授天下學子,才導致敗壞大道,流禍國家,社會奸偽成習。……《太平經》對儒家浮華文風之批判,既有對當時社會陋習的反思,也遙承了莊子對儒家思想的鄙薄態度”[1],把《太平經》中批評“邪偽文”“浮華文”的對象認定為“儒家文風”。論文引用了《太平經》中的幾段文字為證:“今者承負,而文書眾多,更文相欺,尚為浮華,賢儒俱迷,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復流言也。”[2]155“他書非正道文,使賢儒迷迷,無益政事,非養其性。經書則浮淺,賢儒日誦之,故不可與之也。”[2]230顯然,劉湘蘭先生把《太平經》中的“賢儒”理解成了“儒家”,才導致了這樣的判斷。那么,《太平經》作為道教經典,其中的“賢儒”能不能理解為“儒家”?其真實含義究竟是什么?對于《太平經》“賢儒”含義的正確把握,直接影響到對《太平經》中文論批評對象的理解,進而影響到對《太平經》文學思想的精確認識。
一、 《太平經》中的“賢儒”泛指“賢能之人”
連登崗先生發表于《中國語文》1998年第3期的論文《釋〈太平經〉之“賢儒”“善儒”“乙密”》指出,“賢儒,指道教徒中賢能有道術的人”。其論據有兩點:第一,“《太平經》作為道教著作,宣揚的是道教教義,稱說的是道教人物,……‘賢儒’是《太平經》中的名號之一,它的所指也應該是道教徒眾”;第二,“‘儒’在《太平經》時代,不僅用來稱呼儒家學派人士,而且也可以用來稱呼那些有專門技藝的人”。作者以《太平經》中的相關句子為例,并引《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俞樾《群經平議·周官一》“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漢書·司馬相如列傳》顏師古注“凡有道術者皆為儒”等為證。同時,作者還指出在《太平經》中,“大賢儒,指道教中的高級道術之士。大儒,即大賢儒之省”。[3]此外,連登崗還在另一篇論文中指出《太平經》中的“賢柔”“賢渘”“大渘”“大渘師”等詞,是“賢儒”“大儒”“大儒師”的變體。[4]
連登崗先生的論據不夠充分,論證邏輯也不夠嚴密。首先,《太平經》作為道教著作,其中的人物固然以道教徒眾為主,但也有非道教徒眾,并非只要出現在《太平經》中的就一定是道教人物。例如《太平經》中經常有“君”“臣”“民”“人”,這些都不一定是道教徒眾。這樣,連登崗的第一條論據就站不住腳了;其次,術士并非只有儒道兩家。章太炎在《原儒》一文中指出:“是諸名藉,道、墨、刑法、陰陽、神仙之倫,旁有雜家所記,列傳所錄,一謂之儒,明其皆公族。”[5]即使《太平經》中的“賢儒”指的不是儒家人物,也不一定就是道教人物。連登崗的第二條論據也不夠扎實。
《太平經》中“儒”共出現24次,其中獨立作為一個詞使用,出現2次;與“賢”連用構成“賢儒”,出現12次;與“大”連用構成“大儒”,出現2次;與“大”“賢”“圣”“仁”“明”等連用構成“大賢儒”“賢圣大儒”“仁賢明儒”,出現5次;與其他詞連用構成“善儒”“儒良”“儒雅”,各出現1次。從構詞角度來看,與“儒”連用頻率最高的“賢”,以及“大”“圣”“仁”“明”等詞,均為泛指賢能之人,并無特定指向,這就提示“儒”在《太平經》中也是泛指。當然,泛指的詞語,如果放在一個特定的語言環境中,往往就會變成特指。例如“圣”“仁”等詞,如果出現在儒家經典中,常常就是特指儒家的圣賢;如果出現在道家經典中,常常就是特指道家的圣賢。但從《太平經》的語言環境來看,其中的“儒”及其構成的“賢儒”等詞,常與一些明顯不是道教人物的稱謂并舉,例如卷四十三《大小諫正法》:“‘諾。子詳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誠信而諫正其上也,君不聽用,反欲害之,臣駭因結舌為瘖,六方閉不通。賢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見。君雖圣賢,無所得聞,因而聾盲,無可見奇異也。’”[2]102其中的稱謂除“賢儒”外,還有“臣”“君”“忠信”“圣賢”等。這里,“臣”“君”顯然不必然是道教人物;“圣賢”與“君”對應,也不是特指。又例如卷四十四《案書明刑德法》:“明刑不可輕妄用,傷一正氣,天氣亂;傷一順氣,地氣逆;傷一儒,眾儒亡;傷一賢,眾賢藏。凡事皆有所動搖。故古者圣人圣王帝主乃深見是天戒書,故畏之不敢妄為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2]109這里的“儒”與“賢”并舉,都沒有特指的意思。“圣人”“圣王”是否特指道教人物,難以判斷;但“帝主”顯然不是道教人物。而且這一段說的意思是不能輕易用刑,刑律的對象是全體民眾,不會是特指道教徒眾。再例如卷一百一十六:“此諸廢氣動搖樂之,則致惡氣大發泄,賢儒藏匿,縣官失政,民臣難治,多事紛紛,不可不戒之慎之也。”[2]642這段話與“賢儒”并舉的,是“縣官”“民臣”。“縣官”在漢代口語中指“天子”,和“民臣”一樣,都不是特指某一類宗教人物。
王充《論衡》與《太平經》同為東漢時期的作品,其中有《狀留篇》,專論“賢儒”與“俗吏”的異同。把“賢儒”與“俗吏”作為兩個對立的概念,說明了“賢儒”和“俗吏”作為語詞,其內涵只包括人的才能,而不涉及學派或教派。《狀留篇》又引“呂望”“百里奚”作為“賢儒”的代表:“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發。……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6]“呂望”“百里奚”都是賢能的典范,卻不是道家或儒家的代表人物。這也說明了“賢儒”在《論衡》中只是泛指賢能之人。
宋張君房編撰的道教類書《云笈七簽》中也有“賢儒”一詞,從文義來判斷,也是泛泛而指。例如卷三十八《說戒部·大戒上品》:“戒曰:勸助國王父母,子民忠孝,令人世世多嗣,男女賢儒,不受諸苦。”[7]這里“賢儒”與“男女”“國王”“父母”“子民”并舉,泛指世間大眾,沒有特指道教徒眾的意思。
“賢”“儒”作為兩個詞分開來使用很常見,但連在一起使用卻很少見。秦漢諸子、《史記》、《漢書》中,都找不到“賢儒”一詞。東漢以前,似乎僅在《太平經》和《論衡·狀留篇》中出現過“賢儒”這個詞,東漢以后出現的也不多。由于道教與下層民眾的聯系很緊密,《太平經》《云笈七簽》等道教經典中,有很多是向下層民眾傳教的內容,因而有著比較明顯的口語化傾向。劉祖國先生的博士論文《〈太平經〉詞匯研究》指出:“〈太平經〉作為中國道教的第一部經典,其宣講對象主要是下層民眾,為宣揚教義的方便,是書采用一問一答的對話體寫成,行文通俗淺顯,包含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征口語成分。”[8]據此推斷,“賢儒”一詞,可能是東漢以來流行于民間的口頭語詞,和《太平經》《云笈七簽》中經常出現的“諸賢”“大賢”“賢者”“賢仁”“賢孝”等語詞一樣,都是泛指一般的賢能之人,帶有一定敬語的意味,是一種客套話。
二、《太平經》文論的批評對象為早期道教文書
《太平經》中的“賢儒”只是泛指一般的賢能之人,和儒家沒有必然的關系。這樣,《太平經》對于“邪偽文”“浮華文”的批評,也就并非特別針對“儒家文風”而言。事實上,聯系《太平經》上下文來判斷,其中的“邪偽文”“浮華文”,針對的都是道教文書。
《太平經抄甲部》:“甲部第一又云:‘誦吾書,災害不起,此古圣賢所以候得失之文也。’又云:‘書有三等,一曰神道書,二曰核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精一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核事文者,核事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也。’又云:‘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太平之時。故此經云,應感而現,事已即藏。’又云:‘圣主為治,謹用茲文;凡君在位,輕忽斯典。’”[2]9-10“神道書”“核事文”“浮華記”等“書”,上承“誦吾書”之“書”,下接“此經”“茲文”,顯然都是特指道教文書而言。又例如《太平經卷之三十七·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大頑頓曰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為何等事生?為何職出哉?’……‘真人更明開耳聽。然,凡人所以有過責者,皆由不能善自養,悉失其綱紀,故有承負之責也。……故此書直為是出也。……其后世學人之師,皆多絕匿其真要道之文,以浮華傳學,違失天道之要意。……’”[2]54、55這里“浮華”之文上承“天師上皇神人”的“此書文”和“真要道之文”,顯然也都是特指道教文書而言。
即便是劉湘蘭先生引用的含有“賢儒”的片段,如果把上下文通讀下來,也可以非常清楚地得出《太平經》文論的批評對象為道教文書的結論。例如“今者承負,而文書眾多”一段,下文是“‘……但當實核得其實,三相通即天氣平矣。天法者,或億或萬,時時不同,治各自異,術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氣且至,當實文本元正字,乃且得天心意也。子不能分別,天地立事以來,其治億端,行其事,悉得天應者是也;不得天應者,非也;是即其大明天券征驗效也。寧解耶?’‘唯唯。’‘行去,勿得復問。今非不能為子悉記,天地事立以來,事事分別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難勝記,不可為才用,無益于王治,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夫治不理,本由天文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時賢圣所共憎惡也。故道為有德君出,不敢作文,皆使還守實,求其根,保其元,乃天道可理,國自安。真人雖好問,勿復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2]155、156其中“實核得其實”“實文本元正字”,就是“核事文”;“大明天券”,也就是“神道文”;“益文”,就是“浮華文”,也就是上文“文書眾多”的“文書”。“悉指授要道”,傳授的當然是道教的道法;“故道為有德君出,不敢作文”,這里的“文”也是指道教文書。這一整段對話中的“文”“書”,指的都是道教文書,令“賢儒俱迷”的當然也不例外。又例如“他書非正道文”一段,上文有“其中大賢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別為索殊方異方,還付其帝王,故當賜以道書文”一句,下文有“然同可拘上古圣經善者,中古圣經善者,下古圣經善者,以為文以賜之”[2]230一句。“道書文”“圣經”,指的都是道教文書,“使賢儒迷迷”的,當然也是道教文書。再例如劉湘蘭先生引用“是故夫下愚之師,教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秘道真德敕教之,反以浮華偽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賢得邪偽巧文習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賢得習偽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其謹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無義理,欺其父母,巧其鄰里,或成盜賊不可止。賢不肖吏民共為奸偽,俱不能相禁絕。睹邪不正,乃上亂天文,下亂地理,賊五行所成,逆四時所養,共欺其上,國家昏亂,其為害甚甚,不可勝記”[2]431一段,出自《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中心意思是“天師都開太平學之路,悉敕使人為道德要文,不得蔽匿”。“道德要文”,當然是道教文書;“下愚之師”,指的也是傳道的道教徒,所以才會“不以要秘道真德敕教之”。“浮華偽文”與“要秘道真德敕”并舉,已經說明了這里的“浮華偽文”不會是儒家經典;上文又有“今旦可言,因使真道道絕也,邪道起,故不可理也”一句,下文又有“真人反言小人不宜聞要道要德,反當以邪巧偽之事教化,使天下人眩瞑,共習偽非,而不自知,遂俱為無道耶”[2]431一句,“真道”“邪道”“要道”“無道”,都是道教的“道”。綜合起來判斷,《太平經》對于“邪偽文”“浮華文”的批評,無疑指的是道教文書,絕不可能是“儒家文風”。
劉曉先生《〈太平經〉的詞匯研究》一文指出,《太平經》的“作者都是下層讀書人,與廣大社會聯系緊密,著述的目的還在于‘傳經’”[9]。《太平經》之所以這樣下氣力批評“邪偽文”“浮華文”,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傳教,向各位“賢儒”推銷“吾書”“吾文”,也就是自己教派的著作;而不是像劉湘蘭先生分析的那樣,是“對當時社會陋習的反思,也遙承了莊子對儒家思想的鄙薄態度”。《太平經》中共出現“吾書”“吾書文”“吾書言”“吾書辭”“吾文”“吾文言”“吾文書”等198次,都是在自夸“吾書”“吾文”的神奇。例如卷四十六《道無價卻夷狄法》:“子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纮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絕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復相傷,同心為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多少,子亦知之耶?”“吾書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復戒之。”“吾書乃三光之神吏常隨而照視之〈止〉也。”“吾書即天心也意也,子復深精念之。”[2]128、129極力夸贊“吾書”,目的無非是傳教。對“吾書”“吾文”的夸贊,是和對“邪偽文”“浮華文”的批評結合在一起的。例如太平經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吾書敬受于天法,不但空陳偽言也。”[2]152卷四十九《急學真法第六十六》:“以吾書不信也,使凡人見吾書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來,有善道者皆相教閉藏,不肯傳與其弟子,反以浮華偽文教之;為是積久,故天道今獨以大亂矣。”[2]162卷五十《葬宅訣第七十六》:“可知吾書,猶天之有甲,地之有乙,萬世不可易也。本根重事效,生人處也,不可茍易,而已成事,□□邪文為害也,令使災變數起,眾賢人民苦之甚甚。”[2]183卷九十七《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故吾書本道德之根,棄除邪文巧偽之法,悉不與焉。”[2]431在批評“邪偽文”“浮華文”的同時,強調了“吾書”“吾文”的神妙,這也是教徒傳教慣用的手法。
三、《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內涵及時間范圍
《太平經》是現存最早的道教著作,而史籍記載的最早的道教文書,是齊人甘忠可編撰的《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時間是在西漢成帝時期(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現在一般認為,《太平經》就是在《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在這以前,還有哪些早期道教文書,現在已無法確知。由于“植根于中國封建社會土壤之中的道教,從其產生的思想淵源來看,其特點是‘雜而多端’,包括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墨家思想、神仙思想、神仙方術、古代宗教思想和巫術等許多學派的內容”[10],早期道教文書必然與各家著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據《太平經卷之四十一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唯唯。今小之道書,以為天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辭以為圣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辭以為德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賢明之辭以為賢經也。今念天師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愿天師闓示其門戶所當先后,令使德君得之以為嚴教也,敕眾賢令使各得生校善意于其中也。’……‘然,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書者,假令眾賢共讀視古今諸道文也。如卷得一善字,如得一善訣事,便記書出之。一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萬卷得萬善,億卷得億善,善字善訣事,卷得十善也,此十億善字;如卷得百善也,此百億善字矣。書而記之,聚于一間處,眾賢共視古今文章,竟都錄出之,以類聚之,各從其家,去中復重,因次其要文字而編之,即已究竟,深知古今天地人萬物之精意矣。因以為文,成天經矣。子知之乎?’”[2]83、84根據這段話,包括《太平經》在內的早期道教文書,是從“古今諸道文”“古今文章”中摘錄加工而成。這樣,《太平經》文論的批評對象,其實就包含了上述各家的著述,而不是針對某一家而言。源自于先秦的儒家、道家等思想,進入漢代以來,均由漢人對其進行了改造,與漢代盛行的陰陽五行、神仙方術等結合形成了儒家神學、黃老道學。由于《太平清領書》等早期道教文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11],與陰陽五行、神仙方術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早期道教文書所涉及的各家著述,又應以漢人用陰陽五行、神仙方術等改造過的學說為主。這是《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內涵范圍。
《太平經》里反復出現“上古”“中古”“下古”的時間概念,“邪偽文”“浮華文”是從“中古”開始出現的。想要確定《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時間范圍,就要確定《太平經》里“中古”的界限。“上古”“中古”“下古”的時間概念,在許多古書里都出現過,而含義各不相同,例如《漢書·藝文志》“世歷三古”顏師古注引三國魏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12]1705這里的“中古”指的是商周時期;《韓非子·五蠧》:“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13]這里指虞夏時期。從文義來判斷,《太平經》里的“中古”,指的是春秋戰國時期。例如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七《天咎四人辱道誡》說:“三王紊亂,五霸將起,君臣民更相欺慢,故偽作癡狂。……欲修中古霸道法,真道不得來。”[2]665、666“五霸”,據《白虎通義》的解釋,是指“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其中的齊桓公、晉文公,可以確知是春秋時期的人物,所以所謂的“中古霸道法”,其中的“中古”就可以確定為春秋戰國時期。又例如太平經卷之三十六《事死不得過生法》:“中古理漸失法度,流就浮華,竭資財為送終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為祟,不可止。”[2]52、53其中寫到“中古”喪葬日漸奢華,也與《墨子·節葬》中所寫的情形相符合,而墨子則是春秋末年戰國初期的人物。這樣,《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時間上限,可以確定為春秋戰國時期。
但是,如果僅僅將《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時間范圍確定為春秋戰國以來,那么《太平經》文論批評其實和漢代一般的認知沒有什么不同。《漢書·藝文志》開篇寫道:“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12]1701所謂“真偽分爭”“紛然殽亂”,也就是《太平經》中所說的“邪偽”“浮華”的情況;“仲尼沒”“戰國從衡”,也指明了時間上限為春秋戰國。由于《太平經》記載了早期道教文書的成文方式,例如前文所引《太平經卷之四十一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中“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辭以為圣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辭以為德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賢明之辭以為賢經也”,以及“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書者,假令眾賢共讀視古今諸道文也。如卷得一善字,如得一善訣事,便記書出之”的寫作方法,如果能夠把《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時間范圍再劃定精確一些,就會對研究某一時期具體作品的形成過程提供線索。考慮到早期道教主要在民間生成并傳播,《太平經》作者的學識修養總體未必很高,其接觸到的書籍應以當時在民間廣為流傳的道教文書為主。此外,《太平經》文論批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排斥其他的道教文書,弘揚自己的教法,從這個角度考慮,《太平經》文論批評的對象也應以當時流行的道教文書為主。這樣,就可以將《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時間范圍縮小至西漢成帝至東漢順帝(126—144年)大約170年左右的時段,《太平經》文論批評直接反映了這一段時間里的文風。再考慮到早期道教文書有一個積累演變的過程,這個時間上限還可以提前一些。如上文所述,早期道教文書與陰陽五行、神仙方術等有著密切的關系,它的形成不應早于陰陽五行、神仙方術在漢代開始興起的時期。神仙方術興起的時間要早一些,漢初以黃老之學治國,其中即包含大量的神仙方術。陰陽五行在漢代的興起則要晚一些,一般認為是在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董仲舒以陰陽五行之說解釋儒家經典,形成了儒家神學體系,陰陽五行之說才開始風靡朝野。據此,可以將早期道教文書形成的時間上限提前至漢武帝時期,而《太平經》文論批評對象的時間范圍也就擴大為西漢武帝至東漢順帝大約300年的時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