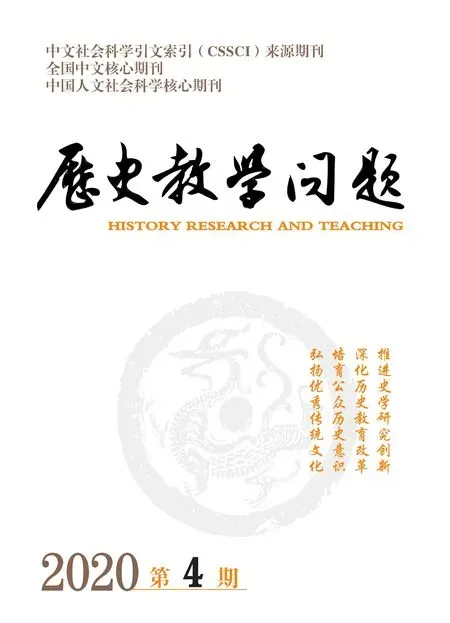以歷史學(xué)為方法:再論內(nèi)藤湖南的東洋史研究
黃 艷 陳 陽
內(nèi)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著名學(xué)者、中國史研究專家,也是日本明治后期、大正時(shí)期、昭和前期在公共輿論界有影響力的人物。二戰(zhàn)后,在日本和中國分別進(jìn)行的對(duì)戰(zhàn)爭思想的批判之中,內(nèi)藤湖南的部分作品和思想曾被指出具有為日本侵華服務(wù)之性質(zhì)。①日本方面以野原四郎、增淵龍夫的批評(píng)尤為知名:野原四郎「內(nèi)藤湖南『支那論』批判」,『アジアの歴史と思想』所収,弘文堂,1966 年(初刊于『中國評(píng)論』第1 卷第4 號(hào),1946 年11 月);增淵龍夫「歷史意識(shí)と國際感覺——日本の近代史學(xué)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Ⅰ)、「日本の近代史學(xué)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Ⅱ),『歴史家の同時(shí)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所収,巖波書店,1983年(初刊于『思想』464 號(hào)、1963 年2 月,『思想』468 號(hào)、1963 年6 月)。此外,增井經(jīng)夫「內(nèi)藤湖南と山路愛山」,『近代日本と中國』所収,朝日新聞社,1974 年;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xué)』,青木書店,1976 年,等論(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內(nèi)藤的學(xué)術(shù)研究有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wù)的性質(zhì)。中國方面在20 世紀(jì)60 年代,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出版《外國資產(chǎn)階級(jí)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dòng)學(xué)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 卷),收錄了內(nèi)藤的《支那論》《新支那論》中的部分內(nèi)容(商務(wù)印書館,1961 年、1962 年)。近年的批評(píng)性研究可參看龔詠梅《試論近現(xiàn)代日本中國學(xué)與日本侵華政策的關(guān)系》,《湖南社會(huì)科學(xué)》2001 年第1 期;王向遠(yuǎn)《近代日本“東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華圖謀——以內(nèi)藤湖南的〈支那論〉〈新支那論〉為中心》,《華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6 年第4 期;李少軍《武昌起義后內(nèi)藤湖南、桑原騭藏之涉華議論評(píng)析》,《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 年第3期;曹星《略論內(nèi)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史學(xué)理論與史學(xué)史學(xué)刊》2010 年上卷;楊鵬《中國史學(xué)界對(duì)日本近代中國學(xué)的迎拒》,華中師范大學(xué)2011 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楊棟梁《在學(xué)識(shí)與良知之間——國策學(xué)者內(nèi)藤湖南的“支那論”》,《史學(xué)月刊》2014年第7 期等,錢婉約《內(nèi)藤湖南研究》(中華書局,2004 年)中亦指出內(nèi)藤的中國時(shí)事論富有帝國主義色彩。但自20 世紀(jì)90 年代以來,在日、中史學(xué)界,對(duì)內(nèi)藤湖南的正面評(píng)價(jià)開始增多,這些評(píng)價(jià)多數(shù)聚焦于內(nèi)藤湖南的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②在對(duì)內(nèi)藤的肯定性評(píng)價(jià)中,多認(rèn)同內(nèi)藤的中國研究是真正遵循中國歷史與社會(huì)的內(nèi)在邏輯來認(rèn)識(shí)中國歷史,在研究方法上體現(xiàn)了對(duì)中國的“內(nèi)在理解”,對(duì)內(nèi)藤的文化史觀持肯定態(tài)度。其中日本學(xué)界1996 年以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為中心成立的“內(nèi)藤湖南研究會(huì)”很有代表性,該研究會(huì)體現(xiàn)出對(duì)日本戰(zhàn)后內(nèi)藤湖南評(píng)價(jià)的“反批判”傾向,其研究成果有論文集『內(nèi)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 年,中譯本見內(nèi)藤湖南研究會(huì)編著《內(nèi)藤湖南的世界》,馬彪、胡寶華等譯,三秦出版社,2005 年)和『內(nèi)藤湖南研究——學(xué)問·思想·人生』(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8 年),該會(huì)成員近年亦有相關(guān)研究陸續(xù)發(fā)表,如高木智見『內(nèi)藤湖南:近代人文學(xué)の原點(diǎn)』(筑摩書房,2016 年),山田伸吾在近年也發(fā)表了多篇論文。此外,山田智,黒川みどり共同主編的論文集『內(nèi)藤湖南とアジア認(rèn)識(shí)——日本近代思想史からみる』值得關(guān)注,該書反對(duì)將內(nèi)藤置于“漢學(xué)家”或“支那學(xué)家”身份并脫離其所在時(shí)代的評(píng)價(jià),其編者在序章指出,“對(duì)于他的中國觀和文明觀,只有在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脈絡(luò)中經(jīng)過研究性的討論,才能夠正確地做出評(píng)價(jià)”(山田智「序章にかえて」,山田智、黒川みどり共編『內(nèi)藤湖南とアジア認(rèn)識(shí)——日本近代思想史からみる』,勉誠出版社,2013 年,第iii 頁)。中國方面約在21 世紀(jì)前后,對(duì)內(nèi)藤的積極評(píng)價(jià)增多,多數(shù)集中于其“唐宋變革論”方面。2013 年9 月,南開大學(xué)召開了與日本關(guān)西大學(xué)聯(lián)合主辦的“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認(rèn)知——內(nèi)藤湖南與中國”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錢婉約教授在會(huì)議的總結(jié)報(bào)告中說:“大凡側(cè)重研究內(nèi)藤學(xué)術(shù)思想的,往往多肯定、嘆服、贊譽(yù)內(nèi)藤的創(chuàng)新性和獨(dú)到見解;側(cè)重研究內(nèi)藤社會(huì)政治學(xué)說的,往往多批評(píng)、指責(zé)他的擴(kuò)張殖民心態(tài)。”這兩種矛盾的價(jià)值判斷“是內(nèi)藤湖南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一個(gè)特征”,基本可視為國內(nèi)大陸學(xué)界對(duì)內(nèi)藤評(píng)價(jià)的簡要概括。見錢婉約《內(nèi)藤湖南的當(dāng)代意義——“內(nèi)藤湖南與中國”國際學(xué)術(shù)會(huì)議綜述》,收入閻純德主編《漢學(xué)研究》第17 集,學(xué)苑出版社,2014 年。美國學(xué)者傅佛果以“實(shí)學(xué)”溝通了內(nèi)藤湖南的政治關(guān)懷與學(xué)術(shù)研究,指出看似可分割開的兩個(gè)領(lǐng)域在內(nèi)藤身上有著內(nèi)在統(tǒng)一性。①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1980.同名著作在美、日、中出版,中譯本見傅佛果著《內(nèi)藤湖南:政治與漢學(xué)(1866—1934)》,陶德民、何英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實(shí)學(xué)”即學(xué)術(shù)要服務(wù)于現(xiàn)實(shí),該書從理解式的立場來解讀內(nèi)藤,基本認(rèn)同其學(xué)術(shù)及其諸多論說的真誠性,并以“思想中的矛盾”和“不成熟”來解釋內(nèi)藤作品中顯見的沖突。這種研究路徑得到相關(guān)研究者的肯定,但亦如學(xué)者所指出“在提供了對(duì)內(nèi)藤湖南命運(yùn)的新洞察的同時(shí),也顯示了巨大的曖昧性”。②高波:《內(nèi)藤湖南的“整體性”》,《讀書》,2017 年第8 期。而觀察內(nèi)藤諸論說,可見其內(nèi)在理路和整體結(jié)構(gòu)始終是明晰的。其取徑于歷史學(xué),采用文化史敘事方式,建構(gòu)東洋文化的一體性并以文化空間替代地理空間,擇取中日史事在不同層面展開論證,在學(xué)理層面完成了以近代日本為中心的“東洋”政治一體性的合法性論證。其頗具學(xué)術(shù)面貌的“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和更為著名的“宋代近世說”亦以其“東洋文化”大勢論為基礎(chǔ),構(gòu)成為其論證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
一、內(nèi)藤湖南東洋文化史觀的構(gòu)建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在追求擺脫西方政治軍事壓力的同時(shí),也逐步醞釀出面向東亞的戰(zhàn)略構(gòu)想;與此同時(shí),日本對(duì)自身和世界的認(rèn)識(shí)都發(fā)生變化。③近年關(guān)于日本近代亞洲觀念的研究指出,在明治維新以后出現(xiàn)的各種面向東亞的思潮中,存在著不同形式的主張“中日提攜”“興亞”“與西方列強(qiáng)爭衡”、強(qiáng)調(diào)亞洲區(qū)域文化自我的各類型“亞洲主義”思想。這類思想的根源復(fù)雜,既根基于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歷史文化牽連,受動(dòng)于日本自被迫開國以來面臨著的西方政治軍事壓力乃至殖民危險(xiǎn),也激發(fā)于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興起面向東亞的戰(zhàn)略構(gòu)想。此方面研究較多,也存在分歧,東北師范大學(xué)趙軼峰先生《現(xiàn)代日本歷史編撰學(xué)的幾種伴生觀念》(《安徽史學(xué)》2018 年第2 期)率先在學(xué)者歷史觀層面對(duì)影響現(xiàn)代日本歷史編撰學(xué)的“亞洲”“東洋”等幾種觀念進(jìn)行了分析與歸納。到19 世紀(jì)末期,日本學(xué)術(shù)界出現(xiàn)了“東洋學(xué)”及“東洋史”研究熱潮,④一般認(rèn)為,日本“東洋史”創(chuàng)始于那珂通世。1894 年,那珂通世在一次由日本高等師范學(xué)校長召集各大學(xué)教授、高等中學(xué)教授等討論中等學(xué)校各學(xué)科問題的會(huì)議上,倡導(dǎo)開設(shè)與西洋史相對(duì)的東洋史,其內(nèi)容以中國史為中心,兼顧東洋各民族的歷史,該建議獲得與會(huì)學(xué)者普遍贊同,之后又獲得日本文部省通過。見三宅米吉述《日本文學(xué)博士那珂通世傳》,黃子獻(xiàn)譯,《師大史學(xué)叢刊》1937 年第1 卷第1 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史亦被包含于“東洋史”內(nèi),并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中國認(rèn)識(shí)傾向,一是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等持中國文化價(jià)值否定論、中國文化停滯論,并主張日本與中國區(qū)別化的傾向,⑤江上波夫編,田中正美撰:《東洋學(xué)的系譜·那珂通世篇》,童嶺譯,《古典文學(xué)知識(shí)》2010 年第6 期。一是以內(nèi)藤湖南為代表的主張日中文化同源、肯定中國文化價(jià)值、反對(duì)中國文化停滯論的傾向,其論說基礎(chǔ)是東洋文化史觀的構(gòu)建。
東洋文化史觀是一種在“東洋”的地理范圍內(nèi)以文化為中心的歷史認(rèn)識(shí)視野,它的突出特點(diǎn)是相對(duì)于民族國家的超越性。這種歷史認(rèn)識(shí)視野的建構(gòu)首先始于將文化設(shè)置為歷史發(fā)展的中心和目的。內(nèi)藤在多篇文章中都不同程度表達(dá)過這種觀點(diǎn),在《論民族文化與文明》中,他反復(fù)提出這一問題:“國民,或者民族,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目的是僅僅在于聚斂財(cái)富呢,抑或在于創(chuàng)造能使全世界人類向上發(fā)展的文化?”他回答說:“國民也好民族也好,今后最需要考慮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使文化發(fā)達(dá)起來。……文化的價(jià)值在于超越國家而存在,……文化的發(fā)達(dá)不像聚斂財(cái)富,不是一兩百年的努力就能達(dá)成的。……(文化)往往即使在國家滅亡之后,也不至于消亡。”⑥內(nèi)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林曉光譯,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6 年,第132、134、133 頁。原文載于大正十五年(1926)一月三日至八日『大阪每日新聞』。“國家原初的目的乃是在于文化”,⑦內(nèi)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第168 頁,原文載于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大阪每日新聞』。即國家是具有歷史性的,是有限的,而文化一旦被創(chuàng)造出來卻是真正具有恒久性價(jià)值的。
以文化為其歷史觀的中心,內(nèi)藤建構(gòu)起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nèi)的“東洋文化”的整體性。內(nèi)藤強(qiáng)調(diào)日中文化同源,極力反駁日本國內(nèi)將中國和日本差異化并強(qiáng)調(diào)日本文化是獨(dú)自形成的觀點(diǎn)。早在1891 年內(nèi)藤為三宅雪嶺代筆寫作的《真善美日本人》中他就已經(jīng)表明:日本與中國在人種上同屬于蒙古人種,在文化上亦同屬發(fā)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國文明體系中的一員,與現(xiàn)實(shí)中國共同分享著具有豐富歷史和優(yōu)秀人物的中華文明。在后來關(guān)于日本文化的講座中他一直不遺余力地強(qiáng)調(diào)日本文化是依賴中國文化而形成,從而將日本與中國都置于同一個(gè)體系內(nèi):
文化最早在黃河沿岸一帶萌芽,然后向西或向南發(fā)展,再漸漸轉(zhuǎn)向東北方面,最終達(dá)到日本。這種文化逐漸向四面擴(kuò)散,影響了各地方的民族,在這種影響下,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產(chǎn)生了新的文化,這種影響最后波及到日本,日本也就形成了今日的文化。
所謂日本文化,其是東亞文化、中國文化的延長,是同中國古代文化一脈相承的。……認(rèn)為東亞史是日本史以外之物的觀點(diǎn)是完全錯(cuò)誤的,東亞文化與日本文化同樣是交織在一起的。①內(nèi)藤湖南:《何謂日本文化(二)》,載內(nèi)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劉克申譯,商務(wù)印書館,2012 年,第10—11 頁,第12 頁,原文為1921 年的講演。
內(nèi)藤對(duì)日中文化一體性的敘述是其東洋文化史觀的重要內(nèi)容。這樣,經(jīng)由文化為中心的視角建構(gòu)起具有超越性視野的“東洋文化”,同時(shí)便消解了現(xiàn)實(shí)中的民族國家疆界,并以文化空間代替了地理空間。在內(nèi)藤的諸多相關(guān)論說中可看到兩者間的相關(guān)性,1921 年內(nèi)藤針對(duì)梁啟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yè)之成敗及今后革進(jìn)之機(jī)運(yùn)》一文發(fā)表評(píng)論文章《作為中國人觀的中國將來觀及其批評(píng)》,一方面肯定梁氏看到了中國國民的“世界主義”特征,一方面批評(píng)其將視界限于中國范圍過于狹隘,他指出“開闊的視野”是包含日本:
如梁氏所述,中國國民最初僅居于黃河沿岸之一部分,漸次向東南擴(kuò)張,將苗族、羌族、匈奴、東胡都包括于其中。然而這一包括是否到此為止?——例如說,是否延伸及于朝鮮或日本?則并未言及。
在當(dāng)今時(shí)代,梁氏單單考慮到中國國民的形成,已經(jīng)是不正確的了。從中國國民性的超越國界特性,以及從中國國民的發(fā)展歷史來看,理所當(dāng)然,都應(yīng)該將日本納入其領(lǐng)域之內(nèi),從極為開闊的視野進(jìn)行觀察。②內(nèi)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第153、155 頁。原文載于大正十年(1921)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
在1924 年出版的《新支那論》中,他說:
中國也好,日本也好,朝鮮也好,安南也好,有著各自的國民,這在考慮各個(gè)國家的問題時(shí)是相當(dāng)重要的。然而,從東方文化的發(fā)展這個(gè)整體上來考慮時(shí),這些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問題。東方文化的發(fā)展并沒有顧及其國民的異同,而是按照一定的經(jīng)路發(fā)展起來的。③內(nèi)藤虎次郎「新支那論」,『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5 巻,筑摩書房,1972 年,第508 頁。
在以“東洋文化”消解民族國家的同時(shí),中國文化也被與其承載主體剝離,并被作為“東洋文化”的中心而備受肯定。內(nèi)藤指出“東亞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以中國為中心”。內(nèi)藤自身從不諱言對(duì)中國文化的熱愛與贊美,面對(duì)當(dāng)時(shí)日本思想界以西歐為標(biāo)準(zhǔn)、蔑視中國的傾向,內(nèi)藤極為肯定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路徑,他說:
通觀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總體,宛如一棵樹,由根生干,而及于葉一樣,確實(shí)形成為一種文化的自然發(fā)展的系統(tǒng),有如構(gòu)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歐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國歷史為標(biāo)準(zhǔn),所以把中國史的發(fā)展視為不正確,但這卻是謬誤的。在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中,文化確是真正順理成章、最自然地發(fā)展起來的。④內(nèi)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nèi)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夏應(yīng)元選編并監(jiān)譯,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4年,第6頁。
在與西方文明的比較中,內(nèi)藤不斷為中國辯護(hù),提出中國文明相對(duì)于西方文明更加具有優(yōu)越性:
如果變化遞移就是西方人所謂進(jìn)步的話,中國未嘗沒有進(jìn)步……(西方近代文明)是形而下的文明達(dá)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它的弊端也存在其中。……中國的文化雖然平實(shí)穩(wěn)健,難以使人動(dòng)好奇之念,入門或許太慢,但是一旦入了門,連它的殘羹冷飯,也足以醫(yī)治他們被甘美傷害的口腹。⑤內(nèi)藤湖南:《所謂日本的天職》,內(nèi)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wèi)峰譯,中華書局,2007 年,第181、182 頁。
因內(nèi)藤的此類論說,日本和中國都有學(xué)者樂于談?wù)搩?nèi)藤對(duì)中國文化獨(dú)有價(jià)值的揭示。但須注意的是,在內(nèi)藤的此類話語中,飽享贊譽(yù)的只是中國文化而非現(xiàn)實(shí)中國;因“東洋文化”的建構(gòu),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都不獨(dú)屬于中國,而歸屬于、也代表著包含日本在內(nèi)的整個(gè)“東洋”。
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與內(nèi)藤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超越性并構(gòu)建東洋文化史觀的同時(shí),其民族國家觀念并未真正從其歷史觀中消失。其論日中文化淵源時(shí)雖否定日本文化的獨(dú)立性,但這并不妨礙其對(duì)日本民族主體性的強(qiáng)調(diào)。⑥傅佛果分析青少年時(shí)期的內(nèi)藤湖南時(shí)指出其具有“日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見傅佛果:《內(nèi)藤湖南:政治與漢學(xué)(1866—1934)》,第61—73 頁。錢婉約亦分析指出內(nèi)藤思想中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見錢婉約:《內(nèi)藤湖南研究》,中華書局,2004 年,第28—35 頁。如1888 年內(nèi)藤刊文肯定當(dāng)時(shí)的國粹主義刊物《日本人》及《東京電報(bào)》時(shí)說:“日本非德國、非英國,日本就是日本。日本有與日本國相當(dāng)?shù)恼w、與日本國相當(dāng)?shù)漠a(chǎn)業(yè),日本人有與日本人相當(dāng)?shù)慕逃c日本人相當(dāng)?shù)淖诮獭⒚佬g(shù)、工藝。”①內(nèi)藤虎次郎「新雜誌及び新聞」,『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1 巻,第440—441 頁。原文載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 年)四月十五日『萬報(bào)一覽』第173 號(hào)。1894 年論日本的“天職”時(shí)說“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風(fēng)尚風(fēng)靡天下、光被坤輿”,鮮明地表達(dá)了其日本民族主體意識(shí)。在涉及日本的對(duì)外關(guān)系時(shí),內(nèi)藤維護(hù)日本國權(quán)的立場也非常明顯,如1895 年“三國干涉還遼”發(fā)生后,內(nèi)藤連續(xù)發(fā)表《受動(dòng)的外交》《伊藤侯不宜出使之任》《讀宋史》等文,措辭嚴(yán)厲地指責(zé)日本政府對(duì)俄外交的軟弱,并以中國歷史上澶淵之盟為喻諷刺日本政府放棄遼東半島。在1902 年10 月到1903 年1 月,內(nèi)藤赴中國東北考察俄國在此地區(qū)的經(jīng)營并留下豐富筆記,回國后發(fā)表《滿洲撤兵》《歡迎滿洲問題》《滿洲的價(jià)值》《滿洲論的分派》等文,宣傳對(duì)俄主戰(zhàn)、維護(hù)日本國家利益。1904 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后,內(nèi)藤亦發(fā)表一系列有關(guān)日俄戰(zhàn)局的言論表達(dá)同樣的立場。日本學(xué)者田澤晴子曾根據(jù)內(nèi)藤《關(guān)于承認(rèn)中華民國》等文明確指出:“一旦涉及到是否應(yīng)該承認(rèn)中華民國等兩國之間的現(xiàn)實(shí)問題時(shí),內(nèi)藤湖南便會(huì)以維護(hù)日本國的利益為基準(zhǔn)進(jìn)行判斷。”②田澤晴子「內(nèi)藤湖南におけれ二つの近代と政治」,山田智,黒川みどり共編『內(nèi)藤湖南とアジア認(rèn)識(shí)——日本近代思想史からみる』,勉誠出版社,2013 年,第71 頁。因此,內(nèi)藤“東洋文化史觀”的超越性立場主要體現(xiàn)為面向中國的立場,面向日本的現(xiàn)實(shí)利益時(shí)內(nèi)藤始終保有明確的民族國家觀念。這兩種互相區(qū)別的視角是面對(duì)內(nèi)藤“東洋文化”諸說時(shí)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
二、日本“天職”說與其歷史依據(jù)
內(nèi)藤在構(gòu)建東洋文化史觀的同時(shí),也在其時(shí)事評(píng)論中初步提出了日本的“天職”說。1890 年底,內(nèi)藤發(fā)表《亞細(xì)亞大陸的探險(xiǎn)》一文,提出“亞洲事由亞洲人處理,歐洲事由歐洲人處理,這是所謂各盡天職”。并指出亞洲人都在困倦醉臥之中,“唯獨(dú)日本才有一種覺醒之感,日本的天職愈來愈重,愈來愈大”。主張日本人要在歐洲人尚未行動(dòng)之前去亞洲大陸探險(xiǎn)。③內(nèi)藤虎次郎「亞細(xì)亞大陸探撿」,『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1 巻,第535—538 頁。原文載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人』第63 號(hào)。“去亞洲大陸探險(xiǎn)”在此文中主要指學(xué)術(shù)上日本要先于歐洲展開有關(guān)亞洲的研究,在內(nèi)藤后來的文章中被不斷重提,內(nèi)藤本人亦身體力行,以此作為他身為日本學(xué)者的使命。該文一方面采用亞洲門羅主義式的宣告主張亞洲相對(duì)于歐洲的獨(dú)立性,一方面明確提出了日本有面向亞洲的“天職”。1894 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內(nèi)藤于當(dāng)年8 月日本在牙山海戰(zhàn)獲勝后不久發(fā)文《所謂日本的“天職”》,他指出,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這次嚴(yán)重對(duì)抗,是日本接受天命、發(fā)揮其天職的機(jī)會(huì),至于這一“天職”的實(shí)現(xiàn),則要以“中國為主要對(duì)象”:
日本的天職,就是日本的天職,……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風(fēng)尚風(fēng)靡天下、光被坤輿的天職。我們因?yàn)閲跂|亞,又因?yàn)闁|亞各國以中國為最大,我們天職的履行必須以中國為主要對(duì)象。④內(nèi)藤湖南:《所謂日本的“天職”》,內(nèi)藤湖南:《燕山楚水》,第172—183 頁。
去亞洲大陸探險(xiǎn)、發(fā)揮日本在東亞的“天職”,此類主張都有政治意味,但內(nèi)藤并非單純的政論家。1894 年11 月,內(nèi)藤又接連發(fā)表了《地勢臆說》和《日本的天職與學(xué)者》兩文,采用歷史分析的視角,擇取相關(guān)史事,勾勒出日本和中國歷史文化發(fā)展變遷的“大勢”,提出“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并將之確定為適用于“東洋”的一般性原理,從而形成對(duì)日本的“天職”說的支撐性論說。在《地勢臆說》中,他首先指出:“地勢和人文相關(guān),或以地勢為因,人文為果,或以人文為因,地勢為果。小到都邑盛衰之因、大到邦國興廢之致,民物的豐歉、文化的隆污,其徵往而推來,比龜卜數(shù)計(jì)更為顯著。”提出這一看法之后,他首先驗(yàn)之以日本歷史,簡要分析了神武天皇時(shí)期至明治維新時(shí)期政權(quán)依次從九州向近畿、大阪、關(guān)東的遷移,證明地勢與人文之間的關(guān)系。之后指出“可以此理來觀察坤輿大勢的遷移”。該文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以“此理”來觀察中國的“大勢遷移”。他先后援引趙翼《長安地氣說》、顧祖禹《燕京論》、計(jì)東《籌南論》、章簧《南北強(qiáng)弱論》等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者相關(guān)論說并在此基礎(chǔ)上加以改造,勾勒出中國歷史上地勢和人文變遷的路徑,即:中國文明最早發(fā)源于冀、豫二州,以洛陽為中心,到了戰(zhàn)國末期,洛陽的地氣和人力都已經(jīng)衰竭;于是從西漢到唐末,長安繼起成為新的中心,隨著長安的衰落,自宋代之后,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發(fā)生分離,出現(xiàn)了政治中心在燕京,文化中心則移動(dòng)到江南的情況,同時(shí)廣東地區(qū)也逐漸被包納進(jìn)中國文化圈之中,進(jìn)而成為新的文化中心所在地。由此,內(nèi)藤通過對(duì)日本和中國歷史變遷特征的描繪,將“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敘述為“坤輿大勢”。該文最后,內(nèi)藤說道:“嗚呼,支那的存亡,確實(shí)是坤輿之一大問題,考慮其分合之形勢,地力人文中心之處所,徵其往而推其來,以今日情況概論之,考今后文明大勢轉(zhuǎn)移之方向,必非無趣味之事,愿就此與同好之士更加詳論。”①內(nèi)藤虎次郎「地勢臆說」,『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1 巻,第117—125 頁。本段引文分別見第117、118、125 頁。原文發(fā)表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 年)十月一日、二日『大阪朝日新聞』。
在《地勢臆說》發(fā)表的八天后見諸報(bào)端的《日本的天職與學(xué)者》中,內(nèi)藤開篇便說到“日本將是大有受命之所,識(shí)者須久審此事”。該文再次討論了“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并明確指出:“文明之中心,今又將有大移動(dòng),識(shí)者實(shí)早已了解其間要領(lǐng),此乃日本將承擔(dān)大命之際也。”為承擔(dān)此“大命”,內(nèi)藤也提出了具體的方法,即日本學(xué)者向亞洲大陸探險(xiǎn)、收集學(xué)術(shù)資料,由此創(chuàng)造出東洋學(xué)術(shù)上的新局面。這樣,由日本來“成就東方之新極致,以取代歐洲而興起,新的坤輿文明之中心,豈不在反掌間耳?”②內(nèi)藤虎次郎「日本の天職と學(xué)者」,『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1 巻,第126—133 頁。本段引文分別見第126、130、132 頁。原文發(fā)表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 年)十月九日、十日『大阪朝日新聞』。至此,采取歷史學(xué)方法建構(gòu)的“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與日本“天職”說形成為一個(gè)體系。
可見,內(nèi)藤“東洋文化”論說的真正結(jié)構(gòu)是:通過確立文化為歷史發(fā)展的中心,消解了現(xiàn)實(shí)中國;通過深描日中文化的歷史牽連,構(gòu)建出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nèi)的具有一體性的文化“東洋”,在“東洋文化”得以建構(gòu)并作為其論說基礎(chǔ)后,對(duì)日本特別是中國歷史發(fā)展路徑的描述成為其“東洋”范圍內(nèi)“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的歷史依據(jù),從而表明日本有成為主導(dǎo)東亞的新興文化中心之歷史正當(dāng)性。隨著20 世紀(jì)日本東亞戰(zhàn)爭的步步推進(jìn),這種論說結(jié)構(gòu)在內(nèi)藤后來的作品中反復(fù)出現(xiàn),并更加明確地與日本和中國的政治“統(tǒng)一”相聯(lián)系。在1921 年反駁梁啟超的文章里,內(nèi)藤指出:“在我看來,中國固有之民族,以其文化漸次包含其他民族,這確如梁氏所言。然而同時(shí)還應(yīng)當(dāng)考慮到的是,其勢力中心、文化中心也在漸次移動(dòng)。”在借用中國歷史論述文化中心和勢力中心的移動(dòng)之后他說:“對(duì)于今天在中國領(lǐng)域之外的日本也好朝鮮也罷,也都應(yīng)當(dāng)與現(xiàn)代中國國民一視同仁,納入中國國民的勢力中心、文化中心的移動(dòng)區(qū)域之內(nèi)。”由此他勸諭中國人對(duì)日本的勢力影響“實(shí)不應(yīng)抱有嫌惡猜忌之心”。并以其一貫的超越性視角勸諭說:“世界大勢漸次向著超國界的方向發(fā)展,而這一方向的第一步,就由中國來踏出。”③內(nèi)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第153、154、155、157 頁。在1924 年的《新支那論》中,他再次不遺余力地復(fù)述中國歷史上文化中心移動(dòng)的過程,之后指出:既然日本已成為新的文化中心,如果通過某種機(jī)會(huì)再實(shí)現(xiàn)了政治統(tǒng)一的話,那么就會(huì)如同中國之前的歷史一樣,中國人會(huì)接受日本的統(tǒng)治:
由于文化中心的移動(dòng)不以國民的區(qū)域而停頓,而是繼續(xù)前進(jìn)的,所以在接受中國文化上絕對(duì)不會(huì)比廣東等地晚的日本,今天若要成為東洋文化的中心,并對(duì)支那文化產(chǎn)生有力的影響,這并無任何不可思議之處。現(xiàn)在的日本已經(jīng)成為超越支那的先進(jìn)國家,盡管對(duì)于日本的興盛,支那人投以猜忌的目光,但倘若通過某種機(jī)緣,使日本與支那形成一個(gè)政治上統(tǒng)一的國家的話,文化中心移入日本,那時(shí)即使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上社會(huì)上很活躍,支那人也不會(huì)把這視為特別不可思議的現(xiàn)象。④內(nèi)藤虎次郎「新支那論」,『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5 巻,第508—509 頁。
在內(nèi)藤構(gòu)建的文化史觀中,不同民族間的戰(zhàn)爭以及日本和中國的政治“統(tǒng)一”都是文化最終獲得發(fā)展的必然過程。他從促進(jìn)文化發(fā)展的目標(biāo)出發(fā),將中國歷史上曾發(fā)生的民族戰(zhàn)爭解釋為促進(jìn)中國文化長久維持的“非常幸福”的事;同時(shí)基于“東洋文化”的超越性視野,將日本對(duì)20 世紀(jì)中國的侵略與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zhàn)爭同質(zhì)化,由此日本的侵華行為就將成為促進(jìn)東洋文化發(fā)展之歷史正當(dāng)性的延續(xù)。他說:
支那論者特別是近來的論者,總以為外來民族侵略是對(duì)支那人民的不幸,其實(shí),支那之所以能維持這么長久的民族歷史,全靠了這屢次襲來的外來民族的侵入。成吉思汗說得好,‘支那人搞不好自己的國家,那就毀了它建成大牧場,為蒙古人的國家所用。’支那民族靠這種外族精神和耶律楚材那樣深謀遠(yuǎn)慮的政治家恢復(fù)活力,是非常幸福的。……必須看到,東洋文化發(fā)展的時(shí)代正在變化,旨在改變支那現(xiàn)狀、或許也是不自覺的日本的經(jīng)濟(jì)運(yùn)動(dòng),對(duì)于延長支那民族將來的生命,實(shí)際上有莫大的效果。支那民族若阻止這一運(yùn)動(dòng),恐將自取衰死。①內(nèi)藤虎次郎「新支那論」,『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5 巻,第513 頁。
內(nèi)藤認(rèn)為,這種文化發(fā)展的正當(dāng)性在過去的歷史里是無法阻擋的,在20 世紀(jì)的現(xiàn)實(shí)里依然無法阻擋。基于此,內(nèi)藤提出,為了實(shí)現(xiàn)這一偉大的天職,即使對(duì)中國采取武力手段也是正當(dāng)?shù)模?/p>
由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對(duì)支那實(shí)行侵略主義或軍國主義之類的議論沒有價(jià)值。討論日本與支那關(guān)系時(shí),單純考慮侵略主義或軍國主義是甚為不當(dāng)?shù)摹?/p>
為了開墾大塊田地,就要開鑿灌溉用的溝渠,而疏通溝渠的中途,時(shí)而會(huì)遇到地下的大巖石,這就需加之以大型斧頭或炸藥。但是不能把爆破和破壞土地當(dāng)成目的,而忘了真正的目的在于田地的開拓。當(dāng)今日本的國論就忘了自己國家的歷史和將來應(yīng)走的道路,把作為一時(shí)應(yīng)急手段而采用的武力說成是侵略主義或軍國主義,這是在自我貶低。②內(nèi)藤虎次郎「新支那論」,『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5 巻,第513—514 頁。
由于在內(nèi)藤的論說中關(guān)于武力入侵中國的主張并不多見,不少論者據(jù)此指出,內(nèi)藤對(duì)中國的主張中并無真正的武力侵略之意。③內(nèi)藤在1894 年《所謂日本的“天職”》中曾批評(píng)武力征服論者的主張,他以歷史學(xué)家的身份歷數(shù)了歷史上落后民族征服開化民族后反被開化民族同化的事情,指出即便日本能夠“控制禹域全境,而怎么能夠在胡服辮發(fā)之后移風(fēng)易俗呢……那些利源論家所言,現(xiàn)在還不能不說是失策”。內(nèi)藤湖南:《所謂日本的“天職”》,載內(nèi)藤湖南:《燕山楚水》,第172—183 頁。但事實(shí)上內(nèi)藤并不反對(duì)武力的使用,只是在其論說中,武力入侵并非最終目標(biāo)也非真正有效方法,內(nèi)藤的思慮更為深遠(yuǎn)。
三、“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與“宋代近世說”
在日本,內(nèi)藤的主要身份(尤其入職京都大學(xué)以后)不是政論家而是東洋歷史學(xué)家,內(nèi)藤也常以這種學(xué)者身份自居,宣稱從“順應(yīng)歷史發(fā)展大勢”“適應(yīng)中國國民性”等出發(fā)點(diǎn)立論。④前語見于《支那論》,該文以“代替中國人為中國人著想”并提供政治建議知名;后語見于《作為支那人觀的支那將來觀及其批評(píng)》,內(nèi)藤面向中國人的勸諭在兩文中都較為明顯。內(nèi)藤也確實(shí)不負(fù)中國史專家之名,其在中國史研究領(lǐng)域興趣廣泛,有龐大的作品體系存世。其頗具學(xué)術(shù)面貌的“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和更為著名的“宋代近世說”因其影響力廣泛可作為分析內(nèi)藤東洋史結(jié)構(gòu)的典型案例。
由于中國文化已被“東洋化”,“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便是內(nèi)藤在“東洋”視野下以中國史為主要對(duì)象提出的宏觀歷史分期說。在《支那上古史·緒言》中,內(nèi)藤曾指出:“余之所謂東洋史,即是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歷史。亞洲大陸的土地,是以蔥嶺、西藏等的高原地帶為中心,向四方擴(kuò)展的形勢。……只是北方,由于寒冷并未擁有完整的歷史,其他三方面都各有其歷史。”即內(nèi)藤所言的“東洋史”,在地理范圍上指的是以蔥嶺、西藏等高原地帶為中心的、其東面的歷史,日本史自然包含于這一“東洋史”的范圍之內(nèi)。這一概念再次表明,中國史是為“東洋”區(qū)域所共有,“代表東洋整體”。正是出于這樣一種立場,內(nèi)藤反對(duì)基于中國自身歷史的朝代劃分,他說“從作為代表東洋整體的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來說,這種劃分是沒有意義的”。他指出真正“有意義的劃分”是從中國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中來觀察整個(gè)東洋的歷史文化發(fā)展波動(dòng)大勢:“如果要作有意義的時(shí)代劃分的話,就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從內(nèi)外兩方面加以考慮。”所謂“內(nèi)”指的是“在上古的某個(gè)時(shí)代,由中國的某個(gè)地方發(fā)生的文化”,所謂“外”,指的是“中國文化向四方擴(kuò)展”,其“四方”的邊界則是整個(gè)東洋。基于這種視角,內(nèi)藤提出了“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即:第一期,從開天辟地到后漢中期,是為上古時(shí)代。內(nèi)藤認(rèn)為這第一期還可以再劃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是中國文化的形成時(shí)代;后期是中國文化向外部發(fā)展,演變成為所謂東洋史的時(shí)代”。第二期,從五胡十六國到唐的中期,是為中世時(shí)代,“這一時(shí)代,可以說是由于外部種族的覺醒,這一時(shí)代的文化力量在反彈作用之下而及于中國內(nèi)部的時(shí)代”。第三期,宋、元時(shí)代,為近世時(shí)代前期;第四期,明、清時(shí)代,為近世時(shí)代后期。由于第三期和第四期可統(tǒng)稱為“近世時(shí)期”,因此可將之概括為“三區(qū)分說”。三個(gè)階段之間包含兩個(gè)過渡期:第一過渡期,從后漢的后半期到西晉,是“中國文化暫時(shí)停止向外發(fā)展的時(shí)代”;第二過渡期,由唐末至五代,“這是來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國達(dá)到頂點(diǎn)的時(shí)代”。⑤內(nèi)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nèi)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引文出自第1—7 頁。國內(nèi)學(xué)者多因內(nèi)藤所論以中國歷史為主,便將內(nèi)藤這一主張稱為“中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實(shí)際上忽略了其“東洋”的建構(gòu),無意間遮蓋了內(nèi)藤的真意。
這種歷史分期標(biāo)準(zhǔn)也見于內(nèi)藤其他中國史作品中,如在《中國中古的文化》內(nèi)藤講到“中古”的時(shí)段劃分時(shí)說:
所謂中古,大體可視為從后漢末期至唐末。在這一時(shí)期,從古代發(fā)展而來的中國文化在達(dá)到成熟后,由于自身文化的毒害,產(chǎn)生出一種分解作用而逐漸瓦解,其徹底瓦解大體是在東晉時(shí)期。此后在中國,又根據(jù)在本國萌生出的文化以及從外國傳入的文化,生成一種新的文化。當(dāng)這一文化逐漸成熟后又再次發(fā)生分解和崩潰。此次過程發(fā)生在南北朝時(shí)期至唐代末年。①內(nèi)藤湖南:《中國中古的文化》,內(nèi)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第233 頁。
該書大部分內(nèi)容講的是自漢代以來的文化如何發(fā)達(dá)乃至發(fā)生了“中毒”,顯而易見,這里的時(shí)代劃分標(biāo)準(zhǔn)和基本編撰思想與《支那上古史·緒言》“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是一致的,即內(nèi)藤以其上述分期說的核心依據(jù)“文化發(fā)展波動(dòng)大勢”為觀察和編撰中國史的基本思路是始終清晰的。
應(yīng)用于歷史分期方面的內(nèi)在理路亦同樣見于前述內(nèi)藤關(guān)于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關(guān)系的論說中。在1921 年《何謂日本文化》的演講中,內(nèi)藤在向日本國民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日中同源和東洋一體的“事實(shí)”后,便借用這種文化發(fā)展波動(dòng)說指出日本文化對(duì)于東洋的價(jià)值:
文化有自中心向終極方向發(fā)展的運(yùn)動(dòng)以及再由終極向中心反向發(fā)展的運(yùn)動(dòng),在其反向發(fā)展的運(yùn)動(dòng)中,有源自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運(yùn)動(dòng)與源自純粹文化的運(yùn)動(dòng)……日本的權(quán)力影響又是如何波及中國的呢?由于同中國相距遙遠(yuǎn),權(quán)力影響的波及也相對(duì)遲緩,但最晚在明朝時(shí)期,眾所周知的倭寇已經(jīng)在中國的沿海一帶騷擾,這應(yīng)該是日本的權(quán)力影響波及中國之始。最近又有日清戰(zhàn)爭以及其他種種事件,現(xiàn)在中國人非常擔(dān)憂,稱日本是軍國主義,這就是因?yàn)槿毡镜膭萘σ绊懙街袊木壒省?/p>
這種文化發(fā)展波動(dòng)說與內(nèi)藤之前的“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的建構(gòu)方法相同,都是在將中國“東洋”化之后,經(jīng)由對(duì)曾為“東洋”中心的中國之歷史發(fā)展特征的描繪而提出的適用于整個(gè)“東洋”文化發(fā)展的一般原理;在效果上互為補(bǔ)充,共同論證日本成為新的東洋中心是大勢所趨:
從單純的文化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不斷移動(dòng)著的。其最早發(fā)源于黃河流域,而現(xiàn)在中國文化的中心應(yīng)該是長江下游地區(qū),……與傳播到各地的文化逐漸向中國的中心逆向發(fā)展一樣,現(xiàn)在日本對(duì)著中國的文化逆向發(fā)展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這正是日本文化在東亞的真正價(jià)值,隨著它的傳播,日本文化的真正價(jià)值也逐漸體現(xiàn)出來。
由此他在該文中勉勵(lì)日本人說:
由此看來,日本文化的起源即使是中國,也不會(huì)因此而毫無價(jià)值。從整體來看,日本文化是東亞文化的發(fā)達(dá)部分,這一部分的發(fā)達(dá)給整個(gè)東亞以很大影響,因?yàn)槿毡疚幕@一體系屬于東亞文化。②內(nèi)藤湖南:《何謂日本文化(二)》,內(nèi)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第11—14 頁。
至此,日本“天職”說的論證體系更加豐富。
內(nèi)藤的“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還包含了內(nèi)藤另一更為著名的關(guān)于中國歷史的分期判斷“宋代近世說”,該說被歐美學(xué)界稱為“內(nèi)藤假說”(Natio Hypothesis),對(duì)二戰(zhàn)以后世界范圍內(nèi)的中國史研究都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該說從八個(gè)具體層面論述了宋以后中國與此前時(shí)代的不同,即:貴族政治衰落和君主獨(dú)裁興起、君主地位的變遷、君主權(quán)力的確立、人民地位的變化、官吏錄用法變化、朋黨性質(zhì)變化、經(jīng)濟(jì)性質(zhì)變化、文化性質(zhì)變化。其中貴族政治衰落和君主獨(dú)裁興起及人民地位的提高是該說核心判斷。③內(nèi)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義》中所列標(biāo)題,載內(nèi)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第324 頁。從表面來看,“宋代近世說”與“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同作為以中國歷史為主要對(duì)象的分期論說,在分期標(biāo)準(zhǔn)上并不具備一致性:“宋代近世說”著重于中國社會(huì)內(nèi)部變化;“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從“東洋”范圍內(nèi)文化發(fā)展內(nèi)外互動(dòng)關(guān)系來把握。④傅佛果著作中曾指出內(nèi)藤關(guān)于“中古”的論說也是以君、臣為中心,即對(duì)“中古”歷史進(jìn)行分析時(shí)采取的視角與“宋代近世說”一致。但實(shí)則不同,內(nèi)藤《中國中古的文化》確實(shí)多以君、臣等人物與事跡為中心展開論說,但并非如“宋代近世說”以君臣地位變化所體現(xiàn)的政治模式變化為歷史觀察視角乃至分期標(biāo)準(zhǔn),其“宋代近世說”中“人民地位提高”這一同樣重要的方面亦未涉及。在內(nèi)藤后來的作品中未曾解釋過這種分期標(biāo)準(zhǔn)的不同,對(duì)此筆者也初為不解,后發(fā)現(xiàn)兩者實(shí)殊途同歸。
從發(fā)表時(shí)間上來看,“宋代近世說”的提出要早于“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論”的形成。根據(jù)最初公開發(fā)表“宋代近世說”的文本《支那論》來看,內(nèi)藤是出于回答辛亥革命后中國當(dāng)走向共和制還是君主制這一現(xiàn)實(shí)問題而上溯中國歷史發(fā)展大勢,從而正式提出“宋代近世說”。①據(jù)《內(nèi)藤湖南全集》編者所著之內(nèi)藤年譜,該說初倡是在1909 年京都大學(xué)課堂授課之中,則內(nèi)藤彼時(shí)已產(chǎn)生宋代為中國近世之始的看法,但從《全集》第10 卷收錄的講課記錄來看,其內(nèi)容與后來發(fā)表的該說有較多差異(內(nèi)藤乾吉「支那近世史·あとがき」,『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10 巻,第527—529 頁)。內(nèi)藤以后的日本學(xué)界及日本以外學(xué)者都以內(nèi)藤在1922 年發(fā)表的《概括的唐宋時(shí)代觀》作為該說的代表性文本,而包含該說兩方面核心判斷即“貴族政治轉(zhuǎn)化為君主獨(dú)裁”和“人民地位的提供高”的文本雛形則是發(fā)表在1914 年的《支那論》(內(nèi)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內(nèi)藤湖南全集』第5 巻,第308—329 頁)中。通過對(duì)宋以來漫長“近世”特征的分析,內(nèi)藤指出:宋以后中國具有在帝制滅亡后實(shí)行共和制的內(nèi)在力量,但是卻因?yàn)殚L期君主專制等弊端而不具備實(shí)現(xiàn)共和制的現(xiàn)實(shí)能力,因此最好的途徑是放棄國家統(tǒng)一、剖割領(lǐng)土、接受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國際托管。②黃艷:《從“宋代近世說”到日本的“天職”——內(nèi)藤湖南中國論的政治目的分析》,《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 年第3 期。因此,“宋代近世說”所論證的辛亥革命后中國歷史發(fā)展趨勢正與支配其“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的文化發(fā)展波動(dòng)大勢說相合:“宋代近世說”表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已經(jīng)進(jìn)入了自宋以來中國社會(huì)自身發(fā)展的矛盾性僵局;“文化發(fā)展波動(dòng)說”意味著,此時(shí)正是日本作為新的文化中心和勢力中心要反作用于中國的時(shí)期。在這一過程中,因“東洋”的建構(gòu),中國作為民族國家是否存在早非內(nèi)藤關(guān)心的問題,重要的是以促進(jìn)“東洋文化”的歷史發(fā)展為名,20 世紀(jì)的日本將作為東洋文化的中心而有所作為——此即日本的“天職”。內(nèi)藤在1922 年發(fā)表《概括的唐宋時(shí)代觀》時(shí)刪去了與時(shí)政分析相關(guān)聯(lián)的部分,使得“宋代近世說”以純粹學(xué)術(shù)面貌呈現(xiàn),但同樣作為以中國歷史為主體的歷史分期論說,其被刪去的部分及其分期標(biāo)準(zhǔn)的差異正顯示出該說與“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貌離神合,都有序地存于內(nèi)藤東洋史整體結(jié)構(gòu)之內(nèi)。
不少學(xué)者指出,內(nèi)藤的東洋史研究在尊重中國古典文化、重視與中國學(xué)者交往、重視中國典籍,乃至倡導(dǎo)“樸學(xué)”、反對(duì)一味迎合政府立場等方面都有相對(duì)鮮明的自身特點(diǎn),此固誠然,其以“文化”為中心構(gòu)筑歷史觀亦使其在許多學(xué)者評(píng)價(jià)中獲得“文化史家”之名。③在許多學(xué)者評(píng)價(jià)中,內(nèi)藤擁有“文化史家”之名,較有代表性作品如連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xué)家——內(nèi)藤湖南》,學(xué)生書局,2004 年;前述日本內(nèi)藤湖南研究會(huì)多數(shù)成員亦肯定內(nèi)藤文化史觀的超越性價(jià)值,臺(tái)灣學(xué)者何培齊的博士論文《內(nèi)藤湖南史學(xué)研究》(中國文化大學(xué),2003 年)亦持同樣觀點(diǎn)。但內(nèi)藤整體研究卻用意尤深:其采用“文化”視角,取代國家觀念、淡化此疆彼界、重構(gòu)地理空間,但民族、國家、疆界、主權(quán)等詞匯已然是20 世紀(jì)最重要的事實(shí),內(nèi)藤將之暗留于日本,大力建構(gòu)具有超越性的“東洋文化”,改造前人史論提出“文化中心移動(dòng)說”并將其敘述為“坤輿大勢”,借助歷史進(jìn)步觀念賦予20 世紀(jì)日本承擔(dān)“東洋文化”發(fā)展之“天職”。由于中國的“東洋”化,則日本對(duì)中國的一切行為均可視為歷史上中國內(nèi)部民族沖突的延續(xù),具有促進(jìn)“東洋文化”發(fā)展之“歷史的正義”。其以中國史為主要對(duì)象的“東洋史時(shí)代三區(qū)分說”是在歷史變遷層面提供的“東洋文化”又一大勢論說,其著力于中國社會(huì)內(nèi)部變遷之跡的“宋代近世說”亦蘊(yùn)于此架構(gòu)中,兩者貌離神合,共同構(gòu)成為日本“天職”說之論證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從整體形式上看,內(nèi)藤完全以歷史學(xué)方法建構(gòu)其論說體系,最終論證出的卻是近代日本重構(gòu)東洋政治一體性之“天職”在其體系內(nèi)既具歷史正當(dāng)性亦具歷史可行性。從史家主體觀念與學(xué)術(shù)研究之關(guān)系這一層面來看,內(nèi)藤湖南的東洋史研究當(dāng)可為典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