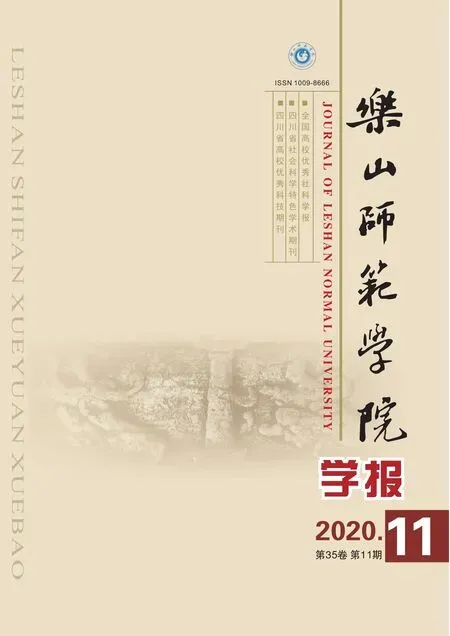生命閾限的儀式書寫
——重讀《我們的小鎮(zhèn)》
蔣賢萍
(西北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70)
《我們的小鎮(zhèn)》(OurTown)(以下簡稱《小鎮(zhèn)》)是20世紀(jì)美國劇作家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的代表性作品,描寫的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格洛佛角小鎮(zhèn)居民恬靜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劇中人物平靜地經(jīng)歷著出生、成長、婚姻與死亡。人類學(xué)家用“儀式”(ritual)這一術(shù)語來指與正式的、非功利目的的地位有關(guān)的活動(dòng),而不是僅僅限于宗教儀式。法國民俗學(xué)家阿諾爾德·范熱內(nèi)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在《過渡禮儀》一書中將“過渡禮儀”(又譯“通過儀式”)定義為“伴隨著地點(diǎn)、狀態(tài)、社會(huì)位置和年齡的每一次變化而舉行的儀式”[1]94,而出生、結(jié)婚、死亡構(gòu)成人的生命“通過儀式”中三個(gè)完整的“閾限”。
弗萊的原型批評(píng)理論認(rèn)為,西方文學(xu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對(duì)自然界循環(huán)運(yùn)動(dòng)的模仿。自然界的循環(huán)運(yùn)動(dòng)可分為春、夏、秋、冬四個(gè)階段。與此相應(yīng),文學(xué)敘述的結(jié)構(gòu)也可以分為四種基本類型:春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喜劇,夏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浪漫故事,秋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悲劇,冬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諷刺。[2]192—277弗萊在自然的四季更替、生物的生命形態(tài)、人類的心理訴求、神話儀式的母題以及“詩學(xué)”文類的敘事特征之間,建立起一種詩性的對(duì)話。這樣的原型敘事仿佛一場生命“通過禮儀”的展演,是范熱內(nèi)普過渡禮儀的個(gè)案之上的美學(xué)概括。[3]302
《小鎮(zhèn)》的創(chuàng)作深受人類學(xué)考古思想的影響。①筆者將結(jié)合范熱內(nèi)普的“通過儀式”和弗萊的原型敘事,對(duì)《小鎮(zhèn)》的儀式書寫進(jìn)行闡釋,指出劇作家將人物命運(yùn)與遠(yuǎn)古的儀式融合在一起,將戲劇的敘事儀式化,小鎮(zhèn)居民的日常生活被賦予神圣的儀式力量。《小鎮(zhèn)》仿佛重新回歸古老的儀式,將其置于自然的時(shí)序儀式當(dāng)中,在四季變遷的自然節(jié)律中體驗(yàn)生命的律動(dòng),其富有詩意的原型敘事是人類生命通過儀式的生動(dòng)再現(xiàn)。
一、春天敘事與出生儀式
弗雷澤在其人類學(xué)著作《金枝》中,循著“金枝”的神話遺跡,對(duì)神話和相關(guān)儀式進(jìn)行比較研究,指出原始人的生活深受春天以及生命律動(dòng)儀式的浸潤。[4]懷爾德在《小鎮(zhèn)》中對(duì)生命閾限的儀式書寫滲透著弗雷澤的人類學(xué)思想。在第一幕中,舞臺(tái)經(jīng)理就說,要在新建銀行的奠基石下放一本《小鎮(zhèn)》,這樣,千年以后的人們也可以通過閱讀劇本了解新英格蘭鄉(xiāng)村曾經(jīng)的生活畫面,“這就是當(dāng)年我們的方式:我們就這樣成長、結(jié)婚、生活和死亡。”[5]28《小鎮(zhèn)》共分三幕:第一幕名為“日常生活”;第二幕名為“愛情與婚姻”;第三幕并未直接命名,但根據(jù)劇情是指“死亡”。劇作家用樸素的語言,記載了小鎮(zhèn)居民的出生、結(jié)婚與死亡,再現(xiàn)了完整的生命通過儀式。正如勞埃德·沃納所說:
一個(gè)人經(jīng)歷他有生之年的運(yùn)動(dòng),從固定在母親子宮內(nèi)的胎盤到死亡和墓碑的終極點(diǎn),最終作為死去的有機(jī)體躺在墳?zāi)估铮@個(gè)運(yùn)動(dòng)被一些重要的過渡時(shí)刻不時(shí)地打斷,所有的社會(huì)都把這些重要的過渡時(shí)刻用適當(dāng)?shù)膬x式將它們儀式化,公開標(biāo)志出來,加深這些個(gè)體和群體在這個(gè)社區(qū)里活著的成員心中的重要性。這些重要時(shí)刻就是誕生、青春期、結(jié)婚和死亡。[6]
特納將其定義為“生命轉(zhuǎn)折儀式”,標(biāo)志著個(gè)人從生命或社會(huì)地位過渡到另一個(gè)階段。
《小鎮(zhèn)》的舞臺(tái)布置非常簡單,只有幾把桌椅,使其超越特定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構(gòu)成神圣的儀式空間。貫穿全劇的舞臺(tái)經(jīng)理被賦予多重身份,既是道具員、故事講述者,又是演員、故事評(píng)論者,他帶領(lǐng)演員和觀眾遍歷小鎮(zhèn)居民的日常生活,并將小鎮(zhèn)與整個(gè)宇宙聯(lián)系起來,成為主持“生命通過儀式”的核心人物。劇中第一幕描寫的是吉布斯醫(yī)生和韋伯編輯兩家人一天的日常生活。清晨,吉布斯醫(yī)生剛剛接生完一對(duì)雙胞胎,吉布斯太太正在為孩子們準(zhǔn)備早餐,韋伯先生家充滿孩子的喧鬧聲和母親的嘮叨聲,伴隨著門外送牛奶人、送報(bào)少年的叫喊聲,演繹出小鎮(zhèn)溫馨的晨曲。“與其說這是一個(gè)故事,不如說是日常生活的畫面。”[7]23在懷爾德筆下,小鎮(zhèn)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儀式化,使其具有儀式的神圣品質(zhì)。
第一幕發(fā)生在1901年5月7日,正值春天。小鎮(zhèn)的一天在黎明時(shí)分拉開序幕,新生命的誕生暗示著“生”的主題,其中展現(xiàn)的是生命伊始的“出生儀式”。劇作家無意詳述新生兒家庭為其舉行的出生儀式,但他用簡單的象征符號(hào),如樹木、花朵、黎明,譜寫了一曲“出生儀式”的美好樂章。“每一類儀式都可以看作象征符號(hào)的布局,一種‘樂譜’,而象征符號(hào)則是它的音符。”[1]47吉布斯夫人和韋伯夫人的花園里種滿玉米、豌豆、蜀葵、太陽花等。這些植物的生命意象與四季的更替循環(huán)類同,在《小鎮(zhèn)》里具有原型敘事的價(jià)值。弗萊對(duì)原型結(jié)構(gòu)的文學(xué)敘事有著獨(dú)特的看法:“我所取名的原型(archetype)是一種典型的或重復(fù)出現(xiàn)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種象征,它把一首詩和另外的詩聯(lián)系起來,從而有助于統(tǒng)一和整合我們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2]99“花園”是貫穿《小鎮(zhèn)》始終的原型意象,將生命通過儀式的不同階段緊密聯(lián)系起來。
在弗萊詩意的想象中,春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喜劇,“它的復(fù)合形象是父親和母親。原型的哲學(xué)與美學(xué)形態(tài)特質(zhì)表現(xiàn)為極致的狂喜;與之相配合的藝術(shù)敘事門類為酒神頌歌和傳奇。”[3]300《小鎮(zhèn)》第一幕不乏對(duì)父母形象的刻畫。吉布斯太太看到丈夫不太開心,便邀他“出來聞聞月光下的向日葵”,之后“他們挽著手沿著腳燈散步”[5]33。弗萊還指出,在春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中經(jīng)常看到少年追求少女的情節(jié)。《小鎮(zhèn)》第一幕呈現(xiàn)了一幅田園牧歌式的畫面:初升的太陽、鳥兒的啼鳴、美麗的花園、月光下的向日葵,還有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喬治憧憬著未來的美好生活,艾米麗也有了自己的“心事”。盡管劇作家由小鎮(zhèn)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漸聚焦于喬治和艾米麗之間的關(guān)系,但“他們也只是美好青春的符碼,代表著兩個(gè)將會(huì)相愛并結(jié)婚,最終承受生死之痛的年輕人”[7]25。
弗萊告訴我們,植物的符號(hào)表述與原始儀式有著脈絡(luò)上的關(guān)聯(lián)。“植物世界為我們展示了一年一次的四季循環(huán),它常常以一位神的形象表現(xiàn)出來,或者等同于這樣一位神:它在秋天死去,或者隨著收割而被殺死,在冬天消失,而春天又得以復(fù)活。”[2]187在弗萊的理論中,黎明、春天是英雄出生儀頌的原型意象。大地復(fù)蘇,萬物生長,生命戰(zhàn)勝黑暗。春天的綠色世界與儀式中豐產(chǎn)的世界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小鎮(zhèn)》第一幕所展現(xiàn)的花園意象是典型的春天敘事。亞里士多德的戲劇學(xué)說認(rèn)為,戲劇源自于對(duì)酒神儀式的模仿。懷爾德在劇中也借用了酒神儀式的敘述結(jié)構(gòu)。在酒神祭祀儀式里,酒神被視為葡萄神(或植物神、豐產(chǎn)神)來崇拜。葡萄、常春藤是酒神生命表述中最為常見的植物敘事符號(hào)。“常春藤有多種象征意義。它的葉子總是綠的,意味著永生……酒神狄奧尼索斯及其信徒所執(zhí)的頂端為松果狀的手杖,也由常春藤所纏。”[8]
特納研究發(fā)現(xiàn),在恩登布人的儀式中,有些象征符號(hào)是支配性的。“支配性象征符號(hào)在許多不同的儀式語境中出現(xiàn),有時(shí)候支配著整個(gè)過程,有時(shí)候支配著某些特殊階段。支配性象征符號(hào)能夠統(tǒng)合迥然不同的符號(hào)所指,其意義內(nèi)容在整個(gè)象征系統(tǒng)中具有高度的持續(xù)性和一致性。”[1]5特納不僅探討了儀式中支配性象征符號(hào)的意義和作用,也討論了它們與其他象征符號(hào)的關(guān)聯(lián),還關(guān)注到象征符號(hào)出現(xiàn)的社會(huì)和文化田野場景。在恩登布人的儀式中,“奶樹”就是支配性象征符號(hào),意指社會(huì)組織的原則和美德,代表著母系繼嗣制度。而《小鎮(zhèn)》中的支配性象征符號(hào)是“植物”,意指四季的更替與生命的輪回。
格洛佛角小鎮(zhèn)上“種著一棵很大的白胡桃樹”[5]6,仿佛創(chuàng)世神話中的“生命樹”。在此,“白胡桃樹”被賦予創(chuàng)世敘事的功能,是“生命”的符碼,其中潛藏著人類早期認(rèn)識(shí)世界的態(tài)度。“生命”話語即存在于“樹”,“宇宙”的生命表征即存在于“樹”。[3]137人類對(duì)生命的認(rèn)識(shí),最早是從植物的變化中感知的,人類從植物的意象中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生命的認(rèn)同。懷爾德在其春天敘事中,為我們展現(xiàn)了人類原初的誕生儀式與生命的喜悅。
二、夏天敘事與結(jié)婚儀式
《小鎮(zhèn)》第二幕發(fā)生在三年以后,1904年7月7日,正值盛夏。開場時(shí),舞臺(tái)經(jīng)理平靜地講述著時(shí)間的流逝與歲月的更迭:“太陽已經(jīng)升起了一千多次。夏天和冬天已經(jīng)讓山巒又裂開了一點(diǎn)點(diǎn),而雨水則沖走了一些泥土……大自然也在以別的方式彰顯造化:很多年輕人戀愛了,結(jié)婚了……屋檐下一些新的家庭組建了起來。”[5]41-42艾米麗和喬治已畢業(yè)并成為戀人,第二幕主要圍繞他們的婚禮展開。喬治清早起床就興奮地冒雨去見新娘,可韋伯夫人告訴他一個(gè)傳統(tǒng)習(xí)俗:“在結(jié)婚那天,新郎是不可以提前見到新娘的,要等去了教堂才行。”[5]49在此,韋伯夫人遵循的是一種禁忌禮儀。懷爾德數(shù)次提到小鎮(zhèn)居民所遵循的古老禁忌,賦予現(xiàn)代戲劇以神圣的儀式感。之后,韋伯先生和喬治之間進(jìn)行了一場父子式的對(duì)話。對(duì)喬治來說,這是一場儀式性的對(duì)話,標(biāo)志著他即將從少年過渡到成年,聚合入。
在喬治和艾米麗舉行婚禮之前,懷爾德向觀眾呈現(xiàn)了雙方及其家庭所經(jīng)歷的心理過渡期。喬治告訴母親他不想長大,而母親告訴他,“你現(xiàn)在是一個(gè)男人了”[5]66。豪伊特對(duì)庫爾奈人(Kurnai)的描述同樣適合喬治的情形:
儀式行為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給男孩的生活帶來突然的變化;他與過去被一溝壑所隔離,他永遠(yuǎn)也不能再回去。他與母親的紐帶被割斷,并由此與成年男人連在一起。他童年與母親和姊妹的游戲娛樂從此被拋棄和隔離。他從此成為一個(gè)男人,被教導(dǎo)承擔(dān)起姆林(Murring)部落成員所應(yīng)有的責(zé)任。[9]58
艾米麗及其家人同樣如此。眼看女兒出嫁,韋伯太太潸然落淚,艾米麗也依依不舍。對(duì)喬治和艾米麗來說,結(jié)婚是其生命旅程中的關(guān)鍵時(shí)刻,是告別童年進(jìn)入成人世界的重要閾限。“結(jié)婚成為從一社會(huì)地位到另一社會(huì)地位的最重要過渡,因?yàn)橹辽倩橐鲆环叫柁D(zhuǎn)換家庭、家族、村落或部落,有時(shí)新婚雙方還需要建立新居處。”[9]87居處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地域之過渡,但懷爾德對(duì)此并未做太多敘述,更多地關(guān)注儀式主人公(閾限人)心理狀態(tài)的過渡。特納的文字能夠很好地解釋喬治和艾米麗此時(shí)內(nèi)心的焦慮:
在討論閾限的結(jié)構(gòu)方面時(shí),我曾提到新入會(huì)者如何從他們?cè)械慕Y(jié)構(gòu)位置中撤離出來,從而離開了與那些位置相關(guān)的價(jià)值觀、規(guī)范、情感以及技術(shù)。他們還被剝奪了過去的思考、感覺和行動(dòng)習(xí)慣。在閾限階段,新入會(huì)者被交替驅(qū)使和鼓勵(lì)著去思考他們的社會(huì)、他們的宇宙和那些創(chuàng)造了它們并支撐著它們的各種力量。閾限能被部分地表述為反思的階段。在此階段,過去那些結(jié)合成形的、被新入會(huì)者們不假思考地接受了的觀念、情感和事實(shí),可以說,都被分解成它們的構(gòu)成成分。[1]105
在婚禮之前,舞臺(tái)經(jīng)理向觀眾還原了艾米麗和喬治決定在一起時(shí)的情境。盡管這一幕呈現(xiàn)的依然是小鎮(zhèn)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沒有激烈的戲劇沖突,但人物之間的互動(dòng)不乏戲劇張力。弗萊認(rèn)為,“對(duì)抗”或者沖突是浪漫故事的基礎(chǔ),或者說是原型主題,而浪漫故事的要素是一連串奇妙的冒險(xiǎn)。[2]233懷爾德無意大肆渲染這對(duì)年輕人的冒險(xiǎn)之旅,只是用樸素的舞臺(tái)語言向我們展示了生命通過儀式中的重要閾限。在兩人的傾心交談中,喬治改變了想去農(nóng)業(yè)學(xué)校讀書的想法,因?yàn)樗J(rèn)為跟喜歡的人在一起“和大學(xué)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5]61。之后,“他們非常沉默地穿過舞臺(tái),穿過韋伯家后門的藤架。”[5]62此處的“藤架”意象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標(biāo)志著喬治和艾米麗從少年向成年的過渡,是其“告別童年”禮儀。“此禮儀之核心仍是通過模仿之門……門是人生兩階段的界線,因而從其下面經(jīng)過便離開童年世界,進(jìn)入青春期世界。”[9]47。該禮儀可謂喬治和艾米麗結(jié)婚禮儀(邊緣禮儀或閾限禮儀)前的分隔禮儀(或閾限前禮儀)的一部分。正如范熱內(nèi)普所說:
某些邊緣禮儀漫長而繁復(fù),可進(jìn)一步劃分,以致形成獨(dú)立階段。訂婚進(jìn)程構(gòu)成成熟期與結(jié)婚期之間的一個(gè)邊緣期;從成熟期到訂婚期指過渡本身的邊緣進(jìn)程構(gòu)成又一特別系列的分隔禮儀、邊緣禮儀和聚合禮儀;從訂婚到結(jié)婚之邊緣過渡本身則另形成一系列從分隔、進(jìn)入邊緣到聚合的禮儀,以致最后進(jìn)入結(jié)婚的狀態(tài)。[9]10
經(jīng)過漫長的閾限前禮儀,喬治和艾米麗終于走進(jìn)步入神圣的婚禮殿堂,舞臺(tái)上響起門德爾松的《婚禮進(jìn)行曲》。在交換戒指、新人接吻等儀式之后,“舞臺(tái)突然變成了一幅悄然凝固的場景。”[5]70此時(shí),扮演婚禮主持牧師的舞臺(tái)經(jīng)理突然中斷婚禮儀式進(jìn)程,用簡單的語言展現(xiàn)了生命的所有流轉(zhuǎn):“農(nóng)舍,嬰兒車,駕著福特在禮拜日下午出行,第一次風(fēng)濕,祖孫,第二次風(fēng)濕,臨終時(shí)刻,宣讀遺囑”。[5]70
在舉行婚禮的這一幕,整個(gè)劇場構(gòu)成神圣的儀式空間,觀眾不再代表遠(yuǎn)離儀式的世俗世界,而是參與其中,構(gòu)成完整儀式的一部分,共同見證兩個(gè)年輕人完成生命進(jìn)程中重要的閾限:“新娘和新郎從過道走出來,表情激動(dòng),但卻努力表現(xiàn)得很莊重……一束亮光投射在他們身上。”[5]70此時(shí)的“過道”意象具有重要的儀式價(jià)值,是喬治和艾米麗生命通過儀式中典型的象征符號(hào)。特納認(rèn)為,通過儀式指明并構(gòu)成狀態(tài)間的過渡,但他“更樂意把過渡(transition)看成一種過程,一種生成,而在通過儀式的情況下,過渡甚至是一種轉(zhuǎn)換。”[1]94因此,“新娘和新郎從過道走出來”意味著兩個(gè)新人社會(huì)身份的轉(zhuǎn)換過程,生命進(jìn)程中的閾限階段。
閾限理論的假設(shè)完全建立在生命的歷時(shí)性維度之上,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生命的自然觀照。人的生命進(jìn)程被視為單向的不可逆轉(zhuǎn)的物理過程。在這個(gè)人類感知的生命流程里面,它可以再被分割成為幾個(gè)重要時(shí)段,在經(jīng)過每一個(gè)時(shí)段的關(guān)節(jié)上必須伴著一個(gè)相應(yīng)的儀式行為,以確立其“過渡”的程序,標(biāo)榜生命行程“通過”的階段性。[3]51
根據(jù)弗萊詩意的理論構(gòu)思,正午、夏天是英雄勝利儀贊的原型意象。“神圣的榮耀,光輝普照,通往天堂道路的美麗神話。它的復(fù)合形象是未婚妻的相伴下,英雄走向勝利的旅途中。”[3]300夏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是浪漫故事。喬治和艾米麗在親友的祝福下攜手走進(jìn)婚姻殿堂的那一幕,儼然是弗萊對(duì)生命詩性演繹的戲劇化注腳。正如弗萊所說:“浪漫故事的完整形式,無疑是成功的追尋……最后是主人公的歡慶階段。”[2]226懷爾德在其夏天敘事中,為我們奏響英雄勝利的贊歌,再現(xiàn)了生命成熟的儀式。
三、秋天敘事與死亡儀式
《小鎮(zhèn)》第三幕發(fā)生在九年后,1913年夏的一個(gè)陰雨天。幕間休息時(shí),舞臺(tái)工作人員把十多把椅子擺成三排,表示墓園里的墳冢。吉布斯太太、西蒙·斯蒂姆森、沃利·韋伯及索默斯太太等,都已經(jīng)離開人世,艾米麗也很快就要加入他們的行列。舞臺(tái)經(jīng)理向觀眾描述了小鎮(zhèn)寧靜的墓園:
這里當(dāng)然是格洛佛角一處重要的地方。它位于山頂——多風(fēng)的山頂——能看到大大的天空和云朵,——也能照到很多的陽光,還可以看見月亮和很多星星。
某個(gè)風(fēng)和日麗的下午,你來到山上,能看見層巒疊嶂的山丘——非常非常藍(lán)——佇立在斯納珀湖和溫尼佩紹基湖旁邊……這個(gè)景點(diǎn)風(fēng)光不錯(cuò)。山上有月桂樹和丁香。[5]74
接著,舞臺(tái)經(jīng)理略帶傷感地評(píng)論道:“有很多的哀愁,都在這個(gè)地方靜靜沉淀下來。那些悲慟欲絕的人們帶著自己的親屬來到這座山上……當(dāng)傷痛平復(fù)后,我們自己也會(huì)安身于此。”[5]75-76
當(dāng)小鎮(zhèn)墓園的場景出現(xiàn)在舞臺(tái)上時(shí),給觀眾以極大的震撼。艾米麗因難產(chǎn)而死,舞臺(tái)左邊出現(xiàn)為她送葬的隊(duì)伍。此時(shí),索默斯太太發(fā)出這樣的感嘆:“生命真是可怕……但又美好。”[5]78接著,艾米麗作為死者出現(xiàn)在舞臺(tái)上:
突然,艾米麗從雨傘之間現(xiàn)身。她穿著一件白色連衣裙,頭發(fā)垂在后背上,系著個(gè)白色蝴蝶結(jié),就像小姑娘一樣。她走得很慢,疑惑地看著那些亡者,有點(diǎn)暈頭轉(zhuǎn)向。
她停在半途,淺淺地笑了。她看了一會(huì)那些悼念的人,然后就緩步走向吉布斯太太旁邊的空椅子,坐了下來。[5]81
在以上簡短的文字當(dāng)中,劇作家涵蓋了死亡禮儀中的分隔禮儀、邊緣禮儀和聚合禮儀三個(gè)完整的部分。她“從雨傘之間現(xiàn)身”標(biāo)志著離開生者世界的分隔禮儀,緩步走向死者的過程可謂從生者世界向亡者世界過渡的邊緣禮儀,而她坐在“吉布斯太太旁邊的空椅子”上標(biāo)志著她加入亡者世界的聚合禮儀。災(zāi)難、死亡是悲劇的原型主題。如果說小鎮(zhèn)第一幕是恬靜的牧歌,第二幕是溫情的浪漫故事,那么第三幕就轉(zhuǎn)向了悵惋的哀歌。對(duì)于悲劇的涵義,弗萊有著獨(dú)特的解讀:
在完美的悲劇中,主要人物被從夢(mèng)幻中解放出來,這一解放同時(shí)又是一種束縛,因?yàn)榇嬖谥匀恢刃颉o論一個(gè)悲劇中點(diǎn)綴了多少幽靈、兇兆、女巫或預(yù)言者,我們明白,悲劇主人公都不可能簡單地用點(diǎn)亮一盞燈并喚來一位神怪來把自己救出困境。[2]253
艾米麗有過美好的童年,幸福的婚姻,但她依然無法逃脫人類的終極宿命。只有在離開人世之后,方才意識(shí)到曾經(jīng)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有多么美好,但“活著的人們是不會(huì)懂的”[5]83。
在弗萊的詩意想象中,悲劇是秋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黃昏、秋天是英雄死亡禮儀的原型表述。“毀滅的命運(yùn),垂死的英雄,野蠻的弒戳,祭獻(xiàn)與犧牲,孤獨(dú)的英雄神話……原型的哲學(xué)美學(xué)形態(tài)特質(zhì)表現(xiàn)為悲壯的苦難;與之相配合的藝術(shù)門類為悲劇和挽歌。”[3]300人類學(xué)研究發(fā)現(xiàn),植物神祗一般都在秋天死去,在春天再生。懷爾德并沒有將艾米麗的葬禮安排在秋天,而是夏天大雨滂沱時(shí)節(jié),或許是為了避免秋天所傳遞的“悲劇”原型意義,減少生命消逝的悲劇色彩,旨在告訴我們:“死亡乃永恒之歸宿,與自然萬物的生滅并無區(qū)別。艾米麗之死因而也不是個(gè)體事件,而是代表了一種類型化的死亡,其本身并無悲劇意義。”[10]78懷爾德試圖糾正觀眾對(duì)葬禮場景的誤讀。盡管如此,艾米麗的生死告白卻成為悲劇的高潮,懷爾德一直試圖疏離的悲情(Pathos)在劇終時(shí)獲得強(qiáng)化,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悲情謬誤。
劇作家的有意回避并未減損劇作本身的悲劇價(jià)值,他“以最微小的生活細(xì)節(jié)揭示了人生的短暫和構(gòu)成短暫人生的悲傷和痛苦”[7]13。這個(gè)悲劇不只與作為個(gè)體的艾米麗相關(guān),而且與整個(gè)人類相關(guān)。懷爾德以人類學(xué)家的視角記錄著人的生命通過儀式,但其中蘊(yùn)含著深深的悲憫之心。艾米麗并不是傳統(tǒng)的悲劇英雄,沒有非凡的、近乎神性的品質(zhì),她代表著世俗的人類,無法脫離命運(yùn)的單向軌道與難以捉摸的限度。艾米麗的死亡具有儀式性的崇高價(jià)值。“悲劇需要濃墨鋪墊,它需要最偉大的詩人筆下的最壯麗的辭藻。盡管災(zāi)難通常是悲劇的結(jié)局,但它被同樣意義深遠(yuǎn)的原初的偉大——一個(gè)失去了的天堂——所彌補(bǔ)。”[2]258艾米麗盡管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媽媽的花園(喻指永恒的伊甸園),但她因此獲得了“原初的偉大”。正如弗萊所說:“不可思議的悲劇主人公作為對(duì)夢(mèng)幻的模仿物,像驕傲而緘默的天鵝一樣,在死亡的關(guān)頭變得能言善辯……隨著主人公的墮落,他的偉大的精神一直勾劃的那個(gè)更偉大的世界一剎那間變得隱約可見,然而,那個(gè)世界的神秘和遙遠(yuǎn)感卻仍然存在。”[2]264
特納指出,比起與死者的關(guān)系來,葬禮和生者更有關(guān)聯(lián)。在所有的生命轉(zhuǎn)折儀式中,所有與儀式相關(guān)的人,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都會(huì)改變。當(dāng)某個(gè)人死去,所有和他有關(guān)的紐帶一下子被突然斬?cái)唷K勒咴街匾粩財(cái)嗟募~帶就越多,牽涉的范圍就越廣。[1]8艾米麗也意識(shí)到,“喬治沒了我,一切都會(huì)變得不同了”[5]83。當(dāng)送葬的人群都散開,喬治來到艾米麗墓前雙膝跪下,俯身趴在艾米麗腳下,但此時(shí)他們之間已是陰陽相隔。但令人欣慰的是,艾米麗加入的“那個(gè)世界與我們的世界相似,但更美好,其社會(huì)組織也與我們的一樣。因此,每個(gè)人重新回到曾經(jīng)所屬于的氏族部落、年齡群體或前世所從事的職業(yè)”[9]111。
儀式理論與實(shí)踐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duì)于任何個(gè)人和社會(huì)來說,由一個(gè)“閾限”向另一個(gè)“閾限”的過渡都是不可或缺的,仿佛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所進(jìn)行的規(guī)律性“通過儀式”。弗雷澤的《金枝》講述的就是儀式對(duì)于生命在不同狀態(tài)下的轉(zhuǎn)變所必備的程序,“弒老儀式”對(duì)于部落新的生機(jī)就是一種宗教上的必然手段。同樣,對(duì)于格洛佛角小鎮(zhèn)來說,艾米麗的死亡也是一種必然的儀式過程。懷爾德認(rèn)為,死亡并非人類存在的終點(diǎn),而是回歸自然,融入永恒的宇宙。
現(xiàn)在有些東西,我們都知道,卻很少拿出來端詳。我們都知道,某個(gè)東西是永恒的。它不是房子,不是姓名,不是土地,甚至也不是星辰……每個(gè)人在骨子里都明白,某個(gè)東西是永恒的,它和人類有關(guān)。所有曾在世的偉人都講述過它,講了五千年,然而你們會(huì)覺得奇怪,人們卻總是沒能記住它。這個(gè)永恒的東西在極深之處,它關(guān)乎每一個(gè)人。[5]76
懷爾德在《小鎮(zhèn)》的秋天敘事中,揭示了生命存在的原初意義。
四、冬天敘事與復(fù)活儀式
艾米麗來到亡者世界時(shí),由于依戀人間希望能回到過去。舞臺(tái)經(jīng)理建議她選擇“生命里最不重要的一天”[5]86。于是,艾米麗回到了她12歲生日那天。那是1899年2月11日,正值寒冬季節(jié)。熟悉的小鎮(zhèn)、雪后的黎明、白色的籬笆、依然年輕的父母,過去的一切重新出現(xiàn)在艾米麗眼前,使她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重返過去,艾米麗方才發(fā)現(xiàn),看似最平常的一天卻如此美好,但人們卻熟視無睹。返回墓地之前,艾米麗深情地與這個(gè)世界進(jìn)行告別:“再見,再見,世界。再見,格洛佛角……媽媽,爸爸。再見,我的鬧鐘……媽媽的太陽花。食物和咖啡。新熨好的衣服,還有熱水澡……睡覺和起床。哦,地球,你太美妙了,以至于無人能認(rèn)識(shí)到你的好。”[5]93這是艾米麗與生者世界所作的告別儀式。
在重返人間前,舞臺(tái)經(jīng)理告訴艾米麗:“我們會(huì)從黎明開始。你記得的,那時(shí)下了好幾天的雪;但是在前一夜雪停了。他們開始清理道路。太陽出來了。”[5]86這段文字頗有深意,是艾米麗“復(fù)活”的詩意寫照。在弗萊的理論建構(gòu)中,植物神祗一般都在秋天死去,在春天再生。盡管艾米麗的“復(fù)活”發(fā)生在冬天而不是春天,但雪后黎明的原型意象清晰地表達(dá)了復(fù)活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艾米麗“重返人間”的再生禮儀是其死亡儀式中“邊緣禮儀”的延伸,旨在使其聚合入亡者世界。在此,其死亡禮儀與再生禮儀合而為一。范熱內(nèi)普研究發(fā)現(xiàn),古埃及喪葬禮儀是過渡禮儀模式的恰當(dāng)演繹,并探討了其中的奧西里斯(Osiris)禮儀:
其核心意義是為了一方面將奧西里斯與亡者認(rèn)同,另一方面也將亡者與太陽認(rèn)同。我認(rèn)為,最初一定有兩個(gè)分開的儀禮,后來則將死亡與再生的主題結(jié)合在一起。作為奧西里斯,亡者先從人界分離,再被重新組合;他已死亡,但在亡者世界得到重生,因此有一系列再生禮儀。作為太陽(Ra),亡者在每個(gè)傍晚到達(dá)冥府時(shí)死去。他的木乃伊尸體被拋棄掉;但在黑夜里他經(jīng)歷一系列使他逐步復(fù)活的禮儀,當(dāng)太陽出來時(shí),他獲得再生,重新開始每日在生者世界的旅程。[9]115
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使之陌生化就意味著將其放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從另一個(gè)視角重新審視。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藝術(shù)的存在就是為了喚醒主體對(duì)生活的感受。布萊希特也認(rèn)為,陌生化的最終目的并不是制造間隔,而是消除間隔,達(dá)到對(duì)事物更深刻的熟悉。陌生化是指對(duì)日常事物進(jìn)行藝術(shù)化的處理,使之與審美主體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使主體獲得陌生美感。[11]懷爾德借助艾米麗重返人間這種陌生化的藝術(shù)手法,旨在喚醒觀眾對(duì)生活的感受,這也是其戲劇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性所在。平凡生活中那些最平凡的小事,在劇中具有了儀式的神圣性,獲得了崇高的價(jià)值。正如懷爾德在《戲劇三部》的前言中所說“《我們的小鎮(zhèn)》無意提供新罕布什爾州鄉(xiāng)村生活的圖畫……該劇的宗旨在于發(fā)覺我們?nèi)粘I钪凶瞵嵓?xì)平凡事件的價(jià)值。”[12]xi觀眾不僅能夠在陌生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獲得陌生美感,而且能夠在“復(fù)活”敘事中重新感知生命的真諦。
《小鎮(zhèn)》里的舞臺(tái)經(jīng)理是劇中的核心人物,被賦予多重角色,更像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具有無限的創(chuàng)造力,主宰著人物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在帶領(lǐng)艾米麗重返人間的旅程中,舞臺(tái)經(jīng)理扮演了向?qū)У慕巧拖竦 渡袂分械膫ゴ笤娙司S吉爾。②如果說《小鎮(zhèn)》是一場神圣的生命通過儀式,那么舞臺(tái)經(jīng)理就是主持儀式的牧師,不僅帶領(lǐng)艾米麗完成生命中的重要閾限,而且使觀眾獲得全新的生命認(rèn)知。對(duì)觀眾來說,這何嘗不是一種神秘的心靈(或精神)“通過儀式”,“一種展示只有經(jīng)歷某種凈化后才能看到某種圣物的禮儀”[9]68,在艾米麗戲劇化的“復(fù)活”儀式中獲得全新的生命感知。
在弗萊的理論表述中,夜晚、冬天是英雄苦楚儀殤的原型意象,“理性的坍塌,命運(yùn)的苦斗,人類的毀滅與復(fù)歸于混沌神話。它的復(fù)合形象為巨人和巫師。原型的哲學(xué)美學(xué)形態(tài)特質(zhì)表現(xiàn)為拼搏與抗?fàn)帯!盵3]300冬天的敘述結(jié)構(gòu)為反諷與諷刺,“缺乏英雄氣概和有效行動(dòng),分崩離析以及注定失敗,混沌和無秩序籠罩整個(gè)世界,是反諷和諷刺的原型主題。”[2]233艾米麗的“復(fù)活”恰逢冬季。正是在艾米麗生命的儀式性回歸中,劇作家揭示了兩種存在論的諷刺性對(duì)立:“生者‘不懂’生之意義,徹悟的死者卻又陰陽永隔。”[10]78
特納研究發(fā)現(xiàn),在恩登布人的儀式象征體系中,“庫索羅拉”一詞指“揭露真相的地方”,它們是“專門圣化了的地點(diǎn),僅用在重要儀式的最后階段,古怪的儀式在那里上演,神秘的事物被展現(xiàn)給入會(huì)者。”[1]48在這個(gè)意義上,《小鎮(zhèn)》具有了某種儀式的神圣價(jià)值。劇作家揭示了人類全部的生命閾限,讓我們認(rèn)識(shí)到“日常生活中最瑣細(xì)平凡事件的價(jià)值”,從而完成象征意義上的儀式性過渡。正如特納所說,“閾限也許可以看作對(duì)于一切積極的結(jié)構(gòu)性主張的否定,但在某種意義上又可看作他們一切的源泉,而且,不只如此,它還可看作一個(gè)純粹可能性的領(lǐng)域,從那個(gè)地方觀念和關(guān)系的新穎形貌得以產(chǎn)生。”[1]96
從《小鎮(zhèn)》第一幕新生命的降臨,經(jīng)過第二、三幕艾米麗的婚禮、艾米麗因難產(chǎn)身亡后返回人間,這一切構(gòu)成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循環(huán)往復(fù)。而閾限理論的假設(shè)完全建立在生命的歷時(shí)性維度上,人的生命進(jìn)程是不可逆轉(zhuǎn)的物理過程。
在這個(gè)人類感知的生命流程里面,它可以再被分割成為幾個(gè)重要時(shí)段,在經(jīng)過每一個(gè)時(shí)段的關(guān)節(jié)上必須伴著一個(gè)相應(yīng)的儀式行為以確立其“過渡”的程序,標(biāo)榜生命行程“通過”的階段性。毫無疑問,它符合生命的物理性質(zhì),可是它同時(shí)與生命的心理期待有所沖突,并在許多宗教信仰現(xiàn)象中加劇這樣的生命理解:人的生命禮儀在年齡的物理過程中“通過”,最后體現(xiàn)為死亡狀態(tài)。人的生命禮儀在年齡的心理期待中“通過”,它最終體現(xiàn)為生的永恒。[3]51
“抗拒生命”構(gòu)成人類最深層的悲劇心理結(jié)構(gòu)。艾米麗重返人間的戲劇語言無不傳遞著人類“抵抗閾限”的心理情結(jié)。肉體的生命形式沿著時(shí)間走向遵循著“單線性”的閾限通過儀式,而“復(fù)活儀式”的深層結(jié)構(gòu)卻在強(qiáng)調(diào)“可逆性”的閾限通過儀式。“人們以在時(shí)間上拒絕死亡的方式獲得再生,以滿足時(shí)間的重復(fù)性質(zhì)。這樣才能達(dá)到時(shí)間在生命上的永恒性和社會(huì)秩序的穩(wěn)定性。”[13]懷爾德在《小鎮(zhèn)》的冬天敘事中,戲劇化地再現(xiàn)了遠(yuǎn)古的復(fù)活儀式,揭示了人類生命的不可逆與人類“抵抗閾限”之間的悖論所在。
《小鎮(zhèn)》是一首“溫柔的田園短詩,洋溢著令人心醉的憐憫和樸素情致的人類悲劇。”[12]封底同時(shí),其創(chuàng)作深受人類學(xué)研究的影響,借用儀式原型展開神圣與世俗之間的對(duì)話,是人類生命閾限的儀式化書寫。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經(jīng)過一次次的“閾限”,最終完成生命的循環(huán),這一循環(huán)正是人類對(duì)永恒不朽最貼切的理解,是其對(duì)感知的生命和目的的最佳藝術(shù)表述。[14]人類對(duì)生命的體驗(yàn)來自生命的自然演繹。懷爾德將生命通過儀式置于自然節(jié)律的運(yùn)動(dòng)當(dāng)中,使之呈現(xiàn)出詩意的色彩與神圣的品質(zhì),體現(xiàn)了對(duì)人類生命的終極關(guān)懷。正如奈特所說:“偉大的戲劇有時(shí)不僅是供人娛樂的。我想稱它為一種典禮或儀式,即用一種鄭重的方式展示某種深刻的涵義結(jié)構(gòu)”。[15]懷爾德用儀式化的戲劇語言,旨在喚起人們對(duì)日常生活的重新認(rèn)識(shí),從而實(shí)現(xiàn)戲劇的社會(huì)功能,對(duì)集體心靈施以教化。懷爾德對(duì)生命閾限的儀式書寫是一種詩性敘事的回歸。
注 釋:
① 懷爾德大學(xué)畢業(yè)后曾經(jīng)在羅馬學(xué)習(xí)過一年的考古學(xué),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關(guān)于歷史和時(shí)間的態(tài)度,進(jìn)而成為他許多作品的共同主題。
②懷爾德在《戲劇三部》序言中指出,《小鎮(zhèn)》有關(guān)情節(jié)是借鑒于但丁的《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