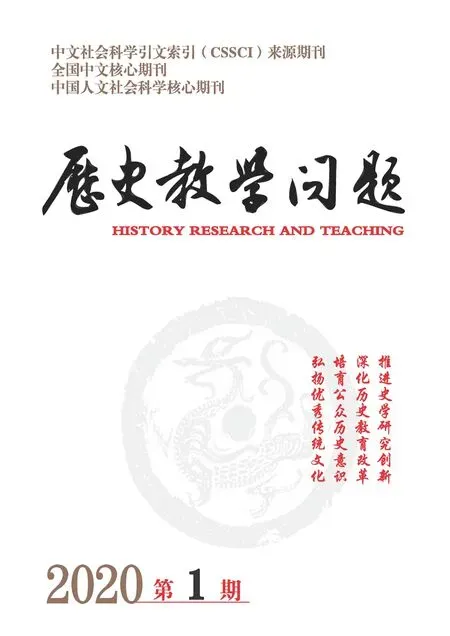“再造身心”:《旅行雜志》與民國中期城市知識群體的休閑旅行書寫
周 博 韓賓娜
近年來,隨著歷史人類學和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游記作為研究民國時期社會生活的一種史料,其價值逐漸引起了學界重視。《旅行雜志》(1927—1954)是近代中國第一本旅行類綜合刊物,自1927年創刊至七七事變之前的“黃金十年”是民國時期城市化活躍發展的時期,休閑旅行者或游走于城市與鄉野的山水之間,或穿梭于傳統與現代的異樣空間,通過這種跨越邊界的身心體驗,既可白描民國中期城市知識群體的旅行動機,也可窺探現代性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國的生成路徑。現有研究成果從旅行活動、文化意義、社會生活、旅行觀念等角度闡述了《旅行雜志》的多重意義,但對休閑旅行與游記作者主體的身心話語表述之間的透視尚顯不足。因民國中期休閑旅行基本集中在國內范圍,故本文以《旅行雜志》在1927—1936 年間刊載的536 篇國內游記為中心,兼及同時期其他旅行刊物,梳理民國中期城市知識群體的主訴出游動機及其促發因素,并管窺其身心話語中的現代性指向,以期深化對不同歷史時期旅行書寫與身心認知之理解。
一、逃離塵囂:擺脫嘈雜環境和枯燥工作
在1927—1936 年間刊登于《旅行雜志》的國內游記中,作者們較多地使用“煩膩”“苦悶”等表達負面情緒的詞匯形容自己所處之城市生活。譬如,生活在鄭州的林夙根提及旅行緣由:“終日里擾擾攘攘過著都市的生活,忒膩煩了。”①林夙根:《百泉記游》,《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12 號,第39—43 頁。居于北平的去病更是直言:“凡是看過‘城市之夜’國產影片底人,大概多感覺到都市生活,是萬惡底窟穴,毀人底洪爐。”②去病:《定縣實驗區》,《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2 號,第7—14 頁。“居于滬上”的葉作舟亦因“久苦都市生活”,故而在友人邀其一同往游天目山時,“欣然諾之”。③葉作舟:《秋日登天目記》,《旅行雜志》1935 年第9 卷第12 號,第23—26 頁。同樣生活在上海的朱曼華也自稱是“對都市生活過得煩膩的人”。④朱曼華:《消夏勝地》,《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8 號,第8—9 頁。故而,在談及個人出游動機時,不少游記作者均坦言因“煩膩”城市生活而產生了“逃離”的迫切愿望。從時間角度而言,此種“逃離”并非永久性地舍棄城市生活回歸鄉野,而多為暫時性的躲避,主要是試圖通過休閑旅行的方式驅散心中“煩膩”“苦悶”的情緒;從空間角度而言,通過休閑旅行“逃離”城市的所去之處,并非僅限于與城市相對的鄉村和田園,只要是非慣常生活環境即可,既包括鄉村亦包括其他城市空間。
(一)逃離城市嘈雜和煤煙空氣
城市知識群體在游記中多直言對城市喧囂的厭煩和逃離的渴望。1928 年,《旅行雜志》主編趙君豪就在《首都之游》一文中寫到:“余年來萍梗江南,卒卒鮮暇,喧囂城市,都無好懷。”①趙君豪:《首都之游》,《旅行雜志》1928 年第2 卷冬季號,第3—8 頁。表達了對城市喧囂生活的不滿。1930 年,居住在上海的秦燮源深感“草耕滬濱,久苦塵囂”,②秦燮源:《蘇錫四日記》,《旅行雜志》1930 年第4 卷第3 號,第41—44 頁。趙幼文在游覽青城山后返回成都時認為自己是“重入喧囂”,③趙幼文:《青城山之游》,《旅行雜志》1930 年第4 卷第9 號,第35—41 頁。的錚稱結束魯北旅行返回天津后又要過“醉生夢死的生活了”。④的錚:《魯北十日記》,《旅行雜志》1930 年第4 卷第11 號,第37—42 頁。30年代中期,城市喧囂更甚,繆鏞樓稱之為“市廛栗六,日處塵囂”,⑤繆鏞樓:《金蘭游記》,《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7 號,第17—19 頁。閻重樓無奈地寫道:“八年來我沒有離開過這煩囂的都市,對于那些能夠遠足旅行的人兒,當然存著羨慕和嫉妒的心哪。”⑥閻重樓:《陜行速寫》,《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9 號,第53—59 頁。
城市喧囂首先源于人口密集和空間狹小,擁擠和局促的感覺易使人產生厭煩情緒和逃離動機。20世紀上半期,城市化帶來城市人口的激增,由傳統的低密度生活空間轉入現代的高密度生活空間,城市居民因空間環境的突然“擁擠”而產生了心理焦慮和行為異常,催化了逃離城市的意愿。例如,30 年代初期生活在“東方第一大都市”的不少上海人認為“誰都感覺到生活上的苦痛”,這種苦痛是與鄉間生活比較而產生的,主要是因為空間的狹小,譬如鄉間住房十分寬大,而上海普通城市居民經濟能力有限,“幾家同住一幢,人聲喚鬧,污穢不堪”,“精神上也覺得痛苦得很”。⑦佚名:《都市生活的衛生方法》,《新民》1933 年第1 卷第11 期,第15—20 頁。1936 年,孫沛甘諷刺道:“上海的三部相——地狹、屋小、人眾——除了極少數的享受階級者外,格外的叫人覺得悚然。”⑧孫沛甘:《仲夏午之游——高橋海濱浴場印象記》,《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8 號,第3—6 頁。
在游記中,城市知識群體還常常提到逃離城市的另一原因,即逃離城市污濁的煤煙、煙塵或汽油味空氣。1932 年,暫居上海的祖雨人寫到久居繁華都市的人們每日只能“飽吸那充滿煤煙的空氣”,作者更因自己已居留上海三年有余,深感氣悶到極點,因而“一有幾天的空閑,總是拔起腳向上海的近郊游覽”。⑨祖雨人:《平蘆點滴》,《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7 號,第59—70 頁。自稱“服務于都市”的蕭亢石將都市生活和鄉鎮生活相比,深感“無上的枯寂,無聊”,“高巍的洋房,彌漫的煙塵,是都市的特有”,“在工廠林立的地方,空氣自然要遠遜于鄉間”。⑩蕭亢石:《從都市生活聯想到鄉村生活》,《上海民友》1932 年第61 期,第15—16 頁。1935 年,同樣居住在上海的赫森也寫道:“凡是喜歡吸些新鮮空氣的人們,大概久住在混合著煙煤汽油的空氣里的上海,沒有不覺得心地悒悒。”[11]赫森:《峭寒里的無錫》,《旅行雜志》1935 年第9 卷第2 號,第49—57 頁。空氣污染對身體健康有即時的影響,嚴重的空氣污染會使人頭暈眼花、頭痛、眼熱、咳嗽,這也與田園鄉村的新鮮空氣、寧靜氛圍形成鮮明對比,從而驅動城市居民渴望逃離城市而重返田園。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是中國城市的第二次變革期,由傳統城市向現代城市轉變,城市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功能凸顯,工廠數量劇增。根據1933 年《申報年鑒》統計:天津市有工廠2186 間,[12]天津庸報:《六大都市:天津市各業工廠及工人數》,《申報年鑒》1933 年年刊卷,第1137 頁。上海市工廠數為1887 間,[13]黃寄萍:《六大都市:上海市各業工廠及工人統計表》,《申報年鑒》1933 年年刊卷,第1096 頁。漢口市工廠數為165 間。[14]蕭勃:《六大都市:漢口市工廠統計表》,《申報年鑒》1933 年年刊卷,第1130 頁。此外,上海商號總數為72858 家,另有銀行65 家(包括總行在上海者、分行在上海者、專設上海者及外商及中外合辦銀行四類)、錢莊112 家。[15]黃寄萍:《六大都市:上海市銀行及金融機關調查表》,《申報年鑒》1933 年年刊卷,第1092 頁。在工業化、現代化潮流下,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和現代化公共交通體系的形成,所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就是對城市原有環境的破壞。正如時人所言:“科學之進步,表示機械萬能時代,工商業之發達,交通之頻繁,人口之稠密,嘈雜的都市與污濁的空氣,應時而生。”①佚名:《都市的嘈音》,《科學圖解》1934 年第1 期,第24 頁。
(二)逃離機械枯燥的工作
除外在的城市環境,城市知識群體試圖“逃離”的內在對象則是城市中機械、枯燥、程式化的工作。生活在近代中國最大都市上海的普通勞動者,此種感受最為明顯。30 年代初,蔣維喬稱自己赴海寧觀潮之游程的起因乃是友人湯愛理的提議:“吾曹平日困于筆墨,腦筋過勞,當此秋色晴明,正可往西湖盤亙數天。”②蔣維喬:《八堡觀潮記》,《旅行雜志》1931 年第5 卷第10 號,第45—46 頁。祖雨人也認為,久居繁華都市的人,每日除了“去作那例行的機械工作之外,可還哪里再找得出人生的真意味來呢”,于是趁著四日休沐閑暇前往新倉游玩。③祖雨人:《平蘆點滴》,《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7 號,第59—70 頁。1936 年,伯樂在《青陽港記游》中寫到,在江南初春萬物生趣盎然之時,生活在上海的人們所感到的卻是“煩囂,枯悶,惡濁”,作者解釋導致這般不快的因素乃是“坐在辦公室的我們,整日埋頭思索,振筆急書,忙得吐不出氣來”,并訴說對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樂趣的無限向往。④伯樂:《青陽港記游》,《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3 號,第25—31 頁。
此種逃離城市繁復枯燥工作的渴望并不僅限于上海,而是城市知識群體的普遍心態。例如,30 年代初生活在天津的汪季文因深感“終歲碌碌,埋頭案上”之枯悶,“深欲登山涉水,一滌凡塵”。⑤汪季文:《舊都四日記》,《旅行雜志》1931 年第5 卷第8 號,第71—78 頁。隨后,他在另一篇游記中亦寫到:“我們完全恃工作來生活的人,換空氣在身心上比闊人們尤其是需要”,因而在春假中“照往年的成例”,仍去北平游覽了四天。⑥汪季文:《北平經濟游》,《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11 號,第59—62 頁。同樣,生活在北平的張士清因公務繁忙,雖對近在咫尺的北平湯山溫泉“神往久矣”,卻始終未得一游,后因友人沈元熙等組織湯山溫泉旅行團而相偕前往,游后深覺“蕩滌襟懷,庶使精神振奮,于事務身心,兩有裨益也”。⑦張士清:《游北平湯山溫泉記》,《旅行雜志》1933 年第7 卷第6 號,第59—60 頁。1934 年,生活在山西太原的淩宴池在游記中記錄了暮春三月“脫公務之羈絆”,與妻兒一同赴晉祠游覽的經過。⑧淩宴池:《游晉祠考録》,《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7 號,第59—62 頁。自稱“在京服務”的汪叔梅因感“終歲勞形案牘,亟思出游,以舒胸襟”,而在明知“途程遼遠,山徑險阻”的情況下,毅然單槍匹馬遠赴陜西之華岳游覽。⑨汪叔梅:《華岳記游》,《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9 號,第11—23 頁。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星期工作制度傳入中國并在城市中得到廣泛實踐,工作時間被程序化和固定化,“一般機關、公司、大商店、工廠等都有固定的工作時間”。⑩編者:《工作時間與閑暇時間》,《民生》1932 年第1 卷第8、9 期合刊,第1—2 頁。這種制度使城市工作者每星期七日中有六日均處于從早到晚的忙碌工作狀態,僅有星期日一天的閑暇時間,工作時間與閑暇時間逐漸分離,而且每日工作時間時有延長,工作負荷加大。例如,1930 年,國民政府內政部曾因蔣介石提議每日工作10 小時,而將工作時間由8 小時延長至10 小時,結果卻被認為是“利無而弊大”。[11]音青:《內政部實行十小時工作之結果》,《生活》1930 年第5 卷第50 期,第827 頁。又如,1934 年《山東省政府秘書處暨各機關各縣政府每日工作時間表》規定:上午辦公時間為7:30—11:30,下午為13:30—17:30,共計8 小時。[12]《令發工作時間表仰遵照(附表)》,《財政旬刊》1934 年第12 卷第1 期,第3—4 頁。如果說政府機關尚能遵守八小時工作制,那么私營單位就未必能夠如此了。同年,《民眾教育》報館曾在其刊物內刊登《本館消息:工作時間加長》的通知:“各機關辦事時間,每天照例是八句鐘,本館同志因為矢志民教,犧牲精力起見,向來工作時間均為九小時。現在因為季節關系,天候較長,又因暑假開始,城市休學青年日多,每日來館者日多,故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每日辦公時間,上午為八至十二時,下午為一至七時。”[13]念滫:《本館消息:工作時間加長》,《民眾教育》1934 年第1 卷第1 期,第42 頁。可見該報館的每日工作時間由原來的8 小時先后延長至9 小時和10 小時。1936 年,自稱是“小學里一個高年級級任教師”的劉社延在《小學老師的希望——八小時工作》中,詳細記錄了其一天由早晨7 時起至晚上12 時止的超負荷工作,以至于因為“每周要做教學報告,每學月要出測驗題,看測驗卷,有時學校里在晚飯后開會”,使得作者無形中增加了工作時間,以至“遇到星期例假,也要像坐牢樣坐在屋內批改簿本”,并且這種生活是“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以后日日如此”,“我固如此,他也是如此,同事都是如此”,由此作者特地撰文提出“八小時工作”的要求,并自嘲這暫時只能算是一種希望。①劉社延:《小學教師的希望——八小時工作》,《中國出版月刊》1936 年第6 卷第2 期,第11—14 頁。正如一位旅行者所言:“處都市者,每限于職業,不能恣情山野。”②高事恒:《雁蕩巡禮》,《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11 號,第17—23 頁。
可見,星期工作制的實施及工作時間與閑暇時間的分離,催生了城市知識群體在假日中逃離城市以暫時性地擺脫工作束縛、釋放持續工作壓力的動機。然而,“職業”“工作”既是推動城市居民逃離城市的促發因素,又是影響其逃離城市的制約因素。
二、尋求愉悅:因“性本好游”而“借地消遣”
在民國中期《旅行雜志》所刊載的國內游記中,作者主訴出游動機除消極被動地逃離外,亦有積極主動地溢出。此類動機主要體現在旅行主體因“性本好游”而選擇“借地消遣”,與在電影院、咖啡館等現代都市空間中的休閑活動本質相同,區別之處則在于是否與慣常生活環境產生較大空間距離。
(一)“性本好游”的內生動機和生活方式
民國中期,《旅行雜志》之游記作者均表示自己生性好游,樂于寄情山水。如珍重閣在游覽越溪時稱“生平所嗜,山水清游”,③珍重閣:《越溪記游》,《旅行雜志》1928 年第2 卷夏季號,第7—12 頁。俞劍華直言自己“性本好游”,④俞劍華:《雁蕩寫生記》,《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2 號,第15—24 頁。孫肖泉亦稱“余性素愛汗漫游”。⑤孫肖泉:《山西解縣之游》,《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3 號,第1—10 頁。30 年代初,張滌俗在游覽故都北平時寫到:“草草勞人,百感縈懷,念浮生之若夢,宜及時而行樂”,“彈鋏之余,輒喜作汗漫之游”,且將旅行視為“唯一消愁之事”。⑥張滌俗:《故都屐痕》,《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2 號,第25—34 頁。楊振岳亦表示:“余素以旅行為無上樂事。”⑦楊振岳:《成山記游》,《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8 號,第17—22 頁。如果說旅行是一件“樂事”,那么對此“樂事”的追求則是人之本性的一種體現。1928 年,趙君豪明言:“天下之樂,無過旅行。”⑧趙君豪:《首都之游》,《旅行雜志》1928 年第2 卷冬季號,第3—8 頁。30 年代初,高鳳紀在《廣西紀游》中寫到:“予生性好游,凡佳山水,輒向往之。”⑨高鳳紀:《廣西紀游》,《旅行雜志》1931 年第5 卷第7 號,第79—82 頁。方山在漫游塞外時寫到:“余性磊拓,喜遠游,好攝影,尋幽探勝,足跡遍南北。”⑩方山:《塞外漫游隨筆》,《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11 號,第57—64 頁。由上可見,對旅行本身的熱愛是民國中期城市知識群體主動出行的內生動機。
“性本好游”作為旅行主體的出游動機,久而久之便會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如游興甚濃的周瘦鵑稱:“每年春秋佳日,我總要鼓動游興,往杭州蘇州無錫那些地方去游一下子”,[11]周瘦鵑:《富春江上》,《旅行雜志》1928 年第2 卷春游特刊,第15—21 頁。“十載以還,每值春秋佳日,恒招邀俊侶,共作清游”。[12]周瘦鵑:《黃山紀游》,《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1 號,第50—54 頁。1932 年,王啟熙與友人乘船由上海出發,經過70 小時抵達廈門游覽,他稱此行的兩位旅伴“黃君小魯和石君明勛,也都是慣于旅行的”。[13]王啟熙:《廈門游記》,《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9 號,第45—52 頁。唐玉虬則“每值休沐日,蹤跡恒在西湖湖上諸山”,[14]唐玉虬:《諸暨採風記》,《旅行雜志》1933 年第7 卷第6 號,第63—69 頁。又利用杭徽公路沿途旅行,“蓋暇無不游,游無不暢”。[15]唐玉虬:《杭徽公路旅行記》,《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1 號,第47—51 頁。姜亦溫在1930 年春“尋食漢皋”期間,每逢星期休假“輒好漫游,客居兩載,游蹤殆遍”。[16]姜亦溫:《漢皋話舊》,《旅行雜志》1935 年第9 卷第7 號,第39—41 頁。1935 年,留學期間逢假必覽異邦山水的繆鏞樓自稱回國后亦“每當春光明媚,輒喜縱覽國內勝境,歲以為常”,[17]繆鏞樓:《寧臺七日游記》,《旅行雜志》1935 年第9 卷第7 號,第11—16 頁。可見作者利用閑暇時間外出旅行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二)“借地消遣”之娛樂新風尚
1932 年,《民生》雜志的編者曾言:“人類是愛好閑暇的,歡喜悠游自在,歡喜做隨心所欲的事。”①編者:《工作時間與閑暇時間》,《民生》1932 年第1 卷第8、9 期合刊,第1—2 頁。閑暇是一個時間概念,1899 年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指出,閑暇時間指人們除勞動外用于消費產品和自由活動的時間。②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26 頁。可以說,休閑的本質是自由,即可以自由地支配閑暇時間。星期工作制、休假制度以及國慶日等現代假日,給城市知識群體和市民階層提供了更多的休閑旅行和娛樂機會。
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娛樂活動始終是人們利用或打發閑暇時間的一種重要方式。民國時期,城市生活方式日趨現代化和多樣化,城市娛樂業亦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樓嘉軍在考察20 世紀初期上海城市娛樂體系的演變后,提出20 世紀20—30 年代是上海開埠以后經濟發展最繁榮的階段,上海城市娛樂發展呈現空前繁榮景象,具體表現為“娛樂部門齊全,娛樂場所眾多,娛樂樣式多元”。③樓嘉軍:《20 世紀初期上海城市娛樂體系的演變》,《歷史教學問題》2006 年第4 期,第12—19 頁。這種城市娛樂的繁榮景象并非上海所獨有,而是中國城市發展的一般趨勢和特點。1928 年,珍重閣介紹了紹興游覽區布業公所的繁榮景象:戲臺、茶肆、浴池、園林、京劇場、電影院等一應俱全,建筑為三層樓,“列坐擁擠”,夜市營業直至11 時許,作者自稱“游倦歸來”。④珍重閣:《越溪記游》,《旅行雜志》1928 年第2 卷夏季號,第7—12 頁。1929 年,南京社會局對娛樂場所之統計結果為:“室內游藝,計有清唱十九處,電影七處,說書三十六處,京劇二處,新劇一處,彈子房五處,聯合游藝二處;露天游藝,計有說書十一處,京劇二處,唱書十四處,書片六處,武術四處,提線戲二處,奇異動物三處,幻術一處,雜耍三處,共計一百一十七處。”⑤《社會消息:娛樂場所之統計》,《首都市政公報》1929 年第48 期,第31 頁。1934 年,《申報年鑒》曾統計天津市娛樂場所數,計有球社4 家、跳舞場2 家、電影院12 家、舊劇劇院6家、茶園8 家。⑥天津庸報:《申報年鑒》1933 年年刊卷,第1144 頁。雖較上海稍遜一籌,但新式娛樂設施的逐漸擴展是民國中期的一種趨勢。
在城市娛樂方式和種類多元化的潮流下,在“新式交通出現以后,舒適快捷的旅行方式代表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⑦聞虹、曲曉范:《民國時期鐵路旅行指南與旅游地空間結構的嬗變——以環渤海區域為中心(1912—1937)》,《歷史教學問題》2019 年第1 期,第60 頁。加之新式旅館的建成、旅行服務機構的設立等諸多客觀保障條件的完備,城市居民的娛樂活動范圍得以大幅度擴展,休閑旅行逐漸成為大眾娛樂的一種新風尚,尤其受到城市知識群體的熱切追捧。早在1925 年,江亢虎一語中的:“旅行即娛樂也。”⑧江亢虎:《旅行與娛樂》,《商旅友報》1925 年第20 期,第31 頁。《京報》副刊曾刊登《國慶日的娛樂》一文,列舉北平市居民在國慶日假期的娛樂活動,包括“去逛公園,去逛北海”,“去登八達嶺”,“到湯山洗澡”,“打雀牌依然八圈”等,⑨余上沅:《國慶日的娛樂》,《京報副刊》1925 年第294 期,第13—15 頁。可見逛公園、泡溫泉、游覽名勝已成為市民階層的休閑娛樂新風尚。
此外,在《旅行雜志》刊載的國內游記中,作者亦較多地記錄了旅途中目睹的各地休閑旅行之興盛景象,此種景象無一例外都發生在當時的主要城市及其周邊游覽勝地,“借地消遣”之人絡繹不絕。1927年,一帆在描述游覽蘇州虎丘所見的景象時稱“山塘虎阜一帶,游客如云”。⑩一帆:《虎丘游記》,《旅行雜志》1927 年第1 卷夏季號,第46—49 頁。李申秾在游覽蘇州時寫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風景的美麗是享有悠久的盛名的。外埠到蘇州來游覽的人,年以萬記。”[11]李申秾:《記洞庭西山之勝》,《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6 號,第29—32 頁。趙君豪在《莫干山小記》中記述:“比年以來,國人每于夏期避暑海濱或清涼之山中,若青島北戴河牯嶺一帶,往游者絡繹于途。”[12]趙君豪:《莫干山小記(消夏名區之一)》,《旅行雜志》1927 年第1 卷夏季號,第29—40 頁。1931年,汪季文在與妻子及友人赴北平游覽故宮時,聽聞“游人總數,據收票者統計,約有一千二百余”,隨后赴游中山公園,夕陽之下,又見“游人如過江之鯽,或攜情侶,或邀友朋”。[13]汪季文:《舊都四日記》,《旅行雜志》1931 年第5 卷第8 號,第71—78 頁。30 年代中期,馮植芳因海珠橋的建成,“由廣州市起程,過河南大約行個把鐘即到漱珠崗”,途中見“往游者紛紛,紅男綠女,結隊成群,大有游客如云之象!”①馮植芳:《漱珠崗游記》,《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8 號,第39—43 頁。
三、“再造身心”:城市知識群體休閑旅行的補償與療愈功能
民國中期《旅行雜志》的游記作者群體,雖然在休閑旅行記錄中聲稱他們對城市喧囂、擁擠環境和煤煙空氣十分厭惡,時時表現出逃離城市的愿景,但他們所尋求的絕不是長期隱居田園的鄉野生活,而是通過暫時性的逃避來緩解或補償城市生活的壓力,即通過休閑旅行獲得內心的愉悅從而實現身心補償功能。
早在1922年,姜子榮就對作為外來語的“recreation”一詞有獨到的見解:“英文娛樂recreation這個名詞,就是re-create恢復疲勞——心理的和生理的——再造身心的意思。”②姜子榮:《教師的娛樂》,《中華教育界》1922 年第12 卷第3 期,第1—11 頁。1931年,小芳在游覽北平西山后稱:“這個旅行,使我過于快樂了”,因為旅行的快樂既來自“身體的鍛煉”,又來自“精神的修養”,故而感慨“旅行,真是一件最高尚的消遣”。③小芳:《雪后游西山》,《旅行雜志》1931 年第5 卷第3 號,第25—29 頁。1936年,高梧軒在《西蓮峰下送殘春》中寫道:“以勞人草草,就海上行役之繁,遂至日共囂塵,無由擺脫”,作者之應對良策即“十年以來,一臨盛夏,即謀旅游,用資習靜”,因而牯嶺、青島、莫干山、普陀山,“幾乎無不一再流連,襟痕波影,相與縈洄矣”。④高梧軒:《西蓮峰下送殘春》,《旅行雜志》1936 年第10 卷第7 號,第3—15 頁。
對民國中期的城市知識群體而言,逃離城市喧囂的休閑旅行是一種使人忘卻煩惱、親近自然的途徑。1927 年,戴欲仁記述到普陀山昔日交通不便,“除進香之善男信女外,絕少游其地者”,但輪舶的通行誘使游客接踵而至,每逢夏季均有中外人士前來避暑,以至“森嚴僻靜之佛地,將一變而為旅行者必游之地,亦為久處空氣惡濁繁盛都市之人,調節生活之地矣”。⑤戴欲仁:《普陀游記(消夏名區之一)》,《旅行雜志》1927 年第1 卷夏季號,第41—45 頁。陳慧一在感覺城市生活“煩囂愁困,中人欲死”時,“差幸得間赴莫干山小駐旬日”,由此“一暢胸襟”。⑥陳慧一:《重游莫干山記》,《旅行雜志》1928 年第2 卷秋季號,第13—18 頁。1932 年,陸丹林看到廣州白云山“逢著星期例假,游人很多”,作者也在游覽期間看著滿山矮松、聽著枝頭鳥語和游人談笑的聲音,認為此情此景“和那繁忙的都市比較起來,簡直是人間天上”。⑦陸丹林:《南歸雜憶》,《旅行雜志》1932 年第6 卷第5 號,第1—5 頁。1935 年,徐珊在《浙東山水歷目記》開篇即寫到:“生在都市里,長在都市里的人們,只要有機會,沒有不想到山水勝處”,因為這不僅可以領略大自然的美麗,更可以“洗滌積滯在胸襟的渣滓”。⑧徐珊:《浙東山水歷目記》,《旅行雜志》1935 年第9 卷第4 號,第13—27 頁。
被標準化的時間表支配,再加上單調、機械、高壓的城市工作,城市生活有時會令人有絕望之感,所以要有身心的休息和調節,使體力有所恢復和增長,精神有所寄托和轉換。利用余暇時間短暫地休閑旅行,便成為一種工作補償的有效手段。20 世紀30 年代初,陳存仁因應世界書局之約編寫《中國藥學大辭典》,“搜集標本,參考古籍,征求意見,撰述文稿,四年以來,幾無片刻閑暇”,而且作為醫生,他還須于每日日間照常應診,導致“精神大受損害,發生腦病,面黃力弱,痛苦已極”,作者“深知此病非藥石所能為力,決以旅行代藥餌”。⑨陳存仁:《華南旅行記(上)》,《旅行雜志》1934 年第8 卷第5 號,第5—16 頁。
綜上所述,民國中期的“黃金十年”提升了近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電影院、咖啡館、歌舞廳一樣,休閑旅行也成為城市新潮生活方式的象征之一。圍繞在《旅行雜志》周圍的有較為穩定收入且有相對集中閑暇的城市知識群體,其記述語境呈現“現代化敘事”傾向。⑩孫遜:《虛構的貧窮——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經濟身份認同》,《歷史教學問題》2018 年第3 期,第40 頁。外在的城市環境壓力和內在的工作壓力共同催生了城市知識群體逃離慣常城市生活環境而外出尋求消遣之休閑旅行動機。從心理預期和現實成效上看,休閑旅行既可逃避城市喧囂環境和繁復枯燥工作,又可通過異地游覽而尋求愉悅。逃避喧囂與尋求愉悅,二者相輔相成,使城市知識群體在現代生活中的身心困境和角色負荷獲得補償和解放。休閑旅行是民國城市知識群體在應對城市化和職業化壓力以及追隨現代生活方式時采取的身心均衡策略,是一種現代性的身體形塑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