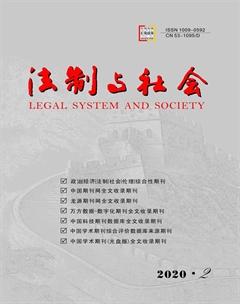夫妻忠誠協議的可訴性
李浩宇
摘要 當今社會,婚姻家庭觀念受到利益至上觀點的強烈沖擊,故而實踐中出現多種忠誠協議以維護婚姻的穩定。而我國現行法對忠誠協議的效力問題進行了回避,導致實務中對忠誠協議是否可訴產生較大分歧。忠誠協議作為當事人之間真實的意思表示,理應納入法院的受案范圍。本文將從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角度分別論證其可訴性。
關鍵詞 夫妻忠誠協議 身份協議 財產協議 可訴性
中圖分類號:D92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019
一、忠誠協議可訴性問題的源起
2002年上海市閔行區法院做出一份承認“夫妻忠誠協議效力”的判決將夫妻忠誠協議拉入到大眾視野之中。顯然這只是問題的開始,在一年后,上海高院出臺的民事法律適用問答中明確了這樣一種觀點,“《婚姻法》第四條的‘忠實義務只是一種道德義務而非法律義務,夫妻一方以這種道德義務為對價與另一方簽訂的協議,不能認定為確定具體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故而,夫妻一方僅以對方違反忠實協議為由,起訴要求對方履行協議或支付違約金及賠償損失,法院對此不予受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高院否認了忠誠協議的可訴性,認為單獨對夫妻忠誠協議起訴的案件以及在離婚案件中附帶提出以一方違反夫妻忠誠協議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請不予受理。
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此態度并不統一,上海高院的觀點并不代表全國法院的通常做法。北京、河南、廣東等地更傾向于承認夫妻忠誠協議的效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將其納入法院的審理范圍。在這種大前提下,法院單獨對夫妻忠誠協議進行審理的情形也較為少見。筆者通過在北大法寶上運用關鍵詞“夫妻忠誠協議”進行檢索發現,在司法實務中,忠誠協議一般是在夫妻雙方起訴離婚之時附帶作為賠償請求的證據提出,一方當事人可能會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或者協議內容限制人身自由等理由對該協議的效力進行否認,在此時忠誠協議作為一項賠償與否的證據被納入法院的審理范圍中。
由此可見,夫妻忠誠協議單獨起訴是否予以受理在現階段仍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應當明確將夫妻忠誠協議納入法院的受案范圍,賦予其單獨可訴性,以維護當事人之間的信賴利益。
二、承認忠誠協議可訴的現實困境
不可否認的是,承認忠誠協議具有單獨可訴性在我國確實存在一些一定的困難。
首先,我國對于夫妻忠誠協議缺少立法上的規制。現行婚姻法中對夫妻間的忠實義務僅進行了原則性規定,并未如法國、瑞士等國明確了夫妻一方違反忠實義務的后果,由此,不僅導致忠實義務成為一紙空文,受損害方無法從該條文中得到救濟,而且使得學界對忠實義務的定位也產生了分歧。
其次,在學理上,從前文對夫妻忠誠協議效力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有部分學者認為,夫妻之間相互忠實是一種道德義務,法律不應當對此進行規制,否則有過度適用法律之嫌疑,從而將夫妻忠誠協議在法院的受案范圍之內排除。從上海高院的民事法律適用問答中可以看到,法院內部也存在這種擔憂。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是反對忠誠協議具有單獨可訴性的主要理由。
最后,在司法實務中,有法官認為,目前法院受理的關于忠誠協議的訴訟不多,一旦最高院規定對忠誠協議予以受理,將大量增加法院的工作量,甚至助長捉奸行為,敗壞社會風氣。
三、我國忠誠協議的可訴性論證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實體法的角度出發還是從程序法角度的衡量,夫妻忠誠協議都應當被賦予單獨可訴性。
(一)實體法層面
支持忠誠協議具有單獨可訴性的學者主要從忠誠協議的目的出發,認為忠誠協議是為了維護婚姻關系的穩定而產生的,如果否認其單獨可訴性,認為只有在進行離婚訴訟時方能對其進行審查,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當事人的離婚自由。筆者贊同這種觀點,忠誠協議應當被賦予單獨可訴性。“存在即為合理”,夫妻忠誠協議的本質歸根結底還是在物欲橫流的今天,弱勢一方對婚姻關系的穩定、維護自己的權益所做出的一種努力,是一種挽救破碎婚姻的手段。誠然目前對忠誠協議的單獨可訴性仍未有定論,但若按照反對學者以及一些法院的做法,對僅以忠誠協議為訴訟請求的訴訟不予受理,顯然違背了忠誠協議誕生的最初目的。甚至在只有離婚時才能對忠誠協議進行受理的大背景下,一些當事人可能會在一種不冷靜的情況下或者“被迫”直接提起離婚之訴。
其次,關于夫妻間的忠實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從而將其排除在法院的受案范圍之外的觀點,筆者認為,姑且不論忠實義務到底如何定性,究竟是一種道德義務還是法定義務,即使將忠實義務看作是一種道德義務,但此時當事人通過協議將這種“虛無縹緲”的忠實義務固定下來,從而具有可履行性;在此,忠實義務已經轉化為協議中所要求的當事人雙方具體之行為,不再受“道德義務”的桎梏,也即是說,當事人通過協議約定,將這種道德義務變更為對雙方的一種意定義務,應當可以直接適用民法總則中以及合同法中關于無名合同的相關規定。
最后,關于一些法官對承認忠誠協議單獨可訴性后法院工作量的擔憂以及社會風氣可能的走向。筆者認為,法官從法院系統內部人員的角度出發,這種憂慮是有一定道理的。現今,當事人單獨提起關于夫妻忠誠協議的訴訟,多數法院會選擇不予受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法院內部的工作量。然而,僅僅因為法院系統工作量的增加而剝奪公民的訴權,顯然有失偏頗,同時也有違憲法精神。我國司法系統內部正在進行體制改革,其也有解決“案多人少”之初衷,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下,這種情況勢必有所改善。至于捉奸行為增加,敗壞社會風氣這一論調,實屬杞人憂天。捉奸的現象從古至今一直存在,即使因為忠誠協議具有單獨可訴性之后而導致捉奸行為的增加,其原因也不能歸根于忠誠協議。如若不是違約方先違反雙方的協議約定,又何來捉奸行為呢?敗壞社會風氣的也是違約一方造成的。忠誠協議具有單獨可訴性后,反而增加了忠誠協議對雙方的約束力,更好的維護婚姻家庭生活的穩定,不存在敗壞社會風氣一說。
(二)程序法層面
起訴的高階化是我國目前在案件受理層面最突出的問題,之前所進行的立案登記制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法院在審查當事人的訴求能否進入法院審判環節時仍然依據相關的訴訟要件進行判斷。由于篇幅受限,筆者對此不予討論,僅分析在現行起訴條件下,夫妻忠誠協議能否被法院受理。
現行法中規定的起訴條件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和一百二十四條,其中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了起訴的積極條件,第一百二十四條則是起訴的消極要件。對于第一百一十九條中的“直接利害關系”如何認定,肖建華教授認為,應當解釋為原告在起訴時需證明自己因訴訟可能獲得的“利益”。
從這一角度分析,針對夫妻忠誠協議進行訴訟的案件原告在起訴時需要證明自己由此可能獲得“利益”。筆者認為,只要忠誠協議的標的具有可履行性,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和公序良俗,一方就可以通過提起忠誠協議之訴獲得可期待利益。如果是一種金錢之債,原告可能會因為被告的違約獲得相應的賠償;若是非金錢之債,則首先需要判斷協議的內容是否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范以及公序良俗,防止一方借忠誠協議之名侵犯另一方的人身自由權、配偶權等合法權利,如果有違反,此時應當允許忠誠協議進入訴訟程序,在訴訟系屬中被宣告無效;若協議內容合法且未違反公序良俗,此時這種忠誠協議可能涉及的是當事人雙方的某種行為,如前文所述以“家務”為對價的忠誠協議,這種忠誠協議應當也屬有效,但出于涉及當事人的自由安排同時這種標的很難進行強制執行,其更多的是出于當事人的自愿履行,因此對此種類型的忠誠協議應當排除其可訴性。
簡而言之,夫妻忠誠協議具有單獨可訴性,但同時應對其有所限制,即協議標的屬于合法的非金錢之債的忠誠協議,由于在強制執行上存在困難且屬于當事人對自己的生活安排,應當將其排除在訴訟程序之外。
四、結語
婚姻不僅是為了滿足愛情的需要,其還有更重要的、至少是與其同等重要的社會功能⑥。故而,婚姻生活的安定不僅關系著每個家庭的和諧,還事關社會的穩定。將夫妻忠誠協議納入法院的受案范圍,不僅為缺乏安全感的婚姻注入穩定劑,也有利于社會的平穩運行。與此同時,法院在立案階段需要進行個案衡量,對于明顯不應當立案的忠誠協議及時將其排除在訴訟系屬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