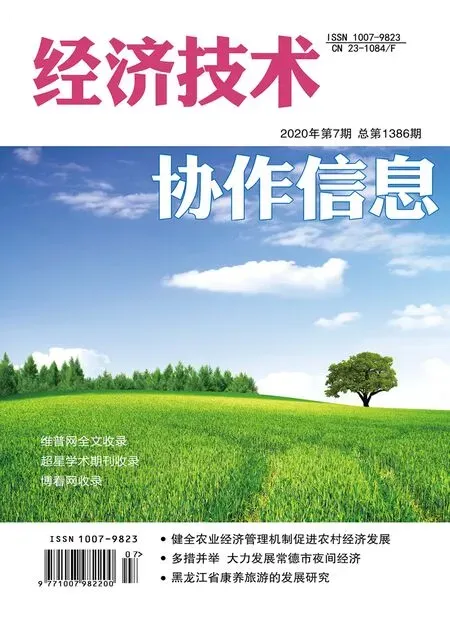莫言小說《紅高粱》的民間敘事研究
◎趙琦潔
一、紅高粱家族的想象與重構
莫言認為他的創作完全是虛構的,從主觀意識形態的角度去看,但也可能是作者真正的創造性現實。所以陳思和教授評價《紅高粱家族》,“它以虛擬家庭記憶的形式使用所有油墨來描述土匪指揮官余占鰲為首的組織的民間武裝力量,以及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各種故事。”[]作品中的令人難忘的對紅高粱描寫的場景,還有小說中的“余占鰲”與奶奶之間的愛恨交織、陰險狡詐的冷麻子隊和愛耍小聰明占便宜的江小腳隊、正義卻死得荒謬的任副官,這些人物之間的故事都涉及作者的想象,小說中,大量的地方由本土文化風格的修飾語、修辭方式來表達高粱的場景,通過寫高粱的形式,聲音,影響和誘惑,使用這些豐富的詞語創造一種超越事物實際存在的氛圍和想象,給讀者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二、多面又矛盾的人物形象
小說中“爺爺”余占鱉的形象是很多面的而且有時又是相互矛盾的,他有時候的行為不會按照他的日常思維,一邊痛罵不守信用沒出現在戰場上的冷支隊為“狗”,一邊還是帶領所剩不多的兄弟們伏擊日本鬼子,盡管損失慘重,但還是血戰到底。莫言從一般的人性的發展走向去預測了小說人物性格的發展趨勢,從而即使是在想象與重構的歷史敘事中,它也可以在整歷史背景下自由轉變作者的觀點,使言語意識形態的敘事更加文明,但跳出小說,作者是一位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修養,敘述者的所聞所說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官方歷史的影響,所以敘事語言是多方面的。小說中所描述的環境有些超出當地的真實形態,升華了高密東北鄉的人文和地理、當地習俗、小說里人物品質性情,它們夸張,極端和神秘,使小說的印象更加深刻和獨特。這樣敘事風格創造了很多經典場景,而且它也是基于真實風格的流派,只不過是讓場景的真實感受增添更加神秘和悲情的色彩。
《紅高粱家族》對余占鰲這個人物的刻畫一直以一種高調的贊美的風格,以第一人稱“我”的崇拜語調襯托著,但有時候也會不經意間出現擔憂的情緒。這里所反映的不僅是余占鰲心中的憂傷與困惑,還有“我”的迷惘。在現在的更合理文明的社會中,規章制度也更多,余占鰲殺和尚的理由也已經站不住腳。殺和尚這段,“我”這個敘事者不再出現,而是余占鰲的視角,應該是敘事者在這件事上選擇逃避的做法,那為什么會選擇逃避,顯然是敘事者對那個世界的一直憧憬與向往,所以不會選擇以現代的視角去評判。
三、民間文化的敘事方式
《紅高粱家族》這本小說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首先從他敘事的角度來說的話,這本小說大部分的視角都是“我父親”這個視角,以“我父親”為敘事人去回憶爺爺那輩人的生活,一下子就讓讀者們進入到了那個年代,其實,那個年代是充滿苦難,充滿未知,充滿悲情的一段日子,但是當時父親的年紀小,以他的角度去看的話,至少會把現實世界的一些復雜的東西變得更加單純。
此外小說中關于時間的敘事,也是別出心裁。全文的大致脈絡是在講述爺爺余占鰲的傳奇的一生,但是中間也有采用倒敘,插敘等方式,讓這個故事更加的生動,也為了不讓讀者在讀的時候感到枯燥,開頭直接寫爺爺帶著父親去打仗,一下子就吊起了讀者的心,在行軍的過程中,作者也借機介紹高粱地的周圍的環境,讓讀者們大致對高粱地這個有了最基本的了解,這里是展開這些故事的地方,其中穿插了日本人對羅漢大爺的殘忍暴行,通過作者細致的描寫,讀者們也能更為直觀地感受當時戰亂中低層人民的苦難。
小說里的人物幾乎都具有類似于這樣的善與惡,甚至是連出鏡率不高的余大牙身上也同樣具有這樣的復雜性,他既是能對未經世事的小姑娘行污穢之事的混蛋,但在臨死之前也表現出了不怕死的硬漢形象,所以莫言筆下的這些民間人物的性格都是具有兩面性的。不難發現《紅高粱家族》中的人物都是具有很強烈的性格特征,紅高粱的主題也是要弘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作者為什么那么強烈的要突出這些人物的性格,無疑應該是為了喚醒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那些枯萎的生命力,萎靡的生活狀態的那些人,借那個年代自由自在,充滿活力激情的民間鄉土生活,來點醒現實中裝睡的那些人,小說中那些激烈的殘忍的畫面,就是為了不去逃避和超越所謂的憐憫,去崇尚生命的強力和贊美個性生命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