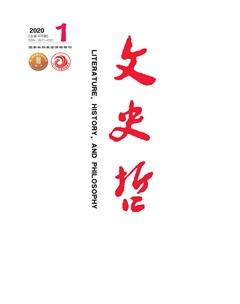行走的書簏:中古時期的文獻(xiàn)記憶與文獻(xiàn)傳播
于溯
摘要:在東漢到唐的幾百年間,物質(zhì)文獻(xiàn)因紙張逐漸代替竹帛而發(fā)生重大變革,與之同步發(fā)生的另一個重要的文獻(xiàn)史現(xiàn)象是,文獻(xiàn)記憶極度興盛,記憶成為紙張之外另一種重要的文獻(xiàn)載體。由文獻(xiàn)記憶形成的“記憶本”,被當(dāng)時人視為版本學(xué)意義上的文獻(xiàn)形態(tài),它全套移植了寫本從制作到校勘各個步驟的概念,并可以與寫本自如互校。記憶本較寫本更為易得、易讀、易檢、易攜,它迫使物質(zhì)文獻(xiàn)不斷自我改進(jìn),以期盡可能模擬到記憶本之優(yōu)長,使讀者從記誦中解放出來。文獻(xiàn)記憶和物質(zhì)文獻(xiàn)共同參與了中古文獻(xiàn)的形成和流通,中古文獻(xiàn)史的面貌,要比學(xué)界過去認(rèn)識的更加復(fù)雜。
關(guān)鍵詞:文獻(xiàn)記憶;記憶本;書籍史;文獻(xiàn)史;寫本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1.12
作為人類本有的一項生理功能,記憶力深刻地參與了人類文明進(jìn)程。誕生于各文明早期的神話故事曾憑藉記憶口耳相傳,在古印度,佛教經(jīng)典也長期通過口誦流布。古希臘人甚至已經(jīng)有了系統(tǒng)訓(xùn)練記憶的技藝,這種技藝后來受到羅馬演說家的大力推崇,他們將“記憶術(shù)”列為古典修辭學(xué)的一部分,還奉希臘詩人西摩尼得斯為記憶術(shù)的發(fā)明者。但是,隨著書寫和文獻(xiàn)制作技術(shù)的逐漸發(fā)達(dá),是用記憶來承載和傳播文明,還是用文字、文獻(xiàn)來承載和傳播文明,人們有了兩種選擇。既然記憶作為知識和信息的一種載體,在功能上和文獻(xiàn)是有所重疊的,它與文獻(xiàn)的關(guān)系就成了一個經(jīng)久不衰的話題。柏拉圖在《斐德若篇》中就假借埃及法老塔穆斯之口說,文字會導(dǎo)致人們善忘,因為人一旦學(xué)會文字就不再努力記憶了。這種記憶與文獻(xiàn)對立競爭的觀念影響至今,比如文藝復(fù)興史學(xué)者葉芝認(rèn)為,記憶技藝的衰落正是緣于印刷書籍“摧毀古老的記憶習(xí)慣”,阿萊達(dá)·阿斯曼在研究記憶史時也表示,那既能放在書里的,就不必放在腦中,記誦的衰落“正與外在于人體的功能強(qiáng)大的知識存儲器飛速增長的容量相對應(yīng)。”
從一個長時段的視角看,人體外的知識存儲器最終戰(zhàn)勝有生理局限的人體本身,無疑是確然的;但是在每個具體的時空中、在特定的文化觀念和歷史情境下,文獻(xiàn)和記憶的關(guān)系還遠(yuǎn)非那么簡單。印度佛教一度依賴口誦傳教,據(jù)說就是因為那里的學(xué)者和哲學(xué)家看不起文字。中國文化對文字和書寫極度推崇,漢字擁有神圣的起源故事,書寫擁有高于口說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敬惜字紙觀念,但背誦作為一種特殊的記憶與文獻(xiàn)的結(jié)合方式,也長期受到不亞于物質(zhì)文獻(xiàn)本身的重視。在《金石錄后序》那個著名的片段里,李清照這樣描述她和丈夫的日常生活:“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fù),為飲茶先后。”——那能放在書里的,不但也要放在記憶里,而且是連書一起放在記憶里的。
“文獻(xiàn)記憶”是記憶的一個獨(dú)特的分支,它是以記憶的老對手——文獻(xiàn)為對象的記憶,是以字句為元素的記憶。這種記憶活動只能發(fā)生在文字出現(xiàn)后,也只能發(fā)生在識字并能接觸到書的人身上。在不同的文化或時代中,文獻(xiàn)記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即以對文獻(xiàn)記憶的指稱為例,至遲在中古漢語中,已經(jīng)有“諷”字表達(dá)“記憶文獻(xiàn)”(“倍[背]文日諷”);而在英語中就很難為“背文”找到一個對應(yīng)單詞,只有長詞組“word-for-word/line-for-line repetition"能描述它。擁有專稱,這是文獻(xiàn)記憶在古典中國文化中相當(dāng)被關(guān)注的一個體現(xiàn)。另一個有趣的文化對照是,希臘人發(fā)明了“記憶術(shù)”,中國人則發(fā)現(xiàn)了“文獻(xiàn)記憶方”:“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陵陽子仲服遠(yuǎn)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方和專稱一樣,也說明文獻(xiàn)記憶得到了格外關(guān)注。而這種關(guān)注度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些時代的人比其他時代的人更關(guān)注文獻(xiàn)記憶,留下了更多關(guān)于記誦的故事。傅漢思在研究唐代正史之《文苑傳》時就發(fā)現(xiàn),在唐代史官們看來,“驚人的記憶力似乎是當(dāng)時文人不可缺少的特點(diǎn)”。事實(shí)上,這個特點(diǎn)既不限于文苑,也不限于正史,也不限于唐代。在中古時期的各種性質(zhì)的人物傳里、各種性質(zhì)人物的傳里,記誦能力都是常見話題,比如:
誦經(jīng)日萬言,過目則能。(《出三藏記集·竺法護(hù)傳》)
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晉書·苻融載記》)
初出身為領(lǐng)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lǐng)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暗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jīng)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宋書·吳喜傳》)
大眼雖不學(xué),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競不多識字也。(《魏書·楊大眼傳》)
經(jīng)目必記,歷耳不忘,求籍人間,閱書肆里,不知雨風(fēng),豈悟坑穿。(《魏張滿墓志》)
讀書數(shù)行并下,過目皆憶。(《梁書·昭明太子傳》)
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shù)遍而成誦在口。(《舊唐書·蔣義傳》)
“驚人的記憶力”并沒有特定的人物群體偏好,它可能發(fā)生在知識精英身上,也可能發(fā)生在胡人、武人、胥吏甚至不甚識字的人身上。這些記載唯一的共性是出現(xiàn)在中古時期,而清代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在“博文強(qiáng)記部”抄錄了清以前106個文獻(xiàn)記憶故事,其中中古時期的就占到了71個。同樣產(chǎn)生于這一時期的《抱樸子》中出現(xiàn)誦書仙方,絕非偶然。可以說,中國文化之格外強(qiáng)調(diào)文獻(xiàn)記憶,這個特點(diǎn)正是在中古時期形成的。
但問題是,在物質(zhì)文獻(xiàn)史上,中古時期正是紙代替竹帛、書寫越來越便利、書籍越來與豐富的時期,文獻(xiàn)有了更好的、更多的物質(zhì)載體,為什么反而更需要記憶這個載體?為什么記誦高手在這個時期的史料中井噴式地出現(xiàn),而不是在文獻(xiàn)流通更艱難的古代,或者接觸書籍機(jī)會更多的雕版印刷時代?
一、文獻(xiàn)記憶:文獻(xiàn)還是記憶?
支配文獻(xiàn)記憶行為的是文獻(xiàn)記憶觀念,后者同樣是隨時變化的。比如體現(xiàn)在計量方式上,今天人們說背誦一篇文章、一段課文、三百首唐詩,計量單位(篇、段、首)多是根據(jù)文本內(nèi)容設(shè)定的。而前引《抱樸子》收錄的背誦仙方中,有一道藥效是“日視書萬言”,“言”(字?jǐn)?shù))作為記誦單位今日已罕有使用,在中古時期卻相當(dāng)常見,比如:
(司馬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shù)十萬言。
(李郱)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余萬言。除了“言”以外,“紙”也常常用來衡量記誦量:
姚主即以藥方一卷,民籍一卷,并可四十許紙,令其誦之三日,便集僧執(zhí)文請試之。乃至銖
兩、人數(shù)、年紀(jì),不謬一字。
(長孫紹遠(yuǎn))年甫十三……讀月令數(shù)紙,才一遍,誦之若流。
兄敬嗣,時因稟訓(xùn),讀《上林賦》于前。太妃一覽斯文,便誦數(shù)紙。
屬顏魯公許試經(jīng)得度,時已暗誦五百紙。比令口諷,一無差跌,大見褒異。
字?jǐn)?shù)和紙張數(shù)都與文本內(nèi)容無關(guān),而與物質(zhì)文獻(xiàn)的視覺樣態(tài)有關(guān)。而且,它們其實(shí)也是中古時期寫本制作的計工單位。用字?jǐn)?shù)和紙張數(shù)計量背誦量,說明在當(dāng)時人的觀念中,文獻(xiàn)記憶與物質(zhì)文獻(xiàn)有相當(dāng)?shù)耐|(zhì)性。可以說明這種同質(zhì)性的另一個例子是,《漢書·藝文志》著錄小說家時特別強(qiáng)調(diào)其口語記憶的源頭(“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而且這個源頭與小說被置于諸子十家之末且獨(dú)被著錄者評日“不可觀”有直接關(guān)系;但是《漢志》著錄伏生本《尚書》,并不因其來自文獻(xiàn)記憶而區(qū)別視之。寫出記憶中的非文獻(xiàn)內(nèi)容和寫出記憶中的文獻(xiàn)性質(zhì)截然不同,對后一個行為,“來源于記憶”這一點(diǎn)被完全忽視了。這也說明,文獻(xiàn)記憶在當(dāng)時更多地是被從文獻(xiàn)而不是記憶的角度來認(rèn)識的,它的產(chǎn)物作為一種虛擬書籍,與實(shí)體書籍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不過一個是儲藏在體內(nèi),一個是在篋中而已。
人體能夠成為書籍的儲藏地,這種觀念也在當(dāng)時的很多言論中有所體現(xiàn)。漢末的趙壹在《刺世疾邪賦》中寫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世說》載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對日:“我曬書。”東魏的崔慢被人稱贊“胸中貯千卷書”。文籍滿腹、曬腹曝書、胸中貯書,這種描述方式就和早期文獻(xiàn)中的“多識前言往行”(《易·大畜》)、“博聞強(qiáng)識”(《禮記·曲禮》)、“前事之不忘”(《戰(zhàn)國策·趙策》)之類不同,落腳點(diǎn)在人體與書,而不是記憶與知識。更直觀的例子是,漢唐史料中常可見“書笥”“書廚”“書簏”“書箱”“書庫”“書篋”一類人物綽號,還有人被稱為“皮里晉書”“皮里陽秋”,被稱為“肉譜”,乃至有被完全取締了“肉”的存在而直呼為“人物志”的。這些綽號無論褒貶立意何在,它們能以這樣的面貌出現(xiàn),都基于人可以作為書籍儲藏地的認(rèn)識。而這種認(rèn)識,與以字?jǐn)?shù)、紙張數(shù)來計算記誦成果,是相互吻合的。
如果人體是書籍的儲藏地,那么文獻(xiàn)記憶的行為,就是為書籍制作一個藏于此地的復(fù)本,這與抄寫一個復(fù)本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因此,制作“記憶本”的流程、要求,與制作寫本也是一致的。
文字準(zhǔn)確是制作寫本的核心要求。早期的文獻(xiàn)記憶,正如朱熹指出的,孟子憑記憶引據(jù)《詩》《書》每每有誤;漢人憑記憶授經(jīng)也常出現(xiàn)錯字,當(dāng)時并無一字不可差的要求。但在中古史料中,用“不差一字”“一無舛誤”描述文獻(xiàn)記憶已經(jīng)非常常見了,文獻(xiàn)記憶理論上應(yīng)與誦本嚴(yán)格一致,應(yīng)該正是在這個時期逐漸確立的準(zhǔn)則。
至晚在南朝后期,“不差一字”、“一無舛誤”的標(biāo)準(zhǔn)已經(jīng)不僅適用于書籍內(nèi)容,而且還適用于書籍的作者、書名、目次、版式等信息。據(jù)說當(dāng)時蕭勱能把《東觀漢記》背誦到“卷次行數(shù)亦不差失”的程度,而長于記誦的劉杳能準(zhǔn)確識別各種文獻(xiàn)片段的出處。文本與書名目次版式間的有效對應(yīng),使人體中的一部部書籍卷帙分明、互不混雜,就像它們的體外版本一樣。
南朝的藏書家們宣稱,抄書、藏書的目的是“備遺忘”,換言之,物質(zhì)文獻(xiàn)是作為“記憶本”的校本被收藏的。不惟物質(zhì)文獻(xiàn)可校“記憶本”,“記憶本”也可校物質(zhì)文獻(xiàn),《舊唐書》載唐玄宗見凌煙閣“左壁頹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隨行的蔣義認(rèn)出這些文字是圣歷中侍臣圖贊,“即于御前口誦,以補(bǔ)其缺,不失一字”。這就是以記憶本為校本的一個實(shí)例。
字字對應(yīng),不脫不訛,定名析卷,布置版式,最后以字?jǐn)?shù)和紙張數(shù)計算工作量,這本是制作寫本的相關(guān)概念,而文獻(xiàn)記憶也一一接受了。不僅如此,物質(zhì)文獻(xiàn)的校勘概念也被文獻(xiàn)記憶接受了。“記憶本”和寫本二者間可以自如互校,這更說明當(dāng)時人使用物質(zhì)文獻(xiàn)的制作和校勘概念去描述文獻(xiàn)記憶,并不是一種文學(xué)性的比喻,而是真正將“記憶本”視為版本學(xué)意義上的文獻(xiàn)形態(tài)。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時期人有將文獻(xiàn)記憶直接視為一種文獻(xiàn)的傾向。
二、記憶本及其特性
就像面對“選擇記憶還是選擇文獻(xiàn)”的時刻一樣,現(xiàn)在人們面對文獻(xiàn)也有了兩個選擇:記憶本,還是寫本?
記憶本的一個顯著優(yōu)勢是成本低。對沒有經(jīng)濟(jì)能力置辦實(shí)體書籍的人,記憶本的意義尤大。《后漢書》載王充早年家貧無書,就去賣書的地方蹭看,“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荀悅據(jù)說也是“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借書并制作一部記憶本是貧者求學(xué)的常態(tài),東漢延篤學(xué)《左傳》而無力置辦紙張抄寫,就找人借一部背了下來,梁代的任孝恭也是“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還有人利用傭書的機(jī)會,在為雇主制作寫本的同時為自己制作了記憶本,比如東吳的闞澤、南朝的王僧孺和朱異。而記憶本的低廉不僅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成本上,也體現(xiàn)在知識成本上,非但不花錢可得之,不識字也可以,北魏名將楊大眼就是通過有聲讀物的方式獲得書籍:“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
記憶本的另一個優(yōu)勢在機(jī)動性。人們即使擁有了物質(zhì)文獻(xiàn),也可能在戰(zhàn)亂、火災(zāi)、遷徙等等不測中再次失去;或者物質(zhì)文獻(xiàn)沒有亡佚,卻在需要使用時恰巧不在場。但記憶本總是隨身的,蔡琰在漢末的流徙中丟失了父親蔡邕留下的四千余卷藏書,她后來仍憑記憶重新寫出了四百余篇。梁代的陸任借得一部《漢書》而不慎丟失其中四卷《五行志》,后來也是憑記憶“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唐太宗命人寫《列女傳》以裝屏風(fēng),一時找不到書,虞世南現(xiàn)場默寫,“不失一字”。記憶本一旦擁有,就與記憶者同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擁有一部書的記憶本,才是真正擁有了一部書。
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diǎn),中古時期的藏書家并不以收藏實(shí)體書為最終目標(biāo),藏書的終極追求是藏得記憶本,獲得實(shí)體書只是藏書流程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前文提到,南朝藏書家蕭鈞和王筠都稱自己抄書、藏書的目的是“備遺忘”:抄是為了幫助記憶,藏是為了給“記憶本”保留一個校本,俾其永遠(yuǎn)完善地存于體內(nèi)。如果對記憶力足夠自信,甚至這個校本也不必備,陳代學(xué)者沈不害寫文章“操筆立成,曾無尋檢”,而家中也從不置藏書,大概因為實(shí)在用不上。柏拉圖擔(dān)心的文字使人們不復(fù)記憶的情況,在沈不害這里遭遇了反例。
沈不害的故事也說明記憶本還有可“尋檢”的優(yōu)勢。在沈不害的時代,書籍的流行裝幀是卷軸裝寫本,這種形態(tài)的書籍盡管已經(jīng)較簡牘取閱為易,但查檢信息仍是極不方便的。英國古典學(xué)者對希臘書卷之缺陷的一些總結(jié),完全可以移評中國的卷軸書籍:
讀者慢慢展卷閱讀,同時用一只手將已經(jīng)讀過的部分收攏,這個過程結(jié)束就是將整個卷軸的內(nèi)外層次倒轉(zhuǎn)過來了,所以在下一個讀者展讀之前要重新卷一遍。這種圖書形式的不便之處顯而易見,尤其別忘了當(dāng)時有些書卷長逾十米。另一個缺點(diǎn)是圖書所用的材料不結(jié)實(shí),容易損壞。不難想象,當(dāng)一個古代的讀者需要去查證一處文獻(xiàn)時,不到萬不得已,都會盡量依靠記憶而不愿費(fèi)事去查檢,況且這個過程還會增加書的磨損。
正因為如此,當(dāng)中古時期的讀者需要檢索文獻(xiàn)時,有時不是去查書,而是去找人。《梁書》說沈約、任昉等人“每有遺忘”就去訪問學(xué)者劉杳,沈、任都是中古時期第一流的藏書家,但對他們而言,劉杳的記憶本顯然比自家的寫本使用起來更便捷。北齊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人一次討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于是呼王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身邊有書但“討閱不能得”,這個缺陷使寫本無法與記憶本相抗衡。
記憶本的第四個優(yōu)長在利于理解,或者確切地說,是中古時人人為地在熟讀成誦與理解文意間建立起了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似肇見于魏明帝時董遇的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而其影響至為深遠(yuǎn)。在蕭梁,蕭繹敦促子弟讀五經(jīng),也強(qiáng)調(diào)“讀之百遍,其義自見”。唐人王友貞九經(jīng)皆讀百遍。乃至7世紀(jì)末留學(xué)印度的義凈會以“斯等諸書,并須暗誦……同孔父之三絕,等歲釋之百遍”的格義式描述介紹當(dāng)?shù)匚逄焖讜慕虒W(xué)情況。所以記憶本不僅自帶檢索工具,還長期被認(rèn)為自帶解讀工具。
從義凈的說法來看,根植于印度文化的口誦觀念,和中土自產(chǎn)的以誦讀求理解的觀念,在當(dāng)時人心中大概是混雜糅合的。而這種糅合的結(jié)果就是,有些俗書的讀誦或背誦行為也有了誦經(jīng)般的儀式感和修行色彩,甚至產(chǎn)生了誦經(jīng)般的祛魔感應(yīng)效果。記憶本通向理解,甚至制作和不斷誦出某些特殊文獻(xiàn)的過程通向功德,這是記憶本性質(zhì)中最為特殊的兩點(diǎn)。
由此看來,記憶本在獲取、攜帶、傳播和使用方面,都有寫本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但寫本是可視的,可分享的,而且是可以穿越時空分享的,這些優(yōu)勢記憶本也不具備。至此這里其實(shí)已經(jīng)可以回答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文獻(xiàn)記憶與物質(zhì)文獻(xiàn)同步繁榮,正是因為此時它們二者間有互補(bǔ)性;關(guān)于記誦的故事在中古時期井噴式的出現(xiàn),就是因為物質(zhì)文獻(xiàn)的發(fā)展增加了人們接觸書籍的機(jī)會,但其結(jié)構(gòu)設(shè)計、制作工藝、存藏條件還遠(yuǎn)遠(yuǎn)實(shí)現(xiàn)不了那時人們對文獻(xiàn)的所有要求。因此,為文獻(xiàn)制作記憶本仍是必要的,而且對于某些內(nèi)容的文獻(xiàn),人們可能更傾向于制作記憶本。
三、記憶本的內(nèi)容偏好
除了作為基礎(chǔ)知識構(gòu)成的儒家經(jīng)典外,最容易被人們選中制作記憶本的文獻(xiàn),一定是最需要利用記憶本優(yōu)勢的文獻(xiàn),或者說,最需要避免寫本劣勢的文獻(xiàn):大概不會有人去背誦類書,因為類書自帶的檢索便利,消解了辛苦記誦的意義。
譜牒是中古時期一個有時代特色的記誦對象,前文提到的唐人李守素,就因長于此道,人稱“肉譜”。在李守素之前,南朝背譜之風(fēng)更盛,蕭繹說自己13歲就開始背《百家譜》,甚至背到身心嚴(yán)重受損。譜牒在當(dāng)時有多重社會功用,選官、議婚、避諱都要以之為據(jù),而主要是指導(dǎo)日常避諱的功用引發(fā)了制作記憶本的需求,因為總不宜在接對人物時臨場查本。關(guān)于譜牒文獻(xiàn)的記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王弘得了王僧孺的《十八州譜》后能“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顯然已經(jīng)有復(fù)本在體。齊競陵王蕭子良命譜學(xué)家賈淵修過一部《見客譜》,從性質(zhì)看,大概也是要背下來的。
譜牒類文獻(xiàn)內(nèi)容無邏輯可言,背誦難度大,因此常在傳記中作為展現(xiàn)傳主記憶力的道具出現(xiàn)(或者是與譜牒性質(zhì)相近的名籍、宮籍、批量人名),其實(shí)傳記作者的這種主題偏好,還是受了他們自己所處時代的背譜之風(fēng)的影響。眾所周知,譜學(xué)在極為興盛,但流傳下來的譜牒文獻(xiàn)卻幾乎沒有。前人論此,多歸因于江陵焚書之厄和后來的隋末戰(zhàn)亂,但某一類書在書厄面前特別脆弱,根本上還是因為這類書相對于其他類書,復(fù)本更少。換言之,在譜學(xué)興盛的時期,很多譜牒恐怕是以“肉譜”的形態(tài)活躍于世的。《魏書》說高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nèi)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紙譜本來就是肉譜的衍生品,如果后者無意著述,不發(fā)生這種衍生,那譜牒就不免隨肉身湮滅了。
另一個常見于中古時期的記誦熱點(diǎn)是故事類文獻(xiàn),如歷朝史事、注記、律令、奏章、儀注等等。《魏書》有一段記載生動地體現(xiàn)了熟記故事的政治效力:延昌四年正月某夜,宣武帝崩于式乾殿,留下年僅五歲的太子,兩天后,宣武帝的同母弟、一直被軟禁在華林園的廣平王元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nèi),呼侍中、黃門、領(lǐng)軍、二衛(wèi),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人見主上”。面對突發(fā)的逼宮,大臣們愕然相視,莫敢抗對,侍中崔光“獨(dú)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意橫劍當(dāng)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wù)吣环Q善,壯光理義有據(jù)。懷聲淚具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以古事裁我”的強(qiáng)大威懾力,體現(xiàn)了故事行政被廣泛承認(rèn)的權(quán)威性,也說明腹中儲備故事以備非常的必要。
檔案、注記類故事文獻(xiàn)成為記誦熱點(diǎn),也與其接觸群體有限、且集中貯藏于相關(guān)政府機(jī)構(gòu)的特性有關(guān)。這種典型的集中秘藏易致集中焚毀型文獻(xiàn),正是記憶本發(fā)揮優(yōu)勢所在,尤其在政權(quán)頻繁交迭的時代。蕭齊初建時,大概臺閣故事又一次毀于易代戰(zhàn)火,徐勉向蕭道成推薦能夠背誦晉、宋起居注的孔休源為尚書儀曹郎,自此“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jī)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防常謂之為‘孔獨(dú)誦”。所以在中古時期,尤其在禮儀制度、銓選制度尚未得到系統(tǒng)、穩(wěn)固建設(shè)的唐代之前,常能見到熟誦歷代故事的人物頗得以接近權(quán)柄,成為重要的政治顧問,像孔休源,以及前文提到的因博悉晉代故事號為“皮里晉書”的劉諒,并皆其例。
從崔光的事例還可以看到,漢故事在當(dāng)時仍有政治效力,因此《漢書》在魏晉已降也是一個非常突出的記誦熱點(diǎn),所以范曄對《漢書》有“當(dāng)世甚重其書,學(xué)者莫不諷誦焉”的觀察。除提供故事外,史書中另有豐富的政治、社會、軍事、地理信息,也常因此為經(jīng)世者所措意,庾信在《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中就夸贊時任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的崔說“敦煌實(shí)錄,宛在胸襟;玉門亭障,無勞圖畫”。
唐代以后,隨著詩賦舉士政策的推行,詩文作品又成為一個新的記誦熱點(diǎn),像前引韓愈《李郱墓志》,就提到李郱能暗記《文選》。《文選》白文也約有40萬字,體量不俗,它和各種別集的熱門,恐怕擠壓了傳統(tǒng)背誦熱點(diǎn)的記憶空間,按代宗朝禮部侍郎楊綰的說法,就是“幼能就學(xué),皆誦當(dāng)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jīng)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由此也可見,記憶本的內(nèi)容偏好是隨時變化的,但總以實(shí)用為指歸,人們?yōu)閰⒄痴b歷朝故事、起居注、史書,為選舉而背誦詩文,為社交需要而背誦譜牒,所以蕭繹盡管少年時躬丁其酷,后來也還是教導(dǎo)子弟要特別留意譜牒。
總之,記誦是一種非常實(shí)用主義的行為,而不是我們過去常常理解的文人炫博。有誰會為了平生未必能碰到幾次的表演機(jī)會,逐字逐句連內(nèi)容帶版式信息地背誦下一部部稀見書?當(dāng)人們?yōu)橐环N文獻(xiàn)制作記憶本,主要還是意圖利用記憶本擁有而寫本不具備的某些特性而已。
四、寫本的新變與記憶本的衰落
記憶本和寫本既是兩種互有短長的文獻(xiàn)形態(tài),那么對于藏書家來說,最理想的收藏大概是所有文獻(xiàn)兩種載體各入一本,而這就會導(dǎo)致寫本越多、越易得,人們想背誦的書籍、能背誦的書籍就越多。事實(shí)上,記憶本確實(shí)有和寫本同步擴(kuò)張的跡象。以記誦量來說,從“十來歲為秦博士,到九十多歲也不過能背《尚書》二十九篇”的伏生,到2世紀(jì)末“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jīng)本文”(按總字?jǐn)?shù)將近40萬)的賈逵;再到8世紀(jì)中期十四五歲時已經(jīng)“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余萬言”的李郱,背誦體量是一路飆升的。以記誦范圍來說,人們的涉獵領(lǐng)域也在跟隨著寫本擴(kuò)張。齊梁時期,搜羅珍奇書籍成為一時風(fēng)尚,文獻(xiàn)記憶活動中就迅速出現(xiàn)了稀見書。當(dāng)時拼比文獻(xiàn)記憶力的隸事游戲,就以背出別人不知道的典故為勝;而前文提到的那位為人提供肉體檢索的劉杳,在他憑記憶給出的檢索結(jié)果中,也能看到《論衡》《新論》、朱建安《扶南以南記》、楊元鳳《置郡事》等超出常規(guī)經(jīng)史范圍的書籍。
但是另一方面,史料也告訴我們,除了那些第一流的學(xué)問家、藏書家外,最常見的記憶對象還是幾類實(shí)用性文獻(xiàn)。人的記憶力是有限的,務(wù)實(shí)雖然不是最理想狀態(tài),卻是大多數(shù)人的選擇。實(shí)際上,能將最實(shí)用的文獻(xiàn)記誦下來難度就已經(jīng)不小。《梁書》說蕭繹五歲能誦《曲禮》,將他描繪成典型的中古記誦神童,但如前文所說,他本人也坦承背《百家譜》背得“感心氣疾”,差點(diǎn)出生命危險。而在李郱的背誦書單里,出現(xiàn)的其實(shí)都是應(yīng)明經(jīng)、進(jìn)士科涉及的常規(guī)書目,可背誦總字?jǐn)?shù)已經(jīng)達(dá)到了百萬級。基礎(chǔ)背誦量已然巨大,新書籍還在不斷生產(chǎn),毫無疑問,記憶本以無涯逐有涯的步伐終會停止下來。
而且,物質(zhì)文獻(xiàn)不僅體量將不斷膨脹,制作技術(shù)也將不斷進(jìn)步。技術(shù)進(jìn)步會導(dǎo)致成本降低,成本低會導(dǎo)致價格下調(diào),也會因此產(chǎn)生出更多的復(fù)本。一旦書籍復(fù)本增多,即使遭遇戰(zhàn)火,記憶本的價值也不會那么大了。根據(jù)學(xué)者對歷代書價的考證,8世紀(jì)后半葉每卷書折米量59斤,9世紀(jì)上半葉激增到100斤,可以明顯看到安史之帶來的價格波動;但12世紀(jì)后半葉書價每冊折米量13斤,與11世紀(jì)中葉的數(shù)據(jù)持平,南北宋的更迭對書價的沖擊已不明顯。這種趨勢說明,由于有了更進(jìn)步的書籍制作技術(shù),記憶本的優(yōu)勢已經(jīng)被部分削弱了。
而記憶本最為擅場的檢索優(yōu)勢,還受到了類書的挑戰(zhàn)。早期的官修類書往往卷帙龐大,動輒仿象天地,包羅萬有,并無檢索優(yōu)勢。但隋唐以后私撰類書大量增多,這些類書的特點(diǎn)就是貼合作者自己的檢索需要來設(shè)計,比如李商隱編寫過兩卷的小冊子《金鑰》,這部書僅由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四部分構(gòu)成,以為“箋啟應(yīng)用之備”。唐代的兩位制誥大家張說和陸贄也編有類似的工具書,張書名為《事對》,全書10卷,陸書名為《備舉文言》,全書20卷。后蜀文谷“雜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備遺忘”,書名就叫《備忘小抄》。當(dāng)時的私人小工具書也在需用者之間流通,像《新唐志》錄有東川節(jié)度掌書記李途的《記室新書》三十卷,“纂集諸書事跡為對語,列四百余門。職方郎中孫樵為之序。”請人作序,可見編纂的初衷就有流通之意;文谷《備忘小抄》據(jù)說也“世多傳寫之”。總之這些實(shí)用性類書卷帙往往不大,方便檢閱、攜帶和流通,它們的出現(xiàn),也可以看作是寫本結(jié)構(gòu)設(shè)計上的一個新創(chuàng)。
寫本不可能取得記憶本的所有優(yōu)勢項,但是隨著技術(shù)的進(jìn)步,它改善了自身的很多劣勢項,而且新結(jié)構(gòu)類書的出現(xiàn),使寫本也模擬到了記憶本的重要特長,那么隨著書籍的增多,逐一制造記憶本,不僅將是不可能的,也將是不那么必要的。而一旦這種情形發(fā)生,人們對記憶的觀念必將變化,戲劇性的記誦故事將不再那么吸引人,人們對記誦的追求也將趨于理性化。
這種記誦觀的理性化在宋代就已經(jīng)很明顯。以史籍記載的記誦速度來說,漢末夏侯榮能每日能背誦千字,東晉道安可以達(dá)到五千余字,而《抱樸子》的仙方明確告訴我們,當(dāng)時人理想的記憶速度是日誦書萬言。但宋人鄭耕老《讀書說》卻實(shí)實(shí)在在地說,中材之人每日能誦300字,“天資稍鈍,中材之半”的,每日能誦150字。以史籍記載的記誦準(zhǔn)確度來說,中古史料中觸目皆是“不差一字”、“一無舛誤”,程頤卻說這種追求是玩物喪志。而記誦和窮理的關(guān)系也得到了一些反思,像“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這句話,就被《冊府元龜》歸入了“偏執(zhí)”門。記誦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固然不可能到就此停止發(fā)揮影響,但不同聲音的出現(xiàn),說明記憶本的黃金時代畢竟已成為過去了。
結(jié)語
《漢書·藝文志》說,《詩經(jīng)》能遭秦火而全,“以其諷誦,不獨(dú)在竹帛故也”。不須上溯秦漢,即使在寫本甚至刻本都已經(jīng)成熟的宋代,對一些因特殊原因無法產(chǎn)生寫刻本的文獻(xiàn),記憶本仍是珍貴的機(jī)會。女詞人朱淑真死后,手稿就被父母“一火焚之”,直到后來魏仲恭在旅店聽人背誦朱詞,大受打動而錄以成集,這才有了我們今日仍能看到的《斷腸集》。問題是,記誦雖然長期默默參與著文獻(xiàn)的傳遞,卻因其無形而難為后人察覺。尤其對物質(zhì)文獻(xiàn)明顯走向繁榮的中古時期,我們只顧勾勒竹帛到紙的物質(zhì)文獻(xiàn)史,卻基本忽視了在數(shù)百年時間里一直在和寫本一起承擔(dān)著文獻(xiàn)傳承任務(wù)的記憶本。盡管史料中突然出現(xiàn)了數(shù)量多到驚人的記誦的故事,而當(dāng)我們注意到這些故事時,新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在流傳下來的中古文獻(xiàn)中,有哪些經(jīng)歷過文獻(xiàn)記憶再誦出的環(huán)節(jié),就像蔡文姬背出的四百余篇那樣?有哪些像經(jīng)過記憶本的配補(bǔ)校勘,就像陸任交還的《漢書》、蔣義補(bǔ)全的“圣歷中侍臣圖贊”一樣?
記憶本對文獻(xiàn)流傳的參與,其實(shí)可以從古文獻(xiàn)的同音異文中看到一些痕跡。柯馬丁在研究郭店楚簡、上博簡和馬王堆帛書所反映的中國早期寫本形態(tài)時就推測,文獻(xiàn)中大量同音異文的存在,說明記憶可能參與了文獻(xiàn)的傳播。而同音異文,尤其是音誤字,在敦煌寫本中仍然大量存在,比如伯3480號王粲《登樓賦》中,“陶牧”的“牧”被寫為“沐”,“人情同于懷土”的“同”被寫為“通”,這種誤字,基本可以判斷是默寫造成的。更明顯的例子是,敦煌寫本中的音誤字還有不少帶著西北方音特色,比如“色”“索”二字在唐五代西北方言中讀音接近,因此常見混用。同音異文不僅見于敦煌寫本,在今存唐詩中也大量保留著,宇文所安因此猜測,部分唐人詩集是當(dāng)時詩歌被吟誦后、由聽者根據(jù)記憶抄寫出來而形成的。如果考慮到不同的背誦者、記錄者合作形成的口錄本、作者自錄的初稿本、作者多次反覆修改流出的一二三稿本及其再次形成的記憶本、口錄本,這些版本全部參與了文獻(xiàn)的形成,那么正如柯馬丁指出的,在寫本間建立文本族譜的研究模型是十分危險的做法,中古文獻(xiàn)的形成和流傳史,因為記憶本的加入,恐怕要比我們過去想像的復(fù)雜得多。
記憶本的意義不僅在于傳承文獻(xiàn)或者傳承文獻(xiàn)的一個版本,作為一種需要憑藉天賦和努力才能獲得文獻(xiàn)形態(tài),它的得來不易,始終在刺激著物質(zhì)文獻(xiàn)謀求創(chuàng)新,不斷模擬記憶本的優(yōu)點(diǎn),以冀減輕記憶的負(fù)擔(dān)。因此,書籍的制作原料、工藝、裝幀乃至內(nèi)容結(jié)構(gòu),都不是孤立的問題,這些要素始終在互相配合、不斷調(diào)試著,以盡可能多地取得記憶本易得、易讀、易檢、易攜的優(yōu)點(diǎn)。推動物質(zhì)文獻(xiàn)發(fā)展的,有記憶本這雙看不見的手。
跳出文獻(xiàn)史,記誦行為的文化意義也頗值得關(guān)注。中古社會在承接前代文獻(xiàn)遺產(chǎn)的同時,也在以比前代更快的速度生產(chǎn)新的文獻(xiàn),同時由于紙張逐漸代替竹帛,文獻(xiàn)因制作成本降低而流通量更大,這些都意味著人們有比過去更多的機(jī)會接觸到書籍,并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接觸到書籍的機(jī)會——無論是借、蹭、看、聽——獲得一個記憶本。每一個背誦者都是肉體的書籍、肉體的圖書館,不僅如此,他們還是行走的書麓,通過他們,書籍可以再次傳播出去,甚至能傳播給無法閱讀的人。中古時期書籍的流通量,恐怕也比我們過去想象的要大。
背誦是如此平常,以至于我們從不把它作為一種獨(dú)立的文獻(xiàn)和文化現(xiàn)象來考察。但事實(shí)上,記憶本分擔(dān)寫本的責(zé)任,改變寫本的面貌,刺激寫本的發(fā)展,并服務(wù)到了寫本服務(wù)不到的對象,沒有記憶本的中古文獻(xiàn)世界,反倒是無法想像的。
[責(zé)任編輯: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