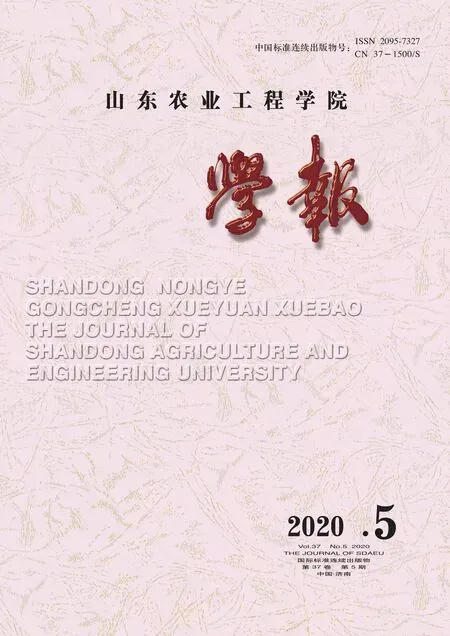八大山人繪畫的“廉”與“空”
(泉州師范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明朝皇室后裔朱耷(1626-1705),號八大山人,分封南昌,明朝覆滅后,出家為僧,不久還俗當了道士,定居南昌青云譜。他的花鳥畫師承林良、徐渭、陳淳的水墨寫意,發展創新出筆墨豪放、單純含蓄的獨特風格;其山水畫受董其昌的影響,從筆墨形式結構重塑繪畫風格史,并進行個性化的詮釋;其寫意畫法對石濤等后代繪畫名家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八大山人的畫,無論是花鳥畫,還是山水畫,畫面空闊,筆墨寥寥,給人予“空”的強烈感受。這種“空”是如何產生的?原因是什么?又有著怎樣的深刻含義?
一、“廉”與“空”
(一)“廉”
朱耷曾稱自己的畫“廉”。所謂“廉”,就是少、簡、省。觀八大山人的畫,不論是構圖,還是筆墨,或用色,從中不難讀出“廉”字。而這“廉”即是構成“空”的基礎,也是形成“空”的必然。
1.構圖之“廉”
八大山人的畫,往往只描繪二、三個形象,有時甚至僅描繪單個形象,描繪的可視性形象少之又少,畫面留有大量的空白處,構圖真可謂是達到了簡之峰巔、廉之極至。
一般來說,山水畫的可視性對象是豐富的,但是八大山人的山水畫,構圖可以做到非常的簡略。如《山水花果冊十開(之一)雙松》,畫面中只有兩棵相互依存的松樹,加上很少的一點山崖和四個小小的遠山。再如《山水花果冊十開(之九)山水》,畫面上只有一株松樹加幾株雜樹,一段危崖和幾個遠山,一只風帆。類似的畫作還有《墨筆雜畫山十(之五)山水》、《書畫合壁冊二開(之一)山水》等。
八大山人的花鳥畫,更能顯示其構圖之廉。一些圖像比較多一點的,可以由一兩只鳥、一兩條魚,或者一兩朵花,搭配一點其它的景物而構成。如《荷池雙鳥圖》,由一個太湖石、兩只鳥和幾枝荷花構成;《魚鳥圖軸》由一塊危石、一只鳥和兩尾魚構成;《雙雀圖》只有兩只麻雀。一些圖像比較少一點的畫,可以只是由一條魚、或一只鳥、或者一兩朵花再加一點其它的景物構成。尤其是畫面只描繪單個形象,使八大山人的繪畫構圖達到了廉的極致。如《孤鳥圖軸》,只畫一根豎立的光禿禿的樹枝和一只立著的鳥;《山水花鳥類圖(雞雛)》也只畫有一只小雞;《安晚冊二十二(之九)貓》,也是只畫了一只伏在地上的貓;還有《安晚冊二十二(之六)魚》、《傳綮寫生冊十五開(之十二)玲瓏石》、《古梅圖軸》等等畫作都是如此。
2.用筆之“廉”
八大山人的畫,用筆非常簡練,無論花鳥畫,還是山水畫,總是簡筆勾勒,寥寥幾筆,就描繪出活靈活現的形象來,活靈活現。
觀八大山人的花鳥畫,用筆真可謂簡省。如康熙三十一年的《花果鳥蟲冊》里的《涉事》,畫中只有一個花瓣,共用了七、八筆。又如《石榴圖頁》,一筆縱貫到底勾勒出石榴老樹枝,四短筆畫出一枝鮮嫩的新枝,再用兩筆描繪出枝上的兩枚石榴。再如《雜畫冊十四開 之十二 梅》,兩筆畫出一根梅枝,四個小圈圈出四朵梅花,兩點點出兩個短枝。《花鳥圖(枯木孤鳥)》、《書畫合裝冊十六開(之六)蘭花》、《蔬果卷》、《書畫(魚)》等畫作,無不是以極簡的筆畫便使所繪形象躍然紙上
八大山人的山水畫用筆也是十分簡練,簡化到類似白描的手法,只以線條勾勒出山水的輪廓。如前文提到的《墨筆雜畫山十(之五)山水》、《書畫合壁冊二開(之一)山水》、《山水圖》三幅畫就是如此。特別是 《書畫合壁冊二開 (之一)山水》,簡直就是一幅山水簡筆畫。又如《山水冊十開(之八)山水》,其中的山嶺樹木和亭子只是寥寥幾筆勾勒出來,連點染的筆畫都少見。
3.用墨之“廉”
正如前文所述,構圖“廉”,用筆又“廉”,那么,用墨自然也就是“廉”。八大山人在一首題畫詩中自稱他的畫是“墨點不多”。觀其畫,他確實用墨非常精到,把寫意的手法發展到極至。他的畫幾乎不用墨色層層渲染,只是在很必要的地方稍加點染,意到為止。
除了上文所舉的例子都可以看見這個特色之外,此類畫作還有:《貓石雜卉圖軸(之一)》中的貓和石頭,在勾出一個輪廓之后,只是在貓的兩個耳朵加了兩點較厚重的墨,背部和尾部稍加渲染,在石頭的凹陷處用淡墨進行了輕輕地渲染;《雜畫圖(一)》畫中兩只小鳥相對而立,它們的身軀只是一小團濃淡變化的墨,眼睛為一個小墨點,其它的輪廓線只有幾筆淡墨勾線;《書畫(花)》畫面中的一枝花,只有三片葉子和花蕊的墨較濃,花莖、花瓣和花苞的都是淡墨畫成;《山水花果冊十開(之五)山水》畫面幾乎全是淡墨,只是幾片稀疏的樹葉用較濃的墨勾出,近處石頭縫隙中點染了幾點濃墨。
4.用色之“廉”
在八大山人的畫中,幾乎看不見色彩,能見的只有印章的朱紅色。他畫中的色彩,主要是依靠墨色的濃淡干濕來體現。他充分利用宣紙浸水的特點,用中國畫“墨分五色”的技法,來展現他畫中的色彩。實際上,真正的色彩用得很少。前文所舉的畫作中,不管是山水畫還是花鳥畫,都是如此。
(二)“空”
由于構圖、用筆、用墨和用色都到達了高度的廉,少之又少,這樣,整個畫幅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自然顯得空。由此可見,八大山人繪畫的廉,為他繪畫的空奠定了基礎。
反向視角觀察八大山人的畫,其繪畫在構圖上的空,指的是一幅畫上沒有一物,或者是只有少量的物象,即畫幅存在大量的空白。綜觀八大山人的畫,應該說是空白多于物象,正如前文所說,正是由于只畫了少量的物象,只用了少量的筆墨和少量的色彩,使大量的空白出現,才呈現出空。這種空,就是由于廉而產生的,是先有廉為基礎,而后才空的。因此,八大山人的畫之空,又是廉的結果。
(三)“廉”與“空”相輔相成
廉是空的基礎,空是廉的結果,八大山人的畫,廉與空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首先,沒有廉就沒有空,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反之,沒有空也就沒有廉,也不難理解。也就是說,就一幅畫而言,根據所繪圖像的多少,用筆、用墨和用色以及空白處所占畫面位置的大小,才斷定繁簡。在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幅畫大面積是空的,繪畫要素偏少,那么它就是簡的,就是廉的,反之亦然。八大山人的畫,畫面空之又空,繪畫要素少之又少,簡之又簡,因而是廉之又廉。八大山人繪畫的“空”是與“廉”緊密相結合的,“廉”是“空”的基礎,“空”是“廉”的結果,二者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二、佛學淵源與繪畫表現
八大山人幾十年的出家為僧經歷,具有深厚的佛學造詣。他繪畫的“廉”與“空”的形成,與他的佛學淵源密不可分。
(一)佛學修煉經歷
朱耷(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六子寧獻王朱權之九世孫。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時年十九歲的朱耷隱姓埋名,隱跡于山野空門,避禍全身。順治五年(1648年),二十三歲的朱耷,出家于奉新縣耕香寺,削發為僧,住山講經。據邵長蘅 《八大山人傳》:“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余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五十三歲,病癲,裂其浮屠服焚之。康熙十九年(1680年),五十五歲,還俗。
據康熙《進賢縣志》卷十七宏敏傳說:“法嗣傳綮,號刃庵,能紹師法,尤為禪林拔萃之器。”[1](p259)可見八大山人不止是一位有佛學修養的僧人,而且是一位很有建樹的,出類拔萃的大器之僧。八大山人是曹洞宗第三十世的弟子,與其師穎學弘敏皆是曹洞宗壽昌法系的嗣傳弟子。雖然是曹洞宗的弟子,他卻融合了曹洞和臨濟兩門之法。八大山人在《題個山小像》中說:“生在曹洞臨濟有,穿過臨濟曹洞有,曹洞臨濟兩俱非”,表明了他是吸收兩宗思想的精華的。禪宗對八大山人影響極深。八大山人并不受到門戶的限制,而是打破門戶之間的鴻溝,博采眾家之長。[2](p60)八大山人的佛學修養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
八大山人在山門修行幾十年,晚年由于狂病,癒后還俗,但是,在他的思想意識當中,一直沒有脫離佛門,行動上也沒有中斷與佛門的聯系,經常與禪門中人往來,佛學思想進一步地發展,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禪悟方面,晚年的八大山人已臻于無上境界。一九九二年,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羅漢巖發現了款為八大山人的題壁之語:“甲申冬佛臘之辰游仙蹤,空即色,色即空,無瞻無礙□□同,浮生如春夢,轉迅即成空。有人識得真空相,便是長生不老翁。八大山人題。 ”[3](p279)這是八大山人晚年的題詩,即為一個例證。
(二)佛學“空”的思想
佛教的經典博大精深,然而,一個“空”字成為各時期、各教派的基本思想。在佛教中,“空”為梵語(sunya),音譯為舜若。它是與“有”相對的,表示“非有”、“非存在”的一個基本概念,意譯為空無、空虛、空寂、空凈、非有,在一切存在之物中,皆無自體、實體、我等,亦即謂事物之虛幻不實,或理體之空寂明凈。空是大乘佛教,特別是般若經系統的大乘佛教思想的理論基礎。雖說佛教各時期、各派別對空的解釋不一,然而有著幾十年出家為僧崇佛修身的八大山人無疑是繼承并且發展了佛學中關于“空”的基本思想的。
(三)佛學的“空”與八大山人繪畫的“空”
八大山人的繪畫,與他的佛學修持有密切的關系,其畫面構圖、筆畫、用墨和用色的高度的廉,畫幅留下大量的空白而出現的空,只是一種形式,本質上卻在解釋著他自己的佛學思想。
“大乘佛學講真空妙有的道理,認為一切法,都為空相,皆虛而不實。空不是說具體形象上空虛而難見,而是強調本源的空,即性空。佛學認為,一切法都本因緣而生,故無自性,故說是空相。佛教所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禪宗推崇的到彼岸的大智慧 (摩訶般若波羅蜜),就是性空的智慧,‘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八大藝術很大程度上在詮釋這一內涵。”[3](p268)
關于空,八大山人在《傳綮寫生冊》上,題有“十年如水不曾疏,欲展家風事事無”之語。家風是禪宗顯現一個宗門的特點,八大山人稱家風“事事無”,他對佛教核心精神的理解,就在一個“無”字,即“空”字上。這個“無”字,是南宗惠能禪法的真意,南禪被稱為“無相法門”,以無念、無相、無住為其核心思想。八大山人以“無”和“空”來把握禪宗的根本。八大山人的“畫者東西影”也與空有關。八大山人認為,一切畫中的相都是幻而不實的,都是空相,都是“假名”,八大山人畫這個“相”,但心念卻在“空”,他要畫出“空”的“相”,在“空”的“相”中表現“實相”,表現有意義的世界。所以,八大山人作畫,不離“相”,又不在“相”,“相”即非“相”,“實相”即在非“相”中。[3](p268—269)由上可以看出,八大山人繪畫的廉與空,實質上就是對佛教空的思想的一種解釋的方式。
三、“廉”與“空”的審美情趣
八大山人的繪畫的廉與空,具有很高的審美情趣,從而造就了八大山人繪畫高超的藝術成就。他的繪畫前無古人,后人也難以企及,也正在于這一點上。
(一)恰到好處
八大山人繪畫廉與空的美學特征之一,在于它的恰到好處。
戰國時期,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里評價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這是恰到好處的典型例證。若以此而論,八大山人之繪畫,堪稱畫中的東家之子。
清代評論家秦祖永,評論八大三人的畫“以簡略勝”。綜觀八大山人繪畫的筆墨,已經達到廉的極至,精簡得不能再精簡了。在他的畫幅中,往往很難找到能夠去掉的多余的筆墨。在其花鳥畫中,很難想象能夠去掉一草、一花、一只鳥,或者是一尾魚;在他的山水畫中,也很難想象,能夠在那個部位去掉一棵樹、一塊石。鄭板橋稱八大山人的畫為“簡筆畫”。相反,同樣也不能在八大山人的畫中增加一點筆墨。你不能夠想象在他畫的梅花中增添一根枝條、一朵梅花,在他的松樹上增加一些松葉,在危石上添加一只鳥,在空白處補畫一尾魚。任何的添加都是多余的,都是沒有必要而沒有意義的。可見,八大山人的畫,雖然看起來廉而空,其實是廉而不廉,空而不空,其中的廉和空之處自有它充實的內容。
(二)空靈境界
從審美的角度看八大山人的繪畫,它的廉與空營造了一種空靈的境界,這是八大山人繪畫的又一審美特征。
在美學上,所謂空靈的藝術風格,主要特點在于,“以清遠雋永、變幻飄渺的藝術形式書寫寧靜淡泊、高遠飄逸、超凡脫俗的心境,形成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韻味。”在中國古代的詩歌中,就有這種審美方式。“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倡‘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4](p58)。認為空靈的境界,應該是澄澈、透明、玲瓏、剔透的,如空音、鏡花、水月的意境。在中國傳統的繪畫中,那種追求象外之象、境外之境,筆墨盡而意無窮,通過畫幅上有限的圖景,去給欣賞者留下無窮想象的余地的,有限中包括無限的藝術境界,就是空靈的境界。
八大山人繪畫的廉與空,給畫面留下大量的空白,把這些空白給予欣賞者,讓他們去想象補充,營造的是眾多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具有豐富的蘊涵,創造了如空音、鏡花、水月般的意境,富于空靈的審美情趣。如《墨筆雜畫冊八開(之一)瓜鳥》《墨筆雜畫冊八開(之二)孤鳥》《雙魚圖軸》《山水冊十開 之三 山水》等,都留有大量的空白,給觀者以充分的想象,因而具有典型的空靈特征。
結語
八大山人的畫,計白當黑,廉而不廉、空而不空,圖像簡而蘊涵博,創造了一個無限空靈的藝術世界,樹立了中國繪畫史上的一座豐碑。賞析他的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中既能看到他佛學思想的光輝,又能看到他作為王朝皇室后裔的生活經歷和情感歷程。廉和空是八大山人繪畫的形式和手段,也是所包含的內容和追求的目標。然而,不管作為形式還是內容,手段還是目標,它們都深深地根植于佛學思想之中,是對 “空”和“妙有”的一種詮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