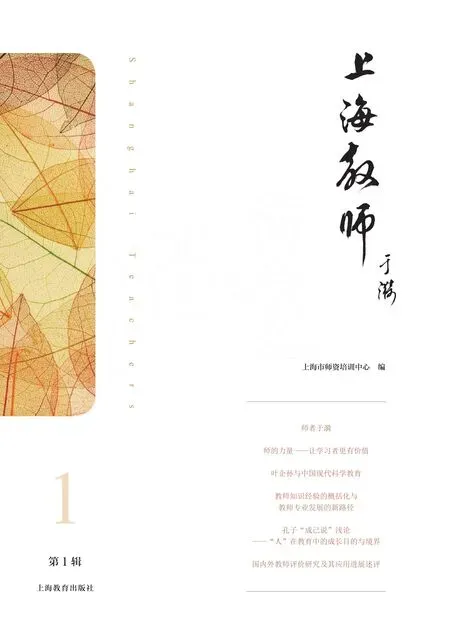面向人類學的教師教育改革:理論透視與實踐路徑
李云星
(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浙江金華 321004)
一、引言:作為教師教育基礎學科的人類學
教育人類學家拉德森(Ladson-Billings Gloria)曾批評美國教師教育過度依賴心理學而忽視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人類學的現象。他指出,盡管心理學提供了兒童成長心理機制的知識,但它缺乏對學生文化的關注。典型性的職前教師會選修大量關于歷史、哲學和教育社會學的基礎課程。然而,課程開設存在強烈的心理學集中傾向,相關課程主要涉及兒童或青少年發展、認知與學習、特殊例外(如具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在美國,理解教學就是要理解整個心理領域。[1]
拉德森的批評至少隱含了如下含義:教育與教學不僅僅與心理認知有關,它還涉及文化。人類學作為研究文化的學問,能夠為教師培養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人類學能對教師教育有所貢獻,在于人類學與教育學的內在關聯。不論是教育學還是人類學,成人都是其核心研究對象。略顯差異的是,人類學關注的是“何以成人”,即成人是如何發生的。教育學更關心“以何成人”,即如何做才能成人。這一差異也造成了人類學家與教育者在提問方式上的差異:人類學家追問的是“事情是如何的(how things are)”;教育者的提問是“對于這件事,我們能做什么(what can do about the way things are)”。[2]沒有對“何以成人”或“事情是如何的”的了解,教育者無法回答“以何成人”或“對于這件事,我們能做什么”。在此意義上,人類學應當是教育學的前提性或基礎性學科之一,自然也應當成為教師教育(學)的基礎學科。兩者的內在關聯構成了人類學介入教師教育的可能性前提。本文并不試圖“照著講”教師教育為何需要人類學,而是嘗試“接著講”人類學能夠為未來教師貢獻什么,以及面向人類學的教師教育改革實踐路徑。
二、理論透視:人類學對未來教師的可能貢獻
(一)認知視角的貢獻
人類學對未來教師的貢獻首先在于認知視角,包括整全視角、文化視角和他者立場(內部人視角)。
1. 整全視角
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曾將整全視角作為人類學的基本特征:
這一寬廣的視角——有時會用一個專門術語“整體觀”來表示——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人類學特征。不管一個人選擇什么樣的人類學定義,它都會著重強調,這是一個從整體上去理解人類許多方面的準則。進行整體思考,就是要將部分放到整體中來理解,設法掌握更大的背景和框架——在這一背景與框架內人們會有種種表現和體驗。人類學的整體觀至少包含三個層面:一是人類學總是試圖從整體上認知和理解每種體驗;二是人類學總是試圖描述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而不是從中抽象隔離出部分;三是人類學往往會綜合多學科、多領域的知識和視角來理解研究對象。[3]
與其他學科強調由部分認識整體不同,人類學強調對局部或部分的認識必須立足于整體。當且僅當我們對整體有認知的時候,才能發現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聯系。人類學的這一認知視角與教育學,尤其是與當代學校教育學不同。教育學通常將對象聚焦到“具體個人”或“群體之人”。因此教師容易陷入就教育談教育的誤區,而忽視具體個人或群體背后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聯系。以人類學觀之,學習并不僅僅局限于學校,也不僅僅是知識傳遞或技能提升,而是涉及師生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的重構。從教育發展史來看,早期教育屬于非形式化教育,教育與生活融合在一起。伴隨著形式化教育尤其是制度化學校的出現,教育與生活發生了割裂與脫離。盡管學校有其存在價值,但其功能、使命和內在運行邏輯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學校教育不僅要從重構學校教育文化角度統整考慮教育問題,更要從與整體社會文化銜接、融通的角度重構學校與社區的關聯。
2. 文化視角
人類學不僅關注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生活及自然生活中人類所處的位置,而且尤為關注人類為了使其生活變得有意義而建構文化框架的方式。[4]人類學嘗試以文化為對象和方法,理解、構建關于異域或他者的理論。教育作為文化保存、傳遞、更新和創造的事業,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類學文化視角對教師的意義包括兩個層面。
一是有助于教師從文化視角切入、理解并解決教育問題。以人類學視域觀之,教育的問題往往是文化的問題。例如,印第安人學生對教師的提問往往會報以沉默,這并不代表他們不理解或不會,而是與他們的文化相關。研究發現,印第安人學生在課外表現為“吵鬧、勇敢、大膽和變化無常的好奇”,但在課堂上總是沉默。這是因為在印第安人的文化里,個人才能的展示會被看作對其他孩子的貶低。這一研究也彰顯了印第安人文化與盎格魯—美國人文化的差異。在美國白人的文化里,個體學生的主動性、競爭力和成就被認為是有價值的;而在印第安人的文化里,同樣的行為是被認為不可接受甚至是不道德的。[5]人類學提醒教師:當遇到教育問題時,首先需要從文化視角重新審視現象或問題本身,透析其原因,并尋找應對方法。文化視角對于理解并解決當代中國鄉村教育問題或城市學校中農民工子弟學生的教育問題尤其具有實踐意義。
二是有助于教師在教育實踐中確立文化相對主義的價值觀念與意識。文化相對主義觀念由來已久,人類學對不同的文化有著天然的敬畏之心。文化相對主義首先表現為對不同生活方式、文化價值的尊重,其次表現為對不同文化的敏感與意識。當教師學會用文化來看待問題時,會習得文化敏感。
3. 他者立場(內部人視角)
人類學的他者立場,強調從研究對象的視角——內部人視角(insider perspective)而不是研究者的角度理解他們的意義世界。被研究者既是研究對象,又是研究方法。人類學的他者立場致力于理解他者,返回自身。這有助于教師獲得關于學生的置身式理解。他者立場強調站在他者的立場或視角看待問題,即“put yourself into other’s shoes”。在人類學視域下,強調要將他者的行為或語言置于他者的文化實踐中理解。對教師而言,則強調將學生置于學生的成長環境中理解。這一理解,有助于教師認識到家庭環境對學生發展的形塑與制約。
在教育學史上,學生立場的確立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革命。教育學視域的學生立場,強調以學生的發展作為教育的目的和終極評價標準,立足學生的發展需要和發展規律,開展、實施教育教學實踐活動。盡管教育實踐界認可學生立場的價值與意義,但囿于“教師中心、課堂中心、教材中心”傳統教育實踐文化的強大抵制力量,仍需確立學生立場并提升踐行學生立場的能力。
他者立場對教師的啟示在于: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應避免用自己的思維“強牽”學生的思維;避免用個別學生或部分學生的視角、思維與問題代替全體學生的視角、思維與問題;避免輕視學生的思維與經驗;避免用習以為常、例行的模式來解讀學生,或者用“好學生、壞學生”的二分法來區分學生等。他者立場強調教師應關注學生的日常語言和日常思維,尤其關注學生的敘述、對問題的理解和分析以及學生自己的術語和概念。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學生的聲音,哪怕是不成熟的聲音不應該被當作需要清除的雜音,而是教育教學實踐的起點。
(二)本體論層面的智識啟迪
在人類學看來,成人主要是通過學習(文化)機制,而不是神經化學(本能)機制來滿足生物學和環境需求。成學(to learn),不是非自愿的回應,是成人(to be human),成人即成學(to be human is to learn)。[6]這表明“成學”(教育)本是“成人之學”的研究對象。
人類學家很早就開始關注教育。早期人類學家對教育或學習的理解,遠遠超出學校教育范圍。當大多數人將學習看作從教師到學生的科層制組織時,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通過對薩摩亞人的研究,已經將教育看作與成年人或同伴一起做事的橫向聯系。金·萊夫(Jean Lave)等人的研究則聚焦日常生活中的學習,通過對裁縫、水手、屠夫等學徒制的研究,強調學習是一種合法性邊緣參與的過程。在萊夫看來,學習是學習者在實踐共同體中的社會參與,知識是個人與社會情境或物理情境之間互動的產物。人在實踐共同體中的互動,會建構出意義與身份,它們與更廣泛的情境脈絡密切相關。[7]萊夫關于情境學習的研究受到了教師教育界的極大認可和關注,他的研究高居21世紀以來國際頂尖教師教育SSCI期刊論文高頻引用文獻之首,總計被引269次。[8]人類學的智識啟迪還重構了對教育或學習的理解。正如萊夫所揭示的,日常生活中的學習是一項由邊緣到中心的合法性參與過程,其中伴隨著學習者意義和身份的建構。就此而言,學校教育也應當是學生意義和身份建構的過程,而不僅僅是知識接受的過程。教師的職責在于設計相應的做中學項目,讓學生主動參與其中,在做的過程當中習得知識、能力、方法和思維。
人類學智識啟迪還表現在通過呈現文化的多樣性和揭示生活的多樣可能性,讓教師反思自我文化的刻板性。例如,霍爾通過對西太平洋上特羅布里恩島上的居民研究發現,他們的時間觀并不是基于現代時間觀的。現代時間觀認為:時間是線性的、進化發展的,是寶貴的資源,浪費時間就是浪費生命。特羅布里恩島居民則認為,時間并不是一條一個人順其發展的直線,而是一個人坐在一旁拍濺或在里面打滾的水坑。[9]這一時間觀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現代時間觀,但它至少彰顯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人類社會發展最大的障礙即失去對可能性的想象,而統統歸結于一種單向的生活。“可能性”的存在,既需要知道存在多樣性可能,也需要對“主流可能”或“唯一可能”進行反思。人類學的諸多研究可以讓教師重新反思“現代”“文明”“中心”“城市”等概念,并重新認識“落后”“野蠻”“邊緣”“鄉村”。遷移到教育,教師也可以借由人類學思維重新思考“成功”“優秀”“進步”等概念,而回到學生對上述概念的自我認知,并基于學生的認知和理解,促進學生的發展。
(三)方法論層面的民族志方法
在人類學、社會學和教育學領域,民族志是關于文化的研究。做民族志的一個原因是讓那些通常不可見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習慣變得可見,以理解那些已經掌握這些模式和習慣知識的人,并確認特定人員知道(或不知道)和理解(或不理解)這些模式的影響。因此,民族志既是在特定社會群體內觀看、觀察生活的一種方式,也是記錄、分析并表達生活的方式。[10]研究表明,民族志方法可以提供影響教育的文化和社會洞見。[11]人類學視域下的反思性實踐可以提供一種策略,幫助教育者解決他們實踐中的“困擾”,并在文化多元課堂中改進實踐。一方面,諸如文化、背景、社會結構、權力等人類學概念提供了理解多元文化課堂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諸如觀察、靈活訪談和人工分析有助于獲取有用信息。通過運用人類學概念和信息,教育者可以通過有效的干預以改進教育實踐。[12]
例如,民族志觀察因本身帶有內部視角以及相應的文化關切,因此更能夠深度破解教育實踐的內在機制。與一般量化觀察不同,民族志觀察強調聚焦事件、過程、主體感受和意義。教師可以單獨觀察教學學習過程中的學生,如準備開始學習較慢的學生和迅速開始學習的學生,并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驗。同樣,對于那些溫順的、安靜的以及仔細思考問題的學生也給予足夠的關注。日本的研究表明,民族志有利于教師加深對學生的認識,并采取相對應的教學策略。在課例研究過程中使用民族志和田野筆記的教師,可以在課堂管理中創造并運用替代性策略。基于民族志的課堂觀察更有利于解釋學生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教師在課堂里應該做什么。[13]另有研究通過使用民族志視角幫助候選教師(teacher candidate)成功進入一個發展中的課堂文化,并讓一位休學四個月的五年級學生重新融入原來的班級。研究表明,使用民族志的觀察和解釋技巧,通過重組由課堂互動而已經形成的社交和學術方面的模式化實踐,既可以幫助候選教師,也可以幫助返學學生成為具有社交和文化勝任力的成員。[14]
簡而言之,作為人類學核心的民族志可以幫助教育者懂得更多的學校文化和學校教育總體背景,讓他們處于一個更好的立場以改進教育實踐。民族志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替代性選擇,將教育體系作為整體,并檢驗其中許多部分的關系;為不同群體、學校和學校社區的多樣性提供豐富的民族志描述;民族志研究同樣有助于促進家庭和學校的密切聯系;它可以形成重要形態的質性評估數據,這是傳統學生學業成就測評提供不了的。
三、面向人類學教師教育改革的實踐路徑
(一)目標更新:培育具有文化回應教育能力的教師
伴隨著文化多元時代的到來,國際教師教育呈現出鮮明的文化轉向特征。越來越多的國家強調教師的文化意識、文化敏感、跨文化能力和多元文化教育能力。例如,德國教師教育標準規定,未來教師需要了解學生的社會文化生活條件,包括在理論教學階段、設計教育教學過程時注意跨文化維度,了解性別特征對教育過程的影響及其意義;見習階段要注意到各個學習小組中的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多樣性等。[15]西班牙小學教師專業培養目標也要求教師能有效處理多元文化和多種語言環境下的語言學習問題,熟悉和處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學校狀況,能將教育與社會環境聯系起來,并與家庭和社區開展合作,以批判的方式分析和思考影響家庭和學校與現實社會有關的問題,如代際關系的變化、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社會歧視與融合、促進忍讓等。[16]
略顯遺憾的是,中國教師教育存在文化缺失或忽視問題。以“文化”為關鍵詞檢索國家教育部頒布的《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小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和《中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發現,僅有四處提到“文化”。其中三處出現在“終身學習”理念中的“優化知識結構,提高文化素養”。僅《中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中教育知識部分提及“了解中學生群體文化特點與行為方式”。顯然,這不符合多元文化時代的發展趨勢。
在文化傳遞、融合和創新進程中,教育承擔著重要的使命。面向人類學的教師教育改革,首先在于目標更新,即培育具有文化回應教育能力的教師。文化回應教育(culturally responsive education)旨在立足學生文化差異,利用差異化文化資源,通過發展與學生文化背景和個性特征相適切的課程、教學和管理策略,以實現教育的目標。有研究者提出,文化回應性教師(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er)的典型特征包括:具備社會文化意識;對多樣化背景學生的堅信;認為教師有責任并有能力讓學校變得更公平;懂得學生如何建構知識并有能力提升知識建構;知道學生的日常生活;在引領學生超越熟悉的時候能夠基于學生已經知道的設計教學。[17]事實上,這一界定是文化意識、教育態度、教育過程知識和教育設計能力的綜合。面向人類學的教師教育目標需要整合人類學的獨特優勢并結合教育自身的特點和目的,對未來教師提出新的要求。基于這一要求,文化回應性教師至少應具備四個層面的素養。
一是文化意識與敏感。它包括對學生、家長及其社區文化的尊重與敬畏;能夠用文化視角和眼光看待透視教育問題等。
二是文化研究能力。它包括能夠通過與學生、家長或其他人士的交流,明晰教育利益相關者的文化理念和教育期待;能夠探究、分析學生的知識建構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影響等。
三是文化回應教育能力。在尊重文化、敬畏文化、研究文化的基礎上,教師需要具備將作為資源的文化轉化成課程、教學以及管理的設計和實施能力。它包括營造相互尊重、安全的文化氛圍,創造學生實現能力的良好環境;整合學生的地方性知識或本土化概念進行教學設計;針對學生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學習方式采取不同但適切的教學策略;發掘地方文化資源,整合開發學生學習課程等。
四是文化反思能力。教師實踐不是從已知技術工具箱中選擇最佳方案的活動,它面臨著復雜性、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價值沖突。教師需要運用實踐智慧,從具體情境中構建出問題及其解決方案。在此過程中,教師需要不斷地反思建構自己的專業知識。[18]教師的文化反思是教師反思的一種,但又具有獨特的價值和蘊含。它促使教師思考:教育問題的產生是否存在文化差異的因素?如果存在,是哪些因素?教育如何根據這些因素進行調整設計?教育實踐中有哪些文化資源可以用于教育的改進?教師自身的文化如何形塑影響教育手段和教育效果?如此等等。
需要指明的是,上述四個層面的能力或素養并不是并列或相互割裂的,而是彼此聯系的統一體。
(二)課程引入:作為改革重心的人類學課程
教師教育培養目標的更新必然要求課程的變革。就人類學在教師教育實踐中可能扮演的功能作用而言,至少存在以下三種形態的人類學。
1. 作為公共基礎課程的人類學
公共基礎課程旨在為師范生奠定教育教學的理論基礎、知識基礎和方法基礎。通常它包括“教育學”“心理學”“課程論”“教育研究方法”等所有師范生必選的公共基礎課程。人類學作為學科基礎課程包含兩個目的向度:一是為未來教師提供人類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框架和基本視角;二是為未來教師提供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基礎。前一目的向度的課程改革可以將“教育人類學”作為師范生必選或選修的課程;后一目的向度的課程改革可以與現有的“教育研究方法”進行整合,強調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學習與運用,包括參與性觀察、傾聽、訪談等技術的扎實學習。作為方法的人類學課程實踐在國外早已有之。人類學家蘭德斯(Ruth Landes)很早就將人類學田野方法引入教師教育課程,讓未來教師通過回溯家族文化遺產來反思個人的文化觀念,并挑戰、反思關于學生和自己的深層次假設。隨后,蘭德斯會要求未來教師采取人類學家的立場,在課堂中觀察并做田野筆記,以此深化他們關于學生和他們自己行動和理念的理解。
2. 作為學科專業課程的人類學
作為學科專業課程的人類學,強調將人類學的基本理論、知識、方法作為學科教學的內容、資源、手段和策略。換言之,人類學相關知識或理論不再是作為透視教師研究、透視自己或他者的工具,而是作為實現教育目標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或工具。國外教育實踐中已有大量的實踐案例。例如,有教師將人類學作為一個內容領域或單元,幫助學生學習文化、歷史、理論、工具、實踐,以及理解人類學主體知識的分類。在此基礎上,人類學課程還被用來幫助學生理解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更廣泛的社區。也有教師讓學生主動實施人類學研究,包括合作參與和自主參與人類學研究。例如,有教授四五年級的教師讓學生與當地文化人類學家合作,實施一年的社區研究項目。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讓班級學生訪問、記錄、分析當地農民和社區教堂的福音歌手,以獲得文化理解、語言技能、研究經驗和分析能力。[19]還有教師讓學生用人類學方法研究課堂行為,編制“民族志書(The Ethnography Book)”。學生在此過程中需要學習觀察、解釋、感知并分析課堂行為。“民族志書”也有助于教師獲得學校生活中學生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學生的所思所想。[20]更有教師在課堂中引入人類學方法,如在課堂中引入“民族志思維(Ethnographic Ways of Thinking)”,幫助學生將人類學工作、思維方式和理解復雜情境的愿望轉換到學校和生活的情境之中。[21]
除上述實踐案例之外,還存在基于人類學民族志與學科深度融合的課程開發與實施案例,如民俗數學(ethnomathematics)。民俗數學強調對傳統和日常數學的研究,并將研究發現整合進符合內容標準的課程中。民俗數學承認兒童自身攜帶知識的價值,并鼓勵兒童參與基于日常數學的活動,幫助他們發展有意義的問題解決能力和更好的數學能力。[22]關于民俗數學,國內已有研究者開始關注[23],但在教師教育專業課程的設置方面的實踐相對較少。民俗數學僅僅提供了人類學深入學科及其教學的一個案例。類似的實踐還包括涉入科學課程、社會研究課程、語言藝術課程等。[24]換言之,上述相關的師范專業都可以將人類學作為學科專業課程,以探討人類學與學科基礎知識及其教學的整合。
3. 作為教師實踐課程的人類學
《教師教育課程標準(試行)》提出,師范生教育應涵蓋公共基礎課程、學科專業課程和教師教育課程。其中,教育實踐課程不少于一個學期。具體到各層次師范生培養課程標準,它們都強調師范生應具有觀摩、參與、研究教育實踐的經歷與體驗。在此要求的背景下,各師范專業都設計實施了教育實踐課程。但目前教師教育實踐課程主要聚焦師范生課堂教學規范習得、學生管理技能學習、學科教學知識運用等方面,缺乏對教育社區的深度關注,更缺乏對學生及其家庭生活方式的置身認知。在教師教育實踐課程中,人類學課程及其實踐的介入,不僅可以拓展教育實踐的內涵,也能豐富教育實踐的視角和方法。基于人類學的教育實踐強調關注學生及其家庭、社區的文化。以超越認識工程(Beyond Awareness Project)為例,該項目旨在讓未來教師從僅僅意識到文化差異轉向發展思維習慣,包括理解學生文化并賦予其價值,認可在教學實踐中考慮這些文化的需要。項目要求未來教師對所在學校的社區進行跨度為7個月的文化觀察,觀察點可以是圖書館、課后項目、地方餐館或宗教機構,觀察次數不少于6次。觀察的重心不局限于種族問題,而是涵蓋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如關注人們的互動方式、行為模式、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運用等。未來教師需要記錄這些觀察,并就觀察對課堂教學的啟示寫一篇反思筆記。這些觀察也會被研究者進行編碼,以備后續深度分析。通過人類學方法的運用,未來教師開始與不同于他們觀點的人互動,通過這些互動,未來教師可以超越認識,去教課堂中所有的學生——尤其是那些因其文化遺產或差異而被忽視的學生。通過人類學研究,未來教師能夠更加批判性地檢視他們所觀察的情境,并質疑他們關于社區的信念和理解。[25]
四、結語:讓教師成為人類學家
利特福德(Littleford Michael S)曾提及教師與人類學家的諸多相似之處:“沒有對需要處理的多樣化情境的系列描述,教師和人類學家都無法完成他們的任務,因為在卷入之前,無法獲知所有的重要問題。他們都必須隨著新形態和關系的出現以及新問題的發現隨時調整他們的思維。為了操作更為有效,教師和田野人類學家都必須成為敏銳的參與性觀察者,這些參與性觀察者能夠運用必要智力工具以讓工作中錯綜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變得明確。”[26]利特福德認為,深度卷入、文化敏銳、參與性觀察、實踐智慧等構成了教師和人類學家的共通點,也蘊含了他對教育的理解:教育是一項需要教師深度了解、置身其中且充滿實踐智慧的文化實踐活動。就此而言,每一位教師都需要成為人類學家。讓教師成為人類學家,并不是讓教師成為教育實踐的旁觀者和描述者,而是主張教師運用人類學的視角、眼光、方法和知識,在系統觀察、描述和研究實踐的基礎上系統設計課程、教學和管理方案,從而實現教育目標。讓教師成為人類學家的理念對于多元文化激蕩的當代中國教育尤其具有實踐價值,它需要教師教育機構的理念更新和實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