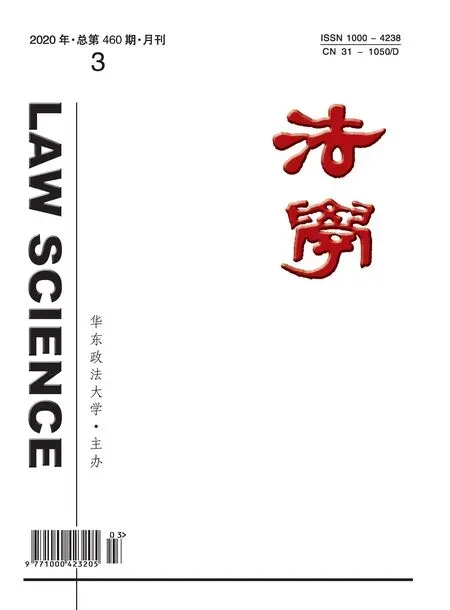“人民教育家”高銘暄先生法學教育思想研究
●徐 宏
一、引言
新中國七十華誕來臨之際,我的授業恩師高銘暄先生在榮獲“最美奮斗者”的表彰稱號之后,又榮膺國家最高榮譽——“人民教育家”的光榮稱號。黨和國家對這位為新中國刑法學教育和刑事法治事業不懈奮斗近七十年的泰斗級資深學者和教師給予了充分的褒揚與贊譽:“當代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作為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學者、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的撰寫者和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的主編者,他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這不僅是對先生個人的肯定與禮贊,也是對先生所念茲在茲的新中國刑法學發展的肯定與期許;不僅是先生個人的榮譽,更是所有為新中國法學和法治事業奮斗的同仁的共同榮耀。先生投身刑法立法六十余載,從全國人大成立伊始即全程參與刑法立法賡續至今,可以說新中國刑法立法的每一項成果都凝結著他的心血,堪稱新中國刑法史的全程見證者和參與者;先生亦投身刑法學研究和教學近七十載,著書立說未盡、教書育人無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高銘暄”,這三個字是改革開放以后所有法科學子和司法工作者都繞不開的名字,過去三四十年間幾乎所有的法學學子都是讀著他的書成長起來的,在這一意義上,他也是這些萬千莘莘法科學子的刑法學啟蒙老師。“人民教育家”這個殊榮,對先生來說是實至名歸。
作為教育家的先生曾經在多個場合闡述自己在法學教育領域的理念與方法,最集中系統的是在2013年12月2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新中國刑法學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暨高銘暄、王作富刑法教育思想研討會”上,先生發表從教六十周年感言,談了自己的五點體會:第一,要熱愛專業。第二,要武裝頭腦。具體而言,要做到以下四點:要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世界觀和方法論有所了解和掌握;要熟讀西方近現代刑法學名著;要對本國刑法學的宏觀發展有所了解,熟讀當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以及公認的水平較高的專著;要熟讀相關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釋。第三,要有良好的授課藝術。具體表現為四個“言之有”,即言之有物(向學生說明授課內容)、言之有理(有道理)、言之有據(有根據)、言之有情(有激情和感染力)。第四,教研結合。教學能夠發現疑難點,為科研提供素材和動力,科研能夠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反過來促進教學。第五,精心指導,做好研究生培養工作。具體而言,要遵循“三嚴四能五結合”的教學方法。“三嚴”即對學生要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訓練;“四能”即培養學生的讀書能力、翻譯能力、研究能力和寫作能力;“五結合”即學習與科研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面掌握與重點深入相結合、研究中國問題與借鑒外國先進經驗相結合、個人鉆研與集體討論相結合。〔1〕參見蔣安杰:《高銘暄、王作富刑法教育思想研討會在京舉行》,載《法制日報》2004年1月1日,第3版。這些看似平淡實則深遠的識見,乃是先生對他自己教育事業最為全面系統的回顧與總結。
作為受他親炙的弟子,在為先生成就倍覺與有榮焉之余,也懷著對先生至為崇高的敬意,嘗試對先生近七十年的教育成果、教育理念展開整理研討,茲以為不僅是對先生的責任,更是對中國法學界的交代。我認為,先生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始終秉持法學教育的人民性,始終抱持改革創新的精神,在法學教育領域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特風格的理念與范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理論體系的建立、發展和完善作出了開創性、關鍵性的貢獻。具體而言,在教育的認識論上,一貫性地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緊密結合、歷史和現實的共同關切、教學和科研的相互驅動,在教育的方法論上,創造性地踐行綜述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和討論教學法。
二、高銘暄先生的法學教育理念
(一)理論和實踐的緊密結合
理論聯系實際,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的正確思想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也是先生那一代馬克思主義學者治學立身的根本指針,可以說構成了先生作為人民教育家最鮮明的本色。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5月視察中國政法大學時指出:“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法學教育既要重理論,又要重實踐,法治人才素質的核心就是實踐能力”,“法學專業教師要在做好理論研究和教學的同時,深入了解法律實際工作,促進理論和實踐相結合”。〔2〕《習近平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 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養 勵志勤學刻苦磨煉促進青年成長進步》,載《人民日報》2017年5月4日,第1版。事實上,這也是先生長達半個多世紀一以貫之的治學執教理念與作風。關于這個問題,先生曾經有過多次透徹的闡述:“刑法學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法律學科,不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同時下功夫,不可能有深邃的造詣。我經常提醒博士生,既要掌握堅實寬廣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刑法學知識,注意理論研究,加強理論思維,又要時刻關心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進展,善于發現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不斷積累材料,注意面向實際,作出理論說明。不聯系實際,單純搞抽象的所謂理論研究,對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是不會有幫助的;但是缺乏理論分析,僅僅就事論事,那也是沒有說服力的,對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同樣是沒有幫助的。正確的做法是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從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際出發,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規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也就是說,一切結論都力求來自于實踐,并反過來服務于實踐。”〔3〕《高銘暄教授談:培養博士生的一些體會》,載《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95年第3期,第32頁。“要重視對刑法理論的學習,把刑法理論中的重點問題和疑難問題弄懂弄通,又要注意了解司法實踐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帶著這些問題有針對性地去鉆研刑法理論,鍛煉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真正把刑法學好學活。”〔4〕子犢:《高銘暄教授談如何學好〈刑法學〉》,載《法學之家》(法律版)1986年第1期,第24頁。先生特別指出:“關于理論聯系實際問題,我是不厭其煩地反復強調。”〔5〕同前注〔3〕。對于這個先生不厭其煩強調的問題,每一位弟子們都有深刻的體悟,陳興良教授就明確指出:先生和王作富先生作為偉大的刑法學家、教育學家,最突出的刑法教育思想是理論聯系實踐,并服務于刑事立法、司法。〔6〕同前注〔1〕,蔣安杰文。在七十年的教學科研生涯中,先生始終要求學生不要有象牙塔里做學問的夜郎思維,而是密切瞄準更為廣闊的法律實踐,他從來不將自己的舞臺局限于學校、課堂與講壇,而是積極地走出去,走入城鎮社區,走進辦案一線,走向國際社會,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情懷,不僅在學術界而且也在實務界結交了很多朋友,他對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群體和他們的職業生活都有深刻的理解,這些使得他的教學和科研始終展現出面向實踐、與時偕行的品格。先生的這一治學風格,也非常清晰而鮮明地體現在他的諸多學術成果之上。如1981年,受司法部委托,由先生領銜,集結了來自天南海北的在全國刑法學界皆稱一時之選的頂級學者編寫《刑法學》,作為新中國第一部高等學校統編法學教材,“在當時代表了我國刑法學的最高研究水平,其所建立的刑法學體系為后來的各種刑法論著和教科書所接受,成為各種同類著作的母本”,〔7〕陳興良:《轉型與變革:刑法學的一種知識論考察》,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10頁。在新中國刑法學發展史上具有拓荒開山的地位,整整教育了幾代法科學子,該教科書被當時的國家教委評價為“體系完整、內容豐富,闡述全面、重點突出,縱橫比較、線索清楚,評述客觀、說理透徹,聯系實際、解決問題”。〔8〕張杰、孫曉:《春風化雨 桃李天下》,載《教育與職業》2008年第19期,第67頁。又如,1988年,先生與王作富教授聯袂主編的《新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對犯罪論、刑罰論和罪刑各論中的一系列重要課題展開了專門、系統、深入的研究,開創了刑法專題研究論證之先河,成為當時刑法學專業研究生的必讀之書,從書名中即可望文生出其研究視角與路徑——理論與實踐的融合。
必須強調的是:盡管“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些話語框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風格,但是作為一種理念內核,也是全世界所有文明國家法學教育的共識元素,而且,在英美法系國家,這一元素表現得尤為突出并且愈發清晰。如2007年2月,美國卡耐基教學改進基金會發布題為“培養律師:為法律職業做準備”的主題報告,倡議法學院理應將學生所學習的法學理論、法律實踐知識和職業身份進行綜合。報告發布之后,引發了全美法學院對法學教育課程結構與內容的審視與修正,這種審視與修正的基本旨趣就是通過大學法學教育“搭建理論知識和實踐分析之間的橋梁”,將“正式的法律知識”和“法律實踐經驗”結合起來,將知識世界和現實世界融合起來,為學生將來從事的法律職業做準備。“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理念,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但是,在先生那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教育家那里,它特別綻放出熠熠的光彩,因為這是屬于他們的哲學底色。
(二)歷史和現實的共同關切
茹古涵今、鑒古知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要求,也是中國學術研究的傳統理念。先生在法學教學科研中,一方面始終將研究焦點置于現實的立法文本和司法實踐,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對歷史資料的整理和歷史資源的挖掘這樣一種刑法學元研究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后者,成為先生教學科研別具一格的特色。在先生的著述中,非常具有風格性元素的就是他帶領學生們完成的關于刑法和刑法學歷史的作品。如果說像《新中國刑法立法文獻資料總覽》(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中國刑法立法文獻資料精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這些著作僅僅具有史料價值的話,那么像《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以及作為這本書的修訂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這一部部嚴謹厚重的作品,無一不是新中國刑法學史上具有風向標或者里程碑意義的史論著作。《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1949—1985)》所開啟的文獻綜述式學術史研究范式影響及于整個中國法學界,《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則填補了新中國刑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這兩部跨越近四十年的接力之作,以翔實豐富的文獻資料和歷史信息,構成新中國刑法立法的縮微檔案館和全景紀錄片,在中國刑法學界引起巨大反響,先生的同事、北京大學資深刑法學教授儲槐植先生認為是“史詩般的書”,先生的弟子、時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姜偉贊譽該書是對刑法發展歷程全景式的敘述,是解讀刑法精神的教科書、描述刑法發展變化的編年史、介紹刑法條文沿革的路線圖〔9〕參見蔣安杰:《高銘暄:30年磨一劍》,載《法制日報》2012年10月10日,第9版。。作為唯一的新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刑法立法的全程見證者和參與者,先生以當事人和旁觀者兼具的視角,把新中國刑法立法的歷史掌故與細節向我們如敘家常般娓娓道來,讓我們充分領略了新中國刑事法治建設一路走來的風雨兼程。并且,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兩部著作里,先生花費了很多筆墨把立法機構、司法機關和專業學者這些中國立法的多元參與群體在一個條文、一個規定上的不同方向、不同方式的參與原汁原味地向讀者呈現出來,而且這種呈現是中立的、不帶偏見和傾向的,只有客觀的敘述,不作長短的評價,如同一個紀錄片的攝影師一樣。這種高峻和沉穩所體現的是對學術知識的平等尊重和開放包容,這恰恰是中國學界所匱乏的學術涵養。可以說,先生長達半個多世紀參與國家刑事立法核心過程的實踐,在世界法律史上都是極為鮮見的。新中國刑法每一次前進的步伐,背后都有先生的推力。像先生這樣資望的人物來講述新中國刑法的變遷歷史,的確可謂如數家珍了!而除了先生以外,恐怕真的很難找出第二人能夠擔當這一角色了!這兩部作品在中國刑法學術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怎么評價都不為過。在2013年12月28日的“新中國刑法學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暨高銘暄、王作富刑法教育思想研討會”上,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教授盛贊先生和王作富先生能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國問題,完美地將歷史文本解釋與立法、司法相結合,這是其他學科需要借鑒的,〔10〕同前注〔1〕,蔣安杰文。這也可以視為對先生這部作品的精準評價。
當然,我們還應當看到:先生在這些經典作品中展現的追本溯源、探賾索隱、旁搜遠紹、鉤沉發微的治史藝術,絕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懷舊與厚古情結。回顧歷史,從來都是為了審思現實、展望未來,歷史是給當下和未來的一面鏡子,這一點在《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中已經做出清晰的交代。先生在學術上不僅不屬于抱殘守缺,反而具有強烈的開拓創新意識,他如炬的學術目光,及于歷史和未來,達于中國和世界。他從來都是直面中國刑法學的嚴峻問題:“四十年來,受法律實用主義影響,刑法學的理論研究完全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否認刑法學自身的理論特點和學術品格,要求刑法學研究完全圍繞注釋法律、圖解政策來進行。這樣,刑法學理論就得不到全面系統的發展,應用性過于突出,注釋刑法學發展較快,而理論刑法學發展則比較緩慢。同時,受法律教條主義影響,刑法學研究存在著脫離我國實際情況,硬性照搬蘇聯刑法學理論的現象。迄今為止,我國刑法學理論體系仍沒有大的變動,仍然是蘇聯50年代的模式。”〔11〕高銘暄主編:《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他“一直認為自己的外文不夠好,為不能閱讀更多的外國法學典籍原文而深感遺憾。在對博士生的指導上,總會告訴學生自己的不足和遺憾,希望他們不要被相同的不足所束縛,努力提升外文水平,盡量做到閱讀法學典籍的原文”。他認為“現代法學的源頭,根植于西方國家,而且各國的法學發展各具特色,在全球化日漸加速的當下,要做好刑法學研究,就必須擁有世界的眼光和角度,不僅要看中國固有的法學文獻,還必須多多閱讀外國的法學典籍”。〔12〕高銘暄口述、傅躍建整理:《我與刑法七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8-101頁。先生對于中國刑法學犯罪構成理論的堅守,并不是學術利益之爭,而是對自己學術信念的執著,先生并不先入為主地反對某一種特定的刑法學理論或者話語,相反,他對學術發展始終抱持開放樂觀的姿態,他所反對的只是純粹做外來知識的物理搬運工或者以推倒重來的方式實現所謂知識革命,因為這些方式都違背了知識的自然演化秩序。尊重知識的生成進路和生長秩序,通過平等的學術批判的方式與路徑,實現中國刑法學知識體系的持續更生,這是先生以及先生這一代刑法學者們樂見其成的事情。“刑法學者應當獨立思考,堅持學理探討,具有高度的科學信念。學術上沒有禁區,應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3〕高銘暄:《十年來的刑法學研究》,載《法律學習與研究》1989年第5期,第8頁。,這也是他一貫的主張。所以,他曾經非常深情地說:“我從事這份職業也有一點目標追求,我是想把中國刑法學能夠搞上去,不甘心落后,要躋身于世界之林,讓世界承認中國刑法學也是有它的特色和獨到之處的。”“我認為只要我們國家富強,有影響力、有吸引力,刑法學就會做大做強,不會矮人一截,不會跟著西方的屁股亦步亦趨,這點志氣我是有的。”〔14〕蔣安杰:《八十八歲高銘暄教授成為最年長“法學博士”》,載《法制日報》2016年11月30日,第9版。對于中國刑法學自強的誠摯期望,溢于言表,令人動容。
(三)教學和科研的相互驅動
述學立論與傳道授業相結合,研究與教學相支撐,既是中國學術的傳統理念,也是現代大學的核心理念。一流的大學必然是一流的研究機構,一流的教書者也必然是一流的學問家。先生的弟子胡云騰在2013年12月28日的“新中國刑法學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暨高銘暄、王作富刑法教育思想研討會”上強調先生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持續不斷的科研成果作為教學的支撐〔15〕同前注〔1〕,蔣安杰文。,這是非常到位的總結。先生曾經說過:“我信奉你要給別人一桶水,你自己必須有十桶水的說法。這是我的恩師李浩培對我作為教師的耳提面命。”〔16〕同前注〔12〕,高銘暄、傅躍建書,第90頁。所以,他非常重視教學與科研相互反哺的效果,堅持認為:“教學能夠發現疑難點,為科研提供素材和動力,科研能夠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反過來促進教學。”“只有真正做到教學與科研兩者并重,才能達到啟發學生思維、教會學生學習方法,教學相長、教研并進的良好效果。”〔17〕同前注〔8〕,張杰、孫曉文,第 66 頁。2019年11月21日,先生受邀在北京大學舉行主題教育專題講座,在其中更是明確指出:“大學教師要正確處理教學和科研的關系。科研是教學的基礎與后盾,能夠充實教學內容;但如果只一味強調教學內容,而不掌握科學的教學方法,也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收獲良好的教學效果。因此,大學老師應當妥善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實現教學和科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18〕http://pkunews.pku.edu.cn/pub/pkunews/xwzh/83059041607a437abe6b393c5641b70b.htm,2020年1月7日訪問。
可以說,支撐先生教學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不僅僅是一種基于熱忱的情懷,更重要的是寬厚的學殖、穩健的學養。特別是碩士生、博士生培養,沒有科研的支撐和夯實,是無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說,研究生培養的本質要義就是科研引領和驅動。先生在執教治學路上為我們奉獻的一系列作品,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他和弟子們集體工作的成果,他是其中的導引者、參與者,更重要的是,他是永遠的創意者、構思者。如1994年10月,先生主編的法學鴻篇巨帙《刑法學原理》三卷本,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成果,就是先生與一眾弟子十余載心血的結晶,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刑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精華之大成,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刑法學的最高理論水準和學術品位,事實上也成為其后近十數年間中國刑法學碩士生、博士生的基本專業教材,因其紅色封面裝幀而被刑法學子們親切地稱為“紅皮書”。該書出版之后,囊括了許多學術與出版界的至高榮譽,1995年榮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1996年摘取國家圖書最高獎項——第二屆國家圖書獎。可以說,改革開放以后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帶領學生完成的一部部鴻篇巨著,在新中國刑法學領地上,既是留下來的一串串厚重的足跡,也是攀爬過的一座座巍峨的高峰。而先生的弟子們,也正是在這種永無止境的行進與攀登中獲得豐富的歷練,得到壯碩的成長。在當代中國法學界,有的學者基于學術獨立責任的精神認為學術創作是學生個人的事情,甚至認為教師與學生合署發表或者聯名出版學術作品不符合學術生產的真實機制,也不契合學術市場的競爭規則。但是,在先生那里,他認為研究生導師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通過合作撰文、集體出書這種協同性科研生產,在培養學生學術創作水準的同時,也提升學生在學術市場的能見度,對于后者,他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先生曾經用“孵小雞”來比喻這種集體學術訓練,他認為老師應該像母雞孵化小雞一樣把學生一個個帶出來,而這種集體科研生產機制就具有某種“孵化器”的意義。我們在先生過去三十四年間所催生的一部部學術作品中所看到的那些名字,當年或許有些青澀,而在今天的中國刑法學界已經如雷貫耳了,這些名字所組成的名單實在太長太長了,這是先生對新中國刑法學教育最為實質性的貢獻,誠如2015年4月第十三屆聯合國預防犯罪與刑事司法大會上國際社會防衛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ocial Defence)為先生頒授“切薩雷?貝卡里亞獎”時所給予的贊譽:“他的教學研究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資深學者,他們活躍在世界各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長為國際學術界的棟梁之材”,“大師之所以謂大師,不僅在于其著述,還在于其培育團隊和學派的能力,這正是高銘暄教授”。是的,如果說成為一個法學家,或許只要成就自己就可以了,但是要成為一名法學教育家,那么更重要的則是成就他人,而相對于“法學家”而言,“法學教育家”意味著多了這樣一種境界:“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寬闊胸懷與博大胸襟。
三、高銘暄先生的法學教育方法
(一)綜述教學法(Literature Review Teaching)
文獻綜述是西方學術界的一門基本技能,也是現代大學教學中的一項重要方法。但是,在先生這里,將文獻綜述引入教學領域卻是具有濃厚的故事色彩的。這個故事還要回到文革歲月,1971年1月,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勞動鍛煉的先生被通知回到北京,因為原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在三個月前的1970年10月已被宣告停辦,所以只能被分配到當時的北京醫學院工作。這樣,先生在北京醫學院一呆就是八年,直到“文革”結束后兩年的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恢復建校。在北京醫學院,先生先是做教務工作,后改做醫學史研究工作,接觸到大量醫學科研資料,發現了醫學研究者慣于采用文獻綜述的方法開展研究,于是他就開始關注醫學綜述方面的文章,并且嘗試撰寫了大量的醫學史文獻綜述資料。后來,他重返刑法學講壇,就嘗試將這種方法引入了刑法學教學研究領地。“在刑法學研究中,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是一種調查研究、獲得規律性認識的有效方法。我們要求研究生在專業學習階段,每個學期都要做刑法學文獻研究綜述。他們根據選擇的課題,對建國以來針對這個課題所發表的文件、教材、論著、文章,通過閱讀、摘錄、做筆記、從中比較其觀點的異同,并作定量和定性分析,然后客觀地加以歸納總結。”〔19〕高銘暄主編:《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頁。“文獻綜述推行后不久,學生們紛紛表示,一個大課題做完,差不多也把一門課程學透,獲益良多。這種方式,不僅培養了他們閱讀能力,還大大拓展了視野,最重要的是讓他們學會了思考,學會了形成自己的觀點,培養自己的學術方向。”〔20〕同上注。陳興良教授在回憶到師從先生學習刑法學的路程時動情地說:“在刑法總論講授中,高銘暄教授布置我們每人做一篇綜述,正是通過綜述的方法,使我進入刑法學研究的大門,成為刑法學術活動的起點。”“我們是恢復學位制度以后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因而也是高銘暄教授綜述方法的第一批受益者。”〔21〕陳興良:《始于綜述的刑法學術之路——師從高銘暄教授研究刑法的個人經歷》,載《中國審判》2007年第9期,第23頁。
事實上,先生的文獻綜述不僅體現在教學領域,也體現在科研領域,首開先河之作就是曾經在新中國刑法學史上具有開拓性價值的以“工作札記”命名的立法回憶錄。1981年,先生以自己在1964年撰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學習紀要》為底本,參酌自己珍藏的刑法草案第22稿、第33稿以及1979年刑法典文本,參照當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刑法起草班子工作時期所做的筆記,寫出了近20萬字的書稿,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個工作人員的札記》,忠實記錄了新中國刑法典從1954年到1979年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孕育、難產、分娩的全過程,不僅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部刑法學專著,而且也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部法學專著,以此拉開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法學學術研究的帷幕,被學界譽為刑法學的“源頭活水性”著作、“拓荒之作”,連先生的刑法學啟蒙恩師李浩培教授都給予了極高評價:“這是我國刑法學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如果欲諳熟我國刑法,是必須閱讀的。”〔22〕趙秉志、陰建峰:《新中國注釋刑法學的扛鼎之作——試評高銘暄教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08頁。該書甫一出爐,在那個知識極度貧瘠的年代可謂炙手可熱,刑法學界爭相傳閱,競相援引,幾至“洛陽紙貴”,一度脫銷斷供,甚至有手抄本面世。此后,中國刑法漸次發達,由疏臻細,由粗轉精,單行刑事法律和附屬刑法規范接踵出臺,先生與時俱進地厘訂與充實了這本書,于2012年出版了85萬字的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陳興良教授認為:“在1980年11月寫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的序中,高銘暄教授就已經使用了綜述一詞,稱該書是根據在長達30年時間里參與立法積累的資料、記錄和筆記, 按照刑法的章節條文次序所作的一個整理和綜述, 實際上也就是一部回憶性的學習札記。高銘暄教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稱為一部綜述性的著作,當然是一種謙遜的說法。實際上,這本書中包含了高銘暄教授對刑法中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當然,由于這本書的性質所決定, 其中確實主要是對刑法制訂過程改動情況的一種綜述。”〔23〕同前注〔21〕,陳興良文,第22頁。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這本小冊子只是形式意義上的綜述,那么六年之后的1986年,由先生主編完成的《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1949—1985)》一書則直接將“綜述”這種研究方式推向了學術舞臺的前沿,在該書序言中,先生對綜述方法作了以下總結性的評價:“在刑法學的研究中,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是一種調查研究、獲得規律性認識的有效方法。通過專題性綜述,不僅使作者本身科研的基本功得到訓練,而且也給其他人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調查研究資料。所以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方法。”〔24〕高銘暄:《新中國刑法學研究概論——〈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1949-1985)〉序言》,載《法律學習與研究》1986年第6期,第23頁。此后,受其示范激勵,我國幾乎各部門法學的綜述性著作猶如雨后春筍般地生長發育起來,例如,1990年,《法學研究》編輯部組織編撰了《新中國民法學研究綜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參與其事者包括張新寶、孫憲忠、徐國棟、張廣興等教授,如今均已成為民法學界一方大家,1991年,出版了常怡教授主編的《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綜述》(長春出版社1991年1月版),還出版了兩部行政法學綜述性著作,分別是許崇德教授和皮純協教授主編的《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1949年-1990年)》(法律出版社1991年6月版)和張尚鷟教授主編的《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綜述與評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9月版)。此外,綜述研究方法還超出部門法范疇,及于會議、專題等各個領域,比如,幾乎所有的學術會議特別是年會都會形成一份綜述性論文,這在刑法學界已成定則。由此可見,先生“在法學界首倡的綜述方法,不僅惠及刑法學界,而且也被其他部門法學界所采用,這是高銘暄教授對我國法學的貢獻。”〔25〕同前注〔21〕,陳興良文。先生對自己的這項創新成果也懷有非常珍視的情愫:“隨著中國學術界與國際接軌日益頻繁,風行于歐美各個領域的文獻綜述,逐漸為中國相應的領域所接納。然而,在中國刑法學研究領域,卻是我首先從醫學領域借鑒來的。此后,文獻綜述在法學研究范疇內大量使用,乃至在一些特定的活動中,把這種方式作為固定的科研手段。”〔26〕同前注〔12〕,高銘暄、傅躍建書,第91頁。
(二)討論教學法(Discussion Teaching)
討論式教學是培養獨立人格、批判精神與合作意識的必由之路,意味著在課堂這個空間里,不僅學生和學生之間是平等的,而且教師和學生之間也是平等的,教師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而且教師本身也應當從學生中獲得知識的增長,這就是所謂的師生互動、教學相長。討論式教學,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的早期歷史中,在孔子和蘇格拉底那里,都是主流教學方法。這一傳統在西方一直得到了傳承與延續,但是,中國在西漢中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就窒息了教學中的討論空間,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教學純粹成為傳播甚至灌輸知識的單維行動,師生之間也形成一種尊卑高低的等級秩序。辛亥革命之后,西學東漸之風日盛,西方的開放式、討論式教學模式在中國漸次生長起來,先生在浙江大學法學院和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習中都從中獲得教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跟隨蘇聯專家的學習中,先生也感受到了“課堂討論”(семинар)的魅力。當時蘇聯的教育體制與理念雖然表現出強烈的集中統一的政治色彩,也非常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和系統知識的傳授,但是,作為歷史文化上的西方國家的傳承,具有歐陸教育傳統意義的“習明納爾(seminar)”即課堂討論在蘇聯教育體系中仍得到保留,并且在社會主義教育民主化、大眾化的意識形態浪潮中加以發揚。這種教學方式同樣契合了新中國教育領域反封建、獨立自主的意識形態主流,因此在建國初期被作為蘇聯經驗引進我國,而作為實踐“以俄為師”典范的中國人民大學無疑在其中發揮了先行和示范角色,“中國人民大學在教學工作中引進了蘇聯各方面的經驗,‘習明納爾’是其中重要的經驗之一”。“‘習明納爾’即在教員的直接領導下有計劃、有重點、有準備地進行關于課程內容的討論與研究的一種教學方法。”〔27〕劉經宇:《中國人民大學的“習明納爾”》,載《人民教育》1951年第5期,第29頁。“早在1950年代,人大法律系就形成了大課、‘習明納爾’、輔導相統一的教學方法。‘習明納爾’是在大課講授之后用來復習的有效方法,其作用在于檢查學習、加強復習與應用,在鞏固教學效果和培養學生思考能力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28〕韓大元:《中國法學的“人大學派”》,載《法學家》2010年第4期,第4頁。在自己走上講壇之后,先生就以各種方式積極實踐這種教學方法,他非常明確地強調:“要提倡啟發式,反對注入式,精講勤練,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除了課堂講授外,還要通過案例討論、輔導答疑、模擬法庭、調查研究、實地參觀、法律咨詢、業務實習、寫作論文等各個環節,加強理論聯系實際,培養學生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調查研究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進一步獲取知識的能力。”〔29〕高銘暄:《搞好教學改革,為培養具有較高水平的法律專門人才而努力》,載《法學雜志》1984年第5期,第8頁。為了使這種討論式教學法得到落地,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創造性地提出“三三制”的課堂互動教學模式,即提前確定刑法學中若干專門的問題,由研究生分工進行準備,就某個問題,對國內已經發表的所有文獻資料(包括教材、專著、論文)進行閱讀,然后加以綜述,分析在該問題上都存在哪些不同的觀點,理由論據是什么,本人的意見是什么,也就是提出一篇讀書報告或者文獻綜述,然后,在課堂上,先由研究生作中心發言,約占1/3時間,再由別的研究生提出質疑、補充或大家進行討論,占1/3時間,最后1/3時間由導師進行小結。〔30〕同前注〔3〕,第 31 頁。可見,先生所創的討論式教學,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以閱讀為前置,以科研(即文獻綜述)為核心,這就確保了課堂討論的學術訓練的品格與氛圍,從而避免成為不著邊際的空談、清談。在新中國法學教育的那個初興時期,即使是蘇聯的“習明納爾”這樣一種具有社會主義親緣關系的教學方式在中國也因為不能兼容于強大的傳統文化而銷聲匿跡,整個教學環境被刻板的說教灌輸模式所覆蓋,先生能夠重視學生的課堂主體作用,將合作式、啟發式、討論式方法引入教學,委實展現了一種遠見和勇氣。誠如方流芳先生所言:“嘗試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方法是需要一定勇氣的。因為,一個不向學生推出正確結論的教授往往被認為無能,而一個敢于對教授質疑的學生往往被認為不敬,這已是相沿成習、難以改變的課堂規矩。”〔31〕方流芳:《中國法學教育觀察》,載《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8頁。
(三)案例教學法(Case–based Teaching)
案例教學法是英美國家法、商、管、醫等專業學科最具特色的教學訓練范式,但是其最初落地還是屬于法學教育領域,最早由英國學者貝葉斯在19世紀20年代引入,然后在19世紀70年代為哈佛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蘭德爾教授所革新光大,經過一百多年的創新發展,如今已演化成為西方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法學教育奪目的異彩,并且在這個教育理念的基礎上衍生出“模擬口頭辯論練習”(Oral Argument Exercises)、“診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等風靡全球的情景化、實驗性法律教學方法。但是,勿庸諱言,因為中國教育至今仍未走出知識傳播工具理性的歷史因循,中國的法學教育素來都是經院式、偏人文性的,案例在中國法學教學中仍然是邊緣化的。先生的案例教學理念的濫觴,則應當從他的刑法學啟蒙恩師李浩培教授那里尋獲。1947年9月,先生入讀浙江大學法學院時,第一個學期的刑法總則課程即由畢業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李浩培院長親自教授。先生對他的記憶是極其深刻的:“他站在講臺上,給我們講授刑法,思路清晰,案例生動,板書漂亮。也許是從英倫學成歸來,他看起來風度翩翩。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刑法學好。”〔32〕韓寒:《高銘暄:一部刑法典38稿 25年》,載《光明日報》2012年9月15日,第9版。作為留英歸來的學者,李浩培教授將英倫教學旨法帶入自己的課堂,他特別喜歡援引各類案例,深入淺出地講解刑法法理,燃起了先生對刑法學的濃烈興趣。在先生后來的教學生涯里,他一直認為法學是世俗的學問,要求學生關注現實,著眼于中國法治實踐的原生態,在生動豐富的實踐素材、實踐氣象中推動刑法學知識的生長更新,他用案例教學法來填充、夯實“三三制”討論式教學法的內容,注重在案例的推演剖析中拓展學生的法律人思維訓練,強化學生的問題發現、識別和歸納、解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養成未來法律人對法律職業理想的皈依、對法律職業倫理的認同以及公共精神、社會責任意識。并且,先生對于案例的視野,不僅及于教學領域,更及于科研領域,他一直以來都在各個場合強調中國這樣一個成長中的土地、人口大國基于案例豐富性、生動性而賦予中國刑法學研究的優越的資源稟賦:“現實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也非常豐富。中國所辦的刑事案件比外國哪一個國家都要多,應該可以支撐我們這門學科成為顯學。”〔33〕同前注〔14〕,蔣安杰文。在先生這種學術銳意的背后,是一位老一輩學者對中國刑法學寄寓的厚重期望。這個時代的中國比歷史上所有時代的中國都要精彩繽紛,身處這樣一個挑戰與機遇并存的生機蓬勃的國度,對于刑法學研究來說是一種難得的福祉,也可以說今天是中國刑法學人不應辜負的黃金時代。
四、結語
通過上述檢討,我們可以獲得這樣一個結論:先生的教育理念和范式,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基調和底色的映襯下,既有中國傳統的教學相長、疑義相析、青藍互動等元素,又有西方現代的批判思考、平等對話、個性發展等元素,這一切充分體現了一位人民教育家的現代視野、國際眼光以及求真、務實、開放、創新的品質,是先生對于中國法學教育事業垂范深遠、彌足珍貴的貢獻。
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中國政法大學時指出:“法學學科體系建設對于法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在法學學科體系建設上要有底氣、有自信。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深入研究和解決好為誰教、教什么、教給誰、怎樣教的問題,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建設作出貢獻。”習總書記提出的這個問題,也是先生不懈追問與深思的課題,而且,他對這個教育問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思考、探索和實踐,促成了中國刑法學陣容的根深枝繁、葉茂花榮,構成了法學教育的中國風格、中國流派,這是我們禮敬先生的理由,也是先生摘取“人民教育家”桂冠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