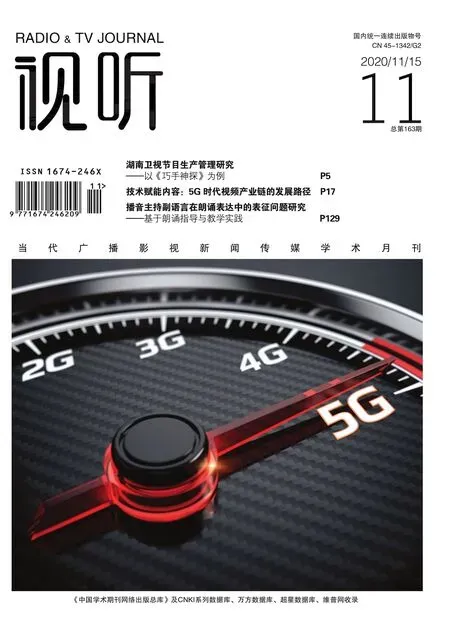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ALMA》:一部人性異化的鏡像寓言
□ 樊黎明
西班牙導演Rodrigo Blaas執導的恐怖動畫短片《Alma》,是一部具有鮮明寓言特征的短片。片中沒有傳統恐怖片經常出現的血腥暴力、廝打殺戮等驚悚場面,也沒有妖魔鬼怪、殘肢斷臂等重口味元素的直接出現,卻依然帶給觀眾驅之不散的精神夢魘。而造成這種觀影體驗的,正是隱藏于情節背后的深層主題。
如將《Alma》置入精神分析視野里進行觀照,就會發現這是一部具有高度拉康品格的動畫,片中包含明顯的“鏡像”情境再現,蘊含人類自我認同的本質真相。本文以鏡象理論為參照,探討影片的主題意蘊,分析影片內在結構的具體隱喻與表達方式。
一、“鏡像理論”闡述
“鏡像理論”由后現代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提出,其概念涉及“主體”“自我”“他者”“大他者”。其中“大他者”指的是主體誕生的場所,包括語言文化系統、父母的話語、社會主流意識等,代表一種社會秩序和規則。“小他者”也是“鏡像”,是別人的形象,代表的是秩序規范的理想自我。
“鏡像理論”具體講的是“嬰兒/主體”最初并沒有自我概念,直到在“母親/大他者”的指認下通過鏡子看到自己,把鏡像當成自己,對“我”產生類似弗洛伊德闡釋的自戀情結,標志著“自我”意識的萌芽。但是,這種“自我”是一個幻象,本質上是由別人指認的形象,是個“小他者”。而這種對鏡像的誤認卻是一種終生模式,主體在成長過程中會尋找各種形式的“鏡像/小他者”來修正自己的存在。因而,主體追求“自我”的過程實際上是被“小他者”改造的過程,主體的欲望其實是他者的欲望。不幸的是,主體對此毫無意識,主體意識的自主性表面上看起來是主體的選擇,而實際上都受到“大他者”的影響與驅使。
拉康的鏡像理論是對主體、自我、小他者、大他者之間關系的深入思考,是對人的主體精神意識運行的本質研究。
二、鏡像隱喻與意象表達
《Alma》故事講述了主人公艾瑪與玩具店之間的一場誘惑與欲望博弈。玩具店以一個和艾瑪外形一模一樣的人偶為餌,對艾瑪展開欲擒故縱的引誘,而艾瑪在誘惑面前,逐漸喪失理性,迷失在對人偶的占有欲中,一步一步被引誘到玩具店內,成為囚禁在人偶體內的欲望奴隸。我們以拉康鏡像理論來解讀《Alma》的劇情,不難發現這部影片講述的其實是人與鏡子的故事,是一個拉康式的主體異化寓言。影片中的玩具屋、艾瑪、人偶等形象與鏡像理論中的“大他者”“主體”“小他者”等概念形成完美對應。
(一)艾瑪:主體
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主體”的意象表達。一般影片里的角色視覺造型,無論簡單還是復雜,其中年齡、性別等基本身份屬性,是觀眾認識角色的一個直觀印象,是觀眾可以通過外貌獲取的初步信息。但是該片中主人公不管是外貌、穿著還是行為舉止都偏向中性化設計,無飾品的毛氈帽、齊耳短發、坎肩垮褲的穿著,以及角色大大咧咧的動作都沒有明確的性別指向。直到影片講述主人公在墻上寫下自己的名字Alma時,才揭示其身份是個女孩。而Alma這個名字的含義還有生命、靈魂、人、主體等含義。導演顯然是借用名字的意義與超越性別的視覺設計,讓這個角色代表“人”這一符號——一個精神分析語言系統中的主體。尤其是Alma又是影片的片名,該角色象征意義也得以證實。
(二)玩具屋:大他者
玩具屋是“大他者”的意象表達。玩具屋的出場形式就極具意味。開片第一個鏡頭結尾處,當主人公走出畫面,鏡頭不但不跟隨人物運動,反而搖向相反的方向,將畫面投向了玩具屋。畫面中的玩具屋有個巨大的櫥窗,窗欞輪廓像一只張開大嘴的怪物形象,窗沿墻體有鱗片化的圖案,整體設計有一種強烈的生物性特征。而此刻的窗玻璃正好映照出畫外的主人公:主人公此時正注視著一堵簽名墻。這種“畫中畫”構圖所傳遞的視覺意義具有多義性,一方面它暗示出看者與被看者之間的窺視關系,讓觀眾感覺到玩具屋如同一個怪物,悄無聲息,虎視眈眈地監視著闖入它領域的獵物,給主人公的命運鍍上一層不安的色彩;另一方面,在鏡頭語言表達中,帶著折射內容的鏡子、玻璃以及其他反射物,往往是一種具有精神分析意義的敘事鋪墊與伏筆。在這場戲中,主人公凝視著一堵簽名墻,玩具屋在背后凝視著主人公看簽名墻,其情景猶如嬰兒凝視鏡子,母親在背后影響并控制著嬰兒。片中的玩具屋,正是鏡像結構中的“母親/大他者”,指的是“嬰兒/主體”存在的權利場所,它暗中操控著主人公自我意識的產生、建構與異化。
(三)簽名墻與人偶娃娃:鏡像/小他者
簽名墻和人偶娃娃,是對“鏡像/小他者”的意象表達。簽名墻是艾瑪的第一面鏡子。當艾瑪看向簽名墻,不甘落后在上面簽下自己的名字,這一模仿舉動印證了鏡像誤認的核心邏輯——通過認同別人、模仿別人來完成自我認同,通過認同別人的形象來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構。因此,簽名墻這個場景元素對于艾瑪來說就是一面合格的“鏡像”,它激發了艾瑪“自我意識”的覺醒。
人偶娃娃是艾瑪的第二面鏡子,推動主人公完成了自我的最終異化。如果說簽名墻作為鏡像的意象表達還比較含蓄,那么這一次鏡像關系隱喻中,導演利用玻璃、艾瑪版娃娃與艾瑪一起又一次復現了嬰兒照鏡的情境。當艾瑪透過玻璃窗與一個與她一模一樣的娃娃對視時,一個完美的鏡像隱喻得以清晰呈現。艾瑪在翻版娃娃身上找到理想自我而陷入幻想式的認同,于是鏡像迷戀情結在艾瑪身上被觸發,讓艾瑪對這個人偶娃娃展開了入魔般的追逐。
(四)影片結局:異化宿命論
蘇聯劇作家霍洛道夫曾說:故事的結局是領悟劇本的鑰匙。可以說,結局是一個主題表現與把握、創作理念與敘事風格緊密相關的問題。出色的影片結尾往往能成為升華影片主題的重要技巧。
影片結局,艾瑪追逐著人偶一步一步被引誘到店內,猶如一個強迫癥患者,眼里除去追逐的目標,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自投羅網的那一刻,艾瑪肉體消失,靈魂則被吸入人偶,與人偶融為一體,一瞬間自我被他者異化的結果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影片的尾聲,鏡頭緩緩拉出,讓我們看到屋里還有眾多與艾瑪一樣被囚禁著靈魂的人偶,國籍各異、年代各異的娃娃,亞洲的、歐洲的、中世紀的、現代的……故事本該到此結束,然而影片卻又啟動了一個新開始。在熟悉的開場音樂旋律中,一個紅袍女孩人偶在玩具屋櫥窗口旋轉升起。其出場的視覺方式,與故事開場艾瑪版人偶的出場非常相似。這種處理方式,顯然不是為了加深觀眾的記憶,而是為了激發觀眾的聯想,讓觀眾意識到故事在結構層次上形成一個首尾呼應的架構,并讓觀眾能夠將艾瑪與其他人偶的故事巧妙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緊密呼應關系的整體。縱觀全劇,囚徒艾瑪的經歷不僅是玩具店里所有人偶們的悲劇縮影,更是下一個孩子命運的冷酷寫照,以一斑窺豹的方式傳遞群體命運的普遍性與自我異化的永恒性。
三、結語
綜上所述,動畫《Alma》通過嚴謹的鏡像結構設定,建構起一則關于靈魂自省的鏡像寓言。玩具屋、艾瑪、人偶娃娃等角色設定和他們之間呈現的鏡像結構關系,以及顯而易見的鏡像情境再現,都揭示了拉康式的主體異化命題。而抽象的理論闡述,被導演轉化為各種可視可聽的意象符號,不落痕跡地穿插在影片的視聽結構中。小到角色名字、場景道具,大到情節主題,都被賦予象征意義,使得這部短小精悍的動畫呈現出意蘊無窮的解讀空間,引導觀眾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潛伏在精神世界的災禍,警醒人們在這個無序繁雜、充滿誘惑的世界中追尋自我身份與價值的同時,務必時不時停下腳步,回望與反省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