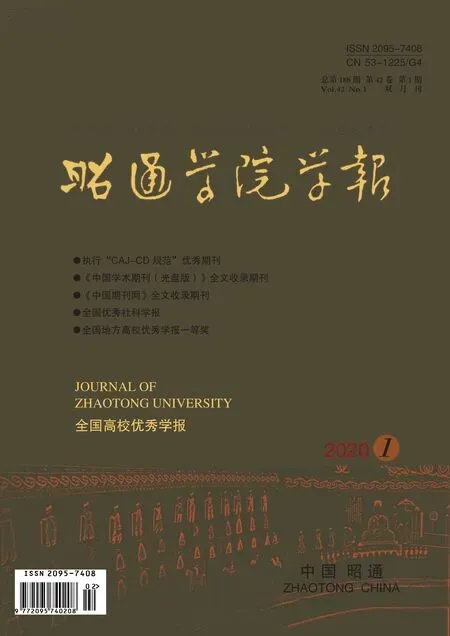源承、及物與模仿
——漫談王單單的詩
魯守廣
(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 文學院, 云南 麗江 674199)
新世紀以來,詩歌一直舉步維艱,諸如“下半身寫作”“垃圾派詩歌”“低詩歌寫作”“梨花體”“羊羔體”“裸體朗誦”“詩人假死”“新紅顏寫作”等等野怪黑亂的浮躁式噱頭式表演層出不窮。而近年來,云南大批的青年詩人凸顯,被稱之為“云南青年詩人群”,這在國內詩歌界不容樂觀的邊緣化、低端化、粗鄙化和娛樂化的大環境下極為難得。云南作為天生的“詩域”,是現代與后現代進程中殘存的“山水”物化之實體,其詩意已然是一種“人生之常”,滋養了一代代或無名或“有名”的詩人。針對云南當下的新詩研究,從大的范圍來看,是較為活躍的。云南省內學者宋家宏、胡彥、蔡毅、李騫和馬紹璽等均寫有論述于堅或雷平陽詩歌的文章或者專著;洪子城與劉登翰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涉及到于堅和雷平陽,在評述80年代中后期的詩和90年代的詩時,用很大篇幅介紹到于堅的詩歌道路;吳思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在“詩人型評論家”這一章重點談到于堅的詩學思想。已故學者陳超、南開大學羅振亞、西安財經學院沈奇和中山大學謝有順等也均寫有研究于堅或雷平陽詩歌的論文。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的霍俊明對云南詩歌界一直較為關注,對于堅、雷平陽乃至王單單多有論及,2019年出版有《于堅論》。另外,美國漢學家梅丹理、德國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與荷蘭漢學家柯雷對于堅的詩歌創作比較關注,柯雷寫有《于堅詩歌中的客觀化和主觀化》。從以上梳理可知,很大一部分學者的關注點多集中在于堅與雷平陽身上。這種研究狀況在近年來已然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變化。王單單、祝立根、胡正剛與張雁超等人已經成為云南詩壇新生的重要力量,評論界對這一群體創作的整體關注度開始提高。2016年9月由中國作家協會和《詩刊》社主辦,中共昭通市委和云南省作家協會聯合承辦,在昭通市舉辦了“茶馬古道上的云·云南青年詩人研討會”。時隔兩年后,在2018年11月24日,由《詩刊》社、云南省文聯、云南省作協聯合主辦的“云南青年詩人研討會”又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在這個云南青年詩人群體中,王單單是較為搶眼的一個。
一、源承
作為雷平陽的嫡系傳代人,王單單在創作上又同時打上了于堅的烙印,王單單的幸與不幸均在于此①。同為新詩界的兩大巨頭,于堅和雷平陽的詩與詩學對云南詩歌現場以及發展向度的影響極為深遠。在于堅的詩中存在著先鋒與傳統的二律背反,但又并非先鋒與傳統所能窮盡。于堅主張詩教,注重人生在大千世界中的種種具體狀況以及具體的情感性存在,以“詩”對抗庸常,傳達出生活中的詩意之美,從而引領世人的日常生活,其詩歌創作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不舍眾生”。作為大地詩人,于堅的詩是通過具有神性或者說巫性的漢字神化或者升華了的人生經驗。所以說,以“先鋒”名世的于堅,在本質上卻是最傳統的詩人。于堅的詩與詩學文本在蘊含上極有廣度,其詩學思想來源較為駁雜,對于中西方思想資源都有所吸收轉化,所以不好把握。雷平陽詩歌的受歡迎程度較高,獲得了大眾較廣泛的接受。筆者在《略論雷平陽的詩歌精神》一文中認為雷平陽的詩歌是有操守和風骨的,絕不只是大多數人所理解的所謂苦難的敘事,而是與中國傳統的古典詩文創作一脈相承,蘊含著關注現實的理性思考,針砭時弊的憂患意識,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以及遺世而獨立的出世精神。于堅與雷平陽的詩歌創作與其詩學思想引發了云南新詩創作萬紫千紅式的爭奇斗艷,其中對王單單的影響更是深入骨髓。
在新詩的第一個百年中,為了強調不同于古典詩詞的特質,新詩傾向于學習西方現代詩歌,對古典詩詞的繼承是不夠的,再加上人們對傳統詩歌的審美惰性,導致了“新詩的合法性”等諸多問題。在新詩的第一個百年中,正是于堅等人“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篳路藍縷,披荊斬棘,所以新詩才有了“光明的去處”,開啟了新詩的第二個百年,而王單單的詩歌創作與新詩的第二個百年是同步的。新詩與傳統古典詩詞緊張對立的焦灼關系在第二個百年減輕了許多,王單單在此時“上場”,有“天時”;王單單身處云南,是其走向詩歌之路的“地利”;尹馬、朱零、雷平陽與霍俊明等人,是其“人和”。上述天時、地利與人和,加上其本人的才與識,造就了其近年來在詩歌界的風生水起。
二、及物
詩歌界一直以來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許多人躲在心靈的一角,撫摸自我的小情緒小靈感,以“個人化寫作”或者“獻給無數的少數人”為幌子,實際上降格為私人化,可以說喪失了詩魂,遠遠無法為時代命名。崇尚“大乘性”寫作的于堅一直呼吁新詩應當正視它的成熟,不能總是一場青春期的胡鬧,而王單單的詩歌創作恰恰是對當下多種詩歌歧路的一種反撥。詩歌不是科學,詩歌不會像科學那樣一直向前進化,王單單的詩歌所關注的正是每一個時代中亙古不變的最基本的人生之常。其詩歌的寫作對象,諸如大地上的高山、河流與眾生,不可知的漂浮不定的命運,對幸福生活飛蛾撲火式的追求,被歷史遺棄的背時者的落寞,對人世間苦難的悲憫等等是詩歌的永恒主題。《山岡詩稿》開篇的《雨打風吹去》極具歷史感與滄桑感,詩人的歷史感也使這一首詩擁有更大的時空和更豐富的內涵。詩中的這一個浮沉千年的家族如同激流中的小舟被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礁石沖撞的七零八落,家族中的一個個成員命運各異,各有各的不幸。但不管是年近花甲卻依舊向往遠方的父親,還是渴盼外出謀生親人歸來的叔父,還是心靈找不到皈依之所的“我”,最終都是被“雨打風吹去”。這首詩中人物的命運具有代表性,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有自己的悲喜苦樂。概言之,此詩有哲思,有內容,有風骨,還有一種內在的節奏和肌理。《河流記》中:“河水在河床上從來沒有睡著/像一條蛇,穿梭于山川與峽谷”[1]37這句話與孔子所感慨的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可以形成一種互文關系,真正的詩人看到“生命之常”時其內心是相通的。這首詩的最后部分寫道:“同一條河流/沒有相同的兩朵浪花/有時候,錯過一朵浪花/就錯過它一生的綻放”,此句同樣引人遐思,哲思中帶著憂傷。
王單單的心靈與時代共振著,他筆下人生圖景中的一個個形象是那樣的蕩人心魄:“丁卡琪”式的風塵女性(《丁卡琪》),把臟污的零鈔當做命根子的賣毛豆的女人(《賣毛豆的女人》),過時了的街頭理發匠(《路邊的理發匠》),采石場帶著嬰孩勞作的女工(《采石場的女人》),輟學、嫁人又十九歲就“二孩結扎”的“盧金花”(《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饑餓的夢見自己也變成鐵的賣鐵男孩(《賣鐵的男孩》),成為“孤魂野鬼”無法為老母親養老送終的阿鐵(《尋魂》),提醒“我”把路走正的在底層摸爬滾打的“二哥”(《二哥》),想為亡妻打口棺材故而申請砍樹的劉長貴(《申請書》)……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這些事也都是時代中普普通通的事,但是詩人用帶有神性的漢字和悲憫情懷挖掘出了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卻又容易視而不見的詩意。王單單的詩歌創作是及物的,有根基的,刻錄著時代的痕跡。王單單與于堅和雷平陽一樣,對人世間生命的體察與感悟是其寫作的根基與核心。
王單單的詩元氣滿滿,對日常生活極具透視力,這得益于他一直身處鄉土。他的詩歌不是固步自封的書齋式的“紙上文本”,而是出自鮮活鄉野的生態式“大地文本”。雖然已經從偏遠鄉鎮轉到昭陽區,但是他一直在昭通城外十余公里的布嘎回族鄉花鹿坪村定點扶貧,現在又奮戰在抗擊“新冠肺炎”的疫情一線。這種生命體驗使得他的詩歌始終處在一種“活潑潑”的本真狀態中。借用民族學與人類學的一個術語來講,王單單的詩歌創作是一種“詩歌田野”,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近作《花鹿坪手記》《花鹿坪扶貧記》《花鹿坪防疫記》與《雪夜防疫帖》中很明顯的體現出來。王單單用帶有溫情的筆觸,以“他者”的眼光審視這一塊原鄉之地,還原了一個偏遠而真實的鄉土中國。《花鹿坪手記·5》寫村婦們介紹馬鞭燒、羊蹄根與蛤蟆葉的草根可以治病,這里涉及到了“啟蒙”主題;《花鹿坪手記·6》提到了幾十個村民不會寫自己的名字而讓詩人代簽,同樣涉及到啟蒙主題;《花鹿坪手記·7》寫因手上沾滿泥巴而摁不出手印的陳啞巴;《花鹿坪手記·12》記錄了至死都沒有脫貧的吳二錢;《花鹿坪手記之二·5》寫打牌的幾個老者像在賭生死,可知村民們的精神生活值得關注;《花鹿坪手記之二·6》寫老寡婦陳石芳扎了一個稻草人丈夫,可知詩人有顆悲憫之心,且這顆悲憫之心足夠柔軟;《花鹿坪手記之二·8》寫一個微信名為“女人不哭”的帶著頭巾的賣早點婦女,她背后的故事讓人放心不下;《花鹿坪扶貧記·2》寫一位老無所依的孤苦婦人陳石分,愛的缺失,讓她如此的焦灼;《花鹿坪扶貧記·3》寫堅持勞動從而想著要減輕兒子負擔的村婦李家英;《花鹿坪扶貧記·4》寫村民周史玉拒絕贍養他78歲的老母親張家會,真正的萬惡之源不是金錢而是貧窮;《花鹿坪扶貧記·6》寫一個對生活不抱希望但心中還有是非觀念的懶漢陸應章,在一定程度上有代表性;《花鹿坪扶貧記·7》寫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婦女以煮光緒年間的錢幣這樣的方式來治病;《花鹿坪扶貧記·8》寫性格執拗的村民周國馳;《花鹿坪扶貧記·10》列舉了一些村民的名姓以及一些生命力極為頑強的野草,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天地之大德曰生”;《花鹿坪扶貧記·11》寫出了對鄉村未來美好生活的展望和向往,通過憑借數萬畝的蘋果基地搞旅游開發,還要建機場。王單單的“扶貧系列”詩歌可謂是這一塊厚重土地的“實錄”,寫出了世世代代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以及葬于斯的村民們的鮮活、粗糲、頑強、堅韌、偉大、卑賤、惰性、蒙昧、善良、懦弱、狡黠、幸福、痛苦和希望。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詩歌沒有缺席,但是許多詩歌只是空洞的口號。部分詩人把詩歌寫成了分行的講稿、社論或者標語,“強行抒情”,概念化、標簽化嚴重。當然,身處抗擊疫情的全民戰爭,詩人們“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用詩文來抒發心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值得贊許的事情。然而部分詩人盡管激情高昂,情感也十分真摯,但是缺乏抗擊疫情一線的切身感悟,寫出來的詩自然乏善可陳。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十一》中有言: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2]意為學畫的人大都臨摹名畫《秦川圖》,卻沒有幾個人親自到過長安,喻義自明。而王單單“向世界挺身而出”,一直堅守在抗擊疫情的一線戰場,這也是作為“抗疫詩”的《花鹿坪防疫記》《來自一個青年詩人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一線防控報告》與《雪夜防疫帖》寫得較好的原因。《來自一個青年詩人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一線防控報告·9》中寫道:“對那些一手扶著烏紗/一手拿著指揮棒的表演者/表示嚴重唾棄”,流露出一個詩人的良知與擔當。《雪夜防疫帖·4》寫道:“四歲半的孩子/給我背:/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稚嫩的聲音里聽出蕭瑟之意”《雪夜防疫帖·5》寫道:“也想到了死。恐懼/令我幾番輾轉,終于難眠/如果我真的離去,這世間/誰是我的托孤之人?”②這些詩句中的心理刻畫是自然且真實的,詩人做了最壞的打算,殊為難得。還有《雪夜防疫帖·10》:“山坡上,夜深人靜/路卡無人進出/而帳外,大雪紛飛/幾個身影擠在帳中/偎著噼啪作響的火膛/從遠處看過去,像一盞燈籠/懸浮在山頂,幾個守卡人/擰成一股繩,成為/它的燈芯”作為抗擊疫情的“逆行者”,王單單這樣的一線奮戰者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但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正是有這樣在大雪紛飛中堅守的人,才保證了一方百姓的平安。不管是作為一個扶貧的抗擊疫情人員,還是作為一個詩人,王單單都無愧于這段特殊的“抗疫”時期。
三、模仿
王單單的詩歌創作的最大問題是對于堅和雷平陽的模仿痕跡很重③,可以說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王單單的“事件詩”(《事件:溺水》《事件:瓦斯爆炸》)對于堅的“事件系列”詩歌(《事件:鋪路》《事件:停電》《事件:誕生》《事件:談話》《事件:棕櫚之死》《事件:裝修》《事件:圍墻附近的三個網球》《事件:挖掘》《事件:結婚》《事件:暴風雨的故事》《事件:翹起的地板》《事件:呼嚕》《事件:探望患者》《事件:溶洞之旅》)的借鑒顯而易見。王單單的《順平叔叔之死》與于堅的《舅舅》之間,王單單的《河流記》與于堅的《河流》之間,王單單的《將進酒》和于堅的《成都行》等等,有一種很明顯的相承關系。
王單單詩歌中的寫作對象和雷平陽詩歌中的寫作對象也如出一轍,如王單單的《我懇求一場雪》《給母親打電話》《父親的外套》《雨打風吹去》《祭父稿》《遺像制作》和《堆父親》等等與雷平陽的《親人》《母親》《背著母親上高山》《祭父帖》和《在墳地上尋找故鄉》等等都是對故鄉和親人的歌唱,這一類詩歌在兩位詩人的創作中都占有很大部分。在這一類詩歌中,具體字句上也有許多類似之處,像王單單在《祭父稿》中寫道:“曠野之中/那根卑賤的骨頭/是我的父親”,而雷平陽在《祭父帖》中是這樣說的:“他的一生,因為瘋狂地/向往著生,所以他有著肉身和精神的雙重卑賤!”其他的,像王單單的《殺膳》與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之間,王單單的《丁卡琪》與雷平陽的《當代妓女》之間,王單單的《多年以后》和雷平陽的《高速公路》之間,王單單的《采石場的女人》與雷平陽的《戰栗》之間均有一種源承關系。
詩歌理念方面,王單單在《春山空》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時代讓我重返大地,與漫天黃土站在一起,這是‘招魂’的場,這是詩歌的原鄉。既然命運給我‘還鄉’的機會,那我就該拿出十足的耐性,靜心做一個‘巫師’,讓詩重啟我與諸神對話的按鈕。”[3]這一段話可能源自于堅的《還鄉的可能性》。王單單本人也這樣說過:“模仿是初學者在詩歌中爬行的第一步,學會爬才能學走,想走就得有屬于自己的路。”[4]模仿當然是一個寫作者的必經階段,任何人都不是在一張白紙上創作,但是能不能形成具有辨識度的獨一無二的風格是成為大家的重要因素。
王單單也不是一味模仿,在某些方面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特點,例如音樂性方面。如《致Y》:能否把整個村莊搬到水上/那樣,在我遠渡重洋時/只需在內心抽出一束月光/就可以為你點亮整個海洋/能否讓我把天涯搬回來/隔一條漣漪,與你比鄰而居/那樣,在我孤獨時就可以/用一滴水珠,敲響你的軒窗/或者,干脆這樣吧/讓我睡在你的睫毛上/那樣,只需你一睜眼/我就會擦去你眼角的憂傷[1]42。這首詩大致押ang韻。《一個人在山中走》雖不押韻,但有明顯的節奏感,而節奏感也是音樂性的一種體現。在《一個人在山中走》中,詩人先是投石問路,接著又開始慢跑,之后在風口眺望,進而反思自己。詩人登上山頂之后,心生悲涼與荒蕪,眼前無路了,又想回頭。一個人在絕端的孤寂中才能夠意識到自己內心最深處最難以割舍的東西,才可以看清自己的真面目,這也是儒家看重慎獨功夫的緣由。這首詩可以說是有節奏感的,有意境的,有“內蘊”的。這一類詩還有很多,像《我行其野》:偶回故鄉,就去野外/認父親留下的土地。近處的/有人種,是誰,并不知曉/遠處的,長滿蒿草/隔著大溝,扔一塊石頭過去/會驚飛幾只鳥[1]77。還有《夜行遇雨》:曠野中裸露的墓碑/像一粒拾落的麥穗,正等待收割者返回/我有點心虛,想大步離去/但滿是泥濘的路,宿命般/咬住我的雙腿[1]80。這幾首參差頓挫的詩,其內容、文字和音樂性是渾然一體的。筆者以為新詩要重視音樂性以及節奏感,音樂性與節奏感是詩歌的本質屬性之一。
四、結語
王單單的詩大都是對人間事的直覺感悟,是對種種世態世情的省察和體認,單刀直入。雖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但“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王單單在這方面似有所欠缺。當然,有些時候詩的“別材”和“讀書窮理”好比一個沙漏的兩端,是你多我少的反比關系,所以要“執兩用中”。王單單在現實與藝術真實之間也做得不夠,就是說在藝術轉換方面有所欠缺。這一點在其創作中也很明顯,部分詩作可以說是失敗的。錢鐘書在《談藝錄》中也說:“持其情志,可以為詩,而未必成詩也。藝之成敗,系乎才也。”[5]語言是詩歌靈魂的外化,所謂“即目所見”“出口成章”,實際上都是經過錘煉的。只有經過錘煉,才能在一次次的否定之否定中完成自我超越,從而建立起自我詩歌與眾不同的情感形態、想象特征和詩語生成方式。在這一點上,王單單要下苦功夫硬功夫,否則很難超越自己。一個詩人要一次次的蛻變,一次次的否定之否定,才能一直走下去。王單單應該具備與其詩歌雄心、寫作欲望和使命感相匹配的文化積淀和精神深度,這就涉及到“心性”。“心性”是很重要的,決定著一個人可以走多遠。孔子問禮于老子,老子對孔子說:“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6]筆者以為這段話也可以送給王單單,愿其剔除身上的驕氣與浮氣;愿其不招惹不介入詩壇上的是非,愿其“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慢一點,再慢一點。當下,對王單單來說,關鍵是如何突圍,即怎么樣從于堅和雷平陽這兩個龐然大物的籠罩中走出。筆者以為,王單單是有真性情的,若能依照自身的生命體驗出發,繼續關懷那一片世間苦難不曾缺席的烏蒙大地,繼續為那一群默默無聲的了無痕記的人留下點“雪泥鴻爪”,強化思想意識和精神向度,將當下的現實進行詩意的創造性的藝術轉換,則必能樹立起自己的獨立的詩學品格與氣場,把血液中的詩歌之火點燃,從而照亮我們這個時代!
注釋:
①“幸”在于前人開好了路,“不幸”在于難以開創具有自我辨識度的詩學之路。
②所引用的王單單的詩,若無說明,則均摘自其微信公眾號“王單單和他的朋友們”。
③近來又傾向于短章集束式或截句式的詩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