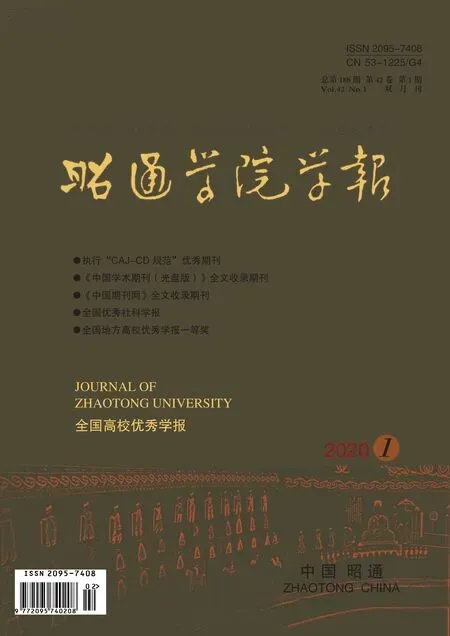從明代筆記看江南文人與明初政權沖突
——以楊循吉《吳中故語》為代表
黃靜靜, 李 志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傳聞一戰百神愁,兩岸強兵過未休”,易代之際,紛飛的戰火燒灼的大多是無辜百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特指江蘇南部與浙江西北部)更是中國偌大版圖上一塊群雄環伺的肥肉。短暫的元明易代之際,江南地區就歷經了元,張氏和朱氏政權的統治,在這樣紛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江南士人的心態也就更為復雜,而與不同政權的親疏也造成了他們與當時政權或親近或對立的不同心理,由此也為他們帶來了不同的命運。
一、江南文人與明初政權沖突的社會歷史背景
要探討江南文人與明代政權的沖突,首先要了解江南地區元末明初幾經改易的政權狀況。正是這些不同政權奉行不同的統治策略,使得江南文人的社會生活環境有了極大改變,因之,他們對元,張氏,朱氏政權便有了鮮明的親疏態度。大致上來劃分,又可分為受江南士人擁戴的元末及之后的張士誠政權,以及對江南實行嚴酷統治而不得士人之心的明初政權。
(一)元末及張士誠政權下的江南文人
從中統末年(1260)忽必烈稱帝,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順帝被朱元璋趕出大都,元朝歷時一百零八年。作為異族統治,元朝在統治初期一直實行著對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壓迫和剝削政策,然而到了元后期,這種統治政策有了明顯改善,尤其是在江南地區,薄賦輕徭役的政策使江南成了經濟富庶,文化昌盛,士人爭相往之的勝地。清人潘耒在《送湯公潛庵巡撫江南序》中也說到:“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在這樣寬松富足的社會環境中,江南士人的生活可謂優渥, 劉基不由感慨:“士大夫安享富貴而養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升平,極盡奢靡之能事。”于是,盡管處于異族統治之下,江南士人和地主階級依然安于這種太平富足的生活。對此,張士誠在割據統治甫始,就采取積極穩定江南的政策,社會政策上幾乎沿革元朝統治,使江南地區得以穩定且繼續繁榮,這些舉措從根本上迎合了江南士人的利益,因而使得張氏政權為江南士人和地主階級所接受。此外,張士誠積極的采取拉攏江南士人的策略。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稱:“士誠遲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譽。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輿馬,居室,無不充足。”此外,“張士誠據吳時,還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及二十六年(1366)兩次于浙江行省舉行鄉試,網羅江南人才,因此博得避難江南的元官及江南地主的擁護。”[1]這一系列舉措,不僅使張士誠在富庶的江南站穩腳跟,而且廣泛的贏得了江南人心。蘇州城困,三載始破,足見張士誠之得江南人心。有史料曰:張士誠“為政寬簡,吳人愛之,有肖其像而祀之者”“太祖(朱元璋)使人徇于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秕尤足支數年,豈降汝乎?”[2](《吳王張士誠載記》卷五引《吳王張士誠傳》)
(二)明初江南地區嚴酷的統治策略
正如前面所談到的,張士誠政權在江南地區深得人心,蘇州城困三年而不破,朱元璋對此耿耿于懷,在其政權穩固之后,對江南地區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報復,一改元末以來的輕徭薄賦政策,對其實行嚴苛的重賦政策。洪武三年九月庚戌“戶部奏蘇,松,嘉,湖四府官民田租不及六斗者,請輸京倉;六斗以上者,輸鎮江瓜洲倉。上令租之重者于本處倉收貯,余皆令輸入京”[3](如上所引潘耒《送湯公潛庵巡撫江南序》:“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三升”,足見明江南稅收之重)。這種重賦政策對江南經濟造成了重創,百姓生活困苦,民生凋敝,原本繁華的江南很快落寞下來。重賦,只是朱元璋報復江南的措施之一,與此同時,朱元璋還采取了另一舉措,徹底摧毀了江南地區的經濟,沉重的打擊了江南文人。洪武三年六月辛巳,“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眾,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故鄉也,田多未辟,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以資譴之,仍三年不征其稅’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戶”[2](《明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辛巳,第1053頁)江南士人生活的富足正是依賴于地主階級和富商大賈以及江南世家大族,朱元璋此舉,不僅徹底摧毀了江南經濟發展的動力,更是徹底毀掉了江南文人的生活,這一釜底抽薪似的打擊不可謂不毒辣。
經濟舉措之外,朱元璋還將江南設為軍事要害之地,在江南廣建衛所,攻下蘇州之后旋即設立蘇州衛指揮使司。“據洪武二十六年刊印的《諸司職掌》載”“江南衛所占全國總數的1/3左右”。[3]153這種布置,一反明朝之前歷代王朝“重北輕南”的軍事部署,足見明初朱元璋政權對江南地區的提防之重。軍事之外,蘇州知府頻繁的人事變更,也從側面反映了朱元璋對江南尤其是蘇州地區的嚴密防范,朱元璋稱帝的31年中,蘇州知府前后換了30人。更為打擊江南文人的則是明初朝廷在官員選拔任用上的歧視和南北偏見。朱棣有意培植北方勢力,使得江南文人的上進仕途艱難重重。“高皇帝制直隸蘇,松二郡人不得官戶部”更是從政令上歧視打壓江南士人。
元,張政權之所以得人心,根本上還是因為他們維護了地主階級及江南士人的利益,順遂了他們生活自由富足的意愿。而由于朱元璋對江南地區的報復心理以及自身性格缺陷,一開始便對江南采取了極其嚴苛的統治,致使江南文人多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進行消極抵抗,或有順從于其政權者,最終也多難以善終。正是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江南文人的生活在易代之際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原本的寬松閑適一去不返,代之以高壓和威逼,動輒得咎的社會現實讓他們清醒的意識到明初政權的殘酷,他們與明初的政權就越發的難以親近且心理沖突也日益增強。
二、明代筆記反映的江南文人與明初政權的沖突
(一)明代筆記與社會生活
“‘筆記’二字,本指執筆記敘而言。如《南齊書·丘巨源傳》所說‘筆記賤伎,非殺活所侍’的‘筆記’,即系此意。”“后人總稱魏晉南北朝以來‘蠶叢小語’式的故事集為‘筆記小說’,而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寫零星瑣碎的隨筆,雜錄統名之為‘筆記’。”[6]筆記之定義,又如鄭憲春在《中國筆記文史》中所指出:“筆記是絕對自由的文體,它可以不拘體例,只要隨筆記錄便是深得筆記三昧。”明代筆記總量龐大,約成書1300多種,內容豐富,舉凡民俗,宗教,歷史,人物,文化,無所不涉及,全方位的記錄了明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在這一千多種筆記當中,記載史料的筆記尤為眾多,其歷史價值也較為突出。關于筆記史料價值,祝允明在《寓圃雜記》序中說:“蓋史之初為專官,事不以朝野,申勸懲則書。以后,官乃自局,事必屬朝署章碟則書。格格著令式,勸懲以衰。又以后,野者不勝,欲救之,乃自附于稗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后,復漸馳。國初殆絕,中葉又漸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觀矣。”[7]魯迅也提倡“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是雜說。”
著史的傳統在文人之中由來已久,是文人留取“身后名”的重要途徑之一,隨著社會經濟和印刷出版的不斷發展進步,與前代相比,明代史學越發繁榮,“史著數量明顯增多,僅《明史·藝文志》不完全記載,明代修出的史著便達1300余部,將近三萬卷”,“而與以前史學所不同的是,私家撰述風氣甚盛,特別是正德以后,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史學家,出現了各種體裁的史書和種類繁多的筆記”[8]。這些筆記或出于館閣大臣之手,或出于下層文人之手,詳細記載了明代社會百態,立體地再現了明代歷史。正如陳梧桐所說:“很多是記述當代史事和人物的,材料大多具體實際,記載更加接近事實,可以補官史之不足”。通過研究這些筆記,我們能夠更好的把握歷史的脈動,探究歷史的真相,社會文化的發展狀況,以及士人之心態等等。這里以楊循吉《吳中故語》為切入點,探究明初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江南文人之命運心態,及其與明初政權之沖突。
(二)《吳中故語》反映的明初江南文人的坎坷命運
“楊循吉,字君謙,南濠人,因讀書南峰山,自號南峰。少敏慧,從舅氏劉參政昌學《易》。弱冠領成化丁酉鄉薦,甲辰成進士,受禮部主事。”[9](崇禎《吳縣志》卷四十八)《吳中故語》是楊循吉創作的一部筆記,所記皆為吳中地區掌故,顧元慶在編纂《顧氏四十家小說》時收錄其中,題跋曰“此卷有裨史學,黃氏《吳中》,祝氏《猥譚》,鄙褻馳頹,遠不及也。”該書共有《太傅收城》《魏守改郡治》《嚴都堂剛鯁》《況侯抑中官》《富豪錢曄陷知府楊貢》《王文捕妖》《三學罵王敬》七篇,計四千余字,體量上并不龐大,但是所記的內容對于探究明代吳中歷史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透過《吳中故語》所記這些歷史掌故,我們也得以窺探當時之文人之生存狀態,把握明初江南文人之心理脈動。
如前文所述,江南地區歷經政權更迭,在明初統治者眼中不可謂不是一大隱患,而由于朱元璋的狹隘報復心理及嚴酷的統治策略,對江南文人始終有所防備和歧視,明初入仕的江南文人多命運坎坷或不得善終,這一點從《魏守改郡治》和《嚴都堂剛鯁》皆可得到證明。《魏守改郡治》記載了明初一次重要的文禍“高啟《上梁文》”事件,“是日,高太史為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并死都市”[4](楊循吉.吳中故語《煙霞小說》本),這一事件的直接結果是朱元璋一次殺掉了魏觀,高啟,王彝等人。《吳中野史》稱,高啟是因《宮女圖》一詩獲罪致死,但考察其他文獻,這一觀點不能完全成立。《雙槐歲鈔》卷八‘名公詩讖’條載:“季迪辭侍郎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讖也。”《明史·文苑傳·高啟傳》云:“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帝見高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于市。”呂勉在《槎軒集本傳》中記載:“蓋觀為勝國遺才,頗自矜詡,矧解《青烏經》術。到任,第欲更張,以吳門無蛇門,則自東南水陸來之生氣間沮,故百年之富,極品之貴,甚有所防,圖欲辟之。先是,城渚委港久淤,舟艇往來不便,役民挑浚甚急,已多斂怨;又以府治乃前元都水屯田司,偏于西,則在武衛之下,即城中共舊治而新之。吳帥慮其居左,且觀由內出,諸帥俯見,弗為禮,銜而密疏之。尋有張度御史微行,廉其跡,以先生嘗為撰《上梁文》,王彝因浚河獲佳硯,為作頌,并目為黨,俱攣赴京。”因呂勉之身份,在論說“上梁文”這一事件時,難免有所偏頗,但事實確是高啟因《上梁文》直接獲罪。但高啟,魏觀等人之死,確僅由一篇文章所致?事情真相恐怕遠非如此。高啟《上梁文》原貌今已不得見,《高青丘集》卷一五《七言律詩》有《郡治上梁》詩一首:“郡治新還舊觀雄,文梁高舉跨晴空。南山舊農千云器,東海初生貫日虹,欲與龍庭宣化遠,還開燕寢賦詩工。大材今作黃堂用,民庶多歸廣庇中。”這首詩并無涉及政治敏感話題,于高啟文禍應無關聯。但高啟因詩文獲罪,確是無誤的。據支偉成《吳王張士誠載記》卷三稱,高啟《上梁文》原文中有“龍蟠虎踞”之語,因而御史張度在給朱元璋的奏報中說:“興滅亡之基,開敗國之河”,一下戳中朱元璋要害,張士誠于江南之陰影始終使朱元璋如鯁在喉,加之高啟先前所作《宮女圖》《題犬圖》,于是朱元璋痛下殺機,敲山震虎,以高啟之禍來警示江南文人。南炳文,何孝榮在《明代文化研究》中介紹高啟時說:“又因作詩有所諷刺,終于洪武七年(1374)被朱元璋借故腰斬于市,死時年僅39歲”,這一說法的確無可非議,但是,如前所說,高啟之死,表面上是文禍,實則是朱元璋統治江南,震懾江南的政治舉措。“事實上,高啟被處決的真正政治意義在于朱元璋想借此恐嚇潛在的持異議者。”[5]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江南文人命運不可謂不坎坷,如《嚴都堂剛鯁》所記:“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
三、《吳中故語》體現的江南文人的復雜心態及其與明初政權的沖突
(一)對張士誠政權的追惜
正史中關于張士誠蘇州城破的記載多一帶而過。《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記載:“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妻,必不負君。’乃積薪齊云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張廷玉《明史·太祖一》中僅粗略記載一句:“辛巳,徐達克平江,執士誠,吳地平。”《明史》一百十一:“二十九年九月,城破,士誠收余眾戰于萬壽寺東街,眾散走。倉皇歸府第,距戶自縊。”然而《吳中故語》<太傅收城>條關于此事的記載卻頗為詳細,并且使張士誠這一形象飽滿而有仁義,“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厚有稱于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擇地視東南若歸。”“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云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雖然這些情節多有和正史不和之處,其中的對話顯然不是作者親歷的,但是這些虛構出來的人物會話使得張士誠的形象更加飽滿生動,與正史相比,楊循吉在這里似乎是有意將張士誠刻畫為一個失敗的英雄。一個末路英雄的悲劇客觀上自然會引發讀者的同情和哀憐,而創作者本來也必然是懷著同樣的心情來記錄這一悲劇。
“跡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于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為張王云。”如前面所述,張士誠政權在蘇州深得人心,而其覆滅之后的朱元璋以及明初政權采取處處打擊江南的策略,江南文人飽受不公和歧視,這種不同境遇的對比,使江南文人對張士誠政權始終存有好感,因而即使到了明中期楊循吉筆下論述張士誠時猶是滿懷追惜。作為吳中文人的一個杰出代表,楊循吉對于歷史現實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吳中文化圈的影響,因而,其對于張士誠政權的追惜感慨不可謂不是一大部分江南文人的普遍心態。
(二)對江南士人悲慘命運的感嘆
《魏守改郡治》中有一段記載:“時高太史季迪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被殷勤,竟遂棄寐告,為忘形交,然未有驗。”依此所記,高啟與魏觀原并不熟識,然考查資料可知,高啟在京為官時即為魏觀手下,彼時魏觀為國子監祭酒,而高啟為翰林院國史編修。黃瑜《雙槐歲鈔》“內府教書”條記載:“國初,設大本堂于內府,東宮,親王讀書其中。學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為講授,而選國子生為伴讀,則布衣高啟、謝徽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常茂、康鐸等人侍。于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啟、徽亦各授官。”《明太祖實錄》卷五九記:“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以翰林侍讀學士魏觀為國子監祭酒,編修宋濂為國子司業。’”高啟《書博雞者事》:“余在史館,聞翰林院天臺陶先生言博雞之事”,可見二人早已熟識。查其他著有高啟文禍一事之筆記,皆與《吳中故語》此處所記不同。劉鳳《續吳先賢贊》“高啟”條所記 :“高啟者,長洲人。少時以詩為饒介所稱。介在偽吳間,喜文學,垂意啟良厚,乃去之,隱青丘。洪武初以史事召,預執簡巳,乃命教冑子。上忽令與謝徽同對,時巳暮,面授侍郎戶部,以不經為吏,且金谷重孤遠驟當寄任,力辭得罷,仍賜金遣歸屬。魏觀為守,故與相優,尤禮遇之,魏得罪遂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書曰:《為鳴鳧》,藻學者多有之。”《皇明詞林人物考》記載:“公歸,教鄉里自給。時魏觀自太常卿俸璽書守郡,賢才而禮之,欲徙郡治,成,乞公文上梁,衛帥誣公徙治為有異志,公亦逮,罹大辟,時年三十九。”這兩種筆記皆無楊循吉所記的“夢中題‘魏’”字一事,可見這一部分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情節很有可能是楊循吉所撰。這種源自小說家筆法的想象為我們解讀楊循吉心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突破口。這里所虛構的“夢中題‘魏’”字,既有著對高啟命運的同情,又隱含著江南文人的一種避禍心理,倘若高啟聽從夢中父親囑托不見魏觀,或許真得以茍全性命。然而觀史書之描寫,這種夢兆的虛構,始終彌漫著命中注定的悲劇成分。
“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在明初的高壓統治下,動輒得咎的生活狀態,讓文人對于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慨。楊循吉所記高啟一事,便是江南文人悲慘命運的一個投影。在這種陰影的籠罩下,加之對于張士誠政權的追惜,明初江南文人大多采取“不合作”態度,或隱居避世,或受詔后以病辭官,以此消極對抗明初政權。種種這些都表明了江南文人與明初政權的沖突,并且這種沖突還有著在吳中文化圈的延續性,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多以狂放任誕來包裝自己,這些舉措無疑是沖突的繼續和對明代政權下的悲慘人生命運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