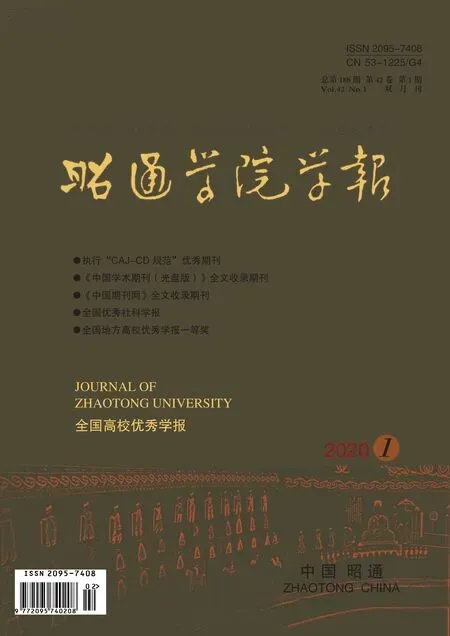近代昭通歷史文物保護與云南地域文化研究
丁長芬,楊夢媛
(1.昭通市博物館;2.昭通學院 學報編輯部, 云南 昭通 657000)
一、孟孝琚碑
孟孝琚碑于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出土于昭通白泥井,高1.33米,寬0.96米,出土時碑首殘缺,碑底刻玄武,碑棱左雕青龍右雕白虎,直行十五行,字體為隸書,共計260字,是云南最早出土的漢代長篇碑銘,于地處偏僻、史乘不足之云南而言,其蘊藏的歷史價值和承載的歷史使命,能否為鄉人識別并加以保護和研究,至關重要。關于這一點,孟碑無疑是幸運的。
第一位詳細記錄孟孝琚碑發現經過的是昭郡郡庠胡國楨,他在《孟孝琚碑發現記》中寫道:余生平嗜學,情殷好古,暇時博訪周咨,搜羅金石。光緒二十七年夏五月,有南鄉回民馬正衛至舍,間詢及昭通梁堆,其中曾有漢洗、古鏡、銅盤、寶劍等類,遂云:“離郡城十里白泥井,有一梁堆,堆前現一石,出土尺許,村中莫識者。”余乃以分書貼示之,即云:“與此相同。俟余鄉試歸來,再去往觀。”晉省垣,鄉試不售,旋歸梓里,邀謝太史履莊往觀,見其書法蒼勁,文辭雅健,渾樸古茂。呼鄉人鋤地五尺許,果有五銖錢數十枚,遂移置郡城鳳池書院藏書樓下。[1]4
移置鳳池書院后,翰林謝崇基寫了一篇跋文,刻于孟孝琚碑末行處,全文為:碑在昭通郡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旁,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出土,同里胡茂才國楨為余言之,因偕往觀。石高五尺,廣二尺八寸,側刻龍形各一,下刻物形若龜蛇,其文辭古茂,字畫遒勁,方之滇中古刻,遠過兩爨諸碑之上。雖碑首斷闕,間有泐痕,年代無考,然以文字揆之,應在漢、魏之間,非兩晉六朝后物,洵可寶也。遂移置城中鳳池書院藏書樓下,陷諸壁間,以俟博雅嗜古君子鑒訂焉。
上述昭郡胡、謝二人對孟碑發現、保存的記述,未能在國內廣為刊布傳播,至今學界鮮有關注。文中實地調查核實的記述,是昭郡域內耆儒鄉紳保護、研究孟碑之肇始。“移置郡城鳳池書院藏書樓下”,雖略顯簡單,卻使云南首次發現的漢代長篇碑銘獲得初步有效的保護,為深入的考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孟碑出土時碑首殘缺,作為云南首次出土漢代長篇碑刻,其立碑年代、碑銘補闕成為當時昭通學術界面對的費解而又必須解答的難題。昭通名儒謝崇基、陳愛棠、蕭瑞麟等,都曾向域外友人寄贈拓片。隨著拓片的流播,孟碑碑銘內容引起了清末民初國內金石學界的極大關注,碩學名家根據殘存碑文拓片對孟碑的立碑年代進行考證。
由于殘存孟碑卷首僅有“丙申”二字卻無年號,而兩漢又有八“丙申”。據民國昭通舊志載,當時學界考證孟碑的立碑年代,有以下六種意見:謂為成帝河平四年者,上虞羅振玉、滇袁嘉谷,新會梁啟超、劉頤;斷為后漢時不著年月者,錢塘吳士鑒;指名光武建武十二年者,善化黃膺、滇方樹梅、袁丕鈞;謂為桓、靈間者,宜都楊守敬;確定為桓帝永壽三年者,東莞陳伯陶、海寧吳其昌、郡人謝文冏;謂獻帝建安二十年者,劍川趙藩。[2]諸家各執一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孟碑立碑年代考訂結果的不同,導致學術界對其評價也不一樣。持孟碑年代為西漢成帝河平四年的石屏袁嘉谷跋曰:“滇中古石,以兩爨及王仁求、鄭回諸碑為著,《孟孝琚碑》最后出恩安縣,西漢物也,應定為滇中第一石。西漢碑海內罕傳,傳者亦多殘石,或數字,或數十字。碑存字260,字字可辨,應定為海內第一石。[1]7考證孟碑立碑年代為光武建武十二年的善化黃膺鹿泉甫記曰:“建武去今將二千年……此石晚出,乃古漢碑第一,慨獨滇南瑰寶,亦寰宇希世之琛矣。”[3]關于這一點,有學者已注意到,作為云南迄今唯一存世的東漢長碑銘,其滇中第一的地位,毋庸置疑;至于“海內第一石”“海內漢碑第一”的評價,則是基于年代推斷為西漢至東漢初年的不統一所致。[4]
與學界對考證立碑年代給予極大熱忱相比較,孟碑碑銘補闕卻略顯滯后,僅昆明陳榮昌和昭通謝飲澗兩人對孟碑缺失碑銘進行了臆補。其中陳榮昌對孟碑的臆補似未盡如人意,昭通學者謝飲澗借鑒其他學者考證思路,旁征博引,以干支長歷悉心研究考據,結合漢代碑刻、經籍,考證孟碑為東漢永壽三年物。在此基礎上,擬補孟碑缺文88字。
謝飲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學術界近乎一致的肯定和極高的評價。著名學者由云龍在《書謝飲澗先生孟孝琚碑考后》一文中有如下評價:“依原碑文字,補其上方剝蝕之88字,風格淳古,幾與原文語氣無別……列舉數證,均極允當,孟孝琚碑得此考,可謂無遺憾矣。”[5]此后,聚訟紛紜的孟碑年代考訂趨于平息。
時至今日,我們仔細梳理史料,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影響了學界考證孟碑的立碑年代:一方面是對孟碑碑體承載信息了解不完整,直接導致學界對其年代考訂的紛訟及對其地位評價的分歧。孟碑出土后即收藏于鳳池書院藏書樓,“陷于壁間,郡人亦無察覺”。刻于碑體左右兩側的龍虎紋,雖然謝崇基附嵌于孟孝琚碑原碑末行空隙處的跋文曾有提及,然并沒有引起昭通學人的注意。直到1945年移出碑體時才發現碑兩側刻有龍虎,即漢代典型的左青龍右白虎,這一具有年代卡尺價值的刻紋,在這之前并未被學界所認知。另一方面是諸家考據,均憑拓片。流播域外的孟碑拓片拓工有精粗,稍不留意,便失本真。而本地學者則有機會親觸孟孝琚碑,對其進行近距離研究和考證。正如謝飲澗所說:冏也后學,何幸得與《孟碑》同里,爰取初拓精本,親蒞碑下,凝神佇視,以手摩挲再四,其古意真趣,皆非拓本可及。[1]16
自孟碑出土至1945年,其間共有三次決定孟碑命運的保護舉措,至今仍未為學界所關注。孟碑首次藏于鳳池書院藏書樓有九年時間,從現代保護文物的視角來看,這是一次略顯粗放簡單的保護舉措,但其歷史意義卻不可忽視。
第二次是昭通士紳推動官方制定搨拓管理辦法。因當時影印傳播條件有限,無論是做研究還是收藏,對孟碑拓片的需求仍屬首選,求者愈眾。從光緒二十九年(1901)孟碑出土至宣統二年(1910)九年時間內,大量塌拓碑體拓片用于研究考證。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昭通士紳敏銳地認識到,無限制搨拓會導致碑體的永久損壞。宣統二年(1910),昭通邑紳黃紹勛呈請昭通府知府陳先沅,出示嚴禁,交議定印資,刊碣于碑側。此即《孟碑旁昭通府陳氏勒石》全文如下:
花翎三品銜在任升用道調署昭通府正堂陳為給示勒石事。據籍紳黃紹勛、李臨陽、王正觀、耿存光等稟稱,恩安高等小學堂舊藏謝檢討崇基、胡茂才國楨尋得漢隸孟孝琚碑,經京外通人博考,有定為建武時物者,有定為河平年物者,皆由碑首脫去年號數字,諸家考據莫衷一是,以字體而論的系漢物。竊思海內所存漢碑無幾,識者比之“五鳳”“地節”,故嵌之藏書樓壁間。乃歷時未久,漸近模糊,推原其故,實因私搨太多所致。近日學堂隨在需款,是以紳等公議,此后每張定價大龍壹圓,售價即作學堂購書報之資,他事不得挪用。惟搨碑時,必須學堂管教各員監視,每年只搨一次,得價若干,年終由堂填表匯報,不準私搨、私售。俾古跡得垂久遠等情。據此除批定案外,合行給示勒石。為此仰學堂管教各員認真監視,以示珍重。倘有私搨私售,一經查出,定即議罰,切切特示。右仰通知 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示 發恩安高等小學堂刊石。
陳氏勒石是以昭通官府名義出示的保護孟孝琚碑的正式禁令。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對孟碑的保護并未達到預期,出現“迄今三十余年,時有所拓,字漸模糊。”[2]這種情況大概延續至上世紀四十年代。
第三次是建亭保護。民國乙酉年(1945),時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捐資建亭于昭通民眾教育館,將孟碑從藏書樓遷置亭內珍護。這次保護孟孝琚碑的舉措,是將孟碑碑體鑲嵌于亭中墻壁內永久保護,直至今日。建亭永久保護孟碑,是包括省政府主席在內的社會各界保護歷史文化遺存的重要舉措,其中的保護措施至今仍可圈可點:一是保護規格高,碑亭由皖籍書法家王景茀書“漢孟孝琚碑亭”[5];鑲嵌于亭中墻壁內的孟碑碑首由民國國學大師吳敬恒題“漢孟孝琚碑”。二是保護研究兩不誤。碑亭建成后,考慮到方便搨拓研究,又籌資另在碑亭內刻立了一塊與孟碑完全相同的復制碑,且在復制碑底座刻石將上述保護孟碑的經過完整地記錄下來。
近半個世紀保護孟碑的歷程,顯示出云南及昭通各界保護歷史文化遺存意識的加強、保護手段和理念的不斷更新。尤其是1945年建碑亭保護并于原碑側復制同樣的“孟碑”供搨拓之用,禁止對原碑進行搨拓,至今仍是我國保護古代碑銘的重要理念。
如果說近代云南、昭通各界對孟碑碑體保護研究不斷探索,改進保護手段和方法,是“庶原碑永垂不朽”的話,對于孟孝琚墓的保護則開創了近代云南歷史文化保護及文脈傳承的先河。
孟孝琚墓的保護源于云南晚清經濟特科狀元袁嘉谷,在張希魯《屏山師回憶錄》中就詳細記錄:袁嘉谷曾委托李守莊“于白泥井補立墓石,題曰‘漢孟孝琚墓’。先生常念念于懷,恐其未立。己已冬初,連楙歸里,特命訪其石立否。迨訪后,其石已立,因作七古詩一首以報。……偶游至城前元寶山南,見巋然豐碑,上刻‘漢經師孟孝琚故里’數大字,下署先生名,乃知先生于先賢表彰,無所不至也。”[6]袁嘉谷于此有跋:“碑之出土,……在縣治南,七尺之封土隆然。今既移置縣中鳳池書院,爰與鄉人醵資補立墓石,題曰‘漢孟孝琚墓’。樵牧護惜,士夫衿式,可忽乎哉?”[3]251-252
百年以后的今天,我們仍能見到位于昭陽區城郊白泥井的孟孝琚墓前豎立的這一豐碑,刻顏體楷書,正中曰“漢孟孝琚墓”,兩旁小字,首刊“原碑移置郡城內鳳池書院”,末有“宣統元年(1909年)乙酉十月李臨陽敬書補立”。袁嘉谷先生倡導對孟孝琚墓的這一保護措施,不僅使晚清發現的孟孝琚墓得以保存至今,起到“保衛先陵而禁樵牧,后起者其留意焉”之作用,而且對后世歷史文化遺存保護有著深遠的影響。
圍繞孟孝琚這塊補立的墓碑,還有一個傳奇的故事。張希魯有對其也有精彩的描述:“即馬正衛自經他來城報告胡氏,將孟碑用牛車運到鳳池書院,掛了他一匹紅,又賞他幾兩銀子。從此他在家,他的腳就大痛不已,時間延長到七八年。人人都說是孟孝琚的靈魂來問罪,為什么要掘他的墓志?把馬正衛害得一個無法。為求腳的速愈,只好備香燭三牲去祭。可是祭后還是照樣地痛,千方百計都治不好。直到宣統元年李守莊依袁樹五先生的建議,去代孟孝琚補立了一塊墓碑,馬正衛的腳霍然好了。在一般人只知道袁、李兩先生為昭通留了一個古跡,還不知道救了馬正衛的腳,真可謂一舉兩得,雅俗并有的盛事。”[7]134無論馬正衛的腳疾與補立孟孝琚墓碑有無關系,這都是云南文物保護史上的一件趣事。
孟孝琚碑的研究保護成果,使近代以來國人重新認識了所謂“南蠻”或“蠻夷之地,幾無文化可言”之云南的歷史和文化,不但開創了偏遠地區歷史文化研究的先河,還開啟了國人研究云南邊疆歷史和文化的大門。更為可貴的是,晚清民國以來包括省、地官員在內的云南、昭通各界保護孟孝琚碑、孟孝琚墓的舉措,其保護理念和實施手段與21世紀國家文物保護的法則并無抵牾,對區域歷史文物保護影響深遠。
二、梁堆
“梁堆”指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古墓葬,因封土高聳形如山梁而得名,時代從東漢沿續至唐中期,主要分布于昭通、曲靖、昆明、保山等地之地勢開闊的壩子、較為平緩的山間平壩或河流沖積地帶。關于“梁堆”遺存,除向達《蠻書校注》有零星記載之外,其余史籍鮮有提及。云南近代文獻稱其為“梁王堆”“糧堆”“徭堆”“梁王塚”等。昭通鄉人稱其為“梁堆”,現代田野考古學沿續“梁堆”稱謂,特指封土堆下的墓葬。
目前資料顯示,“梁堆”一詞最早出現于昭郡郡庠胡國楨光緒二十七年(1901)撰寫的《孟孝琚碑發現記》里。[7]132-133文中詳述孟孝琚碑發現經過的同時,還論及當時昭通四鄉可見的漢冢——梁堆。胡國楨關于“梁堆為漢塚”的論斷,由于其文當時未刊行,并不為學界所知,亦未引起昭通學者的關注。民國時期,昭通城外更多梁堆被發現,有人便認為“梁堆”是“傜堆”的轉音,視其為傜人的窩棚,墓中出土的銅器、印紋磚和五銖錢也被稱為傜銅、花磚和傜錢。[8]民國十八年(1929)張希魯自省垣回昭,從胡國楨之子胡正陶處“得讀胡君未發表過的《孟碑序》遺文,方悟得梁堆確有研究的價值。”[7]141其時,國內考古之風已盛,頗具學術眼光的張希魯將其學術視野延伸至尋找、發掘梁堆,開啟了云南梁堆的調查、發掘、研究和保護。
其時張希魯受聘于昭通省立中學,“有暇則親往四鄉訪問,擬再獲漢物,將孟孝琚碑年代證明,以解海內學者之惑。”[9]通過下鄉訪問,張希魯將梁堆、花磚、五銖錢之間的關聯梳理清楚,同時又知道昭通的梁堆屬特殊的古跡,不但全國所罕有,云南別方亦未聞(當時)。[7]142在實地調查的過程中,張希魯訪問了數百個梁堆,認定昭通后海子一個梁堆有發掘的價值,并于1930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從《昭通后海子梁堆發掘記》中,我們雖然看不到發掘過程之全程記錄,但從張希魯盡其所能的文字記述以及繪制的主要出土遺物的非測量略圖來看,于地處偏遠的云南而言,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至今仍為學界所關注。學者徐堅這樣評價張希魯發掘后海子梁堆:“不僅是歷史上第一次發掘梁堆,也是云南的田野考古學的開端。”[10]
梁堆因其高大封土之形,很容易被盜掘或人為破壞。張希魯在調查梁堆的過程中,發現了多例人為破壞的情況,基于強烈的鄉土文物古跡之愛,呼吁政府對其進行保護。如1933年在灑漁河發現兩座梁堆,“一為石砌,一為磚甃。入城即將此事告知李文林縣長,李君一面命該地農民負責保護,一面請我同鄢若愚去照相”[11]。更有一例,1934年1月,張希魯帶領學生親往灑漁李家灣實地調查《東昭新聞》登載之磚屋古穴(即梁堆),并手書《與李縣長書》:望縣長速令該區民眾妥為保護,不得毀其原狀,以備各方人士參觀研究。[12]昭通政府及鄉民保護以梁堆為代表的文物古跡的種子,在張希魯不間斷地從事梁堆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不斷生根、發芽。新中國成立后,云南各地及昭通大量梁堆的發現和考古發掘與張希魯調查、發掘和保護梁堆緊密相關。
基于對云南、昭通鄉土史的摯愛,調查發掘梁堆之余,張希魯撰寫了一系列考古學文章,如《昭通后海子梁堆發掘記》 《考古小記》 《云南古物的價值》《西南古物的新發現》《跋漢建初畫刻》《古物的搜羅與保護》等,這些文章使得張希魯早期考古發現的漢代遺物及研究成果公之于眾,更多的學者關注云南和昭通漢代的歷史遺物。1935年發表于考古社刊第二期的《考古小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為第一位云南人撰寫的考古學文章在國家級專業刊物發表,在當時的西南地區也屬罕見。其它未能公開發表的系列考古學研究成果,其內容隨后大多編入《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獻,原文在張希魯逝世后,由昭通地區文化局集結出版了《西樓文選》。
近代昭通以胡國楨、張希魯為代表的學儒,對梁堆即漢代墓冢內涵的認識,及其實地考察、發掘、研究,奠定了學術界認識云南梁堆墓這種古代遺存的基礎,為解放后云南開展現代考古發掘、清理工作提供了重要資料。尤其是對這類分布于云南、具有典型特征的古代墓葬“梁堆”之定名,至今仍為現代田野考古學所沿用,這在國內考古學界亦是罕見的。
三、朱提堂狼銅器
朱提堂狼銅器,屬東漢朱提(今云南昭通)鑄造的青銅容器,學界習慣稱其為“朱提堂狼洗”。因其器底部鑄有“朱提”“堂狼”“朱提堂狼”“朱提堂狼銅官造”銘文而著稱。從現存實物來看,朱提堂狼銅器,除數量較多的洗以外,還有釜、盤、斗、鋗等多類器型。[13]銅器銘文多由鑄器年號和地點構成,年號如建初、元和、章和、永元、永初、永建、陽嘉、永和、建寧等,款銘涉及地名“朱提”“堂狼”。
關于朱提堂狼銘銅器,史無記載。據汪寧生考證,從宋代開始不斷有人對傳世的朱提堂狼銘銅器進行收集和著錄。[13]晚清至民國時期,隨著出土的朱提堂狼銘銅器的增多,收集和著錄更加豐富,此時昭通四鄉多有這類銅器發現,并為士紳所收藏。[14]昭通士紳收藏保存的本地出土的朱提堂狼銘銅器,對深入研究這一獨特銘款的東漢銅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梳理史料我們發現,在張希魯之前,并沒有人對傳世和出土的朱提堂狼銅器做過專門研究,著錄、收藏者僅錄洗的名稱,如永元洗、建初洗等。考證昭通出土的朱提堂狼銘銅器以及由此延申至研究昭通歷史,張希魯為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張希魯獲取朱提堂狼銅器的渠道來自昭通的銅匠鋪,據先生所言:“我個人物色的銅器,不得之農村,也不在古董鋪中,往往發現于銅匠手里”[15]。通過這種方式,據張希魯《跋昭通漢六器》一文記載,至1939年搜集銅器已達三四十件,其中“建盉重五十斤”朱提銀、銅洗如“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和“陽嘉二年邛都造”等重要遺物,引起省內外同行高度關注。學界開始以朱提、堂狼、邛都造銅器以證《漢書·食貨志》、《后漢書·郡國志》等史籍記載的地處偏遠之朱提縣、堂狼縣的建置以及這個區域的重要資源——銀、銅。昭通發現的署有明確紀年和地點的漢代文物,使得漢王朝開發朱提、堂狼(今巧家、會澤、東川一帶)的歷史為學界所關注。關于這一點,張希魯曾指出“‘朱提、堂狼、邛都’諸器先后出土,……乃知昭通一帶,在東西兩漢間已大開發,古物與史乘一一吻合。昭通在漢代不僅與中原同風,且為銀礦和銅礦的供給地,故自古銀以地代別號‘朱提’”[15],這一論斷亦是今天學者研究昭通漢代歷史的基礎。
張希魯在1934年至1936年間域外游學,不但結識了滇中在京諸師友,還拜訪了一大批學界宿儒,增長了見識,開擴了視野。1936年,張希魯正式加入容庚創建的考古學社,成為第三期社員。同期會員還有于省吾、羅振玉、楊樹達、陳中凡等學術名家。期間張希魯撰寫的《西南古物的新發現》一卷,刊于旅平學會季刊中,袁嘉谷評曰:“云南文物貢獻與國人矣。”[16]這篇文章使地處偏僻的云南之漢代歷史物證進入國人的視野。從上世紀30年代至解放前,張希魯與國內學術大家探討學術之書信往來可以知道,張希魯的鄉土史地研究并非獨自一人閉門造車,其學術的深度、廣度和視野為后世學者所稱道。
上世紀30年代正是中國傳統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過渡的時期,張希魯搜求、護藏古物不免受國內考古風氣影響。誠然,鄉土之愛成為其考證古物、研究昭通鄉土歷史之旨趣,正如其在文中描述的那樣:“有科學趣味的人,遇古物出土,只問有無文字與花紋及風格等,不問它是金銀銅鐵或是磚瓦木石。有許多人不了解研究歷史的旨趣,往往誤認考古為想發猛財。”[15]不得不說,張希魯這種尋求古物歷史信息進而進行歷史研究之理念,與現代考古學不唯遺物價值而重遺跡關系及其蘊含的歷史信息的解讀不謀而合。張希魯這種幾近自創的學術理念,使其每遇一件古代遺物,都作詳細記錄。比如在銅匠鋪搜集到的漢代朱提堂狼銘銅器,張希魯均要追溯銅器的來源,并親臨銅器的出土地進行實地調查,進一步核實其出土環境和同出器物組合。1935年秋,昭通鄭家山后的皮匠地出土了一件“建初八年朱提造作”銅洗,兩年后張希魯收購了這件銅洗。之后便刻意打聽它是何時何地何人發現的,有沒有共同出土的器物組合等。在《記漢建初兩器出土處》一文中,張希魯詳細地記錄了他經過實地調查的這件銅洗的發現者、發現經過和共同出土的器物——“蟲魚洗”、枯木和被稱為“漢白金”或者“漢銀錫白金”的朱提銀塊。[17]此事并不是個案,在調查考證梁堆、石棺、五銖錢及花磚(漢晉墓磚)等漢代遺物時,張希魯也是同樣處置。[17]這種當事人所進行的田野工作流程記錄的保存,為后人留下了不僅如銅洗、銅鍪、銅罐和銀塊乃至木塊的共存關系,還為后世學者進一步揭示這些遺物所包含的相關歷史信息提供了重要資料。
正因為以探究云南及昭通古代開發的歷史為始終的目標,張希魯在對昭通出土的朱提堂狼銅洗等漢代遺物作研究后,得出“云南的開辟,要以迤東最早,而昭通為最”的論斷。[18]126這也意味著,處于上世紀30年代搜求古物的張希魯,與傳統古董收藏愛好者有著本質的不同。他認為“古物并非古董,不徒用來賞玩,是要證明史地的。云南歷史,文字記載既不詳明,有了古物的發現,就不可望之流出。”[18]127張希魯這種研究鄉土史地使命情節之學術探索,貫穿于《跋漢金(二則)》《漢洗記》《書漢洗記后》《古物記(附昭通城東訪古記)》 《滇東古物目略》 《跋昭通漢六器》 《跋蜀郡器》《跋漢朱提銀錫合金》《漢建初器與蟲魚器跋》《記漢建初兩器出土處》《跋漢陽嘉四年堂狼洗》等文中。張希魯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以方國瑜為代表的云南學者的高度認同。其后,方國瑜將張希魯搜集的朱提堂狼銅器及漢代重要遺跡遺物資料,吸納到其編撰的《新纂云南通志》之《金石考》中。對此,方國瑜在為《西樓文選》所作的序中稱:“瑜為《新纂云南通志》編撰《金石考》,得希魯先生提供資料,多已收入,為世人所稱道。”
張希魯對朱提堂狼銘銅器之保護、收藏以及研究云南及昭通鄉土歷史的貢獻,先生自傳有述:“唯以二十年心力,博讀群籍,搜羅金石古物,咸于云南文獻有密切關系,此海內人士所稱許,非個人自夸也”[9]。在與浦漢英書中,張希魯將畢其一生對昭通歷史文化遺產調查保護之成果寫了出來:“……三十年來的文物研究,得了一個總結。圍繞昭通飛機場的各鄉,如白泥井、諸葛營、施家溝、水塘壩、甘河鄉、曹家老包等地,都曾發現漢代明確的文物。可知一千八百年前,此地的農業生產和冶鑄業是何等的發達。”[19]后世學者對張希魯的評價是:“以朱提堂狼洗實證為特色的早期滇東考古研究不僅在云南罕見,在西南也屬最早的。”[10]
張希魯晚年病危時將自己保存的全部文物捐獻給國家,并望責成專人管理,以免有失,“好讓后來學人,對研究地方歷史作出其應有的貢獻”。籍此,1980年成立了昭通地區文物管理所,保護管理張希魯先生捐獻的所有文物。
四、唐袁滋題名摩崖石刻
唐袁滋題名摩崖石刻刊刻在鹽津縣豆沙關五尺道邊的懸崖上,刻石高60厘米,寬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計122字,正文楷書,末行篆書“袁滋題”。石刻記載了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御史中丞袁滋率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一行到云南冊封異牟尋為南詔,途經石門,刊刻紀事。南詔內屬歸唐,是唐中期的一件大事,袁滋一行赴云南冊封南詔,新、舊《唐書》、《資治通鑒》、樊綽《蠻書》等史籍均有記載。然袁滋在石門題記并刊刻記載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石刻,歷代史籍罕見著錄,不為世人所知。
清光緒元年(1875),赴京趕考的昭通籍舉人謝文翹途經石門關時,在關前崖壁上發現了這一見證歷史的千年石刻。謝文翹當即對其進行現場辯讀并拓片。抵京后,謝文翹將其所攜之拓片分送友人[20],袁滋摩崖石刻始為學術界所知。作為唐中期南詔內屬歸唐的重要實物證據,因其地處偏遠,拓片難度大,不甚精致的拓片直接影響了學術界的關注度。
至民國,昭通學者張希魯經過實地探查,探究到袁滋摩崖石刻保護研究的瓶頸:“余到豆沙關時,訪其地人士,對之詳釋,并囑共同保護。不但是西南有數的古跡,就全中國亦罕見。惜此處地大荒僻,拓本每多不精。……擬將來要特募人去精拓,介紹與國內學者,勿使此瑰寶久湮,亦證明其關系云南迤東史跡,不在孟孝琚碑下。”[7]132
張希魯將精拓的石刻拓片遠寄省外學者,袁滋摩崖石刻重要的史學價值和中唐大書法家袁滋之篆書墨寶,漸為國內大家所關注。如著名哲學史研究專家、民俗學家容肇祖于1939年11月致函張希魯:“前兄賜贈之豆沙關題記拓本,已轉贈陳寅恪先生。將來兄如有機會,可以購得或拓得豆沙關之題字時,萬望代為購取或拓一份。”[21]
按張希魯記述,注意此石刻最早者,為云南袁嘉谷、袁丕鈞叔侄。[7]131之后由云龍、黃仲琴、方國瑜、向達、陳一得、張希魯、謝飲澗等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或序跋,或考證,或品鑒。對這項涉及唐中央政權與南詔地方政權關系史的重要實證文物,各家圍繞以下方面進行考證:高度評價摩崖石刻的政治意義;書體方面,袁滋摩崖石刻內容為楷書,末尾袁滋題名則為篆書,由于袁滋書法世所罕見,其書法價值首為袁丕鈞考證、確認,開啟了后人對袁滋書法的研究;謝飲澗則從石刻刊刻形式方面進行了考證,其考證成果得到學界的肯定;摩崖石刻在西南古代交通史方面之意義,袁嘉谷、方國瑜、陳一得和向達各家分別進行了考證,意見略有分岐。
關于袁滋題名摩崖石刻所涉西南地區古代交通史之意義,直至上世紀80年代之后才又引起學界關注。于西南地區而言,袁滋題名摩崖石刻是唐貞元年間中原、巴蜀與云南交通史的重要實物證據,因其地處偏遠,當時國內學界并未意識到其在西南古代交通史研究方面具有的里程碑式意義。
西南古代交通,史籍早有記載,如《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所記載的“蜀身毒道”“牂牁道(夜郎道)”,《華陽國志.南中志》《三國志》《后漢書》《水經注》《新唐書》《蠻書》等文獻中均多次提及的“步頭道”和“進桑道”。梳理史籍可知,唐朝成都通往云南的道路共三條:一條從邛部舊路即經過涼山地區通往云南,一條從敘州經石門到云南,一條繞道貴州,其中前兩條是主要的交通線,第三條路途險遠。當時處于特殊戰爭時期,邛部舊路即經過涼山地區通往云南的道路由吐蕃把持,石門有烏蒙部落阻隔。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唐中央政府的冊封使者能安全按時到達南詔,使臣南行的道路選擇了從敘州經石門到達拓東(即今昆明)這條道路,即漢晉時期西南地區的交通大動脈——“蜀身毒道”。袁滋一行從宜賓經過石門到達拓東的這一段即“蜀身毒道”最重要的一段——五尺道。
對于袁滋一行行經道路關注最早的是袁嘉谷,但其意見后來被方國瑜所否定。1934年,方國瑜考證說:袁滋行經豆沙關,即取樊綽《云南志》卷一所謂之石門道……此道即漢之僰道,自來為滇、川間交通要道。又自成都至大理,別有一道經邛部,則樊《志》所謂之清溪道。《通鑒》大中十二年曰:“初,韋皋開清溪道,以通群蠻。”即邛部舊路。袁樹五先生以為,袁滋使滇即取此道。然清溪道經今之建昌,石門道經今之昭通,不容相混,樹五先生蓋未考也。[1]145上述方國瑜的考證,明確袁滋使滇取道石門,糾正了袁嘉谷“清溪道”之說。繼之,向達亦對唐時自四川至云南之南北二道進行了論證:“從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云南,謂之南路;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州,至云南,謂之北路。貞元十年袁滋諸人冊封南詔,所取即北路也。”[1]146
方國瑜、向達兩位先生從不同的視角對袁滋一行至云南冊封南詔路線進行了研究,認為袁滋入云南取道今昭通之石門路,這一觀點為后期發現的大量考古遺存所佐證,成為今天學界之共識。可以說,清末發現的袁滋摩崖題記,作為西南地區古代交通研究的第一實物例證,奠定了國內學術界關于《史記》所記載的“蜀身毒道”交通線路考證研究的基礎,是研究“南方絲綢之路——五尺道”的重要實物資料。
不得不提的是,唐袁滋題名摩崖發現之前,學術界對五尺道開辟歷史、線路走向及其在西南地區古代交通史上的地位認識不足。這種情況甚至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仍有學者根據豆沙關唐摩崖所留當時袁滋題名,得出石門路是隋代為通南詔而開辟之判斷。[22]
綜上所述,唐代袁滋摩崖石刻,作為統一國家的唐中央政權與南詔地方政權關系史中一項重要的實證文物,與前述漢孟孝琚碑、梁堆、朱提堂狼銅器等漢代遺存相互印證,揭開了昭通乃至整個滇東北漢唐歷史考古研究的序幕。其保護研究成果,奠定了古代云南在西南地區的歷史文化地位,并為之后發現更早的云南歷史文化遺存奠定了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