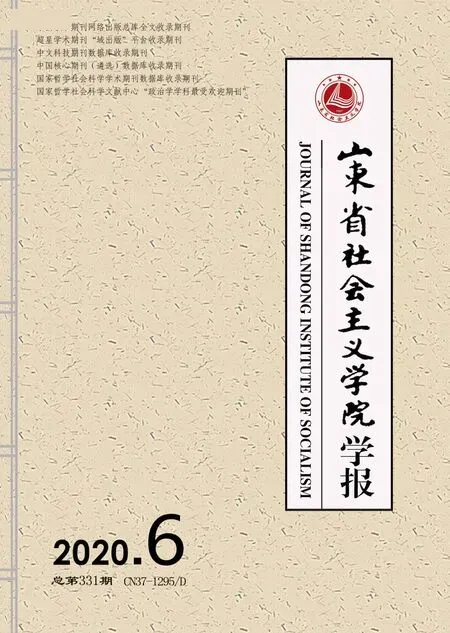中華文明的特質與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
作為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斷流的古老文明,中華文明既具有整體性、內聚性,又具有開放性、包容性,還具有“大一統”歷史的連續性。在當代,中華文明的這些特質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文化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根柢
特殊的地理環境是中華文明整體性、內聚性特點得以形成的地域條件。同時,中華文明能夠在開放中吸收異質文明,在包容中消化異質文明,在多元融會中更新自身。各民族文化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文化根柢。
(一)整體性、內聚性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性較強的地理單元。北有西伯利亞荒原,西北橫亙著大沙漠和沙漠化的干旱地區,西面聳立著青藏高原,西南有橫斷山脈,東部地區臨海。這種封閉性的地理環境,使得中華文明形成內聚性特點。外來文化傳入較晚,原生型的華夏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圈的核心文化,并具有求同存異、兼容并蓄的特點。所以,華夏族同周圍其他民族在長期競爭中又互相吸收融合。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集中探討政治統一、“華夷一體”等問題。一部先秦史可以說就是夷夏融合、由“夷”變“夏”的歷史。秦的統一是這個歷史水到渠成的結果。漢承秦制,延續和發展了空前統一的政治格局,漢民族以空前繁榮的經濟文化、眾多的人口和廣大的地域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及凝聚的核心。[1]以漢族為主體的秦漢帝國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促進了多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倫理等方面的進一步統一,加強了邊疆與內地、“中原”與“四夷”一統的觀念。這之后,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主持中央政權,都以統一作為最高目標。尤其是元朝和清朝,把全國所有民族地區納入版圖,并置于中央王朝直接管轄之下,標志著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形成。這種“天下統一”的局面,成為中華文明整體性、內聚性特點形成的標志,不僅造就了中華民族這一龐大的民族集合體,也延續和發展了中華文明,使之成為綿延至今的古老文明。
(二)開放性、包容性
在數千年文明史中,產生于先進的農業文明之上的中華民族文化是先進的民族文化,作為該文化起源和核心的華夏文化,及后來形成的主體民族漢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兼容并蓄和開放開明的氣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2]
根據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所謂“多元”,是指中華民族不是單一的民族,而是由56個兄弟民族所組成的復合民族共同體。所謂“一體”,是指56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中國各民族在歷史舞臺上扮演不同角色,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大致可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華夏族團的形成;第二步是漢族形成,從華夏核心擴大而成漢族核心(在秦漢時代,當中原地區以漢族為核心實現了農業區的統一的同時,北方游牧區形成了以匈奴為核心的統一體);第三步,兩個統一體的匯合才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進一步的完成。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形成后,對中華民族強烈的認同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基礎。長期的歷史發展,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強烈的認同感和凝聚力。這種認同感和凝聚力不僅存在于56個民族內部,同樣也存在于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共同體之中。各民族內部人民相互信賴,相互依靠,通過民族共同利益的實現來實現個人和群體的利益。各民族之間也是通過共存共生、共同發展來實現本民族的利益。在古代,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往往自稱華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與漢族認同,以謀求自己的發展。如匈奴貴族劉淵利用歷史上與漢朝的甥舅關系,上接漢統,標榜自己政權的正統性;鮮卑拓跋氏以漢魏正統自居;契丹耶律氏以軒轅之后自居;黨項人以夏人之后自居。這些都說明在古代統一的中華民族概念已深入到少數民族之中。
在此基礎上,各民族文化也相互交融,結果是中華民族文化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在長期的文化交融中,各民族分別以其文化的個性,使中華文化異彩紛呈,又以其文化的共性,表現了中華文化的趨同性和整體性。如果說中華民族存在多元一體的格局,那么中華民族文化也存在多元一體的特點,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特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基礎。
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表現在:一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56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獨特傳統,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二是地域文化的多樣性,中國地域遼闊,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各地區均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和語言也有較大的差異。較為典型的是漢民族文化,東西南北文化習俗的差異很大,八大方言的差異比許多民族語言間的差異還要大。
中華民族文化一體性則表現在文化同一性、同質性。一是中華民族文化不是56個民族文化加在一起的總稱,它是各民族、各地區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文化整體。二是各民族、各地區在長期的文化互動交流中形成同質化、一體化現象。價值觀念的一體化或同質化進程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爭霸,人們認識到天下要安寧必須統一。孔子提出“大一統”的主張,孟子主張天下“定于一”,韓非子力主建立中央集權制,以實現統一。這種追求國家統一、多元文化整合的價值觀念和趨勢,反映了各地各族人民實現大一統的要求。秦朝實施的“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等舉措,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固的基石。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促進了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統。唐朝時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民族,吸引了許多少數民族歸附、內遷并互相融合為一體。
總之,中華文明包容開放的特點,有助于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助于保障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有助于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
二、民族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前提
中華文明一個重要特點是“大一統”歷史的連續性,體現在疆域統一、“夷夏一體”、制度有效、文治教化。中華文明在統一與分裂、興盛與衰落中交替演進,但以統一和興盛為常態,以分裂和衰落為變態。即使在分裂時代,分裂政權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統一作為最重要的奮斗目標。[3]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要實現大一統,必須解決“夷夏之防”的矛盾。大一統既指“諸夏”一統,也蘊含著“夷夏”一統,它不是將“夷狄”摒棄于中華之外。一是認為王者無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王者一統天下,也包括夷狄,正如何休所說“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二是強調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中國疆域內的各民族皆是“中國人”。清人段玉裁撰《說文解字注》,在注釋“夏,中國之人也”時說:“以別于北方狄,東方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焦僥,東方夷也。”這是依據古義和傳統觀念做的解釋。王紹蘭在《說義段注訂補》中對這條段注加以訂補,謂:“案京師為首,諸侯為手,四裔為足,所以為中國之人也。” 三是強調肯定各個民族的不同特征和差異性。“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禮記·王制》),并提出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四是確立了“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的民族政策:羈縻制。推行“遐荒絕域、刑政殊于函夏”(唐高祖)的羈縻制度。
在此基礎上,在漫長歷史過程中,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秦漢的統一與邊疆開發,奠定了我國疆域的基礎,創造了“夷夏一體”的現實,邊疆與內地、“中國”與“四夷”一統的觀念得到加強。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大動亂時期,也是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期,同時也是強烈追求統一的時期。這種大遷徙、大融合,進一步加強了中華各民族間的內在聯系與密不可分的整體性。隋唐是“大一統”實現的時代,統一而穩固的疆域使“大一統”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人們無不以“一統”為常,而以分裂為變。“大一統”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交融進一步加強。唐朝出現了“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的歷史壯觀。宋代的現實是遼、金、夏壓境,一統無存,宋人于是強調“正統”,以表明宋室天下一統的合法性。與此同時,遼、西夏、金積極推行漢化與認同,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統一,發展了“華夷一體”“共為中華”的思想,使中華整體觀念得到強化和發展。元朝是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政權,它所實現的空前統一,結束了自唐末以后的分裂局面,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中華整體觀念的加強。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詔告天下說:“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忽必烈據漢文化經典而改建國號,進一步表明他所統治的國家,已經不再單是蒙古民族的國家,而是“大一統”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繼續。明朝建立者以“華夷之辨”作為號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但當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之后,明帝開始強調正統,一變而稱“華夷一家”,強調“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這充分說明,經過遼、宋、夏、金時期的民族交融與文化認同,又經過元朝“大一統”的民族大熔爐的鍛煉,中華整體觀念已深入人心。清入關后,即以宗主視天下。為了樹立“大一統”正統王朝的形象,鞏固其對全國的統治,清王朝接受并發展了“大一統”思想。清朝抽去了“大一統”理論中“華夷之辨”的內容,改造為“四海之內共尊一君”的君主專制“大一統”觀念,形成以推重“大一統”政權為核心、以政權承緒關系為主線、以取消“華夷之別”為特征的正統論,并將其貫徹于歷史評斷之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統治和思想控制。清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據出現,同時密切關注邊疆事務,勵精圖治,苦心經營,完成了對邊疆地區的統一,建立起一個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鞏固的“大一統”帝國。[4]
分裂與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經常出現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說來版圖會擴大一次,到清朝版圖是非常大的,這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幾千年來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所自然形成的。經濟文化的密切關系,需要政治統一來加以鞏固。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這一句話并不是泛泛而談的。[5]正是因為大一統,中華民族歷經滄海桑田而生生不息。一部中華民族史就是一部中華“大一統”的發展史。[6]
中國歷史上形成了漢族地區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一國多制”的治理體系。以清朝為例,清朝實現了大一統的民族整合,解決了中原和異族的矛盾。在民族政策方面,實施蒙古八旗制度、西藏噶廈制度、西南土司制度等,保持對蒙古、回部、西藏和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皇帝兼任滿族族長,保持著滿人的認同,形成漢族地區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 “一國多制”的治理體系。在宗教政策方面,以“崇儒重道、黜邪崇正”為綱,通過度牒發放來管理佛道正教,嚴厲打擊白蓮教等邪教,對藏傳佛教頒布金瓶掣簽制度,把達賴、班禪繼任人選的決定大權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朝廷中央。
三、文化認同、民族認同與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文化認同是最深的認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7]當前,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更要建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認同,以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
(一)以文化認同激發各民族同胞對中華文化根源的懷想
“認同”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迄今為止并無一個統一的定義。英國學者麥克蓋根認為,“認同是一種集體現象,而絕不僅是個別現象。它最頻繁地被從民族主義的方面考量,指那些身處民族國家疆域之中的人們被認為共同擁有的特征。”[8]一些社會學還分析了認同現象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比如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等。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關系極為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基石,后者則是前者的膠合劑。
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由此形成了一個族群的“自我意識”、傳統文化意識、倫理道德觀念以及他們所特有的語言、習慣,是保持其獨特性的基礎。具有整體性、內聚性、開放性、包容性和大一統歷史連續性的中華文化,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作用。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多民族的主權國家都在不斷增強各民族的價值觀念的同質性或共同性,不斷推動一體化或同質化進程。我們在建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方面,一方面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特點,另一方面要建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認同,培育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事實上,中國幾千年以來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而不完全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中華民族這種始終不變的大一統格局,原因有三:第一,中華民族的統一是基于文化的統一,政治的統一隨之。第二,中華大地曾同時并存許多部落種族,之所以能融合為一個大民族,就是由于中華文化具有特別強大的同化力。第三,中華民族的歷史之所以綿長不絕,關鍵在于其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因一時武力上的失敗而衰亡。幾千年來,不管什么朝代,不管是不是征服民族,也不管中間有多長多短的分裂,一個民族只要到了這塊土地上,往往被中華文化同化,認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信奉“大一統”“大中華”的理念。所謂“征服者被征服”,指軍事征服后,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被毀滅,而是征服者的文化被中華文化同化。
在當代,增強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有助于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助于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有助于中華文化的復興。
(二)以民族認同激發全體中華兒女骨肉同胞之情
民族由許多因素構成,包括名稱和共享的記憶,在血緣紐帶、文化傳統和習俗、體質方面與其他群體的不同,還有集體認同等。民族認同是指個體對本族群的信念、態度和參與行為,個體對族群的認同主要依賴于體質體貌特征、記憶、血緣紐帶和歷史文化傳統等要素。民族認同是文化認同的基石,文化認同則是民族認同的膠合劑。一個人若無民族認同感,固然無法產生民族文化認同感;而文化認同感不存在或不強烈,也無法產生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由于民族是由血統、遺傳決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選擇,但文化則是可以選擇與改變的,所以文化認同比民族認同更為復雜。因此,民族認同感必須同時含有血統與文化兩種成分,單憑血統而產生的民族認同是不完善、不牢固的,對于強化民族或國家的凝聚力,也不能產生持久可靠的作用。
應增強中華民族認同,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現代中國的“大一統”,集中體現為作為現代“超多民族國家”的建構。這一“超多民族國家”的存續是當代中國政治的重大關切,甚至是根本關切。在民族問題上,民族主義并不符合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國現代民族觀依然帶有傳統中國的印記,強調共性而非差異,追求交融而非分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堅決反對操弄族群意識,進一步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牢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