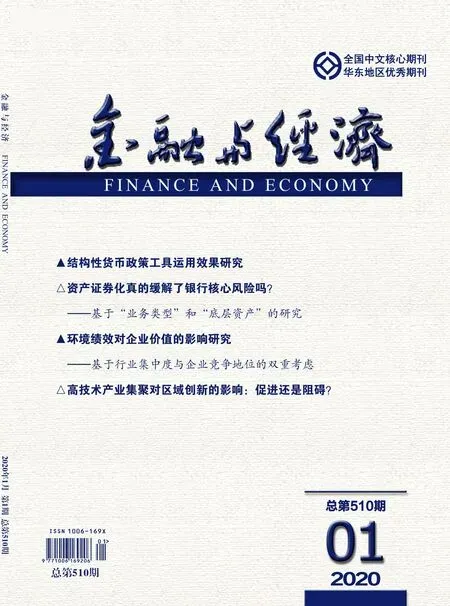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
■梁權熙,譚思夢,謝宏基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為實現經濟復蘇而頻繁調整現行的經濟政策,使得全球經濟政策環境始終處于高度不確定性狀態。2018年爆發的中美貿易戰更是將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推向新的高點。根據Baker et al.(2016)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已從2018年初的122.94低點急劇飆升至2019年11月的935高點,接連創下歷史新高。現有大量研究表明高度不確定的政策環境對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產生了一系列負面沖擊。其中,對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微觀經濟效應研究主要集中于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鮮有研究涉及對資本市場上的微觀主體,特別是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因此,本文將考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
近年來,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規模、交易規模、持股規模不斷擴大,機構投資者逐步取代個人投資者成為我國股票市場最主要的參與者①根據Wind數據,截止2018年9月,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已經占整個市場流通股的52.65%。。機構投資者作為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和知情交易者,對于提高股價信息含量和資本市場效率,降低股價波動性和穩定資本市場(祁斌等,2006)等至關重要。而且,機構投資者與實體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具有長期投資視野的機構投資者往往更看重長期投資回報,從而更為積極地參與公司治理,監督所投資公司的研發、并購活動以及高管薪酬等以確保其獲得更好的長期業績表現(Aghion et al.,2013)。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公司未來現金流形成負面沖擊時必然會影響到機構投資者所持有股票的長期投資價值,促使機構投資者根據公司發展前景以及自身投資風格調整其投資組合。因此,研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引發的經濟后果。加之,市場經濟制度不夠完善,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表現出更頻繁的政府干預和更大的波動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我國微觀市場主體行為的影響也更為嚴重。因此,我國政府經濟政策變動頻繁的背景為本文更好地識別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提供了理想的制度環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對于機構投資者而言,其持股行為主要受到來自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以及公司層面的特質風險的影響。基于現金流折現的股票定價模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作為系統性風險(Pastor&Veronesi,2013),可能會通過影響預期折現率和未來現金流來影響機構投資者的股票回報率進而改變持股決策行為。
一方面,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可能通過改變折現率來影響機構投資者的股票回報率從而改變持股行為。具體而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作為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會對金融市場及其資產價格造成一系列的負面沖擊。近期有部分研究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納入資產定價模型中,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是影響資產價格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Pastor&Veronesi,2013)。首先,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環境不僅增加了機構投資者所面臨的長期風險,還可能使得其對金融資產的定價出現偏差(Croce et al.,2012),從而加劇了資產價格的波動。其次,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在加劇資產價格波動的同時,也必然會使得機構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以補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Pastor&Veronesi,2013)。最終,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和風險溢價的上升會不斷抬高股價估值的折現率(Pastor&Veronesi,2012,2013),擁有較強信息挖掘和分析能力的機構投資者會將修正后的高折現率納入股價估值模型中,從而壓低了資產的價格和回報率(Francis et al.,2013)。因此,從系統性風險的角度來看,較高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通過提高折現率來降低機構投資者的股票回報率,從而抑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
另一方面,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還可能通過沖擊企業的未來現金流量來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決策行為。由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抑制了企業的投資以及創新活動等,從而降低了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Francis et al.,2013)。同時,政策不確定性還會影響機構投資者對企業未來投資機會、預期盈利能力以及未來現金流等基本面的判斷。如Belo et al.(2013)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擾亂了企業未來的經營現金流量從而影響到投資者對股價的預測能力。Francis et al.(2013)發現在政策不確定性較高的選舉年份中,被動型指數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收益表現更差。作為價值型的長期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最為看重未來現金流量所帶來的長期投資回報(Cohen et al.,2002),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公司未來現金流量形成負面沖擊并損害機構投資者所持有股票的長期投資價值時,機構投資者能夠及時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并根據公司的短期或長期發展前景重新調整其投資組合并降低持股比例。
此外,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還可能通過信心效應(confidence effect)或風險厭惡渠道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行為。在Ilut&Schneider(2011)的模型中,不確定性使代理人無法形成關于未來的概率分布,假設代理人具有悲觀信念(pessimistic beliefs),則由于“模糊厭惡”,他們將根據最壞的可能結果進行決策。隨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投資決策所帶來的最壞可能結果進一步惡化,機構投資者的風險感知和“模糊厭惡”也隨之不斷提升,這將促使其更傾向于做出延遲投資的決定(Pastor&Veronesi,2012)。另外,現有文獻還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于投資者當期回報的影響主要是由其預期收益變化驅動的(Brogaard&Detzel,2015)。在經濟政策不確定、信息不完全的環境下,“模糊厭惡”強化了機構投資者非理性的悲觀預期,從而使得機構投資者更傾向于減少其持股行為。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抑制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行為,政策不確定性越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低。
三、實證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3~2016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其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數據通過上市公司披露的前十大股東數據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源于Huang&Luk(2018),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險行業和主要變量有缺失的公司樣本,最終樣本包含分布在2288家公司共21205個公司-年觀測值。為減少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文對非虛擬變量都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
(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度量
本文主要采用Huang&Luk(2018)構造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度量機構投資者所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①該指數遵循了Baker et al.(2016)的編制方法,但選取了更多的內地報紙數量來平滑個別報紙的特質與偏見,從而更能客觀地衡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另外,該指數還進一步細分為財政政策不確定性(EPU_Fisc)、貨幣政策不確定性(EPU_Monty)、貿易政策不確定性(EPU_Trade)和匯率政策不確定性(EPU_EXR),有利于我們更好地識別不同類型的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本文使用年度算數平均值的方式將月度數據轉換成年度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EPU)。下圖1描繪了Huang&Luk(2018)和Baker et al.(2016)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在2003~2016年間的走勢,發現兩個指數不僅走勢基本一致,還與我國重要的經濟歷史政策時間相吻合,表明該指數能有效地反映我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圖1 2003~2016年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走勢圖
(三)模型設定
為檢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本文設定如下多元回歸模型并運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進行回歸:

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公司和年份。EPU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變量,DOMINST表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參照黎文靖和路曉燕(2015),本文度量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指標是上市公司所有境內機構投資者持股數量占公司總股本的比重,包括券商、國內基金、保險、社保、信托、財務、銀行以及其他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CONTROL(k)為第k個控制變量,ξt為隨機誤差項。本文參考Chou et al.(2014)、黎文靖和路曉燕(2015)等的做法,選取公司規模(SIZE)、財務桿杠比例(LEV)、資產收益率(ROA)、企業年齡(AGE)、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流通股比例(TSHRATE)、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USRATE)、獨立董事持股比例(OUTD)、是否國有企業(STATE)、是否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BIG4)和GDP增長率(GDPGR)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此外,本文還在所有回歸中引入行業虛擬變量以控制行業固定效應的影響。

表1 主要變量定義表
②參考饒品貴和徐子慧(2017),除以100主要是出于回歸系數大小的考慮。
四、回歸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中可知,我國境內機構投資者的平均持股比例為20.5%,與黎文靖和路曉燕(2015)使用的截止至2009年數據相比,近年來我國境內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實現了穩步增長,但與歐美發達資本市場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EPU的均值為1.292,標準差為0.312,表明我國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存在明顯差異。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3報告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以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總指數EPU為自變量,在控制了一系列宏微觀層面的影響因素之后,EPU的系數為-0.044,并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該結果隱含的經濟含義為,平均意義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變動一個標準差(0.312),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下降1.37%(-0.044*0.312=0.0137)。進一步地參考Gulen&Ion(2016)的做法,在(2)~(5)列中分別以財政政策不確定性(EPU_Fisc)、貨幣政策不確定性(EPU_Monty)、貿易政策不確定性(EPU_Trade)和匯率政策不確定性(EPU_EXR)這四個分指數作為自變量,來考察不同類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從結果可知,EPU_Fisc、EPU_Monty、EPU_Trade和EPU_EXR的系數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與總指數EPU的方向保持一致。以上結果提供的證據有力地表明,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環境降低了機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從而抑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驗證了研究假設H1。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風險機制
在前文分析中,本文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顯著負相關。然而,由于企業或行業風險特征的差異,不同的企業(行業)受到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沖擊程度有所不同,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也會存在顯著差異。參考Boutchkova et al.(2012)、饒品貴和徐子慧(2017)等的做法,本文接著分別從企業所面臨的系統性風險、行業政策敏感性、公司成長性、產權性質和公司規模等五個方面考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是否受企業(行業)風險異質性的影響。為此,建立了如模型(2):

其中,RISK用于衡量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分別由系統性風險BETA、行業政策敏感性PI、公司成長性HighTech、產權性質STATE和公司規模SizeDum等五個變量代理;模型(2)的其他變量設定與模型(1)相同。
從系統性風險角度來看,本文使用Beta系數來度量企業的系統性風險,Beta系數可以有效衡量公司股價對整體經濟波動的敏感性,直接反映出市場風險對公司的影響程度。本文按照企業Beta系數的均值進行分組并構造系統性風險啞變量BETA,若公司當年的Beta系數高于均值則BETA賦值1,否則賦值0。表4的第(1)列給出了系統性風險如何影響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關系的回歸結果,交乘項PU×BETA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在那些面臨更大系統性風險的公司中更為明顯。
從行業政策敏感性來看,參考Kostovetsky(2015)的分類方法,本文將煙草產品、酒類、醫藥類、軍工、能源開采和石油天然氣等行業歸類為政策敏感性行業,并以此為基礎構造行業政策敏感性啞變量PI。若公司屬于上述行業則賦值1,否則賦值0。表4的第(2)列給出了不同的行業政策敏感度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影響的回歸結果,交乘項PU×PI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值,表明較高的行業政策敏感性放大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負效應。
從公司成長性來看,采用是否屬于高新技術行業來捕捉公司的成長性。其中,高新技術行業的劃分標準參照Cui&Mak(2002),并根據證監會2012年發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研發強度較大的行業劃分為高新技術行業。然后構造了一個公司成長性啞變量HighTech,若公司屬于上述行業則賦值1,否則賦值0。表4的第(3)列匯報了公司成長性如何影響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關系的回歸結果,交乘項PU×HighTech的系數為正值并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在成長性更高的公司中更為顯著。

表4 機制檢驗
從產權性質來看,本文將產權性質變量STATE與EPU交乘,以檢驗不同產權性質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差異。回歸結果如表4的第(4)列所示,交乘項PU×STATE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值,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
從公司規模來看,按照企業總市值的均值分組并構造公司規模啞變量SizeDum,若公司當年的總市值高于均值則SizeDum賦值1,否則賦值0①我們也嘗試按總資產規模進行分組,結果不變。。然后將SizeDum與EPU交乘,以檢驗不同公司規模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差異。回歸結果如表4的第(5)列所示,交乘項PU×SizeDum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值,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在小規模公司中更為顯著。
綜合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當公司為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系統性風險、所在行業的政策敏感性更高、具有更高的成長性或規模較小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
(四)拓展性檢驗
Bloom(2014)指出,在考察政策不確定性的經濟效應時,區分政策不確定性的不同來源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文進一步參考Gulen&Ion(2016)的做法,通過回歸方法將機構投資者所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分解為全球層面和國家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并分別考察它們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本文選取Baker et al.(2016)基于報紙報道構造的“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用于捕捉全球層面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其經濟政策變動往往會影響全球各個國家的經濟政策變動。更為重要的是,中美兩國經貿往來密切,許多影響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因素也會影響我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因此,設定了如下兩個計量模型:

通過模型(3),可以將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CN正交分解為與︵全球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相關的部分PUCN(即模型(3)中的擬合值)及不相關的部分eC(N即模型(3)中的殘差),而eCN即為純粹國家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類似地,也可以通過模型(4)分解出純粹全球層面的政策不確定性eUS。然后將這些指標同時引入基準回歸模型(1)中,檢驗來自不同層面的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差異。從表5的回歸結果可知,機構投資者與純粹國家層面和純粹全球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都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但eCN和eUS的系數沒有通過差異性檢驗。這表明,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球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都顯著抑制了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行為。

表5 拓展性檢驗
五、穩健性檢驗
(一)內生性問題
本文采用的Huang&Luk(2018)構造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沿用了Baker et al.(2016)的編制方法,但Bloom(2014)認為此類方法構造的指數作為主要解釋變量時,遺漏變量問題才是內生性的主要來源。為此,本文綜合采用如下方法來緩解內生性問題:
第一,采用更為“干凈”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借鑒拓展性分析中的方法,通過提取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中與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正交的部分來消除非政策相關的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干擾,獲得的殘差即代表了更為“干凈”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N),用eCN替換EPU重新估計基準回歸模型(1)。第二,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第三,盡可能控制其他宏觀變量的影響,包括股票市場指數年收益率的橫截面標準差(IndxVol)、宏觀經濟先行指數(MCIL)和省級官員是否變更變量(PU_Prov)。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EPU的系數大小和方向并沒有明顯變化,從而印證了表3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6 內生性檢驗
(二)變更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度量方式
出于穩健性的考慮,本文進一步采用以Baker et al.(2016)構造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2)作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代理變量并重新估計模型(1)和模型(2)。重新估計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第(1)列EPU2的系數顯著為負值,與表3的基準回歸結果相一致。第(2)~(5)列的風險機制檢驗結果也與表4的回歸結果保持了較好的一致性。

表7 變更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度量方式
(三)重構“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本文參考饒品貴和徐子慧(2017)的做法,采用不同的方法將EPU的月度數據轉化為年度數據。首先,采用年度中位數的方式獲得年度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_median)。另外,將EPU在年度時間序列上劃分為高低兩組并構造啞變量(EPU_dum),較高組取值1,否則為0。最后,將EPU按年度均值進行排序后劃分為5組,然后標準化為0~1之間的變量(PU_order),這種變量設定介于連續變量和虛擬變量之間,兼具兩者的優點。從表8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變量的系數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值,表明基準回歸的結果并未受到“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轉化方法選擇的影響。

表8 重構“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四)重構機構投資持股變量
由于本文所用的機構投資者持股變量為年末的時點數據,難以全面刻畫全年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變動情況。出于穩健性的考慮,進一步參考Chou et al.(2014)的做法,重新構造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變量,用半年報和年報披露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加總取均值,得到年均數據(DOMINST_AVG),接著重新估計了模型(1)和模型(2),主要回歸結果并未受到影響①限于篇幅,結果留存備索。。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Huang&Luk(2018)構造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度量我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考察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影響。基于2003~2016年間的A股上市公司樣本數據研究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顯著負相關,表明高度不確定的經濟政策環境會抑制機構投資者的股票投資行為,降低其持股偏好。進一步地,本文從多個角度考察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作用機制,發現當公司面臨更高系統性風險、更高行業政策敏感度、更高的成長性以及屬于非國有企業和小規模企業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最后,本文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分解為來自全球、國家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后發現,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球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都顯著抑制了機構投資者的持股行為。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啟示:第一,本文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顯著抑制了資本市場的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相關部門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過程中要特別注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資本市場的沖擊,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第二,政策制定者在出臺或調整經濟政策平滑經濟波動、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從而穩定資本市場的政策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