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豐村小說《美麗》的“道德試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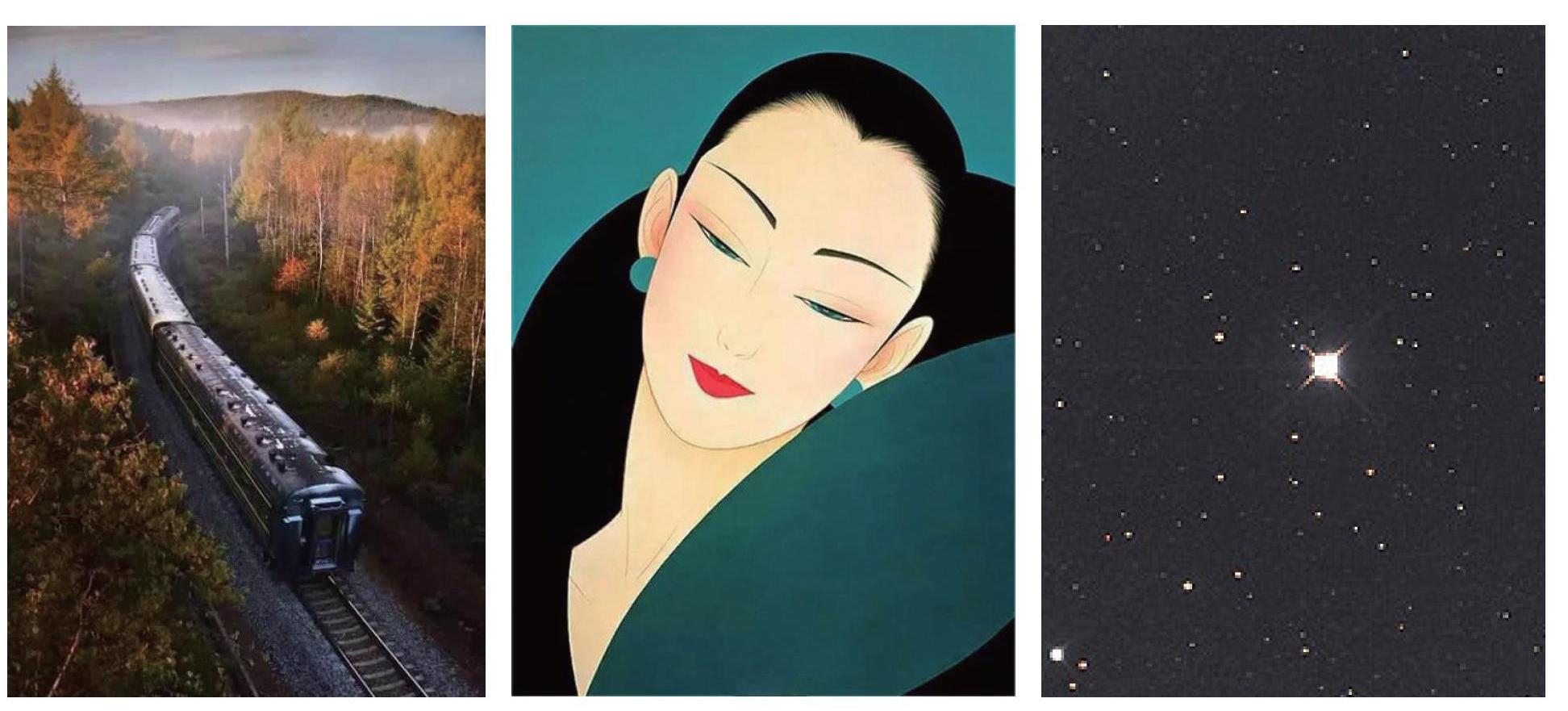
摘? 要:豐村的《美麗》是一部以婚外戀為題材的小說,由于其所處特殊的時代性,使這篇小說成為“道德試錯”的典型,具體體現在人物關系的設置以及“小我”成全“大我”的自我犧牲精神等方面,所依據的仍然是政治標準。這既有其特殊年代的局限性,也有作者主觀上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處理態度。
關鍵詞:道德試錯;三角戀;“小我”與“大我”
1956年,黨中央提出“雙百”方針后,文學界曾出現了一批所謂“干預生活”“寫真實”“寫人情”的作品。其中,尤以婚戀題材的小說受人關注。豐村的短篇小說《美麗》面世之初便受到極大爭議,其后在反右運動中又被冠以“宣揚資產階級個人愛情觀點”之名定為“毒草”。直至1979年,才被作為“重放的鮮花”之一再次面世。而作為“鮮花”重新開放,所依據的更多是政治標準,在文學史上也多是以“突破題材的禁區”來概括這一文學現象,而孫先科先生則從文本出發,將《美麗》認定為“道德試錯”的典型。 所謂“道德試錯”便是“主人公由尋求一種新的感情關系開始,使舊的平衡遭受破壞,但“嘗試”過后,經過自助或他助、自律或他律的修復過程,重新回到舊的感情狀態。”[1]29-37本文將以此概念為基礎,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從人物設置,“小我”成全“大我”以及“道德試錯”的實質來具體分析這篇小說的“道德試錯”性。
一、“道德試錯”的前提
——人物關系的設置
黑格爾認為人物關系設置對敘事具有整體的影響。人物之間的關系不僅是情節形成的基礎,更影響著故事的走向。小說《美麗》中的人物關系可分為兩重——三角關系和上下級關系,而無論就其中的哪種關系來看,都是具有不倫性的,這也給人物的“道德試錯”提供了前提條件。
(一)季玉潔與首長。季玉潔作為首長的秘書,對工作盡職盡責而又嚴格苛刻,尤其對自己的上司從生活到工作照顧得可說是無微不至。在她的認知里,她的責任就是為首長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成為首長的“記事本”“眼睛”“耳朵”“腳和手”。在季玉潔的描述中,首長是一個完全稱職且令人尊敬的領導形象,也是一個典型的“十七年”時期的干部形象:對下屬理解、體貼、負責,但也相對嚴格。對首長的欽佩使這個剛步入社會的女大學生不愿意看到首長對自己工作的任何不滿意,也就不自覺地擴大了她的工作范圍:從首長的作風、習慣、興趣到身體健康,無所不至。正是這種“過度”的工作熱情與責任,使她產生了對首長超出上下級關系的男女之情。她會為了首長“青年干部應該有時間學習”的建議熬壞身體,也在病中期待又恐懼著首長的到來,以至“我不見他,我就擔心,我希望看見他,而我一看見他的眼睛就會不安,接近他我也會心跳”。但這種理應受“道德譴責”的感情沒有得到她本人認可而選擇了壓抑,即使在首長的妻子姚華去世后也未曾接受首長的求愛。姚華的仇視與臨死前的不甘以及外界的議論讓她無法對自己所愛的人敞開心扉,后來進京看望老首長,也因為家里多了個“不是什么生客”的女人而選擇再一次啟用道德力量來壓抑自己的真實心跡。
(二)季玉潔與首長夫人。季玉潔和首長夫人姚華可以說是“親近”的,但無形中她們也是“情敵”的競爭關系。在季玉潔的感情并未明顯外露時,二人之間可說是互幫互助的姐妹關系,她們之間關系的轉折則是因為姚華對季玉潔情感心理的察覺:“我們家像有一塊吸鐵石吸著你哩”,對季玉潔漸漸敵視。可以說姚華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形象,認為幸福應該體現在家庭,即使生病也不愿意離開家庭,但受過革命與戰爭鍛煉的姚華似乎也缺乏著一份傳統女性所特有的溫柔與智慧,臨死之際沒有譜寫托孤托夫的頌歌,而是竭力阻止季玉潔占有自己的丈夫與家庭。正是在姚華無情的“維權”的對比中,季玉潔的形象竟變得無辜可憐起來。在她察覺對首長的心意后,竭力壓抑自己的情感流露,并向黨支部書記尋求幫助,向組織證明自己的“清白”。而對于姚華,即使她對自己仇視憎恨,季玉潔也會提醒首長去看望重病的妻子,這種無私的行為背后,難說沒有作為“第三者”的心虛與愧疚。無論如何,季玉潔與首長最終的無法結合,姚華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首長與首長夫人。這是一對典型的在革命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夫妻,二人在革命時期同生共死,感情的基礎與穩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姚華作為妻子,深愛丈夫也懂得如何愛,在與季玉潔的關系惡化后,也盡量避免在丈夫面前表露,更不會將之歸責丈夫而產生爭吵。即使臨死之際,也要宣布對丈夫的永久霸權,但卻沒有得到丈夫的最后一眼。生活于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首長對于姚華,無疑是有愛情的,但終究因公而未能見妻子最后一面,是典型的“十七年”時期的英雄敘事。恰是出于這樣的革命愛情,首長即使已經察覺季玉潔的心意卻沒有點破,也為季玉潔情感的不倫性增設了前提。
豐村便是設置了這樣的一個三角戀愛網。首長作為兩個女性追逐愛戀的對象,在這段關系中是一個缺乏明確態度立場的主體,他的存在只是保證一個道德視角和道德主題的形成以及這段三角關系穩定性的保持。季玉潔作為“第三者”出現,實際上將兩角的愛情關系轉換為“三角”的道德關系,她在小說中承擔的不僅是三角愛情關系中的一角,更是承擔著一種“符號的,抽象的功能”——道德抉擇。
與鄧友梅的《在懸崖上》不同,季玉潔作為“第三者”這一形象與其感情承受者——首長有著另一層身份關系——上下級。在季玉潔對首長妥善細心照顧的同時,他們之間的關系成為他人揣測的對象,“機關里的同志也不是沒有意見呵”“但你對秘書長的態度,是不是有向上爬的思想呢?”這種上下級關系的嚴肅性使單純的愛慕變成他人眼中向上爬的工具,如果季玉潔后來沒有拒絕首長的求愛,那么不難預測這種結合勢必會成為一部分人口中的“向上爬”。這種“辦公室”戀情的身份設定也給本已“不正當性”的感情增添了一把道德的枷鎖。
二、“道德試錯”的實現
——“小我”成全“大我”
對于季玉潔和首長以及姚華的三角糾葛,豐村給出的解決方式便是“小我”成全“大我。誠如孫先科所言:“以犧牲愛情的立場解決“三角”沖突,以維護道德選擇的合法性”[1]29-37。
那這種成全是如何實現的呢?當季玉潔意識到對首長感情的異樣時,知道自己不能愛他,否則就會陷進錯誤的泥坑,所以寧愿自己承擔痛苦也不愿破壞首長的家庭,這在道德上是值得歌頌的,也是很順理自然的情感。但在姚華病逝之后,首長的求愛此時已經具有一定的正當性,畢竟“三角關系”這一道阻礙已消失。若此時季玉潔答應首長的求愛,在合理性上是無可指摘的。筆者認為,此時她依然顧慮著他人的話語評價以及姚華臨死時的威示,使得道德上的“大我”依舊占上風,而無法遵從真實的人性自我。如果說第一次拒絕首長的求愛尚有這兩件枷鎖的阻隔,那么時過境遷之后,季玉潔再次見到首長并打算表明心跡時,她此時的退縮則是作者“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有意為之。究其原因,“作品為表彰一種自我犧牲的道德(為他人、為工作),人為地將感情邏輯扭曲、復雜化了”[1]29-37,只是因為首長家里多了個“不是什么生客”的女人,就將自己再一次置于“第三者”的位置上,以道德的名義壓抑自己的感情,而她的這種感情最終破滅的痛苦亦是作者為凸顯她的道德性而強加的。為了強化季玉潔犧牲“小我”的崇高形象與合理性,作者給予她一種至高的褒獎:“北京的夜是多么好,在深夜里,你就會覺得與毛主席在一起哩。”在這失戀未眠的深夜,“大愛”戰勝“小愛”的季玉潔,內心個人情感也完全被道德壓榨殆盡,能給她以安慰的也只有自己所信仰的主流價值觀。
作者在將“小愛”升華為“大愛”時使用的邏輯是非此即彼的,二者互相不見容于對方,有人認為這是將“大愛”與“小愛”根本對立起來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的“虛設。”[1]29-37這一點也可以從季玉潔與外科醫生的愛情上體現出來。在與外科醫生相處的過程中,由于工作原因,季玉潔多次爽約,將培養愛情的情人間正常的交往行為看成與工作所代表的具有崇高性的“大愛”相對立的一面。這種“小愛”與“大愛”根本對立的思維模式使她發出反抗:“為了愛情,要我放棄工作,改變職業這是不可能的”。如此為了突出季玉潔崇高的“大我”形象而使她為工作事業做出情感的犧牲,在一定程度上是做作的,不自然的,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病態的“自虐”。
而作為人性之一部分的自然情感訴求遭到壓抑,勢必會對其本人造成一定的影響與改變。從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失去“小我”情感的季玉潔并非像季大姐所說的那般幸福,這體現在季玉潔敘述這段感情經歷時憂傷、愁苦的外部環境:“火車轟轟地飛奔,窗外的春天的黃沙仿佛霧氣一樣,緊跟著狂跑的火車流滾。不知什么時候起了風,風在車窗外面的曠野上嘶叫著,有時也發狂地碰動著火車的窗戶。”故事是在一個并不晴朗的環境中展開的,故事的主人公——季玉潔在回顧自己的愛情經歷時始終有一種“別扭”的表情:“也許是由于心情的沉重和煩亂?皺了皺慣于思索的眉頭,遲疑著坐在了我的身邊,久久沒有說話。”而季大姐作為故事的轉述者,無論怎樣給主人公的結局添加幸福的因子,小說中也始終彌漫著一種“苦澀情結”。
季玉潔選擇壓抑“小我”的人性私欲,除了失去愛情,還成為了“無愛”的女性。但作者畢竟帶著“突破束縛”的文學寫作使命,與當時正在出現的男性化的、缺乏個體情感的“鐵姑娘”不同,有著人性情感的因素,融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于一體。但是,這樣的人物形象,也顯示出寫作者面臨的一個無法消除的悖論:既不愿意按流行模式寫作又不能真正沖決模式,因而小說中的女性只能不斷地清理、拋棄自己的自然屬性(女兒性),不斷加添自己的社會性因子,最終變得“無性”和“無情”。對于這種女性,作者仍是采取一種歌頌的態度,“一個事業上的勝利者,在生活上會是敗北的嗎?”作者通過抽空幸福的所指,將幸福與事業強行聯系在一起。“她仿佛是企圖說服我似的”“你看著,玉潔會是幸福的,她怎么會不幸福呢?”這里季大姐也即作者想要說服的不僅是聽故事的“我”,更是聽到這個故事的所有其他聽眾以及季大姐本人:季玉潔所作的犧牲是正確的,能夠敢于犧牲“小我”的人必定是一個有自己的想法和有主張的人,也一定會因她的犧牲而成為一個更“幸福”的人。筆者認為,作者對季玉潔生活態度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存在的極左思潮對創作和個人生活及思維的影響。
三、“道德試錯”的寫作實質
——公共話語對個人話語的壓抑
“雙百方針”提出后,文學領域比較活躍,出現了一批突破了之前極左文學思想“禁區”的各種題材的作品,但強調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仍然是最重要的原則。豐村的小說《美麗》雖然以“婚外戀”題材寫人性人情,與前期小說相比有所突破,但所觸及的只是題材禁區,其內核仍是政治性道德小說,或者說這種“道德試錯”小說是一種對政治與道德宏大主題的“深度模式”改寫。
既然作為實質上的政治道德小說,季玉潔個人對愛情的自然情感訴求受到道德和政治的雙重克制就在所必然。支部書記在小說中是政治力量的化身,她讓季玉潔對黨保證自己的思想動機,而她后來也基于對黨和支部書記的保證,拒絕了首長的求愛,且最終與期待的愛情擦肩而過。作者加于季玉潔工作與愛情的沖突,虛設二者的絕對對立性,將情感的“小我”完全壓抑,形成張揚夸張的“大我”形象。以至于如有的論者所說,“婚姻已經是高張道德的場所,正常的兩性之間的情愛已經被異化。私欲之愛與道德訓誡為指向上的大愛之間呈現為一種兩分的矛盾和斷裂,私欲之愛只是充當了一個供道德訓誡進行否定和批判的不光彩角色。”[3]同時期鄧友梅的小說《在懸崖上》也是以婚戀為題材的同類型作品,我們也可以從小說中科長的話里找到這種壓抑個性的愛情觀:“我們這個杜會的人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不就是要這樣的關心別人,關心集體么?對別人負責,對集體負責,互相都把對方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說穿了,共產主義精神不就是這么個內核嗎?
之所以如此,從寫作者的因素來看,當然受著社會思潮的限定,而且豐村本人從抗日戰爭時期投身于革命事業,創作體現為政治服務也是必然。在自述中說,自己之所以會寫這篇小說,是因為“1955年,周總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著名報告,啟發、教育了我”,小說寫的“僅僅是忠于黨的事業,熱愛工作,勇于生活的普通青年知識分子。小說里也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事件,只不過寫了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4]。可見作者的寫作起點仍是為大時代代言。這就不難理解小說《美麗》既想張揚人性有所突破,卻又使故事的發展表現出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而兩種話語的沖突與矛盾性使小說作品“發出的聲音難免含混不清”,在文學性上也有一定的缺陷。
雖然作為道德小說的實質沒有改變,但涉及到對人性的分析與探究仍是一種文藝創新的好苗頭。這篇小說在題材上將“三角戀”和“婚外戀”這種廣受爭議的男女關系引進小說,甚至讓國家干部也成為關系中的一角,如此大膽的取材,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作者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定的自覺性和文藝創新意識。而對人性的大膽描寫——季玉潔對首長炙熱而隱忍的愛,姚華臨死之際對于愛情婚姻的霸權心態等,其中一些真實的人性因素的顯現也成為這篇小說后來備受爭議的重要原因。
綜上,評價一部文學作品,一定要回到它所在的歷史現場。《美麗》雖然脫離不了其特殊的時代局限,但在文學創作上的突破——對人性的試圖描寫卻是值得承認的。而在文學創作上,正如為了迎合主流話語而損害作品的文學性一樣,當下不少文學作品也走向了反面極端——為了遠離主流話語而對歷史及其人物進行著顛覆性的改寫,賦予其過多的“人性”而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其本身所應具有的“史”的正面意義。因此,文學如何與主流話語保持一定的“產生美”的距離則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與思考。
參考文獻:
[1]孫先科.愛情、道德、政治——對“百花”文學中愛情婚姻題材小說“深度模式”的話語分析[J].文藝理論研究,2004(1):29-37.
[2]楊匡漢,孟繁華,主編.共和國文學50年[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李松濤.欲言又止的秘密訴說———試論百花文學中愛情題材小說的聲音多重奏[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29.
[4]豐村.豐村小說選·后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90.
作者簡介:周文娟,煙臺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