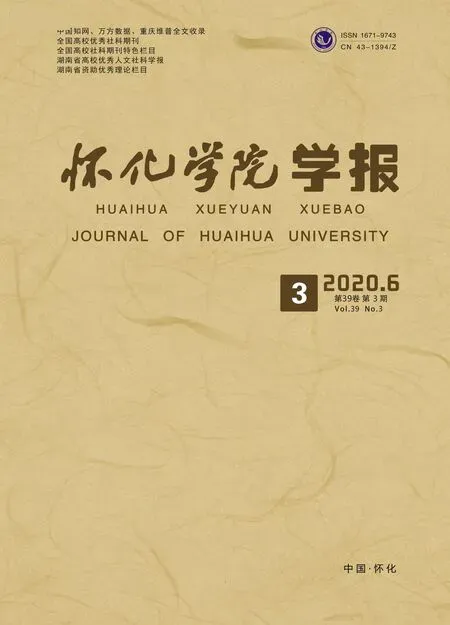跨文化語境中的語言游戲
——維特根斯坦“ 語言游戲” 視域下的《戀人版中英詞典》
強 云, 許俊農
(合肥師范學院1. 外國語學院; 2. 圖書館, 安徽合肥230601)
“語言游戲” 是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思想的理論精髓,標志著他從邏輯哲學向語用哲學的轉變。他對語言關注的焦點亦從邏輯層面的語言分析轉向日常生活中實際使用的語言。維特根斯坦通過對語言游戲、生活形式、遵守規則等問題的哲學探究,揭示了語言的本質特征。
《戀人版中英詞典》 是英國華裔女作家郭小櫓創作的首部英文小說,在海外引發熱烈反響,并成功入圍英國頗負盛名的柑橘小說獎。小說主人公是一位來自中國小城鎮的 “Z” 姓女孩,被父母送往英國學習語言。小說采用獨特的 “字典—日記” 體敘事結構,以第一人稱敘事視角記錄了女主人公在跨文化語境中語言學習的心路歷程,以及伴隨而至的一段跨國戀情。僅從書名就不難發現語言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中英詞典不僅是女主在異質疆域中賴以生存的語言工具和愛情的幕后推手,更是成為其生活的一面鏡子,折射出跨文化語境中語言游戲的本質面貌。而女主亦在這場跨越異質疆域的語言游戲中完成了跨語言的蛻變,從最初只關注詞典中的理想語言,到最終深刻理解現實中實際使用的語言,并在親身參與跨文化語言游戲的實踐中實現了自我的成長與文化身份的重構。
本文基于維特根斯坦的 “語言游戲”,探討《戀人版中英詞典》 中女主人公在跨文化語境中所親歷的他者語言游戲,以及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游戲規則與語言意義之間既關聯又沖突的辯證關系。
一、維特根斯坦的 “語言游戲”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由前、后期兩個迥然相異的哲學體系構成,前期以《邏輯哲學論》 為代表,主張 “語言圖像論”,以圖像為喻,描繪 “語言與世界的邏輯對應關系”[1]52;而后期之《哲學研究》 則在批判前期人工語言邏輯分析的基礎上提出 “語言游戲”,擺脫形而上的、靜態固化的哲學框架,在實際動態使用中探究自然語言的本質。
“語言游戲(Sprachspiel)” 之釋義可追溯至《藍皮書和褐皮書》,“對語言游戲的研究就是對語言的原始形式或者原始語言的研究”[2]102。維特根斯坦進一步認識到現實使用中的語言在功能和用法上的多樣性,并在《哲學研究》 中將語言游戲描述為“語言及與之相交的活動所構成的那個整體”[3]13。
現實世界中的語言游戲是一個遠超于編碼和解碼的復雜過程。它并非是 “由單純描述事實的命題組成的單一構造物,而是豐富多彩、功能多樣的異質類聚物”[2]105。而 “語言的說出是一個活動或者一個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3]24。維氏的語言游戲觀凸顯了語言在本質上與人們的生活形式、行為活動相互交織的鮮明特色。而 “生活形式” 與 “語言游戲” 則構成維氏后期哲學的靈魂[4]11。語言非孤立地存在,且語言的使用也并非在真空中進行。源自于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自然語言之所以會呈現出多樣性,則是由多元化的生活形式所造就。鑒于此,我們對語言意義的理解基于我們自身所處的相對熟悉的生活形式。“想象一種語言,即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3]18任何語言游戲都無法脫離息息相關的生活形式而存在。
另一方面,語言既為游戲,必然具備一定的規則,而參與游戲則需遵守游戲規則,這也是語言游戲實踐的基礎。盡管維特根斯坦并未對遵守規則做出明確的界定,但他強調 “遵守規則是一種實踐”[3]144。只有在親身參與語言游戲的實踐中才能真正體會規則需要遵守,而 “規則本身亦非靜態、一成不變的,而是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5]101。日常語言中語言游戲的多樣性無法被嚴格的規則束縛,規則的適用性依據具體的語言使用情境而定,同時,“規則在具體實踐中所形成的張力導致了語義的不確定性”[5]102。語言的意義并非內在固有的,而是依附于語境,隨著歷史、文化語境的變化以及語言游戲使用情境的變化而變化。
二、維特根斯坦 “語言游戲” 之跨文化解讀
(一) 跨文化語境中的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
“語言游戲植根于生活形式”[5]100,無法脫離作為其基礎的生活形式而存在。身處于不同生活形式之中的人往往會對同一種語言游戲產生不同的解讀,抑或使用不同的語言游戲表達同一種生活現象。理解語言游戲所依附的生活形式是理解語言的前提條件,任何割裂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的嘗試必然導致認知上的消極受納,甚至扭曲、變形和誤解。小說中女主在跨文化語境中所經歷的種種從一個側面映射出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之間交織繁復的關聯。中西方迥然相異的文化衍生出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而基于生活形式的語言游戲亦因此大相徑庭。
由于本身英語基礎薄弱,初到英國的女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語言困境。當她第一次在英國乘坐出租車時,司機反復多次地提醒她:“請恰當地(properly)關好車門!”[6]40可是身處異質語境下的她完全無法理解司機所謂的恰當是何種恰當。誠然,依據《柯林斯英語字典》 “恰當” 一詞的字面意思為 “正確的行為”[6]40,然而,若給恰當、得體下定義,顯然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會給出不同的解答,因為這些語言本身已然不再是單純的詞語或結構,而是刻有文化烙印的生活形式在語言世界中的回應。換言之,語言不僅是對世界的反映,更是對世界的反應。正如女主想要在《柯林斯英語字典》 中找尋自己的行為與出租車司機所言不相吻合的答案,結果卻只是徒勞。因為語言游戲的答案不在語言本身,而是在作為文化載體的生活形式之中。在語言學校,女主因不當的英語言語方式而遭人詬病,被冠以 “不懂禮貌” 的惡名聲,同學稱其為 “那個粗魯的中國女孩”。在女主眼里,“英國的禮節太復雜,中國的禮貌不是這個樣子”[6]60。盡管女主對中國文化中有關禮貌行為的認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同的文化習俗及其相應的生活形式對同一種行為的理解亦有千差萬別。語言游戲無法超越生活形式之上,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習俗中,語言游戲才得以理解。在跨文化語境下,女主面對他者的語言游戲之所以會遭遇理解上的瓶頸,并非其能力所致,而是她所置身的充滿異質文化的生活形式引發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女主而言,想象一種新的生活即是學習一門新的語言。而如何按照英國人慣常的生活形式去駕馭語言游戲,學會得體、恰當、禮貌地說話行事是女主在異質疆域中不得不學習的第一課。
不僅如此,由于語言游戲背后所關聯的蘊含不同文化習俗、思維習慣、行為模式的生活形式,同一種語言在兩種文化中亦有可能激發截然相反的情感態度和反應。小說中描述了一個極其有趣的例子。在咖啡館里,一位英國老人放了個屁,女主出于對語言學習的狂熱,不以為然地詢問男主 “屁”(fart)在英文里如何表達,老人對此感到極為羞愧。女主故而發現英國人 “因為羞于發出這個音,而從來不用這個詞, 甚至連英文字典都說那是一種禁忌”[6]162。然而在女主慣常的中式思維之作用下,她理所當然地認為 “屁” 乃人中之 “氣” (Chi),與健康息息相關,因而并無產生任何排斥的情緒。在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中,中國人十分看重與“氣” 相關的一切事物,在中文里也存在大量與此相關的詞語,如太極、氣功、氣場等[6]162。由此可見,英國老人與女主對同一個詞語所引發的迥然相異的反應,與其說是兩種語言使用上的差異,毋寧說是社會文化影響下的兩種思維模式的迥異。維特根斯坦強調 “語言是一種習慣、一種制度、一種社會文化,屬于語言游戲的是整個文化”[7]5。這也意味著,“設想一種語言,即設想一種文化”[7]5。
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的不可分割性在小說中得到了有力的彰顯,同時女主通過參與跨文化語言游戲的親身實踐揭示了兩種文化間隔閡與沖突的本質根源——植根于不同文化傳統之中的生活形式所引發的相異的語言游戲。
(二) 跨文化語境中的游戲規則與語言意義
任何游戲都有一定的游戲規則可循,語言游戲亦是如此。參與其中的人只有在語言游戲的實踐中遵守規則才能順利進行游戲,并最終實現理解語言意義的目標。同理,個體從本土文化跨越到異質文化之中,參與他者的語言游戲,同樣需要遵守他者的游戲規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中女主在跨文化語境下語言學習的過程即是一個參與他者語言游戲的過程。她在跨文化語言游戲的親身實踐中,在遵守規則與違反規則的矛盾過程中,找尋語言意義的真諦。只是對女主而言,由于他者文化及生活形式的異質性,這一實踐過程波折更多。
一般而言,擁有同一種生活形式的人對特定的游戲規則認知基本一致。這種文化內的共識也是語言理解和人際溝通的基礎。然而對于來自異質文化的個體而言,他者的游戲規則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參與他者語言游戲的實踐實則是從無意識地違反規則到有意識地遵從規則的漸進過程。初到英國,女主對異質文化語境中游戲規則與語言意義的認知極為匱乏,天真地以為只要有一本紅寶書——《簡明英漢字典》 在手,就可以在語言學習的道路上一帆風順。盡管她竭盡全力地隨時隨地收集和記錄下每個新詞,依據《簡明英漢字典》 進行對照、檢測,拼湊出語句,從而獲得所謂的語言意義,但是結果卻事與愿違。種種現實促使她發現他者的語言游戲并非如此運作。在小說的最初幾個章節中充斥著大量 “違反游戲規則” 的英文表達。這些以詞語堆砌、以中文邏輯串聯而成的句子雖在英文中顯得毫無意義,卻成為女主了解他者游戲規則進而理解語言意義的第一步。她在語言的實際使用中逐漸意識到語言的意義構成不僅僅依靠詞語的排列。每一個詞代表了個體想表達的一部分意思,但如果孤立地看待每一個詞,最后就有可能演變成邏輯不通的句子。雖然詞語串聯成句,但全句卻喪失了語言完整的意義。作者借用女主的口吻誤用、錯用英語,以示從一開始,語言就非純粹的、非自然的,極度依賴語言使用的語境。語言規則在作者的筆下被挑戰、被破壞,而碎片化的英語則被賦予了超越語言規則的意義。此外,語法是語言規則最直接的體現,這恰恰也是女主最為薄弱的環節。她常常混淆作主語的“I” 和作賓語的 “me”;她質疑英文單詞的時態之分,如 “love” 因不同的時態而變得有時限;她對泛指人時用 “he” 而非 “she” 感到困惑;她對英文句子中將主語 “人” 置于句首的構造同樣不解。這些他者的游戲規則與女主所熟悉且擅長的語言游戲大相徑庭。若想在他者的語言游戲中游刃有余,遵守語法規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事實上,與其說語法差異反映出不同文化間語言游戲的不同所在,不如說語法在語言規則之外投射出一個異域他者的世界。對女主而言,理解語言的意義不僅僅是辨識語法的正確與否,更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后所蘊含的深刻的文化內涵和迥異的思維模式。
然而,語言的意義并非完全由規則所決定。一方面,我們借助語言而生活,游戲規則通過語言的反復使用而蘊含其中。另一方面,未知的生活形式中常有超出規則限制的情境。“規則始終處于變化之中” 才是恒久不變的真理,亦是語言游戲的必然結果。小說中每一章節之首均附有一個英文單詞及其相應的字典釋義,但幾乎每個字典條目之后的故事無一例外地打破了規則的束縛,所謂字典中的語言意義在不同的情境中消解,而有關語言意義的真相浮出水面,即 “語言的意義只存在于語言游戲之中”[8]34,在語言的使用中得以彰顯。這一真相亦體現在特定的語境中女主對某些詞語的 “擅自改造”。例如,女主稱 “Big Ben” (大本鐘) 為 “Big Stupid Clock” (大笨鐘)[9]14。“本” 在漢語中發音等同于“笨”。但女主之所以故意這樣稱呼它,則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她被父母強行送往英國學習語言,對于即將面對的陌生世界內心本就充滿了抗拒、恐懼和擔憂,加之初來乍到的各種遭遇導致她對倫敦倍感厭惡和不悅。“Big Ben” 這一原本中性的詞語被女主人為地添加了負面的感情色彩,其語言意義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無獨有偶,女主將單詞 “illegal” 拼寫為 “Ill- legal”[9]17,亦映射了單詞拼寫規則之外的隱藏含義。女主試圖通過異乎尋常的拼寫來嘲諷自己來到英國三天已然變成了 “小偷”。為了節省開支,她將咖啡杯、多余的早餐偷偷地帶回;她努力地學習英語,并想象在不久的將來甚至偷了他們的語言。ill 即意味著 “病態的、不健康的”[9]18,其中蘊含著女主強烈的、負面的個人色彩。顯然這樣的拼寫擺脫了詞語常規的語義,在跨文化的語境中獲得了不一樣的新意。維特根斯坦指出,我們知道一個詞語的中心含義,并非等同于知道它所有的用法。相反地,語言使用中的語言意義才是最重要的。盡管字典中包含了大量有關語言使用的例句,但也無法涵蓋語言所有矛盾的、情感的、反邏輯的方面。女主置身于跨文化的語言游戲中,在各種游戲規則的碰撞中習得了語言意義的真諦。
三、結語
維特根斯坦的 “語言游戲” 對我們理解跨文化語境中語言游戲的運作和語言意義的獲得具有重要的啟示。 《戀人版中英詞典》 通過對女主跨文化語言游戲親身實踐的描述,揭示了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在遵守游戲規則的實踐中把握語言的意義。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語言作為文化符號之跨文化解讀尤為重要。在跨文化的語言游戲之中,跨越異質文化的障礙,擁抱多元化的生活形式,并基于規則的開放性和多變性,“搭建從語義到語用的橋梁”[10]466,回歸語言的實際意義,是在跨文化語境中消除誤解、彌合分歧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