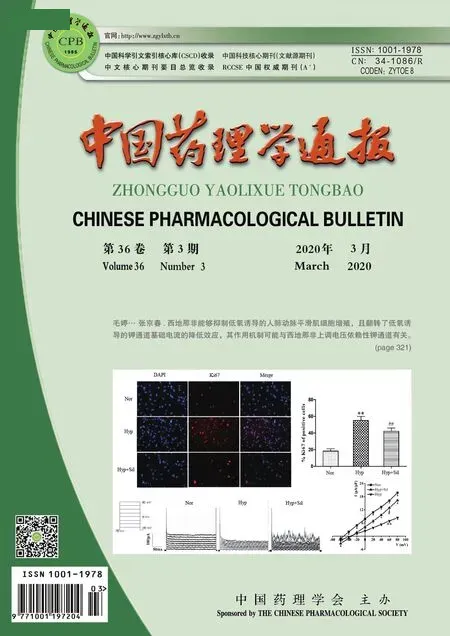Nupr1/ERS/NLRP3炎性小體在甲基苯丙胺誘導的神經毒性中的作用
楊根夢,曾曉鋒,張冬先,洪仕君,李利華
(昆明醫科大學法醫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METH)屬于苯丙胺類興奮劑,俗稱“冰毒”,具有神經毒性大、依賴性強、復吸率高等特點[1],我國最新毒品報告顯示,METH已取代海洛因成為我國濫用最多的毒品。長期濫用METH對中樞神經系統可產生明顯的毒性作用。METH毒性作用可能與氧化應激、神經細胞凋亡和自噬[2]、膠質細胞激活[3]以及炎癥反應[4]等有關。但截至目前為止,METH誘導神經毒性作用和成癮機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Nupr1核蛋白1(nuclear protein 1,Nupr1)可通過內質網應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途徑介導METH誘導的神經細胞凋亡和自噬[5]。Nupr1作為應激蛋白,可通過線粒體經典途徑在METH誘導內皮細胞凋亡中發揮重要作用[6]。并且ERS可參與METH誘導血腦屏障損傷過程[7]。此外,ERS可激活NLRP3 炎性小體,并參與認知功能障礙和抑郁樣表現[8]。METH濫用可激活小膠質細胞NLRP3炎性小體[9],NLRP3 炎性小體可活化caspase-1來誘導IL-1β和IL-18前體的成熟并釋放IL-1β和IL-18,從而引起炎性反應。本文通過對Nupr1、ERS和NLRP3 炎性小體與METH神經毒性的相關研究進行總結,旨在為進一步研究METH神經毒性作用機制提供參考。
1 Nupr1與METH神經毒性作用
Nupr1可參與多種病理生理過程,尤其是對腫瘤的調節具有雙重作用,Nupr1即能促進腫瘤的生長和進展,又具有抗腫瘤活性。正常情況下,Nupr1表達水平很低,但在缺氧、氧化應激、DNA損傷和其他應激條件下,Nupr1可被誘導并發揮相應的作用。研究發現,Nupr1在METH誘導神經細胞毒性作用中發揮重要作用。METH對大鼠,PC12細胞和原代大鼠皮質和紋狀體神經細胞產生的毒性作用(主要表現為凋亡和自噬)具有METH濃度和時間依賴性,同時Nupr1的表達水平也明顯升高。沉默Nupr1基因后,凋亡和自噬相關蛋白表達水平不同程度的降低,說明Nupr1參與調節METH誘導的神經細胞毒性作用[5]。此外,研究發現,METH給藥后,人臍靜脈和大鼠心臟微血管內皮細胞Nupr1表達水平具有METH濃度和時間依賴性,同時內皮細胞發生明顯凋亡。通過沉默Nupr1基因證實Nupr1的激活是METH誘導內皮細胞凋亡所必需的[6]。上述研究說明Nupr1參與METH誘導神經毒性作用的調節。
2 ERS與METH神經毒性作用
內質網是蛋白質合成、加工和運輸的主要場所。外界因素的刺激可引起內質網內錯誤折疊蛋白增加和未折疊蛋白聚集等,該過程稱為ERS。正常情況下,細胞會通過誘導未折疊蛋白反應(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UPR)來減輕ERS對細胞的損傷。而長時間ERS會破壞內質網的保護能力而導致促神經毒性的炎癥反應和凋亡程序的激活[10]。并且長時間ERS會導致慢性和持續的UPR,而UPR會通過上調激活轉錄因子4激活細胞凋亡通路而導致細胞死亡[11]。研究表明,ERS參與毒品濫用誘導的神經毒性作用。如可卡因可通過ERS激活自噬而誘導星形膠質細胞發生炎癥反應[12],通過ERS-自噬通路和ROS-ERS-ATF4-TLR2通路激活小膠質細胞而誘導神經毒性作用[13,14]。METH可通過激活氧化應激和ERS促進細胞死亡[15]。應用C57BL/6J小鼠和BMVEC細胞進行研究發現,METH可通過損傷BMVEC細胞的血腦屏障,導致細胞凋亡從而降低細胞的存活率,同時,ERS相關蛋白p-PERK ,p-IRE1α,ATF6,和GRP78/BIP的表達水平和CHOP表達水平明顯升高。說明METH可激活ERS,并上調促凋亡蛋白CHOP的表達,而CHOP是ERS的主要調節者,同時也是細胞凋亡的執行者。因此,METH可通過激活ERS誘導內皮細胞血腦屏障損傷而引起細胞凋亡。此外,METH可誘導大鼠神經膠質瘤(C6)細胞表達ERS相關蛋白明顯升高,METH激活ERS后細胞存活率隨著METH濃度的增加逐漸降低[16]。Shah等[17]應用SVGA細胞和人胎兒星形膠質細胞為研究對象,發現METH可通過ATF6,IRE1α和PERK途徑激活ERS而誘導星形膠質細胞發生Ⅰ型程序性細胞死亡。且METH可通過多巴胺Ⅰ受體激活ERS而誘導大鼠紋狀體神經細胞凋亡[18]。上述研究均說明METH激活ERS與其誘導的神經毒性作用密切相關。
3 NLRP3 炎性小體與METH神經毒性作用
NLRP3炎性小體由NLRP3蛋白本身、凋亡相關斑點樣蛋白和半胱天冬酶-1前體(pro-caspase-1)組成。pro-caspase-1經加工形成具有活性的caspase-1,隨后切割IL-1β和IL-18的前體,最終分泌成熟的IL-1β和IL-18[19]。NLRP3 炎性小體是神經系統炎癥反應的核心。在病理狀態下,線粒體-ROS-NLRP3炎性小體,ROS-NF-κB-NLRP3炎性小體和自噬-NLRP3炎性小體通路對機體的調節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20]。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參與了藥物濫用如酒精、可卡因、嗎啡和METH濫用等的調節[19]。METH可明顯降低大鼠海馬CA1區星形膠質細胞抗氧化酶SOD和GSH的表達水平,同時誘導MDA、TNF-α、GFAP和caspase-3的表達水平明顯升高。說明METH通過激活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誘導神經細胞凋亡[21]。IL-1β是中樞神經系統炎癥反應中較為重要的細胞因子,可增加藥物依賴的風險。研究表明,IL-β基因多態性與阿片類藥物和酒精依賴有關,位于511和31位點的IL-1β單核苷酸可明顯增加IL-1β的釋放,隨后可激活谷氨酸受體、NMDA受體和多巴胺受體,最終引起藥物依賴[22]。METH可激活NLRP3 炎性小體并對脂多糖誘導小膠質細胞產生和釋放IL-1β具有明顯的增強作用。METH激活NLRP3 炎性小體具有時間和濃度依賴性。且METH通過刺激線粒體產生大量ROS和破壞溶酶體的通透性來激活炎性小體,從而促進IL-1β的成熟和分泌,最終加重小膠質細胞的神經毒性作用[23]。此外,Du等[9]以C57BL/6J野生型小鼠和BV2 細胞為研究對象,結果表明,METH可激活NLRP3炎性小體,同時誘導iNOS表達水平明顯升高,同時發現METH可通過MiR-143 /PUMA軸激活NLRP3炎性小體。
總之,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在METH濫用中發揮重要作用,首先METH濫用可刺激神經細胞釋放一些危險相關因子如細胞因子、內毒素和神經毒性有關因子等;其次METH濫用可破壞血腦屏障,上述與神經毒性有關的因子可通過血腦屏障,從而激活小膠質細胞和誘導IL-1β和IL-18前體明顯增多,并激活NLRP3炎性小體。再者METH濫用可激活小膠質細胞釋放大量鉀離子,ROS和激發ERS,從而促進IL-1β和IL-18的成熟和釋放。IL-1β的過量釋放可引起明顯神經元炎性反應而導致神經元損傷[19]。上述研究均說明NLRP3可作為抗神經炎癥治療的新靶點。
4 Nupr1、ERS和NLRP3炎性小體之間的關系
Nupr1可通過CHOP-Trib3介導的ERS信號通路調節METH誘導神經細胞凋亡和自噬,通過沉默Nupr1基因,發現ERS相關蛋白(CHOP/Trib3)表達水平明顯降低,同時METH誘導的神經細胞凋亡和自噬水平有所下降。而沉默ERS相關蛋白(CHOP/Trib3)之后,Nupr1表達水平不受影響,而METH誘導的神經細胞凋亡和自噬水平有所下降,說明Nupr1作為ERS的上游,而神經細胞凋亡和自噬作為ERS的下游[5]。此外,METH可激活Nupr1-Chop/p53-PUMA/Beclin1途徑誘導線粒體介導的內皮細胞凋亡。該研究也說明Nupr1與ERS密切相關,且Nupr1作為ERS的上游[6]。作為ERS感受器的IRE1α可通過介導NLRP3的激活誘導線粒體功能障礙,而激活IRE1α可使線粒體釋放大量ROS,并增強NLRP3與線粒體之間的關聯性。IRE1α是通過NLRP3、caspase-2和Bid相互作用誘導線粒體功能障礙,同時ERS通過NLRP3-caspase-2 軸激活NLRP3炎性小體并釋放大量的IL-1β[24]。上述研究均說明Nupr1、ERS和NLRP3炎性小體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關系。
5 總結與展望
總之,大量研究表明,Nupr1、ERS和NLRP3 炎性小體均參與了METH誘導的神經毒性作用,但具體作用機制及信號通路尚不清楚。且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公認的有效藥物可以治療毒品成癮。因此,研究METH誘導神經毒性作用和成癮機制以及尋找有效干預治療藥物將會是今后該領域研究的重點和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