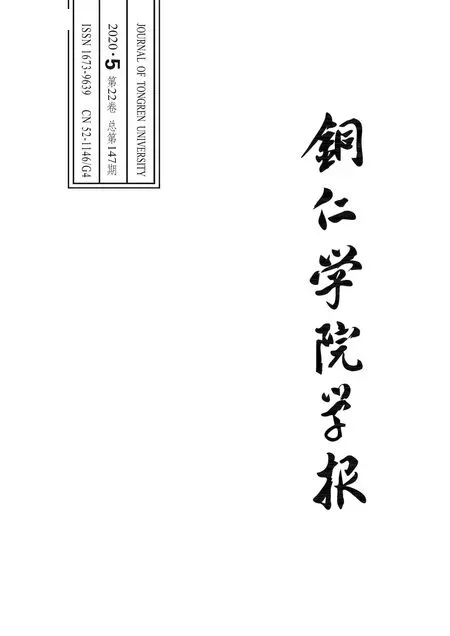顏延之《庭誥》與漢魏道教文學(xué)思想——以“心性論”為核心
徐東哲,蔣振華
【文學(xué)研究】
顏延之《庭誥》與漢魏道教文學(xué)思想——以“心性論”為核心
徐東哲1,蔣振華2
(1.山東理工職業(yè)學(xué)院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山東 濟(jì)寧 272067;2.湖南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湖南 長沙 410081 )
一直以來,儒家與佛教為顏延之思想之源頭的觀點(diǎn)已成為學(xué)者之共識(shí),但有關(guān)道教對顏延之思想影響的研究卻有所忽視。在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影響論之外另辟蹊徑,從道教思想對顏延之文學(xué)觀念的影響方面入手進(jìn)行分析,通過對《庭誥》條分縷析地解讀,及同漢末道教經(jīng)典文獻(xiàn)《老子想爾注》的對比中,證明《庭誥》中的“心性”文藝?yán)碚摚耸穷佈又趯h魏道教文學(xué)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中形成的。其將心性涵養(yǎng)與文學(xué)修養(yǎng)相統(tǒng)一的文學(xué)認(rèn)識(shí)論、“本之自性”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論和“心照若鏡”的文學(xué)批評論,及其倡導(dǎo)的恬淡寡欲、辭簡意深的風(fēng)格論,共同構(gòu)成了基于漢魏道教思想、獨(dú)具特色的文學(xué)理論體系。
心性; 玄學(xué); 般若學(xué); 道教
南朝宋時(shí)的顏延之《庭誥》,其書主旨乃在教授顏氏子孫立身修德、為人處世之道,可謂是顏氏家族現(xiàn)存最早的家訓(xùn)作品。正如顏延之本人所言: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nèi),謂不遠(yuǎn)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1]55
顏延之將自己的道德觀念與處事原則凝結(jié)在《庭誥》一書中,以此勸誡家族子弟修身治學(xué),這是其著書的本來宗旨。但其書并非僅有家風(fēng)家訓(xùn)方面的內(nèi)容,而是雜糅了顏延之的宗教哲學(xué)、政治態(tài)度、文學(xué)主張等多方面的思想,尤其是在文學(xué)思想上《庭誥》之材料尤為豐贍。但究其本源,顏延之尤其重視的是人的心性涵養(yǎng),其書立論之宗亦是以“心性”思想為理論根基。故其在《庭誥》開篇便點(diǎn)名此義:
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1]55
顏延之之所以重視心性修養(yǎng),主要是由其個(gè)人經(jīng)歷與社會(huì)思潮兩個(gè)方面所決定的。個(gè)人方面而言,其子顏竣無疑對其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顏竣是劉宋位極人臣的重要人物,但其心性狷介,剛愎自用,不僅與同僚間關(guān)系惡劣,后來甚至與宋孝武帝之間也產(chǎn)生了隔閡矛盾。顏竣過分的自我膨脹使得顏延之對其命運(yùn)憂慮不已。顏延之曾當(dāng)面向顏竣提出批評,告誡他:“驕矜傲慢,其能久乎?”但無奈的是,顏竣對其訓(xùn)誡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顏延之亦無可奈何。這點(diǎn)在《宋史》中有著清晰的記錄:
(顏延之)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后人笑汝拙也。”[1]57
顏竣的性格缺陷使得顏延之深刻地反思對家族子弟心性修養(yǎng)教育的必要性,這也是他在《庭誥》中不厭其煩地去訓(xùn)誡后人摒棄私欲、克己治心的重要原因。后來果不出顏延之所料,顏竣因“訕訐怨憤”觸怒孝武帝,被下獄賜死,顏竣的人生悲劇可以說是顏延之重視心性教育的最好注腳。
從社會(huì)思潮方面而言,由于《庭誥》誕生于南朝,故其成書必然要受到南朝社會(huì)風(fēng)氣、宗教思想、政治環(huán)境等多方面的影響。而劉宋正值玄學(xué)與佛教般若學(xué)盛行之時(shí),適時(shí)般若學(xué)中有關(guān)“心性”的理論對社會(huì)影響尤其深刻,在關(guān)于“性”之存滅的大辯論中,顏延之甚至親自執(zhí)筆反駁何承天的“性滅論”。由此而言之,顏延之對“心性”之學(xué)的造詣是極為深厚的,這點(diǎn)直接決定了他在《庭誥》的撰寫中大量地采用了“心性”之學(xué)的理論來闡述其思想主張。
值得注意的一點(diǎn)是,《庭誥》中所體現(xiàn)的“心性”思想絕非僅限于般若學(xué)的范疇,而是顏延之博采眾家之長后,所形成的獨(dú)特理論體系。一直以來,儒家與佛教為顏延之思想之源頭的觀點(diǎn)已成為學(xué)者之共識(shí),但有關(guān)道教對顏延之思想影響的研究卻有所忽視。但無可否認(rèn)的是,《庭誥》中大量的思想材料都證明了漢魏道教思想對顏氏的影響是十分之深的。本文首先對《庭誥》中的“心性”思想材料進(jìn)行解讀,并溯其源流、通其脈絡(luò)。唯有明了《庭誥》中的道教思想因素后,對其“心性”文學(xué)思想的解讀方可避免以偏概全。
一、《庭誥》“心性”思想原型解構(gòu)
通過對《庭誥》的思想分析,可知其思想構(gòu)成十分復(fù)雜,而其“心性”思想之主旨乃是以道教觀念為原點(diǎn)而引申出的,飽含道教心性之學(xué)的哲理因子。顏延之撰《庭誥》的初衷,便是論治心之術(shù),《庭誥》有云:“今所載或其素蓄,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雖然儒家對修身養(yǎng)性之道亦多有闡釋,但若深入剖析《庭誥》文本,可以發(fā)現(xiàn)其所闡發(fā)的治心之道與儒家心性之學(xué)之間是有所差異的。儒家講修心之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禮制欲,使人之身心更合乎人情倫理之要求,其道乃人道,而顏延之在《庭誥》中則著重強(qiáng)調(diào)人的“靈性”,主張人應(yīng)恢復(fù)到先天所具備的真性,而不以后天人倫束縛本性,漸至扭曲。這一承運(yùn)順化的思想主張與道家相一致,可知顏延之所云之“道”正是老子所云之“天道”。天道之運(yùn)行的至高規(guī)律便為“道法自然”,唯有順應(yīng)自然,心方歸清靜,心性如若澄明,即使沒有仁義道理約束,人也自然而然地歸于樸素本性。顏延之在論“慈孝有悌”之義時(shí),便是以“天道”觀念進(jìn)行闡釋的。《庭誥》曰:
身行不足,遺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zé)弟悌務(wù)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1]56
《老子》中即有曰:“六親不和,有孝慈。”《老子想爾注》釋云:“道用時(shí),家家慈孝,皆同相類,慈孝不別。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親不和,時(shí)有一人行慈孝,便共表別之,故言有也。”[2]43顏延之從“天性之道”的觀點(diǎn)出發(fā),指出“慈孝友悌”乃是由感情的相互作用所產(chǎn)生的和諧親情關(guān)系,并非是由倫理綱常所引發(fā)出的概念,在這對倫理關(guān)系中,倘若一方失和,那和諧關(guān)系必將整體崩潰。故《庭誥》有云:“夫和之不備,或應(yīng)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1]55顏延之對人倫關(guān)系的認(rèn)知正是以老子的樸素辯證法為基礎(chǔ)來闡釋的,而沒有從社會(huì)人倫關(guān)系來著眼。
《庭誥》反映出的道家天道思想,還可以通過其對“心性”的認(rèn)識(shí)中加以理解。顏延之論“性”,包含著濃厚的宗教神秘色彩。雖然其對性出之于心的觀點(diǎn)與儒家并無二致,但其卻將性視作一種永存不滅的恒定存在,不因人的生死而改變,這一點(diǎn)可謂與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南朝時(shí),曾有一場關(guān)于“性滅”與“性不滅”的重大爭論,而顏延之所持之立場正是“性不滅”觀。乍看之下,顏氏所云“性不滅”乃為佛教之觀點(diǎn),與魏晉道教大有差別。因?yàn)槲簳x南朝道教尚重視煉形,未建立起自身的性命雙修理論。但通過析研《庭誥》卻能發(fā)現(xiàn),顏氏已有意識(shí)地調(diào)和佛道兩教觀點(diǎn),認(rèn)為兩者思想觀上其實(shí)并無本質(zhì)差別,他在《庭誥》中申明:
達(dá)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繇途參陳,要而會(huì)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jīng),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xué),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差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nèi)。一以此思,可無臆裁。[1]57
其實(shí)在南朝之世雖然佛道之爭已呈愈演愈烈之趨勢,但主張二教合流的道教人士亦多有之。《中國道教思想史》對其問題有所論證:
在(魏晉)佛道二教相互對立的激烈爭論中,仍有調(diào)和二教的聲音存在。張融、劉法先、孟景翼、陶弘景都為調(diào)和論的支持者與倡導(dǎo)者。[3]545
從顏延之《庭誥》此段文字中可以窺見其將二教思想有意識(shí)地相統(tǒng)一的思想傾向,尤其對二教主張心性長存的認(rèn)識(shí)更是深感贊同,認(rèn)為其源出無二,差別無非是修煉方式的不同。但無論是重形修命的道教還是治心養(yǎng)性的佛教,最終都可以達(dá)到“性不滅”的至高精神境界。張融在《門論》中亦有與顏延之相同的觀點(diǎn):
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無動(dòng),致本則同。感而遂同,達(dá)亦成異。[4]38
所以在研究顏延之思想時(shí)應(yīng)該認(rèn)識(shí)到,其思想構(gòu)成并非限于佛道中的一門,更不是簡單地各取所長,而是在其本身的“心性不滅”的認(rèn)識(shí)下,將二教視為一個(gè)整體。正是在南朝顏延之等通達(dá)之士的前識(shí)之下,三教一本的思想才逐漸發(fā)揚(yáng)光大,為后來道教內(nèi)丹學(xué)說及心性修養(yǎng)理論的誕生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
研析《庭誥》有關(guān)“心性”理論對佛道思想攝取的源頭,亦可以發(fā)現(xiàn)道教思想對其影響之深。顏延之在《庭誥》中闡釋“心性”之說時(shí),常借佛理研析心性文理。如其有曰:“夫以怨之非為心者,未有達(dá)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1]55此處所云之“達(dá)無心救得喪”正源出魏晉間佛教思想。
魏晉之世正值般若學(xué)昌盛之際,其時(shí)佛學(xué)研究者圍繞心性之有無問題各抒己見,形成了“六家七宗”的法系之別。其中僧肇之般若無知義受到了中土人士的大力推崇。關(guān)于僧肇的理論觀點(diǎn),馮友蘭的《中國哲學(xué)史》中的一段文本闡釋得相當(dāng)透澈:“第三溫法師用心無義。心無者,無心于萬物,萬物未嘗無。”[5]55此段論無心之義乃是本之于“有無”這對哲學(xué)范疇來談的。這與魏晉玄學(xué)思想命題相一致。般若學(xué)在中土發(fā)展之初便與玄學(xu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甚至有眾多士人將其與玄學(xué)視為同源一脈的思想產(chǎn)物。由于佛教思想中諸如“緣起性空”“萬法皆空”等諸多思想在初入中國時(shí)并沒有相應(yīng)的哲學(xué)理念與其互為補(bǔ)充,故而佛教的晦澀義理難以被廣大人民所接受,而要進(jìn)行更為深入的佛理研究便更無從下手。為解決這一問題,魏晉間諸多僧人就將佛理嫁接于當(dāng)時(shí)大為流行的玄學(xué)理論上,采用玄學(xué)的思想來闡釋佛理,這便使得佛教思想更易為士人所理解與掌握。
彼時(shí)很多精通佛理的知名僧人也同時(shí)為技藝超群的玄學(xué)思辨大師,如支道林解釋《莊子》,使眾人為之嘆服就是一個(gè)很經(jīng)典的例子。佛教作為一個(gè)專注于精神修煉的教派,更為注重超脫彼岸,而以為此生此世如“夢幻泡影”,皆為虛幻,這一點(diǎn)同追求“與世長存,畢天不朽”的道教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故而后世道教人士會(huì)嘲笑佛門弟子,“只知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但不應(yīng)被忽視的是,道教對于心性修煉方面的內(nèi)容同樣十分重視,早在內(nèi)丹道興盛之先,道教修行者已將“心性”視為重中之重。
早在先秦時(shí)代,道家文獻(xiàn)中便已有豐富的“心性”修養(yǎng)理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莊子》,魏晉間諸多佛教學(xué)者更是直接攝取了《莊子》“心性”思想來補(bǔ)充完善自己的理論。如《莊子》有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yīng)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6]285僧肇在其《般若無知論》中便直接吸收了莊子“用心若鏡”的觀點(diǎn),其文曰:“是以圣人虛其心而實(shí)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dú)覺冥冥者矣。”[7]153
繼承先秦道家思想之正統(tǒng),張道陵開創(chuàng)道教之初亦十分重視“心性”的重要作用,在《老子想爾注》中多次提到“心”對人一身性命的統(tǒng)攝作用。如其有曰:“不欲視之,比如不見,忽令心動(dòng),若動(dòng)自誡,道去復(fù)還,心遂亂之,道去之矣。”[2]47漢代道教文獻(xiàn)《太平經(jīng)》中,亦對“心”之統(tǒng)攝作用有所論述:“天有五氣,地有五位。其一氣主行,為王者主執(zhí)正。凡事居人腹中,自名為心。心則五臟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8]187稍晚于《老子想爾注》《太平經(jīng)》,誕生于魏晉時(shí)代的《西升經(jīng)》,甚至已將修心養(yǎng)性置于養(yǎng)形之上,在其《身心章》即有言曰:“常以虛為身,亦以無為心,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9]50《西升經(jīng)》所謂之心神守一,再后來則轉(zhuǎn)變?yōu)榈澜绦逕捓碚撝信e足輕重的一個(gè)概念。
魏晉間道教理論中的“心性”修煉之道,其所本仍在《老》《莊》,其功用而在于養(yǎng)生修命,頤養(yǎng)天年,這與般若學(xué)借玄學(xué)以闡佛理的初衷并不相同。但在玄理與佛學(xué)的融匯之中,二者關(guān)于“心性”研究課題間的界限已愈加模糊,理念也漸趨一致,這便是佛道二教漸趨合流所不能否定的一個(gè)結(jié)果,《庭誥》所反映的正是南朝宗教思想進(jìn)化的一個(gè)縮影。
《庭誥》“心性”論與道教思想相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個(gè)重要方面則體現(xiàn)在其養(yǎng)生理念當(dāng)中。顏延之對于魏晉道教中養(yǎng)生理論之理解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庭誥》中曾有論述:
為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煉形為上,崇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為先。煉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糇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卻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煙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偽者為之,則忌災(zāi)祟,課粗愿,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1]57
顏延之此段之描述與魏晉間服食養(yǎng)生的道教修身思路幾乎是完全一致,亦反映出南朝道士群體在修煉思想上基本與魏晉時(shí)代一脈相承。而其所指出的道教修行中的種種誤區(qū)也是一針見血,可以說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南朝道教中的邪術(shù)陋習(xí),這足以證明顏延之對道教思想研究的深入。其實(shí)在《庭誥》中有大量文本都是本之于魏晉以來的道教養(yǎng)生思想來闡釋問題的,這一點(diǎn)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而僅僅以儒家思想的角度去進(jìn)行解讀,這一點(diǎn)的確有失公允。如《庭誥》對“欲”之論述中談道:
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熏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1]55
先秦儒道二家對于“欲”都有論述。《孟子》有云:“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有曰:“見素抱樸,少思寡欲。”但此處顏延之所論之“摒欲”,其出發(fā)點(diǎn)乃是從養(yǎng)生之道來談的。他以為“欲”之為害乃在于其傷性害命而使生命不能長久,這一點(diǎn)與道教神思守一之法高度契合。《老子想爾注》有云:“道教人結(jié)精成神,……人之精氣滿藏中,苦無愛守之者。不肯自然閉心,而揣捝之,即大迷矣。”[2]196可見張道陵認(rèn)為養(yǎng)生之本即在于要“自然閉心”,使心神穩(wěn)定。如此方能不害真性,不傷人和。
提及顏延之的養(yǎng)生思想,一人對其影響極為深遠(yuǎn),此人便是“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顏延之對于“竹林七賢”仰慕久矣,但由于其對山濤、王戎后來的顯貴有所微辭,所以嘗作《五君詠》來詠懷其他五人,在述及嵇康時(shí),顏延之詠曰: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yàn)?zāi)桑抡撝瘛A⑺族昧髯h,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shí)鎩,龍性誰能馴。[10]57
言論間不僅高度贊譽(yù)了嵇康高潔傲岸的品行,更是對其養(yǎng)生修性的豐姿羨慕不已。嵇康撰《養(yǎng)生論》闡述其養(yǎng)生理念,可以說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統(tǒng)養(yǎng)生理論。顏延之對《養(yǎng)生論》必然是研究透澈的,故其在《庭誥》中專有一節(jié)闡釋嵇康的養(yǎng)生思想。其論曰:
中散云,所足在內(nèi),不由于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馀食,非粒實(shí)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fù)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yè)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1]55
顏延之此處所引嵇康之言,其意就在于論證養(yǎng)生是自身為決定因素,而不應(yīng)求之于外。之所以要重視自身之因素,其原因便在于“心性”。嵇康《養(yǎng)生論》有云: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yǎng)身,使形神相親,表里俱濟(jì)也。[10]125
嵇康以為形之長存須以神為根基,神滅則形散,而要使神清氣正,則必先使心性安定。嵇康這一思想正是從道教思想中直接攝取而來。《老子想爾注》有云:
求長生者,不勞精思求財(cái)以養(yǎng)身,不以無功劫君取祿以榮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與俗爭,即為后其身也。而目此得仙壽獲福。[2]168
不以俗務(wù)擾心,而專一求神思守一之道,正是漢魏道教養(yǎng)生之法的精髓。在這一點(diǎn)上,顏延之繼承了嵇康與道教養(yǎng)生思想的內(nèi)核,以求“心性”安定為第一要義,從而奠定了《庭誥》全篇“心性”思想之基調(diào)。
二、“凡有知能,預(yù)有文論”——“心性”引發(fā)的文學(xué)認(rèn)識(shí)論
顏延之闡釋“心性”思想的材料中,很多內(nèi)容都直接或間接地映射出其文學(xué)理念,他非常注重將個(gè)體“心性”涵養(yǎng)與其文學(xué)思想相參照,這一點(diǎn)與先秦道家文藝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與儒家“文以載道”的文藝思想不同,道家對文藝之美是尤為重視的。道家向來不將文學(xué)僅當(dāng)作承載“道”的工具,而是將二者合而為一。無論是老子充滿詩韻的五千言,還是莊子“無端崖之辭”的夢幻之筆,都是將無形大道與瑰麗文辭渾然天成地融合為一體,使讀者在閱讀中自然而然地體道悟道,正如莊子所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顏延之亦是在道家文藝思想的感發(fā)下得出了“心性”與文理如一的重要觀點(diǎn),從而使道理與文辭水乳交融地共承一脈。對于“心性”與文學(xué)之關(guān)系,顏延之在承接先秦道家文藝思想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加以詮釋,得出了許多新的結(jié)論。
談及文學(xué)修為與“心性”之間的聯(lián)系,顏延之在《庭誥》中主要從以下幾個(gè)方面進(jìn)行闡述。
首先,便是提出崇高的人格修養(yǎng)可以使人摒卻塵俗凡事,擁有超脫世外的心境,而這種修為離不開文學(xué)的熏染,即文學(xué)對個(gè)體人格修養(yǎng)有巨大的促進(jìn)作用。正如《庭誥》所言:
貧之為病也,不為形色粗黡,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遠(yuǎn)識(shí)者,何能不移其植。[1]56
貧困對人心智的戕害是十分嚴(yán)重的,古諺有曰:“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但此并不能一概而論,顏延之認(rèn)為采用一定的方法便可在貧困中磨練心智。他所提及的“懷古之志”“琴歌之法”,便是借由文學(xué)的力量來提升自我的“心性”。懷古之歌,其實(shí)在《庭誥》中是有所指明的,其言曰:“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以是后之□詩者,率以歌為名。”[1]57
古典詩歌,尤其是《詩經(jīng)》,對人的影響作用十分巨大。孔子所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正合此意。顏延之沿用了儒家“詩禮修身”的教化傳統(tǒng),尤具有進(jìn)步意義的是強(qiáng)化了“詩”的文學(xué)教育對人“心性”修養(yǎng)的重要作用,這一點(diǎn)十分值得重視。他將“詩”中的懷古之志作為“心性”培養(yǎng)的一種極具效用的手段,發(fā)現(xiàn)了文學(xué)對培養(yǎng)人超然心境的教育意義,這一點(diǎn)難能可貴。
其次,是文學(xué)可以培養(yǎng)“心識(shí)”,即邏輯思辨能力。“心識(shí)”對培養(yǎng)個(gè)體察識(shí)事理有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庭誥》有曰:“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1]55在顏延之看來,“心性”與“理”是相輔相成的存在,二者實(shí)為相互促進(jìn)、同步發(fā)展的一對范疇。人要理解與領(lǐng)悟“理”需以“心性”為依托,而“心性”修養(yǎng)亦離不開“理”的塑造,這也正是其所言“得貴為人,將在含理”的原因。人之所以貴為靈長,就在于“含理”,在于“幸有心靈”。“心”是感知萬物之理的重要器官,“心性”正是在人逐步了悟“理”的過程中日趨完善的。那么,如何去用“心”悟“理”,顏延之認(rèn)為亦應(yīng)通過文學(xué)來實(shí)現(xiàn),這便需要人在哲學(xué)思辨上下一番功夫。
魏晉是一個(gè)玄談昌盛的年代,人們在辯論玄學(xué)問題的過程中培養(yǎng)出嚴(yán)密的邏輯思維能力,使得“心識(shí)”提高到了一個(gè)前所未有的高度。顏延之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diǎn),發(fā)現(xiàn)了辯理活動(dòng)對“心性”修養(yǎng)有著巨大的促進(jìn)作用,唯有氣質(zhì)與睿智兼?zhèn)洌娇沙删透呱械钠沸裕?dāng)然,這也是魏晉士人們的共識(shí)。至于如何提升“心識(shí)”能力,則又回到了顏延之最初之觀點(diǎn):“凡有知能,預(yù)有文論”。[1]55
此言確實(shí)非虛。回顧魏晉以來的眾多清談名家,絕大多數(shù)都有作品存世,他們正是靠著自己的理論著作作為支撐,才能屹立于辯場而不倒,其如王弼之《老子注》《周易略例》,何晏之《論語注》,郭象之《莊子注》,都成為了后世玄談名家的理論學(xué)習(xí)材料。時(shí)至顏延之的南齊之世,雖玄談活動(dòng)早已不復(fù)魏晉之時(shí)興盛,但學(xué)者通過立論以相互辯難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已相當(dāng)濃厚,不僅齊皇曾召集文士辯論過學(xué)術(shù)問題,而且參辯人員的身份多種多樣,僧、道、士子、官員都有立論參與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顏延之本人亦立論數(shù)篇,較具代表性的便是其對“性”是否可滅的問題與眾學(xué)者之間的文章辯論。其先后嘗撰《釋達(dá)性論》《駁何承天達(dá)性論》等文與何承天反復(fù)詰辯,力論“性長存不滅”之觀點(diǎn),這也便是后世聞名的“達(dá)性論”之爭。茲舉此例便可一目了然地發(fā)現(xiàn)顏延之對“文論”的熱忱,這可證明顏延之認(rèn)為文學(xué)可以促進(jìn)“心識(shí)”發(fā)展,提高“心性”修養(yǎng)正是基于自己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所提出的觀點(diǎn)。
再次,文學(xué)有提高人認(rèn)知能力,拓展知識(shí)儲(chǔ)量,提高人綜合修養(yǎng)的功能。若無文學(xué)的熏陶與浸染,人的智慧難有突破與升格,由此而言之,文學(xué)并非僅僅是一種知識(shí)技能,它更是一種手段和方法。習(xí)練文論亦非僅限于提升人的文學(xué)素養(yǎng),更在于其能夠提升人的能力。在顏延之看來,文學(xué)能力的提升向來為青少年所忽視,故其言“此顧少壯之廢,爾其戒之。”文學(xué)素養(yǎng)的形成是一個(gè)厚積薄發(fā)、潛移默化的過程,非一朝一夕所習(xí)得,即便是要取得“妙悟”,也需要具備相當(dāng)深厚的文學(xué)功底及苦思冥想后方有所獲,由此而言之,顏延之認(rèn)為“心性”修養(yǎng)與文學(xué)修養(yǎng)乃是相輔相成的,兩者相互促進(jìn),共同推動(dòng)個(gè)人品格修為的提高。
文學(xué)能力的培養(yǎng)在顏延之看來也有著一定的方法,在《庭誥》中他就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交流”的重要作用。其言曰:“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歸,前輩所與,焉得以成名乎?”[1]55這種交流有著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書籍的廣博搜覽,可謂之曰“跨時(shí)空知識(shí)的交流”,即“校之群言”。不僅限于當(dāng)世之人,更要在群書中與諸子百家、前圣往哲對話,在典章史料中校理析辯,方此時(shí)才能打開胸襟,擴(kuò)展見識(shí),提升自我的文學(xué)思辨能力。另一方面,則是人與人之間的學(xué)術(shù)交流,當(dāng)然,也未必局限在學(xué)術(shù)上。顏延之反對一個(gè)人的獨(dú)思異想,“獨(dú)學(xué)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他對儒家這一學(xué)習(xí)思想的體悟十分透徹,《庭誥》言曰:“若呻吟於墻室之內(nèi),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1]55顏延之批判了封閉式的文學(xué)思考方式,并指出文學(xué)交流不應(yīng)拘泥于朋輩小團(tuán)體之間,而應(yīng)盡可能拓展自己的文學(xué)圈子,與優(yōu)秀的學(xué)者及文人產(chǎn)生思想碰撞。唯有如此才能對社會(huì)發(fā)展與文學(xué)思潮有一個(gè)全面的認(rèn)識(shí),充分提高自己的文藝思維能力與文學(xué)認(rèn)識(shí)水平。顏延之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了交流群體的重要性。顏氏極為重視人的周邊環(huán)境,“芝蘭之室,干魚之廝”便是其至理名言。不良的交流活動(dòng)只會(huì)損害人的思想,雖然魏晉以清談馳名,但未必善言談?wù)咭欢ㄓ袠O高的思想造詣,倘若交流對象不當(dāng),其弊端絲毫不亞于獨(dú)唔一室之內(nèi)。
三、“心照若鏡”——以“心性”為旨的文學(xué)批評論
自魏晉以來,中土文士便大量借鑒宗教術(shù)語來進(jìn)行文學(xué)評論活動(dòng),其中尤以佛教術(shù)語居多,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便引入大量佛教概念來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顏延之在《庭誥》中亦采用此種文學(xué)品評方式,借佛教與道教理念來闡釋文學(xué)問題。而在其文學(xué)批評理論中,“心照”這一概念的提出尤為引人注目。《庭誥》有云:
以為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恍惚,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順為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眚其弊,是未加心照耳。[1]56
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顏延之認(rèn)為僅僅憑借感官認(rèn)知世界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必須要加以“心照”方可了解事物的真諦。“照”字經(jīng)常為佛學(xué)典籍所用,指對世界的圓滿無礙的透徹認(rèn)識(shí),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中便將其引入文學(xué)品評中,其言曰:“欲求博觀,必先圓照。”[11]218顏延之在人的文學(xué)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中,亦高度肯定了“照”的必要性,將“心照”作為人洞悉萬物,深察文理的第一要義。
心照之法,概括而言之,便是“以心為鏡”,藉個(gè)體“心性”為本來分析文學(xué)作品。“以心為鏡”要求個(gè)體能夠達(dá)到一種絕對無染,透澈澄明的境界,這與劉勰所提出的“虛靜”的文學(xué)概念乍看之下十分類似,但差異卻是十分明顯的。這主要在于“虛靜”是個(gè)體在鑒賞與創(chuàng)作活動(dòng)的心境體驗(yàn),而“心照”則要求個(gè)體在身心修養(yǎng)中要始終處于清凈無染的狀態(tài)。顏延之認(rèn)為唯有將內(nèi)心純凈保持一種恒長狀態(tài),方可達(dá)到“心照如鏡”的藝術(shù)審美效果。上文所提及的“用心若鏡”正是“心照”之法的直接理論來源。莊子以為,修心達(dá)到此境,已至圣人之位階。這足以見“心鏡”修為之難。如果說“虛靜”是個(gè)體心靈澄澈的基本前提與要素,那么“心照”便是完成心性升格的必由之路。顏延之認(rèn)為洞察物理之極才可達(dá)到的“體神不疑”,唯有通過“心照”方能完成,由此可見,在其眼中“心照”儼然已成為了格物致知的最終奧義。
“心照”盡管是一個(gè)充滿佛學(xué)氣息的概念,但正如前文所述,南朝般若學(xué)的產(chǎn)生乃是佛教借道家思想嫁接所成的產(chǎn)物,其“心鏡”之論更是直接藉《莊子》諸論脫胎換骨而來,所以在《庭誥》中“心照”這一概念的道家思想色彩依然是十分濃厚的。先于《庭誥》的《黃庭內(nèi)景經(jīng)》中,對于自身心靈的觀照之法便已十分成熟,而研析《庭誥》“心性”之說,亦可發(fā)現(xiàn)其對魏晉以來道教修行之中的內(nèi)觀之法有諸多借鑒之處。由此可言,顏延之“心照”的品評概念對道教文藝觀念多有吸收。
顏延之首先確立了文學(xué)評論中的基本尺度為鑒賞者的“自性”,或謂之曰“本心”。《庭誥》有云:
且以己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斡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jì)而合流貫,人靈茂也。[1]56
“天”“地”“人”為道教中所謂的“三才”,當(dāng)人具備絕對“自性”,得萬物之道于心時(shí)便可遍悉萬理。顏延之充分肯定了人在文學(xué)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中的主觀能動(dòng)作用,認(rèn)為當(dāng)人具備了完善的心識(shí)之后,便可使本性澄明無礙,從而能夠在分析作品時(shí)做到公正客觀。顏延之秉持著道家一貫的主張,即認(rèn)為人生來本性皆是圓滿的,并無等級差別。《老子》以為,人從出生之時(shí)起便已具有“精氣”“元?dú)狻保呛筇斓拇輾埐攀沟萌瞬粩鄦适Ь允П拘浴6@一切的罪魁禍?zhǔn)祝闶菈m俗中的積習(xí)陋弊。顏延之在《庭誥》中反復(fù)論述這個(gè)問題,他以貧富差距為例,指出貧窮之所以令人“神心沮喪”,便在于“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的人在世間的境遇本有萬殊,故雖初始性情相同,而后天差異極大。倘若有潔身自好之人,心性會(huì)被打磨得愈加璀璨。“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shí)道愈堅(jiān)”。而更多普通人則會(huì)因困頓而生怨恨心、嫉妒心、分別心,漸漸丟失本心,喪失“性靈”。
顏延之談及塵俗積邪陋弊對個(gè)體污染最為嚴(yán)重的方面便在其心識(shí),其言曰:“習(xí)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1]55塵俗陋習(xí)在改變個(gè)體性情的同時(shí),也在改變其思維方式及心理狀態(tài),使得人心性昏沉,神思迷亂,而至此人已然連正常的是非分辨能力都不具備,又談何“用心若鏡”地去品鑒文學(xué)作品?正因如此,滌除思想雜質(zhì),打磨“心鏡”,便成為了顏延之“心鏡”文學(xué)批判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圍繞這一問題,顏延之從以下幾方面予以闡述。
品評時(shí)“用心若鏡”,首要方面便是要將自我心性“反本”。《庭誥》有曰:“世務(wù)雖移,前休未遠(yuǎn),人之適主,吾將反本。”[1]55“反本”在道家思想中是一個(gè)極為重要且內(nèi)涵豐富的概念,《文子·自然》有曰:“立天下之道,執(zhí)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yuǎn)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jīng)。”[12]176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代,佛教為闡釋心學(xué)義理,遂借鑒了“反本”概念,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嘗有論述:“蓋佛性本有,反本而得。然則見性成佛者,即本性之自然顯發(fā)也。”[13]87顏延之論述人之反本,首先需摒棄外在干擾,從自身著手。他在《庭誥》中便藉嵇康“所足在內(nèi),不由于外”之語言明此意。雖然此句是言養(yǎng)生之道,但這種不依靠外物而憑借自身先天真性的養(yǎng)生思想,同樣與顏延之“反本”的文藝觀相契合。“所足在內(nèi),不由于外”的思想不僅闡明了文藝必須由自身(鑒賞者)態(tài)度出發(fā),發(fā)乎性靈方可得文章真髓,同時(shí)亦強(qiáng)調(diào)唯有“滌除玄覽”,清空思想雜質(zhì),方可正本清源,從正確的觀點(diǎn)評點(diǎn)作品,得出客觀公允的結(jié)論。
顏延之所闡述的“反本”理念,重在研析心性復(fù)歸本源的方法與途徑,其對“本”的認(rèn)知,從《庭誥》此段文本中亦可察驗(yàn):
夫內(nèi)居德本,外夷民譽(yù),……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1]55
研讀此處文本并不難發(fā)現(xiàn),顏延之在“人之本”的理論認(rèn)知上與老子的“道德”思想一脈相承,其倡導(dǎo)“泰淵入道,天人合一”的看法也是魏晉道教人士的思想共識(shí)。而如何使人返本歸元,自性完備,《老子》中亦有論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179顏延之對老子的這一論點(diǎn)高度贊同,其《庭誥》有曰:“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shù)紀(jì)之壽,常以金石為量”。[1]56即以師法天地為治心之本務(wù),而回歸至原點(diǎn),最終追溯為自然之道。
漢代張道陵撰《老子想爾注》,便將“自然”與“道”訓(xùn)為一體,其文曰:“自然,道也。樂清凈,希言入清靜,合自然,可久也”。[2]197可見若要得“反本”之法,必修清靜無為之道,唯靜以修身,方能使心復(fù)歸本性之源。所以在顏延之看來,在文學(xué)鑒賞活動(dòng)中,不僅需要“虛靜”的平和心態(tài),更需要一顆清靜無為的心靈為先決條件;反而言之,倘若心性不正,充滿邪思戾氣,那么便會(huì)對作品的情思理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想要達(dá)到“虛靜”的冥想心態(tài)更是無從談起。綜上所述,顏延之“反本”的觀點(diǎn)乃是由道家的“清靜無為”的修持法引入文學(xué)批評活動(dòng)所得出的成果。
顏延之在研析“心照若鏡”的文學(xué)批評方法時(shí),不僅通過“反本”之法來打磨心性,使之澄明無垢,更是進(jìn)一步提出“德貴有恒,心性勿移”的主張和理念來使“心鏡”長亮不竭。《庭誥》有云:
人以有惜為質(zhì),非假嚴(yán)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wù)謝則心移,斯不恒矣。[1]55
顏延之此段論述闡述了其“有恒為德”的文學(xué)批評理念,即在批評活動(dòng)中應(yīng)建立一套自己獨(dú)立的原則與方法,并將其貫徹始終,絕不因外界環(huán)境與風(fēng)氣的影響而輕易變化。顏延之在下文中舉出文學(xué)批評活動(dòng)中的兩種極端思想來比較論證。其言曰:
或見人休事,則勤蘄結(jié)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huì)以從風(fēng),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yù),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xùn),藉人成立,與人馀論,依人揚(yáng)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yuǎn),忌聞?dòng)佰E,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己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shí)……[1]55
在這兩種極端思想中,一種是過分以自我為中心,刻意打壓和詆毀他人作品,故步自封,無法吸收外界的建議和理念。而另一種則恰恰相反,是毫無個(gè)人主見地人云亦云,只知亦步亦趨地追隨潮流,無條件地接受他人思想觀點(diǎn)。這兩種思想在文學(xué)批評活動(dòng)中是萬萬不可取的,是批評主體沒有用辯證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所形成的錯(cuò)誤認(rèn)識(shí)。
那么,樹立一個(gè)正確的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成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顏延之認(rèn)為,批評主體建立一套基于自我認(rèn)識(shí)的正確文藝觀是十分必要的。通過這一基準(zhǔn),批評者能夠在堅(jiān)持自我主觀能動(dòng)性的基礎(chǔ)上,不斷吸收外界先進(jìn)的文藝批評理念來填充自己,進(jìn)而形成一套自己的文藝批評思想體系。在批評者自己的文藝批評思想建立之后,就猶如形成了一面鏡子,將客觀世界的形象投射成為自我的認(rèn)知概念。根據(jù)顏延之的觀點(diǎn),在以清靜無為作為修持方法之后,個(gè)體“心性”可擺脫塵俗陋習(xí)的熏染,獲得澄明圓滿的心靈境界,而這種心境正是形成自我獨(dú)立文藝思想的關(guān)鍵一步。其言曰:
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jiān)。茍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念,必存從理之心。[1]57
顏延之此處所云之得道者常樂,便在于“心性”堅(jiān)如磐石,可不受外物役使而“自我喪失”。這種自我覺悟乃是在“丹石之性”的基礎(chǔ)上建立的。由此可言,倘若心性蒙蔽,那么建立正確的自我認(rèn)識(shí),形成自己獨(dú)立的文學(xué)思想體系就無從談起。
批評個(gè)體除了須以“心性”為基礎(chǔ)建立自身的文學(xué)認(rèn)知外,廣泛吸引外部的優(yōu)秀文學(xué)思想成果也是十分必要的。作為補(bǔ)充,顏延之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學(xué)習(xí)方法。《庭誥》有曰:“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1]57此言涵蓋了兩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即廣泛閱讀與提煉精粹。此二者并無先后之別,是閱讀活動(dòng)中相輔相成的兩個(gè)方面。
同此相似的論述在劉勰《文心雕龍·知音》篇中亦有之:“是以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shí)器。”[11]219劉勰在此以比喻的手法闡釋了文學(xué)批評活動(dòng)中廣泛閱讀、大量訓(xùn)練所形成的經(jīng)驗(yàn)性認(rèn)知。顏延之則是將此理念抽象為批評理論。結(jié)合之前關(guān)于“心性”的分析可以推斷,顏氏所謂“博而知要”中的“要”,就是個(gè)體在鑒賞活動(dòng)中,通過主觀“心性”鑒照后所提煉出的理論觀點(diǎn)。這些文藝觀點(diǎn),從某種意義上講已從原著中抽離,經(jīng)主體改造成為了自己文藝?yán)砟畹囊徊糠帧9暑佈又^之“萬流可一”,當(dāng)書籍理論經(jīng)自己吸收理解后,所有自己曾吸收的精要都已轉(zhuǎn)化為自己文藝?yán)碚摰挠袡C(jī)組成部分,就有了連貫性與系統(tǒng)性。當(dāng)自我澄明“心性”加之后來萃取的文藝精華融會(huì)貫通,合而為一后,主體的文學(xué)批評思想即得以形成。
“貴德有恒,心性勿移”的文學(xué)批評思想的另一重要內(nèi)涵則是,應(yīng)堅(jiān)持貫徹自己的文學(xué)批評觀念,不應(yīng)受外界潮流的影響,扭曲乃至背離自我的文學(xué)批評初心。章學(xué)誠在《文史通義》中有一個(gè)十分重要的思想原則:“修辭立其誠。”此“誠”的一個(gè)核心要素便是要敢于在文學(xué)作品中展示自我的真實(shí)文學(xué)思想,這一點(diǎn)在文學(xué)批評領(lǐng)域亦是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要素。評論主體在以“心性”為鏡,建立自己的評論思想之后,倘若不敢堅(jiān)持自己的正確原則,為外界影響所左右,那么一切便都是徒勞的。顏延之在《庭誥》中特別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批評的理論自信,是由歷史經(jīng)驗(yàn)中所總結(jié)出的客觀真理性認(rèn)識(shí)。正確的理念盡管具備極高的思想價(jià)值,但要為人所理解與接收卻是一個(gè)復(fù)雜和艱難的過程。老子對圣人“被褐而懷玉”的形象化比喻,極為精深地言明了思想傳播與接受過程的艱辛。而愈是自我獨(dú)立論斷與社會(huì)主觀思想相左,就愈是難以在眾人庸俗的觀念中立足。那么,是否敢于堅(jiān)持自己的真理性認(rèn)識(shí),變成了文學(xué)批評思想傳遞過程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卷首便發(fā)論曰:“音實(shí)難知,知實(shí)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11]218
劉勰點(diǎn)明了文藝批評過程中主體認(rèn)知與社會(huì)認(rèn)知的矛盾,“知音難覓”亦成為了后世文論學(xué)者的普遍共識(shí)。而解決批評主體認(rèn)知與社會(huì)思想潮流矛盾的關(guān)鍵,一方面是要努力完善文學(xué)批評的思想方法,將謬誤控制在真理的范疇內(nèi);另一方面則要求文學(xué)批評者要敢于堅(jiān)持自己的理念和推理判斷,不違背自己文學(xué)思想的初心。只要不違背客觀真理,摻雜個(gè)人功利性目的,那么批評主體的觀點(diǎn)認(rèn)識(shí)必將得到歷史的公允評判。
四、“本之自性”的“心性”文學(xué)創(chuàng)作論
以“心性”思想為本,顏延之在《庭誥》中亦構(gòu)筑了其獨(dú)具一格的“心性”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論。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論方面,顏延之從創(chuàng)作者的“自性”觀念入手,著重分析了個(gè)體情性與作品風(fēng)格的關(guān)系,提出了“本之自性”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念。
誠如前文論述,“心”作為人感知外物的重要器官,是情感產(chǎn)生與性情所在的靈臺(tái),故與文學(xué)抒寫有著不可割裂的聯(lián)系。研析顏延之《庭誥》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論,首先要剖析的便是“情”與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從文學(xué)發(fā)展的大趨勢上看,由兩漢至魏晉,人們對作品評判的標(biāo)準(zhǔn)產(chǎn)生了由“志”向“情”的過渡發(fā)展,尤其是對詩學(xué)而言。在漢代《詩大序》中,漢儒便提出了“詩言志”的主張,旗幟鮮明地指出詩之精髓乃在作者合乎儒家倫理的志向表達(dá),從而將詩歌乃至于文學(xué)都變成了教化的工具與儒學(xué)的附庸。而至魏晉之世,隨著儒家正統(tǒng)思想的土崩瓦解,士人們紛紛投入道家思想的懷抱,尤其是在文學(xué)中更多地去抒心寫性,直抒胸臆,重返向道家返璞歸真的文學(xué)追求。在陸機(jī)的《文賦》中,其已提出“詩言情而綺迷,賦體物而瀏亮”。至此“詩言情”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張便正式確立。盡管在南朝文壇中,儒道文學(xué)思想一直處于交織狀態(tài),但通過對《庭誥》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顏延之對詩以言情主張的贊同。如其言曰:
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fēng)謠以達(dá)民志,《詩》為之祖,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zhuǎn)制衰王,微辭豈旨。[1]57
顏延之首先肯定了詩歌之本為民謠歌曲,是普通百姓最為真摯的情感抒發(fā)。其實(shí)這一點(diǎn)在《詩大序》中也有闡述,但毛詩說肯定的“情”,乃是合乎儒家思想的禮教規(guī)范,而不是“情”本初所指的真性情。這種解釋不僅使得“情”的內(nèi)涵變得十分狹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曲解了“情”的本義,從而使“情”與真性相背離,進(jìn)而與儒教倫理綱常混為一談。
顏延之指出,情志之所以在漢儒的訓(xùn)詁下大變味道,乃是由其“取其正言晦義”以褒貶成辭造成的。顏延之在分析李陵詩后,雖認(rèn)為其為假托之作,但因其悲愴的書寫與真摯的情感抒發(fā),所以可以無視其作者與時(shí)代的錯(cuò)誤,當(dāng)作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來欣賞。故其在《庭誥》中提出:“逮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寫,有足悲者。”[1]57從顏延之對《詩經(jīng)》的分析與“李陵詩”的評判上可以推斷,他所認(rèn)可的情志乃與儒家理論教化思想有別,而更貼近于道家真性的觀念。
可以發(fā)現(xiàn),顏延之“心性”文學(xué)創(chuàng)作思想的核心便是創(chuàng)作者應(yīng)“本之自性”,以自身真實(shí)情感出發(fā)而進(jìn)行文學(xué)抒寫。這一點(diǎn)也成為了后世道教文學(xu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道教詩學(xué)思想作品《二十四詩品》中便有“性情”為本的創(chuàng)作思想。其言曰:
性情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15]65
惟性所宅,真取不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15]176
無論詩歌還是文章,唯有寄托了真性情才能達(dá)到渾然天成的藝術(shù)境界,這其中所蘊(yùn)含的是作者情感的自然狀態(tài),擺脫了一切外物羈絆,這是道教文學(xué)思想所秉承的至臻追求。在確定了“本之自性”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基調(diào)后,顏延之深入探索了性情與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提出了如下觀點(diǎn):
(一)息欲明性——“欲”的克制與恬淡文風(fēng)
情由心中所發(fā),由外物所感而產(chǎn)生喜怒哀樂,但倘若不加以克制,便會(huì)由情中生欲而破壞人情感系統(tǒng)的平衡。《庭誥》有曰:“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熏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1]55當(dāng)個(gè)體情感涌動(dòng)超過一定限度,“欲”便會(huì)從中產(chǎn)生并左右人的心識(shí),使人神思迷亂,心性有礙。因此“欲”的產(chǎn)生對人的心性修養(yǎng)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是十分不利的。那么,適時(shí)的克制情欲就十分必要了。對欲望的克制早在老子時(shí)代便為重要的探討課題,《老子》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老子想爾注》釋曰:
不欲視之,比如不見,忽令心動(dòng)。若動(dòng)自誡,道去復(fù)還,心亂遂之,道去之矣。[2]47
張道陵認(rèn)為心不動(dòng)則萬物皆不動(dòng),萬物不動(dòng)則欲當(dāng)自清,心能自定。顏延之撰《庭誥》之主旨便在于以心性修養(yǎng)勸誡子孫守道惜福,故而對制欲息情之道十分重視。但與張道陵不同的是,他認(rèn)為欲乃是由人之性情所發(fā)之產(chǎn)物,不可與人的性情簡單地二元對立,而應(yīng)看到其關(guān)聯(lián)性。顏延之舉出了“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xì)埞稹盵1]55的例子以說明“欲”與“本性”的關(guān)系。“欲”發(fā)之于性,兩者本為雙生異體,所以簡單地摒棄情欲反而會(huì)走向另一個(gè)極端,即拋棄個(gè)體感情因素而使精神麻木,喪失了主觀能動(dòng)性。反映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則是會(huì)使作品感情枯澀,失去感染讀者的活力,這樣無疑走上了與儒家倫理教條思想一樣封閉僵化的老路,是十分不可取的。
正是基于此種認(rèn)識(shí),顏延之在《老子想爾注》的息欲明性思想上進(jìn)行了發(fā)展。《老子想爾注》有云:
情欲思慮,怒喜惡事;道不所欲,心欲規(guī)之,便即制止解散,令如冰見曰散汋。[2]137
顏延之在《庭浩》中則作出不同的論述: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shí)。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則為美矣。[1]56
雖然二者最終都回歸到以道制妄欲,心定情性的主旨中去,但顏延之卻將情欲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以中和之法來使情歸于平靜,從而使欲望自行消解,在欲望得以克制之后,個(gè)體心性便自然會(huì)趨于純粹,而達(dá)到“恬淡寬愉”的心境。湯用彤在論述情與欲之關(guān)系時(shí),也提出了調(diào)和二者的觀點(diǎn):
情制性則人為情之奴隸而放其心,日流于邪僻。性制情,則感物而動(dòng),動(dòng)不違禮,故行為一歸于正,《易?乾卦》之言“利貞者性情也”。[16]78
在顏延之看來,“恬淡寬愉”乃是個(gè)體擺脫欲望枷鎖后獲得的絕佳內(nèi)心體驗(yàn),此心境反映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則內(nèi)化為作品寄旨遙深,情味難求的風(fēng)格特征。作品的這種風(fēng)味是超越言辭修飾與形象描寫的更高層次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特征,往往需要鑒賞者在形成對作品的整體性認(rèn)識(shí)后方能逐漸領(lǐng)悟,作品語言往往是不能直接傳達(dá)的,正所謂意在言外。魏晉詩作中常見此種意遠(yuǎn)情深、高曠超然的作品,這些作品通常便有著“言不盡意”的結(jié)尾。如嵇康“嘉彼釣翁,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17]60;阮籍“求仁自得仁,豈復(fù)嘆咨嗟”[17]65“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16]79“烈烈褒敗辭,老氏用長嘆”[17]81;陶淵明“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17]258;謝靈運(yùn)“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17]149。其實(shí)單以作品文意去理解,很難去把握其主旨,辟如謝靈運(yùn)此詩通篇繪景,并未言其道如何,阮籍詠懷詩句也并未明言其志,詩評家故有“嵇志清峻,阮旨遙深”[18]156之?dāng)嗾Z。
對魏晉這些帶有道家思想色彩作品理解時(shí),需著重把握的乃是其體道順物、神通自然的心性體驗(yàn),而不能僅聚焦于其內(nèi)心之痛苦。如阮籍詠懷諸作,很多作品都有一個(gè)“內(nèi)心痛苦——自我斗爭——超脫升華”的情感發(fā)展過程,從心理學(xué)來講,乃是一個(gè)自我向本我、超我升華的經(jīng)歷體驗(yàn)。作者在現(xiàn)實(shí)中苦悶、壓抑,借道家自然清靜之道修煉心性,終至達(dá)到“天心順物”的恬淡寬愉境界,而使自我在心性上涅槃新生,重返自由。
鐘嶸《詩品》嘗言顏延之評阮籍詩作時(shí)“怯言其志”[18]190。顏氏不言阮詩之志并非由于其不理解詩作,乃在于顏氏認(rèn)為阮籍作為體道者,其創(chuàng)作早已超脫于塵俗痛苦之外,其詩作中心與天通的恬漠詩意已非人言可描述。《庭誥》有曰:“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1]55此段文字正述此意。當(dāng)個(gè)體以清虛自然之道煉養(yǎng)心性,則其心對外界必定抱有寬容平和的態(tài)度,這種平靜安順的心態(tài)落筆則化為愉淡寬愉的文學(xué)情感。道教于情倡導(dǎo)“至誠”,于自然之認(rèn)識(shí)倡導(dǎo)“至真”,恬淡的文學(xué)境界正是“至誠”“至真”的內(nèi)外整合,頗如內(nèi)心波瀾皆無,鏡照如水,則所映照之世界也必澄明無偽,方此時(shí),心境與自然方可若合一契。
顏延之以辯證的眼光來分析情欲的問題,既正視了文學(xué)書寫中“情”的重要意義,又在對欲望的處理上采取了疏導(dǎo)中和的方法,這是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論的一大進(jìn)步。“制情息欲”并非是要泯滅人的感情,而是要用心性制情欲,不使喜怒哀樂凌駕于人的理性之上。魏晉南北朝玄學(xué)研究中的一個(gè)核心問題,便是圣人“有情”“無情”的論爭,王弼秉持著“圣人有情論”的觀點(diǎn)對人的情感問題作出了精妙論述: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yīng)物。然則圣人之情,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fù)應(yīng)物,失之多矣。[19]450
從《庭誥》的文本中不難發(fā)現(xiàn),顏延之對王弼的思想觀點(diǎn)高度贊同,其對個(gè)體認(rèn)知的最高評判也在于其是否能夠“體神”,這亦是對王弼“圣人有情論”的一種闡述。故顏延之在肯定“情”的立場上,提出以性制欲,而不是扼殺個(gè)體情感,正是與王弼的觀點(diǎn)一脈相承。
(二)“大道至簡”的文學(xué)風(fēng)格追求
道家樸拙至簡的文學(xué)風(fēng)格淵源久遠(yuǎn),早在先秦時(shí)代,老子就對“大道至簡”的命題多次申述,如《老子》有曰:“多言數(shù)窮,不如守中。”[13]100“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辯者不善,善者不辯。”[13]149這一文學(xué)風(fēng)格為道教所繼承,并不斷對其理論予以發(fā)展。如南宋郝大通便對道教樸拙文風(fēng)作出論述:
夫至人達(dá)觀,物無不可,故辭旨所發(fā),務(wù)以明理為宗。非必駢四驪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yè)文者,以聲律意度相夸耳。在禪學(xué)則曰:粗言及細(xì)語,皆成第一義。在孔門則曰:辭達(dá)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為得之矣。學(xué)者不志於道,而惟華采是求,豈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道乎。[20]867
郝大通以三教圓融、萬法一同的高度將簡樸文風(fēng)推上了至高的位置,在此文學(xué)立場上,道教文學(xué)觀念幾乎未曾發(fā)生過改變。在道教思想意蘊(yùn)深厚的《庭誥》中,大道至簡的文學(xué)觀念體現(xiàn)得亦淋漓盡致。雖然《庭誥》的簡樸文學(xué)風(fēng)格思想只是道教文學(xué)思想史上微小的一環(huán),但依然有必要對其思想的生成與發(fā)展及對前代文學(xué)思想的接受過程展開分析。
南朝文風(fēng)以繁縟、綺麗華美著稱,而其浮華空洞的缺點(diǎn)也常為人所詬病。延顏之自己的創(chuàng)作亦未能免俗,但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思想是否與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相一致,則值得探討。《詩品》嘗云: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cuò)彩鏤金。顏終身病之。[18]120
顏延之對湯惠休的評價(jià)終生耿耿于懷,可見對自身文學(xué)作品風(fēng)格并不認(rèn)同,及至反感。這種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與文學(xué)思想的巨大差異,側(cè)面反映出了時(shí)代大環(huán)境所造就的文學(xué)潮流與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之間的矛盾。對于道教文學(xué)思想對南朝文壇的影響程度這一問題,還需要更多地研究探討,但至少在顏延之個(gè)例上來看,其作品難以直觀地傳達(dá)其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思想的認(rèn)知,故借助其思想文獻(xiàn)來進(jìn)行闡釋便十分必要,《庭誥》的價(jià)值就在此處凸顯。
通過對《庭誥》的文本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顏延之極為反對浮華思想,無論是在生活起居、文辭字令、思想修為上,他都極力主張“至簡”。如其有曰:“浮華怪飾,滅質(zhì)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dòng)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yuǎn)識(shí)奪,難用近欲從。”[1]56在顏延之看來,物欲對人心性的破壞作用是巨大的,它會(huì)致人品行墮落,道德淪喪。生活的奢華導(dǎo)致思想精神極度空虛,從而追求種種虛名,致使真性污穢不堪。從顏延之心性文學(xué)思想上來看,心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源頭,源不凈則流必污,不健康文風(fēng)的產(chǎn)生是必然結(jié)果。《庭誥》有云:“及詭者為之,則藉發(fā)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1]56作家一旦為外界名利虛榮所束縛,則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必然失去真率之性,淪為謀取利益的工具,這種作品的危害性極大。
漢代道教曾對華美空洞的文風(fēng)展開了嚴(yán)厲抨擊,《老子想爾注》有云:“道絕不行,耶文滋起,貨賂為生,民竟貪學(xué)之。身隨危傾,當(dāng)禁之。勿知耶文,勿貪寶貨,國則易治。”[2]230可見就道教文藝思想來看,浮華糜麗的作品與聲色犬馬之欲望享受一樣背德害道,不僅會(huì)使人心性迷亂,而且當(dāng)這種不良之風(fēng)形成之后,會(huì)加速社會(huì)的腐化墮落速度,導(dǎo)致國家的衰亡,這與亡國之音并無二致。
縱觀顏延之所生活的南朝時(shí)代,綺麗之風(fēng)與奢靡之風(fēng)一直充斥文壇,文人競相習(xí)仿,甚至形成了專門描述女性與艷情的宮體詩歌。這從一個(gè)側(cè)面表現(xiàn)出社會(huì)的畸形病態(tài),是人道德感與責(zé)任感日漸缺失的一個(gè)縮影。文學(xué)反映出社會(huì)意識(shí)演進(jìn)流變的過程,而這一趨勢的背后正是人們心靈的真實(shí)狀況。道教文學(xué)思想中所倡導(dǎo)的以簡為美,正是在愈演愈烈的繁縟綺麗文風(fēng)下的一股反抗力量,但這一力量終究是過于孱弱,文士在吸收道教文藝中的超脫與逍遙后,始終對其率真的文藝訴求置若罔聞。顏延之雖然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其創(chuàng)作中卻未能有意識(shí)地加以實(shí)踐,以至出現(xiàn)了作品風(fēng)格與思想理念相左的情況。如果不能對其文學(xué)思想全方位加以剖析,則很容易出現(xiàn)認(rèn)識(shí)誤區(qū),這是應(yīng)為文學(xué)思想研究者所注意的情況。
顏延之在《庭誥》中反復(fù)提到“簡”的概念,其概念并非僅指簡其嗜欲,更關(guān)鍵的是要使心性歸真,正謂之“簡以養(yǎng)德”。《庭誥》有云:
豈若拒不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yuǎn)其意,使言必諍厭,賓友清耳,笑不傾耳,左右悅目。[1]56
此段文字所謂之“簡”,正是講清靜養(yǎng)心,究其旨意,最終回歸于“心性”的范疇。顏延之對文風(fēng)尚簡的創(chuàng)作理論的創(chuàng)見在于,其對文風(fēng)誕生源頭開始展開探究,所謂正本清源,方可使文從字順。即創(chuàng)作者心存正性,則作品風(fēng)格亦會(huì)在潛移默化中產(chǎn)生變化。《庭誥》曰:
酒酌之設(shè),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fā),其唯善戒乎。聲樂之會(huì),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jié)其流,意可為和中矣。[1]56
此段文字所論雖為酒酌之事,但其意理極深,可通文道。酒色之欲,歷來為道教攝生者所禁,原因就在于其傷性者甚,但顏延之提出“正性”可使個(gè)體免于耽樂,正與佛教“紅塵之中悟菩提”意同。反映在文藝思想中則是當(dāng)創(chuàng)作者心性簡樸歸真之時(shí),其文字亦將歸于拙樸,而心性樸素則文風(fēng)自歸于簡。《老子想爾注》曰:“樸,道本氣也。人行道歸樸,與道合。”[2]98道教所云之道與儒家之道有所不同,它不僅體現(xiàn)在倫理人情,更體現(xiàn)在萬物運(yùn)行之規(guī)律方面,道教之所以認(rèn)為樸與道合,就在于“樸”是養(yǎng)性全身的根本方法。那么文風(fēng)之中的“樸”,便是摒棄淫思奇巧,回歸于真實(shí)的藝術(shù)境界。文學(xué)之“樸”,不是僅僅精簡文辭所能達(dá)到的,它需要?jiǎng)?chuàng)作者的心性修為也要?dú)w于臻真之境。《庭誥》有云: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生矣。建言所黜,儒道眾智,發(fā)論是除。[1]56
此處所言之“氣”,乃是道教與儒家所謂的先天元?dú)狻5臀膶W(xué)而言,則是指的“文氣”。“文氣”是相當(dāng)早的一個(gè)文學(xué)概念,儒道都對其有所闡釋。《禮記·樂記》有云:“詩、樂、舞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21]432道教《太平經(jīng)》亦有云:“天上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氣出助之;……行文者,天與文氣助之;行辯者,亦辯氣助之;……”[8]238
可知顏延之所謂之“儒道眾智”,正是文道與心志關(guān)系的闡釋。而行文之氣,毫無疑問也正是由心之所發(fā),故簡明心性,正是扭轉(zhuǎn)文氣的最根本途徑。而“大道至簡”的文學(xué)風(fēng)格,也是與心性相統(tǒng)一的整體性概念,當(dāng)創(chuàng)作者以“樸”為心性之統(tǒng)攝時(shí),文氣也自當(dāng)向“情深而文明”的方向去發(fā)展。
[1] 沈約.宋書:顏延之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 饒宗頤,譯注.老子想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卿希泰.中國道教思想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張融.門論:大正藏第5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 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卷下[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6] 孫通海,譯注.莊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8.
[7] 僧肇.般若無知論:大正藏第4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 王明,譯注.太平經(jīng)合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0.
[9] 佚名.西升經(jīng):道藏第11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0] 戴明揚(yáng),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11] 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2] 李定生,徐慧君,譯注.文子校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5.
[14] 饒尚寬,譯注.老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5]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16] 湯用彤.魏晉玄學(xué)論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7]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8] 曹旭,集注.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9] 裴松之,校注.三國志注:魏志鐘會(huì)傳[M].長沙:岳麓書社,2017.
[20] 郝大通.太古集:序道藏第25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1] 王文錦,譯注.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6.
Yan Yanzhi'sand Taoist Literary Thought in Han and Wei Dynasty:With Literary Thought of Mind as the Core
XU Dongzhe1, JIANG Zhenhua2
( 1.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Ji’ning 272067, Shandong, 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
The view tha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re the source of Yan Yanzhi's thought is the consensus of scholars,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on Yan Yanzhi's thought has been ignored. A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fluence theory of Confucianism, this essay analyzes Yan Yanzhi's literary concept from Tao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 Taoist literaturein the late Han Dynasty, this essay proves that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mind inis formed by Yan Yanzhi when he inherits and develops of the Taoist literary thought of Han and Wei. His literary epistemology that unifies the cultivation of mind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the literary creation theory of "self-nature" and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heart shines like a mirror". He advocates that the stylistic is indifferent, concise and profound. They form a unique literary theory system based on Han and Wei Taoism.
literary thought of mind, metaphysics, prajna, Taoism
I206.2
A
1673-9639 (2020) 05-0023-14
2020-07-0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歷代道經(jīng)集部集成編纂與研究(17ZDA248)”。
徐東哲(1990-),男,山東濟(jì)寧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
蔣振華(1964-),男,湖南新邵人,文學(xué)博士,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xué)思想。
(責(zé)任編輯 郭玲珍)(責(zé)任校對 肖 峰)(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