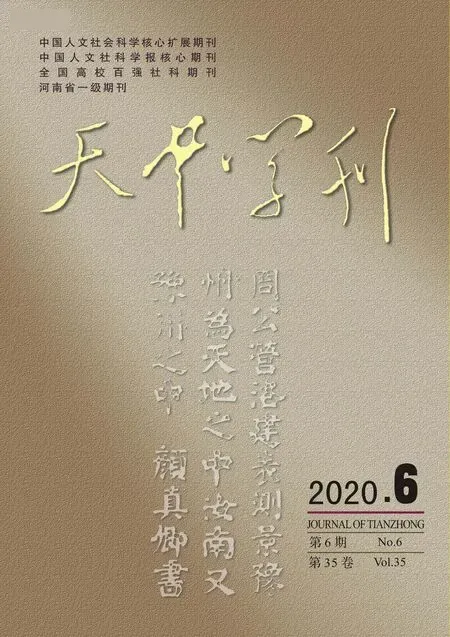西方衛生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引進與傳播
王少陽
西方衛生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引進與傳播
王少陽
(重慶文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2160)
隨著西方近代衛生觀念的引進與傳播,中國傳統衛生觀念開始發生改變,逐漸被賦予了科學、文明和現代性意義,其演變過程充分體現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復雜性,同時也反映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變遷的艱難。
衛生;近代;文明
近代以來,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既有衛生觀念開始逐步發生轉變。一方面,它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養生”和“保衛生命”的基本意涵;另一方面,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面對西方近代衛生觀念的沖擊,它也開始被中國本土的精英人士賦予了諸如“文明”“科學”和“現代性”的意涵,“衛生救國”也一度成為一個響亮的時代口號。
一、近代西方衛生觀念的傳入
“衛生”二字早在中國先秦時期的經典文獻《莊子》中就有記載:“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愿聞衛生之經而已矣。”[1]這里“衛生”主要指“保衛生命”和“養生”。近代以來,在殖民入侵與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西方衛生觀念開始逐步傳入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精英人士不斷對傳統“衛生”概念加以重新解讀與運用,最終促使“衛生”演變成一個與“Hygiene”相對應的具有豐富的社會與文化意涵的現代詞匯[2]。而作為與現代西方文明相伴而生的近代衛生觀念,則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與文化意涵:“自19世紀以來,東西各國于衛生一道莫不極端講求,不遺余力,久為世人所推許,其種族之強,國家之盛,良由是也。”[3]因此,“衛生”不僅被視作現代文明的象征,也是近代國人為實現國家現代化而努力追求的目標,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復雜性[4]。
一般認為,東亞地區近代意義上的“衛生”一詞最早出現在日本。1873年,長與專齋結合中國《莊子》中有關“衛生”的記載以及西方Hygiene的現代意涵,將“內務省”更名為“衛生局”。此后,“衛生”在日本逐漸成為一個通用詞匯,日本的近代衛生事業也隨之取得了長足發展[5]。中國直至光緒年間,隨著西方現代衛生知識不斷輸入,傳統漢語語境中的“衛生”概念才開始悄然發生改變。為方便讀者理解,中國早期的漢英字典和譯著中較多地使用了“保身”“養身”“養生”“慎疾”等中國傳統詞匯來指代現代意義上的“衛生”。
1881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學者傅蘭雅翻譯的《化學衛生論》一書,是國內目前已知最早冠以“衛生”之名且與近代“衛生”密切相關的譯著[6]。它豐富了傳統“衛生”概念的內涵,為此后開展真正意義上的衛生學著作翻譯提供了很大便利①。而1883年出版的由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翻譯的《衛生要旨》一書則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衛生學著作,該書除介紹一些日常衛生知識外,還特別強調了國家與社會在衛生事務中擔負的重要責任,從而將以往僅作為個人私事的衛生問題推衍為國家與社會需要重點考慮和推行的要務[7]。此后,近代意義的“衛生”不僅頻繁出現在書名中,還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正文中,其中很多用法也與今日大致相同[8–10]。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后,日本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作為日本明治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衛生行政日益受到中國社會的矚目。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促動下,越來越多的中國精英人士開始積極主動吸納西方現代衛生知識與觀念,并嘗試創建現代化的國家衛生行政體系。他們迫切希望通過學習西方和日本的先進經驗來改善中國落后的衛生狀況,以期達到“強國保種”的目的[11]。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關注日本的近代衛生文化與制度,由于日語中的“衛生”直接用漢字來表達,這大大增加了中國人使用該詞的機會和頻率。隨著中國人對待西方和日本近代衛生文化與制度的態度越來越積極主動,大量與此相關的信息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這不僅進一步豐富了近代“衛生”的內涵,也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近代“衛生”增強了認識[12–13]。
直到1905年,在借鑒西方和日本近代衛生行政經驗的基礎上,清政府設立了衛生科[14],標志著國家對近代“衛生”的認可。此后,近代“衛生”的使用越來越大眾化,并最終成為一個表示維護健康、預防疾病等含義的社會日常生活用語的一部分,使得近代“衛生”觀念基本得以確立。與此同時,近代“衛生”仍具有一定的傳統因子,傳統“衛生”的使用現象依然存在[15]。
二、近代衛生觀念的傳播及影響
隨著近代衛生觀念的輸入與傳播,國人越來越意識到公共衛生建設不僅關乎個人身體健康,還與強國強種和民族復興有密切關系,并會對社會秩序和國家形象造成影響。對此,一些知識分子認為不能僅將公共衛生看成一般性的清潔打掃,而忽略其豐富的內涵,故對公共衛生建設的主要內容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時人認為,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建設擔負主要責任,不僅需要建立相關專業機構,還需制定詳細的實施計劃。同時,公共衛生建設也離不開廣大民眾的廣泛配合與參與,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預期的計劃和目標[16]。
為改變近代中國內外交困的局面,有人開始提出“衛生救國”的口號,衛生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此項工作“成功著而費用省,足以祛世人之惑,濟行政之窮,為衛生界及教育界所特別注意也”[17]。以作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橋頭堡的上海為例,當地的衛生教育和宣傳最早是由在滬的外國人開展的。比如,1871年,海關醫官亞歷山大·賈米森醫生主編的《海關醫報》出版,對傳播近代衛生知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8]。此后,以伍連德為代表的中國本地西醫隊伍逐漸發展壯大,他們在傳播西方現代衛生知識和衛生理念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比如,在1915年上海博醫會全國代表大會上,伍連德舉辦了一場有關東北鼠疫的專題衛生展覽,他利用圖畫、模型等直觀的衛生宣傳品向前來參觀的民眾傳播有關防治鼠疫等傳染病的衛生知識與方法,受到當地民眾的普遍贊譽[20]。
近代的衛生教育和宣傳活動主要采取衛生運動、衛生展覽、衛生演講、放映衛生電影、印發衛生宣傳品等形式進行。比如,1915年2月,中國博醫會在上海召開全國會議期間,特邀美國醫學博士畢德輝組織了一次大型公共衛生展覽。他借鑒美國醫學會舉辦公共衛生展覽的經驗,和同事們一起制作和購買了大量海報、圖片、小冊子、幻燈片和模型等衛生展覽品,在2000多平方英尺的展區內,充分利用它們向中國觀眾展示結核病和天花給人類造成的種種危害,并傳播有關如何防治此類疾病的衛生知識[21]。在1922年5月由上海青年會舉辦的一場大型公共衛生展覽上,胡宣明、胡厚齋等人都陸續發表了有關衛生的演講,并組織觀眾觀看形象生動的衛生電影,畫面清晰,觀眾贊美不絕。展覽場地更是掛滿旗幟、彩燈、中國衛生會所制作的圖畫和古今衛生箴言,并有專門人員做詳細講解。童子部陳列的中華職業學校制作的梅毒及疫癥細菌模型標本,則讓民眾觸目驚心。中美大藥房、中國化學工業社、華強衛生用品廠展示的各種預防消毒藥品,應有盡有,不勝枚舉。展覽客廳臨時搭建了兩間診室,有眼科醫生劉尊值、牙科醫生葉經甫等現場免費施診。此外,俞家毅和翟志復等人還在現場進行了滑稽表演,令人贊嘆。據統計,此次衛生展覽期間,每日約有萬余人前來參觀[22]。
舉辦衛生運動大會是近代衛生教育宣傳的另一種重要途徑,它形式多樣,內容豐富。1928年4月,經上海市市長張定璠提倡,上海舉辦了一次規模空前的衛生運動大會,僅開幕式當天就有萬余人前來參加。會上,張定璠積極闡釋了衛生對于市民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公共衛生,是要各個市民都能夠完成自己的衛生工作,以免妨礙他人的衛生利益,務使全市人民都得到身體上的健康,精神上的愉快。進一步說,市民有此愉快的精神和健康的身體便能免卻夭折,日登仁壽,便能努力完成他一生的事業和生活上的需要。我敢說衛生是人類于其生活上的基本工作。”[23]而針對當時我國民眾人均壽命低、死亡率高的情況,他也給予市民以希望:“現在,我們為經濟和時間所限制,只能就社會上現行的衣食住行各種制度之下,求十二分的清潔和整齊,并將市內不適用的衛生設備加以改革,以減少病菌,減少疫癘,并避免人生不可預測的各種災害。等到北伐完成,黨內的政治完全注重到建設事業的時候,我們還要把衣食住行逐漸改善,務使市民在生活上得到一個總解決,以完成總理的民生主義。”[23]為達到這樣的目的,他還特別呼吁市民積極與政府合作:“今天衛生運動大會,市民來參加的非常踴躍,很有一種除舊布新的氣象,并且可以表現出市民革命的精神,可以表現出市民與政府合作的觀念,我擔負著市政的責任,對此是如何的歡喜。但是衛生不過是市政的一部分事業,其他市政之應該除舊布新,及應該用革命手段于破壞后來建設的還是很多的,自今天以后,我希望市民對于其他一切市政,都要同參加今天衛生運動一樣的熱烈,與政府合作起來。”[23]此次衛生運動大會的節目有圖畫文字宣傳、衛生通俗演講、衛生專門演講、各影戲院加映衛生標語、各游散場加演提倡衛生的歌曲或表演、衛生商品陳列展覽會、公開檢查身體、游行等[24]。
出版發行衛生書報也極大地推動了我國近代衛生教育和宣傳活動的開展。據不完全統計,僅民國時期出版的衛生書籍就有近4000種之多[25]12。中國近代早期的生理衛生書籍于19世紀70年代后由來華傳教士編譯并出版,《孩童衛生論》《初學衛生論》《居宅衛生論》等書的主要內容均來自西方實驗醫學和衛生知識,主要關注人體健康問題。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精英人士開始積極參與衛生書籍的編譯和出版,極力宣揚衛生對于個人、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近代衛生書籍的編寫和出版與社會風氣、政治形勢以及大眾閱讀心態的變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內容涉及人體健康、家庭、學校和軍隊衛生管理等多個方面。上海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益智書會和上海醫學社等機構因具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豐富的書籍出版經驗以及數量眾多的新學人才,組織出版了大量衛生書籍,為近代中國的衛生教育和宣傳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26]。隨著我國西醫醫院數量逐漸增多,各種衛生報刊也相繼興起。據不完全統計,僅1921至1937年間就有西醫報刊237種,中醫報刊190多種[25]14。由上海市衛生局和中華衛生教育會合辦的《衛生月刊》于1928年創刊,刊載內容有圖書論著、譯述、衛生局工作報告、各種衛生法治規則、世界各國衛生新聞等信息和相關介紹,由國內多名中外衛生學專家常年擔任義務編輯,選取材料以學術研究和事實報告為主,在刊登醫藥廣告方面有嚴格規定,堅決不為藥物成分不明的丸丹制劑等有害藥品刊登廣告,并搜集市場上出售的各種藥品加以分析,將其中有毒藥品的名稱刊登出來,“害人藥品不致暢銷,而市民之受其騙,受其害者日少”,為維護當地民眾的身體健康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27]。
在近代家庭衛生教育方面,由于長久以來,中國家庭衛生意識淡薄,“平日起居飲食既已不慎,臨病時看護不得其法,藥石又復誤投,其不死于非命者幾希,及一旦釀成疫癘,又無防遏傳染之策,以補救于后,故年來各省每至夏秋之際偶起時疫,則十室而九染,朝生而暮死,深堪浩嘆”。對此,越來越多的中國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家庭衛生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應改善中國家庭的衛生狀況,以增進民眾身體健康與國家振興,“此事關系至重,小則保全家庭之安寧,而改良其生活,大則增進國民之健康,而謀邦家之幸福”。對于怎么做才可以普及家庭衛生教育,當時有人提出了以下四項措施。首先,在國人最容易忽略的人生日用方面,最應該講究衛生,如居住室宜通空氣,勤灑掃,必須清潔,室無灰塵,以防微生物傳染疾病;衣服裁制必須適宜,尤當勤洗,以清凈為主;飲食烹調須合法,以清潔為主,尤忌食腐壞之品;疏菜等類不宜置諸地上,又不宜置近其他食物。其次,在日常活動方面也要講究衛生,如起臥須有一定時限,成人者須臥六時,小兒須臥八時,過多過少,均有礙于衛生;唾涕不宜隨意,恐其傳染疾病;作事須有休息時候,過勞或傷福經,或傷體力。再次,在養育方面亦需注意衛生,“養育之法,中國古人頗有注意者,然近來每易誤用,為害滋大,不可不研究也”。如要避免這些危害,在婦人妊娠時,可以借鑒日本有關種種保衛之法的研究專書。而父母養育小兒不可以放任溺愛,“不知愛兒者,則因放任而種種之病生,溺愛其兒者,則因姑息而種種病生,不可不慎”。最后,在疾病預防和治療方面,須注意醫師命令、病人飲食、病氣傳染、病室掃除、交換空氣、病褥清潔、衣服洗濯等。總之,家庭衛生教育無論于家還是于國都很重要,其方法也十分多樣。“所望研究衛生之學者發宏愿,立大志,或仿日本設立衛生學校,或設衛生演說社,分赴各處演說,盡力提倡,以冀一班社會皆知家庭衛生之必要,則其有益于國家非淺鮮矣。”[28]
綜上,近代意義上的衛生不僅關乎個人,更關乎國家命運,需要全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其中。“所謂大眾衛生是沒有階級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衛生的真意。社會上各色人等,無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貴賤,只要他們活著,他們就應該具備這種衛生常識,躬行實踐,以謀自己和人類的幸福。”[29]“蓋國家興衰,以人民之強弱為衡,而人民能否強健,則以公共衛生為準……一個國家的文明與野蠻,就是清潔和污穢的區別……衛生是養成健全民族的基礎。”[30]諸如此類論述在各種近代媒介上十分常見。近代衛生逐漸成為中國精英借以改造國家、社會和國民的工具,他們把衛生對國家主權和政府行為的關注集中在國民身體上,利用衛生來改造一個城市并為自己建立起“現代人”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衛生已包含了一些象征“生命權利”的東西,國家借助衛生這一新工具對國民個體進行管理和統治[31]。首先,衛生的近代化變遷,是中國人近代民族意識覺醒和華洋文化沖突的重要體現,成了雙方用以爭奪話語權的工具;其次,近代中國的衛生事業引發了不同國族之間的文化互動,民間力量的廣泛參與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再次,衛生的近代化是都市文明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衛生事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都市的文明化進程[30]。
因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和將來,衛生始終是人類共同關心和不得不面對的話題,衛生建設始終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和事業。“如今,世易時移,當一份從容和優裕已相對不再是奢望時,撫今憶昔,我們自然不必去苛責先人的努力和局限,但無疑有必要去盡力還原歷史的復雜,讓今人有機會在復雜的歷史圖景中,去發現重新思考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以及反思現代性的靈感和資源。”[32]
① 此后,傅蘭雅以“衛生”之名翻譯了一系列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近代衛生學著作,如《居宅衛生論》《孩童衛生編》《幼童衛生編》《初學衛生編》等。參見羅芙蕓著《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34頁、王揚宗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頁和第132頁。
[1] 莊子今注[M].陳鼓應,注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599.
[2] 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J].東洋史研究,2005(3):560–596.
[3] 天津衛生展覽演講大會布告[N].益世報,1916-05-26(1).
[4] 余新忠.衛生何為:中國近世的衛生史研究[J].史學理論研究,2011(3):133.
[5] 松本順自伝·長與専斎自伝[M].小船鼎三,酒井シヅ,校注.東京:平凡社,1980:133–139.
[6] 衛生化學論[M].傅蘭雅,譯.光緒七年格致匯編館刊本.
[7] 衛生要旨[M].嘉約翰,口譯.海琴氏,校正.光緒九年刊本.
[8] 中山市人民政府.鄭觀應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342–343.
[9] 劉小斌,鄭洪.嶺南醫學史:中[M].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2:46–49.
[10] 高日陽.嶺南醫籍考[M].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1:518–519.
[11] YU Xinzhong.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cepts of Public Health[M]//Angela Ki Che Leung, Charlotte Furth.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51–72.
[12] 鄒振環.疏通知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88–291.
[13] 陳可冀,周文泉.中國傳統老年醫學文獻精華[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7:210–211.
[14] 鄭天挺.中國歷史大辭典:下冊[M].音序本.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2786.
[15] 余新忠.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M]//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新世紀南開社會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273–290.
[16] 朱英.中國近代史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39–341.
[17] 高維.衛生教育淺說[J].中華醫學雜志,1934(3):409.
[18] 戴文峰.海關醫報與清末臺灣開港地區的疾病[J].思與言,1995(2):159–160.
[19] 王哲.國士無雙伍連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20] Hutcheson A C.An Appreciation of the Conference Exhibits[J].Chinese Medical Journal,1915(2):133–134.
[21] BU Liping.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Picturing Health: W. W. Peter and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in China, 1912-1926[M]?//David S.Imagining Illness: Public Health and Visual Cul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27.
[22] 青年會衛生展覽會續紀[N].申報,1922-05-12(14).
[23] 衛生運動大會昨日開幕[N].申報,1928-04-29(13).
[24] 衛生運動大會今日開幕[N].申報,1928-04-28(13).
[25] 王東勝,黃明豪.民國時期健康教育文集[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26]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99–125.
[27] 胡鴻基.衛生月刊之希望[J].衛生月刊,1928(1):1.
[28] 論家庭衛生宜注意[N].申報,1906-06-20(2).
[29] 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125–126.
[30] 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9.
[31] 羅芙蕓.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M].向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318–319.
[32] 余新忠.晚清的衛生行政與近代身體的形成:以衛生防疫為中心[J].清史研究,2011(3):54–74.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Health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WANG Shaoya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modern western health concep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concept began to change. Modern health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ty, its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fully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health; modern; civilization
K25
A
1006–5261(2020)06–0142–06
2020-03-08
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8BS13);重慶文理學院引進人才項目(2017RMK48);重慶文理學院人文社科振興項目(P2019MK19)
王少陽(1986―),男,河南濮陽人,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趙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