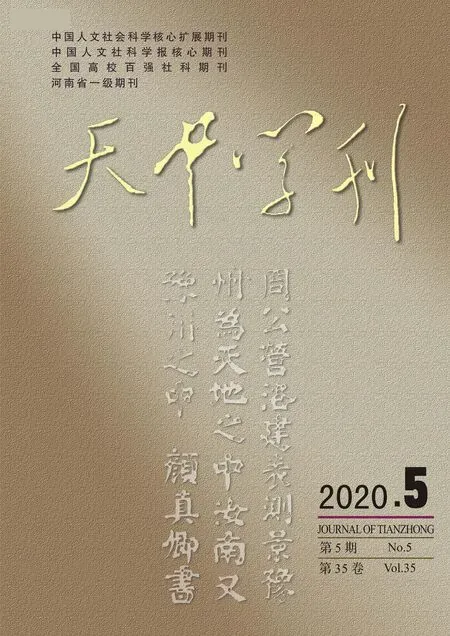論中華先祖部族文化融合軌跡——兼論中華古玉器淵源傳承
李國忠
論中華先祖部族文化融合軌跡——兼論中華古玉器淵源傳承
李國忠
(河南省駐馬店市委 編委辦公室,河南 駐馬店 463000)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既是中華先祖部族文化融合的過程,又是一段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人類文明史起源于新石器時期,而中國與其他文明迥異之處是,中國還有一個明顯的玉器時代,并與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高度重合。從考古發掘來看,遍布全國的文化遺址,諸如東北紅山文化遺址、浙江良渚文化遺址、中原龍山文化遺址、安徽凌家灘文化遺址、陜西神木石岇文化遺址等,普遍存在于距今約8000~4000年的玉文化階段,可稱為沒有文字記載的玉器文明時期。被視為我國古代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時代,實際上也是通過故事化和韻文化進行口耳相傳的,并沒有文字記載。《詩經》《楚辭》《古詩源》的有些樂歌,作為韻文化遺存的補證,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中人與天地、自然的關系,側面證實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存在。5000年中華文明史是眾多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文化不斷傳承融合及轉化創新的過程。
中華先祖;融合軌跡;古玉器;三皇五帝;楚辭
人類文明史應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距今約10000年。維爾·杜蘭特所著《世界文明史》稱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中國是世界曾存在過的五大文明發源地。《全球通史》提及“中東、印度、中國和歐洲四塊地區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1]。英國BBC廣播公司的大型紀錄片《文明的軌跡》將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印度河、黃河稱作世界四大古文明發源地。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時間,國際上認可為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時期,其主要依據是殷墟發掘成果。國內學者也只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建立。其中有不少惡意縮短中華文明存續時間的假說,甚至有受歷史虛無論影響的中華文明“西來論”。
在考古學不發達時期,對中華先祖歷史的研究,較少器物印證,大多依據史籍傳承,輔以推斷假設,把文字記載之前的歷史概稱史前,即在夏朝之前或說大洪水之前。而《春秋》《國語》《史記》等文獻詳細記載了上古世系以及各種文明的創造。直到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發現時代越晚,上古史記載越豐富完整,提出“古史層累說”[2],認為各朝各代在歷史記載中自覺不自覺地增添了自己的想象和解釋,從而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歷史體系,但無法構成新的歷史體系。近代考古學引入中國是在20世紀20年代。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直到20世紀末,考古工作者才建立起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并先后開展了考古區系類型學研究的文化歷史分析,初步認為史前文化的發展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彼此交流逐漸形成一體。他們對上古史的重構,奠定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探討的科學基礎。
一
在中國歷史上,考古學界研究循用世界通用的所謂“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分類法。為了研究那些時代的遺存,考古學界把分布于一定范圍,延續了一定時間并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遺存稱為一種“文化”(這里特指考古學文化)。在歷史學、考古學上對某一文化的命名,習慣上多使用最初發現這種文化的地名,例如仰韶(河南澠池仰韶村)文化、龍山(山東章丘龍山鎮)文化。按地理區域位置,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由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甘青文化區、江浙文化區和燕遼文化區六大文化區組成。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相當于新石器時期,距今約10000-4000年。
在古代,“中國”常常是一個文明的空間概念,而不是一個有明確國界的地理觀念。古人心目中的“華夏”是“中國”的同義詞,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古代先民自稱“華夏”,他們認為自己位居中央,四邊為蠻夷戎狄,自稱“中國”,即中央之國。之后各部落聯盟都自稱“華夏”。從黃帝到堯舜禹時代,史學界一直認為持續了500年。但筆者認為,這是考古學傳入中國之前的成文,從出土玉器所證可知這一時期應為1500年,即距今6000-4500年。也就是說,以大約5600年前進行的炎黃蚩尤大戰為契機,中華民族開始大融合。以此為界,之前中華民族為紅山部落集團、炎帝蚩尤部落集團、黃帝部落集團,之后相繼形成中原黃帝集團、海岱東夷集團、良渚祝融集團。傅斯年從歷史文獻角度提出的“夷夏東西說”甚有道理。實際上,從五帝時代到虞夏商周時代,前期是各部落聯盟爭雄時代,后期是部族聯盟成為區域性盟主,開始建立國家王朝的時代。
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然其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僅開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3]512,至殷墟發掘后提前到公元前1300年。對于之前的歷史,學界在認識上存在分歧。這段歷史常有王無年,因而出現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歷史”的不正常情況。為此,國家于1996-2016年實施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兩個工程對中華文明歷史淵源探索意義非凡。但不足之處在于兩個工程把虞朝排斥在外,其內在原因應為內囿于中原中心說的先入為主,外在原因則是片面依賴于考古挖掘。而且,考古學一般都把重點放在遺址建筑格局、功用和器物技藝上,往往忽略這些器物的形制、淵源、傳承和刻畫紋飾所揭示的信息內涵。王國維認為,考古歷史文化須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印證,缺一不可。
二
舊石器時代以打制石器為文化標志,新石器時代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為文化標志,這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大體是一致的。世界文明的發展軌跡大同小異,我們的祖先同其他人類一樣,從長期的采集、漁獵過渡到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生活。在種植五谷、馴養牲畜的同時,人類先是學會了打造石器,然后學會了磨制石器,進而學會了磨制玉器,并懂得了用黏土制作陶器,從此人類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玉器鮮明的傳承關系和獨一無二的歷史傳統,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明史所獨有的。
從瓷器史上看,原始陶器大體有紅、灰、黑、白之分,“著名的彩陶屬于泥質紅陶,工藝美術講究裝飾和造型。原始陶器的裝飾之美集中體現在彩陶,造型之美突出體現在黑陶”[4]。新石器時期的陶器大體是使用器,主要有飲食器、貯存器、汲水器、炊器、酒器等類別。特別是黑陶文化,可以對應玉器的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但不具備復雜的禮儀專用之器。由于陶器的地方特征比較顯著,考古工作一般把陶器作為識別文化類型的依據,卻忽視了玉器可作為文化劃分類型的更重要依據——玉器器型變化較慢,而形制的繼承性、過渡性、連續性都比較強。
新石器時期的玉器演變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早期源頭分為東北和東南兩大區域。炎黃大戰及炎黃與蚩尤的大戰是華夏民族第一次大融合,從而形成中原部落聯盟,奠定了中華主體民族的形成基礎。制作精美玉器與陶器的前提必須是“定居”,所以人類定居生活的逐漸鞏固,為后來銅器、青銅器和鐵器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中國古玉器發端于東北區域,最悠久的玉器是東北平原上距今約9000年的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的玉器,計有67件。之后是距今8200-7400年的興隆洼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玦等裝飾品。用玉石作裝飾品,說明當時已有發達的農業和長期定居的環境。在距今6000-4500年的紅山文化時期,制玉工藝水平達到了至今也難以企及的高度。東南區域的洞庭湖流域是傳說中炎帝的故鄉,也是中國最早的水稻種植地。距今約7000年的浙江省中部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有玉玦、管、環、珠等裝飾品。一個在東北,一個在江南,兩個史前部落均有玉玦出土,同時河姆渡文化遺址與紅山趙寶溝文化遺址出土的鳥陶盞幾乎一模一樣,而且玉玦的形制、大小、薄厚及用途基本一致,說明有人從東北平原越過燕山,沿著渤海、黃海和東海海岸來到南方,南北民族融合從此開始。
7000年前,河姆渡玉文化及白陶刻繪技術隨水稻種植技術進入長江中下游地區,輻射產生了馬家浜玉文化、大溪玉文化、高廟玉文化。其中,大溪文化遺址是玉玦由東向西沿長江流傳最遠的地方。在距今6400年前后,炎帝南方部落東進北上,在黃河下游和淮北地區,取代太昊氏部落成為地區霸主。
相對于東北和東南區域,黃河流域玉文化發展較為滯后。距今8000-5000年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傳說是伏羲和女媧的故鄉,有高超的細石器加工技術和制陶技術,又稱先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距今7000-5000年。仰韶文化的上千處遺址中出土玉器極少,裝飾性玉器的佩戴和使用也十分有限,沒有形成一定的系統或規模,這說明該區域農業生產水平低于東北和東南區域,并且缺乏玉石資源。
山東文化區域在距今7500-6400年之間孕育了北辛文化。北辛文化遺址出土的大汶口彩陶顯示出黃河裴李崗文化和仰韶文化東傳的痕跡,而且彩陶中常見的八角星太陽紋明顯又受洞庭湖流域長江中游文化的影響。這說明多種文化基因促進了大汶口文化迅速成長。
在距今6000年前,東北平原的紅山文化已經相當成熟;以炎帝為代表的南方部落實力雄厚,積極東進北上,并取代太昊部落成為地區霸主;位于黃河中游的中原部落也十分強大。當南方部落聯盟由南向北與中原部落聯盟由西向東擴張相遇于黃河下游時,南北文化的和平交流演變為沖突。在距今5600年左右,炎黃大戰爆發。《山海經》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5]430黃、炎爭奪華北,黃帝久戰不敵,退守燕山、太行山一帶。關鍵時刻,炎帝部屬蚩尤兵變擁立少昊。無奈之下,炎帝求和于黃帝。炎黃共同與蚩尤作戰仍然不能取勝。于是黃帝只好求助于西遼河平原的玄女之國,稱女魃,大破蚩尤于涿鹿之野。蚩尤死后,黃帝乘勢奪取河北、河南、山東,居淮北都于彭城,遂成天下共主。炎帝去帝號居淮南,少昊居山東,均受制于黃帝。
《易經》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位于黃河與洛河交匯流域的河洛地區,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說法。雙槐樹遺址位于伊洛匯流入黃河處的河南鞏義河洛鎮,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中華文明形成初期階段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專家稱之為“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是呈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現存有大型夯土基址、3處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3處夯土祭祀臺遺址、人祭遺存等,面積達117萬平方米,出土了精美彩陶及與絲綢制作工藝相關的骨針、石刀等。而且,周邊的青臺、汪溝、秦王寨、伏羲臺,洛陽的蘇羊、土門、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等城址群對雙槐樹都邑形成了拱衛之勢,使其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古代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有關于黃帝時代“一百年,地裂,帝陟”[6]401的記載,唐代瞿曇悉達主編的《開元占經》也有“黃帝將亡則地裂”的記載,這表明黃帝部落遷都他處是因為雙槐樹遺址處發生了地震。而在對雙槐樹遺址發掘時,考古現場發現了多處有明顯地層錯位的地震裂縫遺跡,經確認其震級可能在6.0級以上。由此可判定,雙槐樹都邑應為黃帝之都。
雙槐樹遺址中心居址區內發現的由9個陶罐擺放的“北斗九星”圖案遺跡,表明古代中原先民對“北斗天象”的觀測非常精確,已經有了較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觀。遺址發現的用野豬獠牙雕刻的“牙雕蠶”是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與青臺遺址、汪溝村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絲綢實物一起,相互印證了5000多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從事養蠶繅絲。雙槐樹遺址發現3處墓葬區1700多座墓葬,均呈排狀分布。其中一個墓葬區被外壕、中壕圍成一個獨立區域,應是中國早期帝王陵寢兆域制度的雛形。值得一提的是,墓葬中殉葬品沒有發現玉器,其他殉葬品很少,即使規模很大、等級很高的墓葬依然如此,這在全國范圍內都屬于特例。這說明首領掌握軍事權和祭祀權,但宗教色彩不濃郁,具有明顯的中原文明發展模式特點。
距今5600-5300年的長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有大量玉器,玉斂葬規模驚人。玉器器形有鏟、斧、鉆等用具類,鉞、戈等禮儀類及環、璜、玦、璧、鐲、鷹等裝飾品類。王用的河圖洛書(包括玉版、龜筒)、玉冠和神職貴族所用玉龍、玉人等尤其令人驚艷不已[7]。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器具有南方炎帝部落的文化特色,應為退守淮南的末代炎帝家族的用器物。
傳說炎帝死后葬湖南炎陵,其子祝融葬于南岳衡山。“南岳”隋前在安徽西部霍山,并非湖南衡山,距今5600年左右這里還存在著太湖崧澤文化、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和潛山薛家崗文化。潛山薛家崗遺址出土了具有明顯凌家灘文化特色的玉琮形器、玉璜形器和玉鐲,特別是在凌家灘遺址中從未出現過的玉琮,可能產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北方民族向南方移動和擴張的過程之中。
在距今約5300年前,歷史進入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時期——華北有帝嚳,江南有吳回氏祝融集團。天下兵戈初息,但是黃河總是在華北平原上決口泛濫,治河成為北方王朝頭等大事,而吳回氏所居太湖地區則欣欣向榮,來自東方少昊氏和南方共工氏的精英云集,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當時獨領風騷。
公元前3250年,吳回氏、重氏祝融部族集團吸收了凌家灘文明成果,在長江流域建國良渚。良渚國號虞,定都余杭,歷時1100年左右,是中華大地第一個王朝。東夷重氏家族是山東半島最古老的家族,炎帝時重氏擔任神職,炎黃大戰后又為黃帝所用,帝顓頊時擔任“司天”之職。良渚人的始祖吳回是重黎之弟,在帝嚳時繼任祝融一職,他同樣屬于重氏祝融家族。當時良渚集團武力強大,天下無敵,戰國古籍《鹖冠子》記載:“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8]良渚虞國空間分布在環太湖流域,中心面積約3.65萬平方公里,以良渚城為中心。現考古存在有良渚古城、良渚水壩、反山河瑤山遺址。其中,“良渚古城由宮殿區(40公頃)、內城(280公頃)、外城(約350公頃)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組成,內城和外城布局跟中原地區城市建造一脈相承”[9]。由此可推測,良渚文明與中原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僅大件琮璧玉器就有上千件,各類玉器達萬件之多。其中用具類有斧、鏟、鑿、紡綸等,裝飾品類有璜、鐲、玦、管、珠、帶鉤、佩、觿、串飾等,禮儀器類有鉞、璧、琮、冠形器、錐形器、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雕刻的“獸面紋”和人獸結合的“神徽”等紋樣,表現出統一而強烈的宗教崇拜意識。大量同類玉禮器的存在說明該地區存在一個具有同宗、同盟、同禮制、同意識的多層金字塔式社會結構的邦國集團。在出土玉器中,黃河流域的玉錐形器成為僅次于玉琮的法器,說明良渚文化雖師承凌家灘文化,卻不屬于炎帝集團,而是屬于南下討伐共工氏的黃帝一族后代。
禮器是禮制的物質表現形式,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活動時使用,“器以藏禮”[10]873,用以“名貴賤、辨等列”[10]44,區別貴族內部等級。良渚文化遺存中的玉禮器具有青銅禮器的功能,更多用于宗教祭祀,說明當時等級和階層區分鮮明。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只有貴族大墓才隨葬玉器,隨葬玉禮器眾多者中還發現有頭蓋骨,說明有奴隸殉葬。由此可見,良渚文化宗教氣氛濃厚,神權大于王權或掌握王權,禮制和貴族名分制度已形成,奴隸制社會初具雛形,大虞良渚古國初步形成王朝,進入文明古國階段。
良渚國的支柱產業是農業、絲織業、漁業和鹽業。貴族集團以神的名義發布歷法,建立最早的戍邊制度和屯墾制度,普遍使用最先進的石犁、石刀、石錛和石斧。良渚手工業異常發達,除了上述玉器外,陶器、漆器、絲織品等也十分精美。良渚古城遺址出土的玉柄象牙梳媲美商代婦好墓玉梳,嵌玉漆杯較春秋戰國毫不遜色;出土的玉帶鉤表明良渚貴族普遍穿著絲綢縫制的袍服。良渚原始商業貿易活躍,中國最早的集市和商業碼頭在此出現。
良渚國鼎盛時期,勢力遠達蘇北及山東邊界。傳說禹祖先鯀因治水不力被堯治罪,堯借良渚祝融之手殺死鯀,鯀葬于東海羽山。在良渚內部,重黎吳回祝融家族爭斗紛起,政權時時更迭,有虞氏舜在家族繼承中屢受打擊。帝舜有虞氏家族屬良渚貴族重黎一脈,其祖先分別是顓頊、窮蟬、敬康、句芒、蟜牛、瞽叟。舜弟“象”繼父職位后,舜為逃避迫害,率有虞氏一支向北方逃亡。由于有虞氏祖傳高超的制陶技術,北逃的舜先是擔任陶正負責制陶,再任虞官管理山林,后來逐步進入帝堯集團權力核心,并成為堯的女婿。
舜進入帝堯權力核心后,與夏后氏共同為帝堯治水。舜獲得巨大的信任權力后,率部進軍長江流域,南下攻擊三苗人。三苗人是南方種植水稻民族的總稱。據《山海經》載,三苗人并不是南方炎帝族人,而是早已定居南方的黃帝子孫。戰爭相當殘酷、激烈,傳說舜、禹皆死于與強大的三苗作戰之中。作為戰勝方,中原王朝成為正宗。
傳說帝堯晚年時欲“禪讓”于舜,三苗之君強烈反對,所以良渚戰敗后亡國已不可避免。三苗戰敗后大量被俘的良渚人被遷徙到了西方“三危”之地。《史記》記載:“舜歸而言于帝(堯),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3]28“三危”之地傳說在甘肅、寧夏或者青海。這就是齊家文化出土玉琮的原因,反過來也證實所謂三苗人其實大部分就是良渚人或者太湖人。除了少數極品外,齊家文化遺存出土的玉琮大都是光素無紋的,這說明三苗人到了西北以后不再強大和富裕。
中國的史學界對夏朝的起源疑竇叢生,但由于沒有文字證明,我們只能從遺址遺物中尋找蛛絲馬跡。發掘的史前遺址顯示,夏代之前和夏朝后期的遺跡都很完備,但夏朝早期遺留和出土玉器都不足以證明其身世和血脈。大家對河南偃師二里頭夏代遺址毫無爭議,但二里頭夏文化明顯屬于夏代后期。那么,我們只有從夏代玉器中尋找“家傳”。二里頭夏代遺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兩類,一是禮儀兵器類,如玉圭、玉璋、玉鉞、玉戚、玉刀、玉戈、玉璇璣等;二是飾物類,如管、珠、鐲形器、柄形飾等[11]。這些玉器中既沒有紅山文化代表器玉豬龍、勾云形玉佩、馬蹄形器,也沒有南方玉文化的璜、璧類,只有兩件玉琮殘片,而且其中一件又改作他用,這說明二里頭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無關。夏代玉器最顯著的特點是,由兵器轉化而來的大件禮儀玉器很多,玉禮儀兵器都裝飾有扉牙,并呈獸首狀。夏代玉器體現了王權的至高無上,而不是神的權威。
夏代玉器在國內出土最早的是山東海隅龍山文化玉器。山東龍山文化存續于距今4500-4000年間,只有它才能證明夏民族最初的形成及后來向西方的遷徙。目前山東龍山文化存世有明確出土記錄的是3件牙璋。對照二里頭出土的牙璋,它們沒有扉牙,這表明它們比二里頭的夏代牙璋更加古老,同時也證明夏民族起源于海隅,用的是山東海隅文化玉器。山東海隅文化玉器包括長條形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等,都由漁民常用工具進化而來。長條形弧刃或直刃玉刀是剖魚工具;牙璋是原始剖蚌刀造型;玉牙璧(玉璇璣形佩飾)是漁民織漁網或修補漁網用來割斷網繩的工具。夏代玉禮器很多,但唯有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始終保留著山東海隅民族的特色。
山東日照市五蓮山是一座東夷時代的神山,或叫“五連山”,即五峰相連日出之山。后來中原地區出現的玉禮器,如玉鉞、玉牙璋、玉圭、玉刀、玉筒式鐲、玉牙璧(玉璇璣)、龍山玉琮等,均可在五蓮山或日照地區發現祖型。
對于夏后氏起源于山東,《山海經》記載有北海之神禺疆和東海之神禺虢的傳說。在5000年前,山東人將渤海稱為“北海”,將黃海稱為“東海”,將東海稱為“南海”。山東半島是“隅夷”活動的地區,鯀、禹的祖先顓頊從西方來到山東半島而取代東方少昊氏。鯀被殺于羽山,著名的新沂花廳良渚文化遺址就在其附近。“隅”“禺”通禹,禹的祖先鯀死于這一區域,其后代分三支逃亡避難,一支向北逃至遼東半島,一支向西南入川,一支向西到陜西榆林神木石峁。
中國有一句民謠叫:“黃河百害,唯利一套。”黃河河套平原不僅有萬頃良田,而且沒有水害,神木石峁文化遺址就在此。該遺址存續年代距今4300-4000年,遺址面積超4平方公里,出土有127件玉器。其中,禮器類有璧、圭、牙璋,儀仗類有鉞、戚、戈和多孔刀,裝飾和藝術品類有璜、玉璇璣、人頭像及蠶、蝗蟲、螳螂、虎頭等[12]。據放射性碳-14測定法斷代,它們均屬于夏代紀年范疇。值得一提的是,神木石峁文化遺址出土的牙璋,制作精細,形制宏大,年代稍晚于山東龍山文化而早于河南二里頭文化。玉戈、玉戚的出土證明該器型起源于夏初,應該可以肯定神木石峁遺址就是夏早期都城。另外,遺址附近的一個祭祀坑出土了玉器36件,其中有兩件故意對剖成四件,玉器分六排刃口朝下插在坑底,明顯是以玉祀神。神木石峁遺址可以解惑許多史前歷史。《山海經》記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5]472此帝應為天帝。黃帝、顓頊可稱“天帝”,而堯是“眾帝”,故鯀應為堯之前時代人。而且,治罪的原因也不是治水不力,而是“不待帝命”。由此可推斷,鯀是黃帝的后代,卻不是帝顓頊的兒子,出身于顓頊一族;禹不是鯀的兒子,兩人年齡相差至少300年,禹應為鯀的后代。鯀被殺之后,其一支后代逃往河套平原,300年后在神木石峁建立了最初的大夏國。
龍山時代陶寺遺址被稱為中原龍山文化最大的城址,學者們公認它出現的年代早于河南二里頭文化時期。考古發現,陶寺遺址建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面積達58萬平方米,公元前2100年前后擴建成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址附近有一平面呈大半圓形特殊遺跡,復原顯示其夯土有意留出四道縫隙,分別對照的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時太陽照射位置,史學界一致認為這是觀測天象和祭祀的場所[13]。《尚書·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對此可印證。陶寺遺址出土有最早的空腔銅器,并發現了能夠確定為文字的材料。出土玉器可分為禮器、儀仗、裝飾品三類,多質樸無紋,工藝既不及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玉器精細,也不及神木峁集中宏大。特別是兵禮儀玉器只有鉞一種,戈、刀、戚闕如,而且同一種器物如琮、梳、瑗等,往往是石玉并用,不加選擇,這表明玉料的缺乏和琢玉水平的低下。一方面城址巨大,王權尊貴;一方面玉器制作水平較低,這似乎有中原王朝文化的影子。陶寺遺址城址規模巨大,功能分區明顯,出土有象征身份等級、軍事權力的鉞,表明城內統治者已擁有“王”權,疑為二頭聯盟執政之王城,亦有夏早期都城和虞舜龍興地之說。
三
中國的上古時代,指有文字記載出現以前的歷史時代,即一般所指的夏及其以前的時代。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可知,在距今5000年前中華大地就已出現了國家。由于上古時代沒有文字,主要憑借口耳相傳的記憶,而增強記憶的方法就是把抽象平淡的知識賦予情節變成故事,以便深入人心,傳諸久遠。因此,上古神話傳說并非空穴來風,而是確鑿可憑,只是時過境遷,這些傳說被后人當成了匪夷所思的神話。文史典籍所載的史前神話傳說大多是歷史傳說的故事化遺存。《山海經》是我國唯一一部史前史書。從文史典籍中查找史實痕跡,虞夏商周四朝脈絡清晰,躍然紙上,可以佐證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傳承。
三皇五帝實際上是上古時期出現的為早期人類做出貢獻的部落聯盟首領,三皇五帝時代,又稱“上古時代”或“神話時代”。“三皇五帝”構成了神話傳說時代的歷史系統,關于他們的傳說異彩紛呈,蔚為大觀。然而“三皇”“五帝”究竟對應哪些傳說人物呢?實際上有多種說法。“最為久遠也最為模糊的三皇,大抵是創世神話中的神人,史前人類的象征,關于它的說法竟有六種之多:(1) 天皇、地皇、泰皇;(2) 天皇、地皇、人皇;(3) 伏羲、女媧、神農;(4) 伏羲、神農、祝融;(5) 伏羲、神農、共工;(6) 燧人、伏羲、神農。”[14]9“三皇”所處時代,基本對應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此后的五帝大抵是一些部落聯盟的杰出領袖,已經較為具體,但也有三種說法:(1) 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2) 太皞(伏羲)、炎帝(神農)、黃帝、少皞、顓頊;(3) 少皞(少昊)、顓頊、帝辛(帝皞)、唐堯、虞舜。”[14]9“五帝”所處時代,對應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或玉器時代。
炎帝、黃帝,被中華民族尊為共同的“人文初祖”,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就是對共同祖先的尊崇。炎帝,就是神農氏。他和他的部落發明了農業、醫藥、陶器。由于生產工具的局限,當時的農業處在“刀耕火種”階段,所以原始農業和火有著密切的關系。農業社會中,炎帝后裔烈山氏、共工氏分別被后人尊奉為社神、稷神,受到人們普遍祭祀,以后便把“社稷”引申為天下、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稍晚于炎帝的黃帝,號有熊氏,似乎是以熊為圖騰的部落。相傳他率領民眾作戰時,指揮熊、羆等六種野獸參戰,用文化人類學的視角看,其實是指揮以六種野獸為圖騰的部落參戰。“黃帝的發明是多方面的,涉及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他發明冶煉,鑄成銅鼎;鑄造十二銅鐘,和以五音,可以演奏音樂。用樹木制造船、車,用于運輸;發明縫紉,制作衣裳;發明歷法,派人到四境觀察天象,確定春夏秋冬四季,按照四季的變化來播種百谷草木。”[14]10當時社會組織已經有了尊卑之別,人們已知道利用蠶絲編織衣料,并用服飾區別等級。把這些事實與鑄造銅鼎以及由12個編鐘演奏顯示權力威儀的音樂聯系起來分析,國家雛形隱約可見。
根據考古挖掘資料,筆者認為從黃帝到堯舜禹時代持續了1500多年,而不是500多年。這1000多年是虞朝立國建國與中原王朝并存的時期。其間,夷人部落與羌人部落先后加入中原部落聯盟。當時黃河流域一帶的先民自稱“華夏”,或稱“華”“夏”,但“華夏”作為一個概念卻出現得較晚。“楚失華夏”[10]1390是關于中原即華夏大地的最早記載,說明關于“華夏”的記憶由來已久。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對“華夏”注釋時說:“華夏為中國也。”此時,華夏部族聯盟已不再以血緣紐帶為聯系,而是建立了地緣性聯盟,形成了以地緣為紐帶的國家雛形。聯盟議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討論重大事務,推舉聯盟首領。在距今41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達到與海岱東夷地區相當的水平,于是出現了歷史學上的海岱東夷集團與中原華夏集團的聯盟政權,具體表現為以二頭盟主共同執政的禪讓制。
傳說堯年老時,在聯盟議事會上提出繼承人選問題,眾人推舉了舜。舜之后,由于禹治理洪水有功,聯盟議事會又推舉禹擔任首領。這就是堯、舜的“禪讓”故事,傳賢不傳子,被后人傳為美談。堯舜相承為帝之說也有“舜逼堯”[15]406的另外一說:“舜放堯于平陽”[16],“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3]。而禹年老時卻想把權力傳給自己的兒子啟,暗中培植啟的勢力。聯盟議事會先是推舉皋陶,皋陶死后又推舉伯益。禹死后,啟殺死伯益,繼承了禹的職位,于是出現了“家天下”的夏王朝。夏朝的建立,開創了由一家一姓世襲統治王朝的先例。
從部落氏族到階級社會有個過渡時期,此間氏族制逐漸解體,社會內部分化日益嚴重,階層出現,并逐步向國家發展。這些特征在神話上的反映,就是天地通路隔絕和天帝出現。天和地既然有所謂隔絕,就一定有不隔絕。“人之初,天下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17]生動地反映出階級劃分以前人們的平等關系。人類社會劃分為兩個階級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神話上的反映就是天和地通路隔絕。“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5]402“皇帝……乃命重黎絕地天通。”[18]320“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19]562韋昭注《國語·楚語》說:“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
人類社會劃分是怎樣出現的呢?推想起來,必定和氏族解體時期軍事首領在部落聯盟中建立的酋長世襲制有關。軍事首領由于世襲了酋長職位和發動掠奪戰爭而日益擴張其權力,反映在神話上就是出現了所謂的天帝。但那時候傳說的天帝卻不止一個,而是一大群。在《山海經》里,黃帝、女媧、炎帝、太皞、少昊、顓頊、帝俊、帝堯、帝嚳、帝舜、帝丹朱、帝禹、帝臺等,都是當時傳述的天帝,而所謂眾帝、群帝和當時混居中原的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領并非一個的實際情況是大致相符的。后來國家形成,階級劃分,建立了威懾四鄰的王朝,先前世襲的軍事酋長這時搖身一變成為國王,反映在神話上就是獨一無二、至高無上天帝的出現。“我國古代西方民族神話傳說中的上帝,就是黃帝、顓頊;東方民族神話傳說中的上帝,就是帝俊。”[20]33
《山海經》中的黃帝,兼有部落酋長和上帝的形象:黃帝在與蚩尤之戰中是部落酋長的形象,在嚴厲懲罰神國內訌的肇禍者時是上帝的形象。“帝之下都”昆侖山莊嚴宏麗和四周神異景色的敘寫,也是上帝形象的具體表現。“從《山海經》所記的神譜看,不但很多著名的天神,如鯀、禹、禺虢、禺強等,就是下方許多民族,如歡頭、犬戎、北狄、苗民等,都是黃帝的子孫,黃帝因此成了人神共祖。這便在原有英雄崇拜的基礎上,又增添了祖先崇拜的意識。這也是神話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必然發生的演變。”[20]34
傳說帝顓頊王朝歷20余世,存續了350年。此說較之將顓頊僅視為一人一帝,傳世只有一代的說法更為可靠。帝顓頊取代山東少昊氏集團后占據華北,并將少昊家族遷至西方,東方的少昊遂成為西方的帝,之后顓頊氏任用一些原炎帝和少昊集團的精英分子擔任重要職位,包括負責治水的河伯、修訂歷法和主持宗教事務的祝融、負責土木工程的共工以及負責開墾土地的后土。
帝俊在《山海經》中和黃帝一樣是非常顯赫的,他是東夷民族奉祀的上神,也是殷民族奉祀的始祖神。《山海經》中所記帝俊的地方共有16處,少于黃帝的23處,與顓頊的16處并重。《山海經》關于帝俊的記載有三個特點:一是所記皆為片段,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二是僅見于《大荒經》;三是帝俊之名僅見于《山海經》,其他先秦古籍甚至連屈原的辭賦里都沒有。《山海經》關于帝俊的記載材料從內容到形式都十分接近原始狀態,劉歆認為其內容荒怪,記錄凌雜無序,故“逸在外”,到郭璞注《山海經》時才將之注釋收入。從內容看,《山海經》中這一部分材料的成書年代最早。虞、舜、帝俊和夋都是一人,“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燭光”,可見舜作為天帝的神格。舜的子孫為國于下方,有臷國。“臷國在其(三苗國)東”,“巫臷民盼姓,食谷(稻)”[5]371。臷國又叫巫臷民,居住在一個得天獨厚的人間樂園,這里百谷自生,鸞鳳云游,人死可以復蘇。“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鸞鳥自歌,鳳鳥自舞”[5]371–372,渲染了天神后裔的優越性,這和良渚虞朝重巫、美服及居住地理環境高度一致。
《山海經》是一部被忽視和低估的歷史記錄,共18卷3萬1千余字,其中神話資料為我國傳世典籍之最,自古傳為大禹伯益之作。禹之時代尚無文字,不可能有《山海經》這樣完善的著述。但《山海經》其書是像圖以為文,先有圖后有書,因此卻不妨礙其圖來歷甚古。朱熹就稱此書是摹寫圖畫而成。今本《山海經》所有附圖皆為《山海經》古圖亡佚后,后人根據經文附會之作。其《大荒經》中的四方風名和四方神名見于殷墟卜辭。《大荒經》反映的四時觀象制度可與《堯典》所載羲和“歷象日月星辰”及舜“巡守四方”“望秩于山川”之事相印證。《大荒經》以山峰作為坐標觀測日月次舍以確定時節和月序的方法是《周髀算經》蓋天說的濫觴,說明《周髀算經》的天文歷法體系和《大荒經》《海外經》一脈相承。《周髀算經》記載的實測數據有著古老來歷,有的數據觀測時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21],而這正處于傳說中的虞夏時代。
《山海經》為古代巫祝的祭典,書中大量的神話故事確實為上古史實的口耳相傳,光怪陸離的神仙實際上是原始先民對自然和祖先的祭祀形式,是人類早期思維的投影,折射出先民們對祖先的圖騰崇拜。書中的肅慎、匈奴、犬戎、氐人是秦漢時還在北方活動的古族。《海外北經》記載的炎黃兩個部落戰爭反映了炎黃兩個部落融合共同構成華夏族的史實。不論是海內還是海外,射箭者都不敢向軒轅臺引弓,可見黃帝作為華夏始祖在先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山海經》中還詳細敘述了炎帝、黃帝、舜的世系,這對研究上古文明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海外南經》記載了中土本部之外的南部文明,這一部族是傳說中流放的部族,有人認為是帝堯長子丹朱的后代。三苗部族基本是南方良渚部族,在舜帝時遭到圍剿。《海外南經》中還記述了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以及堯帝時十日并出,植物枯死,羿射落九日,為民除害的故事,影射了羿平定九部落之事。另外,《海外南經》記載帝堯和帝嚳都葬在海外的狄山,這表明南方已是中華較發達的地區。《海外西經》記載了巫咸、肅慎等少數民族的名字,表明了上古部落大規模長距離遷徙的可能性。《海外北經》關于歐絲之野的記載反映了我國絲織業的悠久歷史。《大荒東經》記載了少昊和帝俊的國家已經脫離采集漁獵的生產生活方式,開始馴化野獸定居農耕。《大荒南經》記載蒼梧是帝舜葬身之所,季禺國是顓頊后代及后羿射殺鑿齒的神話。《大荒西經》關于夏啟《九辯》《九歌》來歷的說明,內容可與屈原的《離騷》《九歌》相印證。
我國最古老的歷史書《尚書》,記載有從堯舜到周代初年的若干歷史文獻資料,雖然真偽雜出,亦可以與《山海經》《舜典》等神話傳說材料相互補充印證。《周書·嘗麥篇》關于赤帝、黃帝和蚩尤的神話材料“和一般神話傳說或歷史傳說所說的有些不一樣。一般所說的是,先是黃帝和炎帝在阪泉戰爭,然后黃帝和蚩尤又在涿鹿戰爭(其實阪泉、涿鹿都是一地),蚩尤是炎帝的后裔,故黃帝和蚩尤之戰,無非是黃炎戰爭的繼續。這里的說法卻有異于以上所說。是蚩尤要把赤帝(即炎帝)從涿鹿趕逐出去,‘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黃帝這才‘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的。黃帝、炎帝原是和睦相處,毫無爭端,倒是炎帝見逼于蚩尤,向黃帝求救,黃帝仗義,為解炎帝之厄,才將蚩尤擒殺于中冀。這是黃炎之爭的異說,也值得做參考”[20]63。
《左傳》是春秋時期的史書,所載傳說入史材料很多。如《襄公四年》所記有窮后羿興亡史、《宣公三年》所記禹鑄九鼎、《昭公元年》所記主辰主參、《昭公十七年》所記少昊摯事等,都有助于我們探討古史,了解神話。司馬遷在《史記》中也采取了一些神話材料入書,“本紀”“世家”“列傳”乃至“八書”里都有,如《五帝本紀》說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等。
據傳帝顓頊死后,高辛氏奪取帝位,是為帝嚳。帝嚳命顓頊氏裔孫重黎氏祝融率部追剿南方共工氏。重黎先是攻克安徽含山凌家灘,后因作戰不力被殺。于是,帝嚳任命重黎之弟吳回繼續擔任祝融,率兵追殺共工。此時距離黃炎大戰已經過去了300余年。吳回是黃帝集團南下攻渡長江第一人,顯然戰功超過哥哥重黎,功高蓋過帝嚳本人。但是,戰爭亦使吳回部落重創。《山海經》記載,吳回本人失去了右臂;吳回跟蹤追擊共工氏余部來到江南,不再北返。南宋羅泌《路史》說帝嚳封吳回于太湖之地,今江蘇之地古稱為“吳”即始于吳回,吳回遂成天下吳姓始祖。不久,吳回在良渚建虞國,定都余杭。千百年后有虞氏舜出走,良渚虞國反被舜滅,流落為三苗,后“虞”之名逐步為舜所據用。
四
學界在虞朝問題上有兩點誤區:一是認為虞不是單獨朝代;二是把虞誤作舜,認為唐堯虞舜,唐堯不是朝代,虞舜當然也不是朝代。實際上,虞作為一個朝代,與夏商周為上下三代同為四代的概念應該在周初已是共識,但漢后卻湮滅于史。“三代”是一個隨時代遷移而變動的概念,春秋時期,由于當時西周已亡而東周尚存,談話時若要明確周亡或周續時,就分別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兩個“三代”概念。新出戰國時代的郭店楚簡亦有《虞詩》。《左傳》《國語》中虞夏商周四代連稱的文句不勝枚舉,且多為轉述春秋時人的對話。比如,《國語》中孔子回答吳國使者說的“汪芒氏之君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今為大人”[19]213。甚至連各種禮器也都是四代相比,如數家珍:說到車則是“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說到旌旗則是“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22]610;說到尊則是“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22]611;說到黍稷器則是“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22]615;說到俎則是“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22]615。當然,由于虞是第一個朝代,禮器不甚完備,如爵、馬、勺、豆就只有夏商周類比了。
最明確的是《左傳》所證史墨的話:“社稷無常奉,群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10]2079春秋時期仍為周朝,姬姓仍是嫡姓,“于今為庶”就是說虞夏商三后在周前都是天子其姓為嫡,由于喪失天子地位而為庶姓。“于今為庶”的三后明顯指虞夏商三代,“三后”中夏商二代均為獨立朝代,那為什么虞代不是獨立朝代?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由于虞朝與夏商無異,西周建國后還對其后裔予以特別禮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10]1359。與宋、杞合稱“三恪”同受周人客禮待遇,乃是虞、夏、商三個朝代的確證。由此可見,關于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已是共識。否則,周人按照周世“尊賢不過二代”只備杞、宋二恪即可,而不須備足陳、杞、宋“三恪”了。如果虞為唐堯虞舜之虞,那么又為什么不將封于祝的黃帝之后裔和封于薊的堯之后裔一并增入而合稱“五恪”?原因顯而易見,漢代之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虞雖為獨立朝代,卻不是中原王朝所建,不屬于正統且被中原王朝當作蠻夷剿滅,因而無意或故意將之湮滅于史罷了。
當然,這時的王朝不能和秦以后的王朝等量齊觀,《呂氏春秋》說“天下萬國”,《左傳》說“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自然是夸張,反映的不過是指夏朝是松散的諸侯邦國聯盟而已,虞朝也是如此。虞、夏、商、周與此后朝代不同是因為,一方面它們是王朝更替、互相銜接的朝代,另一方面它們又是四個同時并存的部落集團。按照《史記》所說,夏商周三代祖先均在堯舜政權機構中服務。《山海經》多次提到昆侖山是萬山之宗,黃河是萬河之祖,對我們認識華夏民族起源地意義重大,但受成書者的黃河中心局限,長江流域被劃到夷苗之列。
五
《詩經》《楚辭》是古代歷史傳說韻文化遺存。《楚辭·九歌》保留了一些古氏族祭歌頌歌,保存了我國遠古部族圖騰神話,從中可以窺見中華古文明的起源與傳承。由于上古時代沒有文字記錄,所有的知識系統包括歷史知識都是憑借口耳相傳。而保有記憶的機制和訣竅最常見方法就是韻文化,即把歷史和知識編成朗朗上口便于傳誦的歌謠,或變成讓人喜聞樂見的神話故事。中國歷史傳說韻律化雖沒有像荷馬史詩那樣系統的著作流傳下來,但在《詩經》《楚辭》《古詩源》中大量存在。古氏族祭歌和民間傳唱之“風”就是我國古代歷史傳說韻文化遺存。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分風、雅、頌三大類共305篇,產生年代約為春秋及之前,由孔子整理。它大體反映了周代的社會面貌和思想感情,也是一部周族從后稷到春秋中葉的發展史,但又不局限于此。《楚辭》是戰國時期楚國文學總集,收楚人屈原、宋玉等辭賦17篇。“楚辭”是春秋末年生活在長江流域的人民以口頭形式保留的詩歌樣式,其中《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堪稱經典。尤其《九歌》是在楚國民間祭祀樂曲基礎上的記錄創作。“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屈原放逐……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23]。可見其詞曲由民間口口相傳,反映了古歷史文化的端倪。
《古詩源》是清人沈德潛選編的古詩選集,其中卷一“古逸”收集先秦詩謠百余首。其中《伊耆氏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是神農時期的臘祭歌,應是中華民族最早的歌謠,《禮記》亦載之。《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這是《古詩源》開篇之作,傳為堯出巡時見一老者拍其土壤而唱之,表現了堯時的無為而治、天下太平,也符合早期社會統治權力不集中時的社會形態。《康衢歌》“立我臣民,其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與《擊壤歌》主題截然不同。據《列子》記述,堯治理天下50年后,有一次微服游于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東部一個叫康莊的地方聽百姓傳唱,看到百姓怡然自足,非常高興,于是“召舜,禪以天下”。《卿云歌》“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傳為舜所作,《尚書大傳·虞舜篇》有載,也是復旦大學的校名來歷。《堯戒》“戰戰栗栗,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出自《淮南子·人間訓》,是中華民族第一條座右銘。《夏后鑄鼎繇》“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傳為夏后鑄鼎之文,曾見于《墨子》。如此等等,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烙印。
《詩經》中有兩篇“感天而生”的神話故事,分別是商始祖契和周始祖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出自《詩經·小雅·北山》,據說首次出于帝舜之口。《詩經》還不止一次歌頌了大禹治理洪水而締造山川的功績。《詩經·國風》中“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描述了太昊、炎帝之都陳國宛丘的情景。《詩經》中“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言顧之,潸焉出涕……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24]477記述了東夷諸侯國臣民諷刺中原王室只知搜刮財物,奴役人民,不顧東方人民苦難的事實。
《楚辭》中有很多神話和歷史材料。《天問》就是一篇史詩,用一百八十余個問題敘述當時所有的上下古今知識。《楚辭·遠游》“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和《九章·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是關于黃炎舜的記載。《楚辭》中的《招魂》和《大招》是兩首巫歌。《招魂》是招人魂的,《大招》是招鬼魂的。兩首巫歌中所描寫的四方,非出自巫覡杜撰,皆有所依本。《九歌》是屈原作品中最美、最精、最富魅力的詩篇,代表了屈原藝術創作的最高成就。“九歌”是遠古流傳的樂曲,對此《左傳》《離騷》《天問》《山海經》都有記述。“九歌”只是神話中的樂曲名稱,屈原在楚地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改作加工成《九歌》。特別是《九歌》保存的圖騰神話成為認識遠古部族文化和史實的重要窗口,它對部族文化的轉化創新影響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
考古資料和出土玉器表明,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農業生產水平低于長江流域,從黃帝至大禹1500多年的上古中國史,基本上是東夷史。長江下游東(南)夷由于良渚被堯舜滅國后湮沒于史,夷的傳說也就以黃河下游東夷虞舜為主導。東夷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一直處在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其先進性在文化上的表現,便是東夷集團太陽神話豐富、音樂藝術繁榮,并有自己的部族史詩、頌詩《韶》的流傳。《韶》是上古虞舜之樂,又稱《大韶》《韶箾》《簫韶》。《說文》曰:“韶,虞舜樂也。”《虞書》曰:“簫韶九成。”《周禮·大司樂》曰:“九韶之舞。”原始九韶是南方百越民族的巫歌,舜帝韶樂在其基礎上加工而成,并具有娛人、教化功能。該樂在《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古樂篇》《漢書·禮樂制》中均有記載。孔子于公元前517年在齊國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并評論其“盡美矣,又盡善也”。可以說《韶》樂是到目前為止可以基本考實的我國最早的一部區域民族史詩。
東夷集團以太陽為圖騰,以虞族首領帝舜(俊)為太陽神,能夠“使四鳥”和驅使虎豹熊羆,即是統帥以四種鳥和動物為圖騰形象的部落。古文獻中所描寫的《韶》樂就記載了這些內容。“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回答說:“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18]28“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18]50。這與《東皇太一》《東君》和《禮魂》祭祀太陽神的記載高度契合。“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25]52–53“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25]72–73。
在《韶》樂中有關東夷有虞族祖先崇拜的內容,在《九歌》中卻沒有保存。主要是因為長江下游東夷良渚文化已經灰飛煙滅,黃河下游東夷龍山文化后來演變為岳石文化,而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飛速進步,演變至王城崗龍山文化、新砦文化。表現形式便是中原華夏族的禹啟父子,破壞部落集團聯盟“禪讓制”,建立夏族“世襲制”。《韓非子》載曰:“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于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15]340
為了從根源上掌握參加聯盟的各氏族部落的神權、族權、兵權、政權,禹啟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鑄鼎象物”,鑄成“九鼎”,并將他們所崇拜祭祀的天體神靈與祖先神靈圖像鑄在“九鼎”上。禹啟通過宗教手段獨占了各族的兵器和生產資料及各族溝通神靈的權力,并特別針對有虞族奪取其“宗廟之典籍”,其中就包括《韶》樂。這個事實保存在“啟始歌《九招(韶)》”的神話傳說中。“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5]414。這是說夏后啟從天神那里得到《九辯》《九歌》,實際上是以神的名義宣布《九辯》《九歌》是夏族的祭歌頌詩,是夏族神權、族權和政權的象征。
“開焉得始歌《九招》”,肯定了兩點:(1) 始得《九招》說明夏族以前是不準歌舞《九招》的。(2) 既然啟從天神那里所得的是《九辯》《九歌》,那么人間歌舞也應該是《九辯》《九歌》。而《山海經》“開(啟)焉得始歌《九招(韶)》”說的是得到了虞樂《九韶》,而不是夏樂《九歌》。這顯然矛盾百出,不打自招,從而坐實了夏啟奪取虞族《韶》樂,又將其改造成《九歌》的事實。把《韶》樂中反映東夷族祭祀日月神的《東皇太一》《東君》保留在《九歌》中,就是夏啟奪取東夷有虞族《韶》樂而改造成《九歌》的直接證據。日月天神是天下共神,將夷族祭祀太陽神的內容及儀式據為己有,不算違背“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10]377的原則。于是“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原來的掠奪就變成天帝授予了。
實際上,《九歌》即《夏歌》《虬歌》,因為中原夏族以虬龍為圖騰。“禹,從九從蟲,九蟲實即句龍、虯龍也。句、虯、九,本音近義通。”姜亮夫、楊寬考證《九歌》之九實為虬龍之“虬”。世人不明就里,以為《九歌》之“九”是篇,今存《九歌》11篇,爭論不休。《韶》樂又稱作《九韶》實因《九歌》之影響而致。
《九歌·東皇太一》《九歌·東君》《九歌·禮魂》本身就是夷族的祭歌頌詩,是保存最早的原始宗教祭歌,其內容宗旨屬于東夷集團。考古學上的東夷分為黃河下游東夷和長江下游東(南)夷。黃河下游東夷地區先后創造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長江下游東(南)夷先后創造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這些考古學文化序列遺址中,有關太陽神崇拜的遺物蔚然大觀。良渚玉器上的太陽神形象,大汶口大陶尊上的日月山刻紋,龍山文化鳥形陶鬶和鳥足陶鼎太陽鳥圖騰等不勝枚舉。“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5]340;“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5]344;“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5]260。“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5]354;“有黑齒之國,帝俊(舜)生黑齒”[5]348,“有人曰鑿齒,羿殺之[5] ?372。”這些記載一方面說明東夷是崇拜太陽的民族,從地理上證明“湯谷”“扶桑”“十日”神話只能是東夷民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從帝堯時就開始了對東夷的戰爭。
下面再分析一下《東皇太一》《東君》和《禮魂》的唱辭。《東皇太一》是《九歌》中的首篇,是東夷祭祀春神的樂歌。前文我們說過,東夷一直信奉句芒為神,句芒就是春神、東方之神和農神,良渚玉器上普遍可見對句芒神的崇拜。《東皇太一》全詩分三節。首先寫春天良辰吉日,懷著恭敬的心情祭祀東皇太一,以使春神降臨人間,帶來萬物復蘇。“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25]51。其次寫祭祀場面宏大,祭品豐富,歌舞歡快。最后寫春神降臨。“偃蹇兮姣服”寫出春神外表動人,舞姿曼妙,“芳菲兮滿堂”昭示春神帶來了春天的氣息。祭祀的人們也滿心歡喜,鐘鼓齊奏,笙簫齊鳴,祭祀氣氛達到高潮。祭詩層次清晰、場面盛大、氣氛熱烈、描寫生動,充分表達了東夷先民對春神的敬重與歡迎,希望春神能夠賜福人間,給人類生命的繁衍和農作物的生長帶來福祉。《東君》是歌頌太陽神的祭歌。萬物生長靠太陽,東夷諸族對太陽神(日神)的崇拜和歌頌最虔誠,當然也最熱烈。“暾將出兮東方,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25]73–74《東君》篇中由一位覡扮演太陽神領唱,眾覡扮演觀者伴唱,開篇和結尾是對太陽神的想象,中間描述祭祀過程。太陽神駕著神車,從東方扶桑出發就是白天的開始。于是,見到了熱鬧隆重、鼓瑟鐘鳴的祭祀場景。夜晚,太陽神并未隨暮色回返,而是舉起長箭射去貪婪成性妄圖稱霸的天狼星,操起長弓防止災禍降臨人間,以北斗為壺觴,斟滿美酒,為人類賜福,然后駕車前進,直到第二天再次從東方升起。對于《禮魂》,人們有不同的說法:一是認為《禮魂》是十篇共用的“亂辭”,也就是說為前十篇祭祀各神的總送神曲;一是認為該歌詩是屈原對英雄祖先的祭祀,不屬九歌之列。筆者認為《東皇太一》和《禮魂》都屬祭歌,既然有迎神曲,那么肯定有送神曲,因而《東皇太一》就是迎神曲,《禮魂》就是送神曲。“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25]85《禮魂》由女巫領唱,男女青年隨歌起舞。全詩寥寥數語,卻將一個盛大的集會場面描繪得激越恢弘。
既然《九(虬)歌》原是指《夏歌》,那么它除保留《韶》樂中《東皇太一》《東君》《禮魂》等的內容外,也應有夏族自己的祭歌頌詩。《河伯》《云中君》便是夏族《虬歌》的遺存,也是夏族自己的祭歌頌詩。
“河伯”是黃河之神,商周之后被列為天子祭祀,稱為“河神”。“河伯”之名最早見于《莊子·秋水篇》。按照神話傳說,河伯原名“馮夷”,也稱“冰夷”。“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5]316中原部族一直在黃河流域,夏族繼承的也是黃河文化,因而河伯就是黃河之神,“與女游兮九河,沖風起兮水揚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25]75–76。“驂螭”即駕馭螭龍,“九河”即黃河,螭龍、黃河就是中原部族和夏的圖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為兮水中?”[25]76黃河神放蕩不羈,妻子是洛水女神宓妃,黃河沿岸曾有“河伯娶婦”的惡俗。詩歌以河伯洛神游戲情歌作為娛神祭辭。河伯本專指黃河之神,戰國時,人們將各水系河神統稱河伯。
《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辭賦。在我國古代神話故事中,云神名叫豐隆,又稱“屏翳”。馬茂之認為,“豐隆是云在天空中聚集的形象”。中原王朝一直崇拜云神,黃帝部落“云官而云師”,主要是中原夏族農耕生產祈求風調雨順。這首辭前半部分寫人們沐浴更衣,虔誠地迎接神的到來:“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25]54后半部分寫云神從云中來到人間,光芒遍及九州,蹤跡縱橫四海:“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云中。覽冀洲兮有余,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25]55“冀州,位于九州之中,即所謂中原地帶”,“正中冀曰中土”[26]312,“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5]430。郭璞注:“冀州,中土也。”“龍駕兮”“覽冀州兮有余”顯然是對中原夏族而言,應為夏族所祭祀的天體自然神。“極勞心兮忡忡”寫出了中原人民對云神的崇敬和膜拜。
屈原《九歌》中有《大司命》和《少司命》兩篇。司命神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均供奉,因此,這是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司命神的綜合祭歌。《湘君》《湘夫人》《山鬼》是長江中游東(南)夷人后裔楚地楚族流傳久遠的山川祭歌頌詩。《國殤》是楚國的愛國戰魂祭歌。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段沒有文字記錄的歷史。考古學者按照人類使用工具的器質,把人類早期歷史區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但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有一個明顯的玉器時代。東漢袁康《越絕書》引用戰國時代風胡子的話,認為傳說中的三皇時代是石器時代,從黃帝開始的五帝時代是玉器時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是銅器時代,春秋戰國進入了鐵器時代。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的《中國青銅時代》對《越絕書》的這個分期法給予了高度評價。然往昔言史者言史,說文者說文,考古者必發掘,究籍者曰考據,說陶瓷、青銅及玉器者更只是就物論物。本文從玉論史,以玉證史,兼及古籍、傳說、詩歌佐證。中國史前玉器固非中國史前文明之全部,卻是史前中國文明之精華。從玉器的起源傳承軌跡論及中華民族的融合過程,從考古學意義上的新石器時期之后,8000年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史,實際上就是眾多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文化不斷傳承融合與轉化創新的過程。先秦時期,由氏族部落林立到部族聯盟而逐漸形成多部族文化聯合體。從虞開始形成松散的諸侯邦國聯盟形式的國家王朝,與中原部族聯盟對峙。虞亡后進入中原東夷二頭盟主聯合執政,直到夏結束聯盟執政,過渡到商周。即使到周朝時仍為分封諸侯國聯盟體制。秦統一中國至漢以后,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在更大范圍內的民族碰撞對話中最終形成。
[1]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M].第7版修訂版.吳象嬰,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M]//古史辨自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3.
[4] 葉喆民.中國陶瓷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5] 袁珂.山海經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古本竹書紀年[M].濟南:齊魯書社,2010.
[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8] 黃懷信.鶡冠子匯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9] 劉斌,王寧遠,陳明輝.良渚古城考古的歷程、最新進展和展望[J].自然與文化遺產研究,2020(3):26–35.
[10] 左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2] 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會.石峁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4] 樊樹志.國史十六講[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5] 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8.
[16] 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84.
[17] 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M]//定庵續集:第2卷.光緒三年(1877)萬本書堂刻本.
[18] 尚書[M].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320.
[19] 國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78.
[20] 袁珂.中國神話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21] 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153.
[22] 禮記[M].胡平生,張萌,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23]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348.
[24] 詩經[M].王秀梅,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25] 屈原,宋玉,等.楚辭[M].吳廣平,譯注.長沙:岳麓書社,2004.
[26] 何寧.淮南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8.
K87
A
1006–5261(2020)05–0116–15
2020-04-10
李國忠(1963―),男,河南上蔡人,高級經濟師,碩士。
〔責任編輯 趙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