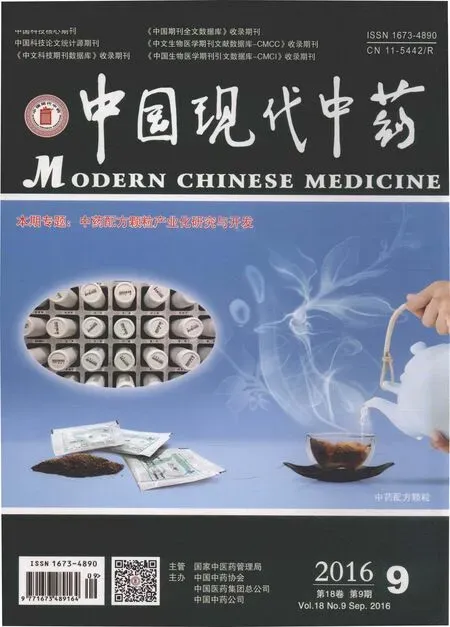高效氯氰菊酯在中藥材金銀花上的消解動態研究△
王鵬思,薛健*,王玉潔,金紅宇,馬雙成
(1.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藥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193;2.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北京 100050)
高效氯氰菊酯在中藥材金銀花上的消解動態研究△
王鵬思1,薛健1*,王玉潔1,金紅宇2,馬雙成2
(1.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藥用植物研究所,北京100193;2.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北京100050)
目的:研究高效氯氰菊酯在中藥材金銀花上的消解動態規律。方法:2014、2015年分別在山東平邑、河南封丘兩地進行田間試驗,采得的金銀花樣品經丙酮超聲提取,氣相色譜-電子捕獲檢測器(GC-ECD)檢測,外標法定量。結果: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消解曲線符合一級動力學方程,其半衰期為1.8~3.0d。在推薦劑量及3倍推薦劑量下,高效氯氰菊酯于第9天的消解率均高于90%。所采用的測定方法在0.10~0.20mg·kg-1的添加水平下,高效氯氰菊酯的平均回收率為93.1%~94.6%,相對標準偏差為4.9%~5.7%。最低檢出量為0.001ng。結論: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消解較快。本實驗建立的金銀花中高效氯氰菊酯的殘留測定方法簡便、快速、可靠,符合農藥殘留分析的要求。
金銀花;高效氯氰菊酯;消解動態;中藥材;氣相色譜
金銀花為忍冬科植物忍冬LonicerajaponicaThunb.的干燥花蕾或帶初開的花。夏初花開放前采收,干燥。金銀花性寒,味甘。歸肺、心、胃經。具有清熱解毒,疏散風熱的功效。用于癰腫疔瘡,喉痹,丹毒,熱毒血痢,風熱感冒,溫病發熱[1]。作為大宗常用中藥材之一,金銀花在我國分布較為廣泛,北起遼寧,西至陜西,南達廣西北部,西南至貴州、云南各省區均有栽培,道地產區為山東平邑和河南封丘[2]。在金銀花的種植過程中,金銀花植株的蟲害種類較多,主要的有蚜蟲、木蠹蛾類、尺蠖和天牛等4種[3-4],其中蚜蟲的危害最為嚴重和常見,且其發生時間正值金銀花植株花期,由于農民分散種植,農藥使用不合理,導致金銀花植株和環境的嚴重污染,使金銀花藥材的農藥殘留嚴重超標,大大影響了藥材的品質[5]。
高效氯氰菊酯是一種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生物活性較高,是氯氰菊酯的高效異構體,具有觸殺和胃毒作用。其殺蟲譜廣、擊倒速度快,殺蟲活性較高[6]。在防治金銀花蚜蟲危害中被普遍使用且效果良好,但是由于沒有相應的“農藥使用規范”,在市售金銀花中有高殘留檢出[7],這嚴重威脅到人民用藥安全,更影響到金銀花出口至國外市場,因此備受消費者和各級政府的關注。為保障人民用藥安全,打破金銀花出口瓶頸,本課題組對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消解動態進行了研究,以期為其在金銀花上的合理安全使用提供基礎數據。
1 材料與方法
1.1材料
供試作物:金銀花。
供試農藥:高效氯氰菊酯(4.5%乳油,山東科大創業生物有限公司),購自北京市植物保護站。
主要儀器:Agilent6890N氣相色譜儀(配μ-ECD檢測器),色譜柱為毛細管色譜柱(AgilentDB-1701,30m×0.32mm×0.25μm),載氣為高純氮氣(純度≥99.999%,北京氦普北分氣體工業有限公司);LABOROTA4000/4型旋轉蒸發器(德國海道夫);Feb-80型離心沉淀器(金壇市醫療儀器廠);SB-5200DT超聲波清洗機(寧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主要試劑:高效氯氰菊酯標準品溶液(農業部環境保護科研監測所);正己烷(色譜純,FisherChemical公司);石油醚(60~90℃)、丙酮均為分析純(北京化工廠)等。
1.2方法
1.2.1田間試驗與樣品采集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所頒行業標準《農藥殘留試驗準則》(NY/T788-2004)[8]進行田間試驗設計。試驗地2014年設在山東平邑,分別設置推薦劑量(29.7g·hm-2)、三倍劑量(89.1g·hm-2)、空白對照三個處理,每個處理三個重復小區,每個小區面積為15m2,小區內種植3年生金銀花6株,小區間設置1.5m隔離行。2015年試驗地設在河南封丘,試驗方法與2014年相同。
在金銀花花蕾初期蚜蟲發生時,對每個小區進行噴霧施藥,并于施藥后2h,1,2,3,4,5,7,9,11,13,15d后隨機采集金銀花花蕾。新鮮花蕾于40℃殺青4h后,55℃烘干10h,干燥后于-20℃低溫冰箱中保存待測。
1.2.2樣品前處理
①粉碎:金銀花粉碎后過2號篩(24目,850μm±29μm),粉碎順序從采樣日期最大(15d)開始,依次遞減至施藥2h。
②提取:準確稱取2.0g樣品置于100mL具塞錐形瓶中,加入丙酮30mL,超聲提取15min(300W,40kHz),過濾,濾渣重復上述操作兩次,合并三次濾液于100mL梨形瓶中,將濾液于40℃水浴中旋轉蒸發濃縮至近干,轉移至5mL具塞試管中,用石油醚定容至4mL,混勻,離心15min,取上清液進行測定。
1.2.3色譜測定AgilentDB-1701毛細管色譜柱(30m×0.32mm×0.25μm);升溫程序:200℃保持2min,以12℃·min-1升溫至260℃,保持20min;進樣口溫度為250℃;載氣為高純氮氣,流速1mL·min-1;檢測器溫度為300℃;進樣量為1μL,不分流進樣。高效氯氰菊酯標準品溶液和樣品溶液色譜圖見圖1。

注:1、2、3、4為高效氯氰菊酯的4個立體異構體圖1 高效氯氰菊酯標準溶液(A)和金銀花樣品溶液(B)的氣相色譜圖
2 結果與分析
2.1提取溶劑的選擇
根據高效氯氰菊酯的溶解特性并查閱參考文獻[9-14]后,本實驗采用直接添加法對丙酮、丙酮-石油醚(1∶1)、石油醚共3種提取溶劑體系進行比較。3種溶劑體系在0.20mg·kg-1的添加水平下平均回收率結果分別為94.5%、67.7%、62.2%,在0.50mg·kg-1的添加水平下平均回收率結果分別為101.9%、88.5%、67.0%。實驗結果見表1。由表中數據可知,在兩個添加水平下,丙酮的平均回收率均為最高,故本實驗選用丙酮為最優溶劑。

表1 三種溶劑體系提取金銀花中高效氯氰菊酯的回收率考察(%,n=4)
2.2方法學考察
2.2.1標準曲線及最低檢出量 分別精密量取高效氯氰菊酯標準品溶液(1.0×10-6g·mL-1)1mL,0.5mL,0.25mL,0.125mL,0.05mL,定容至5mL,則得濃度為200、100、50、25、10μg·mL-1的標準品溶液。按1.2.3節的條件測定,以高效氯氰菊酯標準溶液的濃度X(g·mL-1)為橫坐標,以其色譜峰面積Y為縱坐標,繪制標準曲線,得到其標準曲線方程為:Y=76.47X+393.62,r=0.9994。表明高效氯氫菊酯在10~200μg·mL-1范圍內線性良好。以3倍信噪比(S/N=3)計算,儀器的最低檢出量為0.001ng。
2.2.2準確度和精密度 參考氣相色譜對高效氯氰菊酯標準品溶液的響應情況,以及GB2763-2014中高效氯氰菊酯的最大殘留限量,設置0.10mg·kg-1和0.20mg·kg-1兩個添加水平,每個水平做5次平行實驗。分別量取濃度為0.10μg·mL-1和0.20μg·mL-1的高效氯氰菊酯標準品溶液2mL,精密量取,加至2.0g金銀花空白樣品中,制作農藥添加樣品。按照1.2.2中的提取步驟及1.2.3的色譜條件進行測定,計算加標回收率和相對標準偏差,結果見表2。

表2 金銀花中高效氯氰菊酯的添加回收率(%,n=5)
由表2可知,在0.10 mg·kg-1添加水平下,高效氯氰菊酯的回收率為88.0~101.6%,RSD=5.7%;在0.20 mg·kg-1添加水平下,高效氯氰菊酯的回收率為86.6~96.4%,RSD=4.9%,能達到NY/T 788-2004對添加水平在0.1~1 mg·kg-1范圍內的回收率(70~110%)和相對標準偏差(RSD≤15%)的要求,此方法可行。
2.2.3 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中的消解動態 田間試驗和樣品采集按1.2.1節的方法進行,共獲得噴藥后不同時間金銀花樣品132個,按照1.2.2節的提取方法和1.2.3節的測定方法檢測樣品,同一個處理的三個小區結果取平均值,得到不同采樣時間金銀花上殘留量,將高效氯氫菊酯的殘留量與時間擬合,得到的消解動態曲線見圖2,消解動態方程見表3。實驗結果表明,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中的消解動態符合一級動力學降解模式。

表3 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殘留情況

注:■為2014年山東三倍劑量小區;●為2015年河南三倍劑量小區;◆為2014年山東推薦劑量小區;▲為2015年河南推薦劑量小區圖2 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消解動態曲線
3 討論
3.1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消解特征
由以上的實驗結果可以看出,2014年山東平邑金銀花上推薦劑量和3倍劑量高效氯氰菊酯的半衰期分別為2.0d、1.8d,2015年河南封丘金銀花上推薦劑量和3倍劑量高效氯氰菊酯的半衰期分別為3.0d、2.7d,兩年兩地推薦劑量和3倍劑量高效氯氰菊酯的半衰期分別相差1.0d、0.9d,可見同一農藥即使在相同作物上,其半衰期也會受到時間、地點、溫度等因素的影響。此外,與報道過的高效氯氰菊酯在其他類作物(枸杞[15]:5.2~6.5d,大棚西芹[16]:6.93d)上的半衰期相比,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消解較快。
3.2高效氯氰菊酯在金銀花上的安全使用建議
目前我國對金銀花中高效氯氰菊酯的最大殘留限量(MRL)尚無規定,日常生活中,金銀花常以茶飲和湯藥形式攝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5版[1]規定金銀花最大用量為15g。鑒于金銀花的主要攝入途徑和特點,可參考GB2763-2014[17]中規定的韭菜和蕓薹類蔬菜(結球甘藍除外)的MRL值(1.0mg·kg-1),按推薦劑量使用,建議高效氯氰菊酯的安全間隔期定為9d(消解率大于90%,殘留量低于1.0mg·kg-1),如果以3倍內劑量或推薦劑量使用三次以上,安全間隔期至少要15d以上,以此類推。
[1] 國家藥典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S].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5:221.
[2] 張芳,張永清,馬燕,等.河北產不同等級金銀花藥材脂溶性成分的GC-MS分析[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2013,19(11):58.
[3] 農訓學.金銀花病蟲害的防治[J].特種經濟動植物,2005,8(5):43.
[4] 施仕勝.金銀花主要病蟲防治[J].廣西植保,2004,17(4):20.
[5] 張文玉.不同種類農藥防治金銀花植株蚜蟲的研究[D].濟南:山東中醫藥大學,2006.
[6] 張鋒鋒,姜 瑞,牛 艷.寧夏枸杞中高效氯氰菊酯殘留的風險評估[J].安徽農業科學,2014,42(34):12104-12106.
[7] 金紅宇,王瑩,蘭鈞,等.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測定金銀花中192種農藥多殘留[J].中國藥學雜志,2012,47(8):613-619.
[8]NY/T788-2004農藥殘留試驗準則[S].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
[9] 刁傳蕓,任曉萍,藺 經,等.梨中氯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殘留動態分析[J].江蘇農業學報,2008,24(5):697-698.
[10] 高天兵,張曙明,田金改.三七、白芍及西洋參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的殘留量測定[J].藥物分析雜志,1999,19(5):314-315.
[11] 丁蕊艷,李瑞菊,陳子雷,等.氣相色譜法測定棉籽中高效氯氰菊酯殘留[J].山東農業科學,2012,44(8):116-118.
[12] 單娟,姚國旗,王文博,等.氣相色譜法測定玉米中的高效氯氰菊酯殘留[J].山東農業科學,2010,42(6):98-100.
[13] 黃向麗,傅曉雪,陳章寶.草魚體內氯氰菊酯殘留GC-ECD測定[J].現代農業科學,2009,16(3):71-72.
[14] 楊林飛,胡卓,羅建平,等.氣相色譜法同時測定蔬菜中百菌清、甲氰菊酯、氯氰菊酯及溴氰菊酯類農藥殘留[J].河南預防醫學雜志,2012,23(1):17-18.
[15] 張艷,吳燕,王曉菁,等.枸杞中高效氯氰菊酯的殘留動態研究[J].中國農學通報,2012,28(13):239-242.
[16] 周世萍,段昌群,劉宏程,等.氯氰菊酯在大棚西芹上的降解殘留研究[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06,25(2):482-485.
[17]GB2763—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14.
DegradationDynamicsofBetaCypermethrininHoneysuckle
WANGPengsi1,XUEJian1*,WANGYujie1,JINHongyu2,MAShuangcheng2
(1.InstituteofMedicinalPlantDevelopment,ChineseAcademyofMedicalScience&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Beijing100193,China;2.NationalInstitutesforFoodandDrugControl,Beijing100050,China)
Objective:The purpose was to study degradation dynamics of beta cypermethrin in Honeysuckle.Methods:Field experiments were respectively carried out in Pingy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in2014and Fengqiu County Henan province in2015.The collected honeysuckl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by acetone with ultrasound assistance,detected by gas chromatograph with electronic capture detector (GC-ECD) and determined by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Results:Degradation curves of beta cypermethrin in Honeysuckle conformed to the first-level dynamic equation.The half-life of degradation of beta cypermethrin was1.8-3.0d.At the recommended dose and3times the recommended dose,the digestion rates were both higher90% on the ninth day.At fortified levels of0.10-0.20mg.kg-1,the adopted method’s average recoveries of beta cypermethrin in the Honeysuckle were93.1%-94.6%,with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being4.9%-5.7%.The limit of detection was estimated to be0.001ng.Conclusion:The degradation rate of beta cypermethrin in the Honeysuckle was relatively quick.The method created in this experiment was not only simple,rapid and reliable but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esticide residue analysis.
Honeysuckle;beta cypermethrin;degradation dynamic;Chinese herbal medicines;gas chromatography
10.13313/j.issn.1673-4890.2016.9.022
2016-03-02)
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中藥質量安全檢測和風險控制技術平臺(2014ZX09304307-002)
*
薛健,研究員,研究方向:中藥成分分析及農藥殘留重金屬研究;Tel:(010)57833097,E-mail:xuejian20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