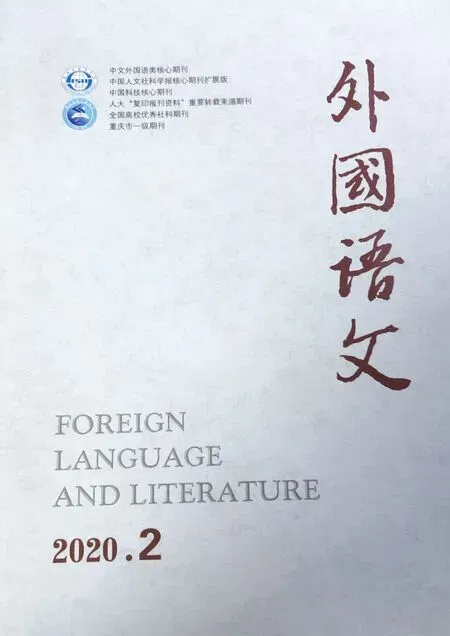實至名歸
——格里美爾斯豪森《癡兒西木傳》
李昌珂 景菁
(1.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871;2.慕尼黑大學 德國 慕尼黑)
李昌珂,1977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法德系德語專業,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浙江科技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全國翻譯資格(水平)考試專家委員會德語副主任委員。主要學術代表作有:《德國文學中國題材小說》,獲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馮至德語文學研究獎”一等獎;《德國文學史》(第5卷),獲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和中國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我們這個時代”的德國——托馬斯曼長篇小說論析》,獲北京大學第十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1 德語經典之作
16世紀中葉,西班牙費利佩王朝末期,西班牙社會“經濟開始衰敗,大批拋棄土地、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淪為無業游民,此外還有眾多的從戰場上傷殘而歸的貧窮的士兵,這些人很難靠勞動糊口和安分守己地生活。他們養就了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毛病。而且當時社會上冒險的風氣盛行”(沈石巖,2006:58)。這個背景下,一部世界名著應運而生,問世后即在讀者群中風靡,在西班牙和其他歐洲國家引發了模仿潮,對西班牙文學和歐洲其他國家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這部作品就是《小癩子》(LaVidadeLazarillodeTormes)(1)這部小說原名為《托爾梅斯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佚名,是一部描寫一個潑皮流浪漢在社會底層討生活的流浪漢小說。
德國人自創的流浪漢小說也陸續面世,其中最負盛名的便是漢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夫·馮·格里美爾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約1621—1676)的《癡兒西木傳》(DerabenteuerlicheSimplicissimusTeutsch, 1669)。該作最初以筆名發表,問世后很長時間內人們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誰。該小說曾風行一時,后遭時間冷落,湮沒了一百多年后被浪漫派作家重新發掘,傳世至今,成為世界文學一部名著。歌德推許它比18世紀的著名小說還要更勝一籌。托馬斯·曼讀后有感:“這是一座極為罕見的文學與人生的豐碑。它歷經近三百年的滄桑,依然充滿生機,并將在未來的歲月里更長久地巍然屹立;這是一座具有不可抗拒魅力的敘事作品,它豐富多彩,粗野狂放,詼諧有趣,令人愛不釋手,生活氣息濃厚而又震撼人心,猶如我們親臨厄運,親臨死亡。它的結局是對一個流血的、掠奪的、在荒淫中沉淪的世界徹底的悔恨與厭倦。它在充滿罪孽的、痛苦悲慘的廣闊畫卷中是不朽的。”(格里美爾斯豪森,2004:譯本序2)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杰拉德·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推崇它為一部“把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廣博的教育小說、流浪漢小說、塞萬提斯式的幽默、法國諷刺模式以及象征性旅行等各種敘事形式鑄為一爐”(杰拉德·吉列斯比,1987:129) 之作。我國學者贊許它“顯示了日耳曼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潛能”(蹇昌槐,1995:102)。
2 戰爭罪惡敘事
《癡兒西木傳》全書結構分為五卷,以一成不變的、有時還直接向讀者打招呼的第一人稱“我”敘事。主人公“我”是個孤兒,從小被偏僻農村農戶收養,沒有受過文化教育,少不更事,懵懵懂懂。小說開篇段落,格里美爾斯豪森巧妙利用“我”對世界的一無所知,寫“我”把自家茅屋贊美得勝過皇宮,“我敢說,任何一位皇帝,即使他比亞歷山大大帝更有權力,也不可能親手蓋成這樣一座宮殿,他不半途而廢才怪呢”(格里美爾斯豪森,2004:3)。把他阿爸的農事勞作比喻成猶如貴族、騎士的消遣式、尚武式生活:“在兵器和盔甲庫里,各種犁耙、釘耙、鋤頭、斧子、鏟子、糞叉、草杈塞得滿滿的,裝飾得漂漂亮亮的。我的阿爸每天都擺弄這些兵器。鋤地、墾荒是他進行的軍事演習,就像古羅馬人在和平時期所干的那樣。給牛套車是他作為司令員所下的命令, 運糞是他的防御加固措施,耕種土地是他進行的戰役,劈木柴是他每天的體格鍛煉。”(4)在文學本體上既把一種流浪漢小說典型的廣場吆喝式語言帶入了敘事,在人物描寫上又表明“我”是個智力低下、不明事理的“傻角”。“30年戰爭”來了,養父母農莊被毀,“我”逃進森林,遇一隱士,被其收留。隱士見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便管他叫“癡兒西木”,教他識字和寫字,還教他祈禱、基督教教義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兩年后隱士辭世,西木獨自在森林里生活了半年,被亂兵洗劫了窩棚,沒了糧食和衣物,只得去外面世界尋找果腹之物。在哈瑙,西木被瑞典士兵抓住,帶到了司令官那里。司令官見西木呆頭呆腦,不諳世事,了無心機,還會識字,便留下他當侍童。西木離開森林后的流浪經歷由此開始,小說故事主線便是西木的流浪。
同樣是流浪漢經歷,作者可以寫流浪者不同的命運,來自西班牙的那部《小癩子》講述的就是一個窮苦流浪兒的故事。《癡兒西木傳》中的西木流浪,很多是以作者格里美爾斯豪森自己的人生經歷為藍本。研究表明,西木的流浪遭遇在小說“第四卷之前幾乎與作者經歷一致”(格里美爾斯豪森,2004:譯本序2),說明格里美爾斯豪森在用文學解他的人生之惑,或疏他的心中郁積。格里美爾斯豪森把自己人生經歷作為小說最核心的寫作資源,不是出于一個作家要表達自我的本能動機,而是因為戰爭是西木流浪的原因,格里美爾斯豪森起筆寫這部小說就是拜戰爭的獸性所賜。《癡兒西木傳》故事的起點就是戰爭,敘事從“30年戰爭”這個歷史關口切入,敘事的開頭就散發著兵燹氣息。小說開篇不久,敘事講述西木被一隊騎兵圍住,西木感覺這些人就是他阿爸時刻在告誡他一定要避而遠之的“四條腿的流氓和強盜”(11),但是天真幼稚的他還是將這些騎兵帶到了他阿爸的莊園。隨即就發生了那些兵匪搜掠搶劫、毀滅村莊、奸淫婦女、施虐雇工之事:
這幫騎兵在我阿爸四壁烏黑的屋子里開始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們的馬牽進馬廄;然后,他們各干各的勾當,樁樁件件無一不是肆意破壞和糟蹋。……我家的使女在牲口棚里給他們折磨得那樣厲害,她再也走不出來了,她被糟蹋了!那雇工,他們把他捆倒在地,往他嘴里塞進一塊木頭,灌了他滿滿一大桶臭糞水;他們把這叫作瑞典飲料……(12-14)
“30年戰爭”期間德國人慘遭荼毒,在第一人稱敘事者那善于觀察的視角和善于細致的講述中重構,呈現在讀者眼前。“我”的講述將讀者帶進猝然降臨的兵災,“我”看見什么就說什么的直白語言大大加強了士兵暴行的兇狠殘暴維度。“我”還特地申明,意愿上他“并不想把愛好和平的讀者和這些兵痞暴徒一起帶進我阿爸的莊園——因為那里發生的事情簡直是糟糕透頂,然而我這部故事的發展卻要求我這樣做。為了讓親愛的后代知道,在我們德國這一次戰爭中,常常發生了一些多么恐怖而駭人聽聞的事情”(12)。將戰爭的動亂記錄下來,讓后來的人們了解和記住“30年戰爭”使德國遭受的災難,很顯然就是格里美爾斯豪森為他的這部小說確定的一個基本敘事觀。
接下來的敘事中,戰爭的罪惡在疊加,平民百姓遭到的戰亂蹂躪在加劇。戰爭敘事的下一個畫面,是殘暴的士兵殘忍地折磨和殺戮農民,子彈沒有打中的就把他們的鼻子和耳朵割下來,“用短刀把農民從頭頂到牙齒劈成兩半”(44),暴行和戕害的動作刺激著讀者感觀,那濃濃的血腥氣似乎仍在強烈嗅出。再次遭遇兇狠士兵的西木于饑寒交迫中昏昏睡去,進入一個夢境:
好像我家周圍的樹一下子都變了樣,外表和原來的完全不同了。每棵樹的頂上都坐著一個騎士,樹枝上長的不是樹葉,而是裝飾著各式各樣的士兵:他們或持長矛、或拿火槍、或短銃、或短刀、或小旗、或鼓、或號、或笛。都那么井井有條地漸次分列兩邊,煞是好看有趣。樹根周圍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手工業者、雇工,大半是農民以及諸如此類的人。他們盡管地位低賤,卻給大樹增添了力量。當大樹欲枯欲傾時,他們便再竭已而輸,注以生氣,用消耗自己來補足大樹因落葉而造成的空乏,致使自己遭受更大的損害。他們朝著坐在樹上的人嘆息,實在并非無病呻吟,因為大樹的全部重量都壓在他們身上,把他們口袋里的錢,甚至連七道鎖鎖著的錢都壓出來了。誰要是不交出錢來,那么司令官就用毛刷去刷他們,這叫作軍法處置。他們只能從心底里發出嘆息,從眼睛里滴出淚水,從指甲里滲出鮮血,從骨頭里流出骨髓……(45-46)
這個夢是小說敘事的一個機關,西木夢見的“戰爭之樹”既是意象也是象征。夢境中的“戰爭之樹”在構建一個情勢框架,其樹上、樹下與四周參差交錯的關系結構將騎士與士兵、城市與農村、手工業者與農民、雇工與小丑、社會下層的人、底層的人與社會上層的人網羅到一起。這個意象看上去比較荒誕,卻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錄,在最真實的意義上表達了對戰亂年代社會情形和生活命運的認知,格里美爾斯豪森用荒誕的筆觸挑開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圖像:動蕩年代地方武裝風涌,各種勢力拉鋸,“草頭王”橫行,到處是毀滅別人和被別人毀滅的雇傭兵現象。
小說第五卷里,格里美爾斯豪森寫了一段話:西木成了香客,跟著朋友去朝圣,到達一個村莊,看到的安然生活情形讓他產生了仿佛置身于“巴西或中國”的感覺。“我看到百姓們安居樂業, 廄舍里滿是牲畜, 場院里雞鴨成群, 街市上游人熙攘, 酒店里賓客滿座,盡在尋歡作樂。這兒完全不存在對敵人的恐懼和對搶劫的擔憂,根本不必為生命財產的安全而牽腸掛肚;人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無花果下生活得無憂無慮。與其他德語國家相比,這里是一片歡樂和愉快的景象,以至于我把這塊國土看作是人間的天堂。”(389-390)西木的這段感言,與混亂年代人們無比盼望和平的內心期冀不無關系。格里美爾斯豪森這樣“美化”中國,不是在對中國投以敬意,而是在以對中國的理想想象寄托戰亂年代人們祈望太平的內心訴求。
3 生存處境的升降沉浮
“戰爭之樹”夢境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上又是格里美爾斯豪森拋給讀者的一段預示,西木那時一會兒是寵侍, 一會兒是跟班,一會兒是命運的寵兒,一會兒又立即變成倒霉鬼的后來際遇,就在這個夢境敘事里已經被預示。西木被戰爭推出生活正常軌道拽入流浪命運后,小說情節在向世道野蠻和荒謬方向發展,講述西木的生存處境被推向了變幻無常的升降沉浮。流浪已是敘事的樞紐,西木生存處境的升降沉浮又是樞紐的樞紐。流浪中西木的生存處境不時經歷著變幻無常的升降沉浮,表面上看是因為西木作為一個下人的粗俗與所謂“正派人”的雅致大相徑庭而遭殃,或是因為西木的天真單純而被人當作是可以任意作弄的蠢貨,背后則是在沒有是非、沒有法制、沒有公理、沒有人權的動亂年代,弱者只能是賠著笑臉接受強者欺辱,人們靈魂深處充滿荒唐的寫照。
被抓進軍隊后,西木生存處境的沉浮便又一次次地開啟。戰爭罪惡畫面描述退到后面,格里美爾斯豪森的敘事策略著意挖掘流浪漢小說敘述模式的“低品”審美,以通俗趣味的講述讓讀者去體驗西木生存處境的升降沉浮,達到的效果越是通俗趣味,西木生存處境的無可奈何就越是彰顯。通俗趣味與無可奈何兩者配合,又生成出第三層意思來。小說第一卷第27章中,西木正對一件讓他感到很是好笑的事開心說笑,于無意中放了個臭屁,頓遭書記官謾罵,把他趕進豬圈,要他從此同豬睡在一起,他原來在寫字間干活的好差事也由此“一下子給斷送了”(85)。臭屁在這里制造了一種讓人預料不到的“笑”,似乎褻瀆了生活的斯文,但真正讓斯文掃地的則是自稱“正派人”的書記官瞬間變成了惡人。“正派人”表面上的恂恂文明和高貴優雅在這里通過臭屁引發的“笑”遭到了民間狂歡式顛覆。
那件讓西木感到非常可笑的事,是一本記載官銜的名稱簿落到了他的手中。在西木看來,“這本名冊里所寫的盡是荒謬絕倫的東西,簡直是我至今從未見過的”,“人所共知的事實是,沒有任何人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沒有任何人是從水里冒出來的,也沒有任何人是像白菜那樣從地里長出來的。為什么只有至尊老八、至貴老八、至高老八、至大老八,而沒有老九呢?或者說那老五、老六、老七在哪兒呢?”,“倘若高貴這個字眼本身的意思不是別的,而是指極高的德行,那么為什么當這個字眼被授予那些出身高貴的人們,即公爵或伯爵時,反而會降低這些爵位的等級呢?出身高貴這個字眼完全是無稽之談,每個男爵的母親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有人問她在生她兒子的時候是什么樣子的話”(84)。仿佛是“傻話”連篇,實卻充滿了皮里陽秋、諫果回甘的滋味,邃使滑稽解構“高貴”的反諷的“笑”又在此產生。尤其是“如果有人問她在生她兒子的時候是什么樣子的話”這句時,把小說的“低品”形態寫到了粗俗鄙下的程度,也把對貴族“高貴”的“笑”推到了讓人啼笑皆非的高度。
小說第二卷幾個篇章,寫西木還是司令官身邊侍童,因單純無知,對一對男女偷情之事說了真話,“她把裙子撩起來,沖著他……要拉屎”(108),便被司令官決定剝奪他的全部智力,要他去當小丑,是西木生存處境在瞬間升降沉浮的又一次寫照。格里美爾斯豪森善用西木的粗話臟話,也善用流浪漢小說夸張、怪狂、畸形的表現形式,將西木被送去當小丑的情節寫得乖僻和暴戾,講述西木被人裝神弄鬼和毒打折磨,為的是要將他本就顯得愚鈍的智力掃蕩干凈,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傻呵呵的癡兒。毒打折磨后西木被穿上新鮮的牛皮,戴上牛角,要他裝扮成一頭會說人話的牛犢供人取樂。一句看似開導西木的話道出:“如今的世界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牲畜和人之間的區別已經很小了;難道你就不愿意跟著一起干嗎?”(118)或許是最早在德國小說中道出這樣的信息:時代混亂,萬事顛倒,人已淪為非人。西木自己也寬慰了自己一句,“我先前曾親眼看見,有些人怎樣比豬更骯臟,比獅子更兇殘,比羊更淫蕩,比狗更下賤,比馬更放浪,比驢更粗魯,比牛更貪飲,比狐貍更狡猾,比狼更貪婪,比猴更愚蠢,比蛇蝎更狠毒,他們卻全都享受著人的飲食,只不過在外表上區別于野獸而已,而在清白方面還遠遠不如一頭牛犢呢!”(118)逼真地道出混亂年代的世相荒謬和冷酷。
4 流浪漢小說的社會諷喻
對戰亂年代洞若觀火,流浪漢小說模式的社會嘲諷也充分到位。不論是對周圍人的一個個幽默嘲諷,還是發生在吝嗇房東與機智寄宿者段落中的暴露不健康心理的自嘲,還是西木被當作一個姑娘遭遇危險時的調情,還是與教士討論信仰問題而把教士玩弄于股掌之中……審丑或激惡,都是對混亂時代社會上出現的各種頹敗流弊的一種指陳。先前,西木那未諳世事的純潔稟性的瞳孔看不懂他周圍人的舉止。他周圍的人在他這個“癡兒”面前也毫不掩飾,將他們行為上的種種輕浮、色欲、物欲、反常、顛倒統統表現出來讓他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我目睹這些賓客的盛宴,其聲像豬,其飲如牛,其狀像驢,到最后嘔吐起來就像癩皮狗。他們用圓桶般的杯子往肚子里灌下那霍赫哈埃姆、巴赫拉赫和克林根貝爾格產的名酒,這些酒也就立即在他們的頭腦里施展出自己的威力。于是我看到了叫人目瞪口呆的情形。”(89)后來,西木已從一個淳樸的“傻瓜”變成了一個聰明的“傻瓜”,發現自己被人當作傻子而因此獲得了“傻子的自由”,有把天然的保護傘, 可以嬉笑怒罵放言無忌,以看似傻了吧唧的荒腔走板將那些涂脂抹粉的假正經、假正派、自以為是、自作聰明的真正傻瓜一一卸裝。“從現在起,人人都管我叫小牛。我也對每一個人報之以特殊的諷刺性的綽號……人家把我當作一個不開竅的蠢貨,我則把人家視為自作聰明的傻瓜……干脆說吧:到處都是蠢人!”(117)“到處都是蠢人”的斷言留給讀者一個回味的觀察空間,小說很多筆墨描述西木裝得傻里傻氣,盡情扮演他的讓人取樂角色已不是閑筆。如下面對話中,西木就以他不懂時髦的“傻”諷刺了上層社會以來自法國的時尚為追逐對象的虛浮頹靡風氣:
“什么?”主人表示驚訝,“難道你以為,這些夫人都是猴子嗎?”我回答:“如果她們現在不是,那么她們很快就會變成猴子的。誰知道事情會怎樣呢?事先也沒料到,我會變成一頭牛犢,可現在不是變了嗎?”主人問我,何以見得,這些夫人會變成猴子。我答道:“猴子的屁股都是光光的,這些夫人也袒露著胸脯,而其他姑娘總是把胸脯遮蓋著的。”“你這個劣種,”主人罵道,“你真是一頭蠢牛,像你這樣的家伙也只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這些夫人是讓人欣賞她們身上值得欣賞的部位,而猴子是因為沒有衣裳才赤身露體的。趕緊彌補你犯下的過錯吧,否則你就要挨揍了,讓狗再把你趕回到鵝圈里去,就像我們對付不知好歹的牛犢那樣。聽著,你究竟還懂不懂贊美一位理應受到贊美的夫人?”……“這位小姐頭發黃黃的,如同小孩子的糞便;她的頭路又白又直,好像用豬毛刷子在皮膚上刷過一般;當然,她頭發卷得很漂亮,看起來好像空心的笛子,或者說好像兩旁掛了幾磅蠟燭,或者一打烤腸。啊,你看,她那鼓鼓的額頭多么漂亮,多么光滑啊,難道它不比一個肥胖的屁股更好看,比一個風干多年的死人面孔更白嗎?十分遺憾的是,她細嫩的皮膚被發粉弄得太臟了,如果讓不知道發粉的人看到,一定會以為這位小姐得了疥癬病了,頭上才有那么多的頭皮屑呢!”(123-124)
符合西木“傻瓜”標簽的民間語言,不雅不潔、粗鄙放誕,形成與流浪漢故事文本吻合的本色感。粗俗粗糙的“傻瓜”語言營造的粗話、怪話、臟話、滑調和油腔,張猛淋漓,上下位移,藏著玄機,意味深長,在小說中寫得浩浩蕩蕩,酣恣筆端,足見格里美爾斯豪森在修辭方面的功力。它們一詞一句褒貶相依,抑揚互換,明褒實貶,一石二鳥,讀起來不疲勞,想起來有味道,尤覺新穎別致,深得流浪漢小說語言運用上活潑恣肆、不拘粗鄙的精髓,小說由此很有流浪漢小說獨有的氣味和魅力。詼諧機敏又毫不留情的“笑”是《癡兒西木傳》的一種標志性建構。通過建構這種諷刺性的“笑”,格里美爾斯豪森在上面那段西木與他伺候的主人的對話里狠狠地諷刺了上層社會對外國摩登的趨之若鶩習氣,不僅是因為在其中看到內在的俗氣和本質的輕浮,更因為看到如此“崇洋媚外”、分裂而弱小的德意志帝國將有喪失其政治上的主體性或者說獨立性的危險,故而憂慮而調笑。
5 德意志民族心態
格里美爾斯豪森為何要讓他筆下的這部小說涵納他自己,但同時也包含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愿望表達,小說第三卷第三至六章中出現的那個高談闊論的尤韋,就承擔著這個表達愿望。這個尤韋滔滔不絕地大講特講要“喚醒一位德國英雄”,對這位德國英雄有著十分明確的政治期待:品質高尚,身體力行,將不惜南征北戰,“用銳利的劍鋒來完成一切事業;處死所有的惡人,保存并提拔那些虔誠的人們”,將使得“所有的大城市都將在他面前顫抖”,將讓“任何堅不可摧的要塞都將在頃刻之間俯首帖耳地聽從他的支配;最后他將支配世界上最偉大的統治者,并且對海洋和陸地進行令人嘆服的治理,使神和人兩方面都能稱心如意”(224),將攘奪王公貴族的權利,推行民主體制,“從全德國的每一座城市里挑選出兩名最聰明、最有學問的人,由他們組成議會,使各個城市之間永遠和好聯合;農奴制連同一切關稅、稅收、地租、債據、捐稅在全德國都要廢除;要使百姓們不再遭受苦役、哨役、戰時特別稅、捐款、戰爭,或者其他負擔的痛苦”(225),還將統一宇內,征服整個世界,由他來對附屬國、臣服國的帝王加冕頭冠,分封土地,“然后就將像奧古斯都大帝時代那樣,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當中出現永恒持久的和平”(227)。在外族入侵國事日蹇,戰爭和戰亂就在德國土地上發生的時代,格里美爾斯豪森卻借善說者尤韋之口想象著一個強大起來的德國如何重塑世界秩序,這里面除了祈盼太平的烏托邦精神,大德意志民族心態和愿望也起著相當的作用(2)由于“30年戰爭”展露無遺地使德國人看到了長期分裂的德國之弱小和無力,激發了社會上一波又一波的愛國主義強烈愿望,致使民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色彩的思想在當時非常流行。格里美爾斯豪森顯然也是受此裹挾。。
6 時代混亂的反映
當然,“喚醒一位德國英雄”只是小說的一個敘事點,整體上,格里美爾斯豪森十分穩定地把握著要反映混亂時代的小說底色。小說世界里,西木被安排重新恢復他的智力,不讓他再做小丑。這時,他被克羅地亞人擄走。為隱瞞過去保護自己,西木不得不時時撒謊,可謂練就一種自保的本領,能夠泰然處之或玩世不恭地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一方面以自由姿態營造小說的流浪漢模式藝術空間,一方面鋪展編排西木在時代的動亂漩渦里身不由己,漂浮動蕩。格里美爾斯豪寫西木又再操小丑舊業,寫他從一方軍隊轉到另一方軍隊,寫他當了馬童,寫他成了蘇斯特獵兵,寫他立了戰功榮譽加身……。敘事文本此時呈現給讀者的是西木在步入社會、宗教、政界、軍界時,眼見和經歷種種墮落和頹敗的一個個開始。小說表現出來“強烈的反對封建專制、貴族特權和教會腐敗的傾向”(格里美爾斯豪森,2004:譯本序3), 也在這一個個開始中成為小說題旨的重要導向。
如同流浪漢小說里主人公先后在伺候過不少主人的“主仆”關系模式,西木在他漂浮動蕩的生存處境中先后跟隨了好幾個軍官和其他人,還遇到了各種身份的各色人物,包括與無賴流氓為伍。不論是作為敵人還是朋友,這些人物都為次要,他們的出現只是把小說情節導入不同的情境和場域,使得敘事更進一步觸及到流浪漢小說的社會批判意涵。或以他們與西木之間形成的關系,或借西木對他們行為的觀察,小說敘事里格里美爾斯豪森講述的不是流浪漢命運的波譎云詭,而是在展開對世相骯臟、人心善惡的暴露和嘲諷窗口。
小說第三和第四卷敘事提供的一幅幅畫面,場景多變、事件繁復,描述西木的個人生活和活動空間在持續變化,表現西木一路不停混跡于世,化身“魔鬼”偷竊食物,通過犯罪攫取財富,從一個底層人上升為一個春風得意的聲名顯赫者,授男爵頭銜,獲女性青睞,間涉風流,韻事不斷,欺騙自己,也欺騙他人,被迫與軍官女兒結婚,為挽救財產不得不去科隆,命運將他帶到巴黎,以婉轉歌喉和英俊面孔一舉成名,領略上層社會放蕩,人生艷福達到高潮,又命運多蹇,及至返回途中,得了天花,臉面變丑,錢也耗盡,再度窮困潦倒,淪為兵痞、騙子、冒充醫生的人和強盜團伙。敘事將西木的這些故事一個個連綴,持續給讀者提供打量那個時代社會的新的視點。一個原來淳樸單純、天真未鑿的“癡兒”,現在變得虛榮、墮落、罪孽、無恥、無道德和善于弄虛作假,既可唾可鄙,也復可悲可憐。格里美爾斯豪森以流浪漢小說同一審美模式的跳躍性敘事片段將這個如今變得“毫不棄惡從善,而是越變越壞了”(340)的西木置于讀者觀察之下,讓讀者看到亂世生活對西木來說既是一所使他成長的學堂,也是一個讓他“近墨者黑”的染缸。西木越是為非作歹,就越是讓讀者感到群魔亂舞的混亂社會和野蠻世道改變了他。社會揭示雖然構成了《癡兒西木傳》一個精神標識,但應當說它對社會伸出的褒貶時弊觸角多少有些失于淺嘗輒止,這又應當說流浪漢小說首先要的就是那份通俗性意識膨脹。
7 并非表現精神的救贖
雖然結交了對宗教信仰虔誠的海爾茨布魯德,但是西木也只不過是出于去一個新地方看看的心理跟著海爾茨布魯德去瑞士隱居,實際上他對自己放縱的生活尚無真正的省思。他也只是表面上皈依了天主教,內心里卻并未放下世俗,也難耐身體寂寞。海爾茨布魯德去世,西木便再次結婚,有了兒子,豈料妻子實際并不愛他,婚姻成了莫大的欺騙。與養父母重逢,西木得知自己本是貴族家庭出身,當年在森林里遇到的那個隱士原來就是他的生父。與魔鬼湖王子交談,生活上已摒棄了信仰的西木聽到了對人生在世的一種認識:世界和人生是上帝對人的考驗,是上帝對人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試金石。西木似乎又有皈依宗教的念頭,但外國軍隊來了,西木再次當兵,流落到了莫斯科,被韃靼人俘虜,流浪至朝鮮、日本、東印度、埃及等地。敘事只是三言兩語簡單講述了西木的這些顛沛,更多是空間變換在構成故事。回到家鄉黑森林,西木對這個“對于你無可信任,也無所期望”(469)的世界發出一番詛咒,決意重新去過隱居者生活。
小說第五卷有幾章,遠離歷史的、社會的、現實的經驗,進入神話色彩的、富有象征意義的想象。敘事講述西木的魔鬼湖及水下旅行,把一些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包羅其中,同時也使得一些“修身文學”(Erbauungsliteratur)(3)“修身文學”是一種宗教文學,廣義指所有的宗教修身讀物,狹義指旨在增強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對信仰虔誠度的作品。參見張威廉主編:《德語文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第767頁。氣息在段落中彌漫。格里美爾斯豪森這樣寫小說的結尾部分,既是對那個時代巴洛克小說中迷信、巫術、鬼怪、魔幻這類故事的美學視角再現,也與那個時候的人們面對亂世社會需要靈魂安置的需求相適應。小說開頭處留下的情節斷線,在西木重逢養父母時被回照,形成完整的故事鏈條。小說開頭寫的是西木被從童年時代的無憂樂園生生拽出,小說第五卷第23章寫的是西木省思自己,為他在小說最后的第24章里決定回歸隱士生活作了鋪墊,全書首尾相應的整體結構得到完成。
我觀察人生和時機,不是為了我靈魂的拯救,而是為了自己的肉體得到享受。我曾經多次拿自己的生命進行冒險,卻從未熱心于使我這一生改邪從善,好使我死后能心安理得地進入天堂。我只看到眼前的一切和我短暫的利益,卻從未想到未來,更沒有想到有朝一日要面對上帝為自己的行為做出交代!(468)
西木“由濁變清”,在懺悔以前的生活,先前的一個罪孽者在用上帝的燈火照破晦暗而精神升華,有“過來人現身說法”的啟示意味。不過,流浪漢小說并不一定要表現精神的救贖。西木的語言雖然在直接傳遞基督教的救世思想,但這有可能只是小說對那個時代宗教信仰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心態的一個簡單應和,并不一定是西木背后的小說作者格里美爾斯豪森立足于他深刻的人生體驗和生命困境的終極思考。(4)格里美爾斯豪森后來還寫了一卷《癡兒西木傳》“續集”,在“續集”中寫了主人公依據所經歷的生活滄桑而拒絕皈依宗教。小說的真正價值,還在于它記載了“30年戰爭”的罪行、社會的病態和人們經受的苦難(5)到了今天,德國文學對“30年戰爭”面貌和狀況的描寫,也大都是根據格里美爾斯豪森小說中的描述。,在于格里美爾斯豪森將他對失衡亂世的見多識廣和感慨諸多注入西木的流浪漢生活,在于它同時高蹈流浪漢小說的通俗藝術,把那個時代的戰爭和社會、人世和人生、兵燹和創殘,混亂和欺凌、惡習和愚頑、烏煙和瘴氣、乖杵和反常、落后和失路、皈依和危機……寫得過目難忘,寫得充滿奇特的幽默和粗俗的生氣,寫得極富丑惡與俏皮同存的特色。德國學者認定它是德國文學第一部近代文體意義上的小說,中文譯者李淑老師評價它是17世紀德國文學的巔峰,無任何其他作品堪與軒輊,是“德國巴洛克文學的豐碑”,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