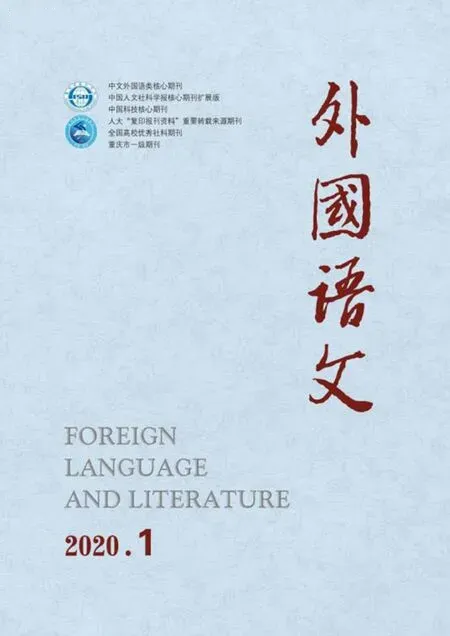論《女巫的子孫》的創傷敘事與時間機制
譚言紅
(重慶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 重慶.00054)
0 引言
在文學界,“從弗洛伊德到德里達,從心理分析到后結構主義,從文學敘事到大眾傳媒,經幾代學者的闡釋,創傷已變成橫跨不同學科和研究領域的重要研究范式”(陶家俊,2011:124)。創傷書寫再現現實社會、歷史事件、個體成長經歷對個體造成的心理創傷,將文學藝術與真實世界、歷史與現實、族群與個體等聯系起來,以文本呈現對個體或群體的現實關懷,修復個體創傷與文化創傷。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 阿特伍德創作的不少文本都可從創傷的視角進行解讀。她80年代創作的小說《可以吃的女人》聚焦性別創傷,“這種精神失調在小說中是一種象征性的假設的疾病,而不是醫學意義上的疾病,20世紀60年代時這種病癥還不為大多數人了解”(傅俊,2003:185)。阿特伍德將女主人公的精神創傷以文學想象的形式呈現給讀者。學者丁林棚在《自我、社會與人文》書中分析了阿特伍德在作品中表現的加拿大在美、英壓力下的國族創傷,認為“加拿大的癥狀就是精神分裂癥”(2016:54),英、法雙元文化的民族文化、身份認同上的無歸屬感,是她作為“社會和文化問題觀察者”對民族文化的反思(2016:53-60)。2016年,阿特伍德應出版社之邀將莎士比亞傳奇劇《暴風雨》(TheTempest)改編為小說《女巫的子孫》(hag-seal),小說基本遵循原作背叛、復仇與寬恕的情節,部分人物沿用原作人名,但她將故事放在當代時空背景中,將原作中的魔法現實化、科技化,消解了原作的奇幻因素,突出了敘事者菲利克斯的個體創傷和囚徒們因種族歧視、戰爭等造成的文化創傷,最終的復仇扣人心弦又合乎敘事邏輯。這部小說從人物時間觀、敘事手法、歷史語境等方面勾勒出深刻的個體創傷及文化創傷。
個體創傷可從受創者菲利普斯的時間觀進行解讀。小說書名中的Hag-Seed(劇作中的島上原住民——凱列班,小說中指代囚犯們)指涉一個心理受創者群體,包括主人公菲利普斯,他們都經歷修復創傷、重塑自我的過程。
1 創傷體驗與時間斷裂
小說主人公菲利普斯是個體創傷的受害者,他經歷創傷后在心理上產生時間斷裂感。作為頗具才華的戲劇導演,菲利普斯從事著自己喜愛的戲劇工作。在他順風順水的人生中,妻子的離世刻下了第一個傷口。之后他把精力和時間投入到莎劇排演,卻缺乏對家人的關懷和對現實人心的觀察,間接導致3歲女兒米蘭達生病未能及時送醫而去世,后來副手趁其不備搶占了他的職位。此后,虛構時間主導了他的物理時間,直到他完成復仇后女兒才徹底從幻覺中消失,“放她自由”意味著他最終修復了自我。
1.1 菲利普斯的雙重時間體驗:幻覺與現實
菲氏個人幻覺中的心理時間與物理時間不相重合,與文本時間形成兩條時間線。菲利普斯的雙重時間結構讓他不斷處于虛構與現實的漩渦,他反復體驗創傷。正如懷特海德指出:“創傷具有一種縈繞不去的品質,通過不斷的重復和返回持續占有主體。”(2011:14)創傷引起受創者時間的錯亂,他們心理的時空規定性被打破。
對于菲氏,線性物理時間被分成了兩條,這種時間邏輯使得不可能的未來具有了真實性,讓創傷主體可以在現實世界之外自欺,而現實生活卻失去了時間感。在他的幻覺中,女兒米蘭達的成長是依序展開的線性敘事:米蘭達并未在3歲時去世,而是健康地成長到15歲,直至他完成復仇她才從他的幻覺中徹底消失。過去的記憶與現實斷裂,卻又在幻想里接續向前延伸——生活中的線性時間邏輯被消解,而他的幻覺卻保持著時間邏輯。“受創者的感覺與行動,看起來就像是神經系統與當下的現實已失去聯系。”(赫爾曼,2017:31)受創者不能將記憶整合在一起,復雜的自我保護系統失去效力,產生出被神經學家和精神科醫生稱為“解離”的情緒反應。
而當受創者從幻覺中醒來時, 往往會產生創傷的再體驗。女兒在菲氏的幻覺中健康成長,幻覺消失后卻是他痛苦的延續。痛苦來自他對父親責任的清醒認識,幻覺來自于對記憶的改寫。
1.2 消解時間背后的倫理關系:幻覺與改寫記憶
菲氏將父親角色投射在幻覺中,他對女兒的摯愛與愧疚的心理體驗使得幻覺少了怪怖(uncanny),多了親情。幻覺消解了菲氏的創傷記憶,但他不同于真正的神經官能癥患者,他的幻覺如同正常記憶一樣有時間邏輯, 這可以說是作家將心理學案例文學化的產物。
“正常記憶應是可以言詞述說的線性故事”(赫爾曼,2017:33),但菲氏的幻覺也保留了線性敘事,他在幻覺中陪伴女兒長大,這抹去了生存與死亡的界限。《女巫的子孫》基本遵照了莎翁的《暴風雨》,而菲氏的幻象體驗就是阿特伍德獨創的心理世界。在這部小說中,菲利普斯試圖通過幻覺來抵消創傷事件帶來的痛苦。他的幻覺是對記憶的改寫,蘊涵著父女間的親情。
《暴風雨》通過身體記憶來引導他人重構自我,修復創傷,“身體是創傷記憶的重要載體。普洛斯帕羅通過喚起米蘭達、愛麗兒、卡列班對過去身體的回憶幫助他們重建身份” (湯平 等, 2017:170)。《女巫》則頻繁地通過菲氏的敘述視角聚焦他對自己扭曲記憶的認知,從而向讀者傳達他并非患上了純粹幻想癥的信息,有效地突出了思女心切的父親形象。“他只是沉迷于這種幻想。似是而非的執念。”(Atwood,2017: 32)當他理性清醒之時,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幻視與幻聽,意識到他被這一創傷事件所控制。他不斷提醒自己幻覺的危險,當他認識到幻覺正作為心理防御系統起作用之時,也是他恢復自知力、重歸真實世界之時。“得打住了”,他命令自己,“要趕緊打起精神,掙脫這個牢籠,你得接觸真實世界”(Atwood,2017:47)。對幻覺的清醒意識意味著菲利普斯開始恢復了自我意識,走上了重塑自我之路。
1.3 幻覺與清醒
菲氏深陷失女的創傷無法恢復,這個事件控制著他的思想和情緒,促成了單向思維和“解離”的心理狀態。他在幻覺中經歷時間斷裂和記憶扭曲,清醒時的意識又強化了創傷體驗。但幻覺也是他克服心理創傷的橋梁,他認識到幻覺改寫了記憶,最終戰勝了精神崩潰,回到現實世界。
在幻覺中,他作為一名普通的父親陪伴女兒長大,分享著女兒的秘密,見證了一個小女孩對生活的期待,這給他蒼白的現實生活添加了色調。小說中的幻覺重復一方面強調菲氏的心理創傷,另一方面也揭示他在產生幻覺后仍能回歸意識。因而幻覺對他的心理恢復并非完全是負面的影響,米蘭達在他幻覺中的成長是菲氏回歸世界的動機,是正面的力量。如果沒有這種幻覺,菲氏可能已精神崩潰,無法恢復自我認知。布萊恩認為“阿特伍德手法高超地讓菲氏(在幻覺中)養育他的女兒,讓讀者感到可信而不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偏執),他同她的幽靈親密自然地相處,陪伴她成長…… ” (Bethune,2016:54-55 )。
幻覺的出現是菲利普斯克服心理創傷必要的環節,在他對幻覺產生清醒認知之后,他最終令人信服地回到了現實時空中,消解了幻覺造成的雙重時間。作者除了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不斷渲染創傷體驗,還通過精巧的敘事時間機制呈現受創者心理時間的變化: 2013年1月7日是他復仇的起點,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文本中有關這一天的描寫占據了大量篇幅,這一天之后他逐漸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產生了幻覺,他對時間的認知也逐漸符合現實邏輯。
2 敘事時間與創傷書寫
敘事時間是敘事學中的重要單元,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著重提到了時序、時距、頻率等,不同的敘事時間結構有助于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主題、展示人物,也體現出作家的創作風格。阿特伍德的文本時間一貫較為復雜精巧,較少單線敘事,常呈現出插敘、倒敘、順敘等多樣化的時間結構。而創傷書寫同樣可從敘事時間入手進行分析,這篇文本展現了人物心理時間與文本時間的交錯,時序與時距的選擇以及不同敘事層的套疊,敘事者采用復雜的時間模式讓文本產生獨特效果,突出了個體及集群的創傷經歷。
2.1 敘事的時間要素與人物創傷體驗
菲氏在女兒去世12年后找到機會進行復仇。小說序章描繪了正在進行的復仇行動,第一章從菲氏在棄屋的心理與言行開始回溯他的生平遭遇,又接回監獄演出,再到演出完成后即復仇完成后的海上旅行。文本敘事從中段開始,這也是古希臘的常用敘事手法,熱內特以《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的憤怒與復仇為例作了詳細說明(Genette,1980:37)。而阿特伍德的這部小說也是從中段開始,過去、現在交織,記憶、現實、幻覺來回穿插,敘述張力十足,生動地構筑一個受創者的創傷文本,與作者獲布克獎作品《使女的故事》及200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洪災之年》等有相似的時間結構。復雜的敘事時間可分為兩個敘述層:第一敘述層是以2013年3月13日監獄戲劇《暴風雨》上演開始一直到復仇結束,菲氏最終獲得了精神的自由,第二敘述層是整體性追述,回顧菲氏12年前的創傷經歷,兩個敘述層之間沒有時間裂痕。第一章從2013年3月13日回到2013年1月7日,菲氏去監獄導演戲劇前在棄屋里的心理描寫與行動,突出了他的憤怒和復仇的決心,再繼續倒敘到12年前愛女去世和副手托尼的背叛,在這個時間點上開始向后敘述,講述了經歷背叛的他如何在棄屋獨居,幻想女兒的陪伴,在棄屋居住九年后,他在監獄劇團找到一份戲劇教學的工作,帶領囚犯們學習莎劇表演。當他在監獄劇團工作三年后,敘述回到了第一幕的開始,即2013年1月7日。這一天對整個文本來說很重要,五個小節重復提到。這一天的重要性在于:在受創12年后,他實質性地走上了復仇之路,邁出了從受創到恢復的第一步。
在菲氏12年的經歷中,敘事者巧妙地選擇了某些事件與時間點展開敘事,推動情節。在這個跨度12年的文本中,重點描述的有兩年,即2001年事件及2013年的復仇。敘事者用接近日志的形式敘述菲氏的戲劇表演課:繼第一幕回顧創傷事件之后,第二幕敘事從2013年1月9日、10日、11日、14日,直到15日結束。第三幕從1月16日開始,前進到17日、18日,跳到2月6日(距離戲劇開演還有5周)、2月9日、2月25日,到3月2日結束。第四幕從3月4日開始,包括3月7日和3月13日,表演這一天在本書中占用篇幅最多,情節緊湊,充滿張力,節奏加快,直到故事推向高潮。第五幕繼續向后寫,是演出結束后一個平緩的階段。從3月15日的最后一堂課,對人物結局的課堂討論,然后是3月31日的尾聲“還我自由”。小說的五章對應《暴風雨》的五幕。
而在這12年間,小說除了以描述性話語勾勒菲氏的生活困境,主要通過菲氏的幻覺展現了女兒米蘭達在他頭腦中虛構的成長經歷,幻覺構成他創傷體驗的重要部分。2013年前采用了省略、停頓等手法加快敘事節奏,2013年后敘述節奏放慢,這種節奏效果強化了張力,增加作品可讀性,以使讀者可以更好地發現菲氏修復創傷之路上的各個細節。而這種敘事時間,偏離熱奈特所說的“敘述等時的假定規范”(Genette,1980:93)。敘事節奏的變化使得讀者更易與人物產生共情,也有利于重現人物重塑自我的過程。
小說中主要的文本時間是從2013年1月7日到3月13日,這兩個多月是主體敘事,復仇計劃、實施方案都得以呈現。這部分占據文本的主要篇幅。12年的時間中,只有這兩個多月被詳盡描述,在敘事時間的取舍之中,隱含著敘事者的敘事邏輯:從創傷體驗到實施復仇,然后再在寬容中克服創傷,構成一個完整的敘事因果鏈。
2.2 個體創傷與時間意象分析
在莎翁原作《暴風雨》中,“劇作家通過書籍、身體、衣物等典型意象巧妙呈現各種創傷場景,喚起戲劇人物回憶過去的權力爭斗、海上船難的恐慌絕望、島上怪獸和精靈反抗主人而遭受懲罰的身心傷痛”(湯平 等, 2017:170)。
而這部文本中,敘事者以照片和法衣作為時間意象,抽象的時間被具象化,承載著時間感的物品被反復提及,回憶與現實糾纏在一起,展現從創傷到恢復的過程。從米蘭達母親的老照片開始,“時間流逝,也像一張寶麗來的老照片,慢慢褪色。如今,她只是一個粗糙的輪廓,一個填滿了他的悲傷的輪廓”(Atwood,2017:7)。他的妻子只是照片上一個模糊的影子,停留在過去,觸不到未來,被鎖在時間的深淵中。但她沒有在他心中留下最深刻的創傷。
另一張照片是米蘭達快三歲時的照片,在“一個神奇之窗的另一側,她依然活著,但如今,只能被鎖在這塊玻璃的后面”(Atwood,2017:22)。12年之后,這個秋千上的小天使依舊被封存在這個銀色的相框中,提醒他這是過去靜止的時間。
而復仇之后,“他拿起裝著米蘭達照片的銀色相框。他在秋千上快樂地笑著,她在那兒,三歲,消失在歲月的紅塵中” (Atwood,2017: 241)。最終,他對她說道“自由地回到空中吧”,終于她自由了,而他,也自由了。這個他總帶在身邊的物件,引起時間的錯亂與幻覺,也是他所經歷的創傷的證物。
反復提到的法衣則既象征著魔法與權力,也是時間的意象。開始他順風順水時,這件由動物皮毛編織成的法衣“有一種超自然卻仍屬于自然的力量,煥發出天地萬物的光芒”(Atwood,2017:9)。那個時候的法衣閃耀著才華與幸運,點綴著志得意滿的驕傲,是他尚未受創時的象征;失意時,這件法衣是一件失敗的披風。現實生活中的法衣成了對過去的哀悼,一個自怨自憐的象征,一個承載著不幸與懊悔的符號。而這個衰敗的符號一直提醒他不要放棄復仇。“自打十幾年前那場陰謀和決裂,他再也沒有穿過這件披風,但他也未曾將它丟棄,而是一直留著,等待時機,現在不是時候穿上它,但他幾乎可以肯定時機很快就會來臨了。”(Atwood,2017:48)小說結尾,當他大仇得報,法衣為他營造的光環正在慢慢褪去,“它淪為一件紀念品,再見了,我無所不能的魔法” (Atwood,2017:283)。法衣作為時間的標記符,折射出菲氏在不同階段的生活經歷和心理變化。
在這部文本中,敘事時間機制有效地呈現了個體時間觀的變化。菲氏的創傷體驗使他的心理時間處于混亂無序的狀態,而戲劇敘事是療愈創傷的方式,這些觀念使得這部文本與《暴風雨》 相比更具有現代性。此外,這部文本關注21世紀的社會問題,這也體現出不同歷史語境下的創傷書寫蘊含著不同的時代精神。
3 歷史時間中的創傷書寫:文藝復興時期與21世紀
本章中的歷史時間是指文本創作時的時間,就此而言,《暴風雨》是文藝復興時期作品,《女巫的子孫》是當代作品,不同的時代精神蘊涵在不同的創傷書寫中。阿特伍德熟悉莎翁作品,在她的第四部小說LifeBeforeMan中就模仿過《羅密歐與朱麗葉》,而《盲刺客》中模仿過《暴風雨》。 如果要改編莎翁作品,她說“當然選擇《暴風雨》了,我已經寫過普羅斯彼羅和其他文學中的魔法人物,……寫過他們的雙重本性:作為藝術家和懷疑者的本性”,而把背景放在監獄也很自然:監獄,不管是真實的還是形而上的,最終會走向“放我自由”(Atwood,2017:277),這也是普氏對觀眾從戲劇中放他自由的吶喊。她擅長把莎翁的時代經驗加諸現代經驗中,同時也把現代經驗加諸莎翁時代中。
3.1 文藝復興時期的殖民創傷
《暴風雨》的歷史時間體現那個時代的文化內涵:在高揚人文主義旗幟的文藝復興時期,莎翁呈現的是個體傳奇式的復仇與寬恕,創傷通過魔法得到康復。文藝復興時期高揚人的力量,而殖民勢力也正在興起,莎士比亞眼中的凱列班是人文主義者想象的一個他者。現代讀者讀出了原住民的殖民創傷,對凱列班這個人物也有認可之處,華泉坤、張浩在《〈暴風雨〉———莎士比亞后殖民解讀的一個個案》中提到:“如果我們真是如其所言忽視《暴風雨》中由其劇中人物的種族差異和性別差異所蘊含的殖民主義的歷史性主題,我們就不能真正領悟本·瓊生把莎士比亞的劇作稱為時代靈魂。”( 2004:46)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不少書籍及文章都論述了凱列班這個形象是對當時殖民主義的折射,本文不贅述。
3.2 現代社會的文化創傷
與此相對照,《女巫的子孫》雖改編自莎翁經典作品,但蘊含著作家對人性及現實社會的反思,揭示了作者鮮明的文化實踐精神。 “她對莎翁的興趣不是在于語言和歷史細節,而是我們(演員,觀眾,讀者)通過莎翁想象我們自己的方式。” (Bethune, 2016:54-55)作為當代作家,阿特伍德通過改寫莎翁作品來刻畫當代讀者的價值觀。她作品中的歷史感和現實感都相當強烈,在寫《使女的故事》時,她就說過“她的作品都有史實或現代事件作為參照”(Mead,2017:40)。因而,原戲劇中奇幻的魔法被替換為小說中具有現實感的高科技,不同歷史語境中的人文精神也有了不同的內涵。作家運用現代寫作手法描繪各種創傷體驗,雖然作為個體的菲氏在寬恕中與創傷和解,而集群的文化創傷仍在延續。
《女巫的子孫》中的囚犯群體指代原著中的凱列班,他們既是輕度違法者,也是受創者群體,有著各種受創經歷。文本中既描繪了個體創傷——“那情景(《麥克白》中麥克德夫夫人及孩子被殺一幕)太悲慘了。一些演員突然記起了他們的童年夢魘:毆打、威脅、瘀傷、慘叫、尖刀” (Atwood, 2017:81),也勾勒了種族、戰爭等造成的集體創傷。 個體創傷與群體創傷相結合,影射了種族、階層等社會結構對個體不可磨滅的影響。
族群創傷體現在囚徒身份中,書中明確指出的囚犯演員就有墨西哥裔、非裔、華裔、愛爾蘭裔和黑人混血、越南裔、東南亞裔等,其中扮演愛麗爾的“八只爪”是東南亞裔,他自認為是替天行道的“羅賓漢”,扮演凱列班的“飛毛腿”是愛爾蘭裔和黑人混血,曾在阿富汗服役,后被診斷為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綜合征),但退役軍人事務部沒有為他支付治療費。“許多人在童年時經歷過虐待或忽視,有些人更應該去精神病院或是強制戒毒所……把這些精神脆弱的人暴露在創傷情景中,激發他們的焦慮、恐懼和創傷記憶,甚至更糟糕的危險的攻擊性行為,這樣做有用嗎?”(Atwood, 2017: 79) 菲氏認為戲劇有著治愈的療效:“戲劇當然包含精神創傷的情景!它招來惡魔是為了通過情感宣泄來驅散它們。” (Atwood, 2017:79)
至于阿特伍德以“凱列班”為書名,把原作中的次要人物變為主題人物群,這更體現出文本的創傷主題。監獄劇團中有15名囚犯要求出演凱列班,他們對這個“女巫的子孫”有深度認同,他們對他有好感,把他這個邪惡、愚蠢、丑陋的怪物當作集體創傷的代言者。凱列班在原劇中野蠻而沒有理性,是“惡”的象征,被普羅斯彼羅剝奪了他認為與生俱來占有這座島嶼的權利,這與囚徒們的心理相契合,凱列班就象征他們自己。同時,小說通過飾演凱列班的囚徒演員,指出凱列班的創傷其實也是普洛斯彼羅的創傷,創傷者的負面心理都是相近的。他(普羅斯彼羅)意識到“凱列班的陰暗面幾乎就是他自己的陰暗面。他們都暴躁,愛辱罵他人,都有強烈報復心;他們是連體的,凱列班就是他另一個陰暗的自己”(Atwood, 2017:267)。
文化創傷也通過菲氏在監獄的話語權得到展現。后殖民主義理論家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導言里有關“對位歷史觀”(contrapuntal perspective)的界定可以啟發我們思考上述問題。賽義德把文化看作一種舞臺,上面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勢力:“文化絕非什么心平氣和,彬彬有禮,息事寧人的所在;毋寧把文化看作戰場,里面有各種力量嶄露頭角,針鋒相對。”(段方,2005:60)菲氏既是受創者,也是監獄里話語權的所有者。在監獄里,他作為象征界的父權秩序,主導著囚犯們的話語,利用他們的演出實施他的隱秘計劃。他如同普氏,通過話語權對囚徒——凱列班們施行文化洗禮,來實現他在囚犯這個邊緣群體中的話語權。在設計思考題開啟心智、組織人物性格討論推動囚犯演員們獨立思考的同時,他也在囚犯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他們實行自己的復仇。監獄是“他統治的島嶼,他的放逐之地”(Atwood, 2017:63),因而阿特伍德說“囚犯們有點不確定普氏是否是凱列班的生物學父親,但他們確定這二者至少有道德上的親緣關系” (Bethune,2016:54-55) 。
個體創傷與文化創傷編織出復雜的創傷敘事,雙重時間結構貫穿了整個文本。在創傷經歷的戲劇化重述中,菲利普斯的個體創傷得到了治愈,而集群的文化創傷仍在延續。
4 結論
《暴風雨》中的普氏是傳奇時間的主宰,他以魔法完成了復仇。阿特伍德把這個傳奇劇改寫為現實小說,改寫本既呼應原著又體現出鮮明的時代風格。作者在改編戲劇時就問過自己:“凱列班是弗洛伊德筆下普羅斯彼羅的本我嗎?他是自然狀態的人嗎?他是否是殖民壓迫的受害者呢,如同他現在常被演繹的那樣?”(Bethune,2016:54-55)小說中的戲劇導演菲氏作為創傷經歷者, 沉迷在幻覺中,把自己封閉在內在經驗里,和外部世界隔離,最終借助戲劇藝術與自我和解,與社會和解,讓自己與米蘭達的靈魂都獲得了自由。他有著精神創傷與自我囚禁的經歷,而象征凱列班的囚犯們有著成長過程中的痛苦記憶,這些都為從創傷視角闡釋這部小說提供了可能性。
在這篇小說中,敘事時間機制有效地呈現了個體時間觀的變化,而與《暴風雨》的對比則體現出不同歷史語境下的文本蘊含著不同形式的個體創傷與集群創傷。 文本頗具現代性反思風格,創傷敘事既包含了個體遭受巨大打擊后心理出現異常癥狀的個體創傷,如菲利普斯遭遇下屬背叛和喪女悲痛后顯現出典型的神經官能癥、出現幻覺與幻聽、性格變異、失去自我認同、封閉自我等,也包含了族裔創傷和戰爭創傷,如少數族裔的邊緣化境遇所造成的精神創傷等。菲利普斯以戲劇藝術來修復自我,但集群的文化創傷仍在延續。而藝術能否修復或減少文化創傷,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