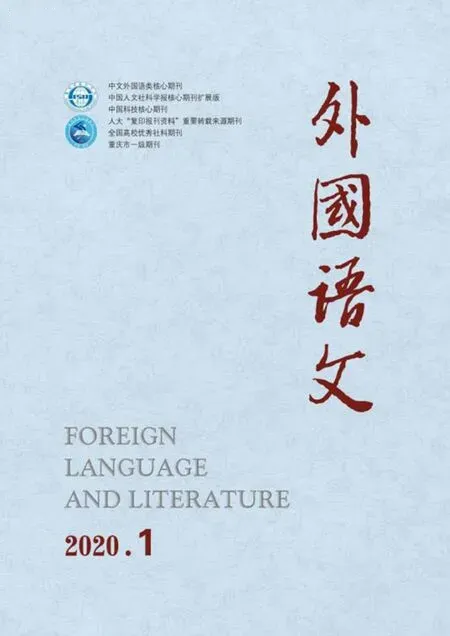對話意識·文本細讀·當下關懷
——論外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
陳茂林 陳韻祎
(杭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11121)
0 引言
外國文學是人類文化最集中、最生動的表達形式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推動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他山之石”,是我們學習外國先進文化的重要途徑。我國正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在這一奮斗過程中,經(jīng)濟的發(fā)展、軍事的強盛固然非常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我們國家的文化戰(zhàn)略發(fā)展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要弘揚中華文化的悠久歷史和精華,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樹立新的國家形象;二是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尤其是那些承載著豐富人文精神的優(yōu)秀文化”(劉意青 等,2012: 5)。外國文學研究在發(fā)展和繁榮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文化創(chuàng)新是國家、民族存在和發(fā)展之魂。復興中國文化,就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復興中國文化,還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文明成果。作為外國文學研究者,如何從事和創(chuàng)新外國文學研究,樹立文化自信,從而為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繁榮,為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做貢獻就成為學術研究的重點,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外國文學研究如何創(chuàng)新?筆者認為,外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就要具備與國內外學界的對話意識,進行文本細讀,觀照并關懷自然、社會和人生。這是外國文學研究創(chuàng)新的關鍵。
1 對話意識
外國文學研究如何創(chuàng)新?首先,要創(chuàng)新外國文學研究,就要有“對話意識”,要認真、細致地梳理國內外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現(xiàn)狀,和國內外學術界展開對話,尤其要與外國的學術同行乃至權威進行深度對話。研究意味著解決問題,而要解決問題,就首先要發(fā)現(xiàn)問題,找準問題,這是一切研究的基本前提。從事外國文學研究也是如此,必須要有鮮明的、強烈的問題意識,而只有在同國內外同行開展深度對話的基礎上,才能夠發(fā)現(xiàn)研究的問題。所以,“對話意識”至關重要,無論是申報項目,還是寫作論文,與學界充分對話始終是研究的起點或切入點。2011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李公昭教授的專著《美國戰(zhàn)爭小說史論》,就首先對國外的美國戰(zhàn)爭小說研究現(xiàn)狀進行了細致梳理,與國外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羅伯特·拉夫立的《小說打內戰(zhàn)》,斯坦利·庫柏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與美國戰(zhàn)爭小說》,約瑟夫·沃德梅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美國戰(zhàn)爭小說》,韋恩·查爾斯·米勒的《武裝的美國:小說中的面目:美國軍事小說史》,丹尼爾·艾倫的《未寫過的戰(zhàn)爭》,彼得·瓊斯的《戰(zhàn)爭與小說家:評價美國戰(zhàn)爭小說》,杰弗里·沃什的《美國戰(zhàn)爭文學:1914到越南》等學術專著展開了對話,發(fā)現(xiàn)“作為對美國戰(zhàn)爭小說的整體把握來說,這些史論往往因過于疏略而缺乏廣度和深度。個別重要時期的戰(zhàn)爭小說,如獨立戰(zhàn)爭的小說、朝鮮戰(zhàn)爭小說等;一些重要主題,如對朝鮮戰(zhàn)爭小說的評價;一些重要戰(zhàn)爭小說家……或避而不提,或一筆帶過,其結果是這類史論在表述美國戰(zhàn)爭小說的全貌時殘缺不全。至今似無一部兼斷代史的深度與編年史的廣度為一身的美國戰(zhàn)爭小說史”(李公昭,2012:7),由此確立了本書的立足點,為本書的學術價值奠定了基礎。
外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不但要與國外學術界對話,而且要與國內學術界對話。只有這樣,才能充分了解國內外相關研究現(xiàn)狀。曾獲全國第六屆高等學校優(yōu)秀成果三等獎的殷企平教授的專著《推敲“進步”話語》第八章,首先與國外批評家林納德對話,發(fā)現(xiàn)林氏在分析特羅洛普的《尤斯蒂斯鉆石》對“進步”話語的質疑時,認為麗萃“在社會舞臺上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是商品,又是消費者”,但卻否認作品對麗萃如何扮演該角色的描寫“構成對19世紀商品文化所依賴的價值觀的挑戰(zhàn)”,“僅僅挑戰(zhàn)了阻礙麗萃消費能力的19世紀社會習俗和文化代碼”(Lindner, 2003: 87)。接著,殷教授與國內學術界的代表朱虹女士展開學術對話,發(fā)現(xiàn)朱女士認為“麗萃確實是由現(xiàn)實丑變成藝術美的一個典范”,但卻對于“為什么丑陋的麗萃同時又是藝術美的典范”未加論證。在此基礎上,殷教授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得出“《尤斯蒂斯鉆石》中關于麗萃的雙重角色及其所作所為的客觀描述本身就是對19世紀新興商品文化的強烈挑戰(zhàn),就是對這一文化賴以生存的社會價值觀的強烈質疑”(殷企平,2009:208-209)的結論。
外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不僅僅需要與國內外學術界對話,尤其需要與外國的研究專家乃至學術權威進行深度對話。畢竟我們是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無法徹底擺脫語言文化的障礙,一般來說,我們的研究相對滯后于外國學者。外國專家或學術權威的觀點往往具有代表性,并影響深遠,難以突破,但國內學者的研究也并非就注定落后。只要國內學者敢于同外國學術權威開展深度對話,鼓起學術勇氣,挑戰(zhàn)、質疑外國的權威,并找出其研究的不足之處,就能有所突破,有所創(chuàng)新。殷教授的《推敲“進步”話語》就表現(xiàn)出超常的學術膽略,敢于挑戰(zhàn)國外的權威。該書第12章,論證并肯定了女作家喬治·艾略特的《亞當·斯密》對質疑“進步”話語的貢獻。以英國當代文學界權威伊格爾頓為代表的國外評論家一直忽視《亞當·斯密》推敲“進步”的主題,認為該作品是一項絕妙的“霸權課題”,“艾略特小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英國新興統(tǒng)治階級的霸權,即打著道德教誨的幌子來麻痹英國勞動階級的斗爭意志,并說服后者認同官方推行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標準,從而心甘情愿地接受統(tǒng)治”(殷企平,2009:309)。這已經(jīng)形成西方評論界的兩種思維定式,要么把小說看作“田園生活方式的挽歌”,要么看作“英國統(tǒng)治階級在鞏固其意識形態(tài)過程中的產物”(殷企平,2009:23)。針對伊氏的觀點,通過仔細研讀文本,殷教授提出了與西方權威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艾略特恰恰奏出了霸權主旋律的反調,奏出了一組質疑‘進步’,質疑速度,質疑‘現(xiàn)金聯(lián)結’的音律”(2009:310)。該書第一章,是針對英國文學評論界的另一位權威威廉斯有關迪斯累里的觀點而展開的論述。殷教授認為,“威廉斯所開列的‘新型小說家’的名單并沒有把迪斯累里包括在內——在威廉斯看來,是狄更斯首先捕捉到了工業(yè)革命引起的問題意識,發(fā)現(xiàn)并清晰有力地勾畫了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轉型時期的情感結構”(2009:18)。針對威氏的觀點,殷教授對迪斯累里的相關作品進行了細讀,并得出了與威廉斯認為狄更斯的小說率先推敲了“進步”話語迥然不同的結論,認為小說家迪斯累里最大的貢獻就是“率先用小說書寫了一部‘進步’推敲史”(2009:33)。我們知道,伊格爾頓和威廉斯都是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家,威廉斯的重要貢獻在于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作為威廉斯的學生,伊格爾頓豐富和拓展了威廉斯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意識形態(tài)”是伊氏文學批評的核心概念,貫穿其批評理論和實踐的始終。兩人都是英國文學界的學術權威,而殷教授不懼權威,展開與權威的深度對話,通過文本細讀,得出了新穎的結論。
2 文本細讀
對話意識是外國文學研究和創(chuàng)新的起點,是確定研究問題或者選題的依據(jù),是問題意識的前提。通過與國內外學界的深度對話確定研究問題后,下一步就是如何解決問題了,即如何進行外國文學研究才能出新。筆者認為,文本細讀是文學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新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文本細讀是研究文學的一項基本技能,指“對文本的語言、結構、象征、修辭、音韻、文體等因素進行仔細解讀”,其主要特點是“確立文本的主體性”,是一種強調內部研究的“文本批評”。作為一個批評流派,“新批評細讀逐漸體系化和制度化”(張劍,2006:630)。文本細讀強調文學研究立足文本,讓文本說話,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主張文學研究應該從文本到理論,而不是從理論到文本,更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目前在我國學界的文學研究中,依然存在著重視理論、輕視文本的傾向,研究自始至終從理論到理論,根本看不到文本的影子,用宏大的理論嚇唬人,得出假大空的結論。這種批評模式“從某個特定的理論視角出發(fā)對具體的作家作品進行解讀……經(jīng)常出現(xiàn)對理論生搬硬套或者把理論與作品強行撮合的現(xiàn)象。不少研究者對理論囫圇吞棗,食而不化,用之于作品解讀時,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對具體問題的闡發(fā)或失之粗疏,或以偏概全,甚至還出現(xiàn)了有違學術規(guī)范與涉嫌抄襲的現(xiàn)象”(張和龍,2013:95)。這種研究方法使文學作品淪落為文學理論的工具,“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失去了它應有的首要地位,淪落為理論的附庸,實為本末倒置。作品本身的分析過程,已經(jīng)不再有趣,因為它必然通向預設的理論觀點”(殷企平,2002:66)。這種批評可被稱為“印證式批評”,其死搬硬套的致命弱點清晰可見,正如殷企平教授所說,“那種一味用具體作品來印證某種理論的文學批評論著大都有一個弱點:人們不用看完全文就知道會有什么樣的結論”(殷企平 等,2011:66)。目前,很多院校的研究生論文開題和寫作中,這種偏重理論的傾向相當嚴重,似乎沒有文學理論,開題就不能通過,論文就沒法寫作。其結果是對理論嚴重依賴,理論束縛了文本分析,受理論限制而預設的結論束縛了研究者的思想表達,嚴重沖淡了文學研究必須具備的“問題意識”,不要說創(chuàng)新不可能,甚至還使文本分析和闡釋脫離文學研究的學科軌道,問題更加嚴重。正如張和龍教授所說,“不可否認,外來理論的引入給文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豐富的資源,但是外來理論如果脫離了具體的文學語境,脫離了具體作品的闡釋行為,就超出了文學研究的范疇。當文學作品中的細節(jié)只是外來理論的印證材料,文學也就變成了脫離文學語境的‘文化研究’,或社會學研究,或心理學研究,成了其他學科研究的附庸和下腳料”(張和龍,2013:98)。
曾獲第十八屆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的吳笛教授的專著《英國玄學派詩歌研究》是文本細讀的典范。該書深入、細致地解讀、闡釋了學術界廣泛認可的十幾位玄學派詩人的近百首詩歌,達到了論據(jù)確鑿、論證充分的學術效果。曾有專家這樣評論,“該成果突出的特色是,作者能夠緊扣文本,細讀字里行間的意義,作為文學評論的方法也好,作為一種務實、嚴謹?shù)淖x書方法也好,在世風浮夸的今天,具有倫理學意義”(吳笛,2013:314)。文本細讀是本書的一大特色,聶珍釗教授評論道,“細膩的文本分析遍及全書,體現(xiàn)了作者不僅具有學理分析能力,而且具有敏銳而強大的文學感悟力。大量詩歌文本的閱讀、翻譯和細致分析,使得本書的理論闡發(fā)有理有據(jù),言之鑿鑿”(2014:170)。殷企平教授的《推敲進步話語》也是文本細讀的典范,第十章對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說《謝莉》對“進步”話語的質疑進行了解讀。從問世起,評論界對該小說的評論就毀譽參半,“對它的指責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提出的批評,而是從藝術角度進行的抨擊”(2009:257)。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是英國文學批評界的兩大權威:伊格爾頓和劉易斯。殷教授不怕權威,與外國評論界的兩個“大腕”進行深度對話,發(fā)現(xiàn)其觀點有失公允,然后立足文本,沿著作品對“進步”話語的解構這一研究主線,對“小說結尾部分的語言、文體、意象——尤其是‘巴比倫通天塔’意象——和敘事策略/聲音進行了細察”(2009:22),得出了《謝莉》是一部毫不遜色的質疑“進步”的力作的結論。這些外國文學專家立足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告訴我們:要創(chuàng)新外國文學研究,就要與學界深度對話,不怕學界權威觀點,立足文本,扎扎實實地進行文學闡釋和探討,不能讓文藝理論主宰文學作品解讀,不能讓文本解讀淪為文藝理論的附庸。要凸顯“問題意識”,圍繞研究問題和研究主線,讓文藝理論服從并服務于我們的文本闡釋,讓文本闡釋服從并服務于論證我們的研究問題。一定要讓文本“唱主角”,一切要為“論證研究問題”服務。這樣才能達到論證充分,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說服力強,結論令人信服的效果,才能夠看到不同的東西,得出不同的結論,有所突破,有所創(chuàng)新。
3 當下關懷
外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不但要與國內外學術界深度對話,不但要進行扎實的文本研究,還要有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和對當下的現(xiàn)實關懷,使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具有現(xiàn)實意義。現(xiàn)實關懷依然根源于“問題意識”。依筆者之見,“問題意識”可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我們在與國內外學界深度對話基礎上發(fā)現(xiàn)的學術問題,二是來自我們作為人文學者觀照現(xiàn)實所發(fā)現(xiàn)的自然生態(tài)、現(xiàn)實社會和人類精神領域存在的問題。兩個問題并不一定總是重合,但很多情況下,二者是可以重合的,這樣就能使我們的研究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xiàn)實意義。要做到學術探討和現(xiàn)實觀照并重,我們首先要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立場,因為我們是研究外國文學和文化的,但我們是中國學者;我們不能站在外國研究者的立場上,純粹研究外國的學術,喪失我們的立場。劉建軍教授指出:“把外國的理論、外國的觀點、外國的想法直接拿過來,然后說外國多厲害,外國多好,外國研究多前沿;完全介紹西方,或者用西方的理論來套中國的事,用中國經(jīng)驗證明西方理論的正確或深刻;這些都是喪失立場的表現(xiàn)。作為中國研究者,我們不能成為外國理論和外國話語的注釋者,而應該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讓它為我們服務。”(翟乃海,2018:4)李公昭教授的《美國戰(zhàn)爭小說史論》就具有清晰、堅定的中國學者的學術立場。該書“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從中國當代學者的角度去審視與研究美國的戰(zhàn)爭歷史與戰(zhàn)爭文學,并試圖對美國各時期戰(zhàn)爭小說中所表現(xiàn)的歷史事實、戰(zhàn)爭觀念、軍事思想、社會矛盾、藝術成就等作盡可能全面、深入的論述,得出較為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結論與評價”(李公昭,2012:8)。在選取研究對象時,李教授參考了國外研究“美國戰(zhàn)爭小說”有影響力的評論家的選材標準,但卻不是照搬,而是立足自己的研究問題和現(xiàn)實關懷,同中有異:切入角度和研究都與國外研究者不同;選取了一些“代表不同觀點、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的作家與作品進行論述”,力爭透視美國戰(zhàn)爭小說的全貌,“如在評介美國獨立戰(zhàn)爭小說時不僅選取19世紀歌頌北美殖民地人民英勇抗擊英軍,歌頌華盛頓英明、偉大的《間諜》《自由之槍》等作品,也選取20世紀抨擊殖民地軍民貪生怕死、見利忘義、臨陣脫逃的恥辱行為,甚至抨擊大陸軍高級將領、當時的美國國會,乃至華盛頓本人的《不可戰(zhàn)勝的人》《武裝的暴民》”(李公昭,2012:8)等作品。在解讀具體文本時,該書擺脫了國外學者乃至權威的學術影響,絕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趨;沒有套用文藝理論,而是文本細讀更加扎實,彌補了國外學界研究的不足,堅持了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立場。正如劉建軍教授所說:“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外國語言研究、外國歷史研究、外國哲學研究等,首先要講的就是立場問題。我們必須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分析問題。說到底,研究應該是為我們自己服務。我們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去證明外國的理論有多么強大”(翟乃海,2018:4)。
外國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我們還要有當下關懷。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聶珍釗教授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就體現(xiàn)出中國人文學者的當下關懷。他研究的是文學倫理學批評這個學術問題,同時觀照著中國的社會現(xiàn)狀。他認為,如今的中國在市場經(jīng)濟影響下,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缺失已造成嚴重后果,市場價值代替了倫理價值,“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的推動之下,追求市場經(jīng)濟利益似乎變成了文學家、文學出版商和批評家結合在一起的強有力的紐帶,出版商的碼洋、銷售排行榜等,似乎成了衡量文學價值的標準。為了獲取最大經(jīng)濟利益,某些人把文學教誨的道德責任放在一邊,一味描寫感官享樂和對物質欲望的追逐,精神食糧的文學變成了物質食糧,文學的出版似乎只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聶珍釗,2014:4)。他對當下中國由于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過快而產生的問題憂心忡忡:“如果文學為了賺取金錢而一心信仰厚黑之學、權術之道、金錢萬能,社會豈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風氣?官場豈能清廉?法律豈能公正?”(聶珍釗,2014:4)他強烈呼吁,文學批評絕不能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文學“要為建設良好的道德風尚服務……要促進我國民族文學的繁榮,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家園的責任,為把美好的中國夢變成中國的現(xiàn)實而服務”(聶珍釗,2014:4-5)。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情懷,這就是中國的人文研究者應有的當下關懷:研究學術,關注社會和人生;研究外國,觀照中國;研究過去,關心當今世界。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xiàn)實意義。
4 結語
綜上所述,外國文學研究要創(chuàng)新,就要具備對話意識,尤其與國內外學界同行乃至外國權威評論家展開深度對話,才能找到研究問題,找到研究的起點或切入點;確定研究問題后,要進行文本細讀,立足文本,圍繞研究問題,緊扣研究主線,分析、闡釋文本,讓文本成為主體,而不要淪為文藝理論的附庸,讓理論服從服務于我們的文學研究,這樣才能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突破,有所創(chuàng)新;外國文學研究要創(chuàng)新,還要堅守中國研究者的學術立場,堅持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立場,秉持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研究學術,關注自然、社會與人生,關懷當下現(xiàn)實。作為外國文學研究者,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好地介紹、研究外國文學、文化,促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文化建設,樹立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軟實力,為中國文化強國和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yè)做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