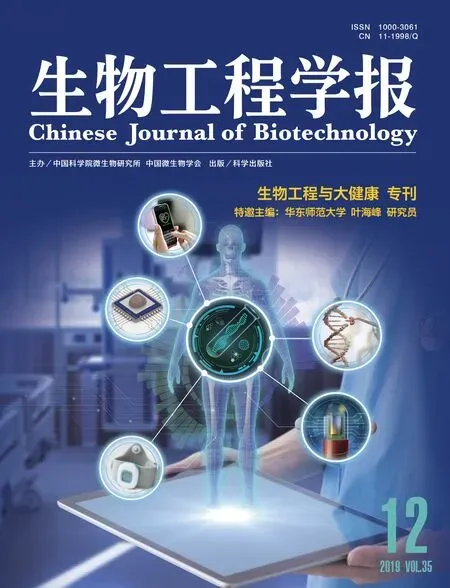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在實體腫瘤中作用的研究進展
白素杭,楊曉悅,張楠,張富涵,沈宗毅,楊娜,張文賽,喻長遠,楊昭
生物工程與大健康

楊昭 北京化工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生物工程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北京腫瘤病理精準診斷研究會常委。2010年獲吉林大學學士學位,2015年獲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學位。致力于腫瘤干細胞和腫瘤免疫治療研究,國際上首次證明了膀胱癌干細胞起源于正常膀胱干細胞或膀胱癌非干細胞,相關研究成果發表于、、、和等國際權威學術期刊。
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在實體腫瘤中作用的研究進展
白素杭,楊曉悅,張楠,張富涵,沈宗毅,楊娜,張文賽,喻長遠,楊昭
北京化工大學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北京 100029
腫瘤是21世紀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疾患之一。臨床上,實體瘤治療仍以手術切除、放化療和靶向治療為主,但這些方法往往不能根除腫瘤病灶,易導致腫瘤復發和進展。腫瘤免疫治療是利用人體的免疫系統,通過增強或恢復抗腫瘤免疫力實現控制和殺傷腫瘤的一種新的治療模式。腫瘤免疫治療能夠在眾多患者中產生持久反應,過繼性免疫治療和免疫檢查點阻斷劑治療均可產生顯著的抗原特異性免疫反應。腫瘤浸潤淋巴細胞 (TILs)是一種存在于腫瘤組織內部具有高度異質性的淋巴細胞,在宿主抗原特異性腫瘤免疫應答中發揮關鍵作用。最新研究表明,在腫瘤發生和治療過程中,TILs的亞群組成和數量與患者預后密切相關;抗腫瘤的TILs介導的過繼性免疫治療方法已在多種實體瘤中取得了良好的療效。文中就實體腫瘤中TILs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實體瘤,免疫治療,預后
腫瘤是一類嚴重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疾病,《2018年全球癌癥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約有1 810萬癌癥新增病例和960萬癌癥死亡病例,其中發病率最高的前10種癌癥均為實體瘤。相比于其他國家,我國癌癥發病率、死亡率均為全球第一。在1 810萬新增癌癥病例中,我國占380.4萬例;在960萬癌癥死亡病例中,我國占229.6萬 例[1]。2012年我國腫瘤登記年報數據顯示,我國發病率最高的前10種癌癥均為實體瘤,占全部癌癥的比例高達77%。其中,肺癌、胃癌、結直腸癌、肝癌和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最高[2]。
實體瘤的發生發展涉及大量的基因突變和染色質結構變異,由于該過程非常復雜,其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臨床上,實體瘤治療仍以手術切除、放化療和靶向治療為主,但這些方法往往不能根除腫瘤病灶,易導致腫瘤復發和 進展。
傳統的腫瘤治療方案,更多的是針對腫瘤細胞本身,但事實上腫瘤是在高度復雜且動態的環境中發展而來的。腫瘤微環境 (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 包括腫瘤細胞和腫瘤相關基質,腫瘤基質由腫瘤浸潤淋巴細胞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成纖維細胞以及腫瘤周圍的細胞外基質等共同構成[3]。TILs是存在TME中具有異質性的淋巴細胞,參與抗腫瘤免疫反應,主要包括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NK細胞、巨噬細胞和髄源性抑制細胞等[4]。在微環境中,腫瘤組織與免疫系統的相互作用常常呈現雙向作用,如機體免疫系統可以對腫瘤產生正向的識別與殺傷,而腫瘤細胞又可通過其表面表達的抑制性分子和分泌腫瘤相關細胞因子來形成免疫抑制性的微環境,介導機體對腫瘤產生免疫耐受,造成免疫逃逸。腫瘤細胞和相關基質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僅影響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并且與患者預后密切相關[5]。因此揭示各免疫細胞的特性及其與腫瘤的相互作用的機制,對于研究者通過重塑TME進而提高機體的抗腫瘤效應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本文就實體腫瘤中TILs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TILs在惡性腫瘤中的作用
1.1 TILs在腫瘤微環境中的功能
TILs是具有高度異質性的淋巴細胞亞群,不同的細胞亞群在TME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其包含具有正向調節免疫應答的免疫細胞,如樹突狀細胞 (Dendritic cells,DC)、CD8+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自然殺傷 (Natural killer,NK) 細胞等。它們通過對腫瘤細胞的識別、殺傷和清除,實現腫瘤免疫應答。TME也包含具有負向調節免疫應答的免疫細胞,如腫瘤相關巨噬細胞、調節性T細胞、髄源性抑制細胞等。它們會分泌大量的免疫抑制細胞因子和生長因子,如IL-6、IL-10、VEGF、TGF-β等,抑制上述DC、CD8+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NK細胞的激活,從而使腫瘤細胞逃脫免疫監視,最終導致腫瘤形成、侵襲與轉移[6]。
1.1.1 具有正向調節免疫應答的免疫細胞
CD4+Th1:CD4+Th1通過與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 Ⅱ)遞呈的多肽抗原反應被激活,Th1主要分泌IFN-γ、TNF-α、IL-2等細胞因子,介導細胞免疫,Th1可增強NK細胞和細胞毒性T細胞的殺傷能力,同時抑制Th2增殖。
CD8+細胞毒T細胞:CD8+細胞毒T細胞主要功能是特異性識別內源性抗原肽-MHCⅠ類分子復合物,進而殺傷腫瘤細胞。殺傷機制主要有兩種:一是分泌穿孔素、顆粒酶等物質直接殺傷把細胞;二是通過表達FasL或分泌TNF-α,分別與靶細胞表面受體結合誘導靶細胞凋亡。
NK細胞:NK細胞是一類表面標志為CD3–CD19–CD56+CD16+的固有淋巴樣細胞,其無需通過提前接觸或激活就能發揮腫瘤殺傷能力,某些腫瘤表面表達非MHC Ⅰ類配體分子的殺傷活化受體如NKG2D同源二聚體和自然細胞毒性受體,NK細胞表面識別這些受體選擇性攻擊腫瘤細胞。NK細胞對腫瘤的殺傷機制和CD8+細胞毒T細胞類似。
M1巨噬細胞:巨噬細胞是一種位于組織內的白細胞。激活的M1巨噬細胞具有促炎和殺傷腫瘤的功能,并分泌TH1細胞因子,如IL-12和TNF-α,以及少量的IL-10和IL-4[7]。
DC:DC是體內功能最強的專職性抗原遞呈細胞,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加工和提呈抗原,從而激活初始T細胞和CD8+T細胞。DC還能夠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調節其他免疫細胞的功能,如DC分泌大量IL-12誘導初始T細胞分化為Th1,產生Th1型免疫應答。
1.1.2 具有負向調節作用的免疫細胞
CD4+Th2:Th2主要分泌IL-4、IL-5、IL-6、IL-10及IL-13等,抑制體內抗腫瘤免疫反應。研究表明腫瘤間質浸潤的Th2細胞數量明顯高于Th1細胞數量,導致Th1/Th2漂移,產生的免疫抑制狀態會嚴重影響機體的抗腫瘤免疫,最終導致腫瘤的發生和發展[8]。
M2巨噬細胞:巨噬細胞具有可塑性,TME中M1巨噬細胞往往可轉變為M2巨噬細胞表型,但這一機制尚不清楚。M2巨噬細胞表達CD163、CD206及CD204等標志物,并分泌Th2型細胞因子,具有較低的抗原提呈能力以及促進血管生成等,具有抑制免疫應答的能力[7]。
調節性T細胞:典型的調節性T細胞是來源于胸腺的CD4+CD25+FOXP3+T細胞 (Treg細胞),Treg細胞在抑制腫瘤相關抗原特異性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它會抑制腫瘤引流淋巴結中的腫瘤相關抗原特異性激活,并進一步聚集到TME中,抑制效應細胞或效應分子的功能。目前Treg細胞發揮抑制作用的機理主要有4種:①分泌IL-35、IL-10和TGF-β等可溶性負性免疫分子發揮免疫抑制作用;②高表達IL-2的高親和受體,競爭性掠奪鄰近活化T細胞生存所需的IL-2,導致T細胞的增殖抑制和凋亡;③通過顆粒酶A、顆粒酶B以穿孔素依賴方式使CD8+細胞毒性T細胞和NK細胞等凋亡;④通過表達CTLA-4等膜分子和分泌IL-35等分子抑制DC成熟和削弱其抗原提呈功能,并促進抑制性DC產生。
1.2 TILs對腫瘤的預后評估作用
臨床預后指標可以幫助評估每一例患者的腫瘤復發和術后生存情況,大量研究證明TILs的密度、亞型和浸潤位置在多種腫瘤如結直腸癌、乳腺癌、黑色素瘤等的預后判斷中占主導地位。且T細胞在多種實體瘤中具有很強的預后價值[9-14](表1)。腫瘤浸潤T淋巴細胞是免疫治療過程中最重要的效應細胞類型,其主要包括以下亞型:CD8+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CD4+T輔助淋巴細胞 (Th)、CD45RO+記憶T細胞 (Tm) 和FOXP3+調節細胞 (Tregs) 等。其中CD8+T淋巴細胞在抗腫瘤免疫中起到核心作用[15]。
同時研究者提出運用免疫評分分期系統來預測腫瘤患者的生存周期,他們發現,通過一系列免疫評分分期和TNM分期的對比,顯示免疫評分對于預測結直腸癌患者的生存周期具有明顯的優勢,結直腸癌TILs的類型及密度是影響患者生存預后的主要因素,提示“免疫評分”在預測腫瘤患者生存預后方面,是一個更加優越的分期系 統[10,16]。這些研究也奠定了“免疫評分”技術的基礎。2013年Galon等提出了一種圖像分析輔助評分系統,命名為“免疫評分”,其是通過檢測腫瘤核心部位和腫瘤邊緣侵犯部位浸潤的CD3/CD45RO、CD3/CD8或CD8/CD45RO淋巴細胞群,并基于免疫細胞的類型、數量和位置3個方面作出評分的方法[9,17]。免疫評分反映了TME的復雜性和動態性,讓我們了解即使在同一腫瘤中,不同部位的免疫細胞也是動態變化的。因此運用免疫評分技術有利于針對不同病例選擇合理的個性化治療方案,防止過度治療和不恰當治療,對評價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作用。

表1 腫瘤浸潤淋巴細胞與實體瘤預后的相關性
TS: tumor stromal; TN: tumor nest; PT: peritumoral; IM: invasive margin; IN: intraepithelial; NSCL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HC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RCLM: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ESC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NBC: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1.3 TILs介導的腫瘤免疫療法
早在1988年,有研究報道TILs在多種晚期惡性腫瘤中參與積極的作用[18],提示免疫細胞的抗腫瘤效果。目前實體瘤的治療手段主要有手術切除、化療、放療及靶向藥物治療,但這些方法不能夠完全清除病灶,尤其是晚期實體瘤治療顯得相當困難。近年來,腫瘤免疫療法蓬勃發展,為實體瘤治療帶來了新的機遇。免疫治療是一種通過增強免疫系統功能達到對抗腫瘤的治療方式,其中免疫細胞在抗腫瘤免疫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免疫治療因其療效顯著、毒副作用小、耐藥性低而備受關注。腫瘤免疫療法的核心思想認為:腫瘤的發生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統被抑制,造成癌細胞不能被清除;只要將內源自身免疫抑制解除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或者外源補充不會被抑制的免疫細胞 (過繼免疫療法),就可能治療甚至治愈癌癥。
過繼免疫療法 (Adoptive immunotherapy,AIT) 主要包括TILs、細胞因子誘導的殺傷細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CIK)、DC、NK細胞、T細胞受體嵌合型T細胞 (T-cell receptor-T cell,TCR-T) 和嵌合性抗原受體T細胞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 免疫療法幾大類,具體內容如下。
1.3.1自體TILs過繼免疫療法
DC-CIK過繼免疫療法:CIK細胞是自然殺傷T淋巴 (NKT) 細胞的一類,表達CD3和CD56標志物,與其他報道的抗腫瘤細胞相比,在體外具有快速增殖、更強的抗腫瘤反應和低毒性等特點。近年來CIK細胞已被用于過繼免疫療法,但CIK細胞治療的臨床試驗未顯示出治愈率或長期生存率方面的顯著改善,因此需要進一步改善此療法[19]。DC細胞可以克服腫瘤相關抑制作用并提高CIK細胞的活性[20]。因此將DC和CIK結合可顯著增強抗腫瘤效力[21]。
TILs過繼免疫療法:基于TILs的過繼性細胞治療是將浸潤在腫瘤周圍的淋巴細胞分離,加入IL-2經體外培養、活化和擴增后回輸到患者體內,從而發揮殺傷腫瘤的作用。過繼治療需要回輸的細胞數量高達1×1011。自從1986年Rosenberg利用TILs對荷瘤小鼠進行治療并發現其療效是淋巴因子激活的殺傷細胞的50–100倍后[22],TILs成為抗腫瘤研究的熱點之一,并且在黑色素瘤的治療中顯示良好的療效[23-24]。
NK細胞過繼免疫療法:NK過繼免疫治療包括同種異體和自體NK的過繼治療,適用于免疫力低下的病人。自體NK細胞KIRs受體和MCH-Ⅰ配體結合能抑制NK細胞的活化,而同種異體NK細胞KIRs受體和MCH-Ⅰ配體不匹配,故打破了這種限制,有效活化NK細胞,啟動抗腫瘤反 應[25]。過繼的NK細胞與DC相互作用,產生的INF-γ能有效刺激Th1輔助細胞,從而進一步增強T細胞抗腫瘤免疫反應。同時,腫瘤致敏的NK細胞分泌IFN-γ能增加腫瘤細胞MHC-Ⅰ分子的表達,從而促進細胞毒性T細胞的特異性識別和殺傷腫瘤細胞[26]。NK細胞過繼治療腫瘤如乳腺癌、小細胞肺癌等,都顯示出其有效性和安全性[27-28]。
1.3.2 基因修飾的過繼免疫療法
在許多情況下,運用自體細胞過繼療法策略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在腫瘤組織中沒有足夠的活檢原料,或沒有足夠的浸潤性淋巴細胞。為了克服這些不足,可以采用基因修飾的策略賦予效應細胞特異性,拓寬AIT對其他癌癥的影響。目前基因修飾的抗腫瘤T細胞應用最為廣泛,且療效顯著,主要包括以下兩種策略。
(1) CAR-T細胞免疫療法
CAR-T細胞是指經遺傳修飾以表達嵌合抗原受體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 的T細胞,CAR由4部分構成,即細胞單鏈抗體區 (Single- chain antibody fragment)、跨膜結構域、細胞內信號傳導 (通常是CD3ζ鏈) 和協同刺激信號域 (CD28、41BB、OX40等)。目前CD19-CAR-T在復發或難治性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獲得空前成功[29]。2017年被稱為“CAR-T”元年,復星凱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Yescarta和瑞士諾華公司的Kymriah被批準上市。但是CAR-T在實體瘤治療中并不像血液腫瘤一樣順利,在實體瘤中療效并不顯著并伴隨嚴重的副作用,臨床應用極為受限。因此要積極開發針對實體瘤的免疫治療策略,目前主要有:①增加CAR-T細胞的轉運和浸潤:構建FAP-CAR-T減少腫瘤成纖維細胞的數量或使CAR-T表達趨化因子受體以達到腫瘤部位。②解除腫瘤抑制性微環境:將CAR-T與免疫抑制劑聯用如抗TGF-β、PD-1或PD-L1等抗體聯用。③提高治療的特異性和安全性如引入串聯基因等[30]。
因此今后聯合治療,尋找特異性靶點及構建通用型的CAR是CAR-T療法未來的發展方向。
(2) TCR-T細胞免疫療法
TCR-T細胞免疫療法是將能識別腫瘤特異性抗原的TCRα和β鏈基因轉染到T細胞中,使T細胞的TCR抗原結合區發生結構改變,從而能特異性識別相應的腫瘤抗原。然后經體外擴增并回輸到人體內,表達特異性TCR的T淋巴細胞可識別腫瘤細胞表面的HLA-肽復合物,并通過磷酸化胞內區免疫受體酪氨酸激活基序,來傳遞抗原刺激信號,進而引發T細胞的免疫效應,達到殺傷腫瘤細胞的目的[29,31]。目前,TCR-T細胞免疫療法在黑素瘤中的臨床研究最多且療效顯著[32]。TCR-T細胞免疫療法在其他實體腫瘤例如宮頸癌、結直腸癌和乳腺癌等中也均有一些嘗試性研究,但其治療效果尚待進一步臨床驗證。
以上療法均是將來自患者腫瘤組織、外周血或引流淋巴結中的淋巴細胞在體外修飾、擴增,最后回輸至患者的療法,與其他抗體或靶向藥物不同,擴增后的細胞回輸到患者體內后將激活并繼續增殖,可以形成持續的殺傷力。AIT已在多種實體瘤中取得了積極的臨床效果 (表2)。但是,AIT在臨床試驗中表現出的毒副作用仍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最常見的毒副作用是細胞因子風暴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CRS指的是由于T細胞增殖和激活,導致細胞因子大量釋放,引起患者發燒、低血壓、心功能障礙、腎功能衰竭、甚至死亡[33]。此外,AIT還會出現脫靶毒性,即T細胞能夠識別表達在正常細胞上的微量抗原。因此除了靶向表達該抗原腫瘤細胞外,還會攻擊表達相應抗原的正常細胞,損傷其他正常組織和器官的功能[23]。為了減輕以上的毒副作用,研究者們開發出一系列的管理策略:①目前,大多數CRS毒性可通過升壓藥,供氧支持,皮質類固醇和IL-6受體拮抗劑等方法來控制和治療[34]。②針對ACT存在的脫靶毒性,可以構建SynNotch、iCAR、引入自殺基因或小分子開關的策略來實現更特異和更安全地靶向腫瘤細胞[35-36]。下面將對不同實體瘤中TILs的研究進展逐一展開敘述。

表2 實體瘤中腫瘤浸潤淋巴細胞的臨床治療
TRMT: tumor-reactive memory T cells.
2 TILs與肺癌
2.1 TILs在肺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肺癌是全球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癥,在美國1/4的癌癥死亡是由肺癌引起的[37]。Kim等發現,無論是吸煙人群,還是非吸煙人群,與未接觸二手煙人群相比,二手煙暴露者肺癌發生風險增加[38]。最近,ShibliShibli等通過對335個肺癌組織切除的微陣列研究發現,單變量分析中腫瘤基質 (=0.001) 和上皮區域 (=0.004) 中CD3+細胞的浸潤能夠顯著延長患者腫瘤特異性生存率 (Cancer-specific survival,CSS)。在多變量分析中,腫瘤基質中CD3+細胞是CSS (=0.005)的獨立預后因素。CD3+T細胞的浸潤與非小細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中改善的臨床結果相關。但在此項研究中,漿細胞和肥大細胞均與預后無關[39]。在另一項研究中,Yin等通過Meta分析研究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與肺癌預后的相關性,結果表明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越高,NSCLC患者的總生存期 (Overall survival,OS) 越差 (=0.001)[40]。Geng等通過對8 600名患者的Meta分析顯示,腫瘤基質或瘤內中高水平的CD8+T細胞和CD3+T細胞浸潤與肺癌患者更好的OS相關。腫瘤基質中高水平CD4+T淋巴細胞浸潤在肺癌患者中表現出更好的OS。而腫瘤基質中高密度的FOXP3+細胞浸潤與患者更差的無進展生存期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有關,認為是預后不利的因素[41]。這表明TILs不僅具有明確的免疫功能,還具有預后作用。
2.2 TILs在肺癌中的臨床治療
TILs的臨床應用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AIT是繼LAK療法之后又一新的殺傷自體瘤細胞的免疫治療方法。Kradin等用TILs對6例原發性肺腺癌患者進行多次5.0×108–4.5×109TILs靜脈輸注或瘤灶內注入,在無白介素-2 (Interleukin-2,IL-2) 和環磷酰胺的情況下,其中4例腫瘤消退且患者有較好的耐受性;他們還對常規療法治療無效的轉移性肺癌和轉移性腎細胞癌等7例患者采用特異性TILs進行治療,也獲得較好的療效[42]。Ratto等利用AIT并結合放射性療法治療113例NSCLC,TILs在術后6–8周靜脈回輸給患者,數量為4×109–7×1010,前兩周劑量逐漸上升,后兩周逐漸下降,持續回輸2–3個月。結果表明,對Ⅱ期NSCLC,AIT治療與對照組(無輔助治療)平均生存期分別為22.3個月和31個月。對ⅢA期NSCLC,AIT組OS顯著高于常規治療組(化療加放療) (=0.06),平均生存期分別為22個月和9.9個月。對Ⅲ B期患者,AIT組OS顯著高于常規治療組(<0.01),平均生存期分別為23.9個月和7.3個月。治療期間,AIT組生存率無明顯變化,而對照組中不少患者死于復發[43]。超過80%的患者未出現嚴重的毒副作用,因此AIT在未來可以作為NSCLC輔助治療方案。Kradin等也開展了TILs臨床應用研究,他們對7名患有肺轉移性腺癌的患者給予T淋巴細胞回輸治療,發現有5名患者的腫瘤減小,但沒有患者達到完全或部分緩解;3名患者出現皮膚遲發性超敏反應。因此得出結論,腫瘤浸潤T淋巴細胞可以安全地輸注到人體中,并且可能會增強免疫反應并介導體內腫瘤的減小[44]。國內也有學者展開了相應的研究,李東復等對7例肺癌患者行TILs回輸免疫治療,結果大部分患者的狀態明顯改善,免疫功能增強,除有輕度發熱及1例血壓下降外,無其他明顯副作用[45]。
TILs臨床初步應用表明,機體能夠耐受一定劑量的TILs,且副作用少;IL-2對TILs發揮體內殺瘤效應有協同作用;環磷酰胺能顯著增強TILs的體內抗瘤活性,但TILs體外活性與體內效應并非總是一致。
3 TILs與肝癌
3.1 TILs在肝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原發性肝癌包括膽管細胞癌,亦有混合性腫瘤的情況,但是臨床上主要以肝細胞肝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最為常見。大量臨床研究發現,TILs的水平與HCC的預后顯著相關。Cai等發現肝癌瘤內DC的高浸潤度提示較高的無病存活時間 (Disease-free survival,DFS),瘤內CD45+細胞 (=0.003)、CD3+T細胞 (=0.005) 及CD8+T細胞 (=0.037) 浸潤均與延長的DFS密切相關[46]。Th17細胞主要效應因子是IL-17,Th17細胞具有強烈的促炎作用,在炎癥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著積極的作用。Zhang等通過對178例HCC患者采用流式細胞術和免疫組化法測定腫瘤內產生IL-17細胞的分布和表型特征,結果表明Th17細胞在HCC患者腫瘤中富集 (<0.001)。大多數腫瘤內Th17細胞表現出效應記憶表型,其中CCR4和CCR6的表達增加。腫瘤內產生IL-17細胞的密度與HCC患者的OS (=0.001) 和DFS (=0.001) 顯著相關,瘤內產生IL-17的細胞密度的增加預示著不良預后。多變量Cox分析顯示腫瘤內產生IL-17細胞的密度是OS (=0.009) 和DFS (=0.002) 的獨立預后因素[47]。
在更深入的研究中,Wang等在對249名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肝轉移分析中,通過對瘤內和癌周區域中CD3+和CD8+T細胞進行免疫評分發現,免疫評分高 (>2) 組相對于免疫評分較低組 (≤2),其無復發生存率 (Relapse-free survival,RFS) (<0.001) 和OS (<0.001) 均顯著延長,免疫評分高組RFS中位數為21.4個月,OS未達到終點;免疫評分低組RFS中位數為8.7個月,OS中位數為28.7個月。因此,肝轉移的TILs可用于預測肝切除術后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預后[48]。另外,來自46項研究涉及7 905名HCC患者的Meta分析顯示,瘤內FOXP3+TILs的密度是最重要的預后因子 (<0?.001)。其密度越高,HCC患者的預后越差;瘤內或癌周CD8+TILs浸潤的患者OS明顯延長 (=0.001);顆粒酶B表達為陽性的T淋巴細胞在瘤內的浸潤與更好的OS (<0?.001) 和DFS (
3.2 TILs在肝癌中的臨床治療
肝癌具有惡性程度高、死亡率高、進展快、復發快、轉移快的特點,HCC占肝癌病例的絕大部分,術后HCC患者的五年復發率高達70%[50]。Pan等在對410例HCC患者研究發現,經過CIK免疫治療的患者OS顯著高于單純手術組 (=0.000 7)。接受≥8周期CIK細胞輸注的患者的生存率明顯高于<8周期組 (=0.027 2),因此CIK細胞輸注術后免疫治療可能是改善HCC患者預后的有效輔助治療方法[51]。在另一項Ⅰ期臨床實驗研究中,15名HCC患者在腫瘤切除后,用其活化和擴增的TILs進行治療。在過繼治療后觀察到T細胞的數量瞬時增加,患者的不良反應主要為輕度流感樣癥狀。中位隨訪14個月后,15名患者 (100%) 存活;12名患者 (80%) 未發現疾病跡象,僅有3名患者腫瘤復發[52]。這些結果表明,用激活并擴增的自體TILs進行免疫治療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特點,因此可以作為HCC患者的新型治療方式。
4 TILs與胃癌
4.1 TILs在胃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胃癌在不同地理和人群中的發病率存在很大差異,韓國、日本、我國等東亞國家胃癌發病率和死亡率明顯高于北美、西歐及非洲地區的國家[53]。全國腫瘤登記中心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胃癌新發病例約為67.9萬例,胃癌死亡病例約為49.8萬例,嚴重危害我國居民健康[54]。微衛星序列是短串聯重復序列,是單個堿基或堿基片段(1–6個堿基) 的重復序列 (通常重復次數在10到60次),他們分散在基因的編碼區或非編碼區。錯配修復蛋白是一組核酶,在DNA復制完成后發揮作用,錯配修復蛋白沿DNA鏈滑動,當遇到基因錯配時便進行修復。如果缺乏DNA錯配堿基修復酶,導致復制錯誤DNA的堆積在增生的細胞中不能被修復,易誘發腫瘤。錯配修復缺失會引起基因組中累積重復幾十到上百次的核酸堿基短序列的異常,稱為MSI,與之相對應的是MSS[55]。在結直腸癌研究中,MSI高頻型 (MSI-H) 患者預后較MSI低頻型 (MSI-L) 和MSS患者好,其5年OS率和DFS率顯著高于MSI-L和MSS患者。Kim等進一步研究了99例MSI-H胃癌患者中的瘤內CD8+和FoxP3+TILs對患者預后的影響,研究表明高密度CD8+或FoxP3+TILs的浸潤比低密度CD8+或FoxP3+TILs的胃癌患者具有更高的總存活率 (分別為0.017和0.013);在多變量生存分析中,CD8+和FoxP3+TILs同時高度浸潤與良好的預后相關 (=0.003),因此CD8+和FoxP3+TILs可共同作為MSI-H胃癌患者的獨立預后因子[56]。另外一項涉及4 942名胃癌患者的Meta分析顯示,瘤內CD8+和CD3+T細胞的高度浸潤與延長的OS顯著相關[57]。
由此看出FoxP3+Tregs在不同癌癥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在胃癌中與良好的預后有關,但在肺癌中與更差的預后相關。
4.2 TILs在胃癌中的臨床治療
AIT雖然在胃癌治療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臨床治療當中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如對胃癌患者的治療中仍存在著靶向性不足,腫瘤細胞免疫逃逸機制使其無法發揮殺傷作用等缺點。因此,如果要達到充分發揮免疫細胞的抗腫瘤作用,需要積極聯合其他手段增強其對腫瘤細胞的識別能力,避免脫靶效應。Peng等利用IL-15基因轉染CIK細胞后,提高了其增殖能力和腫瘤殺傷效果[58]。有隨機臨床Ⅱ期研究將CIK細胞、臍帶血來源的DC和化療3種方式聯合應用于進展期胃癌患者,顯著延長了其無瘤生存期,治療過程中對患者無明顯的毒副作用[59]。由此可見,如果要達到充分發揮CIK細胞的抗腫瘤作用,需要積極聯合其他手段增強其對腫瘤細胞的識別能力,避免脫靶效應。
CAR-T免疫療法已成功應用于多種血液系統惡性腫瘤[60-62],此療法通過在T淋巴細胞膜直接表達腫瘤抗原的受體,使T淋巴細胞的激活不再依賴MHC分子就能激活相應的效應細胞,從而達到殺傷腫瘤的作用[63]。目前針對胃癌治療的CAR-T細胞治療仍在探索當中,其主要難點在于腫瘤抗原的選擇。目前已有研究針對CEA、HER-2/neu、NKG2D等作為胃癌腫瘤抗原靶點設計了相應的CAR[64-66],但均以針對胃癌細胞株的體外實驗、動物實驗為主,部分項目啟動了臨床入組計劃 (NCT02349724、NCT02416466),大規模的臨床應用研究尚未進行,其探索的道路依舊漫長。
5 TILs與食管癌
5.1 TILs在食管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2018年全球癌癥生存趨勢監測計劃CON- CORD-3的研究結果顯示,近10年來我國食管癌生存率增長了7%左右[67]。食管癌常見的類型為腺癌、鱗癌、肉瘤樣癌等,其中以食管鱗狀細胞癌最常見[68]。Chen等在對566例食管鱗狀細胞癌患者的研究表明,上皮內CD4+T淋巴細胞的浸潤明顯高于腫瘤基質區 (<0.001)。上皮CD4+淋巴細胞的浸潤與較長的OS (=0.001) 顯著相關。CD3+和CD8+T淋巴細胞的浸潤均與食管鱗狀細胞癌患者的預后無關 (>0.05)。因此上皮CD4+T淋巴細胞浸潤可能是食管鱗狀細胞癌患者預后的有利指標[69]。另外一項涉及2 909名患者的Meta分析顯示總TILs是食管癌患者OS的有利預后指標 (<0.001)。對于TILs亞群,CD8+TILs與改善的OS (<0.001) 和DFS (<0.001) 相關;FoxP3+TILs的浸潤與患者減少的DFS相關 (=0.003),CD57+TILs浸潤預示患者的OS更好 (<0.001)。此外,其他TILs亞群包括CD3+、CD4+和CD45RO+TILs與患者的生存期無關 (>0.05)[70]。因此,一些淋巴細胞可以作為食管癌預后的生物標志物,但關于TILs在食管癌免疫治療中的應用需要通過大量的臨床研究來驗證。
5.2 TILs在食管癌中的臨床治療
食管癌的治療主要以手術治療為主,術后輔以放化療,但放化療對機體的免疫功能影響較大,中晚期食管癌治療的預后仍不樂觀。Fujiwara等從5例食管癌患者的外周血中分離了DC細胞并進行體外培養,用111In標記成熟的DC細胞,并注射到瘤體內,再進行根治性手術切除。結果顯示,注射到腫瘤組織內部成熟的DC細胞并不能有效地向引流淋巴結遷移,無法獲得最佳的臨床反應[71]。Toh等進一步報道,將來自食管鱗狀細胞癌患者的PBMC在體外用自體腫瘤細胞刺激后,直接注射到原發性腫瘤和轉移部位,同時給予靜脈注射IL-2。離體產生的自體腫瘤激活的淋巴細胞每2周共13次局部注射到患者鎖骨淋巴結,每次注射給藥細胞的平均數量為0.8×109個。在免疫治療期間,觀察到患者2級腹瀉和發燒,在所有病變中獲得臨床局部緩解并持續11個月。由于臨床毒性較小,因此這種免疫療法可能對轉移晚期食管癌患者有效[72]。針對食管癌的免疫治療目前多處于臨床研究階段,尚無成熟的藥物可應用于臨床,需要更多的轉化研究進行探索。
6 TILs與結直腸癌
6.1 TILs在結直腸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臨床上普遍采用TNM分期系統評估結直腸癌患者的預后。近年來,“免疫評分”技術逐漸成為研究熱點。1998年,Naito等運用半定量方法分析了139例結直腸癌 (Colorectal cancer,CRC)患者,首次報道了瘤內的CD8+T淋巴細胞浸潤可能是其獨立的預后因素[73]。Salama等對967個Ⅱ期和Ⅲ期CRC病人研究發現,與正常結腸粘膜相比,腫瘤組織中的FOXP3+Tregs浸潤更多,而CD8+和CD45RO+細胞浸潤很少。FOXP3+Tregs的密度是CRC獨立的預后指標,CD8+和CD45RO+細胞則與預后無關。正常粘膜中的FOXP3+Tregs的高度浸潤與較差的預后相關 (=0.019)。相反,腫瘤組織中FOXP3+Tregs的高度浸潤與改善的存活率相關 (=0.001)。因此,FOXP3+Tregs在CRC中具有強烈的預后意義[74]。
近日,一項涉及5 108名患者的Meta分析研究了TILs的亞群組成、位置對CRC患者的預后影響,結腸癌患者結果顯示,基于TILs細胞類型分析發現,CD8+和FOXP3+T淋巴細胞 (非CD3+T細胞) 與改善的DFS和OS有關;此外,關于TILs的位置研究顯示,只有在腫瘤基質中FOXP3+T淋巴細胞的高度浸潤與改善的OS顯著相關 (=?0.000 7),在腫瘤浸潤邊緣中,CD3+T細胞高度浸潤預示DFS增加 (=0.008)。瘤內CD8+T細胞高度浸潤與改善的DFS相關 (<0.000 01)[75]。
總之,腫瘤組織中TILs的密度或亞型與延長的存活率密切相關,此外,在特定的浸潤部位僅有一些TILs亞型的高度浸潤與良好的預后相關。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TILs在CRC中的預后價值,以進一步增加關于TILs的免疫評分和免疫療法的有效性。
6.2 TILs在結直腸癌中的臨床治療
目前,臨床針對結直腸癌的主要治療方式仍是手術治療,但是單純手術治療效果并不能達到預期,術后復發率較高,且并發癥多。Takeshi等運用NK細胞免疫療法與IgG1抗體聯合治療晚期胃癌或結腸直腸癌來觀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施用IgG1抗體3 d后,每周向患者輸注擴增的NK細胞3次,以0.5×109、1.0×109和2.0×109細胞的劑量逐漸遞增。結果表明,患者體內富集NK細胞 (中位數92.9%) 且NKG2D (97.6%) 和CD16 (69.6%) 高表達。聯合治療結果顯示此療法耐受性良好,無嚴重不良事件。在6名可評估的患者中,4名呈現疾病穩定,2名患者出現疾病進展。在4名疾病穩定患者中,3名患者腫瘤減小,血液中IFN-γ數量增加,Tregs減少。總之,這項Ⅰ期試驗為先前接受過治療的晚期胃癌和CRC患者提供了有希望的治療方法[76]。DC聯合CIK是目前腫瘤免疫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DC和CIK共同培養使CIK細胞溶瘤活性明顯加強,更具特異性殺死腫瘤靶細胞[77]。國內也有研究探討了DC-CIK免疫療法聯合化療應用于晚期CRC中的臨床療效。結果顯示,觀察組治療緩解率顯著優于對照組 (<0.05)[78]。翁海光等的研究也顯示相似的結果,并且DC-CIK組患者的Ⅲ–Ⅳ度不良反應中,血白細胞下降的發生率為22.0% (11/50),低于單純化療組 (<0.05)[79]。說明DC-CIK免疫療法聯合化療可顯著提高晚期CRC患者的臨床療效,延長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存質量。另外在Zhang等的研究中顯示,CAR-T細胞免疫療法對胚胎抗原陽性結直腸患者有良好的耐受性,在10名患者中,兩名患者病情穩定超過30周,且腫瘤縮小;接受高劑量CAR-T療法的患者外周血中CAR-T細胞的持續存在,大多數患者的血清胚胎抗原水平下降明顯[80]。因此,AIT在CRC治療中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
7 TILs與乳腺癌
7.1 TILs在乳腺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嚴重威脅著女性的健康。乳腺癌根據表達受體不同分為3個主要亞型:ER/PR陽性型、HER2陽性和三陰性乳腺癌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乳腺癌中TILs的數量是改善患者存活率的有利預后因素,尤其是在TNBC和HER2過表達的乳腺癌亞型中[81]。近期一項研究收集了2 148個患者樣本探究早期TNBC中TILs的預后價值,共觀察到736例侵襲性無病生存和548例無遠端疾病生存事件以及533例死亡事件。在多變量模型中,腫瘤基質TILs浸潤程度的增加與延長的侵襲性無病生存 (<0.001),無遠端疾病生存 (<0.001)和OS (<0.001)顯著相關。在腫瘤基質中TILs≥30%的淋巴結陰性患者,患者3年侵襲性無病生存率為92%,無遠端疾病生存為97%,總生存率為99%[82]。另外一項242例TNBC患者中發現,與T-bet-腫瘤患者相比,T-bet+腫瘤患者的OS更長 (=0.047)。與CD8+T-bet-腫瘤相比,CD8+和T-bet+的患者具有更好的RFS (=0.037) 和OS (=0.024)[83]。在更深入的研究中,Savas等對乳腺癌患者中6 311個T細胞進行了scRNA-seq,結果顯示乳腺癌患者中含有高度浸潤的組織駐留記憶 (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TRM) CD8+T細胞,并且這些CD8+TRM細胞表達高水平的免疫檢查點分子和效應蛋白。CD8+TRM細胞與TNBC中患者存活率的改善顯著相關,并且比單獨的CD8+細胞具有更好的預后作用[84]。因此,TILs可作為乳腺癌預后因子。
7.2 TILs在乳腺癌中的臨床治療
TNBC患者具有較高的轉移和進展風險,醫生會根據腫瘤的分期和患者的身體狀況,酌情采用手術、放療、化療、內分泌治療、生物靶向治療及中醫藥輔助治療等多種手段。乳腺癌患者的骨髓中含有具有治療潛力的腫瘤反應性記憶T細胞 (Tumor-reactive memory T cells,TC),過繼性T細胞輸注會導致循環腫瘤抗原反應性Ⅰ型TC的產生。Domschke等描述了16名轉移性乳腺癌患者的長期臨床結果及其與腫瘤特異性細胞免疫應答的相關性,TC在體外首先與自體DC細胞和MCF-7乳腺癌細胞的裂解物共培養從而激活,然后擴大培養后輸注回患者體內,結果顯示16名患者中有7名對治療有響應,總隊列中觀察到總體中位生存期為33.8個月,其中3例患者在接受AIT治療后存活時間超過7年。轉移的腫瘤反應性TC的數量與患者的總體存活率顯著相關 (=0.017)。AIT治療后外周血具有免疫應答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明顯長于無應答者 (中位生存期為58.6個月對13.6個月;=0.009)。AIT治療后產生免疫反應的患者OS明顯延長,此療法有良好的應用前景[85]。乳腺癌中常表達細胞表面分子C-Met,因此Williams等設計了針對C-Met特異的CAR,進行了0期臨床試驗 (NCT01837602),以評估通過腫瘤內使用RNA轉染的C-Met CAR-T細胞治療轉移性乳腺癌的安全性和可行性。通過RNA轉染使CAR分子的瞬時表達限制靶標/腫瘤外效應來確保安全性。單次瘤內注射量為3×107個或3×108個細胞。在瘤內注射后不久,分別在2名和4名患者中檢測到外周血和腫瘤組織中的低水平CAR-T mRNA,患者均無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或比研究藥物相關的1級更嚴重的不良事件。因此CAR-T療法在乳腺癌患者治療中具有良好的耐受性[86]。目前,AIT療法在乳腺癌中的研究還較少,仍需要大量臨床試驗驗證此療法的療效。
8 TILs與宮頸癌
8.1 TILs在宮頸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宮頸癌是威脅全球婦女健康及生命的主要惡性腫瘤之一,目前其發病率占女性惡性腫瘤第4位,人乳頭狀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是導致宮頸癌最為常見的因素之一[87]。Carus 等在對101名宮頸癌患者的研究中發現,在癌周和腫瘤基質中CD66b+中性粒細胞和癌周CD163+巨噬細胞的高度浸潤與短RFS顯著相關。多變量分析發現癌周中性粒細胞高度浸潤 (=0.03),CD8+淋巴細胞低度浸潤 (=0.002),可以作為短RFS的獨立預后因素,而CD163+巨噬細胞與預后無顯著相關性[88]。
Asuka等調查了148例宮頸癌患者,發現較高密度的腫瘤浸潤性CD204+M2巨噬細胞與較短的DFS顯著相關,但CD4+、CD8+、FOXP3+、PD-1+淋巴細胞和CD68+巨噬細胞與預后無顯著相關性。且侵襲性腫瘤基質中TILs和巨噬細胞的密度顯著高于原位腫瘤。表達p16的HPV陽性腫瘤中TILs的密度顯著高于HPV陰性的腫瘤。因此腫瘤浸潤性CD204+M2巨噬細胞是宮頸腺癌患者預后不良的因子[89]。
8.2 TILs在宮頸癌中的臨床治療
宮頸癌起病隱匿,早期癥狀不明顯,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宮頸癌篩查手段及治療技術的差異,半數以上的患者就診時已處于中晚期。轉移性宮頸癌是一種典型的化療耐受型上皮惡性腫瘤,Stevanovi?等研究了AIT治療轉移性宮頸癌的療效,患者需之前接受過鉑類化療或放化療,再接受單次輸注腫瘤浸潤性T細胞治療,結果顯示:9名患者中有3名對療法產生響應,其中2例表現出持久緩解 (分別為22、15個月)[90]。另外,楊怡等用DC-CIK治療60例宮頸癌患者,結果顯示與治療前相比,患者的淋巴細胞亞群的數量如CD3+、CD8+、CD56+、CD3+CD8+、CD3+CD56+較治療前顯著升高。顆粒酶B和穿孔素的表達量顯著上調;患者的KPS評分明顯改善(<0.01),疼痛評分明顯降低(<0.05),生活質量提高;腫瘤標志物SCCA和CA125明顯下降(<0.05);沒有出現明顯的毒副反應(<0.05);臨床獲益率能夠達到80%[91]。因此,DC-CIK細胞免疫療法治療宮頸癌能使患者得到臨床獲益,對于促進患者微小殘留病灶的清除以及防止腫瘤的復發和轉移等有一定意義。
9 總結與展望
TME是一個高度復雜且動態變化的環境,TILs在不同實體瘤和不同臨床分期中有著不同程度的浸潤,大量研究證實了通過檢測TILs的亞群組成、數量和區域分布情況對于實體瘤預后具有重要價值。
目前在不同實體瘤中T細胞的研究最多且研究體系較為成熟。且不論是在腫瘤基質、瘤內還是癌旁/周,CD45+T細胞和CD8+T細胞的浸潤大多與實體瘤良好的預后相關。FOXP3+TILs目前在不同腫瘤中的預后作用報道不一,比如結直腸癌和胃癌瘤內FOXP3+TILs的浸潤表明患者的預后良好,而在肝癌和食管癌的報道中,FOXP3+TILs在瘤內的浸潤顯示患者的預后更差;肺癌和結腸癌腫瘤基質中FOXP3+TILs的浸潤,表明患者具有更好的預后,而在結直腸癌癌周部位FOXP3+TILs的浸潤則顯示更差的預后。因此FOXP3+TILs在實體瘤的預后作用仍有待進一步探究。CD66+中性粒細胞和CD204+M2巨噬細胞在瘤內浸潤均與宮頸癌不良的預后相關。因此,多個指標的聯合使用,用于預測腫瘤患者的預后是今后的發展方向。
不僅如此,抗腫瘤的TILs介導的過繼性免疫治療方法已在多種實體瘤中取得了良好的療效。TILs作為效應細胞來自患者自體,其殺傷腫瘤細胞作用強。AIT通過增強實體瘤患者免疫系統的功能,使腫瘤縮小,患者病情穩定時間可以超過數十周甚至更長時間,因此AIT是治療實體瘤患者非常有前景的治療方法。但TILs在實體瘤臨床治療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①其治療對象有一定的限制。患者如果具有嚴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臟器移植病史、哺乳期或妊娠期內、對細胞因子過敏、罹患T淋巴細胞瘤等情況中的一種或幾種時,是不適于接受AIT的。②AIT過程中免疫活性細胞的制備、擴增、回輸等環節復雜,可能免疫效應產生之前對治療效果發生顯著影響。目前不同種類免疫活性細胞的制備尚無統一的標準,不同研究單位選用的材料、方法不同,細胞擴增后細胞的數量和質量無法保障,這也是當前臨床試驗需要解決的問題。③在不同腫瘤類型中,AIT還存在缺乏合適的腫瘤特異性靶標的問題,尋找如EGFRvIII和CD19這樣的特異性靶點是提高AIT治療實體瘤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綜上,TILs過繼治療與傳統治療 (如手術和放化療) 和新興療法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和基因改造) 聯合是未來臨床治療的發展趨勢。不同腫瘤中TILs亞群及功能的進一步研究鑒定,是開發腫瘤免疫治療新方法的基礎。
[1] Bray F,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18, 68(6): 394–424.
[2] Chen WQ, Sun KX, Zheng RS, 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4. Chin J Cancer Res, 2018, 30(1): 1–12.
[3] Hanahan D, Weinberg RA. Hallmarks of cancer: the next generation. Cell, 2011, 144(5): 646–674.
[4] Sasada T, Suekane S. Variation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human cancers: controversy on clinical significance. Immunotherapy, 2011, 3(10): 1235–1251.
[5] Joyce JA, Pollard JW. Micro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metastasis. Nat Rev Cancer, 2009, 9(4): 239–252.
[6] Quail DF, Joyce JA. Micro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umo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Nat Med, 2013, 19(11): 1423–1437.
[7] Biswas SK, Mantovani A. Macrophage plasticity and interaction with lymphocyte subsets: cancer as a paradigm. Nat Immunol, 2010, 11(10): 889–896.
[8] Lauerova L, Dusek L, Simickova M, et al. Malignant melanoma associates with Th1/Th2 imbalance that coincides with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immunotherapy response. Neoplasma, 2002, 49(3): 159–166.
[9] Galon J, Angell HK, Bedognetti D, et al. The continuum of cancer immunosurveillance: prognostic, predictive, and mechanistic signatures. Immunity, 2013, 39(1): 11–26.
[10] Galon J, Costes A, Sanchez-Cabo F, et al. Type, density, and location of immune cells within human colorectal tumors predict clinical outcome. Science, 2006, 313(5795): 1960–1964.
[11] Savas P, Virassamy B, Ye C, et al. Single-cell profiling of breast cancer T cells reveals a tissue-resident memory subset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prognosis. Nat Med, 2018, 24(7): 986–993.
[12] Van Den Eynde M, Mlecnik B, Bindea G, et al. The link between the multiverse of immune microenvironments in metastases and the survival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ancer Cell, 2018, 34(6): 1012–1026.
[13] Sade-Feldman M, Yizhak K, Bjorgaard SL, et al. Defining T cell states associated with response to checkpoint immunotherapy in melanoma. Cell, 2018, 175(4): 998–1013.e20.
[14] Zhang L, Yu X, Zheng LT, et al. Lineage tracking reveals dynamic relationships of T cells in colorectal cancer. Nature, 2018, 564(7735): 268–272.
[15] Chiou SH, Sheu BC, Chang WC, et al. Current concepts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human malignancies. J Reprod Immunol, 2005, 67(1/2): 35–50.
[16] Pagès F, Mlecnik B, Marliot F, et al. International validation of the consensus immunoscor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lon cancer: a prognostic and accuracy study. Lancet, 2018, 391(10135): 2128–2139.
[17] Galon J, Mlecnik B, Bindea G, et al. Towar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munoscor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lignant tumours. J Pathol, 2013, 232(2): 199–209.
[18] Topalian SL, Solomon D, Avis FP, et al. Immunotherapy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using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recombinant interleukin-2: a pilot study. J Clin Oncol, 1988, 6(5): 839–853.
[19] Draghiciu O, Nijman HW, Daemen T. From tumor immunosuppression to eradication: targeting homing and activity of immune effector cells to tumors. Clin Dev Immunol, 2011, 2011: 439053.
[20] Wang QJ, Wang H, Pan K,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n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 of autologous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IK) cells, dendritic cells-CIK (DC-CIK), and semi-allogeneic DC-CIK. Chin J Cancer, 2010, 29(7): 641–648.
[21] Wang M, Cao JX, Pan JH, et al. Adoptive immunotherapy of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LoS ONE, 2014, 9(11): e112662.
[22] Rosenberg S, Spiess P, Lafreniere R. A new approach to the adoptive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with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Science, 1986, 233(4770): 1318–1321.
[23] Rosenberg SA, Restifo NP. Adoptive cell transfer as personalized immunotherapy for human cancer. Science, 2015, 348(6230): 62–68.
[24] Dudley ME, Wunderlich JR, Robbins PF, et al. Cancer regression and autoimmunity in patients after clonal repopulation with antitumor lymphocytes. Science, 2002, 298(5594): 850–854.
[25] Pandey V, Oyer JL, Igarashi RY, et al. Anti-ovarian tumor response of donor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is due to infiltrating cytotoxic NK cells. Oncotarget, 2016, 7(6): 7318–732.
[26] Goding SR, Yu SH, Bailey LM, et al. Adoptive transfer of natural killer cells promotes the anti-tumor efficacy of T cells. Clin Immunol, 2017, 177: 76–86.
[27] Zhang GQ, Zhao H, Wu JY, et al. Adoptive immunotherapy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y NK and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mixed effector cells: retrospective clinical observation. Int Immunopharmacol, 2014, 21(2): 396–405.
[28] Baggio L, Laureano AM, da RochaSilla LM, et al. Natural killer cell adoptive immunotherapy: coming of age. Clin Immunol, 2017, 177: 3–11.
[29] Fesnak AD, June CH, Levine BL. Engineered T cells: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cancer immunotherapy. Nat Rev Cancer, 2016, 16(9): 566–581.
[30] Xia AL, Wang XC, Lu YJ, et al. Chimeric-antigen receptor T (CAR-T) cell therapy for solid tumo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ncotarget, 2017, 8(52): 90521–90531.
[31] Debets R, Donnadieu E, Chouaib S, et al. TCR-engineered T cells to treat tumors: Seeing but not touching? Semin Immunol, 2016, 28(1): 10–21.
[32] Johnson LA, June CH. Driving gene-engineered T cell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Cell Res, 2017, 27(1): 38–58.
[33] Morgan RA, Yang JC, Kitano M, et al. Case report of a serious adverse event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 cells transduced with a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recognizing ERBB2. Mol Ther, 2010, 18(4): 843–851.
[34] Neelapu SS, Tummala S, Kebriaei P, et a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toxicities. Nat Rev Clin Oncol, 2018, 15(1): 47–62.
[35] Lim WA, June CH. The 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 immune cells to treat cancer. Cell, 2017, 168(4): 724–740.
[36] Grada Z, Hegde M, Byrd T, et al. TanCAR: a novel bispecific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Mol Ther Nucleic Acids, 2013, 2(7): e105.
[37] Siegel RL, Miller KD, Jemal A. Cancer statistics, 2017. CA Cancer J Clin, 2017, 67(1): 7–30.
[38] Kim CH, Lee YC, Hung RJ, et al. Exposure to secondhand tobacco smoke and lung cancer by histological type: a poole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Lung Cancer Consortium (ILCCO).Int J Cancer, 2014, 135(8): 1918–1930.
[39] Al-Shibli K, Al-Saad S, Andersen S, et al.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intraepithelial and stromal CD3-, CD117-and CD138-positive cell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APMIS, 2010, 118(5): 371–382.
[40] Renaud S, Seitlinger J, St-Pierre D,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in lung metastasectomy for colorectal cancer.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19, 55(5): 948–955.
[41] Geng YT, Shao Y, He WT, et al. Prognostic rol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Cell Physiol Biochem, 2015, 37(4): 1560–1571.
[42] Zeng DQ, Yu YF, Ou QY, et al.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valu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for clinical therapeutic research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Oncotarget, 2016, 7(12): 13765–13781.
[43] Ratto GB, Zino P, Mirabelli S,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adoptive immunotherapy with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interleukin-2 versus standard therapy in the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of resec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ancer, 1996, 78(2): 244–251.
[44] Kradin RL, Boyle LA, Preffer FI, et al. Tumor-derived interleukin-2-dependent lymphocytes in adoptive immunotherapy of lung cancer. Cancer Immunol Immunoth, 1987, 24(1): 76–85.
[45] Li DF, Zhang XY, Song YF, et alClinical effect of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 infusion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fter operation. Chin J Onco, 1995, 17(2): 152–155 (in Chinese).李東復, 張興義, 宋玉芳, 等. 肺癌術后患者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回輸的臨床療效觀察. 中華腫瘤雜志, 1995, 17(2): 152–155.
[46] Cai XY, Gao Q, Qiu SJ, et al. Dendritic cell infiltration and prognosis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06, 132(5): 293–301.
[47] Zhang JP, Yan J, Xu J, et al. Increased intratumoral IL-17-producing cells correlate with poor survival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J Hepatol, 2009, 50(5): 980–989.
[48] Wang Y, Lin HC, Huang MY, et al. The Immunoscore system predicts prognosis after liver metastasectomy in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7, 67(3): 435–444.
[49] Ding W, Xu XZ, Qian Y,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 Medicine (Baltimore), 2018, 97(50): e13301.
[50] Désert R, Rohart F, Canal F, et al.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with a periportal phenotype have the lowest potential for early recurrence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Hepatology, 2017, 66(5): 1502–1518.
[51] Pan K, Li YQ, Wang W, et al. The efficacy of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 infusion as an adjuvant therapy for postopera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Ann Surg Oncol, 2013, 20(13): 4305–4311.
[52] Jiang SS, Tang Y, Zhang YJ, et al. A phase I clinical trial utilizing autologous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ncotarget, 2015, 6(38): 41339–41349.
[53] Torre LA, Bray F, Siegel R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2. CA Cancer J Clin, 2015, 65(2): 87–108.
[54] Chen WQ, Zheng RS, Baade PD,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2015. CA Cancer J Clin, 2016, 66(2): 115–132.
[55] Kim JH, Kang GH. Molecular and prognostic heterogeneity of microsatellite-unstable colorectal cancer.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4, 20(15): 4230–4243.
[56] Kim KJ, Lee KS, Cho HJ, et al.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tumor-infiltrating FoxP3+regulatory T cells and CD8+cytotoxic T cells in microsatellite-unstable gastric cancers. Human Pathol, 2014, 45(2): 285–293.
[57] Yu PC, Long D, Liao C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density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prognoses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Medicine, 2018, 97(27): e11387.
[58] Peng Z, Liang WT, Li ZX, et al. Interleukin-15-transferred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elevated anti-tumor activity in a gastric tumor-bearing nude mice model. Cell Biol Int, 2016, 40(2): 204–213.
[59] Mu Y, Wang WH, Xie JP,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rd blood-derived dendritic cells plus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Onco Targets Ther, 2016, 9: 4617–4627.
[60] Kochenderfer JN, Rosenberg SA. Treating B-cell cancer with T cells expressing anti-CD19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Nat Rev Clin Oncol, 2013, 10(5): 267–276.
[61] Xu XJ, Zhao HZ, Tang YM.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doptive immunotherapy using anti-CD19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ransduced T-cell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Leuk Lymphoma, 2013, 54(2): 255–260.
[62] Gill S, Porter DL. CAR-modified anti-CD19 T cells for the treatment of B-cell malignancies: rules of the road. Expert Opin Biol Ther, 2014, 14(1): 37–49.
[63] Gross G, Gorochov G, Waks T, et al. Generation of effector T cells expressing chimeric T cell receptor with antibody type-specificity. Transplant Proc, 1989, 21(1 Pt 1): 127–130.
[64] Arakawa F, Shibaguchi HZ, Xu ZW, et al. Targeting of T cells to CEA-expressing tumor cells by chimeric immune receptors with a highly specific single-chain anti-CEA activity. Anticancer Res, 2002, 22(6C): 4285–4289.
[65] Liu XQ, Sun ML, Yu S, et al.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gastric cancer peritoneal metastasis by NKG2D ligands-specific T cells. Onco Targets Ther, 2015, 8: 3095–3104.
[66] Zhang DX, Zhao PT, Xia L, et al. Potent inhibition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by HER2-directed induction of apoptosis with anti-HER2 antibody and caspase-3 fusion protein. Gut, 2010, 59(3): 292–299.
[67] Allemani C, Matsuda T, Di Carlo V, et al. Global surveillance of trends in cancer survival 2000–14 (CONCORD-3):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cords for 37?513?025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one of 18 cancers from 322 population-based registries in 71 countries. Lancet, 2018, 391(10125): 1023–1075.
[68] Gu XS, Zhou K, He XY, et al. Related factors of vascular tumor embolus in esophageal carcinoma. Surg Res N Tec, 2016, 5(2): 108–110 (in Chinese).顧向森, 周凱, 何小勇, 等. 食管癌合并脈管瘤栓的相關因素分析. 外科研究與新技術, 2016, 5(2): 108–110.
[69] Chen KY, Zhu ZY, Zhang N, et al. Tumor-infiltrating CD4+lymphocytes predict a favorabl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operable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d Sci Monit, 2017, 23: 4619–4632.
[70] Zheng X, Song X, Shao YJ, et al. Prognostic rol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gastric cancer: a meta-analysis. Oncotarget, 2017, 8(34): 57386–57398.
[71] Fujiwara S, Wada H, Miyata H, et al. Clinical trial of the intratumoral administration of labeled DC combined with systemic chemotherapy for esophageal cancer. J Immunother, 2012, 35(6): 513–521.
[72] Toh U, Sudo T, Kido K, et al. Locoregional adoptive immunotherapy resulted in regression in distant metastases of a recurrent esophageal cancer. Int J Clin Oncol, 2002, 7(6): 372–375.
[73] Naito Y, Saito K, Shiiba K, et al. CD8+T cells infiltrated within cancer cell nests as a prognostic factor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ancer Res, 1998, 58(16): 3491–3494.
[74] Salama P, Phillips M, Grieu F, et al. Tumor-infiltrating FOXP3+T regulatory cells show strong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colorectal cancer. J Clin Oncol, 2009, 27(2): 186–192.
[75] Zhao YM, Ge XX, He JW, et al.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colorectal cancer differs by anatomical subsit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orld J Surg Oncol, 2019, 17: 85.
[76] Ishikawa T, Okayama T, Sakamoto N, et al. Phase I clinical trial of adoptive transfer of expanded natural killer cells in combination with IgG1 antibody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or colorectal cancer. Int J Cancer, 2018, 142(12): 2599–2609.
[77] Fan Y, Wei FF, Fang N, et al. Effect of dendritic cell-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 autologous immune cell therapy on serum microRNA-21 and mieroRNA-106a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hin J Exp Surg, 2015, 32(7): 1698–1700 (in Chinese).范鈺, 衛菲菲, 方娜, 等. 樹突狀細胞-細胞因子誘導的殺傷細胞免疫治療聯合化療對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血清微小RNA-21和微小RNA-106a的影響. 中華實驗外科雜志, 2015, 32(7): 1698–1700.
[78] Zhang WP.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DC-CIK immunotherapy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reatment of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Prac Clin J Int Trad Chin West Med, 2017, 17(4): 47–48 (in Chinese).張衛平. DC-CIK過繼免疫療法聯合化療治療晚期結直腸癌臨床觀察. 實用中西醫結合臨床, 2017, 17(4): 47–48.
[79] Weng HG, Shen D, Mao WD, et al. Clinical efficacy of DC-CIK immunotherapy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treatment of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Zhejiang Med J, 2015, 37(8): 625–629 (in Chinese).翁海光, 沈冬, 茅衛東, 等. DC-CIK過繼免疫治療聯合化療治療晚期結直腸癌的臨床研究. 浙江醫學, 2015, 37(8): 625–629.
[80] Zhang CC, Wang Z, Yang Z, et al. Phase I escalating-dose trial of CAR-T therapy targeting CEA+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s. Mol Ther, 2017, 25(5): 1248–1258.
[81] Savas P, Salgado R, Denkert C, et al. Clinical relevance of host immunity in breast cancer: from TILs to the clinic. Nat Rev Clin Oncol, 2016, 13(4): 228–241.
[82] Loi S, Drubay D, Adams S, et al.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prognosis: a pooled individual patient analysis of early-stage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s. J Clin Oncol, 2019, 37(7): 559–569.
[83] Mori H, Kubo M, Kai M, et al. T-bet+lymphocytes infiltration as an independent better prognostic indicator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9, 176(3): 569–577.
[84] Savas P, Virassamy B, Ye CZ, et al. Publisher Correction: Single-cell profiling of breast cancer T cells reveals a tissue-resident memory subset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prognosis. Nat Med, 2018, 24(12): 1941.
[85] Domschke C, Ge YZ, Bernhardt I, et al. Long-term survival after adoptive bone marrow T cell therapy of advanced metastasized breast cancer: follow-up analysis of a clinical pilot trial.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3, 62(6): 1053–1060.
[86] Williams AD, Payne KK, Posey AD Jr, et al. Immuno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current and future strategies. Curr Surg Rep, 2017, 5(12): 31.
[87] Li DC, Xiao ZH, Chen Y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HPV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in wuhou, Chengdu. Lab Med Clin, 2014, (17): 2423–2424 (in Chinese).李東川, 肖正華, 陳宇寧. 某地區宮頸癌患者 HPV流行病學調查. 檢驗醫學與臨床, 2014, (17): 2423–2424.
[88] Carus A, Ladekarl M, Hager H, et al. Tumour-associated CD66b+neutrophil count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recurrence in localised cervical cancer. Br J Cancer, 2013, 108(10): 2116–2122.
[89] Kawachi A, Yoshida H, Kitano S, et al. Tumor-associated CD204+M2 macrophages are unfavorable prognostic indicators in uterine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Cancer Sci, 2018, 109(3): 863–870.
[90] Stevanovi? S, Draper LM, Langhan MM, et al. Complete regression of metastatic cervical cancer after treatment with human papillomavirus-targeted tumor-infiltrating T cells. J Clin Oncol, 2015, 33(14): 1543–1550.
[91] Yang Y. The clinical studies on DC-CIK immunotherapy against 60 cases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D]. Guizhou: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017 (in Chinese).楊怡. DC-CIK治療60例宮頸癌的臨床研究[D]. 貴州: 貴州醫科大學, 2017.
Function of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solid tumors – a review
Suhang Bai, Xiaoyue Yang, Nan Zhang, Fuhan Zhang, Zongyi Shen, Na Yang, Wensai Zhang, Changyuan Yu, and Zhao Yang
,,100029,
Tumor is one of the major diseases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 Surgical resection, radiotherapy, chemotherapy and targeted therapy are the main clinical treatments for solid tumors. However, these methods are unable to eradicate tumor cells completely, and easily lead to the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tumor. Tumor immunotherapy is a novel treatment that uses human immune system to control and kill tumor by enhancing or restoring anti-tumor immunity. Tumor immunotherapy has shown to produce long-lasting responses in large numbers of patients, and thereby adoptive immunotherapy and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could induce remarkable antigen-specific immune responses.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are highly heterogeneous lymphocytes existing in tumor tissue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host antigen-specific tumor immune response.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TI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tumorigenesis and treatment. Adoptive immunotherapy mediated by TILs has displayed favorable curative effect in many solid tumo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progress of TILs in solid tumors.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solid tumors, immunotherapy, prognosis
July6, 2019;
October21, 201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602644),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Operating Expenses for Central Universities (No. buctrc201910),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No. 2017YFA0105900).
Zhao Yang. Tel: +86-10-64438058; E-mail: yangzhao@mail.buct.edu.cn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o. 8160264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No. buctrc201910),國家重點研發計劃(No. 2017YFA0105900)資助。
2019-11-1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998.Q.20191108.1111.001.html
白素杭, 楊曉悅, 張楠, 等. 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在實體腫瘤中作用的研究進展. 生物工程學報, 2019, 35(12): 2308–2325.
Bai SH, Yang XY, Zhang N, et al. Function of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solid tumors – a review. Chin J Biotech, 2019, 35(12): 2308–2325.
(本文責編 郝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