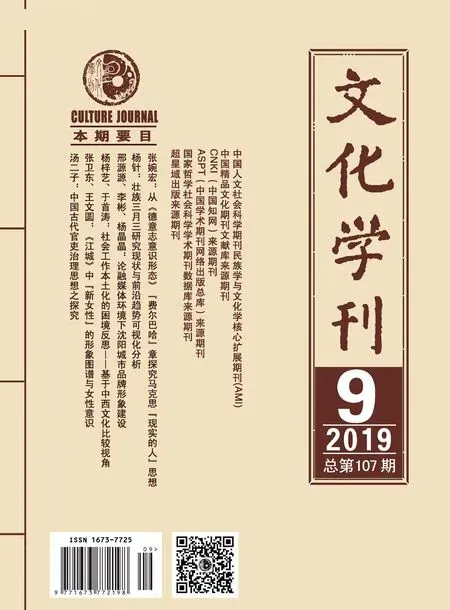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米蘭·昆德拉對陳忠實的創作影響
王浩宇
20世紀末,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進入中國,曾掀起過一波經久不衰的“昆德拉熱”,大家談論外國文學必言昆德拉。很多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響,這其中也包括“陜軍東征三駕馬車”之一的陳忠實。論及昆德拉對陳忠實的創作影響,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對二者之間文學關聯的事實考證。畢竟把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對立來看的觀點已經過時了,二者應該被統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影響研究是基礎,嚴肅的平行研究離不開影響研究。”[1]因此,研究米蘭·昆德拉對陳氏的創作影響時,一方面,需要從昆德拉出發,考察其作為“放送者”是如何得以對“接受者”陳忠實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需要從陳忠實出發,通過分析具體文本對二者之間的文學關聯進行大膽的假設,并通過溯源和典據研究對這些假設的可信度進行求證。
一、譽輿考證
其實早在1973年,米蘭·昆德拉就已經被介紹到中國了。經過對相關資料的仔細考證,這一年,上海市“五·七”干校六連翻譯組集體翻譯了《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紀實》[2]一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以“內部參考”名義出版。此書中有關捷克作家協會的章節涉及了米蘭·昆德拉,并對他的作品《開玩笑》進行了概述。筆者認為,這應該是中國大陸學界引介米蘭·昆德拉最早的文獻。但在迄今學術研究中,這一本著作的存在卻完全被忽視了。之所以如此,可能存在以下原因:其一,在圖書館與相關數據庫中,此書往往被分類列入政治書籍,因而難以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其二,此書問世于“十年動亂”時期,且屬內部發行,受眾群體較小。盡管如此,客觀來看,米蘭·昆德拉早在1973年就被介紹到中國卻是不爭的事實。
陳忠實(1942—2016)接觸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大致始于20世紀80年代。他曾回憶道:
“我大約是在昆德拉的作品剛剛進入中國圖書市場的時候,就讀了《玩笑》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別處》等。先讀的哪一本后讀的哪一本已經忘記,卻確鑿記得陸續出版的幾本小說基本都讀了。每進新華書店,先尋找昆德拉的新譯本,甚至托人代購。”[3]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景凱旋的譯作《為了告別的聚會》和韓少功的譯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隨后,國內首版《生活在別處》[4]和《玩笑》[5]也于1989年和1991年相繼付之梨棗。考慮到陳忠實并無直接閱讀原著的外語水平,他接觸的昆德拉中文譯本應在1987年及以后。
據邢小利著《陳忠實年譜》,陳忠實早在1986年末就已經開始思考通過長篇小說來實現文學創作的突破。次年8月,陳忠實第一次對外透露了他創作長篇小說《白鹿原》的信息。1992年,《白鹿原》經多次修改竣事[6]。《白鹿原》創作之前,陳忠實出于“實用主義”,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再結合“昆德拉的作品截至90年代以前出版的我都讀過”[7],綜合看來,若需在陳忠實創作軌跡中找到一個米蘭·昆德拉影響的原點,根據上述論據,可大致推定為20世紀80年代末,這也正是《白鹿原》創作的醞釀期。
二、篇幅與結構
昆德拉小說最令陳忠實注目的大概就是作品的篇幅了,這與陳忠實當時的創作習慣不無關系。眾所周知,《白鹿原》是陳忠實創作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在此之前,陳忠實擅長的是中短篇小說的創作。陳忠實本人也承認他被初入國門的昆德拉作品吸引:“首先在于其簡潔明快里的深刻,篇幅大多不超過十萬字,在中國約定俗成的習慣里只能算中篇。”[8]在一次采訪中,陳忠實曾齒及在創作《白鹿原》之前,一直借助寫作中短篇小說來訓練自身寫作長篇小說的能力[9]。而早期進入中國的幾本昆德拉作品篇幅并不算長,再加之刪譯和節譯,這無疑使昆德拉作品更加符合陳忠實的口味。
就小說結構而言,國內早期出現的昆德拉譯本也可能對陳忠實產生了一定影響。實際上,早期進入中國的昆德拉譯本即使經過刪節,譯成中文后篇幅也在20萬字左右(1)此處以在國內發行的第一個版本統計數據,《生活在別處》為19.8萬字,《玩笑》為21.5萬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為22.3萬字。值得一提的是,昆德拉的早期中文譯本是文學愛好者自發翻譯的作品,并未獲得正式版權,因為中國1992年7月才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單從字數來看,昆德拉的作品更應當被歸類為長篇小說,但這些小說給陳忠實留下了不逾10萬字的印象,并將其歸類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中篇小說。這種閱讀記憶上的模糊和偏差應該是由昆德拉獨特的小說結構造成的。昆德拉對小說的布局相當講究,出生于音樂世家的他擅長將音樂創作中的“對位法(counterpoint)”引入文學領域進行創作。“對位法”即在創作樂曲過程中,同時計劃演奏兩條或多條不同的旋律。它們雖同時發音,但又彼此融合,最終形成一個優美的整體大旋律。對位法的藝術就是旋律線互相結合的藝術[10]。也正是因為這種創作原則,學者傾向于將昆德拉的小說歸類為“復調小說”。對此,昆德拉本人也大大方方地承認:“從來沒有逃脫過復調小說和滑稽可笑這兩個形式的雙重婚姻”[11]。昆德拉的大多數小說都是由一些互相獨立的短篇構成的,時間和空間的跨度極大,以至于有評論家稱昆德拉小說獨特且場景變換頻繁的篇章安排,使得他的小說更像是鏡頭劇本,不用改編就能搬上銀幕[12]。這些看似分散的短篇又通過一個主題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個長篇。考慮到昆德拉如此特別的創作方式,陳忠實對昆德拉作品篇幅的記憶出現偏差也就不足為奇了。客觀來講,這種片段聯結式的創作方法將數個相對獨立的短篇文本統合為一個長篇小說,呈現了篇幅上潛移默化地由短及長。對于正在練習長篇小說創作的陳忠實來說,分析和借鑒這種小說結構無疑是一種捷徑。所以,以創作為導向的實用性角度來看,昆德拉的作品讓陳忠實在由中篇向長篇過渡的道路上受到了一定啟發。
不過,陳忠實并沒有完全照搬昆德拉的小說架構。在醞釀創作《白鹿原》時,陳忠實試圖通過大量閱讀中外名家經典作品來得到啟發,甚至獲得一種可以完全模仿的結構。不過從結果來看,啟發良多,無從模仿。陳忠實通過大量的閱讀和分析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單純的結構模仿注定只能寫出平庸之作。為此,他將自己接觸的所有中外優秀作品結構進行了雜糅,取其精華,為己所用,最終形成“自己的結構形式”。《白鹿原》的創作結構是依照小說情節和人物的發展來決定的,更進一步說,這個結構是《白鹿原》中各主要人物都得以充分展示各自性格和命運的時空平臺。然而,即使經過如此透徹的吸收和消化,學者仍然能從中發現一些復調結構的痕跡。例如:西北大學學者段建軍[13]就曾在《小說評論》上發文,從復調敘事的角度對陳忠實作品進行了解析和評價。由此看來,昆德拉的作品結構應當在陳忠實的取材之列,這也從側面揭示了米蘭·昆德拉對陳忠實的影響。
三、人物塑造與心理描寫
接受采訪時,昆德拉極力否認自己的小說是心理分析小說。盡管如此,其作品中大段的心理描寫卻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成為后來諸多文學評論家對其作品進行研究的熱點之一。針對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昆德拉有過這樣的闡述:
“讓我們更明確地來看:所有的小說,在任何年代中,都關注著自我這個謎。只要你創造出一個想象中的存在,一個人物,你就自動地面臨著一個問題:自我是什么?如何才能捉住自我?……但是,如果不通過行動來把握自我,那么我們又能在哪里把握住它呢?如何才能把握住它呢?因此,當小說在追求自我時,被迫離開了可見的行動世界,轉而審視無形的內在世界。”[14]
昆德拉認為,一般情況下,人通過獨特的行動將自己同他人區分開來。但是,當行動不能完全反映自身時就需要轉而進入內在世界,從心理上對事物進行分析,這無疑對陳忠實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用陳忠實本人的話說,昆德拉的藝術景觀打破了他小說創作中一直存在的“戒律”[15]。這種被打破的“戒律”指的就是陳忠實以前一直遵循的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原則,即著力于對人物的肖像及語言等進行描寫與刻畫,并試圖塑造出一個典型環境下的典型形象。昆德拉的心理分析主張和陳忠實彼時剛剛接觸到的“文化心理結構說”不謀而合,讓陳忠實明白了對形象的塑造除了追求獨特的修辭,還需要對人物的心理進行獨特的描寫。于是,陳忠實開始了一種迥異于以前的、新的人物形象寫作模式——從心理入手刻畫人物。
“為了準確把握他們的心理結構,我決定對人物不做肖像描寫,這和我以前的中短篇寫作截然不同。除了對白家、鹿家兩個家族象征性的特點作了一個相應的點示以外,其他人物都沒有個人肖像描寫……我想試試看能否不經過肖像描寫,通過把握心理結構及其裂變過程寫活一個人物。”[16]
在創作《白鹿原》之前,陳忠實曾經在構思人物形象的時候犯了難。在他看來,自古及今,文學史中已經誕生了無數經典人物形象,這就使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無法推陳出新,也無法書就讓人滿意的人物辨識度。這正如昆德拉所闡述的,當外界的行動(外貌、行為、語言描寫)不能反映自身時就需要轉而進入內心世界分析。陳忠實以心理描寫為突破口,在《白鹿原》中創作了白嘉軒、鹿子霖、鹿三、白靈等一眾讓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他刻意對這些人物不進行肖像描寫,試圖讓讀者僅從每個人物的心理活動來感受他們的獨特之處。后來,陳忠實接受采訪時也主動談及這一點:“事實上,作品中也的確是除了對兩大家族外形的一個生理特點有一種預設之外其他都沒有描寫,這個特點就是白家的鼻子突出,鹿家的眼睛深陷。”[17]無獨有偶,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中也存在類似表述:“我們對布洛赫的最重要的人物艾斯克的外表知道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他長著很大的牙。”[18]結合前述昆德拉的心理分析主張,這種高度類似的表述顯然不能簡單地用巧合來解釋。
四、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
米蘭·昆德拉對陳忠實最大的影響莫過于對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的切實理解。在以往的多次采訪中,陳忠實每每言及昆德拉,必會談及生活體驗與生命體驗:
“在昆德拉小說的閱讀過程中,還有一個在我看來甚為重大的啟發,這就是關于生活體驗與生命體驗的切實理解。似乎是無意也似乎是有意,《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兩部小說一直縈繞于心中。……我切實地感知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進入了生命體驗的層面,而與《玩笑》就拉開了新的距離,造成一種一般作家很難抵達的體驗層次。這種閱讀啟發,遠非文學理論所能代替。”[19]
從生活體驗層面看,不論是昆德拉的小說還是陳忠實的小說,都無可否認地帶有相當程度的自我指涉,在他們的作品中也都能找到作者生活體驗的痕跡。音樂是一種跨越民族的語言,所以不妨以音樂元素為例進行分析。昆德拉和陳忠實都是資深的音樂愛好者,只不過昆氏喜愛的是歐洲古典樂和捷克民族樂,陳忠實則癡迷于中國西北地區的秦腔。昆德拉的父親就是一位鋼琴家和音樂教授,受其父熏陶,昆德拉在齠齔時代就醉心于鋼琴的即興演奏[20];陳忠實自幼受父親影響,也對秦腔異常癡迷。據陳忠實回憶,在西安讀初中時,他曾經在晚自習后偷偷溜出校外觀看秦腔演出,為此受到了學生生涯中唯一一次處罰[21]。對音樂的癡迷也自然而然地復現于二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昆德拉的小說《玩笑》中,雅洛斯拉夫是一位民族音樂的愛好者,其唯一理想就是將傳統民樂發揚光大;陳忠實小說《白鹿原》中,身為下任族長的白孝文,墮落前的唯一愛好就是聽秦腔。
昆德拉和陳忠實作品中的音樂元素絕非僅僅停留在人物塑造上。讀完昆德拉的所有小說,我們會發現一個獨特之處:除了《告別的圓舞曲》,其他全部由七章構成[22]。這種對“七”的執著無疑和他的音樂修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基于對貝多芬和巴赫音樂作品的分析,昆德拉似乎認定七章是劃分小說章節的“黃金比例”,他也毫不諱言自己如此架構小說確實源于樂理。反觀陳忠實,他創作的《白鹿原》中也多次筆及秦腔,白嘉軒最后一位命短的妻子胡氏就被比喻成了秦腔戲《游龜山》里的胡風蓮,白孝文的墮落也是始于看秦腔戲時被田小娥誘惑。縱觀整本小說,秦腔是《白鹿原》中不可剝離的元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為個別劇情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合理而又自然的場景。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昆德拉和陳忠實都將自己的生活體驗融合吸收到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中。進一步總結,我們能看到二者之間的生活體驗至少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同源,那就是音樂。
至于生命體驗,陳忠實用蛻變的蝴蝶作了形象的比喻,認為生命體驗是對現實生活的升華[23]。他以昆德拉的作品為例,指出其作品《玩笑》和《為了告別的聚會》只停留在了生活體驗,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則不吝溢美之詞,視其為一部進入了生命體驗的佳作。
筆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生命體驗,不得不提及這部作品最后一章《卡列寧的微笑》。著名文學評論家弗朗索瓦·里卡爾(Francois Ricard)在為此書所作的跋中特別就此章評論道:“這幾頁文字(指最后一章《卡列寧的微笑》)給我揭示了另一個昆德拉,或至少迫使我不得不修正我先前對他作品的看法。”[24]在這一章,特蕾莎為了讓愛犬卡列寧脫離病痛折磨對其實行安樂死,弗格茨在柬埔寨戰爭的“偉大進軍”中失去了生命,托馬斯和特蕾莎也因為車禍雙雙離世。昆德拉一反以往對自己意識的準確表達和對社會氣氛的冷酷針砭,用死亡讓我們明白了生命的沉重,與之相比,愛又是那樣的無力。在《白鹿原》中,當白嘉軒愧疚地就“換地”向鹿子霖道歉時,已經瘋掉的鹿子霖卻把一顆羊奶奶遞給他,說道“給你吃,你吃吧,咱倆好!”白嘉軒只能輕輕搖頭,忍不住流下淚來。在那一刻,陳忠實筆下的文字超越了白、鹿兩家幾十年的明爭暗斗,超越了“鏊子”般的白鹿原,甚至超越了那一個紛亂的時代,直接升華到了對人性和命運最本質的思考。
五、結語
深入生活不易,超越生活更難。不論是昆德拉還是陳忠實,其作品都經歷了一段由生活體驗羽化為生命體驗的過程,這種羽化過程又與他們經歷的特殊社會歷史時期息息相關。當“布拉格之春”運動被蘇聯鎮壓后,年輕的昆德拉失去了黨籍和教職,最后不得不出走法國。陳忠實的文學創作和生活也在國內“十年動亂”期間受到了很大沖擊。在經歷過如此社會劇變后,不論是東歐還是國內,當時的人們都面臨著舊的價值觀被打破之后思想上的迷茫。從這個維度來看,當時的東歐和中國在社會環境和意識形態上存在諸多歷史性相似。在波詭云譎的變故中,人人都如同葦草一般,而在一切終歸于塵后,人們又需要冷靜下來對過去進行反思。由此看來,陳忠實對昆德拉的認同和接受也就不難解釋了。這正如樂黛云教授曾經提及的:“接受與影響中最重要的因素有時不一定是影響源本身,而恰恰是被影響者所處的環境及其時代的要求。”[25]
針對巴爾扎克,昆德拉曾經評論道:“與巴爾扎克一起,它(指小說)揭示了人在歷史中的根源(rootedness)。”[26]巧合的是,陳忠實也對巴爾扎克推崇備至,甚至將他的“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直接謄在了扛鼎之作《白鹿原》的扉頁上。通過這種帶有明顯互文性質的文學評論話語,我們不難發現二者之間創作思想的類同。不論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還是《白鹿原》,二者都將所敘述的內容置于一個動蕩而又特殊的歷史時期,都通過不同人物的情感糾葛和無常命運切入,對當時社會中的謬誤與荒誕進行反思。在反思中,二者又獲得了超越時代的思想升華。對于這種升華,陳忠實稱之為“生命體驗”,而昆德拉的升華部分被學者歸結為“存在主義哲思”。殊途同歸,不論是“生命體驗”還是“存在主義哲思”,二者都深刻表達了禍亂交興的時代對人類生存狀態的關注,進而更深層次地探尋了人類的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也就是說,不論是昆德拉還是陳忠實,二者雖然筆涉不同的國家與時代,最終都超越了這些因素,將思考直指最真實、最根本的人的層面,這不僅是對人性的一種回歸,更是二者作品高度一致的人文關懷之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