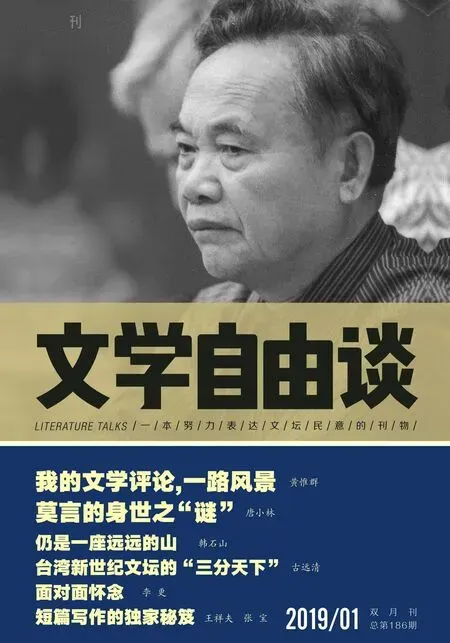時代之大作何以難現
□石華鵬
一 呼喚時代之作
新時代與現實主義,成為一段時間以來頗為熱門的文學話題。投石起浪,事出有因。激起人們談論這一話題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個是人們渴盼出現與這個新時代相匹配的現實主義之作,讓“時代之大作品”的期許落定,而這樣的作品還沒有出現;另一個是有著久遠傳統、深厚土壤和創作實績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今天似乎陷入了某種疲憊之境而缺乏應有的創造活力了,人們呼喚新而有力的現實主義重新復活。
元代學人虞集說:“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所謂“絕藝”,即卓絕的藝術門類。虞集的意思是說,時代之興,也興某類藝術。明代學人王思任說:“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一個時代的作品需傳達一個時代的精神,時代精神把握不準,則作品傳不遠。近代學者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誠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后世”的詩詞曲均“莫能繼焉者也”,但后世之時代也在開辟屬于自己的文學,諸如清之小說、民國之雜文散文等也是別開生面。
時間演進到今天,一個全新時代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物質充盈與生存壓力并存,數字科技與智能生活同構,傳統鄉村與現代都市相交,大眾文化消費與精英精神共存,信息爆炸與媒介更替交織。有人說,這是一個最好與最壞、至繁與至簡、快樂與焦慮的時代。
人們呼喚時代之作,期待出現全面表達這個時代的作品。何為時代之作?概括地說,是指能夠呈現一個時代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的大作品;是指能夠參與到一個時代的精神建構當中,比如提供知識、觸摸真理、塑造心靈等的大作品。
今日時代之作當由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來擔綱。此為共識。許多偉大的作品已經證明,長篇小說是一種偉大的文體,它由長度、密度、難度構成的文本成為一個民族的“秘史”,成為歷史和時代的“交響曲”。長篇小說是文學江海中的一艘巨輪,它滿載人類的故事、經驗、思想和夢想,破風犁浪,駛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港灣。
每個時代都會誕生烙上自己時代印記的文學作品,它所包含的時代背景、時代精神、敘事語言、人物形象等信息留存于作品中,如同隨時等待復活的密碼一樣,成為一個國家大歷史敘事的一部分。這樣的作品早已出現并鑲嵌在我們的歷史進程中,無聲地講述著各自時代的故事,比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楊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劉心武的《班主任》、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等。這些具有時代概括性和歷史參考性的作品,成為文學創作的獨特景觀。
但頗讓人費解的是,二十一世紀過去近二十年,在我們的閱讀記憶中,竟然沒有出現一部或幾部堪稱出色地表達了近二十年來,我們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的時代之作。保守一點估算,我國每年出版長篇小說三千部,二十年六萬部,為何沒有冒出大家公認的時代之作?個中緣由耐人尋味。難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與作品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太近,無法辨別它們的魅力?難道是“一葉障目”“厚古薄今”——我們的審美偏見讓我們對時代佳作視而不見?難道是“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書寫當下時代之難,我們還沒有找到寫出這個大時代精氣神的方法?
幾種緣由或許兼而有之,但面對一個全新時代,我們作家失去了對新鮮、復雜現實的敏銳把握和思考提煉的能力,同時也失去了尋找新的路徑和新的表達的勇氣和雄心,這可能是時代之作遲遲未曾出現的主要緣由。
二 時代與寫作之變
情形大抵也是如此。今天之時代,繁雜多元如網,信息汪洋似海,眾多或隱或現的寫作現實提示我們,作家與時代之間出現了新的矛盾,這矛盾在于,作家正在減弱或喪失的想象優勢、知識優勢和思想優勢與新時代最廣闊的多樣性和最深層的真實性之間的不對等、不相宜、不協調。
自古以來,作家都是阿基米德式的人物,都在尋找那個類似于可以撬動地球的支點去撬動一個時代,印刷時代、廣播時代、報紙電視時代,作家更容易尋找到那個支點——因為讀者獲取的信息量少而單一,作家的想象優勢、知識優勢、思想優勢相對明顯。但是在今天,從物質享用到精神消費,一切天翻地覆,網絡新時代降臨,信息如潮漲潮落一樣海量產生和迅疾流通。一方面,讀者和作家站在了同一信息的高地上,另一方面,構成時代的“點、線、面”復雜多樣且瞬息萬變,作家似乎更難把握所處的時代,更難概括時代的精神實質,更難尋找到那個撬動時代的支點,寫作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種困難和尷尬之中。
但這并不能成為時代之作誕生之難的理由。話往回說,又有哪一個時代不復雜,又有哪一次對一個時代的書寫不是荊棘叢生難度重重呢?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通過描述1805至1820年俄國社會的歷史和生活,展現著整個俄國廣闊和雄渾的氣勢。在有限的敘述時間和空間中如何抵達“時代的偉大史詩”,是托爾斯泰面臨的時代之難。與之相反,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講述的時代背景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加勒比海城市的境況:戰爭、霍亂以及人為破壞,五十年的時代之變如何通過一個愛情故事濃縮起來,讓人得以窺視其時代細節,這是馬爾克斯面臨的時代之難。
無論是托爾斯泰的“以小見大”,還是馬爾克斯的“以大寫小”,每一次對時代的書寫均難度重重,只是今天我們對時代的書寫難度異常突出而已。這難度來源于一個硬幣的兩面。一面是過于龐大而嶄新的時代。城市化推進和科技改變生活——當下兩種龐大的“現實”正塑造著我們的新時代,描摹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圖景。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推進,傳統的鄉村農耕文化日漸弱化,我們的父輩是土地上的最后一代農民,我們的兄弟姐妹奔走于各個城市之間,打工謀生,過著半城市半鄉村的生活。由城鄉對立過渡到鄉村城市化,人的精神現實又經歷了何種嬗變?此外,科技正在打造我們的新生活——足不出戶或遠行千里均可自行選擇,工作和生活系于網絡,自媒體時代正在替代報紙電視時代,信息的發達和暢通讓人們成為無所不知的“上帝”。新生活正在塑造我們全新的觀念和復雜的內心世界,有些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新的時空感覺悄然建立;豐富的社會情態和復雜的內心世界正在悄然形成。一句話,都市文化和技術文化正在塑造新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每一部有價值的時代之作將無法繞開這一現實。
另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滯后于時代。當今天的信息、游戲、影視和廉價小說代替經典小說的敘事魅力時,美國當代著名評論家喬治·斯坦納指出:“在小說家和天生編故事的人之間,已經出現了無言的深刻斷裂”,作家的“想象力已經落后于花哨的極端現實”。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早在1936 年就預言過:新聞信息“給小說帶來了危機”。他將這一切歸咎于經驗的貶值,說:“經驗貶值了。而且看來它還在貶,在朝著一個無底洞貶下去。無論何時,你只要掃一眼報紙,就會發現它又創了新低,你都會發現,不僅外部世界的圖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圖景也是一樣,都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我們從來以為不可能的變化。”
經驗的泛濫和過剩導致經驗貶值的同時,也導致了小說家經驗的逼仄和膚淺,因為經驗的大量傳播和高速度,將具有想象力優勢的小說家置于與讀者平等的地位,小說家經驗甚至不及一個分工細微的職員。所以,在今天的時代,小說家們的想象自信正在被打垮,他們在不斷重復一句話:生活比小說精彩。既然如此,還要小說干什么?還如何寫小說?而過去小說家身上擁有的那種“好的小說永遠比生活精彩”的寫作信念,在今天的時代面前黯然失色。
時代大作難以出現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時代把握之難和作家想象力滯后于現實以外,或許還有一個深層次原因:舊有的長篇小說文體是否無法適應今天的時代了?它是否無法囊括當下龐大而復雜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了?這個時代的表達或許需要一種創新的長篇文體,而這種文體正在醞釀之中。我們的文學變遷軌跡已經見證過史詩和戲劇的衰落,或許它正在見證長篇小說的某種變異。比如網絡小說已經出現了千萬字數的超級篇幅,那么篇幅的延長是否會成為時代之作的新趨勢?德國漢學家顧彬明確表示:“長篇小說的時代過去了,應該回到中短篇小說”,“集中于一個人的靈魂”。他的理由是,長篇小說是一種對整體的渴望,而現代性之一,是全體的丟失,中心的損失。提出“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的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奉勸那些作者不要再野心勃勃地試圖向讀者展示“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他們應該把精力放在描述“一個人對一件事的感受”上。這兩位評論家只是預言托爾斯泰式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在今天的失效,但他們并沒有提出新的解決方式。“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在這個新的時代的節骨點上,時代大作或許會與一種新的表達模式共同誕生。
三 重塑現實主義之魂
作為創作方法,現實主義曾催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品;作為審美原則,現實主義作品曾帶給讀者無數的感動和震撼;作為一種寫作價值觀甚至文學精神,現實主義曾解放了許多作家的寫作思想——如此看來,或許強大的現實主義依然是解時代大作出現之難的有效武器。
當然,今天的現實主義已不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的現實主義,而是拓展了自己在新時代新尺度的現實主義。這新尺度在哪里呢?法國著名評論家羅杰·加洛蒂認為現實主義是無邊的,他說:“每一件偉大的藝術品都有助于我們覺察到現實主義的一些新尺度。”就是說,現實主義的新尺度在新的時代之作里。那么,這里邊出現了一種有趣的互證關系:我們用現實主義創作時代之作,新的現實主義彰顯于新的時代之作里。
無論現實主義的新尺度有何拓展和變化,但現實主義的魂魄一直沒有變,就是尋找無盡現實中的精神沖突和賦予現實新的美學形式,即魯迅先生所說的“表現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別”。我理解,現實主義的根是“現實”——當下那種廣闊的多樣性和復雜的真實性;魂是“主義”——對現實的理解、洞察、價值判斷和精神建構。從現實到現實主義,既考驗作家描摹現實的功力,也考驗作家洞察現實的能力。這道門檻跨過去,時代大作方有出現的可能。
現實主義新尺度的出現和確立,在于對一個時代之文學新路向的把握和新經驗的文學處理上。2018年6月,在江蘇南京召開的第四屆揚子江論壇上,“中國當代文學新路向”成為論壇議題。這是一個具有時代性、歷史性和價值性的議題,這一議題的提出和探討,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正在進入一個全新時代,它與過去的文學正在形成某種真正的“斷裂”,小說家畢飛宇認為:“新一代的作家、新一代的寫作者,他們有自己的思維方式,他們看世界的方式,他們的審美需要,跟我們過去的文學序列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新路向“新”在哪里?“新”在變化之中:文學觀念在變化——探求一種經典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中間道路;寫作主體在變化——“作家”這一職業開始泛化和非專業化,寫作者人數大量增長;文學形態在變化——新舊媒體在交融,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界限在消失,科技因素對文學影響越來越大。
時代大作的誕生有賴于應和文學發展路向上的“新”。“新”即變化,與過去的文學序列發生變化,或應和這種變化,實際上是為寫作確立的新的宏觀方向,舊有的寫作思維方式和表達模式,該舍棄的便舍棄,該調整的便調整。一百年前發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新舊時代交替,文學序列發生變化,古典主義文學終結,現代新文學開啟,當時的文學發展新路向率先由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理論家指出——白話文寫作、為社會寫實、平易的國民文學、“優美之文學,高尚之思潮”等,隨之魯迅創作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與新文學路向相呼應,以時代之作扛起新文學的大旗。由此啟示我們,時代大作的出現需以敏銳的眼力去應和時代之新和文學之變。
從文學內部來講,被拓展的現實主義仍是處理新現實、新經驗的文學手段。本雅明認為,經驗的貶值給小說帶來了危機。這個觀點其實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經驗的泛濫侵占了小說的自有空間,小說的娛樂功能和知識功能弱化;二是小說對經驗的處理呈現出麻木性和無力感,在龐大的經驗面前有些束手無策。如何有效處理新經驗成為時代之作的最大難處。現實主義啟示我們,對現實和經驗的沉淀和提煉,是抵達真實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法,透過新經驗洞察和概括一個時代,只有參與了時代精神建構的經驗才是文學的經驗,所以無論我們時代的現實和經驗多么龐大,去書寫那些與精神建構密切相關的現實和經驗,哪怕它們十分微小也是值得去寫的;如果那些現實和經驗與精神建構無關,即使它們再高大,也是不值得去寫的。
我們不得不追問:今天最大的現實是什么?時代精神是什么?現實主義的新尺度在哪里?
這是三個多余的問題,要么沒有答案,要么有無數答案,但每一個有野心的小說家都無法回避這三個問題,小說家眼里的現實和時代精神,構成了時代大作的思想資源和寫作視野,每一次寫作并非為了給出問題的答案,但每一次寫作均無法繞過這些問題。沒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時代大作的“大”便無從說起。
按照英國學者馬歇爾·伯曼的觀點,今天最大的現實,是“我們所有人被倒進了一個不斷崩潰與更新、斗爭與沖突、模棱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中的現代生活。他說:“今天,全世界的男女們都共享著一種重要經驗——一種關于時間和空間、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種可能和危險的經驗”,“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歷險,去獲取權力、快樂和成長,去改變我們自己的世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要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所知的一切、表現出來的一切”。這種大的現實之下,是與“舊”告別——舊的鄉村、舊的居所、年邁的故人;是與“新”相遇——新的城市、新的居所、新的旁人。這種告別與相遇的變化對個體生命的意義,便構成了小說的價值,也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意義。
如果要為現實主義在今天的新尺度作出描述的話,我認為至少有三個特征:一是日常化的非典型性現實。日常化的非典型性現實的敘述,觸及到了文學最本質的內容:每個小人物、每個普通人物都是一個時代,都是一個世界,對他們的敘述就是對一個時代、一個世界的敘述。“日常化”是回歸生活本來面目的深刻的“日常化”——對每個無名的微小的人和人心的敘述是小說最大的道德和尊嚴。二是朝內轉。每個個體世界,均有內外之別。小說藝術必須朝內轉,背離和拒絕讓人煩膩的新聞式的現實,轉向那個孤獨而痛苦、細膩而復雜的普通人的內心,賦予幽靈一樣游蕩的精神以生活的實質,復活每個個體日常的現實感悟力。三是精致的敘述。敘述一旦開始,將讀者深深吸引住,仍是小說的第一要務。今天的一些優秀小說做到了這一點,它們擁有高難度的敘述技巧、美妙的語言和多元的形式,這種堪稱精致的敘述將毫無耐心的讀者吸引過來。
順著現實主義拓展的新路,我們的時代之大作會出現嗎?或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