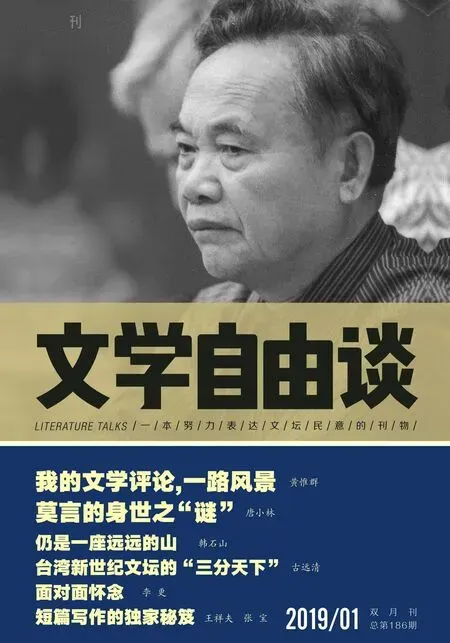仍是一座遠遠的山
□韓石山
能在王府井大街上,一個這么高雅的地方,講講徐志摩,是我的榮幸。有這個機緣,是商務印書館出了《遠山》這么一本好書。這本書,還有個副題,叫《徐志摩佚作集》。這種書,平常都叫“佚文集”,而他們叫“佚作集”,想來是考慮到里面收有好幾種體裁的作品,不全是文。這是一種慎重,也是一種多余。
這本書是我介紹給他們出的,前面有我的序。序里除了對編者給予稱贊外,還說取名《遠山》,似乎在暗示我們,徐志摩仍是一座遠遠的山。
我甚至想過,當年徐志摩去世后,陳夢家給他編了本詩集叫《云游》,用徐志摩的一首叫《云游》的詩做書名,也是有深意的,意思是,志摩先生只是上云端游玩去了,不定哪天就會回來。那是1932年。過了八九十年,再出一本集子,又用了一首詩的名字做書名,叫了《遠山》,意思更深些。會不會是,徐志摩故意留下了這么兩首詩,讓后人給他編兩本書,一本說我走了,你們好好地活著吧;一本是說,我還惦念著你們,在遠遠的山上,而我們呢,只能遠遠地看著他,走呀走,總也走不到跟前。
在當今學術界,無論從哪方面說,我都算是一個對徐志摩有研究的人,寫過《徐志摩傳》,編過《徐志摩全集》,至今仍關注徐志摩材料的發現。若有人問我,現在的徐志摩研究,是個什么水平呢?我只能說,仍在低水平上徘徊,緋聞逸事,才子風流,基本上不知此人的真面目。寫起論文來,碩的博的,論起革命文學家,這個是人格如何,那個是思想如何。你見誰寫文章,說徐志摩的人格如何、思想如何?最普遍的評價,這是一個優秀的詩人。我以為,這樣的評價,對徐志摩這樣的人來說,跟說他是個人,是個男人一樣,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他不是個優秀的詩人,莫非是個平庸的詩人?
不說氣話了。且將徐志摩跟他同時代的三個人作個比較,就能大體估摸出此人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坐標位置。我要說的三個人,都是跟徐有過交集的,一個是郁達夫,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魯迅。他們與徐的關系,分別是同學,朋友,對手。
先說郁達夫。郁和徐,是杭州府中學堂的同班同學,略稱“府中同學”。徐是1911年春天考上,是念完了的。郁也考上了,嫌學費貴,又考到嘉興府中學堂,念了兩個月,嫌路遠又轉到杭州府中,沒念完,辛亥革命爆發,再沒回來。1922年,徐志摩回國不久,郁也來北大教書。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兩人交往甚多。徐死后,郁寫過兩篇文章,表示懷念,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稱贊徐中學時學習好,雖不怎么用功,卻老考第一;二是贊美徐與陸小曼的愛情,仿照電影《三劍客》里的說法,說他就是馬上要死,也要做一篇偉大的史詩,頌美志摩和小曼的愛情。郁是才子,很早寫小說,獲評甚高,舊詩尤其好,被人推為現代作家第一。而徐,一點也不次于郁,新詩可稱第一,散文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從思想觀念上說,郁留學日本,新舊思想混雜,娶王映霞為妻,視為納妾,多次稱王為“王姬”。徐接受的是歐美的倫理觀念,開中國文明離婚之先河,善待前妻,視為好友。大體上說,徐與郁可打個平手,徐略勝郁一籌。
再說胡適。胡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極為尊崇,有“現代孔夫子”之譽。胡與徐是好朋友,徐視胡為大哥。但平心而論,徐有三點超過了胡:一是學術訓練。胡有博士之稱,但學校的經歷,卻乏善可陳,在國內上過中國公學,考上留美官費,到美國在康乃爾大學,先學農科,后轉文科,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論文是關于中國古代哲學的。徐就完善多了,國內在北京大學,學的是法學;到美國在克拉克大學,學的是史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是政治學,畢業論文為《論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到了英國,跟上拉斯基學過經濟學,跟上狄更生廣泛接觸英國名流,參加過英國的基層選舉活動,為工黨拉票。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徐的訓練更全面些。二是見識上,有的地方徐比胡高。1926年胡經蘇聯去英國,路過莫斯科停了一兩天,便著文贊美蘇聯的教育成績。徐在《晨報副刊》發了胡的三封信,同時給以批評。氣量上,也是徐比胡大。新月書店剛成立,胡一時氣不順,要抽出自己的股份,徐勸后收回。三,文學才華上,徐明顯高于胡。胡的《嘗試集》,只能說是新詩胎兒期的牙牙學語,而《志摩的詩》,則已朗朗成誦。
末后說魯迅。魯迅的最大成績,是小說,徐是新詩,在這上頭可打個平手。魯為人稱道的是雜文,徐有許多社會問題的隨筆,實則是雜文,也別有風采。魯中年之前,在社會理念上,看不出什么高明的地方。徐則不然,尊崇科學與民主,辦社團,辦刊物,為中國社會的進步著實努力,從不放棄。他最初的理想,是要做個中國的漢密爾頓(美國開國元勛),一直到死,都是個赤誠的愛國者。魯曾作詩,諷刺徐,頗狠毒,徐未回應。再偏向的人,怕也只能說——不是說而是感到,在徐的毫不在意的寬容面前,魯是個顏面盡失的敗北者。魯的晚年,信奉共產主義學說,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這是魯的光榮與進步,不可多說什么,但我們總可以說,徐也是一個有理想、為社會負責的文化人。
這樣我們就可以轉到《遠山》這本書上了。
看書,要會看。不要老想著學知識。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那是學生娃說的。小學生是學生娃,中學生是,大學生是,碩士博士,都是學生娃。娃就是還沒長成人。三四十歲的人,工作了的人,看書要抱著欣賞的態度,才能輕松自如,也才能堅持下去。這世上唯一能堅持下去的事,只有玩。寓教于樂,寓學于樂,就是要把學習滲到你的骨子里去。能從欣賞中得到教益的書,才會起到這樣的作用,也才是真正的好書。
前些日子,在現代文學館參加一個新書發布會。會上,一個常去日本的學者,很是贊賞日本的“口袋書”,說是價廉物美,便于攜帶,如何的好。說我們的書太貴了,又是精裝,又是塑封,如何的貴,讓人買不起,看不上。輪到我發言時,我委婉地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我認為,書的裝幀設計,一定要貴相,要講究。好到什么程度呢?要好到平日插在書架上不丟份,過年清理雜物時,舍不得賣了廢品。不說內容了,光封面設計,整體制作,這本《遠山》,也是達了標的。你看這色彩,多柔和,多入眼;這設計,多簡潔,多典雅。聽說設計者是呂敬人先生的學生,看來這學生沒白當。
內容,就更不用說了,是我看上眼,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的。不是事中人,絕然想不到,這些年來,研究者們翻騰出這么多徐志摩的佚作。當初兩個編者之一的陳建軍先生,將電子文本發給我看。我覺得夠多的了,足夠出本書,便推薦給商務印書館。沒想到的是,在等待出版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達到141篇(首)。另一個編者徐志東先生,也參加進來。當然,這些佚作,不全是他倆搜集的,好些是匯集過來的。容量大了,質量也更高了。我敢說,這本書的出版,必將推動徐志摩的研究往更深的向度發展。一本書的好壞,在研究上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繞得過去繞不過去。《遠山》在往后的徐志摩研究上,肯定是一本繞不過去的著作。
編過全集,寫過傳記,對徐志摩研究的脈絡,我還是清楚的。
改革開放之前,對徐基本上是潑污水,諷刺謾罵。改革開放后,好長時間也無人插手。最早著手研究徐志摩的,是他家鄉海寧市的一位文化人,叫顧永棣。我去海寧時,見過這位先生,高個子,像個北方人。他編了本徐的詩集,交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后來還寫了本傳記。現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的全集,就是他編的。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徐都沒有熱起來。要熱也是暗地里熱,沒有明著熱起來,只冒煙,沒明火。
頗能說明這一現象的是,1997年我的《李健吾傳》出版,朋友圈都知道我能寫傳記。在山西工作過的老熟人丁冬先生,趁空兒給他妹妹組稿。他妹妹叫丁寧,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當編輯,正在編一套現代作家傳記叢書,已到尾聲,名單上還有三個人,找不到寫手,問我能不能寫一個。我問是哪三個要寫,說是馮雪峰、何其芳、徐志摩。我連想都沒想,就選了徐志摩。如果是現在,一長串名字擺在那兒,都會爭著寫徐志摩。
在徐志摩的研究上,我的“徐傳”是個標志。這個標志說來可笑,甚至被人攻擊是下流。什么地方下流呢?我考證出徐志摩和陸小曼發生性行為,突破男女之大防,是在哪天晚上,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舉了許多證據,寫了好幾百字。接下來說,沒有更為確鑿的證據出現之前,基本上可以斷定,是1925年1月19日。這天晚上,在北京松樹胡同七號,新月俱樂部的院子里,胡適做東,客人有章士釗、林長民、陸小曼等。酒宴之后,大家都走了,陸小曼留下了。徐志摩不能叫做客人,他就住在這兒。就是這天晚上,干柴烈火,一點就著。
前不久,有位青年學者采訪我,說揭示性生活,是當今世界傳記文學的一個新走向,你怎么能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注意到了?我說不是我意識超前,是我尊重人性,覺得這不算個事兒。這個蓋子揭開了,徐的好些“艷詩”,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我是從我寫傳上考慮的,沒有顧到世界傳記文學的什么什么。
我把我的“徐傳”,作為徐志摩研究上的一個重要標志,且是這樣的內容,有人聽了會暗笑。不要暗笑,明笑好了,大笑好了。只是笑過之后,要想一想,這不是個膽量問題,更不是個品質問題,而是個見識問題。對那些批評我、挖苦我的人,能說什么呢?再厚道也得說句“智不及此”吧。
從2001年“徐傳”出版,到現在十好幾年了,徐志摩的研究,并沒有大的進展。卡在哪兒了?卡在材料上了。傅斯年說過,歷史學就是材料學。研究人物也一樣,材料起很大的作用。這么多年,沒有新的材料發現,徐志摩的研究,就一直處于“平不塌”的狀況。
現在不同了,《遠山》出版了,發現了大量的新材料,必將推動徐志摩的研究向更深廣的層面進展。這本書里,詩啦,日記啦,沒什么新鮮的,有看頭,但意思不大。會看,才能看出點意思,不會看的,也就是那么回事。最值得關注的,是散文里的三組文章:一組是1920年8月發表在《政治學報》上的《社會主義之沿革及其影響》等文章,一組是1916年發表在滬江大學校刊《天籟》上的十一篇文章,一組是1921年到1924年間,給英國人奧格登的六封信。
《社會主義之沿革及其影響》等文章的發現,可以確立徐志摩傳播社會主義先軀者的地位,這就不用多說了。《天籟》上的文章,是華東理工大學的研究者發現的。滬江大學的地方,解放后給了華東工學院,華東工學院如今成了華東理工大學,這樣一來,滬江大學的資料,就歸了華東理工大學的圖書館,這樣研究者才能在校刊《天籟》上找到這一批文章。這一批文章的發現,補充了徐志摩學歷上的一個盲點,確認徐志摩的學歷里,有滬江大學這個環節。
在這上頭,我是丟過人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研究徐志摩的時候,編年譜,寫傳記,對徐有沒有滬江大學這個經歷,一直持懷疑態度。在陳從周的《徐志摩年譜》里,確實寫著哪一年冬天,肄業于滬江學院。記得是這么句話,不一定準確。在梁錫華的《徐志摩新傳》里,還有梁錫華從克拉克大學圖書館查到的,滬江大學開出的成績單,按說不該懷疑了。我的疑點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這個地方上過大半年的學,就該有同學。徐志摩的名氣那么大,怎么死后沒有一個滬江大學的同學寫紀念文章呢?于是我便懷疑,徐的滬江大學的成績單,是徐申如為了兒子赴美留學,下了點功夫,從學校走門子開出來的。這樣想了,也就這樣寫了,寫在一篇名為《徐志摩學歷的疑點》的文章上,又收入《尋訪林徽因》這本書里。此書流傳到臺灣,臺灣的一位名叫秦賢次的先生看到了。此人是個史料專家,做學問很是嚴謹。不知是查了資料,還是手頭就有材料,他著文斥責我胡說八道,以臆想代替史實。文章發在2009年某期的《新文學史料》上。我剛看時,也挺惱火的,想寫文章回擊。后來一想,做學問嘛,就是要弄清史實,誰弄清就聽誰的。正好這時候,《徐志摩傳》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要我寫個新序。寫了,也就六七百字,我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感謝這位臺灣學者的指謬。再后來,我買到法學家吳經熊先生的自傳,上面說到跟徐志摩是滬江的同學。這次這批《天籟》上文章的發現,不光確認了,也充實了這段經歷,有人再寫“徐傳”,可增加一章。
最最重要的,還是給奧格登的六封信。這是近年來,徐志摩研究的重大發現,也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主要內容。
先說發現的經過。這幾封信,是北師大學者劉洪濤,在英國訪學時發現的。他寫過一本書,叫《徐志摩與劍橋大學》,臺灣秀威書局印行,給過我一本。書中說,發現這組書信,純屬偶然。他看過梁錫華的《徐志摩英文書信集》,想看徐的原信,但書中未注出處。他去英國,是做訪問學者,名義上是研究羅素與中國。找到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地址,寫信問羅素的檔案,得到許多收藏有羅素檔案的機構名單,其中有加拿大的一家,是馬士德大學圖書館羅素檔案館。寫信去問,館長復信說,他們這兒還收藏有徐志摩給奧格登的一些信,問他要不要。劉先生大喜過望,不久便得到復印件。這批信件,成為他后來研究徐志摩的核心資料。
現在來看看奧格登是個什么人。他1889年生,1957年去世,比徐志摩小兩歲,活了六十八歲。他是劍橋大學的學者。這些信怎么到的加拿大,就不多說了。奧氏1912年創辦《劍橋雜志》,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有關戰爭與政治的國際論壇。奧氏又是劍橋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想組織的創辦人之一,這個組織叫“邪學社”,成立于1909年,起因是奧氏等人對校方強制學生參加宗教活動挺反感,想營造一個能自由討論宗教問題的空間,推動宗教、哲學和藝術的自由討論。主要活動方式,是邀請文化、思想、文學界名人舉辦演講。奧氏先任學社干事,后長期擔任主席。他是個天才的組織者和鼓動者,搞得有聲有色,吸引了大量的劍橋學子。從徐志摩1922年1月給羅素的信看,徐在劍橋,雖沒有加入邪學社,卻能夠參加演講會,可見徐與奧氏及其他邪學社成員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
對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期間所受的影響,劉先生是這樣說的: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是劍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以三一學院、國王學院等學院為代表的劍橋大學,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學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屬于英國上層知識分子團體布盧姆斯伯里集團的成員,是英國現代主義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徐志摩與他們中的許多成員都有密切的交往。徐志摩與英國當時漢學界的代表人物卞因、翟理斯、魏雷等人有深厚的友誼,與作家威爾斯交情甚篤,拜訪過哈代、曼斯菲爾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徐志摩全方位地介入到了英國當時的思想文化運動中。
我的感覺是,以往談徐志摩與英國文學的關系時,往往強調浪漫主義對他的影響。因為這樣的影響,就說他是個浪漫派詩人。反正不是革命詩人,挑個不好不壞的名頭給他算了。看了劉先生的文章,我覺得,這種影響當然很重要,但徐志摩在英國,親身經歷的這種文化、思想的活動,對他的影響可能更大些。最為明顯也最為可貴的是,他把這種人際交往,這種組織方式,帶回了中國。在北京辦新月俱樂部,在上海辦新月書店,都有邪學社的影子。
可惜的是,國內的研究者看不到這樣的承續,也看不到這樣做的意義。在現代文化人物的研究上,用的最嫻熟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相面術,二是看出身。徐志摩長了個好模樣,招女人喜歡,也喜歡女人,又寫詩,當然是個浪漫詩人;留學美英,當然是受外國文學的影響。這不是相面術是什么?
徐志摩的父親是大資本家,也是大地主。中國的鄉鎮資本家,沒有不是大地主的。有這樣的出身,必然有許多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惡劣品質。好的品質是遺傳的,壞的品質也是遺傳的。于是,徐志摩不花花公子,也花花公子了,何況他看著還真的就像個花花公子呢。是花花公子了,怎么不是革命的對象呢?于是對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乃至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眾多作為,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比如早在1929年,他就組織并主持“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這事若是“魯郭茅巴老曹”中任何一個人做的,早就喧到天上去了。
在中國文化里,評價人時候有個奇怪的規律,可稱之為“轉移性泄憤法則”,就是,對一個文化人,若他有某一方面的苦難或是缺憾,對他的另一面,就特別的寬容或寬厚。比如胡適,有個小腳太太,就覺得他的品質一定特別的好,不好也是好。郁達夫嘛,死得那么慘,別說是個進步作家了,說是個革命作家也不為過。魯迅嘛,婚姻那么不幸,思想怎么能不深刻呢?就這個徐志摩,要錢有錢,要貌有貌,要學歷有學歷,要情人有情人,哪樣都比自己強,怎么會是個好人呢?殊不知,中國文化有個強大也特殊的規律,就是“世家子現象”。多少代的積聚,到了某一代,常會出現極為杰出的人物;徐志摩就屬于這種情況。除了這個,別的解釋,都說不通。
單說徐志摩的讓人不服氣,再舉個例子吧。兩彈元勛鄧稼先,這可是個英雄人物。一般人說起來,只說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畢業于西南聯大。實際上,他的身世要顯赫得多:祖上是中國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父親鄧以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學美學的,回國后在北京大學任教,與胡適、徐志摩都是好朋友。這樣的身世,才會有鄧稼先這樣優秀的子弟產生。不要動不動就說,信了什么才會什么什么。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說,評價徐志摩這樣的人,要有持平心,要放在中國文化史、社會進步史的層面上衡量。只說他是個優秀的詩人,實在是小氣了。
我寫“徐傳”時,每每有這樣的困惑:徐在國內嘯聚友朋,抱團結社,南征北戰,興致勃勃,從不氣餒。后來有些疲累了,但意氣未衰,只能說是苦撐待變。這一套學誰的呢?我先前想的是學漢密爾頓。這個美國開國元勛,辦過報紙,寫過政論,精通憲政的一套。但總覺得太大了,也太遠了,有點“八竿子打不著”的感覺。又想,會不會是劍橋國王學院的狄更生呢?也不像。徐志摩去找狄更生,狄外出活動,回來見這個中國青年坐在門前臺階上等他。都不帶他出去活動,能是怎樣的親近?連親近都沒有,又能怎樣的效仿?至于羅素、哈代、曼斯菲爾德等人,就更不著邊際了。
奧格登,只會是奧格登。你看嘛,奧氏是組織社團的高手。劉洪濤在介紹文字中說,在邪學社成立之前,劍橋已有了一些類似的組織,如著名的使徒社便是其中之一。邪學社后來居上,風頭甚至蓋過了使徒社。徐回國后,與各色人等的交往,更是盡顯奧氏的交際本領。還有,奧氏對出版的興致,對徐志摩不會沒有影響。奧氏組織出版的“國際文庫”,徐曾參與其事,推薦了梁啟超和胡適的著作入選。徐后來接受中華書局的聘任,當特邀編輯,一套一套地編書,未嘗不是仿效奧氏的胸襟與做派。正趕上國內新文化運動狂飆驟起,又有梁啟超預先為之布局,這個年輕人便借風揚沙,施展身手,三拳兩腳,便把自己打造成新文化運動的明確的倡導者,切實的組織者。
這樣說,只是我的一孔之見,是不是這樣,且往前走著看吧。好在那座山,離得雖遠,山上的紋路,卻越看越清了。
《遠山》中有許多佚文,從欣賞的角度看,還是蠻有意味的。比如《結婚日記》,若細看,就知道不應起這么個名字。徐志摩是1926年10月結的婚,日記里的是1926年3月底到9月初的事。實際情形是,兩人結婚前,在北京中街的一所房子里,有過一段同居的日子。這束日記,該叫《同居日記》。既是同居日記,其親熱也就不同尋常了。還有《遠山》這首小詩,細品一下,是不是有《沙揚娜拉》的味兒?好書是可以把玩的,能把玩的書,才能激發讀書人的靈性。
不多說了,在這秋雨綿綿的日子,有這么一本書,可以消磨你許多的閑暇。地鐵上拿出來亮一下,會收獲許多羨慕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