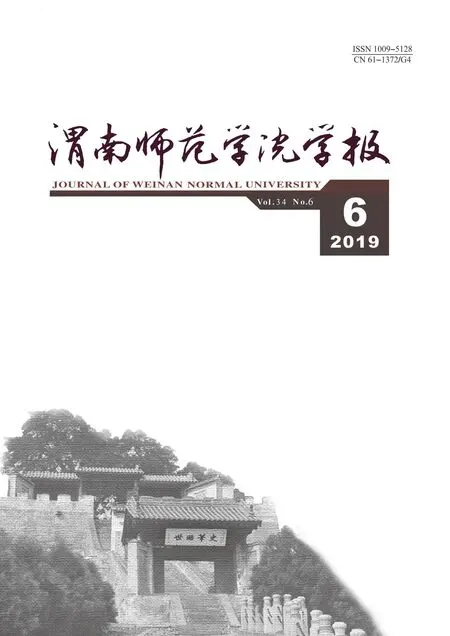莎士比亞政治之園探微
馮 宏
(渭南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陜西 渭南 714099)
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作品對于園林的描寫非常繁盛。文學作品中的園林有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巨匠們對于現實園林的描寫,亦有對于虛幻園林的瑰麗奇特想象。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巨匠,他的詩作中秉承了文學復興時期園林寫作的特色,也有自己獨特的園林創造。“漢金斯指出,莎士比亞作品中總體上有三種‘花園’:除了‘人體—花園’外,還有‘大地—花園’和‘大宇宙—花園’。”[1]43這里的花園實指園林,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對園林的指稱也用了更為豐富的英語詞匯,有直接使用Eden和paradise,如《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場;有時使用garden,如哈姆萊特第一幕第二場用此詞;有時使用orchard,如《凱撒》的第二幕第一場用此詞;當然還有更豐富的詞匯來表現,如park,grange,churchyard和field等。這些詞匯在莎士比亞對于園林的描繪中只是使用了不同拼寫形式,但總體而言其隱喻意義卻沒有大的差異。在漢語中以上英語詞匯被譯成伊甸園、花園、園林、苑囿,花圃、農莊等等。這些詞匯只是在統指莎士比亞對于園林的描述過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漢語譯詞罷了,它們的隱喻意義并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即這些詞匯無論是英語還是漢語,指稱都是“園林”。
關于莎士比亞如何借助園林表現他對于政治問題的問題思考,澳大利亞作家和西方著名的女權主義作家、思想家杰梅茵·格里爾說:“莎士比亞對于思想問題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興趣,但是他并沒有選擇把這些思想觀點簡單化、格式化,或者試圖調和或者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2]186莎士比亞在戲劇創作中有關人類思想問題的思考根源是西方文學藝術作品的源頭,基督教的圣典作品《圣經》;依照杰梅茵·格里爾的觀點,莎士比亞并沒有解決我們實際生活中存在的諸多沖突,當然他也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復雜的思想問題,僅只向我們展演了生活的現實,啟發我們去進行深度地思考。美國著名思想家、政治哲學家、翻譯家和教育家蘭·布魯姆在《莎士比亞的政治》中說:“不理解道德現象的政治科學是粗鄙的,而不為正義之情所激發的藝術是瑣屑的。”[3]1莎士比亞之偉大在于他借助園林表達了他的政治洞見,園林標示了政治的歡愉,園林標貼了政治的友誼,園林更是隱含著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以下僅就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進行探討。
一、政治之園的源頭與現實
圣經舊約的開篇《創世紀》第三章主題是“人類的墮落”(the Fall of Man),它的源頭是伊甸園(Eden),也正是上帝給人類在天堂創造的美麗的花園(garden)。在上帝給人類創造的花園中,花園的功用是產出人類的智慧之果或是文明之果,即禁果,可以明辨是非善惡,但同時又是原罪的開端。智慧的第一要義即分辨善惡[4]57-62,給人類以無限智慧的花園,當人類無法明辨是非,無法按照上帝的意旨在這樣的花園中生活時,無疑它就成了與智慧相悖之所——制造罪惡之所。莎士比亞筆下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很多就是在園林之中發生的。這樣的發生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必然。
圣經中的花園產出了人類的智慧之果或稱人類的文明之果——蘋果,唯此一種已經將人類帶入了墮落又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蘋果也成了上帝給人類的罪惡之果與淫蕩之果。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西方的文學作品一直在重現蘋果給人類所帶來的隱喻。更有趣的是現在的高科技產品——蘋果手機也使用了一個殘缺不全但堪稱完美的蘋果圖案作為它的logo,實際是在提示人們,“蘋果”雖好,但可能會給人們帶來某種致命的傷害,是人類新的罪惡的來源。
人類走出了伊甸園,進入了地球這個大花園。整個世界都在花園之中,但也處處充滿了人類社會政治所帶來的幽微與晦暗。漢金斯所指的人體之園,喻肝臟為大海,血管為江河;大宇宙之園即大地,因此在莎士比亞的筆下英國整個國家也就是一座大花園。在《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場中這樣描寫英國大地這個大花園:
我們這個歷代帝王的寶座,王杖統治的海島;這片崇高的國土,戰神的駐地;這個人世的伊甸園。小型的天堂;這個大自然為自己營造,用以防止疾病傳染和戰爭蹂躪的催壘;這個幸福的民族,小小的世界;這枚鑲嵌在銀色海面的寶石(大海環衛著它。有如深溝高爭,以免天恩較次的國家對它覬覦垂涎),這神靈呵護的土地;這個世界,這片天地,這個英格蘭。這個乳母,這個孕育了無數高貴國君的多產的鄉邦,曾因它的英雄豪杰而令人敬畏,因它的志士仁人而聲威赫赫,因它長征異域對基督教事業的貢獻和真正的騎士精神而蜚聲海外,遠及頑強的猶里——幸福的馬利亞之子、人世的救主耶穌的陵墓所在之處。可現在,這片人杰地靈的土地,我深情摯愛的杰出的國家卻被租了出去,幾乎成了一片承租者所有的土地,無價值的農場。這勝利的大海環衛的英格蘭,它的峻崖峭壁能擊退海神的覬覦圍困,現在卻為恥辱所包圍,為幾張墨跡斑斑的臭羊皮紙所桎梏;往日習慣于征服異國的英格蘭現在卻可恥地被自己征服——一提起此事我便悲慟欲絕。啊!若是這丑事能隨我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即將降臨的死亡將是我多么大的幸事![5]511-512
莎士比亞一生一共寫了十部歷史劇,《理查二世》是劇作創作將達到巔峰時期完成的一部歷史劇(1595年完成),這樣的描寫很明顯地給觀眾傳遞一種信息:英國大地花園上演的一幕幕戲劇無不與當時的政治轉型期的現實有關——伊麗莎白的中央主權由于她的開明政治剛剛得到鞏固,王室跟工商業者及新貴族的暫時聯盟尚在發展,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后國勢大振。雖然這些讓作者對當時的英國政治生活充滿樂觀主義情緒,相信人文主義思想可以實現。但在平靜的社會發展背后,莎士比亞也看到了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英國在農村進行的“圈地運動”正在加速進行,“圈地運動”對當時農業社會的主人帶來的唯一后果就是把他們的家園蠶食殆盡;英國王室的王權和新興資產階級及新貴族的暫時聯盟由于不可調和的因素正在分崩離析;后繼者詹姆士一世的揮霍無度和倒行逆施,更是讓英國社會的陣痛加劇,各地各階層的反抗迭起。社會矛盾深化重結,政治經濟形勢日益惡化,也似人類在伊甸園中因食禁果而被上帝驅離將在地球這個大花園中所遭受的苦難一般,莎士比亞正是在這一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之下充當了上帝的信使,把這一信息重新以劇作的方式帶給英王及其在英國“大花園”中居住的子民。
在這樣的文化轉型、政治碰撞的年代,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必然會受社會變動所帶來的主導意象或類比符號影響而帶有一定載負著那個時代政治與文化的復雜的信息。在莎士比亞的政治劇創作中,尤其是那些重現英國重大事件的十部歷史劇中,這種圣經中所主導的意象,一方面承襲著英國的文化傳統與理念,不斷修正與加重本身的政治文化內涵與意蘊,一方面在劇作文本中清晰地展現各種各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存在的明爭暗斗,在每一部完成的劇作被呈現在觀眾面前時都在傳達著那個時代的真實而獨有的政治氣息。我們細讀文本后會發現,對整個莎士比亞劇作的主導意象進行歷史化和政治化的剖析和闡釋深層挖掘所得到的正是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
二、政治幽微與晦暗之園的展演
莎士比亞對政治幽微與晦暗之園的展演主要集中在他的戲劇創作的盛期,即1601年到1607年之間。這一戲劇寫作階段以悲劇為主,寫了3部羅馬劇、5部悲劇和3部“陰暗的喜劇”或“問題劇”。也可以看到四大悲劇全部完成于這一時期,1601年完成《哈姆萊特》,1605年完成了其他三部。在莎士比亞創作的盛期,從當時的社會形態演變來看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17世紀初期,伊麗莎白女王一世與詹姆士一世政權交替之際的現狀——英國社會政治矛盾激化,社會政治生活丑惡日益暴露——盡數讓處在劇作創作巔峰時期的莎士比亞所目睹。這一時期,莎士比亞的創作思想和創作藝術走向成熟,他的人文主義理想同殺伐紛爭的社會現實發生著激烈的思想碰撞。他對于英國這個“大花園”的美好期許與理想難以在和諧的“理想之園”的現實之園中實現的悲痛,因而他的創作由早期的贊美人文主義理想轉變為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批判,因此也就有了我們得以在他創作的盛期看到的政治花園的幽微與晦暗。
政治花園的幽微與晦暗其實在莎士比亞創作的盛期之前就已經有所發掘,這就是寫作于1598年的《裘力斯·凱撒》。當然我們知道這部劇創作的具體時間與莎士比亞創作的盛期只有兩年之隔,所以從廣義來講,也可以算莎士比亞創作準盛期的作品,僅從絕對具體的時間點上嚴格劃分任何一位作家的創作時期都不能算是恰當的,甚至于是荒謬的,因為作家的思想成熟并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一個過程,是需要一段時間構筑的過程。《裘力斯·凱撒》是莎士比亞對于當時現實社會所帶來的政治花園的幽微與晦暗的展演舞臺嘗試。
《裘力斯·凱撒》一劇的第二幕第一場勃魯托斯密謀刺殺凱撒的地點正是花園(orchard)。在花園中,凱撒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勢很可能使勃魯托斯感到心里不平,因而想擁有權力的虛榮心勾起了他的嫉妒心,刺殺凱撒的陰謀在原罪的發生地醞釀著。由于勃魯托斯一些個人的目的,正如當年誘使夏娃偷食蘋果的蛇,心地并不十分磊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就是他不僅僅一個人在制造罪惡之所的花園中謀劃,而且還招來了他的同黨一起密謀。
勃魯托斯的虛榮心和個人野心,從他在花園中的獨白可以看出。雖然他一再聲稱他個人與凱撒之間并沒有私人恩怨,并將此行動美化為只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但當他知道凱撒所擁有的權力,正是從大眾利益考慮民眾賦予凱撒這樣的權力,對于這些權力凱撒并沒有以獨夫之力搶奪來的時候,他又自認為把這些權力賦予了凱撒,就是“等于我們把一個毒刺給了他,使他可以隨意加害于人。把不忍之心和威權分開,那威權就會被人誤用。”威權在凱撒的手中會被誤用,那么這樣的威權到了誰的手里不會被誤用?除了勃魯托斯之外,恐怕他是不會相信任何人了。“為了怕他有這一天,必須早一點防備。既然我們反對他的理由,不是因為他現在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地方,所以就得這樣說:照他現在的地位要是再擴大些權力,一定會引起這樣那樣的后患;我們應當把他當作一顆蛇蛋,與其讓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還在殼里的時候就把他殺死。”[6]231這里他表明沒有什么可以指責凱撒的地方,但卻像夏娃一樣受到了誘惑,吞下了人類的禁果,欲辨未來的善惡。他把自己視為羅馬未來的救世主:“羅馬啊,我允許你,勃魯托斯一定會全力把你拯救!”[6]232個人的虛榮心膨脹,他也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喜愛光榮的名字,甚于恐懼死亡”[6]216。結果卻是吞下禁果后,走出了花園,實施了罪惡的刺殺行為。
第二幕第一場中的花園密謀,當問到路歇斯及與路歇斯同謀者的情況時,當路歇斯說因為這些人的偽裝無法分辨身份,勃魯托斯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嘆:“陰謀啊,你在百鬼橫行的夜里,還覺得不好意思顯露你的險惡的容貌嗎?……陰謀,還是把它隱藏在和顏悅色的后面,因為要是你用本來面目招搖過市,即使有幽冥的地府也不能把你這遮掩過人家的眼睛的。”[6]232花園的幽微與晦暗在勃魯托斯的心里已經非常明顯,然而他卻不能分辨是非,還要把他的原罪更深一步地表現出來,走向罪惡的深淵。
勃魯托斯一切行為的驅動力還是潛藏在他心底的權力欲念。在刺殺了凱撒之后,他的良知告誡著他,他始終無法擺脫超我的束縛,在原罪與上帝的寬恕中,他最后選擇了自我的解決方式,這也是體現了上帝對原罪的仁慈。最終的自絕才實現了他徹底的解脫,當然最終的死亡也是他的必然結局和最終歸宿。“因為只有勃魯托斯能夠戰勝他自己,誰也不能因他的死而得到榮譽。”[6]302
在揭示人物思想深處的活動,刻畫人物的真實性格方面,戲劇中的獨白往往比人物之間的對話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莎士比亞的戲劇尤其如此。《哈姆萊特》中的主角因為父王的遇害與探查真相的原因,更多時候只能凸顯心理活動的外在表現形式——獨白,來說明政治幽微與晦暗在原罪人類的驅動下所展演的情況。第一幕第二場中丹麥王子道出了一個虛構的花園:“一個荒蕪不治的花園,長滿了惡毒的莠草。”[7]14哈姆萊特有這種看似惡毒的比喻,是因為哈姆萊特對于王室及他所成長的周圍世界,如他的父王被謀殺,他的生母成了父王死亡的幫兇,他的叔父以更大的欺騙在掩蓋這一切,還有他父王以前的近臣也在蒙蔽著他的內心,讓他對于人世有了一種原罪的惡的認識,他認為整個王宮竟然成了“荒蕪”與“惡毒”的代名詞,政治幽微與晦暗在他的眼前已經昭然。
花園這塊罪惡的發源地對這位王子提出了一個嚴正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原罪的命題似乎是上帝送給人類的謎語或是讖語。無論在英語世界、漢語世界還是整個人類世界,成了一個說不完又值得津津樂道的話語。對其多元的解讀似同與“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般,是與非、對與錯、生與死、生存或毀滅、存在與否、忍受或反抗等等,無論被解析成擬或更多的意義,都在說明一個核心:在上帝的花園中因為人類有了原罪被懲罰,受苦受難是人類萬劫不復的命運與生命循環的命題。
哈姆萊特的母親與叔父“或稱之為繼父”因為花園中犯下的罪孽,心里整日惶惶不安。他們在圣潔的“王宮”花園中犯下了世代如其他人類一樣可能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惡。雖然從表面看來他們是光鮮的、平靜的,但上帝在所造的花園中,當人類吃下禁果時,事實上偷食禁果的人類始祖當天并沒有真的死去,只是給自己的后世與后代未來的生活埋下了惡果。這正應驗了蛇的坦言相告:“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世紀》3:4-5)但是他們的心里還是害怕的,喬特魯德在哈姆萊特嚴詞批駁時并沒有任何的辯解,在王子的婚姻問題上這位母親也沒有任何反對意見,雖然對她來說王子的婚姻不是很令人滿意,最后她的死也是作者對起于原罪的丑惡的否定,也算得上是對已經逝去的國王的一種現實懺悔。莎士比亞在劇中情節的進一步展演,王后被自己愛的國王的弟弟,她的現任丈夫的毒酒毒死應該是她的作繭自縛;后繼國王克勞狄斯對自身所做的一切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知道自己:“我的罪惡是臭氣熏天了。”他禱告過,禱告是對他原罪的認識過程與自省,但原罪在釋放之后已經無法彌補,只有通過認知原罪作為心理上的補償。罪惡的人心里的善念很難得到釋放,故在禱告時卻從不欺騙上帝,只是在世間,作為亞當的后代努力消除自己身上可能的原罪。所以新任國王心頭的殺機與貪念始終占據著他的內心——王冠、野心和王后,因為他把花園中吃了禁果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重新演繹。克勞狄斯的性格明顯是勇于攫取與占有的資產階級形象,而不是中世紀的封建君王。在他身上體現出現代人的生存樣式:“世界不再是真實的、有機的‘家園’,而是冷靜計算的對象和工作進取的對象,世界不再是愛和冥思的對象,而是計算和工作的對象。”[8]20
之所以這部劇作的發生地在花園里,而且有人類倫理問題的實踐與思考,因為《圣經》最早的倫理禁忌體現在“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禁果上。人類始祖偷吃禁果帶來了性意識的覺醒,也引起了倫理關系的巨大變化。禁果反映了早期人類對血親婚姻亂倫關系的本能恐懼,到了文明階段,上帝頒發了對“亂倫”的禁令。就古代猶太民族而言,“亂倫”即指違背猶太律法的血親或姻親之間的不倫行為。[4]57-62因此莎士比亞借助于政治權力,無論是大權力還是小權力,通過花園來警示人們身上一直帶有的原罪。
原罪的來源之物——蘋果同樣出現在四大悲劇之一的《李爾王》中,在戲劇開始就把這一禁果之物展演在觀眾面前,當然,聰明的觀眾從這一意象所帶來的隱喻中已經明察到戲劇的發展結局終究是悲劇。
考狄利婭是這一部悲劇中的女主人公,出場不多的她卻有著豐富的內涵和意義,她承載了莎士比亞對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的詮釋與外化。在《李爾王》全部的二十六場戲中,只在第一幕第一場,第四幕的第一場、第四場,第五幕的第二場、第三場中出現過,其中在第五幕中的第二、三場她還是個沒有一句臺詞的過場人物,臺詞總共還不足一百行。這么少的臺詞對一部戲劇的重要人物來講令人難以置信,這在所有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但是莎翁就是這樣,僅用寥寥數筆,百余字就給我們展示了這一重要人物無比豐富的內涵和心靈——對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的揭露,同時在真理和正義的一面,她也有努力消解人類的原罪,對其加以維護和忠誠,讓我們看到了她在人類在原罪面前的嚴肅態度,我們敬仰于她的不再是原罪顯現后的懺悔,而是對原罪本身的自我救贖;但是人類的原罪之深重,不是她一個人這樣做可以拯救整個人類的。她的悲劇,深深打動著我們每一位觀眾的心靈,扣問著我們的心靈,令人難以釋懷,令人深思。從某種層面上講,她是與夏娃相類的形象,接受了明辨正義與分辨善惡的邀約,但卻無法逃離原罪最終帶來的惡果,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最終還是讓她的努力毀于一旦。
李爾王在他的大女兒和二女兒對他的一番恭維與贊譽溢美之后,當李爾王問到他的小女兒對他在還沒有深思貿然分割財產時的態度時,他的小女兒以真實性情表達了對此事的看法。這樣的回答引起了李爾王的暴怒,認為他的小女兒沒有良心,于是當著眾人立刻宣告剝奪了小女兒的財產繼承權,也讓她失去了自己的求婚者勃艮第公爵而遠嫁法蘭西王。李爾王的諫臣肯特被要求在六天之內必須離開這個國家:
我現在寬容你五天的時間,讓你預備些應用的衣服食物,免得受饑寒的痛苦;在第六天上,你那可憎的身體必須離開我的國境;要是在此后十天之內,我們的領土上再發現了你的蹤跡,那時候就要把你當場處死。去!憑著朱庇特發誓,這一個判決是無可改移的。[7]155
在這里李爾王對諫臣的期限是六天,依照舊約所載《創世紀》的說法,宇宙肇始的第六天上帝創造了人類,人類也就進入到真理與罪罰開始博弈的循環中。李爾王斥責她的小女兒說道:“那么讓你的真相做你的嫁奩吧。”[7]155“現代政治合理化的真相是考狄利婭的嫁奩,而不僅僅是她的嫁奩:這是人類對李爾王和葛羅斯特的衰腐的普遍繼承。”[9]106(此句為本文作者自譯)舒爾曼這樣的評價也正是說明人類原罪的不可消除,從伊甸園中所帶來的一切需要人類的子孫后代去繼承與承受。
其后李爾王僅帶一百人的衛隊住在他的大女兒處,結果不久就被厭棄,李爾王馬上決定搬離移駕到他的二女兒處,他的弄人對這事做出了《圣經》寓言式的比喻,李爾王的兩個女兒都是一樣的蘋果(apple和crab),這里用了兩個不同的詞,但其本質意義相同,雖然外表上似有不同之處,這也就是說從源頭上兩個女兒已經無可救藥。最終人類的原罪把李爾王這個家族帶進了權力與欲望的爭斗的深淵,李爾王最后在原野上孤獨悲憤地死去。
最后讓我們再來簡單地看看《麥克白》這部悲劇是如何展演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的。這部戲劇的第三幕第三場中的苑囿(原文用park)中刺殺班柯的劇情發展。這里也是苑囿(park)承擔了罪惡的場所。《麥克白》這部劇巧妙地向讀者展現了命運、志向、野心、人性及迷信對一個人一生所帶 來的影響。麥克白曾經是一個英勇且有遠大志向的戰士,在凱旋后,女巫的預言和國王過分的贊譽讓他的心理與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巫師與國王的角色與伊甸園中的蛇的勸誘不無相似之處。在這種原罪逐漸顯現的過程中,麥克白從一個忠實的臣子變成了一個弒君的逆賊,他使用了不正當的手段登上了王位。他當上國王后開始了他的暴政,他先后殺害了他的好友、臣子及他們的家人,最終自己也走向了滅亡。
三、結語
莎士比亞的政治之園在上述分析的幾部劇作中表達著上帝的花園之音,一切的發生,上帝的詛咒與失樂園、走出伊甸園則涉及犯罪與受罰、寬恕與仁慈、贖罪與拯救等基本倫理道德問題,這些都在劇作中出現,唯有愛是最高的道德目標。[4]57-62“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莎士比亞的名氣是一個帝國主義險惡陰謀的產物。日益壯大的帝國要一個具有相稱水準的詩人來為它做宣傳,于是莎士比亞被選中來做這件事,他是這場政治宣傳運動的得益者。”[10]67雖然這是與本主題無關的評述,但莎士比亞的政治園林卻是真實的存在,其政治的幽微與政治的晦暗卻是對當時社會的恰當的定位與注腳,即使沒有帝國主義的選擇,文學無國界的結果也會讓莎士比亞為人類所熟知并為他的政治園林所折服。正如阿蘭·布魯姆所言,我們感到莎士比亞不僅擁有明澈的智慧,還擁有充沛的感情。如果靜心聆聽莎士比亞政治,我們也許能夠重獲生命的完滿,也許能夠重新發現通往失落的和諧的道路。[3]11正是政治之園造就了莎士比亞劇作的瑰麗與劇作引人入勝的魔力,讓人類秉持建立和諧社會關系的人文主義政治與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