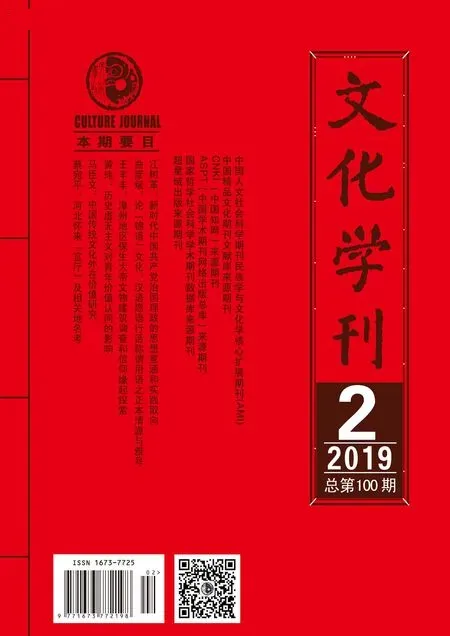漢語和德語語言中的“他者”
張 智
“他者”概念是貫穿波伏娃哲學思想和存在主義特別是薩特的《存在與虛無》(1987)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理論。“他者”是指“那些沒有或喪失了自我意識、處在他人或環境的支配下、完全處在客體地位、失去了主觀人格的被異化了的人”[1]。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女人是他者”的斷言,她用存在主義話語解釋女性的文化身份和政治地位。而語言代表著一種象征秩序。借此,以陽性為中心的語言——漢語和德語不斷地固化和內化著男性主體性和女性他者性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從女性主義視角,從存在論的高度,對漢語和德語中的兩性關系進行重新審視。
一、女性在語言中的他者表征
女性作為他者是相對男性作為此者而言的。薩特認為,每個自為的存在(being-for-itself)通過把他人的存在定義為對象和他者來把自己建構為主體和自我[2]。也就是說,此者必須在樹立起相對立的他者時才能成為自身。每個自身的自我規定他者的角色,并將其描述為內在的及被奴役的,把自我看成是超越的及自由的,從而確立自我為主體[3]。因而,對自我進行定義的過程就成了一個在根本上權力凌駕他人的過程。女性之所以淪為從屬的他者,是在男性把自身界定為自我決定的存在從而對人類社會實施父權統治的過程中被決定的。在兩性不平等的主客關系中,在這種以男性為主體而建構起來的社會體制中,女性是一種附屬的、次要的、被動的存在。他者的地位和特性就是女性的地位特性。男性就是人類的絕對標準,女性不過是從男性的偏離,這種觀點也反映在了語言系統里。
女性的他者地位決定了語言的創造和記錄中,女性是缺席者,是“被凝視者”,語言以男性為中心進行編碼和解碼,語言形式排斥女性,詞匯和語法使女性“失聲”,這些都反映及再現了男性宰制女性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具體在漢語和德語中體現如下。
(一)構詞方面
女性在德語中往往表現為一種附屬或變體,女性人稱名詞常以男性人稱名詞為根本,加詞尾-in或-frau構成,如Student(男學生)→Studentin(女學生),Kaufmann(男商人)→Kauffrau(女商人)。漢語作為孤立語,不同于屈折語,它沒有詞形變化。但在字形構造上也可以看出女性的他者地位,如:甲骨文“女”是女子交臂于前,像一個斂手跪著的人;婦,原為“婦”,指女子拿著掃帚,表示女子被限于家庭的家務中。此外,漢語中有許多含有貶義或負面色彩的字以“女”部構成,如“奴,奸,妖,娼,妓,婊,嫉,妒,婪,妄”等。
(二)性別詞非對稱現象
男性一直壟斷著那些高端的行業和領域,因此德語中長期以來就缺乏相應的陰性職業職務名稱及學銜:如Pr?sident(主席)、Minister(部長)、Ratsherr(議員)、W?hler(選民)、Professor(教授)、Doktor(博士)、Fachmann(專家)等曾經沒有相應指稱女性的陰性形式。同樣,漢語中的“將軍、省長、導師、特警”等詞蘊含有極強的男性性別傾向,在實際運用中往往用于男性指稱。一旦這些詞的所指對象為女性時,則要另外加上前綴語素“女”,從而在性別標記上形成諸如“將軍-女將軍”而非“男將軍-女將軍”的二元對立項,雄性義和雌性義在標記形式上明顯不對稱。
(三)男性詞泛指兩性
在德語中表身份、職業和職務的陽性名詞既可以指稱男人,也可把女性包括在內而泛指兩性,指稱整個人類,但陰性名詞則只能指稱女性,如“Ein Student sollte immer flei?ig sein”(學生總該努力),用男學生指代所有男女學生。漢語中的人稱代詞也有類似特點,用表示男性的“他們”通指男女兩性,而“她們”則僅僅指女性。這種指稱方式體現出人類長期以來的兩性關系,女人只是人類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男人的狀況就是所有人的狀況。
(四)熟語中的兩性地位
德語諺語和習語不斷強化著男子氣概和男性特質,如Ein Mann, ein Wort(“男子一言”比喻“一諾千金”)。而敵視和貶低女性的俗語則俯拾即是,如Klatsche(饒舌婦),das schwache Geschlecht(“弱勢性別”指代“女性”),Gans(“鵝”指代“蠢女人”)。在漢語的諺語俗語中也存在大量體現兩性關系的表達。語言對男性充滿贊譽,如“大丈夫頂天立地”“好男兒志在四方”;而女性則地位卑微,受盡嘲諷,如“頭發長,見識短”“夫唱婦隨”“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三個女人一臺戲”“母老虎”“紅顏禍水”“婦人之見”,等等。語言背后所蘊含的是對男女兩性不同評價的文化積淀。由男性設定并統治著的社會性別表征機制把女性淪為“他者”,使其處于從屬地位,并給其烙上了特有的性別文化內涵意。
二、他者性的揚棄
(一)語言的象征秩序
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交際手段,從存在論的高度,拉康指出語言還代表著一種象征關系[4]。人不僅要存在于與自然的關系之中、與他人的共在中,還不得不存在于與語言的關系之中。語言編織了我們賴以存在的世界,維持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世界的本質就是象征性的符號集合。拉康的理論以“陽性”哲學的面目出現,把父親確定為“象征秩序”的代表,在以菲勒斯為中心的德漢語言表征系統中,女人被表征為“他者”。在某種程度上,“他者”代表著凝固的公眾觀念,它不許人作為本真的、獨立的、個別的意識而存在,女性他者在被凝視的狀態下,其非本真的姿態和觀念在語言系統中被固化。兒童在成長和習得語言的過程中,為適應社會所期盼的角色,通過語言行為無意識地接受和內化了這一象征秩序。通過習得和使用代表象征秩序的語言,女人在自身觀念世界中衍生出“他者意識”,也認同了自身的他者身份。所以說,通過對話語權的占有,男性不僅鞏固了自我主體與女性他者的對立,鞏固了父權機制本身,同時堅定了他或她關于自己的性別意識,被接受了語言教化的人們通過語言行為而成為性別化的存在。以陽性為中心的德漢語言這一“象征秩序”通過內化個人的社會性別角色,而達到對社會的制約,進而使社會能穩定地自我復制,它既創造了貫通個人的文化,又創造了集體的無意識。
(二)語言的變遷
“他者”在后現代女性主義那里有其自身的優越性,她們不是把“婦女是他者”這一處境解釋為應當超越的狀況,而是積極肯定其價值。就像自為依賴自在一樣,主體也依賴于他者的存在,因為主體意識是通過確定它不是他者來規定它本身的。由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她所依附的男性,所以男性需要借助這個女性他者來承認和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同時,女性特有的他者地位,使得作為個體的婦女能夠擺脫出來,有利于她們認清現有的主體性哲學實質是一種男權壓迫和控制的形式,從而能夠批評主導的父權文化力圖強加于所有人,尤其是處于文化邊緣者的那些規范、價值和實踐。女性應當摒棄她們內在化的他性認識,從他者形象中解放出來,在作為人本真的意義上重新認識和確立自己,建構具有主體性精神的女性身份認同,而且還要使那些視女人為對象的人逐漸認識到她們是作為主體存在著的。
在以陽性為中心的“象征秩序”中,人們的語言行為時時刻刻都在能動地生產著主體與對象的關系,強化和維持著不平等的社會機制。要改變這一狀況,一方面我們要從宏觀上改變相應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進而促進女性心理的改變;另一方面,語言是表達法律、政策的形式,也是性別養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我們通過語言實踐形成有關性別、身份、主體位置等思想認識[5],因此,語言中的兩性不平等現象也亟待改變。
德國的女權主義者們對于德語中所表征出來的女性他者地位極為不滿,并進行了嚴厲抨擊,提出了相應的女性主義語言改革措施和建議。德國第一本規避德語中女性性別歧視的語言守則《男尊女卑語言應用的回避準則》于1980年問世。此后,語言改革的熱潮在德國各政府部門、官方機構、學校及媒體蔓延開來,各機構開始制定自己的語言準則來避免語言中的性別歧視,在語言形式上出現了多種兩性通指形式來取代男性詞泛指兩性,其中最為廣泛使用的是兩性并提形式,如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男女學生),此外還有大寫-I形式如ProfessorIn(男女教授),斜線形式如Arbeiter/in(男女工人),括號形式如Sportler(in)(男女運動員)以及中性形式如Lehrkraft(男女師資)等。女性職業名稱在各種官方用語、公共文本及媒體用語中得到了更為顯性的使用。針對女性的一些貶義稱謂也在語用中遭到拒絕,女性在語言中的主體性表征得到明顯提高。
漢語規約性較強,字形相對比較固定,改革起來更為艱難,但也可以看到一些語言的變化。五四運動之前,漢語中指稱女性的代詞為“他”,后來劉半農創造了“她”字才有了女性單數第三人稱代詞;20世紀50年代,有學者寄信給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提議廢除三個帶有偏旁“女”的漢字,并改革十六個帶有偏旁“女”的漢字,考慮到這種人為的改動會給語言交際帶來影響,這一建議并未得到采納,但使得人們開始關注漢語中的兩性和諧問題。漢語不同于德語這種具有顯性語法標記的性別語言,語言變化中雖然不至于通篇出現諸如“男女學生”或“男女教授”之類的兩性并提表達,但是通指男女兩性的人稱代詞從形式上大大提高了女性的主體性,在當前的語言實踐中,“她們/他們”“她/他”以及“Ta”等形式得到越來越多語言使用者的認可。
三、結語
語言對現存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形成和鞏固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語言中的性別建構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性別行為不斷地自我生成和再生成。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我們繼承了語言形式背后所隱藏的對待世界的觀點和態度,并將其進一步內化為自身的思維模式。如果文化的語言和想象繼續宣揚貶低女性價值的觀念,婦女的他者地位就不可能真正改變。要提高語言中的性別意識,就應當重新審視舊有語言模式,改變現存的話語秩序。當人們有了強烈的自我主體認同,那么被排斥于舊有話語秩序主體位置之外的人們就擁有了進入該主體位置的主動性和能力,揚棄他者,最終使人們在運用語言規范方面達成兩性平等的新共識。德語及漢語中現存的陽性中心的象征秩序是可以改變的,改變在于系統地解構和重新建構話語的象征和統治秩序,以支持和強化已經改變了的文化觀念,真正改變女性的他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