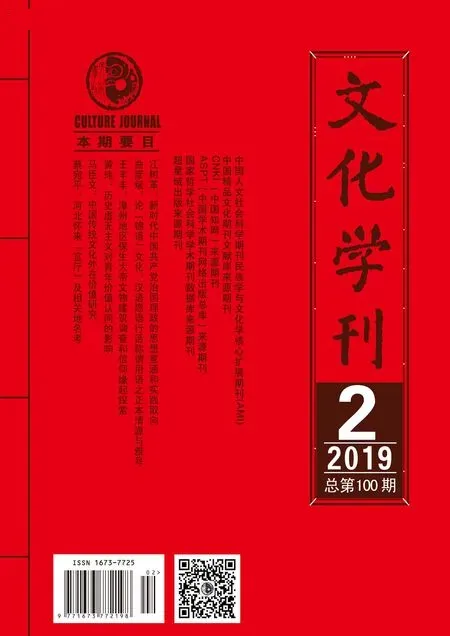中國、西班牙政治話語中“牛”文化的隱喻特征
龔韻潔
動物概念與人類的認知發展密切相關,在人類幾千年的生活和生產中,牛都是與人類關系最為密切的動物之一。因此,無論是在漢語還是在西班牙語中都出現了大量與牛文化相關的隱喻表達。本文的特點與創新之處在于:第一,在政治話語這一特定文體下展開討論,著力于“牛”這一具體動物形象的隱喻研究;第二,從跨文化和認知的角度出發,挖掘涉“牛”隱喻背后中國和西班牙社會所特有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心理,指導政治隱喻翻譯,使其在準確表達源語言基本含義的同時,更加符合譯入語國家讀者的語言和文化習慣。
一、隱喻概述
不同于傳統的隱喻理論將隱喻視作一種修辭手段而過分強調其在語篇中的美學功能,如今人們對概念隱喻的認識,不再局限于語言之外的一種裝飾品。換言之,其不僅是一種語言手段或修辭方式,而是作為一種認知機制,基于兩個事物的意義相似性,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投射。概念隱喻對政治話語的構建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基于概念隱喻本身的認知功能,借助某一領域具體的、有形的、熟悉的、易于理解的概念或經驗,去說明或理解政治領域內抽象的、無形的、復雜的事物;其次,概念隱喻對政治話語的貢獻還體現在從產生隱喻表達的主觀關聯中所得出的觀點和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語言表達中任何一種隱喻機制的出現,都不應當是個人的、偶然的認知方式的產物,而是反映在特定的社會實踐、文化傳統、價值體系、思維習慣、審美偏好等共同作用下,來自同一語言群體的人的相對固定的、集體的思維模式的運作過程。因此,在不同語言中存在的看似相同或相近的隱喻機制,實則承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而將其運用于政治話語中,從產生隱喻表達的主觀關聯中所得出的觀點和評價自然也就大相徑庭。
二、“牛”文化在漢語中的象征和隱喻
我國是傳統的農耕社會,農耕經濟貫穿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始終,直至近代也仍有保留。早在商代[1]就出現了牛耕技術,《戰國策》記載,秦國“以牛田”,即用牛耕地;隨著牛耕技術日益普遍,又發明了“二牛抬杠”“一犁一牛”等。可見,早在幾千年前,牛就開始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所馴服,并在農業生產中拉犁、耕地、拓荒。受農耕文明的影響,“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賦予了人性化的特定品性,寄托了中華民族的特殊情感。《說文解字》中寫道:“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理’就是指牛的內在屬性‘從順、遜順、馴順’的詮釋。‘事、理’也就是人們在對牛的長期馴養中獲得的對牛‘任勞任怨’品質的認識,是人們給牛賦予的文化義上的認識”[2],而這種十分明顯的象征含義又通過大量文學作品(如魯迅《自嘲》、臧克家《老黃牛》等)得以廣泛傳播。因此,在漢文化語境下,常用“孺子牛”“老黃牛”等來形容默默奉獻、吃苦耐勞、勤勉工作的人,這是極具中華民族農耕文明特色的涉“牛”隱喻表達。
例(1):“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我們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使用人才各盡其能。
例(1)中習近平引用了清代詩人顧嗣協《雜詩》中的名句,其釋義為:駿馬可以跨越險境,但要論勤奮肯干、踏實耕地,則比不上牛。在中國古代社會,馬的軍事地位尤為突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就將馬的行為和性格特征等實體屬性自然而然地映射出“無畏沖鋒”“驍勇善戰”等較為抽象的隱喻義。無獨有偶,習近平在任正定縣委書記期間,也曾就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提出要求:“既有老黃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馬的氣勢,既是一個有膽有識的戰略家,又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此處的“牛”喻指務實重干,但卻缺乏遠大的目標。
此外,漢語中還產生了許多與牛耕實踐相關的、具有隱喻意義的熟語。
例(2):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
漢語語言意識中的涉“牛”隱喻,其源域實體是農耕文化中已經被馴服的耕牛,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馴牛的實踐中得知牛的鼻中隔薄而布滿神經,只要牽住并刺激牛的鼻中隔就可以使牛產生痛感從而使其更加馴服,由此發明了牛穿鼻技術,即用一個金屬環穿過牛的鼻中隔并套上繩子就可以牽著犟牛走。因此,在漢語中有關于“牛鼻子”的隱喻表達,喻指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影響全局的關鍵。
以上兩個例子,習近平都借用“牛”這個隱喻意向,通過語義上更具體、更貼近人民生活的熟語來解釋和傳達了較為復雜和抽象的政治概念,同時在潛移默化中向受眾傳遞了其政治觀點和價值評價。
三、“牛”文化在西班牙語中的象征和隱喻
西班牙位于歐洲伊比利亞半島,北鄰比斯開灣,東面和東南面瀕臨地中海,地理位置決定其在抗爭生存中形成了典型的西方海洋文化,以商業貿易、海盜掠奪、殖民拓土為特征,其民族精神也更具冒險性和侵略性。此外,相對于傳統中國社會以耕牛作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動力,西班牙的農耕則更多依靠騾子。因此,在西語中,形容踏實誠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常說“trabajar como mula”(像騾子一樣工作)。
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牛主要在畜牧農耕的生產實踐中發揮作用,在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窟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巖壁畫上就已經有了關于人類與牛搏斗的描繪,不僅如此,公牛、斗牛士的形象也在西班牙畫家畢加索、戈雅等的筆下反復出現,正如加泰羅尼亞詩人杰米·薩巴特所說:“他的公牛是野性的公牛,不是馴服的公牛。是生長在野外、擁有無窮力量且有著強烈沖動的動物。”可見,斗牛運動作為一個極具特點的文化象征符號,已經內化到西班牙的語言文化和思維習慣中。因此,西班牙人語言意識中的“牛”,不再是被馴服的耕牛,而是生性暴烈、勇猛、具有侵略性且有尊嚴的公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受西方海洋文化影響下的西班牙民族精神。在此文化語境下,西班牙語中常用“toro”(公牛)或“tor牛ero”(斗士)等來形容富有勇氣、敢于冒險的人。例如,más valiente que un toro(比公牛還勇敢),más bravo que el toro de lidia(比斗牛還勇猛),bravo como un toro(跟公牛一樣勇猛),más valiente que un torero(比斗牛士還勇敢),等等[3]。以外,與斗牛相關的一些術語也獲得了更為豐富的隱喻意義,并在西班牙政治話語中得以廣泛使用。例如,ruedo/ plaza(開展斗牛的圓形場地/賽場、爭斗之地,有時也引申指西班牙),salir/entrar al toro(靠近公牛/直面問題,積極行動),en corto y por derecho(斗牛士站在離公牛很近的位置引逗公牛向自己發起沖擊/直擊問題的要害不繞圈子),dar/echar un capotazo(展開披風[引逗公牛]/使擺脫困境),burladero(供斗牛士避險的圍欄/避風港)等。
例(3):Y no acudo al pasado reciente, se?orías, para buscar un burladero en el que refugiarme ante una situación tan dramática……Por lo tanto, nada de burladero.
例(3)意為拉霍伊竭力證明其領導的西班牙政府已經堅定地做好準備迎接一切困難,而不是尋找借口和逃避責任。句子中正是使用了“burladero”的政治隱喻意象。
四、中國政治話語中涉“牛”隱喻的西譯策略
中國和西班牙在生存環境、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漢、西語言中關于動物“牛”的隱喻機制存在很大區別。鑒于中、西兩國在語言和文化間的差異,如何通過靈活豐富的翻譯手段和策略,使我國政治話語的西班牙語譯文能夠更好地服務于跨文化交際與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翻譯的完整意義不應該僅僅只是一個語言文字的轉換行為或活動(即“換言易語”),而還應該包含幫助和促進操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際(即“使理解”)。”[4]以中國政治話語中的涉“牛”隱喻為例,我們就應當充分考慮源語國和譯語國在“牛”這個文化意向上的錯位,通過恰當的翻譯使受眾更好地接收文本信息,以實現更好的政治傳播效果。
本文例(1)中“犁田不如牛”的“牛”,在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語版《治國理政》中被譯為“buey”。在西班牙語中使用較廣泛的表示動物“牛”的詞還有“toro”(公牛),“vaca”(母牛、牛肉),“becerro”(牛犢),“cabestro”(公牛群的帶頭牛)。根據《西班牙皇家語言科學院西班牙語詞典》,“buey”是指被閹割后的公牛,或面對引逗過分溫順的斗牛。但查閱大量西班牙語資料發現,盡管西班牙的傳統農耕大多依靠騾子,但也有諸如“el arado tirado por bueyes”(用牛拉的犁)等有關牛耕活動的描寫。由此可見,在漢語西班牙語譯中使用“buey”來指被馴服的耕牛是準確的。此外,上文中提到,在西班牙語中常用“trabajar como mula”來喻指工作上任勞任怨的人,但在西班牙文化中,“mula”還是“蠢笨”的象征。因此,基于漢語和西班牙語雙語文化內涵傳遞與闡釋的需要,此處保留源語中的隱喻意象“牛”,并根據目的語的表達習慣選擇對等翻譯“buey”,使譯文能夠最大程度地貼切原文。
又如例(2)中的熟語“牛鼻子”,首先,概念隱喻的認知功能是基于人們具有某一領域內具體的、有形的、易于理解的概念或經驗,但在西班牙人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卻使用騾子進行農耕,查閱大量西語資料也未發現有關通過給牛鼻穿環來達到馴服牛目的的記載;因此,我們認為,在譯語國文化中并不存在“牛鼻子”這個隱喻基礎。其次,西班牙語言意識中的“牛”是野性的公牛,不受馴服且極具尊嚴,西班牙文化中所崇尚的是即使傷痕累累仍然越挫越勇的公牛,若用金屬環穿過牛鼻就試圖讓其乖乖地被人牽著走,無疑是對西班牙斗牛文化最大的蔑視。正如謝天振[5]指出:“在一種語言中帶有褒義、正面意義的事物,在另一種語言中成了貶義、反面意義的事物,或者,雖然意義不是截然相反,但至少也是大相徑庭的。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意象的錯位。”因此,不同于例(1),此處若再盲目保留源語中的隱喻意象,不但不能幫助譯語國受眾通過隱喻的方式來加深理解,反而還會造成文化上的誤解和誤釋。根據上海外國語大學十九大報告多語種平行語料庫,將源語中的“牛鼻子”作了相應的轉換,譯為“asidero”(把,柄,抓手),使西班牙譯本更加符合受眾的思維和認知模式,進而取得更好的政治傳播效果。
五、結語
本文從跨語言、跨文化的角度對中國和西班牙政治話語中的涉“牛”隱喻進行了對比分析,一方面,幫助西班牙語學習者和翻譯實踐者更好地掌握兩種語言中涉“牛”隱喻的工作機制,加深對相關語言和文化現象的理解;另一方面,借助探討譯語國文化語境中影響和制約涉“牛”隱喻翻譯及翻譯結果的各種因素,啟發如何處理好文化差異下的政治隱喻翻譯,尋求更恰當的翻譯策略,盡量避免由跨文化翻譯帶來的誤解與誤釋,提升我國政治話語在西班牙語國家的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