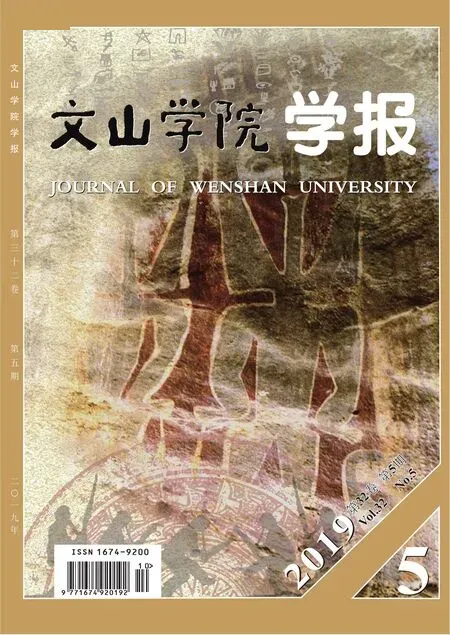中國史學史分期的草創與集大成
——內藤湖南與瞿林東中國史學史分期的比較研究
馬 科
(云南師范大學 歷史與行政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國史學史的分期是史學史學科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分期的依據不同,其結論也往往不同。內藤湖南、瞿林東在這個問題上就展現出了很大的差異。
一、史學史分期的“四段論”與“九段說”
內藤湖南從未就中國史學史的分期作專文闡述,但其分期的方式與結論可從其著作《中國史學史》中看出該書是“后人”根據內藤湖南于1914至1915年、1919年至1921年、1925年三次在日本講授的“中國史學史”這門課修訂成的。修訂始于1923年左右,但因各方面的原因直到194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綜合來看,該書可以說是中國史學史草創時期的著作了。而其史學史分期的結論與方法顯得比較生硬和粗糙,可看作是中國史學史研究草創時期的探索。
內藤湖南以文化史觀為指導,并結合他的“宋代近世說”進而將中國的史學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形成一套較為系統的中國史學史分期方式。
第一個時期:“史學前史的時代”。從有“記錄”開始到兩漢《史記》出現之前。內藤湖南認為“在上古時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稱之為史學的學問的,但是,存在著一個應該對應稱為史學前史的時代。”[1]1所以他將這個階段作為記錄的起源進行探尋。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史學史》前三(四)章的內容。
第二個時期:“真正的中國史學史階段”。“從兩漢到六朝”。對應的是《中國史學史》第五、六章的內容。在內藤湖南看來《史記》的出現是真正的史書出現的標志[1]76-77。真正的史書出現了,才有史學。所以他將“從兩漢到六朝”看作是“真正的中國史學史階段”。谷川道雄在給該書作序時對內藤湖南在這個階段上的劃分作了概括和補充。他說:“像《史記》那樣內容、體例均可稱之為真正史書的著作出現了,《漢書》繼續了這種史書撰述的潮流。盡管兩史之間有著通史與斷代史的區別,但畢竟由此進入了真正的中國史學史階段。特別是《史記》《漢書》構筑了正史編纂傳統以后,以此為中心,史書編撰開始有了慣例的性質。”[1]3這個時期“在圖書分類上,獨立形成了‘史部’的領域”,同時又醞釀著新的史學傾向,即“史書的發展也出現了喪失《史》《漢》那種歷史家精神之形式主義的墮落傾向。而且其中具體的現象之一就是,在唐代出現的正史編纂從一家之著述變成分纂的傾向”[1]3。
第三個時期:中國史學史的“第二階段”,從六朝末到唐代。在內藤湖南看來,與前一個階段的史學相比該時期的史學獨具特色,可以作為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階段。他認為該時期史學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正史。“正史編纂從一家之著述變成分纂”的情況已經很顯著了。不再像《史記》《漢書》那樣具有家學的傳承了。二是類書。“這一時期出現了將史實編纂為類書體的形式。從六朝到唐中葉,類書與史書以及其他諸子類的區別逐漸明顯起來。”“至唐代,類書出現了堪比前代的大型著作,可以說這是類書在編纂當代事實方面的應用,現存的《貞觀政要》就是其中之一。”[1]135三是書寫的語言。“六朝末至唐初之間又有了古文的復興。”四是史評自成一體系。他認為:“直至六朝,幾乎還沒有出現史評這一類書籍,本來在目錄上是沒有這一部類的。但是到了唐代由于《史通》問世,這類書籍多了起來。之后又相繼出了同樣的書籍,以致形成了一個專門的部類。”[1]143五是史注活躍。此時期“出現了對以往那些重要史書的完整的注。而其中最有名者是關于《史記》《漢書》《后漢書》的注”。內藤湖南認為:“作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種單純依據前人之說,而是能夠發表各種對所注釋書籍本身的意見了。”[1]144“與宋朝相比,該時期史注的地位及成就要高出許多。”[1]146六是史學獨立性衰弱。此時期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修史機構——史館,并由專人即宰相監修。而“由于直至唐代都是貴族政治,所以史官也是即便僅限于一代為官,忠于職守之風仍然強盛”[1]148-149。但是該時期由于皇權不斷強化,也導致了史學出現衰落,獨立性逐漸喪失的傾向。他說:“但是畢竟史學卻在逐漸衰敗,作為世襲、家學的史學已經不復存在,記史轉為由宰相監督,作史不再是史官自由了。”[1]149史學越來越受到權力的影響。
谷川道雄在序言中講到:“從六朝時代開始的史評,至唐代劉知幾《史通》終于形成了史評的專著。史注、史評都是從當時史學中那種單純寫史的著作,進而發展為對既成史書加以解釋、評論的產物。這顯示出史學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可謂是一語中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史學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是從“真正的中國史學史階段”即“從兩漢到六朝”這個階段開始算起的,而并非是從“史學前史的時代”算起。因為在內藤氏看來第一階段即“史學前史的時代”只是史學準備階段,還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史學史階段。因此他所說的“進入了第二階段”實際上是內藤湖南整個中國史學史分期體系中的第三個階段。
第四個時期:具有近代性質的史學史發展時期(或稱為:史學新潮流時期),時間為:宋代至清朝時期。其劃分的依據是該時期“歷史編撰法”“帝王學”“經學”等的變化巨大,“正統論”發展興盛。具體情況將在后文作論述。
筆者以為僅將中國史學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太過于籠統,不能深刻反映中國史學史的特點和發展的實際情況。
瞿林東先生關于中國史學史分期的理念在他的《中國史學史綱》中得到了深刻的踐行和闡述,并為學界廣泛接受。在此之前,史學史分期的結論和方法已是層出不窮,但總體上看來分歧很大,問題也不少。[2]
因此,瞿林東先生在深刻總結“前人”的思考和實踐之后,開創性地提出:“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會發展分期觀點與史學發展階段相結合的分期方法及其結論,也不刻意探求從史學自身發展的過程與特點來劃分它的發展階段性的分期方法及其結論,而是采取長期以來人們比較習慣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時段劃分。”[3]3所以,瞿林東先生在進行史學分期時很自然地就根據“人們比較習慣”的方式將中國史學史劃分為九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先秦時期的史學,特點是“史學的興起”;第二階段是“秦漢時期史學”,特點是“正史的創立”;第三階段是“魏晉南北朝史學”,特點是“史學的多途發展”;第四階段是“隋唐五代史學”,特點為“史學在發展中的轉折與創新”;第五階段是“遼宋金史學”,特點為“歷史意識與史學意識的深化”;第六階段是“元代史學”,特點為“多民族史學的進一步發展”;第七階段是“明代史學”,特點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發展”;第八階段是“清代前期史學”,特點是“史學的總結與嬗變”;第九階段為“清代后期史學”,“史學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分化”是其特點。
該分期方法貫穿著深刻的“通”的意識。一方面是體現在時間的銜接上,從先秦開始,按朝代順序一直論述到近代。另一方面體現在對各階段史學特點的準確把握上。各階段史學特點又緊密相扣,將各具特色的各階段的史學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中國史學史的整體了。
二、兩漢時期史學開端論與先秦時期史學興起論
關于中國史學史開端的問題,內藤湖南與瞿林東先生的分歧也是比較大的。在內藤湖南看來從有“記錄”開始到兩漢《史記》出現之前,只能看作是“史學前史的時代”,而“真正的中國史學史階段”是從兩漢時開始算起的。依據之一就是作為“史書的出現”之開始和代表的《史記》問世了。然而,這樣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史記》確實是中國史學上的一座高峰,中國史學產生于何時雖也尚存爭議,但絕不是推遲到《史記》出現的時候。按內藤湖南的算法,顯然是將中國史學出現的時間推后了。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與內藤湖南不同,瞿林東先生認為:“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和人類創造出來文字以后,就有了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有了史學的發展、積累和人們對這種發展、積累的認識,就有了史學史。”[3]1所以他認為“先秦時期是中國史學從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階段,我們把它稱作史學的興起階段。”[3]115《史記》和《漢書》則是中國正史創立的標志。“史學的源頭可以追尋到古老的傳說。”“《尚書》中的殷商、西周人記載和《逸周書》中的西周人的記載,是中國史學上最早的歷史典冊。”[3]125事實上,這些觀點才符合實際并廣為大家所接受。
三、宋代史學近代化與清末史學近代化
在史學史分期中,兩人都提到了史學的近代化或者稱之為具有近代性質的史學。由此也可以將二人的史學史分期看作是可以分為“傳統史學史”和具有近代性質的史學史兩部分的,這是相同點。但這樣的劃分是比較籠統的,終究還是要再化成小階段。
內藤氏認為自宋代開始中國進入“近世”,中國的史學也具有了近代性質。因此,稱自宋至清時期的史學為“具有近代性質的史學史發展時期”。他認為該時期史學特色主要表現在:一是歷史編撰法的變化。他認為自五代到宋初,是歷史編纂法上的變化期。該變化明顯地反映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上。[3]150他說:“《舊唐書》畢竟是依據了唐初的那種歷史編纂法理論而成書的,而不是唐中葉興起之古文與史書相關聯的新型理論的代表作。”而《新唐書》成書于宋代,“能夠應用韓愈以來古文復興的意見,并最大限度發揮了其主張,有著與以往史書完全不同的創新”[3]151。“《舊唐書》由于照用了駢體文全盛時期的史料,所以多使用駢文;這在《新唐書》幾乎全部改寫為古文,詔、令、表、奏等也不僅限于刪改,而是全部用古文重寫。”[3]152所以內藤認為:“《新唐書》創造出了史書體例上的新形式,這是其最顯著的特點,可以說具有正史編纂上劃時代的意義。”[3]154
二是“帝王學的變化”。這個時期產生了許多為帝王提供參考的書籍,他認為皇權逐漸強化,皇帝逐漸成為新型的獨裁君,“因而出現君主應當具備特別修養的需要”[3]159。《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鑒》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內藤湖南稱贊《冊府元龜》“是歷史事實的集大成之作,是以類書體例列項,將史實予以類聚的。總之,將史書作為帝王必要的參與進行編纂,使得《漢書》以來流行之類聚方法在此得以集其大成了”[1]158。《資治通鑒》“不僅在體例上復興了編年體史,在帝王學的編修上他還具有與《新唐書》《新五代史》同樣的意義,亦即作為傳承《春秋》之意,具有一家之見著述這一點上,有著重大意義”[1]160。除此之外,“《太平御覽》是真正的類書,是六朝以來至唐代類書的集大成者,《太平廣記》是野史、稗史的集大成者,《文苑英華》是詩文的集大成者。當然,這些都是為提供帝王參考而作的”[1]158。
三是“經學的變化”。南宋和北宋時期,“有關經學的觀點也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其中有關《書經》,一是出現了關于古文今文的疑問,一是不論對古文今文都提出了各種疑問。”[1]180
四是“金石學的發達”。“在宋代,有關史料研究中最為發達者要屬金石之學。”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王厚之的《王復齋鐘鼎款識》等都是金石學發展的代表。
以上是內藤湖南關于史學近代化的劃分結論與依據。
瞿林東的觀點與之不同。在他看來史學近代化與社會近代化具有一致性。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史學亦是如此。只是在此之前已開始醞釀了。他說:“自明末清朝前期,中國史學已經出現了嬗變的端倪。”而具有近代性質的史學則萌生于“清代后期”,他說:“中國近代史學的萌芽,是在中國歷史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出現的。這個大變動開始的標志,就是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3]742
瞿林東進而指出這一時期的史學特色,“第一個特點,是傳統的經世致用的思想注入了救亡圖強的民族危機意識。第二個特色,是傳統的歷史變化注入了近代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想。第三個特點,是傳統史學的樸素的歷史進化觀注入了進化論思想。”[3]743-744
這樣的劃分,一方面體現了史學近代化與社會近代化相一致的觀點。近代中國面臨著民族生存危機,所以作為意識形態的史學孕育著“救亡圖強的民族危機意識、近代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想和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這符合社會和史學發展的實際,做到了實事求是。另一方面體現了瞿林東先生深刻的社會責任感。如前文所講,史學分期的依據很多,但瞿林東先生卻選擇最能反映時代特點的部分作為劃分依據,這是非常富有社會責任感的。
四、文化史觀的指導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
內藤湖南的學術體系幾乎是在文化史觀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在文化史觀的指導下,內藤湖南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個時期”。“在此之前,雖有中國史學家使用上述名詞進行分期,但只是偏重從時間觀念上使用它,而內藤則按每個時代的文化創造力及時代特點來使用它,賦予時代的內容,以此建立起中國史的新體系,成為內藤對于中國史學領域的新貢獻。”[4]4
在他看來“歷史的發展本身即是各時代文化的發展”。而他所謂的文化,是指廣義上的文化,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思想等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成果。各時代依據這些文化發展的不同內容及形勢,顯示出其階段性,從而成為劃分時代的依據。[4]3也正是對文化史觀的堅持和對“宋代近世說”的運用,他將“中國史學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其著作《中國史學史》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
瞿林東先生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指導開展中國史學史研究和編撰。在史學史分期問題上,亦是如此。
在他看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整體由特色鮮明的各個階段共同構成,而各個階段的史學又是相互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史學史分期上既要呈現出一個嚴密的整體,又要展示出各個階段的特點,還要展示出各個階段之間的關系。所以,最終我們看到了一個嚴密的、有機的“九個階段”的史學史分期方式與結論。
彭忠德曾就瞿林東以辯證發展觀點看待史學史分期的作法進行過闡述。他說:“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解析中國史學。從宏觀方面看,作者(瞿林東)較多地從辯證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如運用辯證發展的觀點劃分中國史學史的分期,將先秦至近代的史學劃分為九個時段。”還稱贊道:《中國史學史綱》豐富的歷史內容得到深刻的理論闡述,又體現了作者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5]
五、結語
總的看來,兩人的分期方式都自成體系,各具特點。內藤湖南的分期方式,問題多,顯得粗糙,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確實符合中國史學史的實際,但以文化史觀為指導,并結合“宋代近世說”進行中國史學史分期,是一種很獨特的視角,也是一次很好的嘗試。這一點應該予以肯定。而瞿林東先生“采取長期以來人們比較習慣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時段劃分”的作法則很好地避免了以往史學史分期存在的問題,做到了能深刻反映中國史學和歷史發展的實際。這是史學史分期對歷史的自然回歸,甚至可以稱之為中國史學史分期的集大成。